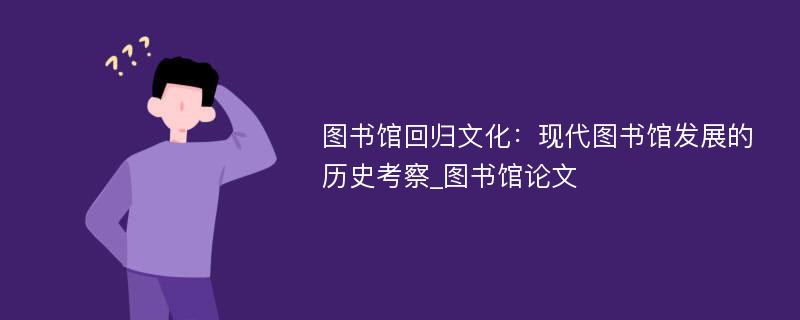
回归文化的图书馆——图书馆现代发展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二战结束后,经济、社会、科技飞速发展,图书馆也进入了现代发展时期。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知识的图书馆”、“技术的图书馆”和现在正在进入的“文化的图书馆”。
1 历史的回顾
从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图书馆在近代发展历史中完成了类型的分化、管理的定型、功能的定位等三大发展任务。类型的分化在20世纪初宣告完成,古代宫廷藏书、寺院藏书、书院藏书、私人藏书的基本模式逐渐瓦解,从中发展出一系列存在至今的各类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科研图书馆、专门图书馆等类型先后出现,并由此奠定了现代图书馆的格局。以英国编目大宪章、杜威十进分类法、英国公共图书馆法等为标志,图书馆完成了微观与宏观管理体系的确立,图书馆的基本业务流程和方法得以定型。以类型分化和管理定型为核心,图书馆明确了功能定位,成为独立的一项社会分工,图书馆工作成为一个社会职业。
近代图书馆的发展历史,是伴随着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的确立而展开的。随着冲破宗教对知识的禁锢,知识开始进入世俗社会生活;而资本主义的确立,则要求对劳动者进行一定的知识、技能的培训,教育开始逐步普及。图书馆在这个时期逐步摆脱宗教、专制权力的束缚,越来越世俗化、平民化,19世纪中后期公共图书馆的普及就是近代化的最典型的进程,而图书馆的功能在这个时期也逐渐由单纯的典籍保存机构演化出知识传播、教育等崭新的功能。进入现代图书馆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发展历史中所完成的图书馆最重要的变革至今依然沿袭着,在现代发展历史中,我们并没有对图书馆的类型、管理定型等做出过革命性的变革。但是,我们在功能发挥、技术手段上的进步却是革命性的。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业界力主要把知识激活,要把知识传递起来,提出了要把图书馆由“知识宝库”变为“知识喷泉”的口号,这些都是注重图书馆功能的发挥,表现出强烈的功利色彩,一切以读者的需求为转移,只要能够把读者所需要的某一知识单元直截了当地提供给读者,服务就算达到了目的。这就是图书馆在现代发展中的第一个阶段——“知识的图书馆”。这个阶段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知识传递看做是图书馆最重要的职能,即图书馆情报职能。这个变化与情报机构的飞速发展密不可分。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对科技知识需求的高涨,在图书馆这个社会实体外,又发展出一个新的、以传递知识为生存目的的社会实体——科技情报机构。情报机构在这个“科技革命”的时期显得如鱼得水,在这个领域中发展起来的先进的检索技术和文献计量方法,对图书馆学以及图书馆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另一方面,这些实用有效、实证色彩浓郁的技术、方法,又对图书馆学以及图书馆工作带来了有益的补充。“图书馆情报化”、“图书情报一体化”既是这个时期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图书馆发展的主流。
随着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图书馆开始使用信息技术来加工、处理、存储、传递信息,这其中有四个重要标志:一是1954年美国海军兵器中心图书馆第一次使用计算机技术;二是1967年美国国会图书馆MARC研制成功;三是以洛克希德公司的DIALOG系统和OCLC的成功运行为标志,图书馆进入远程利用时代;四是199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美国记忆工程”,图书馆发展进入数字化时代。信息技术在文献信息处理、存储、传递中显示出来的巨大作用,使得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的运用日益广泛而深入,这些都标志着图书馆进入了“技术的图书馆”阶段。这个时期,图书馆显示出强烈的“惟技术”的“工具化”倾向。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大量非图书馆机构以商业化运作的模式,利用人力、财力的优势和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在网络上推出了数字化全文图书、期刊、报纸、研究报告等商业化数字资源,成为网络上的“数字图书馆”。这些数字资源提供有偿服务,用户只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就可以自由使用海量的信息。图书馆的到馆读者越来越少,新一轮的“图书馆消亡论”又开始抬头。而这次的“图书馆消亡论”不仅仅局限于业界范围,似乎是社会的广泛共识。当然,受到互联网冲击的还有传统媒体、娱乐业、通讯乃至传统商业购物等多个行业。这些行业用以对付互联网冲击的办法是什么?尽管各有各的招数,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强调本行业中网络所无法替代的独特性。而任何行业的“独特性”,都要追根溯源,追溯到自己行业最初始、最传统的方面,重新发掘、认识这个行业的本真意义。因此,在互联网的挤压之下,许多行业都朝着“文化的”方向发展,强调网络所无可替代的人的因素,这就是朝着文化的回归,形成了回归文化的强大洪流,图书馆也不例外。
2 功利主义和“惟技术”的“工具化”倾向的批判
进入上个世纪50年代后,科技的飞速发展推动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知识爆炸,信息、知识越来越为社会所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图书馆作为“知识宝库”,如何最大限度地挖掘知识的价值、发挥知识的作用,进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成为当务之急。也就是在这个情形下,图书馆的知识传递作用被突出出来。针对读者的特定需要为读者提供特定的信息成为图书馆最为重要的社会职能。情报机构在这个历史时期显得如鱼得水,尤其是以检索系统的建立为代表,情报机构似乎成为科技时代的宠儿。在情报机构的夹击下,图书馆显得包袱沉重,步履维艰。因此,改革步伐加快了,图书馆抛弃了自己的传统,以情报职能的发挥为主攻方向,向情报机构靠拢。这样一种简单转变显示出强烈的急功近利的色彩。事实上,图书馆的社会职能是多样的。保存社会文化的职能、教育职能、文化娱乐职能、知识信息传播职能这四大职能,是图书馆与生俱来的,是社会对图书馆的需求,也是图书馆在社会上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依据。图书馆一旦只强调、只发展其中一个职能,那么,图书馆存在和发展的广泛社会基础就被人为单一化、简单化,图书馆的生存危机也就由此而生。这在我们民间就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本以为自己在努力适应科技时代的发展,其实,自己挖了自己的墙角。
自从信息技术被应用到图书馆领域后,在第一阶段发展出来的功利主义的影响下,图书馆利用一切可能使用的现代技术手段来强化这样一种“点对点”的服务。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使我们图书馆界陷入极端的技术崇拜之中。但是,可悲的是,读者并不买账。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在这个知识、信息成为重要资源、成为竞争的关键因素的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读者却越来越远离号称“知识信息集散地”的图书馆。许多地方、许多大学,都不惜工本建设了大型、超大型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有着美观的建筑、有海量的物理和数字信息资源、有最先进的技术设备、有宽敞明亮的环境,但是,读者寥寥,门可罗雀,无奈地成为某种奢华的摆设。我们常常把这归罪于现代人太功利、太浮躁,已经没有读书的热情甚至习惯;也有人把这归罪于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等等。我们就是没有自我反省,当图书馆变得越来越功利、越来越工具化,越来越缺少“人”的影子,作为“人”而言,不是特别的需要,谁愿意去一个没有“人味”的场所?我们的图书馆管理工作者,在对待人的问题上也是缺乏人文精神。现代图书馆的人才需求,恐怕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计算机人才了,甚至连图书馆专业的人才也要退居其次,更遑论其他所谓“相关专业”人才?大量图书馆的专业技术人员都隐身到了后台,在“读者免进”的工作间里操纵着键盘鼠标;直接面向读者的,往往是图书馆聘来的一般工作人员。他们的普遍特点是业务水平低、整体素质低、工资水平低,只管书架整理、桌椅摆放和卫生维护,根本与“知识”不沾边,几乎不与读者发生联系。读者走进图书馆,只见书,不见人。以这样缺乏人文气氛的环境想牢牢吸引住读者,何其难也。
把图书馆看成是单纯的情报、知识、信息的传递者,貌似把读者的需求满足放在第一位,其实,这是一种对读者的主观臆断。面对科技、经济的飞速发展,图书馆界一相情愿地认为,全民的需求都集中在科技与经济方面,对图书馆的需求都是针对科技研究、经济发展的某些特定问题的解决,这是对社会需求的严重误判,恰恰忽视了读者层次的多样性与需求的多元化。从另一个角度看,图书馆界一直存在着对生存的不自信,或者是一种唯恐被社会边缘化的担忧,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冲锋陷阵,发挥出巨大的作用,让社会高度重视自己的存在。这是导致图书馆在现代发展阶段功能被单一化、功利化的深层原因。
也就在图书馆紧随新技术发展,认为信息技术为图书馆的加工、处理、传递提供了锐利武器的同时,信息技术也在更深层次上对图书馆带来了挑战。1978年,美国图书情报学家兰开斯特就提出了“没有图书馆的图书馆员”的概念,提出了“图书馆消亡”的观点。上个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光盘技术,一项改变人类知识存储方式的技术出现后,“图书馆消亡论”就开始甚嚣尘上。“无纸化社会”的到来,让人们开始怀疑以纸质文献为主体的图书馆的存在意义。整个80年代,国内、国外都在讨论这个话题。有趣的是,化解这场讨论的,恰恰是图书馆出现与存在的最原始、最本真的理由,那就是图书馆是一个社会文化机构。我们回顾一下当年的讨论,反对“消亡论”的学者无不强调人们的阅读习惯、图书馆提供给读者的读书环境、氛围等等,而这就是图书馆的文化意义。这场讨论现在看来已经平息了,图书馆依然存在着。事实已经说明图书馆不是某种或某几种技术的进步就轻易被替代的,图书馆的生命力还是非常坚强而旺盛的。但是,由这场讨论后形成的局面却令人意想不到:我们以“文化的图书馆”击退了“技术至上”者们所提出的图书馆消亡的论点,但是,实际的结果却是引发了图书馆对信息技术更进一步、更深层次的敬畏。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让一个存在了千年的社会实体发生生存危机,这深深刺激了图书馆的从业人员,从而也更坚定了紧跟信息技术发展步伐、不断更新图书馆的技术手段的决心。关于图书馆消亡与否的讨论,不仅没有唤醒人们对图书馆传统的觉悟,反而加深了现代图书馆“惟技术”倾向。
近两年来,图书馆的“惟技术”的“工具化”倾向越来越受到质疑与批评。应当看到,图书馆的“工具化”倾向,并非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它实际上是20世纪现代性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著名社会学家韦伯曾分析过以经济合理化、管理科层制等为特征的现代性的运行机制,还深入分析了现代性的内在冲突,即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张力。胡塞尔在分析欧洲科学危机,即现代人的生存危机时,提出了著名的生活世界理论。他认为,实证化的科学世界在无限发展中,遗忘了自己的生活世界基础,从而导致了价值和意义的失落。哈贝马斯在分析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时,曾提到劳动的合理化导致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的问题,以及服从于金钱和权力的理性化的经济和政治子系统在自己的膨胀过程中把生活世界降为自己的“子系统”,从而导致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问题。图书馆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形: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高效率的社会发展的背景下,以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讯技术、存储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及其各种应用知识进入了原本以人文为重点的图书馆领地,并由于忽略了科学技术的文化价值内涵而蚕食图书馆的人文基础。结果,在越来越精准、明晰的分类、检索过程中,读者成为按照图书馆业务专业规格批量加工的知识、信息的简单接受者,我们得到的不是希望能够得到知识滋润的读者,而是索取与获得的用户。图书馆这个社会文化最集中的场所出现了文化的缺失,图书馆的文化本质相当程度失落了或者被遮蔽
3 回归文化的图书馆
当我们顺着现代图书馆的轨迹,义无反顾地追寻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把功利主义的服务发挥到极致的时候,我们就离图书馆的原始意义越来越远了。图书馆作为一个社会存在,是顺应着社会的文化需要而存在的。图书馆无论是作为人类文化的保存单位,还是作为文化的整合和传播机构,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强烈的人文性。古代,人们对图书馆不仅仅为了去获取知识,而且在图书馆里可以修身养性,陶冶性情,培养情操。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不仅给了马克思以可供查考的书籍文献,也给了马克思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对马克思而言,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查阅文献的场所,更是一个亲切的工作环境和休憩场所。即使是古代的藏书楼,也无不彰显着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天一阁藏书楼不仅仅是一个书籍的保存场所,更为成为宁波范家的家族传承。黄宗羲能够登楼一观,才能成为文化史上的佳话。
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在《21世纪图书馆新论》一书的序言中,引用了一位名叫乔伊斯·卫科夫读者在网络上描绘21世纪图书馆的一段话,这段话让他感觉“意义深刻”:“我们这些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认识和理解,恐怕还没有这位读者那么深刻。”这段话,同样对我也是启发很大,转引如下:“我去图书馆不是为了看书,而是为了获得信息、知识、智慧和教育。因此,我想见到的不是一排排书架,而是人。他们在谈论书,在传授某种知识,在研究某一主题,在创立新的思想。”在这里,读者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些从业人员,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图书馆里巨量而僵化的图书,更想看到的是人,是能够充当起知识的介绍者、引导者、沟通者、启发者的人。
图书馆不能没有文化,缺乏文化的图书馆是可悲的。其实,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入手,无论我们对图书馆的本质进行什么样的追问,提出怎样的解说,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图书馆的本质在于文化,在于文化的保存、文化的整合、文化的传播。
显而易见,今天我们讨论图书馆的文化本质,不是在发现新的真理,而是在澄明被遮蔽的本真的图书馆样态。图书馆从来就不是为了某一个特点的简单目的而存在的。英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做过一个思想实验:假如人类文明及其记录都被毁掉,那么人类要重建文明几乎是不可能的;假如人类文明被毁掉,而记录仍然保存着,那么,要重建文明将是可行的。图书馆与人类文明之间就是这样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保存人类记忆的图书馆,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像现在这样与人类文化如此疏远。如果说,在现代图书馆发展阶段,我们强调图书馆的传递知识信息的职能体现了图书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体现了一定的现代性,也应该看到,正是这样的“单科独进”的功利行为,削弱乃至遮蔽了图书馆的整体的文化功能,同时,也为极端的技术工具崇拜扫除了价值判断上的障碍。当我们以简单功利的眼光来评价技术时,我们只看到技术给我们带来的种种便利,而忽视了技术背后的人文关怀。现代图书馆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现代图书馆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强大支撑,信息技术为图书馆功能的整体发挥和更好发挥的有力保障,反过来又进一步彰显了图书馆的文化价值。信息技术打破了时空界限,使得人们能够更加平等、自由、快速、便捷地得到想得到的图书馆的知识信息,满足他们学习、研究、创造、娱乐、休闲、解决问题、自我提高等多重目的,体现出最大的人文关怀。
图书馆在西方人的视野里,绝对不是仅仅一个为解决某一问题而存在的,他们总是把公平、自由地利用图书馆看成是基本人权之一。而在19世纪大力推广、普及公共图书馆,让公共图书馆遍布城市社区、乡村,其目的也是为了知识的普及、民智的开发,以人民的知识提高来保证社会民主的维护。从我们的角度看,四方图书馆也是含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是承担着维护西方文明的重任的。即使西方科技飞速发展,公共图书馆也没有一味追求简单的直接的为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服务而舍弃其社会责任。为什么美国人把国会图书馆一个文献信息数字化工程——“美国记忆”工程看成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不是美国人对国会图书馆在推动科技、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评价不高,而是美国人的眼光没有那么功利,他们把文明的永续传承看得更高、更重。换言之,他们对图书馆的社会文化的历史使命比我们认识得更深刻、更彻底。印度著名图书馆学家阮格纳赞曾提出过“图书馆五法则”,以最简洁明了的语言揭示了图书馆的本真意义——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围绕着读者服务,体现出深厚的人文底蕴。而美国当代图书馆学家克劳福德(Walt Crawford)与戈尔曼(Michael Gorman)1995年在他们合著的《未来图书馆:梦想、狂热和现实》一书中提出了新的“五法则”:
第一法则——图书馆服务全人类。
第二法则——图书馆尊重各类传播的知识。
第三法则——图书馆善用科技改进服务。
第四法则——图书馆维护自由利用信息的权益。
第五法则——图书馆尊重过去,创造未来。
新“五法则”尽管比阮格纳赞的“五法则”对图书馆的使命描述添加了现代元素,体现了图书馆对人类进步发展的整体意义,但是,在对图书馆的本真意义的解释上却没有超越阮格纳赞,或者说,他们仍然继承了阮格纳赞对图书馆本质的认识,一如既往地弘扬着图书馆的人文关怀。正如该书作者在书中所说:“在思考本书所提出的大议题的过程中,我们阐明了新图书馆学五定律,这是对阮格纳赞的真知灼见在目前和很可能未来的图书馆情境下的重新诠释。我们极其谦卑地提出这五定律,因为我们是站在这个图书馆专业巨人的肩膀上提出这些新五定律的。”
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谢拉在《图书馆学引论》一书中指出:“图书馆事业主要还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事业。”“图书馆在其技术和服务方面日益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靠得更近了,但是我们要提醒自己记住,图书馆学始于人文主义。”回归文化的图书馆,不是放弃、弱化图书馆的传递功能,也不是摒弃、排斥技术,更不是为了给图书馆抹上一丝文化色彩。回归文化的图书馆,就是要回到作为社会文化实体而存在的图书馆的本真,是在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环境里,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全面、综合地发挥图书馆的所有功能。这与建设“图书馆文化”还不一样。“图书馆文化”更多立足于图书馆管理层面,而“文化的图书馆”指的是图书馆理念、图书馆精神、图书馆文化的内涵的根本转变。从根本上说,图书馆的文化本质的真正回归,既不是对图书馆服务与社会经济职能以及技术设备的简单拒斥,也不是在现有体系原封不动的基础上添加某些“文化调料”,而是应当使文化保存、文化传承、文化创造、文化娱乐、文化传播和人文关怀渗透到图书馆的所有领域和所有层面,建构全方位为人服务的文化的图书馆。通过每个个体图书馆的收集、整理、加工、存储、传播、利用的业务活动来为人——读者服务,从而在整体上,保存人类的知识记忆,传承社会文化,丰富和提高社会文化素养,促进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的永续发展。在这个层面上,图书馆与人类发展的价值取向一致起来,把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当成自身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根本推动力。
荷兰图书馆学家舒茨(P.J.Schoots)在谈到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功能时,把公共图书馆称为“市民的第二起居室”。他说:“虽然在信息领域,新的技术正在迫使图书馆和读者改变信息处理、传递以及利用的方式,但是,公共图书馆作为一个为市民服务的社会文化机构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图书馆向公众提供的服务远远超出了信息的范围,比如说娱乐和教育。”图书馆为读者提供的不仅仅是由机器组成的电子世界,而是提供了人与信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舒适空间,是温馨明快的知识乐园。美国图书馆学家西蒙(Matthew Simon)列举出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十大功能:
①公共图书馆是社区和社交中心(community and social center);
②公共图书馆是游乐场所(play space);
③公共图书馆是学习的殿堂(study hall);
④公共图书馆为社区提供经济财产(an economic asset for the community);
⑤公共图书馆是终身教育中心(lifelong learning center);
⑥公共图书馆是博物馆(museum);
⑦公共图书馆是文化中心(cultural center);
⑧公共图书馆是世界之窗(window on the world);
⑨公共图书馆是能源库(place of energy);
⑩公共图书馆是营销研究中心(marketing research center)。
这“十大功能”,尽管不是什么创新之说,但是,却反映了图书馆未来走向:即综合化、多样化的文化走向。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图书馆功能单一化、90年代至今的工具化是相悖的。这应该说是对现代图书馆发展历史的一种纠偏,使图书馆回归到文化发展之路。
我们再来看看在美国大学图书馆出现的信息共享空间。信息共享空间(Information Commons,以下简称IC)是国外大学图书馆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为适应用户的研究和学习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基础设施和新的服务模式。IC自1992年在美国大学图书馆出现以来,备受用户欢迎。在国外大学图书馆中,IC被认为是维护用户公平有效地获取信息的方式,因此发展十分迅速。IC是一种通过重新配置图书馆的物理空间、整合信息资源、提供技术和研究帮助的服务方式。它的核心要素包括:现代化计算机网络通讯服务、参考咨询服务、指导学习研究一站式无缝服务。IC通过设立不同类型的工作站,为用户提供动静皆宜的学习环境,既可以讨论学习,又可以利用计算机获取图书馆信息资源和互联网资源,并在参考咨询人员的热心帮助下,解决信息获取过程中所出现的技术性问题和专业上的问题,创造一个舒适、自由的支持学习和教研的环境。这是以人文关怀为核心,辅助于现代技术而出现的新型服务方式,相对自由的空间,良好的知识研讨环境、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热心周到的服务构成了信息共享空间的主要要素,成为现在技术条件下图书馆服务的新模式。而在这个所谓的“创新”的服务方式中,我们其实看到了传统的图书馆服务的复活,这些服务在新技术的条件下综合集成,共同为读者提供充满人文色彩的现代知识信息服务,体现出技术因素与人文因素的高度结合,标志着图书馆向文化回归的潮流,从而使现代图书馆进入“文化的图书馆”。
收稿日期:2009-0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