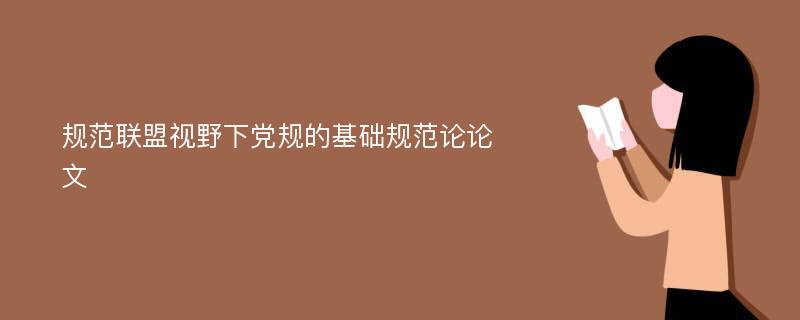
规范联盟视野下党规的基础规范论
王宏哲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 100088)
【摘要】 社会规范之间以基础规范为核心形成一个有机的规范体系或规范联盟。基于国家强制力的基础规范是“硬规范”和“明规范”,而其他社会规范则是“软规范”或“隐规范”,二者生成的“规范合力”建构了社会秩序。党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规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扮演着基础规范的角色,尤其是规范“关键少数人”的纪律性党规与公法一起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范体系的基础。
【关键词】 党规;规范联盟;明规范;隐规范;基础规范
一、社会规范联盟
“社会规范联盟”是不同社会规范基于共同规范价值和规范目标,以基础规范为核心,而形成的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规范系统。
社会规范间是“和而不同”的。尽管规范对象都是“社会人”,且规范目的均为建构有序的“社会网络”,不同规范的规范方式、规范作用、规范力量是有差别的。在对人们行为的规范方式上,道德规范采用原则方式,留给行为者在特定道德情景下的行为裁量权(建议的),而法律则通过具体规则为人们提供普遍的、确定性的行为指引(命令的); 同样是规范人们的思想,宗教采用信仰的证明方式(教义式),而现代法律却采用的是理性的论证方式(反思式);同样是规范公职人员的贪腐行为,法律以行政处分和刑法为依据,以罪与罚进行约束,而党规则以政治伦理之引导和组织纪律之处罚为手段进行约束。不同社会规范尽管扮演了不同规范角色,但在特定社会,所有社会规范在其规范目标上却是统一的。
“规范联盟”生成了“规范合力”。在中国传统社会,法律作为儒家伦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与儒家伦理一起共同服务于封建皇权,以规范的方式保证了封建社会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形成了中国文化独特的社会结构与规范思维。在西方中世纪,所有规范都是宗教的“侍女”,道德和法律都统一于基督教教义所设定的社会秩序,在长达七八年的实际内。在今天,“法治”成为一个跨越不同国家和文化的共识口号,成为宗教、道德、政策、纪律和党规共同“拱卫”的规范目标。
道德规范、宗教规范和法律规范是人类治理历史中最重要的三个规范,在不同时期和国家也分别充当了基础规范的角色。在中国传统社会,在拒斥宗教规范后,形成了儒家思想主导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之间的超稳定的、极富中国特色的“规范联盟”。“德主刑辅”、“隆礼重法”等就是对这种规范系统内部关系的文化表述。由于儒家伦理规范是其核心,可以将中国传统社会的规范系统命名为“伦理型规范联盟”。西方中世纪规范联盟的特点是“宗教型规范联盟”,因为基督教教义成为绝对真理,构成了道德、法律、政治等其他社会规范的正当性来源。随着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观念的兴起,特别是自由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其“规范联盟”内部,世俗规范战胜了宗教规范,法律规范取代宗教规范成为了规范主导,由法律与道德和/或宗教结合形成西方现代文明的规范秩序,基于法律规范的核心地位,可以将其称之为“法律型规范联盟”。庞德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中对道德、宗教与法律三种规范的地位的历史变迁和法律崛起的过程做了详细的论述。
国家是规范联盟形成的“操作者”和“控制者”。不同国家(作为最终社会暴力的拥有者)对规范联盟的生成态度是有差别的,或者积极,或者消极,这主要由该国家的主导型的政治哲学所决定的(规范可以看作是文化的成果)。持有自由主义立场的国家,一般奉行不过多干预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生成的过程,社会规范联盟的形成表现出“自治”特性,国家规范(现代的国家法)对民间规范(社会自生规范)比较尊重,国家规范主要限定在政治的或公共的领域,私人生活领域更多地留给了民间规范。这些国家对规范联盟的控制能力较差。在坚持平等主义的国家,基于正义分配的理由,国家对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进行有意识的建构,国家规范(国家制定的法律或国家欲强制推行的道德与宗教规范)比较强势,它不仅作为强命令要求民众遵行,而且它也越过公共领域进入了私人生活的领地,国家规范甚至强势到可以改造民间规范,后者处于被挤压状态。规范体系(联盟)在这些国家被打上了明显的国家标签。
规范联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和标志。稳定的社会秩序不仅来自于国家政权的稳定,也来自于国家政治秩序建立后的社会规范秩序(规范联盟)的确立,因为社会规范记载的不仅是对人们的行为命令或建议或其他行为模式,它也记载了社会的集体价值(规范价值);同时,实现社会秩序的动态制度也是由社会规范(联盟)确立的。在这个事实上,社会生活就是集体规范的生活,不同社会规范的确立和成熟,以及作为社会规范集合的规范联盟的形成才可能保证制度化生活的可预测性。因而,社会规范的“联盟”、“系统”或“体系”思维是对国家控制的规范化理解的必然体现,是建构稳定社会秩序的规范基础。
国家政策与法律法规。企业战略管理研究中,对于国家政策与法律法规对于企业发展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当然,目前,本文也依旧要提出一切企业的发展都要在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这是底线。另外,企业的战略性发展也要以国家政策为前提,是在符合国家政策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发展。比如说,就最近几年国家政策所提出的绿色发展策略,相关企业可以以此为前提进行发展,具体而言,房地产企业可以此来建设绿色化住房构造,环保清新的住房必然会受到大众青睐。除此以外,相关企业也可就绿色发展的政策独出心裁地创新绿色出行方式。既符合国家政策,又对本企业的战略性发展有重要影响,何乐而不为呢?
二、基础规范:隐规范与明规范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视野下,我国已经形成了以法律为主,以党规为辅,融合道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范联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伟业在最根本上是要看是否形成价值统一、执行有效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范联盟”或“中国秩序”。
基础规范是规范联盟或社会规范系统的核心规范,其可以称之为 “明规范”,它与“隐规范”构成了“规范联盟”中最主要的两个组成部分。“明规范”也可以称之为“硬规范”,是指被国家权力直接支持的规范,它最具国家暴力性,它是国家(统治者)选择的社会规范的胜出者,其他规范不得与其相抵触。“明规范”往往表征着国家治理的水平与特征,这种规范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其规范方式是平衡的(如法律的权利与义务)还是倾向的,其规范生成是“认可的”还是“命令的”等,都决定了社会治理的规范效果。“隐规范”则不同,尽管其规范性的直接来源不是国家权力(在法学知识谱系中,分析法学开创者之一的霍布斯,明确地将法律定义为“主权者的命令”,凸显国家权力才是其规范性核心),可能是于自身(道德的效力来自于正当的“自我命令”),或来自于其他外在理由(宗教的效力来自于对神的信仰)。但由于其往往在更深层次上约束或影响着行为人的行为选择,构成了社会秩序的“价值底座”,因而,可以被称之为“软规范”。现代法治社会的道德与宗教往往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
“明规范”/“硬规范”与“隐规范”/“软规范”可以看作是一对范畴,二者关系是:硬规范由于受到国家权力的直接支持,效力范围主要在公共领域,直接规范对象是人们的外在行为,规范性来源主要依靠国家暴力及其威胁,规范形式是外在化、标准化和文字化的,法律是现代社会典型的硬规范;而隐规范的效力范围主要在私人生活领域、主要规范人们的思想与信仰、规范性来源主要是“认同“或”相信”等自我接受,其规范形式多是非标准化的,甚至可以是口头的,典型的软规范指道德和宗教(中世纪除外)。硬规范与软规范的理论关系是相对的,比如道德和宗教在其本性上应该是软规范,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及西方的中世纪,道德和宗教分别由于国家权力的需要被高度“硬化”,使这两种规范在自己的适用场景中地位高于法律,呈现出一种“法上”优势,获得了硬规范的特征,产生了“硬化了软规范”与“软化了的硬规范”(指法律)并存的特殊规范秩序。硬规范与软规范的实践关系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关系是同质同向,即两种规范之间的价值一致,软规范构成硬规范的实施“土壤”,二者相互支持,放大彼此的规范效果。在规范初期,规范结果偏向于硬规范,但在S拐点之后,规范结果就偏向于软规范。这种“同质同向”的“规范联盟”的规范效果,可能会造成“硬规范软化”现象,即硬规范的“硬壳”被软化,人们对硬规范的遵守的理由不再主要是暴力或其威胁。亚里士多德法治定义中的“守法状态”就是如此。所谓“同质”是指两种规范既可以是同恶,也可以是同善。如纳粹德国时期的法律与道德是同恶关系,而西方法治社会的法律与道德和宗教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隆礼重法”均是同善关系。第二种关系就是同向不同质,在这种分离关系中,规范结果是高度偏向硬规范的,但这种高度依靠国家强制力来维持的规范秩序是偏专制的,由于考虑到专制与恶紧密相连,这种关系非现代文明社会之所取。
三、党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础规范
社会规范之间不是散乱无序的,而是在基础规范的统领下有机统一的。基础规范的领导地位的一个主要来源是价值(集体可接受性及其产生的拘束力)。从价值的规范来源看,尽管集体价值来源于个人价值,但其生成却不是个人价值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价值重整”达到“集体认同”,进而实现社会价值的“集体可接受性”的规范性来源。这一过程实不仅实现了价值主体从单个个人向社会多数的转变,也实现了价值的个人主观特性向集体客观属性的转变,这些转变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治理结果:那就是价值在社会场域具有了客观特性,这使得集体价值具有了“反任意”(个人任意)的规范属性,价值从内在的个人观念变成了需要规范“外壳”传递其信息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社会治理工具。作为 “纯粹的”的规范,其内涵是被规范认同者(制定者或遵守者)所赋予的,可能是价值,也可能是事实(政治的、经济的或其他社会事实、自然事实等),或许是规范持有者的心理态度等。基础规范获得领导地位(规范竞争中获胜)的一个条件是其将国家推崇的或社会公认的集体价值作为自身价值。这是一个规范对价值的寻找过程。规范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发现或契合了时代的主流价值。
基于矩生成函数近似的双媒质协作通信功率优化分配//陈智雄,景一方,韩东升,邱丽君,田新成//(23):159
根据玉米的生长特性,更适合在我国东北种植。玉米本身是一种不需要很高种植条件的作物,但是为了保证玉米的高产和更好地利用滴灌技术,我们还需要选择种植的土壤,并仔细选择。一般来说,我们应该选择更平坦、更肥沃的土地,并在保证土壤厚度的基础上,保证土壤的通风,因为这种土壤更容易保持水肥,便于后期田间管理。
党规是中国特色的明规范。党规具有如法律一样的外在特征,并且由于纪律性党规对“关键少数”实施引起的放大效应,使得党规产生了如法律一样的规范效果。现阶段学者们争论的“党规到底是不是法律”这个命题,就是对党规的明规范特征的一种确认。党规如果是隐规范的话,就不会产生这样一个争论,之所以争论是因为党规在实践中分享了法律的权威和效力。我们需要进一步确定的是:党规和法律是两种不同的硬规范或明规范,根源在于二者分别由党和国家的力量所支持。如果把国家暴力作为硬规范的充分条件的话,那么,党规是实质硬规范,而法律则是形式硬规范,这种界定的根本理由是党领导国家。在现代法治国家,其执政党的党规是软规范和隐规范,其法律是实质硬规范。因而,用西方法治理论来建构中国法治实践就是错位的。党规与法律构成了中国的“明规范”体系,二者在目的上是高度统一的,因而,不能将二者的差异放大,并依此去否定党规的实践价值。
作为实质硬规范的党规是法治中国的“基础规范”,其建立的党规秩序拥有“最后权威”。规范必须具有实在权威,才会有生命力。法律的权威性来自于国家强制力(法律并不是因为信仰而权威,而是因为权威而被信仰),道德的权威性则来自于道德意识和道德秩序(道德是因为基于人伦的“绝对命令”而权威),宗教规范的权威性来自于信仰本身(宗教因为信神而权威)。党规的内在权威性来自于它是党的集体意志和命令,党规的外在权威性来自于党对国家和社会长期的、正确领导。党规的实践权威性来自于其对“关键少数”的正确指引和成功约束。在西方资本主义法治国家,宪法是“基础规范”或“规范之规范”,因其他规范之效力来源于此而获得体系内权威。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家治理的主体是党,是党基于其权威地位领导人民来进行国家和社会治理,这就使得国家治理的规范性只能来自于党。党深刻地认识到,党的规范化和法治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前提和关键。党规由于其要求严于国家法律,故而,在实践中成为法律的重要保障。“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这种特殊的保障作用才是党规权威性的真正体现。由于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拥有领导者的地位,党规为基础的“党秩序”构成了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基础,这种地位以及党规和党秩序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构成了党规特殊权威的来源。
与分离器出口堵塞和上部棚灰的情况不同,返料阀参数变化趋势正好和分离器上部棚灰的变化趋势相反。如果出现棚灰堵塞,将会导致返料阀下部的流化风量剧增,并会使返料风室的压力明显下降,影响到分离器立管压力并呈现出上升趋势。如果是发生返料阀结焦或出口堵塞的情况,就导致增一次、二次和流化风量增大的情况出现,还会使炉膛负压变正,并出现引风机电流增加的情况。如果是堵塞返料阀下部流化风量就会出现剧减,但返料风室的压力却会突然上升,分离器立管的压力也会随之升高,但是分离器回灰温度却没有产生任何的变化。
狭义的社会规范理论,依生成路径,将规范分为自下而上的“社会规范”(民众自发)与自上而下的“国家规范”(国家自主),其中后者主要是指法律。据此二分法,党规被划分为普通的、狭义的“社会规范”或“民间法”。很显然,这是一种“刻舟求剑”式的机械思维。要确定党规的规范地位,关键是要看党规的规范性来源。基于外在的强制与源于内在的接受是解释规范性来源的两个基本进路,这是划分两类规范的基本标准。如果把全体党员作为规范对象的话,党规的规范性来源是“共产主义信仰”,是自下而上的政治性的规范可解释性,但如果把“关键少数”作为规范对象理解的话,党规(尤其是纪律性党规)的规范性来源则是“命令”,即全国人民、全体党员对具体化党的领导权力的个人的外在命令。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组成部分的党规,体现其治理价值的是后者。全体党员视角的党规是隐规范,而规范“关键少数”的党规则是明规范。
参考文献:
[1]陈嘉明:规范性的科学何以可能-关于建立”规范哲学”的思考[J].开放时代,2000(5):52-57.
[2]许竹:论布兰顿之规范性实践概念[J].世界哲学,2010(3):99-109
[3]俞静贤:法概念与法的规范性——以凯尔森为中心的考察[J].清华法学(第九辑):206-221。
[4]陈锐:规范逻辑是否可能——对凯尔森纯粹法哲学基础的反思[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2):131-145
[5]夏建国:实践规范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6]李锦辉:规范与认同[M].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
〔基金项目: 本文由“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创新年度规划项目(2018)”资助,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 王宏哲,中国政法大学发法学院法理研究所,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法理学、党规学。
实习编辑/黄晓茵 责任编辑/陆一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