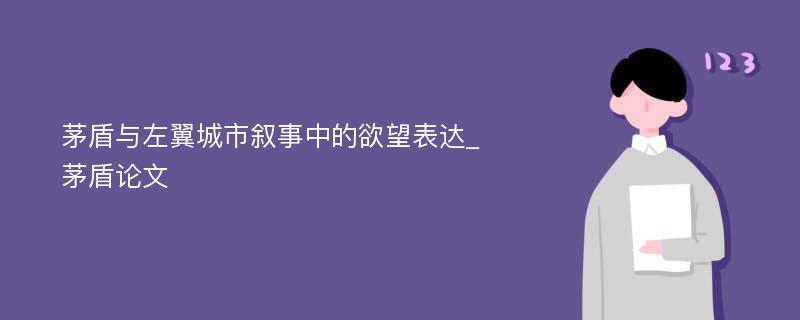
茅盾与左翼都市叙事中的欲望表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茅盾论文,欲望论文,都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3)04-0126-05
在传统的文学史著作中,茅盾的《子夜》通常被认为是一部展现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
社会广阔画面的史诗性作品[1](PP244-254)。在有的学者眼里,《子夜》开卷那段对黄 浦江、苏州河交汇处鸟瞰式的描写具有强烈的隐喻性质[2],它昭示着“西方现代性的 到来”及相伴而来的西方势力的入侵。[3](PP3-5)然而,单从那颇富刺激性的感性景观 层面而言,这段文字以及散见全书的描绘都市景观的段落给人似曾相识之感。但随着阅 读的推进,这些推想被一一否定:他所读到的《子夜》是一部完全不同类型的作品。
《子夜》是都市文学的另一种新样式——左翼都市叙事的范本。它的叙述焦点不再是 个体的精神历程,而革命、阶级、民族、历史潮流这些大写的字眼占据了文本的显要位 置,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损害艺术价值为代价的。而且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 现,这种审美上的缺陷并不是出于茅盾个人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是左翼都市叙事的必 然结果。因此,《子夜》的叙述重心与新感觉派作家和张爱玲有了根本的不同。它由都 市中的个人生活领域转移到了有关中国社会的宏大叙事之中,集团和群体的意愿在作家 眼里成了至高无上的追求目标。这使得它对都市生活中欲望的书写方式也相应地产生了 一系列变异。
熟悉《子夜》的读者会发现,由于叙述重心的变化,作品文本中所蕴含的欲望主体也 发生了相应的置换。在它容纳了宏大的社会画面的叙述框架内,尽管林林总总的各色人 等出没其间,他们有着各自形形色色的欲念和追求,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并不是茅盾 关注的焦点。在《子夜》中,欲望的主体不再是新感觉派作家和张爱玲的文本中那些深 陷于尘世罗网之中的俗人,而是某种非人格化、非个人化的群体:准确地说,是效力于 革命事业的无产阶级,是向往颠覆现存政治、社会秩序的民众。在20世纪左翼的革命话 语中,正是这一非个人化、匿名的民众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占据着价值阶序中的显要 位置,并进而成为持久的革命激情与冲动的源泉之一。[4](PP259-285)
从表面上看,《子夜》描述的是精明、强悍的实业家吴荪甫的悲剧。应该承认,他自 命不凡的性格在其间扮演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他的悲剧从根子上说是 性格的悲剧,“而不是什么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失败”。[5](P287)然而,纵观全 书,虽然吴荪甫的性格给人留下了不凡的印象,但无论是从作者的意图,还是文本呈现 的人物的丰满程度来看,很难将他视为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李尔王、麦克白式的 人物,也很难将他的悲剧视为性格悲剧。他与赵伯韬的殊死拚杀,和在生死线上死命挣 扎的工人间的对抗根本不是纯然的个人气质间的冲突,而是充满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 。茅盾曾说,他的《子夜》禀有“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最初它涉及的 范围包括“农村的经济情形,小市镇居民的意识形态……以及一九三零年的‘新儒林外 史’,——我原来都打算连锁到现在这本书的总结构之内”。[6](P571)后来由于种种 原因,它的规模大大缩小,仅仅聚焦于上海的都市生活。从他对其创作意图的阐述中可 以清楚地看到,他是想借《子夜》来揭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生存困境,并在此基础上 剖析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清晰地勾勒出他心目中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并最终论证他倾 慕的红色社会革命的合理性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作品的标题也佐证了这一点。在写作 过程中,《子夜》的标题前后几次易名。最初,茅盾想到三个书名:夕阳,燎原,野火 。它们极富政治性的意味,后两个喻指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兴起的红色革命,而“夕阳” 则借用唐代诗人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意境,隐射国民党政权正日暮西 山。而最后选定的“子夜”则表明中国正处于最黑暗的时刻,但子夜过后将是黎明,革 命正蓄势待发。[7](PP165,167)
在这一气宇轩昂的宏大叙事构架中,充当欲望主体的只能是那非个人化的群体、组织 、阶级,个人琐屑的欲望遭到程度不一的贬低、鄙弃乃至放逐也是势所必然。《子夜》 中吴少奶奶与雷参谋间令人伤感的旧情,林佩珊与范博文、杜新箨等人的情感纠葛,吴 家蕙四小姐的心理苦闷,原本都是都市叙事文本中抒写个人欲望的绝好题材。的确,它 们在《子夜》中也是引人瞩目的亮色:正因为有了它们,文本中那些对金融、实业界的 描写才显得不是那么单调枯燥。但这些个人化的欲望叙事在整部作品中只是作为次要的 情节引线存在,只是作为作者渲染气氛、烘托主要人物的边角料,它们并没有自身独立 的生命力,最多是作为一种精美的点缀,让这部重量级的作品增添一些血肉丰满的细节 ,使它不致显得干瘪,迂阔。
对于茅盾本人而言,《子夜》对都市人欲望的这种处理方式也不是他心血来潮之际一 蹴而就的结果,它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在他20年代后期所创作的小说处女作《蚀》 三部曲里,有关个人欲望的叙事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幻灭》中的静女士和慧女士 ,《追求》中的章秋柳、王仲昭、张曼青等人的命运轨迹清晰地勾勒出来,他们个人的 欲求、意愿成为作品倾全力表现的对象。但即便在那一时期,茅盾对都市人的欲望的展 现方式便和新感觉派作家及日后的张爱玲有了鲜明的分野。虽然同样写到都市人的欲望 骚动,但它不拘囿于被抽空了时空背景的日常生活之中,不锁闭在个人一己的天地中, 而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向着奔腾不息的历史潮流敞开。捷克学者普实克对 茅盾创作的这一特征作了极为中肯的评价:“茅盾的创作总是与最近发生的事件紧紧地 联系在一起,好像他要把他的国家刚刚经历的暴风骤雨当场记录下来”。[8]茅盾本人 在谈到写作《蚀》三部曲时也说到它与社会政治斗争与历史潮流间水乳交融的联系:“ 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 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 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9]( P626)
就这样,在有的学者看来,茅盾这一时期的小说成了“一个巨量的空间,多姿多彩的 个人欲望与社会力量在其中交锋、斡旋、消融”。[10](P292)这是一个特殊的场域,茅 盾试图将以个人欲望为枢轴的都市叙事与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叙事扭合在一起,达 到一种综合,其间个人与集体、日常生活与革命运动都能得到圆满的展示。然而,在很 多情形中,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叙事无法重合,即便作者勉强将它 们叠合成一体,不谐和的裂缝依旧随处可见。《蚀》问世之后来自左翼阵营的批评之声 便是这种断裂的明证。在左翼批评家看来,茅盾在作品(尤其在《追求》)中流露出来的 那种悲观颓唐的情绪与表现革命发展趋势的历史叙事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抵牾。[11] (PP114-116)仔细审视文本,不难发现“他一再试图构筑‘时代女性’与‘大一统’的 理想时间之间的和谐幻象,却一再遭到他的记忆及女身‘欲望’语言的反叛而失败”。 [10](P337)想要获得左翼批评界的广泛认同,茅盾还需要寻找更合适的都市叙事样式, 他那时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小说本身变成一种向‘革命’开放的形式,既饱含激情而 又指向人类解放的‘必然’目标,其叙事开展能象征不可阻遏的历史方向,借此期盼‘ 革命’的东山再起”。[10](P335)
此外,20年代后期勃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思潮也对茅盾这样一个左翼作家形成了不 言而喻的影响。在从事创作之前,他便是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积极倡导者。在19 25年所作的《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中,茅盾借助当时风行苏联文坛的理论学说,详尽 、系统地论述了无产阶级艺术的特征:“无产阶级艺术决非仅仅描写无产阶级生活即算 了事,应以无产阶级精神为中心而创造一种适应于新世界(就是无产阶级居于治者地位 的世界)的艺术。无产阶级的精神是集体主义的,反家族主义的,非宗教的”。[12](P3 96)到了1928年,李初梨则对革命文学的宗旨、功能和使命作了系统的阐述。在批驳了 当时风行的对文学的两种定义(“自我表现论”和“社会生活反映论”)之后,李初梨遵 奉的是美国作家辛克莱的观点,“一切的艺术,都是宣传”。[13](P581)在此基础上, 他提出了自己对文学的定义:
文学,与其说它是自我的表现,毋宁说它是生活意志的要求。
文学,与其说它是社会生活的表现,毋宁说它是反映阶级的实践的意欲。[13](P582)
在李初梨眼里,这还远不是革命文学内涵的全部。它不能停留于反映的层面,而应该 直接介入到现实生活之中,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文学与生活间的距离被压缩到最小, 乃至合二为一,“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的— —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斗争的文学。”[13](P589)
在革命文学的话语中,无产阶级这一非个人化的群体,无疑是革命运动的主体,是历 史发展中最富创造力的主体,历史未来的进程便是这一集体主体性充分施展其能动性的 过程,它将用一切手段(包括暴力)铲除途中的一切障碍,重塑一个光明的新世界。在这 一话语中,欲望这个与个人密切相关的词汇似乎销声匿迹;但作为人类的基本内驱力, 它不可能也没有消失,它只是改头换面,以一种隐蔽的方式重新出现。摧毁旧世界、建 设新社会便是这一集体主体最大的欲望符码。由此,历史的进程也成了它的欲望符码持 续不断地现实化与受挫的过程。
尽管在1928年那场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中,茅盾曾受到创造社、太阳社中一批激进的 左翼文学批评家的指责,但除了意气之争的因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他们间的争论源于 双方对革命文学理解上的分歧。而茅盾本人并未站到左翼文化的对立面,他在内心深处 一直将革命文学奉为圭臬,并在创作实践中自觉地一步步向它的标准靠拢。1929年创作 的《虹》便是这一努力的成果。在《虹·跋》中他自述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欲为中国近 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14](P271)
的确,和《蚀》三部曲相比,《虹》在个人叙事和展示历史发展潮流两方面的融合上 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依照陈建华先生的看法,在这部作品中,“‘历史’以清晰的面 目开始出现,与小说的主人公形成辩证的关系”,而“‘历史’不仅由事件构成,是开 展中的时间过程,而且含有‘真理’的自足性,带着自由意志向既定的目标前进”。[1 0](P336)而从都市叙事的角度着眼,这部小说只有最后三章才涉及到梅女士在现代大都 市上海的生活,前七章讲述的则是她在四川成都等地的遭际。虽然篇幅在全书中所占的 比例不大,但梅女士的形象只有在她到了上海之后才趋于成熟,全书的意旨才趋于明晰 ,以前的经历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她成长道路上的铺垫。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茅盾在《虹》中展开的都市叙事既不是新感觉派作家笔下充溢着 感官色彩的欲望历险,也不是张爱玲在恒常的日常生活空间中抒写的浮世的悲欢离合, 而是一个知识女性不断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历程。作为都市的上海在这里充当的是一 个各种思潮、各种社会力量竞相登场的巨型舞台,这里有散溢着陈腐气息的守旧派,有 崇尚国家主义的“狮醒派”,还有便是梅女士爱恋的以梁刚夫为代表的革命者。最后梅 女士全身心地投入了革命事业,在声势浩大的“五卅”游行中与激愤的民众合为一体。 作品收尾时的这一壮观场景,不仅仅是对她个人经历的描写,而且极富寓意:她个人的 追求与历史的洪流在宏大的事件中融合为一体,交叠的个人欲望的叙事与对历史发展趋 势的揭示也在此汇聚交合:梅女士成了革命和历史发展的载体。
但先前提及的裂缝依旧存在着。作为欲望主体的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运动尽管在梅女士 的个人经历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展示,但由于《虹》整部作品的叙事框架还是围绕她个 人的命运而设置的,因而虽然作者竭尽全力想将她的个人欲望叙事与历史潮流重叠,但 两者毕竟无法完全吻合。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虹》的文本中有大量无法化约为历史宏 大叙事的过剩性因素,它源自作者个体的情感体验。在王晓明先生看来,茅盾在《虹》 的结尾时着力表现梅女士在示威游行中的勇敢无畏,实际上是“对这体验作政治性的改 造”,“把对她的形象感受纳入一个现成的政治模式”。[5](PP281-282)此外,《虹》 的叙述视角从梅女士一人展开,在描绘丰富多彩的都市生活时常常显得捉襟见肘,无法 满足那非个人化的欲望主体的需求。
到了写作《子夜》时,可以说茅盾实际上采用了一种新的写作手法,它更不依赖于个 人的情感体验,更切近于革命文学的理想模式。显而易见的是,他有意识地将小说“当 作了社会判断的工具”,因而在这种方式下写出来的《子夜》不能不是一部主题先行的 作品。[5](P285)之所以要主题先行,因为只有这样,它才不致像在《蚀》、《虹》那 样受个人情感的掣肘,才能提供一个超越于个人欲望叙事的宽广的框架,才有可能让欲 望主体——无产阶级及其主宰的革命历史运动得以全方位的展现。
在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文艺理论家看来,经典现实主义的创作要使个人与社会历 史命运最紧密地结合起来。问题在于如何将个人化的欲望叙事与宏大的历史叙事融为一 体。个人毕竟是个人,他的全部活动常常无法被规整地化约到抽象的历史意义的框架中 。这也是茅盾在创作《虹》时遇到的难题。为了更有效地表达历史发展的潮流,表达非 个人化的欲望主体的意志,有必要对传统的叙事模式作一番修正。
在《子夜》中人们可以一瞥这一修正后的成果:那一非人格化、抽象的欲望主体终于 在作品文本中获得了主宰性的地位。尽管作品中有着众多的人物,有着丰富程度不一的 情节线索,但并不具备独立的主体性,他们都是从属于那一欲望主体的牵线木偶。个人 欲望的叙事先是被减弱,随后被超越,融解在宏大的叙事话语中,而这一带有强烈意识 形态倾向、革命化的宏大叙事通过吴荪甫的失败和赵伯韬的胜利,展示出了作者心目中 首肯的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发展的前景。欲望主体在这一图式化的意念中得到了圆满 无隔的体现。
在这一集体性、抽象的欲望主体大踏步的凯旋声中,一种崭新的小说形式似乎浮出水 面,但这并不是一种有机的、富于生命力的形式;相反,小说艺术在此却走向了穷途末 路:由于过于急切地想摆脱、超越与生俱来的生活的直接性和偶然性因素,叙事话语在 一种趾高气扬的飞跃中轰然间趋于解体。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在向历史叙述转化。而 只要对历史叙事的特点稍加考察,你便可以发现,茅盾所追求的对历史潮流的展示与意 义的清晰阐述在历史叙述文体内全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满足。
如上所述,在虚构性的小说叙述中,个体生命的经历可以折射出历史发展的潮流与趋 势,但两者间不可能完全合二为一,总存在着某种缝隙与裂痕。但历史叙事不仅在选用 的材料上与小说有着天壤之别,而且它的叙述重心是特定时间框架内的事件,人物虽然 有着无可抹煞的重要性,但它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因此,总体性的历史叙述不可 能以单个人物为对象,它总要包蕴众多的事件。
其次,像新感觉派作家和张爱玲那样,小说叙事可以不向人们提供有关当时社会历史 的潮流、发展趋向的清晰解释,可以用个人化的微型叙事来消解宏大叙事,可以用人物 的主观心理感受来替代对历史的理性化解释;但历史叙事无法逃避这一使命,它不得不 从某一价值坐标系出发,对事件、人物作出褒贬不一的评价,对历史发展的趋势作出说 服力强度不一的阐明。这实在是历史叙述的宿命。茅盾在《子夜》中对自己提出的所有 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在历史叙述中都可轻易地得到实现。
然而,问题是茅盾是在写作一部虚构性的小说。在《子夜》中,小说叙述的个人化、 具体性与他意欲阐明的历史潮流间存在着一种致命的紧张关系。当他遵循自己的个人体 验,围绕人物个性化的欲望法则展开他的都市叙事时,他在小说艺术上获得了成功,但 在对历史意义的阐发和历史潮流的廓清上难以符合左翼文坛的期望;而当他洗心革面, 试图以非个人化、抽象的集体欲望作为作品推进的动力时,他在展示历史潮流与趋势这 方面似乎获得了成功,但在艺术的感性丰满度上却大打折扣。他陷入了一种无法两全的 窘境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但是茅盾个人的窘境,也是整个左翼都市叙事面临的 共同问题。
收稿日期:2003-0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