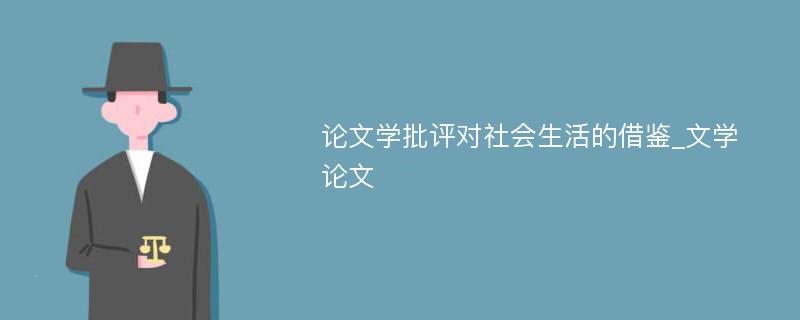
论文学评论的社会人生参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生论文,社会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创作是作家从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生命体验出发,调动自己的形象积累、感情积累,在审美理想的烛照下,围绕着某一线索,经过增删、整理、浸润,而予以书面化的十分复杂而独特的过程,文学作品则自然是社会生活通过作家头脑的语言艺术形式,是作家生命体验的符号化。文学评论,或者称之为文学批评,作为对文学作品及与之相关的文学现象的价值和成就、得失、规律的解读、阐释或评价,当然应当参照社会与人生,以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一
所谓文学评论的社会人生参照,是指将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社会人生图景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与历史事实相比照,与实际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以及真实的人性人情相比照,从而分析、评判其反映社会生活的准确程度,描摹人性人情的妙肖程度,揭示人的心灵、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刻程度。这里所说的准确、妙肖程度是一种“神似”,一种不违背历史真实的“近情近理”、“合情合理”、“入情入理”,一种符合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趋势的“理顺情通”,而并非刻板地记录历史、摹写生活、照相人生,并非与生活的等同;这里所说的深刻程度,是一种生命体验,亦即从作家自己的内心情感和真切感受出发,体验对象的心理波澜和情感状态,而并非对对象做生理的、心理的科学剖析。文学创作既然是在作家审美理想的烛照下进行的,既然通过了作家审美理想的浸润,是作家审美理想的符号化,与生活的等同便是不可能的,与科学的心理分析的等值同样是不可能的。要求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社会人生图景与历史、与社会、与心理科学的研究成果完全一致,是荒谬的。“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对文艺作品超越社会人生的特性的理论表述,毛泽东同志概括的这六个“更”,便是从对文艺作品中所描写的社会人生图景与现实的社会人生的比照中得来的,为文艺评论在实践中运用社会人生参照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
其实,自有文学评论以来,评论者就在评论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社会人生参照。优秀的文学评论从来离不开社会人生参照。叶昼、毛宗岗、脂砚斋、金圣叹等文学评点家,无不把社会人生当作自己评点实践中的参照对象。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在对岗察洛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作品的评论中提出的全部有时代意义的批评命题和振聋发聩的见解,都是与当时的俄罗斯社会现状密切相关的,亦即是从对沙皇专制“黑暗王国”的本质的揭露是否深刻来立论的。因此,他的评论产生的社会效果是加深了读者对现实生活的认识,看到了俄罗斯社会的黑暗、丑陋和污秽种种。即便是分析作品中奥勃罗莫夫等人物的性格,杜勃罗留波夫也不忘记从这些人物性格的社会环境和各种政治、经济渊源上分析出人物性格的形成因素。
如果说杜勃罗留波夫的社会还原的批评过于单纯,缺乏对文学自身结构和内在规律的探寻,那么恩格斯关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则是文学评论最科学的观点。其实,“美学和历史的观点”的真髓即在于社会人生参照。这是因为社会是历史行程中的社会,而任何审美价值的内核都不过是得到“升华”或“醇化”的人的价值,是人的行为和心灵的善与美通过作家心理体验的感性表现——当然审美价值还有其形式方面的因素。但是,无可怀疑的是,人的命运、行为,尤其是隐藏其后的思想、意识、感情,是审美的主要对象。美的本质即在于真和善相联系的、能够体现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创造活动和创造才能、智慧、品格、思想感情的全面本质。
二
坚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当然应当重视社会人生参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对斐·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的评论,恩格斯对敏·考茨基的小说《旧人和新人》的评论,对玛·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的评论,就是运用“美学和历史的观点”评论作品的典范。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中说:“在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句关于现实主义的经典名言是对“美学和历史的观点”的要义的阐释和说明。所谓典型环境,即是围绕并形成和制约、影响着人物生存和生活的文化环境,首先是社会环境;所谓典型人物,即是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独特命运、行为、思想、感情的表现。因此,坚持文学评论的“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就必须在评论实践中坚持社会人生参照。文学评论的社会人生参照并非撇开文学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一种方式,撇开文学能动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规律,简单地将文学作品等同于社会历史教科书,等同于政治学讲义,将文学作品对社会历史现象的形象化描绘等同于社会历史现象的摄影或图解,将史实等同于叙事,将生活真实等同于艺术真实,从而从某种历史观、政治观出发,对文学作品简单地进行历史学、社会学的解剖和宣判,指斥其成败得失。那是一种庸俗社会学的评论,与文学评论的社会人生参照是绝不相容的。文学评论的社会人生参照是包含着美学的评论,是立足于人、面对着作为人的心灵创造成果的文学文本的评论,是一种审美的评论。其精髓在于对时代精神、对历史前进趋势的把握,在于做出符合时代需要的价值选择。
庸俗社会学的评论曾经严重地败坏了文学评论的名誉。在我国极左政治肆虐的那些年月,庸俗社会学的评论曾经成为文学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的审判官,成为绞杀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杀手。这种评论以是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本质为利刃,凶残地砍杀文学。随着新的历史时期对极左政治的清算,庸俗社会学的评论销声匿迹,文学评论在对西方理论的移植、借鉴中走向众声杂噪。一些评论文章极力强调文学的自足性,强调文学作为作家心灵创造物的虚幻性,否定文学反映社会生活、描绘人生图景的真实性原则,嘲弄意义、反对理性,解构历史、躲避崇高,力主非理性、偶然性,欣赏平面、削平深度,认同媚俗化、游戏化,抹杀善恶美丑的界限,推崇血淋淋、肉麻麻、性饥渴、性肆虐的感官刺激和兽性、匪性、痞性描写。文学评论不再是对文学文本及与之相关的文学现象的价值和成就、得失、规律的解读、阐释和评判,而成了对非人世界、对丑恶和粗俗津津乐道的揣摩和赞赏,成了非人文、反人文、与社会生活无关的文字构成物,成了纯形式的语码游戏或堆砌。究其实,这种文学评论是在进行着另一种价值引导,是在消解着文学的社会功能,从而也在消解着文学自身。
三
文学评论的社会人生参照应以对文学文本的正确理解和体味为前提。任何严肃的作家实际上都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他必须直面人生,细心地体察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把握历史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他又必须将这些体验转移到有独创性的想象情景中去,在语言的调遣中深化他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和叩问,进而在诗的话语中艺术地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阐释。因而,文学文本不仅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与体验的载体,而且还包含着作家所发现的、被人们日常经验所忽略了的东西。没有对文学文本的深刻理解和体味,便没有对文学作品中的社会生活图景与“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恩格斯语)的正确把握,从而也便没有对文学作品的价值的正确评判。休谟的一段话说得很好:“我们在评论任何重要作品之前,应该永不例外地把它一读再读,仔细地全神贯注地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观察。初读任何作品,心情上总不免有些忙乱,从而使对美的真实感受到干扰。我们会看不到各部分中间的联系,分辨不清风格变化的真正性质;不同的优缺点仿佛揉杂在一起,模糊地呈现在我们的想象力当中。”(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5集,第9页。)因此,严肃的批评家总是多次阅读作品再作判断。为了对拉萨尔的《济金根》做出准确的评判,恩格斯先后四次阅读了这个剧本。他先把作品读了两遍,获得了初步印象。为了检验自己的这种印象的正确性,他有意识地把剧本借给了别人,在停顿了一段时间之后再阅读它。经过这样多次阅读,剧本所留给自己的印象仍然与先前是一样的,这时他才放心地写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对于规模宏大的长篇小说,正如波兰现实主义作家普鲁斯所说:“在第一次阅读的时候,常常产生一种错综复杂和凌乱的感觉;它是一座‘森林’,在这座森林中有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细心的读者永远也看不见那座‘森林’,可是,一位有经验的批评家就必须发现和提出它的计划。否则的话,他就要变成一位只见树叶,不见树枝、树干和树茎的人那样。”(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5集,第9页。)然而有的评论家却往往并未认真阅读作品,即下笔千言,在贩弄西方文学批评术语中布下语码的迷魂阵,社会人生参照被这种语码的迷魂阵挤入了九霄云外。
文学评论的社会人生参照应以对社会人生的正确体悟和把握为基础。文学评论虽然以文学作品为直接对象,但却间接地、无可回避地指向着社会现实生活。事实上不仅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且文学评论也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认识和评价的一种特殊方式,它总是带着评论社会的性质。其使命以理性建构、价值判断或审美对象的解析为宗旨,其过程以审美接受为标志,但更多、更重要的是评论家把本人的认知体验、研究解析的成果交给读者。“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如果缺乏对社会人生的正确体悟和把握,评论家对作品文本的接受、认知和解析,将处于极浅的层次,何以鉴别作品是否正确地反映了“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何以鉴别作品是否表现了“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或者说何以鉴别作品内容的真与善,何以进行准确的价值判断。所以,评论家应有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眼力,有对社会的特殊敏感,应该熟悉他评论的作品所描绘的历史面貌和社会人生图景。如此,他才能正确地对作品进行社会人生参照,发掘出作品的内在意蕴,并做出科学的价值判断。
文学评论的社会人生参照应以科学的审美观为指导。艺术美建筑于对现实美的确认和超越,具有比现实美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的特性,是一种寓于某种有意味的形式中的、能体现人的自由精神和创造才能、创造智慧、创造品格以及思想感情等全面本质的具体可感的形象,一种与真和善相联系的、能引起人的爱悦感情和心智创造物。美在于真和善,在于“有意味的形式”(克乃夫·贝尔语)。不同的审美观有不同的真和善的标准,有不同的形式追求。只有科学的审美观,能够使评论家对于真和善的辨析,对于形式意味的体悟臻致于深刻和准确的境地,从而做出科学的价值判断。而审美观的科学性,说到底,取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科学性;审美观扭曲的根源应当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去寻找。所以,对于那些以丑为美、以恶为美、以肉感为美、以纵欲为美、以不受社会法律规范、道德规范的“自由”为美的评论家来说,首要的,恐怕在于使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健康化、科学化。
四
我们主张文学评论必须坚持社会人生参照,并不排斥对文学进行形式方面的分析。相反,我们认为对文学的形式分析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对于那些社会性因素极其淡薄的作品,如果用历史社会的方法就显得文不对题;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社会性因素浓重的作品,好的形式分析乃美学批评的题中之义,可以探及艺术结构的微妙之处,可以揭示艺术结构的特征和语言创新的境界。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的形式主义批评在我国大为流行,固然带来不少消极的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批评的领域,丰富了批评本身,使我国的文学批评变得丰富多采。普列汉诺夫说:“评论艺术作品——那就是说了解它的观念、评价它的形式。批评家应该既评判内容,也评判形式;他应该既是美学家,又是思想家。”(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文学理论译丛》1985年第1期。)这是不无道理的。
形式分析可以是文学评论的一种方式,但绝不是唯一方式。事实上不存在绝对的形式评论。即使是真正的形式评论也离不开社会人生参照。但是,有的评论家却将社会人生参照看作外在于文学评论的、绝不必要的东西。他们在评论实践中,往往从某种形式主义出发,或对那些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的作品给予认同,或对那些歪曲现实生活的作品大肆捧场,或为那些描写兽性、匪性、野性、非人性、反人性的行为和违背人的情感逻辑、心理逻辑的作品予以肯定……这样的形式主义批评只能把批评引向歧途,从而也把读者、作者引向歧途。我们必须反对我那种漠视、鄙视、拒斥文学评论的社会人生参照的倾向,在评论实践中,坚持社会人生参照,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评论论文; 社会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美学论文; 作家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