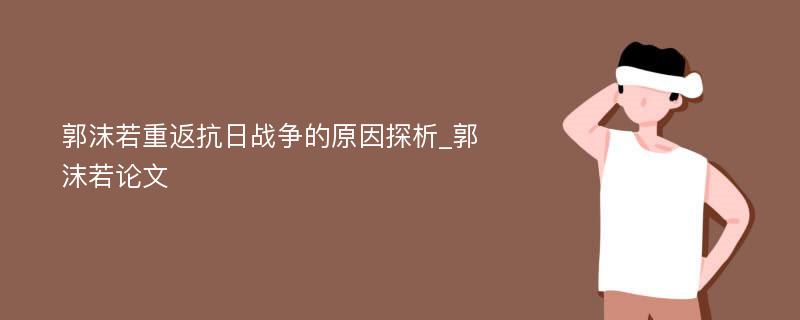
郭沫若归国抗战缘由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缘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问题的提出
就笔者所知,目前在认为共产党在郭沫若归国抗战问题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文章书籍当中,尤以沈鹏年先生的两篇文章写得最详细、最言之凿凿:
祖同亲口告诉我,他“为郭老归国问题从奔走联络到护送抵沪,是阿英的嘱咐和共产党的委托”。关于郭沫若—阿英—金祖同之间的密切关系,在三十年代出版的《秋窗集》(孔另境著)、四十年代出版的《风土小记》(金性尧著)以及最近出版的《阿英文集》和《阿英散文集》中得到印证。足见祖同所言非虚。①
1937年6月,郭沫若要金祖同回国代办一些事务。金与沈尹默谈了郭的归国问题。沈尹默表示:此事本来可托蔡元培和吴稚晖向蒋说情,但怕潘公展等党棍捣乱破坏,感到为难。金把原委告诉阿英后,阿英立即通过李克农报告周恩来。于是郭的归国问题才获解决。同年7月,周恩来、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在庐山继续谈判。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周恩来要求邵力子和陈布雷协助营救郭沫若归国。7月17日国民党收到《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不久蒋被迫宣布承认陕甘宁边区。7月20日,陈布雷的直接下级、侍从室第二处第六组秘书王芃生,指派赴日本搞情报的钱瘦铁,由金祖同陪同拜访郭沫若,商定郭归国的具体事项。7月23日王芃生电汇五百元给郭作安家费和归国之用。7月25日钱瘦铁护送郭上船。7月27日上午当郭沫若安抵上海时,陈布雷早已安排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在轮埠恭候。当天下午,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和司法院院长居正联名,发出宥字第547号对郭“取消通缉”的训令。②
根据这两篇文章提供的线索,笔者查阅了“郭沫若与阿英”、“周恩来与郭沫若”方面的文章,结果却大相径庭。阿英之女钱小惠是如此叙述此事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7月27日,郭沫若怀着强烈的爱国激情,在友人帮助下,历尽艰险,秘密搭轮来到上海。/父亲得到消息,第二天立即赶往沧州饭店看望,一别十年,如今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又见面,双方都十分的激动。”③该部分文字告诉我们,阿英与郭沫若归国关系不大,甚至可以说没有关系——阿英只是在得到消息后的第二天“赶往沧州饭店看望”郭沫若。关于“周恩来与郭沫若”的文章有24篇,除农伟雄先生的《周恩来和郭沫若休戚与共至终》④外,其他23篇⑤都未提及此事。既然沈先生的文章有如此错误,所以郭沫若归国抗战“共产党功不可没”这一主要观点不能不令人怀疑。
由于该问题主要涉及周恩来、陈布雷两个人,所以只要搞清楚他们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到郭沫若归国这段时间里的相关情况即可。
二 问题的考证
根据《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修订本)可以知道,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与陈布雷见面的时段可能有三个:1937年3月下旬、5月下旬末、7月13日(或14日)—7月18日,现在我们就来逐一考证。
1937年3月下旬
关于周恩来的情况为:
3月下旬 由于国共谈判问题已需同蒋介石直接商谈解决,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要求,飞抵上海。先同宋美龄会晤,将根据中共中央十五项谈判条件拟成的书面意见交宋,请她转交蒋介石。宋表示中共可以合法存在。周恩来在上海还同宋子文、蒋鼎文、东北抗日将领李杜等会晤。⑥
关于陈布雷的情况为:
二月十二由沪赴京,十五日举行三中全会,通过根绝赤祸决议案。……三月中旬由京回慈溪祝外舅杨先生八十寿,献寿言一篇,留慈二日仍返京。三月下旬由京赴杭,四月四日再至溪口助理蒋介卿先生丧事,为蒋公撰祭兄文。⑦
结合两段文字可以知道,3月下旬到杭州的周恩来与同在杭州的陈布雷存在着见面的可能性。遗憾的是,这种可能性目前找不到其他任何材料证明——包括陈布雷日记。
至于郁达夫1937年5月18日给郭沫若写信的“历史背景”,郁达夫在当天的信件中有非常清楚的说明:
前月底(按:具体时间为4月30日至5月4日),我曾去杭州,即与当局诸公会谈此事,令妹婿胡灼三,亦亟亟以此事为属,殊不知不待伊言,我在去年年底返国时,已在进行也。此事之与有力者,为敝东陈公洽主席,及宣传部长邵力子先生,何廉处长,钱大钧主任,他们均系为进言者。我在前两月函中,已略告一二,因事未成熟,所以不敢直告。大约此函到后,南京之电汇,总也可到,即请马上动身,先来上海。⑧
从该信可以看出,郁达夫1937年5月18日给郭沫若写信的“历史背景”与沈先生的说法大相径庭:为了郭沫若归国事,郁达夫曾前往杭州“与当局诸公会谈此事”;在陈仪、何廉、钱大钧等人斡旋下,蒋介石才同意郭沫若归国。
5月下旬末
关于周恩来的情况为:
5月下旬末 飞上海。在上海、南京停留的数天内,同各方人士谈话,争取中共的合法地位,并酝酿筹办宣传抗日的刊物。同时还会见了中共在上海的部分秘密党员。
6月4日 抵庐山。⑨
关于陈布雷的情况为:
五月二十日回京,病体仍未痊愈,蒋公闻之,命续假在京静养,以杨济民医生之劝,至鼓楼医院检验身体,知贫血已甚,乃购肝脏制剂饮服且注射焉,疗养匝月,效果殊尠。⑩
结合这两部分文字可以知道,五月下旬末,尽管周恩来在南京“停留”了数天,但他不可能与同在南京的陈布雷见面,因为陈布雷此时正在“静养”期间,不便打扰。
根据以下文字可以知道,周恩来不但1937年5月下旬末没有与陈布雷见面,就是3月下旬也没有与陈布雷见面:
陈布雷过去是听说过这个传奇人物的,这次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和林伯渠、秦邦宪等秘密到了南京,准备商议国共合作抗日事宜。传说中周恩来那雍容、大方、睿智的政治家风度,颇使陈布雷折服。陈布雷很想一亲周的风采。(11)
这段文字首先出现在王泰栋的《蒋介石的国策顾问——陈布雷外史》中,第二、三次出现在《陈布雷传》、《陈布雷大传》时一字未改,第四次出现在《找寻真实的陈布雷——陈布雷日记解读》时少了“那雍容、大方、睿智的政治家风度”中的“那”字,将“一亲周的风采”改成了“一见周的风采”。(12)由此可知王泰栋对该说法深信不疑。(13)尽管王泰栋在前三部传记作品中都认为郭沫若归国抗战共产党功不可没(14),但是他也认为一直到1937年7月初陈布雷都没有与周恩来见面——该段文字是在叙述陈布雷1937年7月初上庐山后的情况时插叙的。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直到1937年7月初,周恩来都没有与陈布雷见面,因而也没有机会委托陈布雷向蒋介石进言。
是否存在这种可能呢?尽管周恩来与陈布雷没有见面,但是他通过其他人请陈布雷向蒋介石进言。这种可能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首先,周恩来到南方谈判是为了解决有关中国命运的国共合作这样重大的问题,相对该问题而言,郭沫若归国问题不值一提;其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周恩来还通过其他人请陈布雷向蒋介石进言允许郭沫若归国,说明周恩来对郭沫若归国问题极其重视,既然重视到如此程度,便不可能通过其他人转达;其三,郭沫若1928年到日本后,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脱离了关系,此时的周恩来对郭沫若不可能有多么深刻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做事谨慎的周恩来不可能为了郭沫若归国问题而影响正在艰难进行的国共谈判;其四,在国共谈判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如果还这样做,很可能会引起人们猜疑,以为郭沫若在共产党内是多么重要的人物,效果完全可能适得其反。
7月13日(或14日)—7月18日
关于周恩来的情况为:
7月13日(或14日) 和博古、林伯渠到庐山。随即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7月14日 会见张冲。张说,蒋介石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十五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说“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指出蒋介石上述要求同六月庐山谈判所谈“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7月17日 洛甫、毛泽东致电叶剑英转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从大局出发,在谈判中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机关可以承认平时设政训处指挥,朱德为正主任,彭德怀为副主任。但战时不能不设军事指挥部,以资统帅。
7月18日 将所拟关于谈判的十二条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蒋介石。意见的主要内容有:应许各报刊载《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中央发出书面谈话表示赞同;迅速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担任正职,由林伯渠任副职,其范围包括现在所辖十八县,其疆界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边区政府划定;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闽粤赣、湘鄂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允许中共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在全国发行;对红军改编的具体意见。由于蒋介石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指挥机关,使谈判陷于僵局。
△离庐山,赴上海。(15)
关于陈布雷的情况为:
陈布雷是7月3日上庐山的,他住在牯岭路54号,隔壁就是谈话会的招待所,来访他的客人经常满座。
……第二期谈话会是在7月28日开幕的,陈布雷再也呆不住了,带着王允默回到南京。(16)
由此可知,周恩来在庐山期间,陈布雷一直在庐山。从地理位置上说,周恩来有条件与陈布雷见面,并请他为郭沫若归国事向蒋介石进言。不过,看看笔者引自《周恩来年谱》中的相关文字便可知道,这种情况不可能存在:一、根据蒋介石“仍不允许中共公开活动”可以知道,周恩来等人在庐山的活动是受限制的,他们不可能随便去拜访国民党要员——包括陈布雷;二、在“华北炮火正浓”的情况下,周恩来希望“迅速解决”的是“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这样重大而急迫的“国内问题”,而不是郭沫若归国问题。如果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还在为郭沫若归国问题操心,那么只能说他太不识时务、太不分轻重缓急了。
那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到底是谁帮助郭沫若归国的呢?对此,可信度很高的《郭沫若归国秘记》(17)有非常详细的叙述。其大致情况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跟从郭沫若学习甲金文的金祖同前来拜访,发现郭沫若心系祖国,并且处境危险,于是动员郭沫若归国。郭沫若“很赞成”金祖同的话,“不过他的脸上还露着一些难堪的表情”:“他的踌躇是他走后他的家庭生活很成问题,而且自己能否平安地离开这里,一时那里有把握?”尽管如此,郭沫若还是写了一张《遗言》给金祖同,“以为万一他不能脱身而遇到了意外危险的时候,我可以把这篇东西替他在国内发表”。金祖同将此《遗言》给了时在日本的金石篆刻名家钱瘦铁,钱瘦铁将其寄给了国内的王芃生。(17)7月24日晨,钱瘦铁告诉金祖同:“王○○已有电报来了,并且汇来五百元旅费”。7月25日,在钱瘦铁护送下,郭沫若与金祖同一道前往神户,下午五点过平安登上加拿大公司的“日本皇后号”。7月27日下午,郭沫若、金祖同到达上海,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前来迎接:“我们才踏上了埠头,在人丛中骞〔蓦〕地走出两个人来,其中的一个拍着鼎堂的肩儿在轻轻地照呼……”(19)根据以上文字可以知道,“七七事变”后,帮助郭沫若归国的人有两类:一是郭沫若友人,如金祖同,二是为国民政府效力的人,如钱瘦铁、王芃生、何廉等,他们都与共产党没有关系。并且,从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上说,是钱瘦铁将郭沫若的《遗言》寄给王芃生,然后王芃生寄来500元旅费,而不是王芃生“指派赴日本搞情报的钱瘦铁,由金祖同陪同拜访郭沫若,商定郭归国的具体事项”。
三 结论
如何看待金祖同“亲口”对沈先生说的话呢?首先,笔者向来对死无对证的话持怀疑态度——根据考证可以知道,笔者的怀疑不无道理。其次,即使金祖同的话属实,我们也不能说郭沫若归国抗战“共产党功不可没”:如果没有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福建省主席兼驻闽绥靖主任陈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群等人向蒋介石进言,不管是“阿英的嘱咐和共产党的委托”,还是“周恩来同志斗争”,都不起作用。并且,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周恩来可能会不顾国共合作这一急事、大事而为郭沫若归国的事情“斗争”吗?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要求(引者按:应改为‘请求’才合乎实际情况)邵力子和陈布雷协助营救郭沫若归国”!阿英则只能“通过李克农、刘少农等同志及时地向周恩来同志报告和请示”!金祖同更只有跑腿的分!所以,郭沫若归国抗战“共产党功不可没”的说法至少是夸大其辞。更重要的是,根据现有资料可以知道,与周恩来、李克农、阿英等有关的说法都找不到其他证据。
沈先生在文章中如此写道:“罗素说得好,‘除非历史学家尽最大努力来保持对事实的忠实,否则历史就不值得称赞。’这个问题似乎更应引起治史者深思。”对此,笔者深表赞同。笔者想补充的是:知道罗素的话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将罗素的话贯彻到治史过程中,哪怕为此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等,甚至为此牺牲宝贵的名誉、友谊、生命等!
注释:
①沈鹏年:《郭沫若归国问题补正》,《行云流水记往(上)》,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76~177页。
②沈鹏年:《共产党功不可没——再论郭沫若的归国问题》,《行云流水记往(上)》,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83~184页。
③钱小惠:《两个“臭老九”——郭沫若和阿英的革命友谊》,《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1期。
④农伟雄:《周恩来和郭沫若休戚与共至终》,《文史春秋》1996年第2期。内云:“当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全面入侵我国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党第二次统一战线促成了。由于周恩来在国民党上层卓有成效的工作,南京国民政府终于被迫取消1927年对郭沫若的通缉令,允许他秘密回国,参加全民族抗日战争。”
⑤按发表或出版时间先后顺序为:《领导、战友、知音——怀念周恩来与郭沫若同志》(张颖,《光明日报》1980年1月27日。收入《相遇贵相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党外人士交朋友的故事》第1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128页;《思情日月长——文艺家的挚友周恩来》,张颖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第72~84页)、《周总理和郭老的友谊》(王廷芳,《文汇报》1986年1月8日)、《周恩来和郭沫若情深意长》(《武汉文史资料》1986年第4辑)、《周恩来与郭沫若》(李畅培,《重庆党史研究资料、南方局党史资料合刊》1988年第1期,《郭沫若研究》第8辑转载。收入《周恩来研究文集》,国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176页;《巴渝文化》第1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23~139页;《周恩来》,肖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0~53页)、《周恩来与郭沫若》(李凤梧主编,《中国现代伟人的家事》,明天出版社1990年版,第220~223页)、《半个世纪的革命友谊——周恩来与郭沫若》(《领导·同志·良师·益友——广交朋友的周恩来》,郑毅涛主编,红旗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6页;1996年版,第24~34页)、《郭沫若与周恩来》(张毓茂,《辽宁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收入《阳光地带的梦——郭沫若的性格与风格》,张毓茂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290页)、《知音——周恩来同郭沫若的交往》(许虔东,《党史纵横》1993年第1期)、《郭沫若紧随周恩来五十载》(魏奕雄,《中华英才》1994年第1期,《科技文萃》1994年第6期转载)、《“疾风知劲草 岁寒见后凋”——周恩来与郭沫若》(曹应旺,《伟人诗交》,曹应旺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175页;《周恩来珍闻·上》,李新芝、刘晴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09~319页;《高端协力中的周恩来》,曹应旺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4~226页;《党史博采》(上半月刊纪实版)2008年第3期)、《半个世纪的革命友谊——记周恩来同志与郭沫若》(郑毅涛、郑宇,《中州统战》1995年第3期)、《郭沫若与周恩来》(魏奕雄,《名人传记》1996年第2期。收入《人民总理周恩来·下》,郭思敏主编,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6~2169页)、《领导、战友和知音——周恩来和郭沫若》(赵长盛编,《周恩来和党外朋友们》,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158页)、《“疾风知劲草 岁寒见后凋”——周恩来与郭沫若的友谊》(秦川,《郭沫若学刊》1998年第1期)、《周恩来——郭沫若的良师益友》(蔡宗隽,《郭沫若学刊》1998年第1期)、《亲密无间:周恩来与郭沫若》(舒以主编,《百年恩来·上》,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709~714页)、《周恩来与郭沫若》(李培栋,《大江南北》1998年第10期)、《历史巨变中的周恩来和郭沫若》(穆欣,《中共党史资料》第73辑,2000年3月。收入《历史巨变中的周恩来》,穆欣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68~299页)、《“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周恩来与郭沫若》(靳希光著,《周恩来与文艺界名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郭沫若与周恩来的交往和友谊》(张荣久,《文史春秋》2003年第1期、《山西老年》2007年第1期)、《忠诚与日同辉耀 天不能死地难埋——周恩来与郭沫若半个世纪的情谊》(张宗高,《党史纵横》2004年第2期)、《周恩来与郭沫若的一世情意》(季克良、郭坤亮著,《周恩来与国酒茅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195页)、《带着大家前进的向导——周恩来与郭沫若》(赵朕、王一心著,《文化人的人情脉络》,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299页)。也许是因为沈先生的两篇文章都发表在影响很小的南京《爱国报》上,否则,向来喜欢攀龙附凤的中国人完全可能为了渲染郭沫若与周恩来的亲密关系而将沈先生的观点添油加醋地写进与“周恩来与郭沫若”有关的文章中去。现在,沈先生的文章结集出版了,看见的人一定会多起来,若不及时正本清源,谁敢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发生呢?
⑥⑨(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367、373、379~380页。
⑦⑩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台南)王家出版社1989年版,第166~167、167页。
⑧《致郭沫若》,《郁达夫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页。
(11)王泰栋:《蒋介石的国策顾问——陈布雷外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王泰栋:《陈布雷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王泰栋:《陈布雷大传》,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
(12)(16)王泰栋:《找寻真实的陈布雷——陈布雷日记解读》,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130~132页。
(13)尽管笔者对王泰栋这四部传记作品中的不少说法持怀疑态度,对该说法却是相信的:在这四部作品中,后两部作品是作者看了陈布雷日记后写的。如果陈布雷日记中记载了他与周恩来见面的内容,王泰栋绝对会大肆渲染,而不是秘而不宣。
(14)王泰栋在《找寻真实的陈布雷——陈布雷日记解读》(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中已不提此事。
(17)留日学者武继平经过考证核实后认为:“金祖同在《郭沫若归国秘记》中涉及的人名、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等除了偶有记忆错误之外,并无半点虚构。”(武继平:《“日支人民战线”谍报网的破获与日本警方对郭沫若监视的史实》,《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1期)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金祖同的《郭沫若归国秘记》尽管有个别错误,可信度却很高。
(18)钱瘦铁为“日支人民战线”中方核心成员,王芃生1936年底回国前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参事。
(19)殷尘(金祖同):《郭沫若归国秘记》,(上海)言行社1945年版,第1~173页。
标签:郭沫若论文; 陈布雷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周恩来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遗言论文; 庐山论文; 历史学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