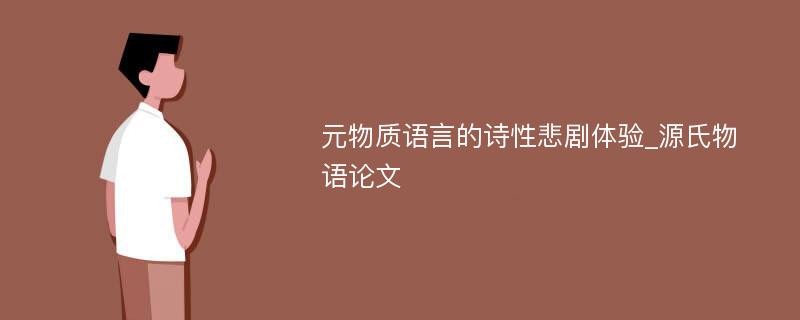
《源氏物语》的诗化悲剧体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氏物语论文,的诗论文,悲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1999)03-0056-07
国别文学的研究者往往只关注于自己所从事研究的国别文学,并不关心世界文学之中的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当把日本文学置于世界文学之中进行考察时,遇到的问题是世界文学之中往往没有日本文学,当然这是指西方学者眼中的世界文学。日本学者们对此也不无感触,日本的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土居光知就有感于此,提倡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研究日本文学。二战以后日本日益受到重视,翻译介绍的作品也不少。吉田精一在东京大学开创文化交流研究时,他就说:“所谓文化交流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名词,然而我认为某种意义上通过日本人的眼睛,客观地审视包括东方在内的世界文学,审视的基点是把日本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而这一基点使日本处于最为有利、最为适切的位置。”[1] 把日本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实则就是把世界文学作为整个日本文学的背景去审视,同时保持清醒的东亚文学的视角。这时会遇到的不单单是日本悲剧文学的悲剧性问题,而且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日本悲剧文学的自身价值的特质。
一
日本文学置于世界文学背景之时,具有极其鲜明的民族独特性,这便是阴柔美。当然阴柔美不是日本文学的全部特性,但它是日本文学之所以成为日本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阴柔美的日本文学缺少中国文学或欧美文学所具有的宏伟瑰丽的想象世界,那种巨大力量之间的尖锐冲突。这种冲突的不可解决大多建立在非日常性的生活表现,把生活中的重大灾难推向极端,使主人公只能走向悲剧的结局。在表现这种超日常性灾难时,又以种种文学手法渲染、夸张,使读者强烈地意识到灾难的悲惨性。《窦娥冤》、《桃花扇》、《李尔王》、《麦克白》等等都是如此。然而在日本文学之中很难看到这种现象,它所表现的往往是细小的场面,细腻的情感,微观的物象,瞬间的感悟,从中流淌出的是日本文学所特有的淡淡哀伤,绵绵愁绪,还有稍纵即逝的恬淡喜悦。它所表现的都是趋于平静的感情,难得体味到冲突的对抗性和激烈性。即使写到重大灾难、尖锐冲突,也要回避正面描写,或者使之淡化,表现出幽远枯淡的美感。如此看来日本文学的这种阴柔的性质,似乎与悲剧格格不入,不易产生悲剧文学。
《源氏物语》可以说是这种阴柔美的最好典范,然而很少有人把《源氏物语》当作悲剧来看,即使把它作为悲剧来看也仅仅是最低层次的悲剧。其原因无外乎就是我们在作品之中意识不到悲剧不可解决的冲突,在作品之中流动的体验流虽然有悲哀,但是这种悲哀尚不足以成为悲剧。《源氏物语》的第一卷《桐壶》是整部作品的引子,写了桐壶更衣倍受皇上宠爱,最终悒郁而死。此后天皇又找到与桐壶长相极其相似的藤壶,然后藤壶又开始走上了充满悲哀的路。虽然这一卷里桐壶之死是极为悲惨的事情,但是紫式部没有正面描写桐壶与身份高贵的后妃之间的较量,也没有直接写出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只是写了她孤独、焦虑、恐惧等等。桐壶虽然深受皇上喜爱,但她并没有因此而不孤独、焦虑和恐惧,相反皇上越是对其爱得深切,她就越觉得恐惧、焦虑、孤独,终于怀着无限恐惧和孤独而死去。然而紫式部也没有直接写桐壶的死,而只是以“家人哭诉”、“使者垂头丧气”带过。接受者把物语中的其他描写都纳入孤独、焦虑的体验之中,作为孤独、焦虑体验的材料。比如嫔妃们对她的种种恶行,虽然这些描写不是直接描绘桐壶的孤独,然而在构造孤独体验时却成了主要材料之一。桐壶死后,深秋黄昏,皇上的枯坐凝思,寒气侵肤;桐壶娘家的庭草荒芜,花木凋零,无不成为孤独体验所构造的意象,随着意象的换移,孤独、焦虑的体验在文中流动。这里没有描绘多少情节发展,情节的发展是作为情感表现的辅助而处理,也就是说情节的发展退隐到次要地位,成为情感的背景,情节的发展也往往不是以情节的冲突作为其内在动力,情节发展缺少情节本身所具有的那种逻辑性。在情节退为次要地位时,紫式部重视的是情感的意象,着力营造出诗的意境,或者说情节的发展只是为创造诗的意象提供一条线索,使种种意境流动转换,同时也表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内心世界的活动与外界世界成了互动的流动过程。因此《源氏物语》应当称之为是诗化小说。在这样的诗化小说之中,虽然可以体验出焦虑、恐惧、怜悯等形式,但是与突出情节发展的作品相比较,在恐惧、焦虑、孤独等体验之中,很难意识到情节发展的冲突性。作品的文字可能使用极富感情色彩的语言,同时夹以诗作,但接受者始终是在较为平静的心态之中接受作品的情感,从而体验所构造的也是淡淡的体验流。
《桐壶》卷和白居易的《长恨歌》之间的关系为人熟知,《桐壶》是以《长恨歌》为基础进行变异和创造的。对于相近的内容,中日两国文学家的处理是不同的。《长恨歌》是一首叙事性的诗,其中也流动着悲剧体验流,在诗开始之后很快就进入了悲剧体验流。先是焦虑和不安的体验,诗描绘了杨贵妃的美貌和李杨爱情,但这爱情很快就被构造为焦虑,因为爱情使得唐玄宗整日沉迷,以至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杨贵妃的美貌尽管能使“六宫粉黛无颜色”,但越是美貌就越使唐玄宗不问政事,这种冲突显然成为焦虑体验形式的内容。当然如果只把李杨爱情作为荒淫生活来写,那么就不可能被构造为焦虑,这里肯定爱情,只是爱情本身产生了负作用。如果他们爱到不与政治冲突的程度,他们的爱情则不够浓烈,他们的爱情的狂热程度与政治的昌明,构成了二律背反的冲突,从而显现为焦虑。随后这种焦虑变成了恐惧,“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种恐惧在加强,直至杨贵妃的死。唐明皇在失去杨贵妃和皇位之后的孤独体验,则完全由爱情的追思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构造而成。“夕殿萤飞思翩然,孤灯挑尽未成眠”。道士从蓬莱仙境拿回钿合金钗,但是那种孤独体验不是减轻而是更加浓厚了。最后虽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但也不能不“此恨绵绵无绝期”。这种绵绵之恨恐怕是无限的爱和无尽的孤独。
《桐壶》与《长恨歌》都可以显现于悲剧体验流中,但是由于作品表现方式不同也使体验流的形式有所不同。前者是没有情节的戏剧性冲突,悲剧体验流的内容也就很少情节成份,没有戏剧性的情节冲突,也使悲剧体验流显得平淡,不易使人意识到其悲剧性。桐壶的人生之中没有戏剧性的突变,她生活于悲剧体验流之中,最终在悲剧体验流中死去。她的悲剧体验流是在日常生活之中绵绵流动。天皇也把她的生活构造为悲剧体验流,同样也不是以情节的冲突构造体验流的。杨贵妃与唐明皇则不同,他们在没有突变时,并没有把他们的生活本身构造为悲剧体验流,并生存于悲剧体验流之中。发生突变之后,唐明皇不能不把自己投入悲剧体验流。尽管如此,它的悲剧体验流是强烈的,具有极强的悲剧性,而不是《桐壶》那样流淌着淡淡的哀伤。《长恨歌》的情节具有传奇性,陈鸿将它写成唐传奇《长恨歌传》。传奇的特点就是情节的传奇性,也就是说重视情节的发展变化,情节的戏剧冲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悲剧所以能使人惊心动魄,主要靠‘突转’与‘发现’。”[2]亚里士多德这段论述, 不能认为是适合于所有悲剧,但它却概括了部分古希腊悲剧情节的特点。《安德洛玛克》、《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作品都是以逆转作为推进悲剧的方式。
在《桐壶》之中已经看到悲剧体验流的形式不同于中国或西方悲剧,表现出一种后者没有的日常性。如果从小说的整体来看体验流的平淡性更加明显,紫式部把这种体验流的平淡性和情节的日常性,在源氏登场以后的物语发展过程中一直贯行到最后。源氏一生不断地追求女人,从一个女人到另一个女人。有的时候是追求一个女人构成一个独立的故事,有的时候则是写对几个女人的追逐。源氏在不断追逐女人的时候,时时流出淡淡的哀伤,从一种哀伤又落入另一种哀伤。哀伤由排遣不尽的孤独、焦虑、怜悯、恐惧等体验构成。源氏与女人的关系之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就是他和后母藤壶之间产生的恋情和通奸关系,这一关系时时落入焦虑、孤独、恐惧的体验,欲见藤壶而又不得的焦虑,思念藤壶而难以排遣的孤独,深爱藤壶而又触犯人伦至极的恐惧。这些对整个作品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紫式部却没有把这些体验放在这种极其可怖、超出日常的情节中去写,而是把源氏与藤壶的通奸情节完全隐去,只是在相关的情节中暗示他们的通奸行为。这样把源氏的悲剧体验完全在日常化的生活中进行表现,把极其恐惧的体验也日常化,从而使冲突在极为平淡的悲剧体验中显现出来,也就是以平面化的悲剧体验构造作品的冲突。源氏追求空禅而不得,空禅后来将随丈夫离开京城,这时源氏不胜感叹。其实这时源氏正在深爱着桐壶、紫上等人,其中自然流出悲剧体验,但是与空禅之间产生的孤独、焦虑等体验材料,与其他女人之间的体验材料没有直接关系,使新的体验没能成为原来体验的绵延,这样就成了一个独立的体验材料。
今日适值立冬,天公似欲向人明示,降了一番时雨,景象清幽沉寂。源氏公子镇曰沉思遐想,独自吟道:
秋尽初冬人寂寂,
生离死别雨茫茫。[3]
这一段文字表现的自然意象,被体验构造为孤独,就是源氏在空禅离去时的体验。然而它同源氏与其他女人恋爱时的悲剧体验没有关系。
首先,《源氏物语》的体验流在一个层面上流动,没有随着情节的发展深化,也没有强化。始终在较为平静的状态下流动,这种流动没有情节的动力,体验流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物的活动显现出来,并把作品的内容显现出来而已。体验流的这种平面化是与情节的并列性相关的。每一个故事都是独立的,《源氏物语》虽然是长篇小说,但却是很多短篇故事贯穿构成了整个物语。这种结构与体验流很难让人把它作为悲剧来看。因为每一个相对独立的故事使体验流不断流动,但同时又不断地破坏体验深刻化的可能性,使体验流总是达不到悲剧所应有的深度。在还没有达到悲剧深度之前,由于故事的转换,使体验流又在同一个层次上重新开始,这种体验流总是在同一层次中流动,构成无始无终的流动。其次,《源氏物语》的体验流虽然在流动,但是它没有节奏感,没有速度的变化,始终以相同的速度在流淌,当然也就没有狂涛巨浪,没有暴风骤雨,没有悲剧作品中常见的紧张感。虽然有很多地方都会流出悲剧的孤独,然而很多孤独体验之间没有逻辑联系。孤独等体验的流动没有其前后的必然性,各种悲剧体验在各不相干的情况下机械地依次显现。这就使人觉得虽然体验在流动,但并不使人觉得在流动,仿佛处于静止状态。因此这种作品不易被人觉察到作品的悲剧性。其三,紫式部显然在追求着一种淡淡的体验表现,那么这种结构最适于表现淡淡的体验流,也具有典型的日本文学所具有的“哀怜”美。各种悲剧体验以内在的必然联系构成一体的形式,不适于日本哀怜美。本居宣长虽然认为《源氏物语》表现的是物哀美,实际上物哀在物语之中只出现过十几次而已,更多的是“あわれ”。久松潜一认为“平安时代的‘あわれ’大体是表示感动之意,同时又表现出和谐的美,在和谐之中感到‘あわれ’”[4]悲剧不可解决的冲突, 在作为情节冲突形式时往往是破坏和谐,而和谐则要把冲突调和,从而呈现平静状态,显然悲剧的不可解决冲突与紫式部所追求的美学理念相悖。如果说《源氏物语》是悲剧的话,那么它只能是和谐悲剧。哀怜从形式上说是和谐的优美,从内容上说虽然它含多种情感,但更多的是悲哀,而悲哀又似乎是冲突的体验构造形式。这里存在一个矛盾,即和谐与悲哀相背离。实际上哀怜的悲哀一般是指无缘无故的哀伤,是来无踪、去无迹的哀伤。如果是具有必然内在联系的哀伤,那将不会是莫名的哀伤。只有如同行云流水的哀伤,才适于和谐的哀怜。因此哀怜似乎没有冲突,即使有冲突也只能是看不见的冲突。
二
然而这种美学理想是否构成悲剧美呢?《源氏物语》淡淡的体验流在同一个平面上流动,表面看来是悲剧体验流所构造的内容是源氏与诸多女人之间发生的细枝末节的小事。但是这个平面的体验流下面还有一个垂直纵深的深层体验流,深层体验流以平面体验流为其浅表,它所显现的是生命的意识。在它的孤独、焦虑、恐惧、怜悯等体验中显现的是生命的流转、宿世的哀叹、死亡的阴影、病态的灵魂。源氏的生活主要是追求女性,由此表现出源氏的好色。他不仅爱着自己的后母,也爱着作为养女的紫上。源氏对他们的爱不能不说深挚而真诚,但是他的爱心并不停留于这世上无双的美人,又不断地寻找其他的女人,这里似乎表现了充分的好色。源氏的孤独、恐惧、焦虑等体验都由爱欲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构成。这是平面的体验流。然而源氏的好色不应仅仅作为好色来看,好色之中有着深刻的冲突。源氏每爱上一个女人,或者与一个女人的分别,都看成是宿世所定,是前世已经安排而不可抗拒和避免。也就是说他注定了要爱上某个女人,同时也注定了他会与另外一个女人相遇,并发生关系。当然在当时日本社会还没有建立起来一夫一妻制度,那种好色行为并非完全受到社会的禁止,好色也常成为风流雅致的标志。尽管如此,他的好色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责难,源氏自己也为此产生了种种罪恶感。他常常倍加小心,对社会舆论、自己的妻子都有所顾忌。但是他仍然抑制不住地去爱其他女人。每每与女人相爱,时常会以宿世二字解释两人的关系。这就是说源氏的爱情注定了不可能停留在一个女人身上,必然会不断地流转。这种爱的情感的流转,实则就是无常。源氏本人虽然对追逐女人有所顾忌,有时甚至想到果报的恶果。但是爱心本为不能常住之物,源氏也必然不断追花逐蝶。表面上是好色,实际上则是无常。源氏追逐着女人,然而却不知晓真正原因,而这是一种深刻的虚无,这是现实的爱心与无常之间的冲突。爱情的无常流转正是人世与生命的无常。源氏真心爱着女人,不过也常常为无常世界所哀叹。爱的追逐之中体验到了生命的无根漂浮状态。这正是紫式部在源氏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源氏作为她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他华美绝伦,精通六艺,才智超绝;另一方面又写他与众多女人的淫荡关系,与宫中老女官发生性关系,与有夫之妇相爱,甚至与后母通奸,害死夕颜,简直污浊不堪,难以入目。他常常陷入恐惧、焦虑之中:
僧都为公子讲述人世无常之理,以及来世果报之事。源氏想起自己所犯种种罪过,不胜恐惧,觉得心中充塞卑鄙无聊之事,此生将永远为此而忧愁苦恨何来世,不知将受何等残酷的果报!想到这里他也欲模仿这僧都入山修行了。然而傍晚所见那女孩的面影,历历在心,恋恋不忘。[3]
连源氏本人都为自己的丑行感到恐惧和颤粟,但是他居然会成为理想的男性形象,这实在是费解。其实紫式部是从无常观来解释当时社会男女关系的无奈现实,也解释源氏的好色行为。好色并非因为源氏这个完美无缺的人物的缺陷,而是现世与生命本是一个无常之物,否则又如何理解源氏这个绝对完美人物身上不可饶恕的罪恶呢?源氏本人也在这无常的现世里,挣扎在孤独、焦虑、恐惧的体验之中。欲望是瞬间生灭的无常之物,无常又是现世的不可解决的冲突,人不可能从无常之中解脱出来。在不可挣脱的无常之中,人完全处于无助状态,不能自救,也不能他救,这是人类生命最深刻的孤独,在这种孤独之中显现的是生命的本质。现世的无常是如此痛苦,似乎应当投入到佛教的彼岸的常住世界,然而无常之中的常住并不是那么容易遁入的。朱雀院把女儿三公主托付给源氏,自己则遁入空门,试图从无常的痛苦世界中解脱出来。然而他仍然不能割断对三公主的牵挂,时时为三公主焦虑。他给紫姬的信中写道:“欲出红法心未绝,入山道上有魔障。”[3] 可见真正具有常住之心是非常不易的。这是宿世与无常内容之一。其二,宿世的一个主要内容便是因果报应,生命的轮回。源氏与后母通奸,其因果报应形式则表现为柏木与三公主通奸而生下薰,罪恶使自己遭应到相同的恶运。当冷泉帝从一个老僧人处得知自己的出生秘密,是源氏与母亲通奸而生之后,极度痛苦,陷入毁灭的体验,甚至想退位。面对宿命的轮回,完全处于无奈的悲哀,体验就把这种冲突构造为生命的孤独。
这里似乎没有悲剧的力度,也没有悲剧的崇高。那么是否可以由此认为《源氏物语》是一部哀情剧呢?美学家帕克在分析哀情剧与悲剧之间的本质差异时说:“正如大部分人类生活都包含着悲剧,因为它培养了一种力量去迎接它的危险一样,人类生活也包含着哀情剧,因为它少在任何时候都进行反抗,常常要屈服,受到摧残,毫无希望。”[5] 帕克运用这种理论进而认为左拉的《小酒店》虽然描写了主人公的悲惨生活,但是绮尔维丝并没有与自己的命运进行抗争,由此认为《小酒店》只能构成哀情剧。《源氏物语》也似乎更多是表现了哀情,而且“哀怜”成为整部作品的美学理想。据日本一位专家统计,整部作品一共用了1044个“哀”字。这样《源氏物语》很明显以“哀”作为作品的基调。如此说来《源氏物语》作为哀情剧来看是最恰切不过了,作品显现于孤独、焦虑、怜悯、恐惧等“哀情”体验流中,但是没有那种崇高。但是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第一、《源氏物语》虽然写了一些较为悲惨的事情,但作者还是力图回避直接写令人发生哀情的悲惨事件。这和《小酒店》描述绮尔维丝悲惨生活遭遇是不同的,源氏的一生虽然经历了流放的不幸经历,但总观他的生活是在荣华富贵之中度过,所表现的哀情不是与悲惨生活相关联的哀情。第二、《源氏物语》以哀情作为基本情感,确实没有崇高体验,但并不是没有与不可解决冲突进行不可抗争的抗争。例如源氏时时意识到宿世的不可抗争,为自己的罪恶而感颤栗,但他并不是完全没有试图超越和抗争。源氏一方面在好色的人生中不断追花逐蝶,另一方面又有遁入空门的冲动,想在遁入空门之中达到净土世界。这种遁入空门的冲动实际上是对好色生活的否定,也是试图从中超越出来的挣扎。然而这种对抗却没有被构造为崇高,原因是源氏所要抗争的并不是什么具体的事情,而是他的整个生命和人生。另外他的抗争形式就是直接走向佛教的形而上的世界,试图在那里找到生命的归宿。由于源氏的抗争并不是以自身的生命力量去征服宿命,而是以皈依佛教形而上学世界的方式逃遁,故此没有可能在崇高体验之中显现出来。源氏死去的一节《云隐》是空白,不知这一节是在流传之中失传,还是紫式部有意只用云隐这样的佛教词汇,来暗示源氏的人生终点。现世的浮华与佛教的皈依之间,始终没有取得调和,构成了作品不可解决的悲剧性冲突。这一心境是紫式部自己心灵世界的表现,她在日记中说虽然生活于富华的宫廷,而内心的孤独、焦虑始终不能排遣。
行幸之日已近,宫内又加修缮,更显华丽。……观览栽种各异菊花之情,正如古语所言,生出不知老衰退散何处之感。然不晓何缘人之忧思倍增,倘使命运适意些许,便索性跃跃欲试风流之好。寄身无常之世,纵有可见可闻可幸可喜之事,亦勾出常挂于心之出家遁世之念,此念弥深益烈,忧满之心,不由哀叹连连,悲苦不堪。处心积虑弃忘一切,却无论何等思虑全为徒然,故此罪孽愈深。夜去天晓,呆望池中水鸟浮游,悠哉无忧。
池中水鸟游浮世,
吾观此身寄无常。
观彼水鸟游乐无忧,然吾身若为水鸟,定将苦不堪言。[6]
紫式部的这一段日记,描绘了居身于富贵,内心却极其痛苦的心境。冲突没有解决,悲剧体验仍然在流动,仍有形而上的指向。然而这种冲突并不是在崇高体验中显现的,没有崇高体验,但仍然不失为悲剧。中国古代亦有相近的现象。陈洪绶所谓“怨谱”,吕天成所谓“苦境”,程瑛所谓“苦戏”,这类理论一方面是中国特有的悲剧理论,另一方面也概括了创作现象,这种理论可以说是一种泛悲剧理论,并没有严格区别悲剧与哀情剧、惨剧之间的区别。从创作现象来看有哀情剧或惨剧等,其中也有悲剧作品。
《源氏物语》的情节结构似乎不能构成悲剧,美国学者唐纳德·金(Donald Keene)曾认为日本小说“很多都是结构拙劣,一篇小说有几个几乎是独立的部分联缀而成,与此相关《源氏物语》就没有欧美小说概念的结构。”[7]《源氏物语》这样的结构方式, 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欧洲早期的小说形式流浪汉小说,流浪汉小说以流浪汉的经历为线索进行结构,故事的发展可能前后没有多大的关系。这种小说在欧洲是近代小说还没有产生发展时期的形式,被认为是小说尚未成熟的形态。那么能否也认为作为世界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源氏物语》的结构形式,是一种比较幼稚、拙劣的形式呢?是不是日本小说尚未成熟的标志?其实《源氏物语》是日本古典文学的成熟标志,它的结构虽然没有欧美小说戏剧的形式,但它是日本文学所特有的形式。这种形式最适于表现日本文学特有的美学理想,即哀怜、余情、幽玄等美学理念。即使到了近代文学时期,引进西方的悲剧、戏剧、小说理论之后,仍然被近代作家所应用,成为近代作家们广泛运用的形式。志贺直哉的《暗夜行路》、谷崎润一郎的《细雪》等作品也都以这种形式表现了主人公的命运,在淡淡的情绪表现之中流淌着悲剧的孤独、焦虑、怜悯、恐惧、毁灭等体验,以古典形式创造出了近现代的悲剧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