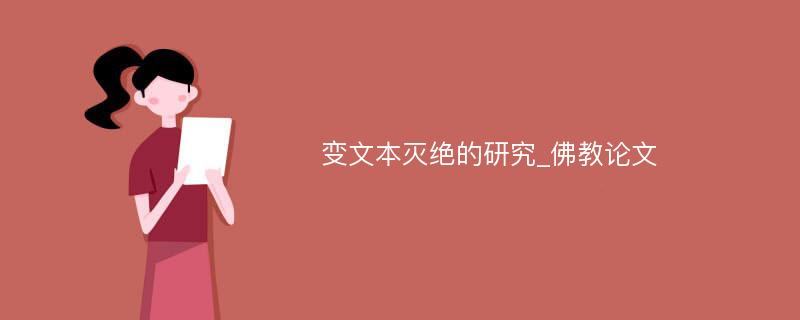
变文绝迹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唐一代通俗文学,最引人注目者,莫过于变文。从敦煌遗书重见天日之时起,变文就引起了文学研究工作者们莫大的兴趣,综观大半个世纪以来敦煌文学的研究历程,专家学者们对有关变文的一些问题,诸如概念的界定、起源、类别、体制、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及对后代的影响等,论述繁多,就中亦不乏真知灼见。然而,对于变文绝迹的问题却鲜有文章或专著提及。试想,变文一体既然在唐代曾经浩浩荡荡,蔚为大观,又为何会在突然之间便销声匿迹,不复流传?其原因自然非常复杂,因而值得深究之,其意义不仅在于敦煌文学研究方面,而且对于中国俗文学史研究以及文体史研究,亦有重大意义。
本文就此问题展开讨论。但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首先就本文所述的“变文”概念进行一个界定。变文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变文,指保存或仅存于敦煌遗书中的说唱类文学作品,包括讲经文、变文、因缘、押座文、解座文、词文、诗话、话本、故事赋等。而狭义的变文,则仅指唐五代时民间说唱伎艺“转变”的底本。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是变文在后代绝迹的原因,故凡不见于后代文学史中的诸种有关变文的说唱文体,均应包括在本文论述的范围之内。据此,本文论及的变文,当属广义的变文。
一
变文一体的成熟与勃兴,与佛教之东渐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汉到唐,中国的佛教逐渐进入繁荣与广大的时代,几个世纪中,由西土流传入汉的佛经渐次增多。这样,为了使更多的黎庶百姓了解佛教,将深奥的佛经通俗化便成了佛教僧徒宣扬其教义的当务之急。用以宣讲佛教经义的诸多通俗文艺形式也相应发展,变文就在此基础上得到发扬广大,成为影响广泛的一代通俗文学。然延至宋,由于统治者借鉴前朝佛教政策的得失,更注重佛教对世俗的影响,所以从开国伊始,中国的佛教就由唐末五代普遍流行于禅宗中的放任自然的出世风气,转向了辅佐王政的入世的道路。佛教的发展历程中政治因素的影响日益显著,统治者在宣扬佛教经义的时候,开始表现出强烈的选择性,以适应当时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他们有选择地发展和改造了佛教之中有利于其统治的种种要素,但也就是在这种“选择”中,变文以其“旁门左道”的罪名被无情槟弃了。这正是所谓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我们不妨从宋诸位帝王对待佛教的态度入手,对变文绝迹的社会原因进行一番考察。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开始。整个一部宋史,外部始终处于异族的觊觎和侵逼之下,辽、西夏、金、元、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大宋;内部则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封建王朝的危机日趋严重。作为对策,在政治上,赵宋统治者采取各种手段,空前加强中央集体权的君主专制,将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大权都集于君主一身;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汉以来的传统儒学也被改造成为“理学”,像二程、朱熹等道学家都希望通过节欲和修身,求得国泰民安,民族强盛。总之,所有的治世之策,都遵循着一个原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宋代佛教的发展也迥异于汉魏六朝与隋唐诸代,它没有了以前历代的大起大落,而是以平安稳定的步伐渐次前行。
从太祖至真宗三世,宋代佛教有一个长足的进展。太祖亲眼目睹了后周世宗禁佛带来的种种社会危机,所以建国初就下令停止禁佛,并度僧八千人,开了兴隆佛教之端绪。此后太宗、真宗均厚佛重法,度僧、修寺、广开译事。其中有两件在佛教文化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一是太祖开宝四年令高品、张从信到益州开雕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汉文木版印刷的《大藏经》,再是太宗七年设译经院,翻译佛籍二百八十四部,七百五十八卷。到仁宗和神宗时,兴隆佛教所带来的社会弊端日益明显,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批儒学之士公开排佛,佛教的发展开始受到了日渐严格的限制,但也只限于禁止异教邪说。宋代佛教唯一一次遭受打击是政和六年时,徽宗曾诏于道院,禁弃佛经;宣和元年又强制僧尼、寺院及佛菩萨等改为道教名号。然至翌年,徽宗又降诏自洗,恢复僧尼名号,大复天下僧尼,所以这次打击的波及面不大。南宋以往,历代君王多保护佛教,或度僧,或写经,或遣僧求法,佛教的发展走向平稳。总之,当权者们大多注意到佛教在民众中的影响,知道应该给它一个适当发展的条件,不过他们又决不佞佛,常常通过行政手段,借译经、印藏为名,严格控制佛教经典的滥传,防止其走向惑众之途,从而危害中央政权的安全。以译经为例:淳化五年(公元994年)译就的《大乘秘藏经》,被审查出“文义乖戾”65处,宋太宗以其“邪伪”,诏令当众焚毁。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译出的《频那夜迦经》,宋真宗因其宣扬“荤血之祀”有“厌诅之词”,禁止入藏,并不许再译类似经文[1]。由此我们联想到变文,对其绝迹的原因可推知一二。
早期的变文多是讲唱佛经的。这一点无可置疑。以俗讲为底本的讲经文,自不必说,以转变为底本的变文也是如此。敦煌遗书中的《八相变》、《降魔变文》、《破魔变》、《目连变文》等足可以证明这一点,然而到了后代,又出现了许多世俗题材的变文,如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舜子至孝变文》、《刘家太子变文》等。而根据郑振铎先生的推测,变文的绝迹当与此有关:
“非佛教故事的变文,今所见的也不少。为什么在僧寮里会讲唱非佛教的故事呢?大约当时宣传佛教的东西,已为听众所厌倦,开讲的僧侣们,为了增进听众的欢喜,为了要推陈出新,改变群众的视听,便开始采取民间所喜爱的故事来讲唱。……但后来也因为僧侣们愈说愈远。离开了宗教的劝诱的目的太远,便招来了一般士大夫乃至执政者们的妒视。到了宋代(真宗),变文的讲唱,便在一道禁令之下被根本地扑灭了”[2]。
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根据后来的研究,俗讲的讲唱艺人当然是僧侣了,而转变的讲唱艺人则除了僧侣外,还有世俗的妇女[3]。其二,郑先生说变文是在宋真宗时被禁,其依据不知为何。但根据南宋释志磬《佛祖统记》卷三十九引良渚在南宋理宗嘉熙年间所撰的《释门正统》中所言,变文的禁绝当在南宋理宗朝(公元1225—1264年):
“准国朝法令,诸以二宗经及非藏经所载不根经文传习惑众者,以左道论罪,二宗者,谓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语,病不服药、死则裸葬等。不根经文者,谓《佛佛吐恋师》、《佛说谛相》、《大小明王出世经》、《开元括地变文》、《齐天记》、《五来子曲》之类。”
关于变文绝迹之原因、时代,时人多以之为是。的确,抛开上述两个细节性的问题不谈,就上述一段话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变文绝迹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归之于政治。作为唐五代宋初推广佛教经典教义的大众化的通俗文艺形式,变文自然要合乎统治者的佛教文化政治政策,但无论是郑先生所言的“离宗教的劝诱的目的太远,便招来了一般士大夫的妒视”,还是良渚所言的“不根经文传习惑众”,究其根本,都是因为变文有违统治者们“淳风俗化万民”的兴国安邦的治国本要的缘故。在这种情势下,变文的被禁也是情理中的事了。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引前人之文证之。俗讲之事,唐时已盛。玄宗开元十九年,曾有《戒励僧尼敕》:
“近日僧尼,此风尤甚,因依讲话,眩惑闾阎,溪壑无厌,唯财是敛。津梁自坏,其教安施?无益于人,有蠹于俗。或出于州县,假托威权;或巡历村乡,恣行教化,因其聚会,便有宿宵,左道不常,异端斯起,自今以后,僧尼除讲律外,一切禁断”[4]。
又唐赵璘《因话录》卷四《角部》亦曾讲到唐代俗讲之情形:
“有文淑(溆)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抉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其甿庶易诱,释徒苟知真理及文义稍精者,亦甚嗤鄙之,近日庸僧以名系功德使,不惧台州府县,以士流好窥其所为,视衣冠过于仇雠。而淑僧最甚,前后杖背,流在边地数也。”
这里的举的虽是唐时的事例,然我们同样可以推此及彼。以有唐泱泱大国之宏大气魄与开阔胸襟,尚不能容忍这些“淫秽鄙亵”之词,以之为旁门左道,那么,宋代统治者对变文的明令禁止,自然也可以理解了。政治之于文学,影响之大,于此可见一斑。
二
至此,我们讨论了有关变文绝迹的社会原因,然而我们的论述却远远不能到此为止。一切文体的兴衰,不唯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亦关乎文体自身之素质,而且,就二者的作用而言,文体自身之缘由更应该居主导地位。变文的绝迹,大宋皇帝的明令禁止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然而我们若能从变文自身进行一番考察,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从今存的敦煌遗书来看,唐五代之变文洋洋大观,其题材之广、著作之丰,令人叹为观止。这些,时贤先达已作过不少详尽而又精辟的论述,兹不赘言。我要这里想说的,是作为唐五代民间通俗文学一种的变文,应该说已经走上了它生命的顶峰。当然,这里所说的“顶峰”,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顶峰,说变文在唐五代时已经发展到了成熟完美的境地,而是从相对的意义上说,后来的变文没有机会和可能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作出新的超越,所以唐五代变文便在变文的发展史上雄踞高峰。毕竟,这是一块文人们未曾涉足或极少涉足的田园。而文学的发展史告诉我们,诗词文赋戏曲小说,究其根本,尽在于民间,然而只有到了文人手中,这些文学形式才会逐渐趋于完美并大放异彩。变文失去这个条件,转过高峰自然便要走下坡路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对照另外一个问题进行思考:同是唐五代民间的通俗文学形式,歌辞能被当时乃至后来的文人们接受并且在宋代发扬广大,成为文苑一枝独秀,而变文却终被堙没,其原因何在?思量良久,认为原因如下:
(一)前文已经论及,早期变文的题材主要是敷衍讲唱佛经故事,宣扬禅门佛理,到宋,由于国难四伏,统治者虽然并隆儒佛,一般士人却注重强调忠孝节义的新儒学,即道学。程颢曾抨击佛学:“其术大概是绝伦类,世间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哪里去?又其迹须要出家,然则家者,不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处此等家,皆以为寄遇,故其为忠孝仁义者皆以为不得尔。又要得脱世网,至愚迷者也”[5]。程颐也讲:“今之学禅者,平居高谈性命之际,至于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晓者,此只是实无所得也”[6]。一代文坛领袖欧阳修也曾因“王政缺”、“礼义废”而极力排佛。这就是说,尽管在宋代儒佛并行,然彼此之间还是存在一条深深的鸿沟。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的儒家知识分子多对佛教持一种排斥的态度。这样,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讲唱佛经理的变文也就很难得到文人们的认同了。另一方面,除讲经化俗外,变文在唐宋兴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悦俗邀布施”[7]。傅芸子先生解释唐以后俗讲兴盛的缘由时说:安史乱后,富家顿衰,再难能一如从前地为寺院作种种布施以及经济上的援助,为此,寺僧们只好借助于当时的民间团体“社邑”,以“社邑”成员共同出资的形式举办俗讲,以求得经济生活上的来援。这样,为了吸引民众,达到邀布施的目的,僧侣们在将深奥的经文通俗化的同时,不免走上了“媚俗”的道路,以淫辞艳语,投民众所好。[8]殊不知一般文人们的兴趣却不同于村野黎庶们。对这种“鄙俗之词”,偶一听之或许可以,但要将其纳入他们心中神圣的文学殿堂,则难矣!
(二)传统的中国文学注重传情达意,先唐的文学作品尤其如此。从传统文学的体式看,先唐的文学作品为一般士人所认可的,无非两大类:诗歌、散文。就诗歌而言,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诗言志”之说,《史记·太史公自序》认为“诗以达意”,《毛诗序》也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至西晋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钟嵘《诗品序》也说“陈诗展义,长歌聘情”。种种说法都说明了一个“情”字对诗歌的重要性。散文也一样,陆机《文赋》在论及为文之动机时归因于二:其一是感于物:“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其二是本于学:“育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刘勰《文心雕龙·定势》言:“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又《文心雕龙·知音》:“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到韩愈又提出“不平则鸣说”。凡此种种,皆足以表明传统中国文学重“情”的特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决定了唐宋文人们对于歌辞或变文这些民间文体的取舍。词在抒情方面“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9],这就决定了人们可以借歌辞这种文体表现其心灵深处的某些更为细腻幽深的情感内容。变文则相反,从敦煌遗书看,无论宗教题材或世俗题材,都是敷衍故事的。与传统文学体式重抒情的特质相比,变文更注重叙事。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叙事文学发展史上,变文的出现是一件具有里程意义的大事。然而,在当时抒情文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变文没有机会,也不可能堂而皇之地走进所谓“雅文学”的大门。因此,如果说歌辞是由于其“狭深”、“细腻”[10]的抒情性赢得了文人的青睐的话,变文则是由于其通俗直实的叙事性能而被文人们拒之门外。从后来的戏曲小说看,直到明清之际仍有人以之为末技而嗤之以鼻,那么变文在唐宋时的不被接纳,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了。
正基于此,我以为变文作为一种民间文体,尽管在唐五代还没有发展到成熟完美的境地,但已经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动力和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遭到政治的扼杀、禁锢,变文就失去了重新焕发生机的可能而只有一去不返了。
三
当然,说变文在唐五代已经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动力和可能,并不足以说明变文在宋时便理该绝迹。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变文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自觉不自觉地为某些更为成熟的说唱文体的形成准备了条件。所以一旦变文被当局者明令禁止,这些新文体就立刻从勾栏瓦肆中走出来取而代之。
这里所说的条件,表现于各个方面。比如说题材:变文中关于伍子胥的故事、王昭君的故事、目连救母的故事,在后代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说唱或戏曲文学中不止一次地被人们搬上舞台,成为历久不衰的传统剧目或曲目。比如说语言:宋以后俗文学诸如诸宫调、杂剧、传奇、小说等之所以能别焕异彩,“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应当是采用一种活的语言作描写的工具。但是用活的语言作描写的工具,绝不是变戏法一样,可以一下子从无中生出有来的。其间一定要经过相当的准备的时期:一方面作收集网罗的功夫,一方面作提炼抉择的功夫。敦煌发见的俗文学材料,正是这样一种情形的表现”[11]。应该说,变文在这些方面对后代俗文学的贡献的确是巨大的。在这里,我主要想从变文对其他说唱文学形式体制方面的影响,以及这些说唱文学形式在宋以后的勃兴,说明变文为什么会一去不返。
变文对宋以后诸种说唱文体的重大影响,早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不过如依据时下流行的看法,认为变文绝迹在南宋理宗朝(公元1225—1264年)的话,那么早在变文绝迹之前,受其影响,已有种种说唱文学形式盛行了。可以想见,作为一种久行于民间并深得民众喜爱的文学形式,变文对于其他文体的影响应当是潜移默化、渐次前行的。不可能说是变文被禁之后,才来了突变,一下子冒出许多新的说唱文学形式来。从宋代的“说话”、“诸宫调”,我们可以明确地看这一点来。
传统的章回小说,它们中间夹杂着一些诗词,宋代的一些话本亦如此。据《也是园书目》和《述古堂书目》,现在基本上可以被确定为宋人作品的话本,如《种瓜张老》、《错斩崔宁》、《西湖三塔》、《简帖和尚》、《合同文字记》、《风月瑞仙亭》及《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等,都是以散语叙说而中间夹杂着诗词。这些诗词又多以七言诗句为主。这在唐宋以前的雅文学作品中所见极少。可以肯定,这种体式的确受了唐五代散韵相间的变文的影响。不仅如此,宋以后话本篇首入话(诗词或故事)——篇中正话——篇尾诗词答结的体制结构,也明显是讲经文开首说押座(多是七言诗句)——开讲本经——结尾解座(也多为七言韵文)这种体制的衍变。
话本以外,诸宫调算是宋时说唱文学中最伟大的一种了。诸宫调了吸取了变文散韵相间、说唱夹杂的体制。有人说“诸宫调的歌唱的调子,比之‘变文’复杂得多,是采取了当代流行的曲调来组成其歌唱部分的”。这个“当代流行的曲调”,就指诸宫调“弃去了变文的三言七言的成法,而别从唐宋大曲,从赚词,从宋金元三代流行的曲调里,任意采取着可用的资料和悦耳的新声。”正因为如此,它比变文更有魅力更吸引人。但不管其曲调怎样变化,其祖祢源于变文,却是可以肯定的。
在宋代,受变文影响的说唱文体还有鼓子词。鼓子词从体制上看,也是说唱相间,且有管弦伴唱,只是篇幅较变文短小而已。
从时限来看,早在变文禁绝之前,说话艺术、诸宫调及鼓子词等早已在民间瓦肆中流行开了。说话艺术产生较早,北宋时就曾有专说《五代史》的说话艺人尹常卖、专说三分的艺人霍四究等。今存的一篇较有代表性的鼓子词便是北宋时赵令畤的《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诸宫调之创于宋代,也应确凿无疑。王灼《碧鸡漫志》、吴自牧《梦粱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都有有关记载。说明早在神宗、哲宗、徽宗年间就有诸宫调盛行。另外,今存诸宫调的代表作《董解元西厢记》产生于金章宗(公元1190—1209年)时,《刘知远诸宫调》则产生于12世纪初,这都是诸宫调盛行于变文禁绝之前的明证。就内容而言,宋鼓子词作品今存不多,但就话本看,宋代说话艺术比较盛行。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肆众伎”一条中记载:“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博刀赶棒及发迹变仄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之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诸宫调也一样,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中曾考证出十余种诸宫调名,涉及烟粉灵怪、长枪大马、依红偎翠、神话历史等各方面,内容堪称广泛。就流传情况看,宋代说话艺术,无论小说、讲史、谈经,在瓦肆中都大有影响。以“说三分”为例,苏轼《志林》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落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语。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诸宫调在宋代亦相当流行。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记载“诸色伎艺人”中有“诸宫调传奇”一项,就中提到了“高郎妇、黄淑卿、王双莲、袁太道”四史诸宫调艺人,卷十又载“官本杂剧段数”中有以诸宫调演唱的官本杂剧《诸宫调卦册儿》、《诸宫调霸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载:“今杭州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后辈女童,皆效此说唱(诸宫调)”。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也说孔三传创诸宫调后,“士大夫皆能诵之”。凡此种种,都说明在变文绝迹之前,瓦肆中已有种种受变文影响而产生的说唱文学与变文分庭抗礼,并行而不悖。
当然,如果再留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宋代话本、诸宫调和变文相比较,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变文的侧重点在佛经的演说、衍讲,而话本和诸宫调则多注重世俗的内容。尽管说话艺术中也有演说佛书的说经一类,讲宾主间参禅悟道的参请一类,然而今存的这类话本却绝少,或许也当是理宗禁绝变文时受到了影响,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佛经题材的变文被禁以后,诸宫调也罢,话本也罢,都不能代替它在瓦肆民众中的影响,所以时隔不久,另一种新的演说佛经的文体宝卷很快就又流行开来。
宝卷是“宣卷”的脚本,内容以演绎佛经故事及因果报应为主,它是由变文直接演变发展而来,堪称“变文的嫡系子孙”。宣卷的仪式与俗讲相仿佛,俗讲有讲师要念偈作梵梵香,称诸菩萨名,宣卷也有开香赞,也要上香、叩头,且宣卷入唱佛号时,听众要与之应和。俗讲有讲师上堂升高座的轨仪,宣卷人也须坐在高台上或正中间。俗讲正式开经前有说押座,宣卷也有开经偈。俗讲结束时有解座文,宣卷也有收经偈。就体制而言,宝卷也是以韵文为主,间以散说。种种迹象均可表明二者之间直接的承继关系。可以想见,尽管变文被禁了,但佛教僧侣的宣传需要和瓦肆听众的娱乐需要却为宝卷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加之至元以后,历代帝王均保护佛教,尤其明中叶以后,佛教徒也以刻宝卷为功德,所以宝卷便取代变文大量流行起来。
总之,诸宫调、说话及宝卷等是受文影响而产生的说唱艺术,然而,也正因为这些新生的说唱艺术从方方面面取代了变文在瓦肆民众中的地位和影响,变文被最后挤出了历史舞台。这也就是所谓的“后来居上”吧。
综上,我以为变文之绝迹,一方面由于未能赢得文人士子们的青睐而失去了继续发展和完善的条件;另一方面,受其影响而产生的种种说唱艺术在后来的崛起和勃兴,又使其失去了东山再起的契机。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变文受到政治的影响,被统治者明令禁止,它就只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民众们淡忘,最终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注释:
[1] 杜继文:《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2]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海书店1987年版。
[3] 吉师老诗《看蜀女转昭君变》。
[4]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5] 《二程遗书》卷二,据《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6] 《二程遗书》卷六,同上。
[7] 《通鉴·唐纪·敬宗纪》,中华书局1956年版。
[8] 据傅芸子《俗讲新考》,《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9] 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10] 杨海明:《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1] 向达:《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