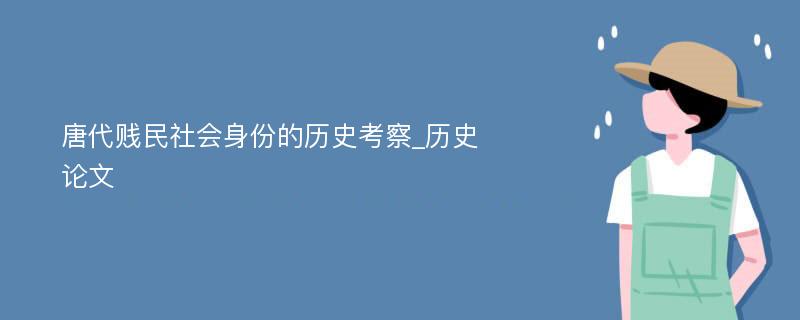
唐代良贱乐人社会身份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身份论文,社会论文,历史论文,良贱乐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唐三百年间,至其盛(玄宗)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① 这一记载表明,唐时从乐艺人数量之巨,以及他们所具有的身份——“音声人”,既是一种呈多元结构的特殊社会现象,又是一种具有某种规律性的文化形态,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中从事音乐职业的乐人制度(institution)的定位与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个独特领域的音乐(music)概念内涵带来理解的抵牾。数十年来,我们的研究多关注于唐时乐人所从事的乐舞活动及乐学形态方面,鲜少注目于这些乐人的社会身份问题。自杨荫浏以来②,仅有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及我国当代音乐学家张振涛、项阳的研究,反映出从事隋唐音乐史研究的人,在治史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已然开了先河。他们或基于隋唐社会政治史层面专题分析研究唐代从乐艺人的分布与活动;③ 或结合社会背景、经济结构的变化及文艺的发展进行考察,集中阐述了我国中古时期乐工所有的血缘宗法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④ 或立足实地寻访,凭借文化遗存来考证封建社会中乐籍制度的影响及乐户传承音乐文化显示出的独特社会群体特征,⑤ 进而强调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专业乐人实际上是制度下的生存群体。⑥ 这些研究虽然只是几例个案,但弥足珍贵,其所开肩的多学科渗透发展的研究思路,对于辩证地认识中国音乐文化和中国音乐家的行为及其对音乐文化的影响,看到乐籍制所具有的外显和内隐双重功能,是唐代政治经济的繁荣对娱乐用乐的广泛需要,非为从乐艺人地位的提高。其显功能表现在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因为统治者对音乐的喜好而需要有驱使以享乐的贱民出现,其存在的形态与相关活动构成了社会音乐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隐功能则揭示了乐籍制作为一种贱籍模式,注籍乐户的生存与地位的低下,无人身自由,他们对于音乐的继承与创造必然会受到影响。本文遵循这一思路,结合唐律所示司法原则,来对唐时乐人的社会身份予以研究并获得粗浅认识,进而表明我们目前的中国音乐史学课题研究方面完全可以走出一条迈向纵深、更趋专题的路子,直至有大的突破。
一、唐代良贱乐人的名色
所谓良贱乐人,是基于伦理身份的一种称谓,定义相对开放。首先指的是从事乐事活动的人与事皆为贱民、贱业。其次是这些贱民所从事的乐事活动本身的接受者却是社会中有着尊贵地位的人。在唐代这样一个以良贱为标准来区分社会身份等级的社会中,从事乐事活动者及其活动的接受者皆有着各自的功能需求,因此会形成一种趋于良口的获得性身份(achieved figure)。作为贱民的从乐之户,用黄现璠的话来讲,“吾人之鄙视奴隶称为贱民”。⑦ 而奴者,为失去自由受人役使的人。
唐人对社会人及其权利常常使用“色”字,所谓“种类”、“色别”。诸色所服之徭役称色役,即某种专门性役使,包括诸色服役胥吏者在内“皆入官之门户”。⑧ 唐律经常提到的有工、乐、杂户、音声人、官户,⑨ 笔者称之唐时良贱乐人,其名色划分繁杂。其“良”即“良口”,其“贱”近于奴隶,“人各有偶,色类须同,良贱既殊”⑩,他们是“居于有若干财富”的阶层,属于半封建化的农民。所谓良、良口、良人,在均田制下常指那些“佣力自资”、“依令授田”的农人和“不附籍帐”的依附百姓(如庄客、佃户、佣工、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等)。与之相对的是多为不立户籍的贱、贱口、贱人。无论良贱,在法律上均属无特权的劳动人民,人身权皆为“半自由民”(11),都是社会生产、国家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良口有地,靠劳作为生;贱口无地,靠色艺谋生,从而形成唐朝区别所谓身家清白的又一条件。本文之称“良贱”,原因在于组成这一贱民阶层的诸色皆为非良人。同时,唐律中并未出现将上述色别之人全称为“贱民”或有清晰定义者,这些非良人“‘避本业’,谓工、乐、杂户、太常音声人,各有本业”,或者遵照所谓“还依本色者,工、乐还掌本业,杂户、太常音声人还上本司”。(12)
唐时贱民阶层,“大体上,可分为官贱民和私贱民二种:而官贱民又分为官奴婢、官户、杂户、工乐及太常音声人等。私贱民又分为私奴婢、部曲、客女、随身等。”(13) 作为我国唐以后社会存在的一个阶层,其中从事乐事活动者,应该不在少数。就像项阳在其《山西乐户研究》中指出的,唐时乐人基本属于贱民阶层,所以这些分属宫廷和各州县,以官贱民和私贱民而居的人,从事着本质上几近一致的活动。
属于官贱民者,有所谓官户,为番户之总称,原是籍没为奴婢,“配隶相生”,隶属于司农寺的官贱民及其后代,由其“执掌”(14),主要在宫廷当值从事乐事活动。包括诸工、乐、杂户及太常音声人四类,都是世代相传籍属官府、不入籍州县的官贱民,他们在官府作专业服役。工户,从事手工业劳动者,由掌管百工技巧为朝廷制造手工艺品的少府监辖治,其中有擅长行乐事活动者“工属少府”,隶属太常(15),称乐户。乐户与太常音声人隶属太常寺的职业乐舞或以作乐为业的贱民,隋末以后,太常音声人得以入籍州县,并非太常寺户,但仍在太常,故名。杂户,前代犯罪没官,散配诸司驱使,(16) 区别于少府监、太常寺之外其他官府服杂役的贱民。“太常杂户子弟”应属番户。(17) 还有太常乐童,“童子能执乐,隶籍太常者”。(18) 太宗长子李承乾就有一名太常乐童,其年“十余岁,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宠幸,号称心。”太宗闻之大怒,悉收称心等杀之,太子嗣后“常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鼓角之声,日闻于外”。(19) 可见太常乐童亦太常乐户之属。
属于私贱民者,有部曲,“自幼无归,投身衣饭,其主以奴蓄之,及其成长,因娶妻。此等之人,随主属贯又别无户籍,若此之人,各(名)为部曲”。(20) 其女即客女,“谓私家所有”,部曲妻及客女亦同,(21) 奴婢,在男称奴,在女称婢,与部曲一样“身系于主”。(22) 官奴婢因为犯罪或坐没而成,(23) 私奴婢大都是卖身的贫苦农民或被劫掠拐卖的平民,同类相婚,贱人的后代一直为贱人。(24) 所谓“随身”,意为雇佣良口为仆从,一般与雇主签订有期限的典雇佣驱使契约,可在契约期满后还身,从现存不多的文献记载来看,其间定有从事乐事活动者。唐时,奴婢、部曲、官户并提,(25) 同属私贱民阶层,但根据史料,奴婢和部曲阶层,依其来源不可混在一起讨论,纵有行乐者,亦是必然。
史料中记载官贱民乐人事件居多,私贱民则散见于唐代文人诗话的行间。这些材料显示出唐时用乐实际上业已形成一个庞大的体系。由于宴乐之风盛行,加之唐时政治制度也僭越或违制约束,缙绅士大夫蓄乐(私奴婢)者,不约而同地使乐人的活动趋向专业化、组织化和制度化。除正史、文集外,这一类文献还体现在各类杂著、笔记、小说、诗歌中,它们基本反映了写作时代的情况,虽不足信但可旁证之。
乐人组织的建立首先得以在政府保障下先行,由官贱民影响至私贱民阶层。按照《北里志》“序”所言,“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唐时乐人管理组织以承隋大业六年(611)始设教坊为继,(26) 开创官奴婢乐人(即“教坊妓”)行乐服务体系,但他们的活动限于宫廷,并依服务对象的不同被分成若干等级,如人宜春院的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家犹在教坊者,谓之“内人家”;得皇帝宠幸者谓之“十家”。其次在云韶院的谓之“宫人”;另有“平人女以容色选人内者”,谓之“搊弹家”。(27)“武德后置内教坊于禁中,武后如意元年改曰云韶府,以中官为使。开元二年,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技,自是不隶太常,以中官为教坊使。”(28) 崔令钦《教坊记》亦有类似的相关记载。中宗时(705),“又太常乐户已多,复求访散乐,独持鼓者已二万员,愿量留之,馀勒还籍,以杜妄费”。(29) 至玄宗时,设梨园于西北禁苑,及隶属太常寺的太常梨园别教院、洛阳梨园新院,“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子弟。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园法部更置小部音声,三十余人。”(30) 其“小部者,梨园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以下”。(31) 陈旸《乐书》“教坊部”载:“唐全盛时,内外教坊近及二千员。梨园三百员,宜春、云韶诸院及掖庭之伎,不关其数。太常乐工动万余户。”(32) 根据文献,仅开元(713—741)间应差于教坊者,“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散乐二百八十二人,仗内散乐一千人,音声人一万二十七人”。(33) 梨园设立伊始,“太常又有别教院……别教院廪食常千人,宫中居宜春院”。(34) 其盛时一如开篇所提及的,“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太乐中,“国家每岁阅司农户容仪端正者……与前代乐户,总名音声人。历代之多,至于万数”。(35) 到大中初(847),“太常乐工五千余人,俗乐一千五百余人。宣宗每宴群臣备百戏,帝制新曲,教女伶数千百人,衣珠翠缇绣,连袂而歌”。(36) 总计上述隶属宫廷、不入籍州县的官贱民(音声人、乐户)都是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的乐人,他们的活动范围以宫廷为主,但影响不完全囿于宫廷,其数量更是相当庞大。此外,根据《乐府杂录》“雅乐部”、“云韶部”、“鼓吹部”、“驱傩”等的记载,(37) 各部所设置乐器件数均需要配备相应人数,所用乐人各司其职,散乐人数尤甚:“古乐工都记五千余人,内一千五百人俗乐,系梨园新院于此,旋抽入教坊”。(38) 上述乐妓列备教坊,有专门供奉宫廷的,也有譬如住在平康里和其他乐坊中的乐妓,逢重大活动如每年新科进士发榜之时携之“曲江宴饮”行狎游之风,虽然籍属教坊,但活动不一定全集中在教坊,寺院也不例外。如显庆元年(656)四月八日,高宗为大慈恩寺书碑并着工匠镌刻好,“将欲送寺,法师惭荷圣慈,不敢空然待送,乃率慈恩徒众及京城僧尼,各营幢盖、宝帐、幡华,共至芳林门迎。敕又遣太常九部乐,长安、万年二县音声共送。……凡三百余事,音声车千余乘”。(39) 但唐朝寺院之特殊,工在寺院的乐户因此也是十分特别的一类,其身份亦别于唐时其他乐户。
官奴婢中,在各州县应差的乐人(官户、乐户)亦遍及官府各种活动,虽然法律地位一致,但在人数、给使、生活方面与两京的官奴婢乐人也有不同。
首先,在官文中,王公贵族所占有之奴婢乐人基本为官奴婢而非私奴婢,其数量因之会受到一定限制。《唐会要》与《通典》对此都有记载:“天宝八载六月十八日敕:京畿及诸郡百姓,有先是给使在私家驱使者,限敕到五日内,一切送付内侍省。其中有是南口及契券分明者,各作限约,定数驱使。虽王公家不得过二十人,其职事官一品不得过十二人,二品不得过十人,三品不得过八人,四品不得过六人,五品不得过四人,京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过二人,八品、九品不得过一人。其嗣、郡王、郡主、县主、国夫人、诸县君等,请各依本品,同职事及京清资官处分。其有别承恩赐,不在此限。其荫家父祖先有者,各依本荫职减,比见任之半,其南口请禁蜀蛮及五溪、岭南夷獠之类。”(40)“八载六月敕男口给使王公家不得过二十人,其职事官一品不得过十人,三品不得过八人,四品不得过六人,五品不得过四人,京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过二人,八品、九品不得过一人。(百官家蓄丝竹及给使口并是朝恩优宠资给,故附于庶仆俸料之后)”(41) 这一类材料显示出地方官奴婢受“朝恩资给”,从事“给使”、“丝竹之口”的营生。
其次,除教坊乐妓外,唐代太常寺所辖音声人和杂户中,也有一部分是散乐,附贯于州县。“或置于州郡藩镇衙门,供刺史、节度使等地方首长公私宴会时,担任侍奉之职”(42),有“府娼”、“郡娼”之谓,以及藩镇乐营所用伎乐,所谓“营妓”。譬如宝历二年(826)九月,“伏见诸道方镇,下至州县军镇,皆置音乐,以为欢娱”;(43) 贞元十五年(799),汴州节度判官孟叔度“多纵声色,数至乐营与诸妇人嬉戏,自称孟郎,众皆薄之”;(44)“凡差卫士征戍镇防,亦有团伍……其居常则皆习射,唱大角歌”(45)……所有这些记载表明,官奴婢分布于宫中、官府与军营,各有其任务。譬如天宝初,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于长安城东浐水傍穿广运潭,以通吴会数十郡舟楫。先是民间戏唱得体歌,及新潭成,陕县尉崔成甫乃翻此调为得宝歌,“广集两县官,使妇人唱之。……和者妇人一百人,皆鲜服靓妆,齐声接影,鼓笛胡部以应之”(46),玄宗欢悦。记载中,地方官奴婢不仅人数要少于两京官奴婢,其生活与地位与之相比也差异甚大。其所司任务中,地方官奴婢还要在用乐上保持地方官府与朝廷的一致性,其实现方式就是要求官户乐户应教习以当值官府甚至朝廷,轮番就役,抑或随时吁请。譬如会昌年间(841),“武宗数幸教坊作乐,优倡杂进。酒酣,作技谐谑,如民间宴席,上甚悦。谏官奏疏,乃不复出,遂召优倡人,敕内人习之。宦者请令扬州选择妓女,诏扬州监军取解酒令妓女十人进入,监军得诏,诣节度使杜悰,请同于管内选择。”(47)
私奴婢之属,也只是个泛称。依奴婢不同的隶属关系区分形成,根据奴婢所有者对奴婢拥有的支配、使用、处置等权有多种称谓,如“民伎”、“家伎”、“市井歌妓”等均属私奴婢。《唐会要》记载,朝廷显然是认可蓄养家妓的:“天宝十载九月二日敕:‘五品已上正员清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当家蓄丝竹,以展欢娱,行乐盛时,覃及中外。’”(48) 如前所述,朝廷对官员蓄养家妓的数量亦有相应的规定,尽管资料阙如,但当时的实际显然都超过了规定的标准。试对照中宗神龙二年(706)九月,“敕:‘三品已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已上,女乐不过三人,皆不得有钟磬’”;(49)而《新唐书》中记载孝恭因功受赐“女乐二部,奴婢七百口”,其“性奢豪,后房歌舞伎百余”。(50) 唐孟棨《本事诗》“情感一”也有:“宁王曼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太和初……有妓善歌,时称尤物。时太尉李逢吉留守,闻之,请一见,特说延之。不敢辞,盛妆而往。李见之,命与众姬相面。李妓且四十余人,皆处其下。”(51) 可见,官吏家蓄乐妓并未减少。其他方面,像《北里志》中所记长安妓女虽然名属官府,要应承官差,但辖治较松,未见有官妓之称,当断为市井歌妓。在白居易等唐代文人的诗集中,散见私妓活动频繁,且不在少数。史料中反映出贵族阶层所蓄家妓之数量、年龄品貌、技艺高下还成为彼此攀比的参照条件。在社会统治中下层的地主官吏那里,抑或寺庙,也以“置田”、“蓄奴”、“佐欢”作为其努力目标,是一时之风气。(52)
部曲,唐律所规定的身份属于贱民阶层是无疑的。在唐贱民中,部曲的身份是高于奴婢的私贱民。从音乐史角度观察,唐代应该有部曲从事乐事活动的情况,但在传世文献中,几乎未见记载。然而,据汉魏以来部曲内涵的变化臆测,原本为军队编制及私兵之称,后发展为作战时是部曲、平时是佃客的生存状态。其中,有一定数量的部曲乐工在军中行礼乐、鼓吹、娱乐之奏诸活动或许存在。部曲作为一个贱民阶层,在宋代已不存在,北宋时期文献鲜见相关记载。(53)
二、唐代良贱乐人的来源
“千万奴婢,果报自随;……汉奴专知仓库,胡奴检校牛羊;斥脚奴装鞍接镫,强壮奴使力耕荒;孝顺(奴)盘鸡炙旌,谗韶奴点醋行姜;端正奴拍箜篌送酒,丑掘奴添酥酪浆;细腰婢唱歌作舞,矬短擎炬子食床。”(54) 这一记载表明了唐时用乐环境与阶层分布之广且细,决定了唐代良贱乐人的形成必定有着一套严密的组织化、制度化、专业化保障体系。
唐代良贱乐人的来源因袭前代如魏、隋制度而又有变异,并趋向成熟。总体上,唐朝廷主管良贱乐人事务的地方在刑部都官,设郎中一员,从五品以上,六品员外郎一名,九品主事二名,书令史十二人,掌故四人。他们所管理的是全国官奴婢中的大多数,有部分属府、州、县役使。中央政府设掖庭局主持,有七品令二人,八品丞二人,计史二人,九品宫教博士二人,其职在“掌宫禁女工之事,凡宫人名籍,司其除附;功桑养蚕,会其课业”。(55) 掖庭作为专为宫廷用官户奴婢进行培训的基地,在对象上有所选择,如《唐六典》所载并注曰:入于掖庭的工巧妇人,“官户皆在本司分番,每年十月,都官按比。男年十三已上,在外州者十五已上,容貌端庄,送太乐;十六已上,送鼓吹及少府教习”。(56) 史料中亦见:玄宗见太子(肃宗)“左右使令亦无妓女”,着高力士为之“阅女子”,于是从“故衣冠以事没入其家者,宜可备选”的掖庭中“按籍阅视,得五人,以赐太子”。(57) 可见掖庭令所辖之掖庭官,为唐代宫廷用乐如太常或教坊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充足的音乐表演人才。这些长于音乐的工巧之人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所述均有具名姓氏之乐人,同于篇幅,从略。
(一)前代遗留
唐代杂户的来源,“谓前代以来,配隶诸司执掌”;官户者,“亦谓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有今朝配没”;(58) 尤其是唐高祖即位后不久,在武德四年(622)九月二十九发布诏书:“太常乐人本因罪谴没入官者,艺比伶官,前代以来,转相承袭。或有衣冠继绪,公卿子孙,一沾此色,累世不改。婚姻绝于士庶,名籍异于编甿,大恥深疵,良可矜愍。其大乐鼓吹诸旧乐人,年月已久,时代迁移,宜并蠲除,一同民例。但音律之伎,积学所成,传授之人,不可顿阙,仍令依旧本司上下。”(59) 说的就是前代官户名色累世不改,但乐户可蠲免而一同民例,只是强调“自武德元年配充乐户者,不在此例”。这些记载与《隋书》所录如出一辙:“自汉至梁、陈,乐工其大数不相逾越。及周并齐,隋并陈,各得其乐工,多为编户。至六年,帝乃大括魏、齐、周、陈乐人子弟,悉配太常,并于关中为坊置之,其数益多前代。”(60) 唐时继承前代遗留乐工人数不在少数。
(二)籍没家口
籍没家口主要体现在罪臣家属及原本属于罪臣的私奴婢的没入。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周以后一直未尝废,至唐前,律书更有明确规定。唐时犯罪家口籍没一般为官奴婢:“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61) 籍没范围包括“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言‘皆’者,最无首从。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注云‘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姐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奴婢同资财,故不别言”,(62) 其“谋反者,男女奴婢没为官奴婢”(63) 等。见于史书记载的有关唐代籍没罪犯家口事件约在50起之上,集中在谋逆、谋反、酷吏所害、坐甘露之变等原因方面,因而使得籍没成为唐朝官奴婢的一个重要来源。譬如:咸通十三年(870)五月,“国子司业韦殷裕于阁门进状,论淑妃弟郭敬述阴事。上怒甚,即日下京兆府决杀殷裕,籍没其家。殷裕妻崔氏,音声人郑羽客、王燕客,婢微娘、红子等九人配入掖庭”。(64) 朝廷管理这些罪臣家属的机构亦在掖庭,由都官郎中主持。“凡公私良贱,必周知之。……凡初被没有伎艺者,各从其能而配诸司,妇人工巧者入于掖庭,其余无能咸隶司农”。(65) 著名的上官婉儿,上官仪孙女。武后时,仪死,随母郑氏配没掖庭,因才气过人,被武则天赏识,在掖庭受教育,并得免籍。(66)
(三)奴婢掠卖
掠夺与买卖奴婢,是唐代补充官私奴婢的一个习惯做法。买卖又包括自卖与他卖。自卖形式中,有衣食无着不得不入籍的,例如“李八座翔,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匪疾而颜色忧悴。殷尧藩侍御当筵而赠诗,曰:‘姑苏太守青娥女,流落长沙舞柘枝。满座绣衣皆不识,可怜红脸泪双垂。’明府诘其事,乃故苏台韦中丞爱姬所生之女也(夏卿之胤,正卿之侄)。曰:‘妾以昆弟夭丧,无以从人,委身于乐部,耻辱先人。’”(67) 掠卖通常是强制性的,如安乐公主之与长宁、安定三家厮台掠民子女为奴婢。(68)“掠”在唐律中称“略”或作“和诱”。(69)“略人为奴婢者,理与强盗义同”。(70) 如《本事诗·情感一》还记有“唐武后时,左司郎中乔知之有婢名窈娘,艺色为当时第一。知之宠爱,为之不婚。武延嗣闻之,求一见,势不可抑。既见即留,无复还理”。(71) 地方官府贡献朝廷的奴婢中有绝大部分是掠卖,如顾况诗《囝》所描绘的,“囝生南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72) 又如代宗时,“元载子伯和,势倾中外,福州观察使寄乐妓十人,既至,半岁不得送”。(73) 唐时奴婢掠卖以后期尤盛,政府虽有律令禁止,但废而不举。掠卖奴婢中,因债务、生活而沦为贱籍从事乐事活动者是唐代良贱乐人来源中的一个重要来源。
(四)家生奴
家生奴,即奴婢所生子女。秦汉称奴产子,晋以后又称家生,以区别于新卖身的或投充的奴婢。唐律规定,奴婢所生子女,永为奴婢。所谓“奴婢贱人,律比畜产”。(74)《新唐书》载有:“廷珪上书曰:……荆益奴婢,多国家户口,奸豪掠卖,一入于官,永无免期。”(75) 著名乐人许永新,“本吉州永新县乐家女也。开元末选入宫,即以永新名之,籍于宜春院”。(76) 奴婢只能同类为婚,婚生子女称家生奴,其身份实为世代相袭的一种。作为一个常规行为,从民间乐户遴选新生歌妓的做法使家生奴成为唐代良贱乐人中比较稳定而且重要的一个来源。
(五)赏赐进奉
赏赐进奉类乐妓,既与唐代发达和畅通的交通有关,亦与大的用乐氛围有关,这一来源存在三种形式。一是与唐朝廷来往密切的国家或地区如高丽、百济、新罗、日本、林邑、尼婆罗、天竺、骠国、真腊、诃陵国、大食、波斯等地,以贡献方式进献乐人。(77) 二是官奴婢赏赐。如地方官府的进奉,取“岁贡”、“阉儿”多种方式;(78) 如宪宗时,李光颜因大败吴元济叛军,与贼军暗中有往来的汴州节度使韩弘在汴城挑选一绝色女子,“教以歌舞、弦管、六博之艺”,欲令李光颜“一见悦惑而怠于军政”而未得逞。(79) 也有像朝廷要求地方官员进奉乐人以填个人喜好者,如文宗时就敕“凤翔、淮南先进女乐二十四人,并放归本道”;后来又下诏“诸道所进音声女人,各赐束帛放还”(80) 等。在唐武德、贞观年间,有大量赏赐奴婢给下臣的记录,总计达十五次逾一千二百人之多。(81)“安史之乱”后,统治者给予受封勋爵赏功的褒奖,虽然人数略有减少,亦有割配,史料所载官奴婢差不多都是以乐妓身份出现的。(82) 三是私奴婢赠送,有唐一代十分流行。
(六)战争虏获
战争中捕获的俘虏,是唐代官奴婢的一个来源。唐代历次战争虏获的人数每次少则成百上千,多则五到十万。对俘虏的处理中,如《唐六典》卷六“刑部都官”所载“薄录俘囚”之说,其没为奴婢者,当不在少数。(83) 譬如天宝末,唐肃宗“宴于宫中,女优有弄假官戏,其绿衣秉简者,谓之参军妆。……蕃将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为优,因使隶乐工。是日遂为假官之长。所为妆者,上及侍宴者笑乐”。(84) 蕃将之妻隶身宫廷乐籍,确证了战争虏获事件之存在,然而有多少配没乐籍行列,相关文献记载不清。
(七)征集良口
新产生的乐工,经过相对的“遴选”、“采择”,用于需要之处,来源较为复杂。其一,如《教坊记》所载:“平人女以容色选入内者,教习琵琶、三弦、箜篌、筝等者,谓之‘搊弹家’”;又有《乐府杂录》载张红红,“本与其父歌于衢路丐食”,后“召入宜春院”,寻为才人,被誉记曲娘子等;宪宗时“教坊忽称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别第妓人,京师嚣然”,有李绛呈折谏劝,宪宗称“朕缘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无侍者,朕令于乐工中及闾里有情愿者,厚其钱帛,只取四人,四王各与一人。”(85) 凡此种种,属合法和买。其二,唐之乐舞,沿用隋朝旧制,列文、武二部。隶属太常的乐工在表演文武二舞时,舞者各64人,其“衣冠各同当色舞人,余同工人也”,(86) 说明舞者属平民身份。《通典》亦持这一看法:“汉魏以来,皆以国之贱隶为之,唯雅舞尚选良家子。”(87) 同样,民间采择入宫的良家女子,先要入掖庭学习一定的礼仪与歌舞技能。受司农寺宫苑使管理,行采择乐工之责,其“容仪端正者归太乐,与前代乐户总名‘音声人’”。
三、唐代良贱乐人的社会地位
以今日之观念观照唐代良贱乐人的组成,主要有官奴婢、私奴婢、部曲三类。这些乐人无论名色、官私之属,皆处贱民阶层。唐律中以明确的言辞将人作良贱区隔,并依人的社会身份、地位、职业等在权力和义务诸方面形成不平等的级次和等第,且各等级不得任意逾越,还要世代相传。总体来说,他们无独立户笈,随主属贯,不合与良人为婚,很少有人身自由,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其生命受法律保护,所谓“诸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一年”。“凡奴婢过失杀主者绞,伤及詈者流”。(88) 按照唐律,作为贱民,乐户、杂户、太常音声人、宫廷乐人等,无论服务处所、服务对象、户籍分属,贱籍一致。当然,这些非良人也可以放贱为良,放免方式有老免、赦免、自赎、代赎、放免等多种。贱民依律放免首先需要履行法定手续,接着比照一定条件实施放免,譬如用金钱赎买者,为主人立功者,具备特殊技能者。奴婢“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则免之。年六十及发疾,虽赦令不该,并免为番户;七十则免为良人,任所居乐住而编附之”。(89) 像杂户就是官奴婢的再放免者。一般而言,奴婢被放免的机会较少,良口一旦没入贱籍,多世代为贱民。
尽管如上所述,在一个尤为看重礼乐制度的王朝,唐代对于乐人、长上乐人、乐户、杂户、官户、工乐、音声人、太常音声人、文武二舞郎、散乐、杖内散乐等名色称谓,以及管理机构的建制,并载于国家法典之中,尤其在一个户口管理制度堪称完善的时代,显然是有着明确的区分与要求的。相应地,这些人的社会身份亦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各有区隔。总体上,雅乐所用乐人应该是地位最高者,它源自一个悠久的传统,“自唐、虞迄三代,舞用国子,乐用瞽师。汉、魏后皆以贱隶为之,惟雅乐尚选良家子”。(90) 因而,同属太常乐工表演文武二舞郎者的身份为平民,而由前代被放免的乐人组成的乐工亦具有良人身份,(91) 但并不能说明除表演雅乐歌舞之外的太常乐工都具有同样较高的地位。这一情况颇为复杂,文献中亦没有相关记载,故不好妄言。
作为官贱民的主要组成部分,唐律给予太常乐工和教坊乐工的身份区隔因此尤具代表性,成为朝廷与地方、管家与私家共同执行的标准。这一标准折射出了唐时乐人管理呈现出了一定的制度化、组织化特点。
(一)太常乐工
太常乐工由太常卿管理,其职在“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凡国有大礼,则赞相礼仪,有司摄事,则为之亚献。率太乐之官署,设乐悬以供其事。燕会,亦如之”。(92) 太常寺之太乐令、丞“掌习音乐、乐人薄籍”,管理太乐、鼓吹二署雅乐歌舞乐工。鼓吹署“所掌颇与太乐同”。(93) 唐史记载,唐时雅乐歌舞表演人员由“容貌最陋,屠沽之流”者担纲,来自平民之属,(94) 以致有奏疏表“望取品子,年二十以下,容颜修正者,充令太常博士”。(95) 加之奏疏中类比周之雅舞者为诸侯子孙、隋制雅舞者为官宦子弟,且“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庙之酎”(96),至唐时雅乐歌舞表演者皆平民而惊怪。观其地位应该等同良人。但这些乐工之簿籍与其他乐工由太常统一管理,恐难真正区隔开来。
根据需要组成的太常乐工中的其他名色如工乐、番上乐户、太常音声人、长上乐户、杂户、官户,其身份就要次于专于雅乐歌舞表演的乐工,在待遇与役使上各有差异。
首先,在户籍方面,诸工(乐工)、乐(乐户)、杂户在州县并无户贯。太常音声人在州县也无户贯,虽然自义宁以来,在州县有了户贯,但仍在太常寺上番。同样上番(服役)官府的官户和杂户,前者在州县没有户贯,后者却有户贯。(97)
其次,服役方面,各色良贱乐人都要以一定的制度轮流上番。根据唐律,每年十月,都官按比。官户上番,可以分番,每年只为本司服役三个月;杂户每二年可以服役本司五个月,共上番75天。“十六以上当番请纳资者,亦听之。其官奴婢长亦无番也。”(98) 音声(人)上番,番期为一月,居一千五百里外,为节省旅程,两番并上。下番日则不给口粮。上番期间,官家发给口粮。(99) 因故不能上番者,可以纳资替代上番。(100) 尤其是两京官贱民上番是必须的,“若有故及不任供奉,则输资钱以充伎衣、乐器之用”。(101)“凡户奴婢及番户、杂户皆给其资粮及春、冬衣服等,数如司农给付之法”。(102) 太常音声人在其所属机构内分番服役,如前注(17)所言。太常乐鼓吹散乐音声人,“并是诸色共奉……宜免征徭杂科”。(103) 如果太常音声人应上番时因故不去,可以纳资替代或者请人代上。(104)
其三,受田方面,“凡官户受田,减百姓口分之一半。……贱口五人给一亩,五口加一亩,其口分、永业不与焉”。(105) 按唐代均田法的规定,男丁所受口分田是八十亩,那么官户就是四十亩了。杂户及太常音声人依令“老免、进丁、受田”,与百姓相同。(106)
其四,户婚限制中,(太常)杂户、官户及部曲、客女、公私奴婢,“止可当色相娶,不合与良人为婚”,不得辄娶良人。工、乐、杂户、官户,如有非同类身份相娶的,皆属“违令”;太常音声人既可以当色为婚(娶太常音声人),也可以“依令‘婚同百姓’,如有杂作婚姻者,依良人之犯论处”。(107) 当然,有乐工依色艺或某种机缘而与良人联姻的,如玄宗之娶赵丽妃,(108) 还如“舞柘枝女,韦应物爱姬所生也,流落潭州,委身乐部,李翱见而怜之,于宾僚中选士嫁焉”。(109)
最后,凡工、乐、杂户及太常音声人,“凡习乐立师以教,每岁考其师之课业,为上、中、下三等”。(110) 他们都收编在有关官署做课业训练,这种训练依法都有时限与考绩制度,课业学成者,皆不配役,回本监署当班;如果课业未完成,依有关的规定服刑役,还不得领衣粮。(111)《新唐书》中记载亦显示唐代乐伎训练与考核制度相当严格,技艺与服务内容、升迁密切相关。(112) 量刑和负担杂差方面,更将乐户、工户与太常音声人和杂户中的部分人所具有的身份相区别。总体上,“若是贱人,自依官户及奴法”。(113) 工、乐与官户犯罪者,“与部曲同例。止坐其身,更无缘坐”。(114) 太常音声人“悉免杂徭,本司不得驱使。又音声人得五品已上勋,依令应除薄者,非因征讨得勋,不在除薄之列”。(115)
由上可见,唐律所谓诸色官贱民中,太常乐工已然可以享受良人身份及待遇,自然为最高者。譬如“于后筝簧琵琶人白明达,术逾等夷,积劳计考,并至大官。自是声伎入流品者,盖以百数”。(116) 这一史料反映了一个乐人的身份放免、因艺加勋的例证。位于这一等级中间的,是杂户。其放免过程即显示了其地位的获得过程。对于太常音声人与杂户,由于此二者皆有州县户贯,有着与百姓相同的正常家庭,如遇反逆缘坐亦与百姓无别。而工、乐官户在州县没有户贯,遇有反逆止坐其身,没有缘坐。由此可见,其地位当属最低者。不过,现实中很难区别,太常乐工的实际地位同于工乐,十分低下。
(二)教坊妓
太常寺所兼雅乐(传统仪式之需)与燕乐、散乐(娱乐音乐之属)之责到玄宗设立教坊之时,更加倾向于管理传统的仪式用乐,致散乐分离出来。于是直属宫廷的教坊伎乐表演人员一时甚众,有所谓内人、前头人、内人家、十家、宫人、搊弹家、皇帝梨园子弟、小部音声、散乐、杖内散乐、长上(乐)人、音声博士等。唐律明确,这些乐妓不隶太常,“饮籍教坊”,地位与官户相近。其间亦是“部有部头,色有色长”,《教坊记》所载教坊妓按色艺和服务位置分列即显示了这些乐人的地位次第。即便是教坊使,其领导归属中官,也不在政府正元官之列,皆属贱籍。譬如“长上人”,可能教坊内部的等级中居于较高地位,(117) 但与太常乐工相比,地位更为低贱。《北里志》所记载之教坊妓,也统合一定的组织之中,未见乐伎个体有自由、独立之身。并且,居所在平康里的乐妓,从南到北三曲,分陈贫富地位高低排列:“妓中有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循墙一曲者卑屑妓所居也。”同太常乐工一样,教坊妓亦有因艺加勋的情况,例如乐人吕元真“上衔之,故流辈皆有爵命,惟元真素身”。(118) 教坊与太常寺的关系显然十分密切。杨荫浏指出:“唐初武德年间开始有内教坊,归太常寺领导。”(119)《唐六典·太常寺》也谈到了太常需要用乐时,则自去教坊访诏短番散乐、长散乐(见前引注(17))。其他情况,由于材料过少,在此难做分析。
值得一提的还有梨园乐工的身份问题,笔者采信岸边成雄对教坊之与梨园关系的论断,“按梨园于成立初期,系以太常寺之乐工子弟三百人与宫女数百、乐妓若干为主,另加小部数十人而成,乐工收容于梨园侧近之本院与太常内之别教院(新院)……乐妓以却以宜春院为本据,却与宜春院之内人,与云韶之宫人以及太常寺移籍之乐工等组成”。(120) 史书无载有关梨园乐工身份之内容,但看到“梨园弟子”之从太常寺坐部伎和宫女中专门选拔的做法,根据太常乐工所有的法律身份,可以想见梨园乐工之地位十分特殊。散见于诗文中的记载和梨园乐工所奏法曲等精细典雅之音乐,表明梨园乐人总体上为唐代宫廷乐人之最优秀者,其获得性身份是不言而喻的。
(三)私奴婢乐人
唐律反映出私奴婢的社会身份与官奴婢在本质特征上是一样的。部曲、部曲妻、客女、随身、奴婢亦“身系于主”,可以随意买卖,同样只准与同类身份者结婚,遇事由主人依“奴法”处理。这几类中,随身系有契约在身者,契约解除后就能还身,其身份自然高于部曲。部曲不同于“资财”(121),是变相的资财,只能转移,不可买卖,其妻通娶良人,故而身份高于贱口奴婢。部曲之女客女亦同。由于奴婢多是卖身的贫苦农民及被劫掠拐卖的平民,这一低贱的来源,加之“律比畜产”,不得与良人为婚,决定了奴婢身份的低下。唐时私奴婢乐人(户),在适逢好的环境之时,亦会获得受尊敬的地位。譬如《旧唐书》所载一事,歌工长孙元忠之祖辈即受业于侯将军处学北歌,此后世代传授其业。(122) 诚如张振涛所指出的,“庇 护者对歌舞伎人赡给衣食,为以技艺为生的乐户解决了吃穿问题,而使其专心从事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123) 笔者以为,这一点对于私奴婢乐人身份的构建尤其重要。在唐及以前的社会中,居于这一身份的乐户不可能独立存在,其身份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并且极不稳定。
余论
基于唐律对唐代良贱乐人社会身份的,历史考察,不仅让我们可以看到唐代乐人的生存背景,还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唐时影响音乐形态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因素更是鲜明地体现出了唐代乐人的社会身份。
总体上,唐律在维护阶级压迫、为等级服务方面具有鲜明的特性。但同时唐律在处理普通社会(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侵害行为时,还体现出鲜明、典型的身份伦理属性。就唐代乐人而言,唐律认识的乐人就是对其从事乐事活动的“身份”的确认以及“身份”关系的法律调适,而非常言之“人”。这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基于伦理关系建构的社会角色,也是唐代乐人活动所具有的外显功能作用所致。唐代由于政治经济的繁荣对娱乐用乐有广泛需要,这样使得唐朝之“乐”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并在统治集团的倡导下得到空前发展。在政治上,由于“乐可以助教”,可以“表兴亡之盛烈”;在生活上因为“功成作乐”,可以满足娱乐享受之需。担纲音乐活动的主角——唐时官奴婢乐人因此具有着强烈的规定性角色。他们虽然身份确认但其地位并没有提高。从乐艺人的理想和信念更多地被专制制度支配,并按照内在的规定性通过音乐表演和创造活动来实现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且也只是观念上的社会地位,是相对的,非契约性的。
另外,唐时从乐艺人的身份制是否存在乐籍制度呢?从唐代乐人活动所具有的内隐功能来看,他们身份的活动并非全然受制度化所决定,而是传统式的伦理制度统御自然形成。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儒教是受过传统经典教育的世俗理性主义的食俸禄阶层的等级伦理……这个阶层的宗教的等级伦理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这个阶层本身,它规定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124) 如是,如果乐籍制度存在的话,那就是结合儒家身份伦理和国家法律的规定的产物。乐人的社会关系的基本性质受着这双重规定,其身份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而他的身份又是由传统的、典型的伦理等级关系来区隔。所以,在一种非契约性的社会关系中,受伦理秩序的制约,唐代良贱乐人依其在社会中占据的地位来标示其身份(先赋性[ascribed figure]),这一点在唐及以前的社会中是明确的。与官奴婢不同,唐时属贱籍的私奴婢乐人游走于规定性和开放性之间,具有较大自由和发挥的余地,加之心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愿景,将其所擅长的乐事活动处理得尤为灵活,并以此谋求获得性身份(除籍)。正是这两种身份乐人的存在,构筑起了唐代音乐上下两极交相辉映的歌舞表演景象。从上而言,唐律并未明确有一种乐人制度存在,而是由于整合了诸如太常乐工、工、乐杂户群体作为生活在这种法制环境中,约定俗成地显示出的一种制度(如项阳之谓“乐籍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或影响着音乐的发展,一方面受社会中“高贵者”的需要而使其乐事与乐充满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一方面既是自身的出现、既是谋求生存发展的需要又为满足享乐阶层的文化娱乐需要,更多地表现出鲜明的商业文化发展特征和充当传播媒介的角色。总之,由于“高贵者”对音乐的喜好而致贱籍乐人大量出现,其存在的形态与相关活动构成了社会音乐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唐代乐人的社会身份的创造、变迁及强化因之表现为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现象,其情状即如此。
再者,唐代业已存在的乐人制度所具有的隐性功能在于这一制度的贱籍模式,表明了乐人生存与地位的低下,无人身自由,他们居于同一阶层并对这一阶层有强烈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不是法律的保障,也不是信仰的作用,而是作为音乐文化的共同体由于参与音乐的传承与创造而产生的亲密感觉而获得归属。在显性的“乐”中,隐形的乐人生活具有着社会生活的抽象特征。他们一方面由于社会地位卑贱而受礼俗的约束与羁绊及社会人的歧视;另一方面又因行业性质特殊和个体艺术魅力而受到捧场,有较大的活动空间。其结果使得他们在社会上形成一种特殊的阶层,在社会上和心理上产生一种隔离现象。这种现象在职业、婚姻上都非常容易形成世袭的职业群体和群体内的婚配,以及近似的生活规律(如不稳定的生活、晚境的凄凉等),同时这两种现象又是互为作用,更加鲜明揭示了乐人社会身份的二重性。唐代乐人贱籍模式的实质反映出来中国古代契约化过程所具有的身份制,实际上是一种恩主-身份制的残余。恩主制作为束缚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契约关系,是宗法家族主义的顽固体现,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内在因素。从乐人制度所具有的隐性功能来看,唐代乐人社会身份的二重性成型于唐,衍生于宋以后,虽有变迁,但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
最后,对唐代良贱乐人的社会身份的历史考察,我们还可以看到唐代乐人所具有的社会身份既是中国古代等级身份制度和儒家礼学观念的反映,又是基于音乐作为一种职业且因其属“太常”可令“国家盛大常存”的实践。(125) 唐代良贱乐人身份制度的典型形成,深受多种因素的作用,它既有现实的社会基础,又有因袭前代的一面,其实质上反映出创造音乐文化的人(良贱乐人)其实依照一定制度的规定在进行音乐创作与表演(生产关系),对社会音乐文化形态的形成,表明了一种趋向专业化、组织化和制度化的行乐体系业已形成,同时还体现出一种文化下移造成的文化日常化、世俗化的趋势正在形成。唐时乐人尤其是私奴婢乐人在民间音乐传播中所起到的作用开始浮现,不仅意味着官府施行的乐人制度基本走向社会,而且这一制度的参与者也由贵族及统治阶层向文人士大夫阶层拓展,更为重要的一点,基于乐人而发生的音乐交往活动的成果成了一种文化积淀,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正是由于这些,对于宋代音乐走向市民化铺就了良好的基础,对于宋以后宫廷音乐的管理与实践提供了现成的传统。
注释:
① (宋)欧阳修撰《新唐书·礼乐志》卷22,载《二十五史》“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58页。
②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236—246页。
③ [日]岸边成雄著,梁在平、黄志炯译《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上、下册),台湾中华书局1973年版。
④ 张振涛《论恩主——关于中古伎乐发展阶段乐户与庇护者依附关系的初步探讨》,《中国音乐学》1994年第3期。
⑤ 项阳《山西乐户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⑥ 项阳《论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的关系——兼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载《当传统遭遇现代》,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⑦ 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⑧ (宋)欧阳修撰《新唐书·选举志》卷45,第131页。
⑨ (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刘文俊点校)卷第3(28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4页。
⑩ 《唐律疏议》卷第14(20条)疏文,第57页。
(11)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史》第4卷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7页。
(12) 《唐律疏议》卷第4(36条)、卷第3(28条)疏文,分别见第97、75页。
(13) 同注⑦,第11页。
(14) 《唐律疏议》卷第3(20条)疏文,第57页。
(15) (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尚书刑部》(陈仲夫点校)卷第6“工乐户”即“工乐杂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03页。另见《唐律疏议》卷第3(28条)疏文,第74页。
(16) 《唐律疏议》卷第12(159条)疏文,第238页。
(17) 《唐六典·太常寺》卷第14“太乐署”条载:“凡乐人及音声人应教习,皆苦薄籍,覈其名数而分番上下(短番散乐一千人,诸州有定额;长散乐一百人,太常自访诏)。”第406页。
(18) (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元代胡三省音注)卷196“唐纪十二·太宗贞观十七年”,中华书局2005年版。
(19)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76“太宗诸子”,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2页。
(20) (宋)此山贳冶子撰《唐律释文》卷第23“斗讼”。
(21) 《唐律疏议》卷第6(47条疏文),131页。
(22) 《唐律疏议》卷第17(260条)疏文,第334页。
(23) 《唐六典·尚书刑部》卷第6“都官郎中”条载:“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第193页。
(24) 《唐律疏议》卷第14(191条),第269页。
(25) 《唐律疏议》卷第6(47条)明确有“诸官户、部曲、官私奴婢有犯”之说,第131页。
(26) (唐)魏徵等撰《隋书》卷15“志第十·音乐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4页。
(27) (唐)崔令钦撰《教坊记》(罗济平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8) 欧阳修撰《新唐书·百官志》卷48,第137页。
(29) (唐)李峤《上中宗书》,载(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247,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97页。
(30) 《新唐书·礼乐志》卷22,第57页。
(31) 据《太真外传》,转引白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第236页。
(32) (宋)陈旸撰《乐书》卷188,载文渊阁影印《四库全书》第211册,第849页。
(33) 《新唐书·礼乐志》卷48,第137页。
(34) 《旧唐书》卷28“志第八·音乐一”,第893页。(宋)王钦若等编撰《册府元龟》(周勋初等校订)卷569亦记有此数据,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
(35)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33“清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13页。
(36) 《新唐书·礼乐志》卷22,第58页。
(37) (唐)段安节撰《乐府杂录》(罗济平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8) 同注(37)。
(39) (唐)慧立、彦悰等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9,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9页。
(40) 《唐会要》卷86“奴婢”,第1860页。
(41) (唐)杜佑撰《通典》卷35“职官十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42) [日]石田干之助著《唐代风俗史钞》“长安的歌妓”(上),第102页。转引自巴冰冰《浅析〈北里志〉中娼妓的属性》,《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增刊。
(43) 《唐会要》卷34“杂录”,第736页。
(44) 《旧唐书》卷145“列传第九十五·陆长源”,第3317页。
(45)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431页。
(46) 《旧唐书》卷105“列传第五十五·韦坚”,第2667页。
(47) (宋)王谠撰《唐语林》(周勋初校证)卷3,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9页。
(48) 《唐会要》卷34“杂录”,第735页。
(49) 《唐会要》卷34“杂录”,第733页。
(50) 《新唐书·列传第三》卷78“河间元王孝恭”,第353页。
(51)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全三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页。
(52) (魏)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校释》(周祖谟校释)卷3·高阳王寺载:“贵极人臣,富兼山海。……僮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则鸣驱御道,铙吹响钹,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7—138页。
(53) 参见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54) 唐五代敦煌写本《下女词》,转自刘半农《敦煌掇琐》,《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特刊》第五号本,1957年版。
(55) 《唐六典·内官宫官内侍省》卷第12“掖庭局”条,第358页。
(56) 《唐六典·尚书刑部》卷第6“都官郎中”条,第193页。
(57) 同注(47)。
(58) 《唐律疏议》卷第3(20条)疏文,第57页。
(59) 《唐会要》卷34“论乐”,第728页。
(60) 《隋书》卷15“志第十·音乐下”,第373—374页。
(61) 《唐六典·尚书刑部》卷第6“都官郎中”条,第193页。
(62) 《唐律疏议》卷第17(248条)疏文,第321页。
(63) 《新唐书·刑法志》卷56,第155页。
(64) 《旧唐书》卷19上“懿宗”,第576页。
(65) 《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435页。
(66) 《新唐书·后妃传》卷76“韦皇后”,第349页。
(67) (唐)范摅撰《云溪友议》卷上“舞娥异”,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68) 《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卷83“中宗八女”,第368页。
(69) 《唐律疏议》卷第4(35条),卷20(292、293条)及疏文,分别见第93、369、371页。
(70) 《唐律疏议》卷第5(43条),第117页。
(71) 同注(51),第4页。
(72) (唐)顾况撰《囝》,载《全唐诗》卷264,中华书局1960年版。
(73) (宋)李昉撰《太平广记》卷188“元载”,中华书局1981年版。
(74) 《唐律疏议》卷第6(47条),第132页。
(75) 《新唐书·列传第四十三》卷118“张廷珪”,第438页。
(76) 同注(37)。
(77) 唐代文献中如《旧唐书》所载“新罗传”、“裴漼传”、“德宗纪上”、“宪宗纪”、“穆宗纪”、“代宗”,及《唐会要》卷99“南诏蛮”等均有记载。专题研究如沈冬《唐代乐舞新论》之“骠国献乐的经过”更是详细地为我们展示了骠国为与唐朝修好,主动要求献夷中的这一历史事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161页)。
(78) 《唐会要》卷86“奴婢”,第1860页。
(79) 《旧唐书》卷161“李光颜”,第3584页。
(80) 《旧唐书》卷17上“文宗李昂”,第437、438页。
(81) 据李季平《唐代奴婢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
(82) 唐代文献中如《旧唐书》卷78“江夏王道宗”、“河间元王孝恭”,“李靖传”、“李大亮传”、“姜谟传”、“薛仁贵传”、“来俊臣传”、“玄宗纪下”等,及《新唐书》“马周传”、“李林甫传”等文献中,对赏赐奴婢事例中数目较大者,均有记载。
(83) 参阅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唐代历次获俘战争统计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8—389页。
(84) (唐)赵璘撰《因话录》卷1“宫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85) 《旧唐书》卷164“李绛”,第3649、3650页。
(86) 《唐六典·太常寺》卷第14“太乐署”条,第404页。
(87) 《通典》卷146“乐六”,第761页。
(88) 《唐律疏议》卷第22(321、323条),第406、407页。
(89) 《唐六典·尚书刑部》卷第六“都官郎中”条载:“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第193页。《旧唐书》“职官志二”亦载有这一放免文书。
(90) 《唐会要》卷33“清乐”,第713页。
(91) 《唐会要》卷86“奴婢”载:“景龙三年,司农卿赵履温奏请以隋代番户子孙数千家没为官奴婢,仍充赐口,给以贵悻。监察御史裴子馀以为官户承恩,始为番户,且今又是子孙,不可抑之,奏免之。”第1860页。
(92) 《唐六典·太常寺》卷第14“太常卿”条,第394—395页。
(93) 《通典》卷25“职官七”,第148页。
(94) 前引注释《唐六典·太常寺》卷第14“太乐署”条(第404页)就载有这一史料。
(95) 《通典》卷147“乐七”,开元八年(720)九月瀛洲司法参军赵慎言《论郊庙用乐表》,第766页。另有二书亦载有赵慎言奏疏一事:《唐会要》卷32“雅乐上”,第694页;赵慎言《郊庙舞人宜依古制疏》,载《全唐文》卷304,第3094页。
(96) 《通典》卷25“职官七”,第148页。
(97) 《唐律疏议》卷第6(47条)疏文、卷第12(159条)疏文,分别见第131、238页。
(98) 《唐六典·尚书刑部》卷第6“都官郎中”条,“番户、杂户,则分为番(番户一年三番,杂户二年五番,番皆一月)”,第193页。另《新唐书·百官志一》卷46“都官郎中”亦见同样记载,第133页。
(99) 《唐六典·尚书户部》卷第3“仓部郎中”条载“诸官奴婢皆给公粮,其官户上番充役者亦如之”,第84页。
(100) 《新唐书·百官志》卷46“都官郎中”载“不上番,岁督丁之,为钱一千五百,丁婢、中男,五输其一”等,第133页。
(101) 《唐六典·太常寺》卷第14“太乐署”条,第406页。
(102) 《唐六典·太子家令寺》卷第27“典仓署”条,第699页。
(103) 《唐会要》卷33“散乐”,第714页。
(104) 参阅《新唐书·百官志》卷48“大乐署令”,第137页;《唐会要》卷33“散乐”,第714页;《唐会要》卷34“杂录”,第733页。
(105) 《唐六典·尚书户部》卷第3“户部郎中”条,第74—75页。
(106) 《唐律疏议》卷第3(20条)疏文、卷第17(249条)疏文,分别见第57、324页。
(107) 《唐律疏议》卷第14(192条)疏文,第270—271页。
(108) “乐人赵元礼自山东来,有女美丽,善歌舞,王幸之,生废太子瑛”,见《旧唐书》“列传第56·张暐”,第2689页。
(109) “舞柘枝女”,见《全唐诗》卷802。
(110) 《唐六典·太常寺》卷第14“太乐署”条,第406页。
(111) 《唐律疏议》卷第3(28条)疏文,第75页。
(112) 《新唐书·百官志》卷48“大乐署令”,第137页。杨荫浏对这一考绩制度有详细解释,只是材料出处有谬。参阅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第233—234页“大乐署”内容。
(113) 《唐律疏议》卷第3(28条)疏文,第74页。
(114) 《唐律疏议》卷第17(249条)疏文,第324页。
(115) 参阅《新唐书·百官志》卷48“大乐署令”,第137页;《唐会要》卷33“散乐”,第714页;《唐会要》卷34“杂录”,第733页。
(116) 《唐会要》卷34“论乐”注文,第728页。
(117) 《唐律疏议》卷第7(64条)疏文:“诸应入宫殿,未著门籍而入;虽有长籍,但当下直而辄入者;各减五等。”疏文有解,长籍,相对于临时应入者的临时名籍而言,长上人及一日上、两日下之人皆有长籍。因此,长上人可能是一种身份称谓,其身份之居于何状况,文献无记载。第155页。
(118) 同注(27)。
(119) 同注②,第234页。
(120) 同注③,第231页。
(121) 《唐律疏议》卷第17(248条)疏文,第322页。
(122) 《旧唐书》卷29“志第九·音乐二”,第908—909页。
(123) 同注④。
(124) [德]马克斯·韦伯,王容芬译《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页。
(125) (梁)沈约撰《宋书》卷39“百官上”,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