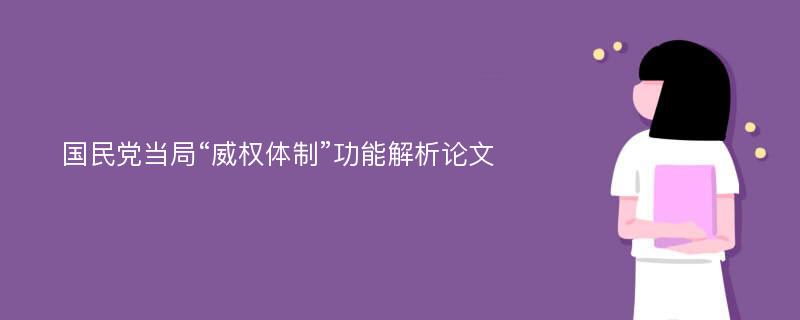
国民党当局 “威权体制 ”功能解析
严 峻
〔内容提要〕 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后,实施一种“威权体制”性质的统治。这种“威权体制”一方面压制台湾民众的政治权利,但另一方面在社会、经济、文化上也发挥了一定的功能:一是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之前,保证了台湾社会的总体稳定;二是台湾经济在这种相对集权体制的推动与保障下快速发展,而且基本上做到了社会贫富差距并未随之拉大;三是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的推广。
〔关键词〕 国民党当局 “威权体制” 功能
1945年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在台湾实行“军政一元”、较为集权的统治。1947年元月“中华民国宪法”公布后,全国进入所谓“宪政”阶段,但国民党当局不久后即以“应对内战”为由于1948年5月由“国民大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紧急处分权”。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当局所谓的“中央政府”正式移至台北,此后不仅延用“动员戡乱体制”,[注] 国民党当局于1960、1966年对“动员戡乱条款”进行修正,大幅增加“总统”权力,使“宪法”中相关条文形同被冻结。 而且通过戒严法令,[注] 1949年5月19日,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签发戒严令,以“确保本省治安秩序”的名义宣布自5月20日零时起全省戒严。这个戒严令的法源依据是国民党政府1934年11月制定的“戒严法”,但那时台湾既未被认定为作战区域,于是在“国防部”电请“行政院”将台湾划定为“接战区域”后,“立法院”于1950年3月14日追认上述戒严令,自此台湾进入戒严状态长达38年,直至1987年7月“解严”为止。 在台湾全面实行“党禁”、“报禁”等措施,[注] 1941年在大陆制定的“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未加改动被沿用到台湾并实施近40年(直到 1987年底才由“人民团体组织法”所取代),成为禁止台湾民众组党之“党禁”的法律依据。另外,国民党当局1951开始严格限制新报纸的登记,等于实行了“报禁”。 使台湾处于某种“威权体制”之下。“威权体制”(authoritarian regime)的概念是由美籍西班牙学者胡安·林兹(Juan J. Linz)在1964年首次提出来的,[注] Juan J. Linz:“An Authoritarian Regime: Spain”, in Erik Allardt and Stein Rokkan, eds., Mass Politics: 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0. 此后被指一种公权力对社会高度控制与支配的政治形式。[注] Perlmutter, Amos, Modern Authoritarian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多年来学界针对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实施“威权统治”的讨论,更多聚焦于其高压残暴的一面,对于这一历史事实,笔者亦赞同。但从全面、客观的角度看,当年国民党当局实施“威权体制”也产生了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等功能。本文重点从这一以前学界较少论述的角度再探国民党当局“威权体制”之功能,以期通过史料梳理,更深入真切地理解今天台湾的政治生态与社会心理。
一 、“威权体制 ”在保持台湾社会总体稳定上的功能
国民党当局迁台后实行一种“威权体制”,从组织上将国民党的控制力深入到各级公权力部门及民间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舆论宣传上保证了国民党的意志在意识形态及思想文化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这种组织与思想的双重控制,使有威胁性的政治异见难以出现,或者出现后难以形成为社会主流思潮,有组织的反对运动更是难以动员及壮大,[注] 20世纪80年代之前,对国民党当局唯一有威胁意义的反对思潮与运动是雷震组织的“自由中国”运动,但这也主要在知识精英中较有影响,在台湾社会普通民众中则影响力有限,当雷震等人试图与地方派系相结合走上有组织的反对运动道路时,当局即对其收监,使该运动夭折。 这基本保证了台湾社会的总体稳定。当然,这种稳定也必须“归功”于严酷的“戒严体制”,[注] 陶涵:《蒋经国传》,台北:时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页。 因为群众聚会、街头抗议、罢工等运动都为戒严法令所严格限制。但学界对戒严时期戒严法令真正实施的程度有不同意见,有观点认为这些法令更多起到的是吓阻的作用,真正实施的仅占全部法令的3%。[注] 孙代尧:《台湾威权体制及其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但也有观点认为多数法令还是被真正施行,“‘戒严令只实施百分之三’的谬论,成为法学界一时之笑谈”。[注] 于尚白编:《国民党台籍政客实录》,台北:台湾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页。 现在学界多认为,当时“戒严法”未全部实施,对民众生活较有影响的方面主要体现在非军人在特定罪名下须受军法审判、限制入出境、管制出版物、禁止组党与游行这几项。[注] 齐光裕:《“中华民国宪政”发展与“修宪”:1949年以来的变迁》,新北:扬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33页。
另外,“威权体制”还防止了多党林立及政党竞争现象的出现,“政治上较易维持团结和谐”,并且“阻止了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和颠覆”。[注] 葛永光等:《现代化的困境与调适:“中华民国”转型期的经验》,台北:幼狮文化公司1989年版,第15页。 可以说,国民党当局在岛内搞“白色恐怖”,“筑起一张又一张的绵密的政治警察网”,而台湾在东西方“冷战”中所获得的所谓“封锁中国大陆的前哨基地”的地位,也“正好为国民党的这种做法提供了绝佳藉口”。[注] [日]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陈培豊等译:《战后台湾政治史》,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11页。 但总体来看,台湾当局法令是“压”、“硬”的一面,国民党影响力的渗透则具有引导及相对柔性的一面,二者相结合,使社会各主要阶层的反抗意识与能力大为下降。例如,国民党掌控下“装饰性、被阉割、御用”的工会组织所拥有的劳工是“和平、温驯、容易管理的社会阶层”;[注] 徐正光:《从异化到自主:台湾劳工运动的基本性格和趋势》,徐正光、宋文理编:《台湾新兴社会运动》,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103页。 “威权体制”下的台湾大学生“顺从权威且保守”,是一群“沉寂的学生”。[注] Sheldon Appleton著,施国勋译:《沉寂的学生与台湾的前途》,载丁庭宇、马康庄编:《台湾社会变迁的经验——一个新兴的工业社会》,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203页。 可以说,在国民党当局“刚柔并济”、软硬兼施的威权统治下,台湾社会至少在上世纪70年代末之前总体上保持相对平稳。
二 、“威权体制 ”在台湾经济发展及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功能
台湾经济自20世纪50年代就成功转化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国民生产毛额”(GNP)在1964-1973年间年均增长高达11.1%,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了以“十大建设”为标志的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虽经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1974-1979年间年均增长率也有8.4%。[注] [日]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陈培豊等译:《战后台湾政治史》,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90页。 虽然在“威权体制”下罢工等权利被压制,但制造业工人的实质薪资却随着经济增长不断上升,年均增长率在20世纪50年代为2.5%,20世纪60及20世纪70年代约为5%,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上升为7.4%。[注] 瞿宛文:《台湾经验:民主转型与经济发展》,载于朱云汉等:《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7-38页。 更为难得的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经济成长一直是在民众所得差距不大的情况下进行的,台“行政院主计处”数据甚至显示,按“家庭收入五分法”统计,台湾最富家庭与最贫家庭的收入比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从1964年的5.33∶1降至1980年的4.17∶1。[注] 台湾“行政院主计处”编印:《“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国民所得统计摘要》,1989年,第56页。 台湾经济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威权体制”有关的部分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如上文所述,“威权体制”造就了相对稳定的台湾社会,这十分有利于吸引外商来台投资办厂,台湾学者调查发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商和日商来台投资最主要的诱因就是台湾“政治安定”。[注] 吴荣义:《美商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台湾“中央研究院”美国文化研究所编印,1978年,第51页;刘泰英:《日商来华投资对我国经济之影响》,台湾“行政院研考会”编印,1985年,第163页。 特别是在1984年“劳工法律支援会”成立前,台湾一直未曾出现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只有非常少量的劳资纠纷,[注] 张茂桂:《社会运动与政治转化》,台北:财团法人张荣发基金会1991年版,第58-59页。 例如1963年一年全台数百万劳工中仅有555人卷入20个劳资纠纷中。[注] 徐雅媛:《劳工立法不容忽视》,台湾:《时报杂志》,1984年7月10日第188期,第45页。 这样的安定环境不仅有利于吸引外资,事实上也十分有利于本地企业的发展。
其次,国民党当局迁台初期的台湾,民间企业力量弱小,这时“威权体制”下的公营资本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引领作用。[注] 当时台湾公营企业(含“国营”企业、台湾省营企业、国民党党营企业)掌控交通、能源、金融等重要经济命脉。 主持制定了台湾第一、二期“四年经建计划”的尹仲容回忆说,制定经建计划的目的,“在求以最迅速有效的方式,动员一切经济资源,从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当局)站在领导的地位,策划、推动、奖励、扶植、保护。如果政府不采取这种积极态度,仅凭民间自动自发地去做,则经济发展的速度将比现在落后得很多”。[注] 尹仲容:《我对台湾经济的看法(三编)》,台北:“行政院经设会”编印,1963年11月,第67、70页。 台湾经济腾飞的重要操盘手之一李国鼎也总结道,虽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是一直朝自由经济方向去发展”,但“牢固、强大的官僚政治和中央集权政府”积极干预经济,可以“帮助经济的各种部分首先站起来,然后学会走路,再放手让他们自己走”,“事实上,政府过去曾担任民营企业的代管人、新事业的创办人、供应原料、收购成品及冒最大的风险提供企业所需的贷款,这些工作在经济进步国家,都是为眼光远大的企业家和银行家所担任的;但在台湾经济发展初期,却缺乏此种人才,如政府不出来担任此种工作,民营工业将很难迅速发展起来”。[注] 李国鼎:《台湾经济发展背后的政策演变》,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243、102、5页。 在这种体制的扶持下,自1958年起台湾工业产值中,民营企业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公营企业,此后并持续直线上升。[注] 瞿宛文:《台湾经验:民主转型与经济发展》,载于朱云汉等,《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当然,国民党“维持国家资本的官营企业及计划主导国民经济的经济体制,乃是国民党政权生存的根本所在”,[注] 刘进庆:《新兴工业国的发展和新经济阶层》,台湾:《五月评论》,1988年7月号,第13页。 因为资金雄厚的党产以及“党库通国库”的做法,是维系“党国威权体制”必需的经济支撑,1952年国民党完成改造时党产约4500万元新台币,但通过多方经营1989年时已达约1000亿。[注] 杨泰顺:《国民党与在野势力的互动关系》,台湾“民主基金会”主办“中国的民主前途:台湾地区政治民主化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1990年11月11-12日,台北)论文,第9页。 但这也为后来国民党因此倍受政治对手攻击乃至2016年后因被清算党产几致瘫散埋下隐患。
2.3 尿酸盐溶液的酸碱度 在生理pH值状态下,MSU结晶的主要组成成分是尿酸盐离子。尿酸盐溶解度在pH值≤6或≥10时最大,在pH值为7~8时最小[10]。这可能与不同pH值条件下尿酸存在的形式不同有关:在37℃溶液中,当pH值较低时是以尿酸为主;在较高pH值时,以尿酸盐离子为主。另一项研究[11]发现,在37℃过饱和溶液中,pH值<5.62时,尿酸的浓度最高;pH值为5.62时,尿酸盐离子的浓度最高;pH值接近9时,尿酸盐离子开始转变为重尿酸盐离子。因此,通过改变尿酸盐溶液的酸碱度,可以对MSU结晶产生影响,微碱性环境促进痛风石的形成。
有观察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也伴随着国民党当局施行“威权体制”而在一定程度上在台湾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与推广。大陆学者周叶中、祝捷指出,在“动员戡乱时期”,国民党当局在台湾推行中华传统教育,“尽管这些活动的目的在于向台湾人民灌输‘反共复国’的思想,但在客观上对普及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台湾青少年的中国情怀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使统一深入人心”。[注] 周叶中、祝捷:《台湾地区“宪政改革”研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03页。 1945年台湾光复后,面对日本统治50年的台湾,国民政府采取相关措施以清除“皇民化”遗绪,例如1946年成立了“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在岛内推广“国语”(即大陆所称“普通话”)。1949年国民党当局迁台后更是大力倡导中华文化,《国民党党章》第二条规定该党要“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从1966年11月开始,国民党当局推展“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将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定为“中华文化复兴节”。在蒋介石的大力推动下,台湾出版了许多中国古代典籍,还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制定了“国民礼仪规范”,在中小学课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言语有关的占了一半左右。国民党当局之所以大力推广中华传统文化,与蒋氏父子及其身边重臣的文化偏爱有关,也与国民党当局强化意识形态功能有关,因为国民党宣称三民主义继承了尧舜以来的中华传统文化之“道统”,而儒家思想的政治理念与“威权体制”对权威的强调有某种契合度,“很显然,直到70年代初期,台湾人民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仍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一直都适应于并支持着国民党政府的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威权统治”。[注] 金耀基:《中国政治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144页。
由于飞船紧急自降到了漆吴山的山脚下,轩辕明只能带着几个学生徒步登上山顶。他指着东边那些丘陵说:“书上记载,漆吴山地处东海,我们正望着太阳所在的地方。”
最后,为使“威权体制”得到多数台湾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当局利用其威权采用相对平均主义式的分配模式,压低城乡、大小企业间薪资水平的差距,[注] 瞿宛文:《台湾经验:民主转型与经济发展》,载于朱云汉等《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而贫富差距不大事实上也有助于台湾社会的总体稳定。诚如有学者指出,“光复后台湾地区威权体制的特色,除表现在以戒严法为中心而限制某些基本人权和公民参政权的政治层面外,还包括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管制……”[注] 萧全政:《国民主义:台湾地区威权体制的政经转型》,台湾:《政治科学论丛》,1991年第2期,第73页。
三 、“威权体制 ”在台湾推广传统文化上的功能
再次,经济技术官僚在“威权体制”的庇护下,能够充分发挥经济专长,拥有较大决策与自由裁量权,这也是台湾经济能够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有研究发现,至少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行政官僚在决策上自主性的上升,党政关系不再是“以主义决定政策”的“以党领政”的关系,相反地,呈现一种党替行政官僚排除政治、社会障碍使其拥有更大决策空间的“以政领党”的关系。[注] 杨泰顺:《国民党与在野势力的互动关系》,台湾“民主基金会”主办“中国的民主前途:台湾地区政治民主化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1990年11月11-12日,台北)论文,第11页;曹俊汉:《塑造中国国民党为公共政策政党刍议》,台湾“民主基金会”主办“政党政治与民主宪政”学术研讨会(1991年3月29-30日,台北)论文,第19页。 这种判断有其道理,但只是看到问题的一面,因为从另一面看,当时专职党工乃至党的高级干部较少干预行政官僚尤其是经济技术官僚决策,恰恰是依循国民党最高领导的旨意。事实上,“蒋介石和陈诚将在大陆的失败归咎于经济崩溃的拖累,所以他们在台湾给予受过西方训练的专家更大的空间,而不像在大陆时那样事事干预”,[注] Thomas Gold,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New York: M. E. Sharpe,Inc., 1986, p.67. 所以先后担任过“美援会”副主委的尹仲容、严家淦及“美援会”秘书长的李国鼎是当时台湾最具实权的技术官僚。[注] 孙代尧:《台湾威权体制及其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 尹仲容甚至不是国民党员,但仍得到国民党最高层的信任与支持,这较有力地排除了国民党党工对经济的干扰,避免了外行领导内行。[注] Wincker, Edwin A.,“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n Taiwan: Fro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The China Quartly,No.99,1984, p.28. 也正因有此底气,尹仲容在经济建设上经常敢于做出高风险的决定。[注] 瞿宛文:《台湾经验:民主转型与经济发展》,载于朱云汉等,《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当然,经济官僚之所以能有较大的自主性,也与美国的态度有关,因为当时“美援”是台湾经济的重要命脉,[注] 从1951到1965年,台湾总共接受美国援助15亿美元,是同期美国对外援助中金额最高者,这对维系国民党当局执政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国民党当局不敢得罪美国援助团的重要原因之一。参见王旭堂:《先进国家与开发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台湾与美国四十年来经贸关系的案例研究》,台湾:《台湾银行季刊》,1991年第42卷第4期,第10页;Tucker, Nancy B.,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1945-1992), 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 1994., p.54. “美援的运用,因需征得美方同意,对国内部分财经政策之形成,往往有决定性的影响”。[注] 尹仲容:《美援运用之检讨》,载尹仲容:《我对台湾经济的看法(续编)》,台湾“行政院经设会”编印,1963年11月,第88页。 而美方与这批大多留美的台湾经济官僚的关系又十分密切,相关经济会议一般只用英语进行,这也是那些语言能力不逮的党工没法参与的原因之一。另外,国民党当局为运用“美援”先后成立的“美援会”、“农复会”、“经安会”等机构的人事、预算,在“威权体制”的运作下均独立于一般行政单位之外,这在相当程度上隔绝了国民党传统官僚对经济问题的干预。[注] 文馨莹:《经济奇迹的背后:台湾美援经验的政经分析(1951-1965)》,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页。 还需要指出的是,出于国际两大阵营斗争的需要,美国虽然也鼓励台湾地区发展私营企业及迈向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但对国民党当局“威权体制”至少是默许的。受国际开发署(AID)委托调研对台“美援”的尼尔·雅各比(Neil H. Jacoby)曾指出,“美国没有利用经援推动(台湾)政治改革及民主化,而是塑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威权政府”。[注] Neil H. Jacoby,U.S. Aid to Taiwan, New York: Praeger, 1986, p.244.
当然,也有学者指出,国民党当局主观上也有以文化标榜其“法统正朔”并以之作为压制手段的用意,这也给台湾社会反对运动利用“省籍矛盾”、“族群矛盾”攻击国民党提供了依据。有观察指出,国民党当局在倡导中华传统文化时,却对同属中华文化的台湾本地文化进行一定的压制,例如不允许在正式场合讲“台语”(其实是中国南方闽南语的一支),并用没有学好“国语”作为排斥、限制台湾本省人进入更高层次公务机关的借口。相关歧视措施引起了台湾本省人的不满,并往往利用选举的“民主假期”用闽南语进行政治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所谓的“族群矛盾”。例如当时“康宁祥创造了一种以台语(福佬话)谈台湾史,对国民党进行异论控诉的政治沟通风格……(选举期间)在街头招致人山人海的场面”。[注] [日]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陈培豊等译:《战后台湾政治史》,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185页。 事实上,蒋经国主政后比较重视台湾本地文化,在文宣上强调台湾人是在台湾拓展的中华民族一份子,台湾文化源于中华大陆,[注] 陈奇禄:《中华民族在台湾的拓展》,载于陈怡真:《澄怀观道——陈奇禄先生访谈录》,台北:“国史馆”1971年版,第327-343页。 这就较好地理顺了中华传统文化与台湾本地文化的关系,得到了众多台湾本省人的认可与支持。
由ADF检验可知,股价的ADF值大于0.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故应当接受存在单位根假设,认为股价是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后的序列,其ADF值小于0.01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差分后的序列是平稳的;同理,投资者情绪序列在0.1显著水平下是平稳的,一阶差分后的序列在0.01显著水平下是平稳的。故股价和投资者情绪的一阶差分序列是同阶单整序列,说明投资者情绪和沪深300指数的波动是平稳的。
总之,国民党当局“威权体制”有其消极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国民党迁台后所建立的威权政体,有效维护了台湾的社会稳定,促成经济的快速成长”,然而“快速的经济成长,及伴随而来的社会结构变迁,激发了人们政治参与的意愿,以及对国民党政权合法性的质疑,而成为国民党政府严峻的挑战,进而促成台湾的政体转型”。[注] 金国柱:《中国国民党的转型:路径依赖的观点》,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54页。
An Analysis of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Kuomintang Authoritarian System
Yan Jun
Abstract : Afterits retreat to Taiwan, the Kuomintang authorities enforced rule of “authoritarian system”. On the one hand, this “authoritarian system” suppressed the political rights of the then Taiwanese,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played a certain role in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first, it assured the overall stability of Taiwan’s society at least until the late 1970s; second, Taiwan’s economy developed rapidly under the promotion and guarantee of this relatively centralized system and at the same time did not widen the social gap between the wealthy and the poor; third, it helped to promot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aiwan to some extent.
Keywords: the Kuomintang administration, authoritarian system,positive effect
〔作者介绍〕 严 峻,全国台湾研究会副秘书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肖杨)
Author: Yan Jun is Researcher and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National Society of Taiwan Stud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