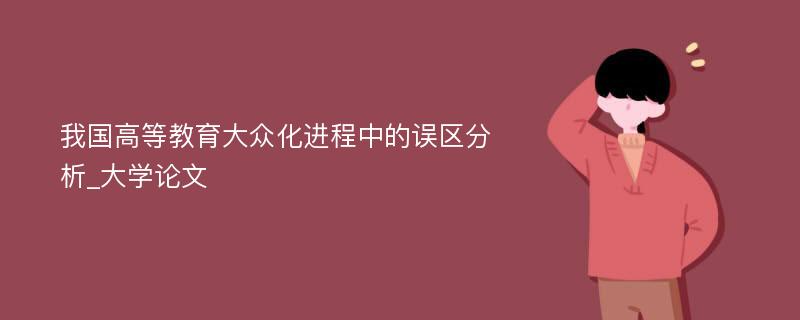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误区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误区论文,进程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3)04-0114-08
所谓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依据美国学者马丁·特罗于上世纪70年代总结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时提出的,即当毛入学率达到15%-50%时,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纵观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轨迹,美国在20世纪40-50年代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英、法、德等西方国家经过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到七八十年代也陆续进入大众化阶段。可以说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由于各国的文化历史传统不同,经济政治发展的特点不同,遂使得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实现的条件、动机、路径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大众化所面临的问题亦各具特点。对此,我们应借鉴西方国家这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先到者”的宝贵经验,科学、理性地推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在高校扩招之后,高等教育呈现出“有需求、无动力”的严峻局面,这是政府、社会以及整个高教界必须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本文仅就大众化的动机、经济基础、社会需求等方面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引起人们的思考。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一个概念的误读
就一般而言,所谓高等教育大众化即是根据美国学者马丁·特罗1973年在《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一文所提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50%,高等教育即进入大众化阶段。从表面上看,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个具有定性性质的数量化指标,其实不然。“高等教育”有着丰富的内涵,不同的解读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高等教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者那里有着不同的解释。在中世纪的西欧,其高等教育仅限于大学——是一种具有行会性质的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专门的、独立的学术与教育机构。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到19世纪后半期高等教育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这在美国表现得比较明显。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签署了著名的《莫里尔法案》,其法案规定:联邦政府按1860年分配的名额,每州按国会议员人数赠予公共土地或相等的土地期票(每人次三万英亩),以作各州办学经费。于是在美国出现了许多“赠地学院”。二战后基于社会需要在大学、学院之下又派生出专科学校、社区学校等。所以,美国的高等教育既包括高层次的研究性大学和一般性的本科大学,同时也包括社区学院、专科学校及“函授”、“业余”、“成人”等非正规大学。可见,美国是把中等教育后的教育均称为高等教育。
而在有着厚重高等教育传统的欧洲,一些国家则对高等教育概念界定得较为严格。《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对高等教育界定后的解释中说:“各国对各级教育机构命名不一,教育体制各不相同,这个解释必然不够全面。世界各国除建立高等教育机构外,又以各种不同方式对那些不能或不拟进入高校,但又愿意继续受教育的年满18岁的成年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一般来说,这种学习与正式大学相比,其学程较短,学习要求也不严格,这种教育以归入成人教育为益”[1](P3)这也就是说:高等教育机构不包括正式大学以外的专科性质的教育及非正规大学。潘懋元先生在我国出版的第一本《高等教育学》中提出:“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一般全日制大学本科生的年龄是20岁左右的青年。”此时,可以认为高等教育是以大学为主的专业教育。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高等教育呈多类型、多层次的发展趋势,高等教育的内涵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把高等教育定义为“完全的中等教育基础上进行的专业教育,是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活动”。但在众多国人的思想意识中高等教育仍局限于正规大学教育。
由于对“高等教育”的内涵理解的不同,其高等教育大众化实现的方略和路径自然也有很大区别。如第一个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美国,由于把中学以上的高等教育均称为高等教育,所以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路径主要是依靠社区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完成的;英、法等欧洲国家受传统高等教育观念的影响,以大学为高等教育主体,所以,其高等教育大众化则主要在正规大学中完成的。结合中国近几年推进大众化的基本进程,笔者发现,虽然我们在理论上把高等教育定义为“中等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也就是说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应该由所有中等以上教育机构完成,但在大众化起步的过程中,我国却从上至下、自始至终贯穿着“大学大众化”、“精英大众化”的思想,这既有悖于高等教育的内涵,也不利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由于对“高等教育”的概念界定不清,在操作过程中出现“精英式”高等教育大众化之现象及有需求无动力的被动局面,具体表现为,大众化战略初始,一些职业技术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纷纷告急,几成崩溃之势。事物的发展规律在于首先要确定是“什么”,即通过分析与综合,清楚明了地界定概念,把握其内涵与外延。要想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进行科学、理性的分析,真正推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清楚高等教育大众化概念的基本内涵。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初始阶段的主观功利性
动机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是获得良好效果的直接前提,是对“是什么”的进一步追问。良好的结果需要善意的动机,但善意的动机未必都能得出良好的结果。其原因在于动机的确立是否揭示了事物的本质,是否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迫切需要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但是,这种必要性和迫切性并不能替代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现实推进路径中的理性追问。应当承认,由于一部分人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缺少深层次的追问与反思,故在大众化的确立之初即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具体表现为:
快速发展高等教育,争当教育强国。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培养人的活动,教育的社会功能决定了在众多情况下,教育是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甚至政治发展的重要支柱及标志。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国人发现西方国家已于战后率先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一种由“落后”而产生的焦虑和急躁油然而生。尤其是到90年代美国毛入学率已达82%,高等教育实现普及化,日、英、法等发达国家及韩国、菲律宾、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在30%以上,而中国的高等教育却仍然在精英教育阶段徘徊。于是在1999年1月提出:2010年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15%,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2001年3月又提出:200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力争达到15%左右。纵观国外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程,无论是西方的发达国家,还是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国家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从本质上看,其大众化的推进大多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内部生成过程,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动因或是由于经济发展,社会需求强烈;或是为提高民众整体素质,争取政治民主、谋求经济发展。例如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就是在二战后大量军人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前提下进行的。而其更为关键性的问题在于,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启动,并未事先设定具体数量指标,并且大众化途径主要通过社区学院完成的。反观我国大众化的运作过程,虽然也是在反映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的,但存在过多的人为因素。其一,人为设定具体量化指标。1999年1月,国家提出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2001年又提出200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力争达到15%左右,甚至有人提出2003年实现大众化。在对自身承受能力和困难估计不足的情况下,将实现的日期从2010年提前到2005年,再到2003年,提出了有悖于实际承受能力的一系列跃进指标。其二,不分层次全面扩招。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众化大多是在社区学院和职业技术学校完成的,形成一个合理的金字塔状的高等教育结构。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则要依靠专科性大学、综合性大学甚至一些国内一流大学来完成,形成了一个倒金字塔。近几年,高等教育扩招后,中等技术教育反倒严重萎缩,在东北、西北等欠发达地区技校几近倒闭,即或一些发达省份也无法对此有丝毫的乐观。如果按着此种思路进行发展,其直接的后果是,高等教育的规模和数量是上去了,但质量却会迅速下滑,既滞缓了跻身于世界一流,又影响了大众化的进程。
拉动经济增长。也可以说是借助社会大众需求(上大学而非一般意义上的高等教育)通过共同承担风险,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90年代以来,鉴于中国经济出现暂时的滞缓,市场疲软,有人提出借助发展教育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众所周知,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来看,教育具有引导社会发展的功能,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可以超前、超常发展,但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国家能否支撑,即国家是否有经济实力;其二,个体可否支持,即个体是否存在用以求学的经济基础和求学需求。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发展,一方面国家急需各专业型的高层次建设人才,科教兴国;另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求学意识普遍增强,国民对接受高等教育需求的呼声越来越高,加之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在国内的大学无法满足其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要的条件下,一些先富起来的家长斥巨资将子女送往国外深造,导致资金外流。鉴于此,有人提出:应通过启动教育消费截留外流资金、拉动国内经济增长,他们乐观地判断:如果在校大学生翻一番,中国的市场就能够活起来。从心理的角度讲,人的需求存在两种状态:一为静态需求,一为动态需求,只有动态的需求才能转化为个体行动的动力。而动态需求的生成,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主体自身有需求,二是客观上存在满足需求的基本条件。目前,中国社会主体中的功利性、精英性教育需求与以专业技术教育为主的大众化现状相矛盾,很多家长及学生有强烈、急切的上大学需求,但满足需求的客观条件与主体需求还有一定距离。一部分人并不满足于上一般大学,尤其拒绝进入中等技术学校,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拒绝到较低次层的院校报到学习。因为在大部分家长看来,投入是为了产出,扩招后子女进入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学校,虽说投入不多,但产出较少,况且面子上也过不去。而出国留学,既动听又实在,投入多多,回报丰厚,所以扩招对这部分人来说难动其心,国家欲依此而回流资金亦难成其行。
重结果,轻过程。自1862年美国公布《莫里尔法案》至19世纪末,其仅有赠地学院69所,1890年毛入学率为3%,1930年为9.60%,1950年为14.3%。英国1938年为2%,1960年为8.4%,1970年为14.1%。德国1960年为7.0%,1970年为13.4%。[2]20世纪8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为1%,1990年超过2%,2000年达到8%,2001年达到11.4%,从2%到8%我国仅用10年,而西方则用20乃至30年时间。[3]我们的确曾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完了别人不曾走过的路程。但同时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我国的经济现状、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社会大众的需求类型与西方国家有显著不同,如果一味主观地追求高速发展,幻想一步达到预先设定的某种量化指标,可能适得其反。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何不以平常心在过程中获得另一种发展。
三、高等教育大众化:基础缺乏,动力不足
经济发展是大众化实现的基础,高等教育大众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大众化的经济基础主要由两方面决定,一是国家整体经济实力雄厚;二是国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个体经济较有保证,就是说百姓手中有钱。按照2000年国家在“十五”规划中提出2005年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战略目标,届时,毛入学率将达到1 600万,也就是说,从现在起,每年将扩招1百万学生,按每生培养费1.5万人民币计,国家每年将多投入150亿。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从1990年为3.04%下降到1999年的2.79%(见表1),这与《纲要》要求的4%有很大距离,与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5.1%的现有水平相差甚远,与世界总体水平的4.9%亦有相当的距离。
表1 1995-1999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GDP)
年份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比例
3.68
3.84
3.49
3.20
3.16
3.10
3.05
2.99
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比例
2.76
2.60
2.50
2.47
2.54
2.55
2.79
(资料来源:1999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从统计数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1986年起,政府对高校经费的支付已逐年减少,虽然自1997年略有回升,但相对高校的大规模扩招,学校经费仍然捉襟见肘,难以为继。继续扩招后,势必加大经费的供需矛盾,有专家预测:将有2/3的缺口。事实上,在高等教育史上,扩大招生规模而使学校经费拮据的情况并不少见。即或是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由于高等学校快速扩大招生规模,也曾使一些名牌大学陷入困境。2002年3月3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题为“牛津大学为何要乞求施舍”的报道:“去年,英国有57所高等教育机构(44%)出现了运作赤字。名牌大学也榜上有名。爱丁堡大学亏损了将近1100万英镑;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出现了500万英镑的赤字;甚至剑桥大学都亏损了980万英镑,剑桥大学预计今年将出现500万英镑的赤字。”英国的大学为何陷入这一窘境?据分析,政府削减拨款和学生人数的大幅度增加是其重要原因。从1976年到1989年,每名学生得到的拨款减少了38%。与此同时,由于政府让50%的中学生进入高等学府,所以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在1981年仅占2%,如今却猛增到44%。因此,即便是像英国经济发达国家也由于资金缺口过大,使得在大学授课和研究领域的良好声誉方面也面临着可能会受到损害的危险[4]。另外,黄志成先生在“拉丁美洲高等教育大众化探析”一文中关于拉丁美洲大众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发展高等教育的速度和投入的比重与发展基础教育不相匹配”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5]
由于资金短缺,有人提出走内涵与外延并举的大众化发展道路。从理论上看,这的确是大众化实现的有效途径。但走外延发展之路也并不乐观。其根本原因在于民办和私立高校尚未形成规模,亟待进一步完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清楚地意识到民办高校的致命弱点及与西方民办高教、私立大学的本质区别。西方许多一流私立大学,不以盈利为目的。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麻省理工等。2000年美国“卡内基分类博士/研究型大学名单”提供的151所研究大学中私立大学近百所,绝大多数为非赢利大学,只有三所为私立兼赢利。[6]另外其教育目的或以人为本,或以社会为本,总之,以发展人和发展社会互为因果,以发展人和社会为第一要旨。反观我国的民办高教和私立大学,究其动机,尚未走出以赢利为目的的发展时期。有的私立高校为扩大招生,竟把远离高考录取线者甚至初一和初二的学生录取上来,这种不规范的私立大学一方面影响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破坏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
再看走内涵发展之路,势必将筹措资金的任务落在学校和学生身上。这样当然可以缓解大众化对国家所造成的压力,但同时可能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让学校筹措经费,可能影响大学的固有特质。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大学是一批大师支撑的强势学科,以追求高深学术为其学术宗旨的学术研究之圣殿,以自由、自治、自律为其理想,以求真、觅善、寻美为其价值追求,培养有大学问人之处所。学校如果把注意力转移到筹集资金和所谓的创收上,势必影响其办学的主方向。学校最便捷、最有效的创收途径:一是直接盘剥学生,二是出卖文凭。目前,人们对社会上制假、售假、买假文凭者深恶痛绝,但对一些高校乱发文凭的作法却熟视无睹。长此以往,高等教育何来质量,大学何谈神圣。
此外,让个人承担大部分高等教育经费亦并非现实。暂且不谈中国有否中产阶级问题,仅就城市与农村的贫富差距就让人无法乐观,据2001年6月28日的《南方周末》报道,中国城乡的基尼系数1994年后已超过0.4这一警戒点,1998年达0.456,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农村居民和城市下岗职工无力承担数额庞大的教育经费。即便是在西方的发达国家,个人也只支付学费的一小部分。如英国仅收1/7左右。[4]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近几年城市下岗职工增加,城乡贫富距离拉大。目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下岗职工和农村子女的生源问题,京、沪等地的高中生入学率已达90%以上,而在农村,尤其是偏远山区,同龄人(非高中生)的入学率与其有天壤之别。据报道,在较为贫困的安徽省,对于偏远城镇和乡村的孩子们来说,上学是一种奢望。在鲍威的村里,读得起初中的孩子不到20%。由于经济因素决定了大众化教育的受教育权的归属,引发教育不公。教育公平是为了使每个人都能通过教育而获得发展,社会必须提供不会受家庭背景、社会经济地位等客观因素影响的相同的教育机会。1963年罗宾斯报告提出一个中心原理:应该使所有在能力和成绩方面有资格并愿意受高等教育的人能受到高等教育。但目前是由于高昂的教育收费,使扩招前原本可以进入大学的优秀青年被拒之门外,使看似平等的现象,带来的却是实际上的不平等。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所出现的教育不公和教育特权等问题应使我们引以为戒。
四、高等教育大众化: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的两难抉择
高等教育的发展依赖于两种需求:国家需求和个人需求。两种需求的满足互为条件,国家需求的满足依赖于个体需求的生成,个体需求的获得依赖于国家对个体需求的支持。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两种需求犹如电脑的不合理配置——不支持。其矛盾冲突的症结在于:个体需求直接指向了精英型教育,国家提供精英和大众两种类型,个体选其一,舍其二;国家需大众、精英两种类型,个体只对其一予以支持。两种需求面临两难的处境:满足精英型的大众化,影响精英的教育质量,提供两种类型,真正的大众化教育类型“后继乏人”。
教育的社会需求即社会对教育提出的要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家对精英和各种专门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社会成员对接受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社会需求是大众化发展的动力。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历史时期,科技兴国、科教兴国是历史赋予时代的重任,从科学技术、人文素养到操作管理,无一不需要高质量、高素质的人才。从世界角度看,社会个体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具有全球性,趋之若骛。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与教育结构、教育观念、社会个体需求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如何根据经济发展的可行性与需要确定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高等教育大众化,必然要求教育结构、办学层次的多样化。所谓教育结构即指办学的梯次,它包括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三个层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以本科教育为主,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状况,直到90年代,我们把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为“基”大于“身”的梯形结构,但专业技术教育发展困难,生源不足,有名无实,令人堪忧。“2001年武汉市38所技校中有10所关停并转,其他20几所也难以为继,处于半瘫痪状态;陕西省173所技校中几乎有一半学校只有勉强做到‘一校一班’,三分之一的技校被分流或停办。”“国家统计局上海市调查队对全市60家制造企业进行调查,目前上海的技术工人队伍中,22岁以下的仅占3%”,也难怪我国技术工人的年收入仅为7000至一万。[7]
中国自先秦就有功利性的教育传统,尤其是在科举制度下,士人普遍将读书与入仕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里,读书和接受教育成为士人跻身官场的敲门砖。北宋时胡瑗首倡“明体达用之学”,明清之际功利主义教育思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自西方步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伴随着科学革命和科技理性的高扬,功利性教育更加成为大学教育的主体。在我国现阶段,国人对教育价值的理解存在着相当大的偏颇,往往把宽泛的社会性教育功能、自我完善性和创新性的教育目的,理解为狭隘的惟独为我所用的功利性教育,上大学成为升迁、就业、赚钱的一种手段,把包括大学教育在内的教育完全理解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面对近年高校收费逐年增多,统招不统配的特点,很多人认为:花那么多钱读书,却换不来现成的工作,光赔不赚。同时在功利观的作用下,国人中还存在明显的精英教育观。在他们看来,只有上好大学,读名牌大学,才能在毕业后获得理想的工作,才能获得更多的钱。在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考生宁愿放弃补录的机会而选择复读的心理。考生对补录的热情并不高,许多考生宁愿放弃补录的机会而选择复读。以往高考招生时那种饥不择食的现象已不复存在,考生已不满足于上大学,而是上什么样的大学。[8]有的在校大学生提出退学申请,退学不是不再读书,而是来年再考,选择更好的更适合自己的大学[9]。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国人可能选择两种基本的行为方式:一,教育以外无路可走时,他会选择接受教育,且是精英式的大学教育;二,教育以外尚存其他捷径的话,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教育。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国家、个人双重功利标准以及日益繁重的双重经济负担影响下,尽管我国大众化的动机和出发点是好的,但无视自身现状和现有条件,将导致高等教育的走向出现“有需求,无动力”的被动局面,国家和社会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但个体行动迟缓。这不仅不利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导致教育不平等、商业炒作、助长教育功利性、教育质量下降等等。所以,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首先要界定清楚概念及其内涵与外延,高等教育大众化不是大学大众化。要利用“入世”的有利时机,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以培养大量的技术操作人员。其次,针对有需求无动力的现状,转变国民教育观念,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和教育发展观,教育(或学习)是过程、是目的,然后才是手段,过程和目的是第一位的,在过程中获得体验感悟人生,把培养人作为最终理想和最高境界,确立终生学习的教育目标,真正实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再次,规范民办高教。树立育人、服务、获利齐头并进,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杜绝欺诈及违规操作行为,保证高等教育、学校、学生的和谐发展,作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有力支撑。最后,树立科学的网络教育观念[10](P113-118),加强网络教育建设,减缓社会需求对大学造成的压力,缓解国家和个人经济上的负担,为国家、大学、个人松绑。网络教育虽然存在诸多不利“人”发展的因素,不利于培养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但在目前情况下,不失为大众化实现的有效途径和辅助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