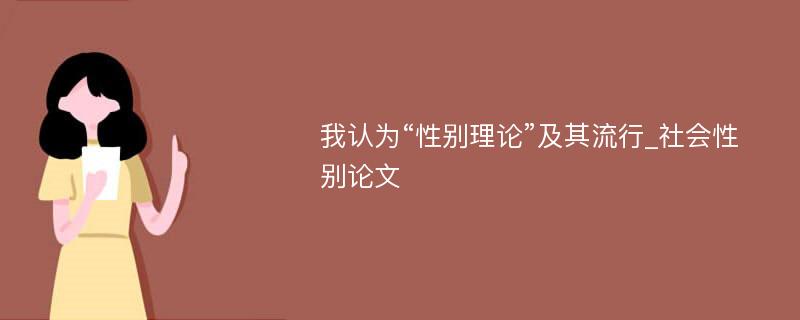
我看“社会性别理论”及其流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看论文,性别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流行是一件好事。好在什么地方,好在学术理论多元化,打破由某一种妇女理论垄断天下的局面;好在观察多视角,避免盲人摸象的片面性,因为再好的理论也有盲点。世上关于两性地位和性别公正的理论观点有千万种,社会性别理论只是其中之一。可以说,有一种哲学或“主义”就有一种关于两性地位和性别公正的理论,同时,对每一种哲学或主义的不同解读又可以派生出不同的关于两性地位和性别公正的观点。
在我国流行的“社会性别理论”有如下要点:男女社会地位是由男女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所决定的、社会性别或性别角色是文化塑造的、塑造社会性别的现行文化基本上是不合理的,因此女性(还有正义男性)要“提高觉悟”,增强性别意识,反其道而行之,赋权增权,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
社会性别理论其实不是新思想。自社会学有“社会化”的概念开始,社会文化塑造角色行为就已经成为常识,性别分层理论中的文化决定论思想,通过美国女性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和法国女性哲学家西蒙娜·波娃的著作在20世纪中期达到高潮。社会性别思想得到过学术界真正重视的是米德和波娃。米德认为:所谓的男子气和女人气是社会性的产物。波娃认为:女人不是生为女人而是成为女人的。终于,玛格丽特·米德的著作遭到了同行的严肃而致命地批评,她一系列著作的学术价值因此大打折扣。以后各类文化决定论的女性主义思潮除了深受女性主义社会运动人员喜欢以外,学术界则敬而远之。这并不是所谓由男性控制着话语权的学术界排斥“女权”观点,米德和波娃就受到过重视,20世纪末期,“用女人的眼睛看世界”这一建立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女性主义著名宣言也震动了学术界,使男人和女人都为之兴奋不已。
社会性别理论有它的价值也有它的局限。社会性别理论的积极意义在于提醒人们注意,当今世界把男人塑造成男人把女人塑造成女人的社会文化有许多不合理之处,并鼓励女性提高觉悟,自信自强,通过与滞后的文化抗争来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性别理论的弱点在于它轻视两性自然差异、否认男女自然差异在性别角色塑造中的重要性;在于它并没有告诉大家塑造社会性别的文化为什么如此塑造性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塑造得不合理、在多大程度上不合理。“用女人的眼睛看世界”与“社会性别理论”分属于不同的女性主义流派,却也同样有其长短,其长处是“用女人的眼睛”确实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新世界。其短处是不知道该由谁来代表女人。其实女人是千差万别的,有誓死不与男人沾边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也有死活要为丈夫殉葬的印度寡妇。往往有人摆出“唯我独女”的姿态自封为女性代言人,殊不知这恰恰违背了“用女人的眼睛看世界”的哲学精髓。
社会性别理论要合理运用。即使是一种好的理论学说也有一个在什么范围内使用和如何使用的问题。在适当的范围内就会得天独厚,使用得当就如入无人之境。反之则牛头不对马嘴。就像一把切菜刀,家家厨房都需要,可是切菜刀不能用来切割钢板,切菜刀也不能让小孩拿在手里,小孩手上的切菜刀不但不能发挥切菜的功能,还很可能伤着自己、伤着他人、伤着家具。运用社会性别理论也是如此。运用得好,比如:它能使人们了解到那种歧视遭受性侵害妇女的社会文化是残酷的男权文化;它能使人们了解到男女公共厕所设计者缺乏性别意识,其观念大大落后于社会发展。运用得不好,就会忽视社会文化的合理成分而夸大其不合理性,把百分之二十的不合理说成了百分之八十的不合理。比如:把市场经济说成是男权文化,把择优录用的性别正视说成是性别歧视,甚至用社会性别理论来分析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是,手持社会性别理论“切菜刀”的“愤女”们就在口诛笔伐间“滥杀无辜”。
社会性别理论的教育和培训正成为时尚,需要区分不同的教育和培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教师,其教育对象是普通学生,一类是“牧师”,其教育对象是女权运动积极分子或女权运动人员。教师传授包括社会性别理论在内的各种知识,并要求学生对任何一种理论学说都持一定的怀疑和批判态度;教师要求学生“理解”社会性别理论,学生是否“相信”这一理论并不重要;教师难免有个人偏好,但不强求学生有同样的偏好。就像介绍关于大蒜的知识,教师只是讲清大蒜在蔬菜族中的特点,并不一定要求学生喜欢吃大蒜。学生都乐意了解知识,一般不会产生所谓“阻抗”心理。“牧师”布“社会性别理论”之道,一般不深究学理,只要“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就可以设坛开讲,并要求女权运动人员全盘接受不能怀疑,“相信”是首要的,是否“理解”并不重要,反正你得把“社会性别理论”这颗大蒜吃下去,还要说好吃,如果你有“阻抗”说不好吃,那“牧师”只能与你说再见了。
需要说明,我不是一概否定“牧师”般地传授社会性别理论,同时认为,作为社会运动的女性主义完全应当存在,女性利益压力集团太少而不是太多。但我们有必要区分“社会性别”教师和“牧师”,以便让其各自遵守自己的职责,以便于学生识别而避免错选导师;我们也有必要区分作为学术理论的“社会性别”和作为社会运动的“社会性别”。对于前者,应当与之讨论个明白,因为这是格物致知,探求真理;对于后者,则大可以宽容。如果你愿意,可以加入其中摇旗呐喊;如果不愿意,可以远远走开,隔岸欣赏这道社会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