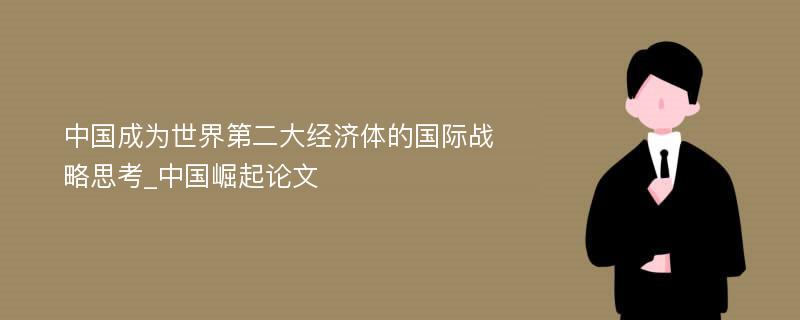
关于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的国际战略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二大论文,中国论文,经济体论文,战略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反霸和不称霸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长期坚持的主要国际战略原则和外交原则。1978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政府经贸代表团时提出:“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即使中国将来发展起来了,也“不能实行霸权主义”,并说“这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制订的对外政策,我们要用来教育子孙后代”。①以后,邓小平同志又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中国要坚持反霸和不称霸原则。如1990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就再次重申“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②。2007年10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明确宣布:“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③不过,对中国几代领导人有关中国坚持反霸和不称霸的反复宣示,国际社会一直将信将疑。
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一国战略能力的增长源于其财富和生产能力,当一国经济增长后,必然要向霸权国挑战。即是说,这种观点认为一个新的大国崛起必然要冲击现存国际秩序。④他们进而推断中国在此之前即使奉行过反霸和不称霸原则,也不是基于外交道德或价值理念,而是基于尚不具备称霸实力,中国一旦强大起来,也会像历史上所有的帝国或霸权国家一样,逃不脱谋霸的“魔咒”。⑤因此,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并攀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新高点,中国是否会继续沿着“和平崛起”路线发展?是否会继续坚持反霸和不称霸原则?一个强大起来的中国将在国际舞台上奉行何种范式的对外战略?会不会以武力颠覆现存国际秩序等问题便进一步浮上台面,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大国更加关切的问题。⑥这同时也是中国自身在继续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大战略问题。
一、中国经济总量即将跃居世界第二
20世纪70年代,当中国明确提出反霸和不称霸原则时,中国确实还处于“不发达”状态,就作为一国综合国力基础的GDP总量、主要工业品产量、人均GDP、人均工业品产量等指标而言,中国确实不具备可资称霸的实力。如,1979年,中国主要工业品产量中:发电量仅为2820亿度、钢产量仅为3448万吨、汽车产量仅为185700辆;工农业生产总值(当时大体等同国内生产总值)为6175亿人民币,约合2500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347元人民币,约合140美元;高等学校在校人数为102万人。⑦与美、苏(俄)、日、德(西德)等相比,中国发电量仅为美国的12.5%、苏联的22.8%、日本的48.5%、西德的75.5%;钢产量仅为美国的27,8%、苏联的23.1%、日本的30.8%、西德的75%;汽车产量仅为美国的1.7%、苏联的8.5%、日本的1.9%、西德的4.4%,以及仅为法国的4.4%、英国的12.6%、意大利的11.4%。⑧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与排名前七的美、苏(俄)、日、德(西德)、法、英、意等相比,大约分别为美国的10%、苏联的16%、日本的25%、西德的33%、法国的43%、英国的61%、意大利的77%。中国人均GDP则仅相当于各主要大国的几十分之一,人均主要工业品产量甚至更低。⑨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实力虽有较大增长,但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综合国力课题组研究,中国的综合国力仍排名世界第七,“综合国力值”仅相当于美国的18%、法国的34%、日本的35.7%、英国的39%、德国的40.6%,以及相当于俄罗斯的68.6%。⑩
因此,中国虽然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奉行反霸和不谋霸战略,但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依然认为中国奉行不谋霸战略不是基于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外交伦理和独特的价值观、利益观,而是基于中国的综合实力仍不足以谋霸、称霸。西方战略界不少人不但否认中国对外战略的和平性质,还不断描绘一个崛起的中国将如何谋求亚洲和世界霸权、进而引发大国冲突甚至战争的悲观前景,“中国威胁论”伴随中国的崛起进程水涨船高,甚而高潮迭起。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更是从进攻性现实主义立场出发,断言“当中国的权力增长后,美国与中国势必成为对手”(11)。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发展不断加快,综合国力进一步增长,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趋势及国际战略取向新的关注。2008年堪称是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撰文称该年是“中国年”。这不单指中国第一次承办奥运会,更是指中国经济实力出现了质的升跃。截至2007年,中国“初步核算”的GDP总量已达246619亿元人民币,(12)按年末人民币与美元7.3046:1的汇价计算,超过33000亿美元(13),较1979年增长近14倍,与居第三的德国不相上下;人均GDP约2500美元,较1979年增长近20倍;外贸总额达21738亿美元,居世界第三,较1979年增长大约100倍;外汇储备达15282亿美元,居世界第一;(14)主要工业品产量:煤产量达25.36亿吨、粗钢4.90亿吨、10种有色金属2351万吨、水泥13.54亿吨,皆较1979年大幅跃升。(15)不仅如此,中国越来越多的具有指标意义的产品总产跃居世界第一,如2007中国粮食总产超过5亿吨、规模以上港口吞吐量50多亿吨、固定电话3亿多户、移动电话5亿多户、高等学校在校学生达1885万人,皆居世界第一。(16)煤炭、钢铁等主要工业品产量也居世界第一。全球观察组织预测,2009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世界比重将增至17%,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17)这意味着中国将替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可被认为是中国实力全面增强的综合性标志。另一个有指标意义的数据是中国因特网上网人数已于2008年6月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18)当然,中国“神七”升空,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51枚金牌,金牌总数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也被认为是中国实力上升的重要标志。(19)总之,按西方的逻辑,中国已非昔日吴下阿蒙,已经具备了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所界定的“谋霸”实力。
2008年春,皮尤公司对全球24个国家的24717人进行抽样调查,受调查者中认为中国“已经”或“将要”替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法、德、澳、西、英、韩等国分别合占66%、61%、58%、57%、55%、51%。美国也有36%的受调查者认为中国“将要”或“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20)这一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世界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将在“某一时间点上”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和超级大国,进一步证明中国实力上升已成为国际共识。
北京奥运后,世界经济出现堪比“三十年代大危机”的“大萧条”迹象,并波及中国,(21)但中国经济仍将克服困难,保持较高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8年8月发表的最新报告虽然把2008年和2009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分别调低为4.1%和3.9%,但预测中国2008年和2009年将分别保持9.7%和9.8%的增长率,并预测日本2008年和2009年的增长率皆为1.5%、美国该两年增长率则分别为1.3%和0.8%(22)。如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为基本依据,即预测今后几年中国保持9.7%的年均增长率(低于过去10年中国的平均增长率)、日本保持1.5%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高于过去10年日本的平均增长率),则在3年后的2011年,按汇率计算的中国GDP总量将超过日本,中国因而将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届时中国按汇率计算的GDP总量将由2007年的33000亿美元增至大约48000亿美元,日本GDP总量则为47000亿美元左右。(23)
实际上,不论世界经济前景如何,只要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高于日本8个百分点左右,中国在三五年内不可免将替代日本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一替代势必引起国际政治结构的巨大变化,中国与亚洲及世界的关系也将发生巨大变化。
二、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烦恼”
在研究中国升格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所面临的“新烦恼”时,不能不考虑中国的特殊性,其中最大的特殊性是中国的崛起规模前所未有。历史上虽然有过几轮大国崛起浪潮,但那些崛起国家在规模上都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19世纪以前崛起的西、荷、法、英、德,其人口规模不过以百万千万计;20世纪崛起的美、苏、日,其人口规模也不过以亿计。中国崛起却是一个人口规模10亿级的大国崛起,这是前所未有的。此外,以往的大国崛起除日本外,地域上主要集中在大西洋沿岸,文化上主要是基督教国家轮换坐庄,种族上也是白种人国家竞相崛起。日本虽在地域、文化、种族上算得上例外,但其在政治文化上西靠,第一轮崛起时经济规模较小,第二轮崛起时政治实力弱,因而影响有限。中国的崛起不但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崛起,也是一个真正的非欧美国家、非基督教文明国家、非白种人国家的崛起。所有这些,也同样规定着中国崛起的特殊性及中国升格为世界二号经济大国所面临挑战的特殊性。
当中国升格为二号大国时,中国从一开始就要面临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引起的国际关系调整的挑战,其中的关键依然是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威胁论”。
早在20世纪90年代,当中国崛起初露端倪时,“中国崛起威胁论”就已抬头。当时不少西方经济机构开始按购买力平价评估中国经济实力,认为中国GDP总量已高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此后,高估中国实力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国际现象。2007年末,世界银行根据修正后的数据重新评估中国经济总量,虽然按购买力平价估算的2005年中国GDP总量由此前的约8.9万亿美元调低为5.3万亿美元,但仍高于日本而居世界第二。(24)最近,世界银行发表新数据,再次按购买力平价确认中国“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5)这种高估中国实力、提前确认中国第二经济大国地位的统计方法,一方面证实了中国实力确实大幅上升;另一方面也正是不论中国如何强调“和平发展”和不谋霸,但各类“中国威胁论”始终如影随形、愈演愈烈的重要背景和诱因;还是三五年后,当中国真正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将面临的主要战略难题的预演。
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战略界根据西方大国竞相崛起轮替的历史经验、辅之以基督教文化背景下培植起来的“生存竞争”思维,创造了一套西方特色的大国崛起与竞争理论,并以此解析中国崛起及崛起后中国的战略意图、指向、行为逻辑与战略影响。在那些继续信奉“权力政治”、“丛林法则”和“零和”游戏、尤其是信奉“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西方人士看来,中国崛起将引起国际地缘政治关系、国际经济秩序、资源能源、环境、发展模式、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巨大变局,与中国加速发展相关联的各类“中国威胁论”,如“地缘政治威胁论”、“经济威胁论”、“资源威胁论”、“环境威胁论”、“粮食威胁论”、“军事威胁论”、“发展模式威胁论”、“中国新民族主义威胁论”以及所谓中国“缺少民主自由”、“人权记录不好”等,应运而生,不一而足。(26)其中,“中国经济威胁论”尤其是当前“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议题。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和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全面概述了西方对所谓“中国经济威胁论”的忧虑,其中提到中国的高储蓄率、高速工业化以及对世界经济“全面开放”引起了四大后果,包括资源供应紧张、冲击全球“价格”机制、对世界贸易的“巨大影响”以及“巨大的资本输出方”等。文章特别提及中国2006年“消费了全世界32%的钢材、25%的铝、23%的铜、30%的锌和18%的镍”,中国将在2010年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将在2015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等。(27)
宣扬中国崛起威胁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尤其是威胁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制”是“中国威胁论”的另一个主要议题。伯格斯滕在《外交》杂志上撰文系统归纳了中国崛起如何威胁西方国际经济体制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国拒绝为多哈回合谈判“作出积极贡献”、企图组建“亚洲集团”、以“怀有政治动机”的区域双边或多边贸易协议抵制全球贸易制度、反对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在能源市场和外援问题上“自搞一套”、以“北京共识”抵制“华盛顿共识”,等等。总之,他认为中国在许多领域“正在推行与现行标准、规则和制度化协议相悖的战略”。(28)
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则是“中国威胁论”的第三个主要议题。《国际先驱论坛报》2008年初的一篇文章称中国“潜艇”数量如何增长快、技术水平如何提高,以及中国如何提高海洋控制力,威胁美国海军的行动自由。(29)《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则渲染中国“用导弹打卫星”、在“南中国海”炫耀武力、在台海部署“1300枚”导弹、阻止美舰“小鹰号”访问香港,等等,并得出结论:“从太空到南中国海,中国的战略野心就是要支配亚洲,崛起为全球超级大国”。(30)
在西方各类报刊漫画中,被刻意“恐怖化”的龙的形象成为一种“时髦”和特定的国际政治文化现象,是当前各类“中国崛起威胁论”的具体写照。如,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一篇谈“中国军事威胁论”文章的题图是一条全身长满“导弹刺”的巨龙用尾巴卷起了地球;(31)美国《外交》杂志2008年第一期第一页一篇谈中国崛起的文章的题图是一条摇头摆尾的巨龙正在张口吞噬地球;(32)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4月一篇谈世界金融危机的文章的题图则是一条巨龙从楼房背后直捣一家银行的营业大厅;(33)北京奥运后不久,《金融时报》一篇文章的题图则是一条中国龙从“鸟巢”飞升。(34)凡此种种,说明“中国威胁论”呈愈演愈烈之势,依然是中国崛起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主要挑战。
在战略层面和操作层面,作为即将崛起为二号经济大国的中国,必须应对的最直接挑战是如何解决好与世界“老大”(Mr.Big)、即与美国的关系。虽然有人预测中国或在2020年、2025年、2030年前后、最迟在2040年左右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35)但如何当世界“老大”是中国今后一代人思考的大战略问题。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战略预谋是如何当好世界“老二”,尤其是如何处理好与世界“老大”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与“老大”的关系,中国不但成不了未来世界“老大”,也难以平安地做世界“老二”。
美国及西方一些研究大国崛起的学者认为,历史上崛起大国挑战世界“老大”通常有两种“范式”:一种是以武力直接挑战握有国际主导权的“老大”,取而代之,使国际秩序作适应崛起国利益的调整。通观近代史上荷、法、英、德崛起历程,皆莫不如此,其中又以德国崛起及其战略选择最有典型性;另一种模式是以温和、渐进、非战争方式实现“权力转移”,这可以19世纪末以后美国崛起并“和平替代”英国的霸主地位为例。20世纪下半叶日本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继续接受美国“领导”、不直接挑战美国霸权,也被美国及西方战略界认为有一定的典型性。(36)
具体到中国崛起为世界“老二”后将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是如何处理与世界“老大”美国的关系,西方及美国战略界、学界有乐观与悲观两种对立的观点。
乐观者(即“接触派”)认为,中国快速发展对美国是一种“机遇”。经济上,中国加速发展可为美国提供巨大的商品市场以及源源不断的资本;(37)安全上,中国面对的不只是美国,而是美国与其西方盟友;中国面对的国际体系以西方为中心,“易于加入,不易推翻”,而“核革命”又使后起大国以战争方式摧毁衰落中的霸权国更加不可能。因此,崛起的中国与美国的冲突“并非不可避免”。(38)在其他方面,如管理和变革国际经济机制、促进繁荣,以及在解决能源资源、气候变化、全球“善治”和地区安全等问题上,中美也有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因此,他们主张美国与中国保持“接触”和合作。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称中国是美国的“利益攸关方”;财政部长保尔森宣称与中国“接触”是美国“通向成功的唯一路径”;(39)伯格斯滕甚至提出“G-2”概念,主张中美合作建立一个“两大国集团”,指导全球管理,应对各种“新老挑战”。他并提出在应对全球经济挑战问题上,美国尤其要把中国当作“主要伙伴,给予某种优先,使之在某种程度上替代欧洲”。(40)
悲观者(即“遏制派”)则把中国崛起类比为19世纪末德国的崛起,把今天的中美关系与19世纪末的英德关系类比。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新近在《外交》杂志撰文分析说,1870年英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对德国享有三比一的优势,但到了1903年,德国经济和军事实力超过了英国。新兴的德国因而不满足现状,要求按新的实力对比安排欧洲事务和国际秩序,挑起了大国“安全竞争”,迫使英国联合俄、法共同对抗新崛起的德国,最终导致了欧洲大战。许多“观察家”(伊肯伯里在文中举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据此分析中国崛起的影响,认为中国经济如“再快速增长数十年”,中国就将陷入与美国“极可能导向战争的激烈安全竞争”。(41)米尔斯海然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更是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大大放慢将对美国很有利”,他公开主张美国应“想办法延缓中国崛起”。(42)
综而观之,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似乎倾向于认为,中国在崛起为世界“老二”后,只能在“德国崛起范式”和“美国崛起范式”之间作“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
三、如何做世界“老二”?
在思考“中国如何做老二”的战略课题时,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范式”、亦即解决“中国崛起范式”问题。迄今美国及西方战略界提出的崛起大国与世界关系、尤其是与世界“老大”关系的两种范式有一定参考意义,但都不适合解析中国的崛起性质与进程。
西方提出的第一种大国崛起范式,即“德国崛起范式”显然不能用于解决“中国如何做老二”的难题,也不适于推测、解释中国的崛起及崛起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性质,这首先是由中国战略传统、战略文化与外交伦理的特殊性规定的。
19世纪的威廉德国和继后的希德勒德国在崛起过程中之所以选择以武力挑战国际秩序和英国的主导地位,以致挑起两次世界大战,从思想文化根源看,主要是普鲁士骑士团的好战传统和容克贵族的好战本质以及德国社会自上而下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普遍狂热崇拜使然。对此,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有非常精辟、深刻的剖析。他从研究希特勒的思想来源入手剖析说:在崛起的德国,“先是俾斯麦这个杰出人物,以后是德皇威廉二世,最后是希特勒,在军官阶层和许多古怪的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培养出了一种对权力和统治的野心,对横行无忌的军国主义的热情,对民主和个人自由的轻视,对权威和极权主义的欲望。在这种情绪的蛊惑之下,这个民族突然兴起,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然后又跌落下来,如此起起伏伏,几经盛衰,一直到1945年春季希特勒的覆亡”。(43)他进而分析说,希特勒的行为根源不但直接来源于威廉二世和俾斯麦等人,也直接承继于对德国历史、哲学、思想、文化影响深远的“费希特和黑格尔,后来是特莱希克、尼采、理查德·瓦格纳,以及一些较为次要的人物”。(44)正是这些“德国思想家各种各样不负责任和狂妄自大的思想”,包括黑格尔的“世界精神论”和战争观、尼采的“超人论”和“权力意志论”、戈平瑙的“雅利安人优越论”以及形形色色的侵略扩张思想,驱动着崛起的德国不惜发动战争,以武力挑战国际秩序,谋求世界霸权。(45)即是说,19世纪德国的崛起范式是“德国历史的延续”。(46)
然而,在中国,不存在德国这样的侵略历史、侵略思想、侵略性战争观以及“弱肉强食”的国际观,也不存在威廉·夏伊勒所称的曾存之于德国历史的那种“古怪的知识分子”和怀有“各种各样不负责任和狂妄自大思想”的思想家。中华民族自古就尊“王道”、反“霸道”、主张“非攻”、倡导“和为贵”与“中庸”以及“天人合一”、“仁者无敌”、“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政治观、战争观、天下观和自然观,这为中国对外战略提供了丰厚的“价值创新”源泉。(47)在国际事务中,古代中国重视国家间交往的“道德力量”而非“物质力量”、崇尚和平与“和合”、主张强国对弱国讲“仁慈”、尤其强调“以大事小须用仁”。这种外交伦理中“没有修昔底德笔下雅典人的那种‘强权即公理’逻辑”,(48)当然更与弥漫于19世纪德国、同时也弥漫于欧洲的侵略性世界观、国际观、战略观、战争观不同。
在实践中,古代中国也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和平主导型”大国。汉、唐、明、清(指清初)时期的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强国。1800年,中国制造业总值超过欧洲各国之和,占世界比重达33.3%;1830年,中国制造业总值仍与欧洲之和相近,占世界比重达29.8%。(49)但强大的中国并不推崇“霸道”、好战文化。在古代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封贡”体系中,中国“重视文治”,未因自身先进、强大而干涉四邻小国和落后国家的“内政”。中国对外用兵谨慎,并不恃强凌弱、恃强称霸。例如,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明皇祖训》中提及:“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他要求后世勿恃国富兵强而“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并开列15个“不征之国”名录,包括“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真腊、暹罗”等。(50)
古代中国以其强大时期的外交实践否定了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有关强大国家一定会称霸、谋霸的政治逻辑,说明西方的大国崛起理论不具有普遍性和普世性;也很能从历史文化根源解释为什么崛起的中国不会选择19世纪的“德国崛起范式”。
中国崛起不会、也不能选择“德国范式”的另一个原因是世界大趋势的新变化使然。这些大趋势概括地说,首推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及其质的升跃造成全球性相互依存。尤其是各种经济、安全问题的发展,如环保、资源能源紧张、传染性疾病流行、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要求世界各国通过国际合作加以解决。在这种大趋势下,非战、和平、合作、共赢等越来越成为国际潮流,好战思潮和传统安全竞争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增高了大国谋霸的门槛和成本,大国谋霸既难以成功,也永远得不偿失。而在19世纪末,战争狂热席卷欧陆,不但德国要以武力争夺“阳光下的地盘”,英、法、俄、奥、意以及土、保和一些巴尔干小国也充斥着军国主义、沙文主义狂热和战争喧嚣。(51)也正因为如此,在巴黎和会上,德国方面坚决拒绝由德国一国承担战争责任,认为“协约国所负的责任并不亚于”德国。(52)
第三个影响中国崛起“范式”选择的因素是非西方国家的复兴及其影响。冷战结束以来,非西方国家发展不断加快,形成群雄并起之势,扎卡里亚(Farred Zakaria)称之为“他者的崛起”和“后美国时代”来临。(53)这些“他者”的领军国家包括“金砖四国”、“钻石五国”、“新钻十一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其人口之和相当于西方国家人口总和的3倍以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占世界比重已达30%,并将在2013年增至35%。(54)而在全球范围,所有非西方国家的总人口约相当于西方国家人口总和的6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占全球比重已从2000年36%增至目前的41%。(55)从发展趋势看,全球力量对比将朝更加不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有人计算,到2050年,世界前七大经济体中,西方国家将从目前的6席降为2席;世界前10个人口大国中,西方国家将只保持1席。(56)这些变化将从根本上削弱西方霸权逻辑的物质基础,传统上由西方主导的主流国际观和霸权秩序观将发生变化。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如核武器对“暴力无限制使用”原则的制约作用等,也将影响21世纪国家崛起的“范式”选择。有人指出,目前种种国际新趋势表明21世纪将是一个“去霸权化”和“霸权终结”的世纪。21世纪既没有长盛不衰的美国和西方霸权,也不会出现新的霸权挑战、更替与转移。(57)在这种大趋势下,历来擅长于宏观思维的中国不会、也不可能逆潮流而动,选择屡屡失败、而且还将继续失败的“第一种范式”崛起,挑战世界秩序。
既然“第一种范式”不可取,那么,中国是否会选择“第二种范式”,即与霸权国合作的“美国崛起范式”以及二战后战败国日本和西德的崛起“范式”而实现崛起?
西方战略界有越来越多的人依据中国战略传统、战略观、利益观及政策实践,开始接受中国“和平崛起论”,开始相信崛起的中国不一定是“修正主义国家”,不一定以“暴烈方式”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58)相信中国有可能避开“第一种范式”而选择与霸权国合作的“第二种范式”崛起。他们并主张美国和西方创造条件,积极引导中国选择“第二种范式”,在崛起过程中及崛起后与美国和西方合作。(59)中国国内也有人主张或欣赏“第二种崛起范式”。然而,迄今为止的中国国际战略虽与西方提出的大国崛起“第二种范式”颇有相似之处,但又有严格区别。
在“第二种范式”中,经济实力在19世纪末与德国比肩超过英国的美国,并没有像德国那样以武力挑战国际秩序和英国的固有大国地位。相反,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与英国结盟,担当了“保卫英国”的角色。美国虽然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但随后搞了个《华盛顿条约》,以补充凡尔赛体系的不足、支撑英国主导的旧国际秩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还积极参与解决战债与赔款问题、裁军问题等,似乎继续认同、支持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崛起的中国面对美国及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国际体系,也采取了合作和积极“融入”战略。正是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中国积极参与了世界大多数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及其下属的大多数机构、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的维和部队人数最多;中国在反恐、反扩散等重大国际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包括主持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参与伊朗核问题和苏丹问题的解决进程、帮助稳定伊拉克和阿富汗局势等。中美还多次举行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最近中国又与美国合作,在应对美国次贷危机、世界经济衰退及能源困局等方面进行政策协调。所有这些,也正是美国及西方的对华“接触派”认为中国会依照“第二种范式”崛起的依据。
然而,中国崛起“范式”又与“第二种范式”、即“美国崛起范式”有本质区别。美国在崛起过程中,不论姿态多么温和,但其要取代英国担当世界“老大”并全面接管、改造、主导国际秩序却是非常明确的。为此,美国对英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支持常常使用双刃剑,既补台也拆台。威尔逊在出兵欧陆参加对德作战时发表了足以抽空英国霸主地位的“十四点”演说;(60)《华盛顿条约》拆散了英日同盟;“道威斯计划”和“扬格计划”明显有扶德抑英之意。二战时期,在英国面临生存危机之际,美国起草《大西洋宪章》有支持英国抗德的一面,更有侵蚀英国海外霸权的意图;罗斯福搞“租借法案”也不无搞垮大英帝国之深意。(61)美国力主创立联合国、创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一个重要目的也是要取代英国的国际经济、金融霸主地位,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成为世界“领头羊”。(62)总之,美国没有像德国那样直接以武力挑战英国的霸权是一系列历史偶然性使然,并非美国人天生就比德国人“温良恭俭让”。在替代英国霸主地位和称霸世界这一目标上,19世纪末同时崛起的美德两国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手段不同而已。
与美国不同,中国的历史经验、重道德不重物质利益的外交伦理、价值观和战略传统,使中国无意追求世界霸主地位。从中国的视角观察,世界“霸主”、即使如孔华润所称是世界“领头羊”,也不是个值得羡慕的角色。美国目前面临的困境无所不包,安全领域有反恐、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朝鲜核危机、伊朗核危机、南奥塞梯冲突、巴基斯坦、泰国等国的政局不稳、苏丹动荡等;经济领域有次贷危机、全球经济下滑、能源价格大起大落、洗钱、多哈回合停滞不前等;战略领域有俄罗斯反弹、新兴大国崛起、“无赖”国家挑战、反美主义高涨、大西洋关系调整等。中国对此看在眼里,思在心中。世界“老大”强大无比,却忙得要死。美国的困境真实展现了21世纪霸权国成本与收益的倒挂关系,也证实了中国不称霸战略的高明与超越。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提出“绞索论”、主张不称霸,邓小平提出“决不当头”,胡锦涛继续倡导不称霸原则,不仅是个外交伦理和战略传统问题,更是中国战略界对国家利益进行综合分析后得出的战略结论,因而有贯彻到底的深厚战略文化基础和现实国家利益基础。
在国际秩序问题上也是如此。中国从“融入”当前国际体系中受益良多,总体上比美国及西方更接受“现状”,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对当前国际秩序完全满意。比如,对于西方搞“价值观外交”和“人权外交”,向非西方国家输出“民主”、搞“颜色革命”、“政权改造”、按西方标准把非西方国家分成三六九等、动辄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甚至进行“先发制人”打击,中国就极不赞成。因此,中国在积极“融入”世界的同时,也主张逐步改革国际秩序的不合理方面。中国在总体上与美国及西方合作的同时,也拒绝盲目“追随”,并会以适当方式与霸权主义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简言之,中国崛起既不会选择“德国崛起范式”,也不会完全复制“美国崛起范式”。中国将选择“第三种范式”崛起,其内涵概而言之,一是在促进国际稳定中实现崛起,在“融入”世界的同时,要积极推进国际秩序循序渐进地合理改造;二是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实现崛起,在与主导国、即与作为世界“老大”的美国保持合作关系的同时,也会坚持与美国及西方的霸权政策进行合理斗争,制约其霸权;三是在坚持不称霸、不谋霸中实现崛起,但要坚持中国的道义原则,维护国际公平、公正,促进普遍繁荣、发展,并以之作为实现中国根本国家利益的根本途径。这些也正是中国倡导“和谐世界”理念的真谛所在。
注释:
①邓小平:“实现四化,永不称霸”,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2页。
②邓小平:“振兴中华民族”,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8页。
③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8页。
④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8,pp.26-27.
⑤[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54页。
⑥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8,p.23.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综合统计研究室编:《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2》,三联书店,1983年,第457-461页。
⑧根据《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2》所载数据计算而得。参见《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2》,第49-58页。
⑨根据《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2》所载数据计算而得。参见《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2》,第457-489页。
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综合国力课题组:《综合国力评估系统(第一期工程)研究报告》,第13-14页。
(11)[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页。
(12)稍后,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修正后的GDP统计,2007年中国GDP增长率由此前的11.4%增至11.9%。
(13)英国《金融时报》文章估算中国2007年GDP总量为32810亿美元。参见Peter March,"US unmoved by imminent loss of top industry slot",Financial Times,August 11,2008.
(1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引自《新华文摘》,2008年第9期,第51-53页;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July 7,2008.
(15)《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4月17日。
(16)《新华文摘》,2008年第9期,第53-55页。
(17)Peter Marsh,"China to overtake US as largest manufacturer",Financial Times,August 11,2008.
(18)"U.S.is losing dominance to new Intermet power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August 30-31,2008.
(19)Hannan Beech,"China Play",Time,September 8,2008,p.52; "Our revels now are ended",The Economist,August 30th,2008,p.27.
(20)Meg Bortin,"The World Watches China's Rise to Power",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June 13,2008.
(21)Alan Beattie,"IMF rules out return to Great Depression",Financial Times,October 9,2008.
(22)Peter S.Goodman,"As U.S.economy gose,so goes world'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August 25,2008.
(23)日本2007年GDP为43840亿美元。参见Emily Kaiser,"Encomic Outlook,Firm Dollar also brings new risk",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August 25,2008.
(24)The Economist,December 22,2007,p.46.
(25)Chris Bryant,"China in second place in purchasing power table",Financial Times,April 12/April 13,2008.
(26)Carla A.Hills and Dennis C.Blair,"Engaging the new China",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April 27,2007.
(27)Martin Wolf,"Asian giants are agents of change",Financial Times,February 5,2008.
(28)C.Fred Bergsten,"A Partner of Equals",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2008,pp.57-65.
(29)David Lague,"China,enhances fleet of modern submarine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February 8,2008.
(30)Victor Mallet,"Intransigent face of the Chinese superpower",Financial Times,January 24,2008.
(31)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December 21,2007.
(32)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8,p.1.
(33)Financial Times,April 16,2008.
(34)Financial Times,September 26,2008.
(35)关于中国GDP总量何时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的预测,经合组织经济情报局、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统括部研究员小峰隆夫分别预测为2020年;原北京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预测为2030年;高盛预测为2041年。资料来源参见: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8,p.36;[日]小峰隆夫:“世界经济长期预测”,载《越洋聚焦-日本论坛》,2007年11月号,第17期,第29页;林毅夫:“中国当前经济形势与未来发展展望”,载《外交评论》,2007年6月,第9页;高盛公司报告:“BRICs——通往2050年之路”。
(36)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8,pp.26-27.
(37)Robert Reich,"Why Economic Isn't A ZEOR-Sum Game",Newsweek,September 8,2008,p.47; Henry M.Paulson,Jr.,"A Stratagic Economic Engagement",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2008,p.59.
(38)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8,p.24.
(39)Henry M.Paulsen,Jr.,"A Strategic Economic Engagement",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2008,p.59.
(40)C.Fred Bergsten,"A Partner of Equals",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2008,pp.66-67.
(41)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8,p.27.
(42)[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44页。
(43)[美]威廉·夏伊勒著,董乐山等译:《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第137页。
(44)[美]威廉·夏伊勒著:《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册),第142页。
(45)[美]威廉·夏伊勒著:《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册),第141-148页。
(46)[美]威廉·夏伊勒著:《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册),第131页。
(47)石斌:“重建‘世界之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3页。
(48)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国际伦理观”,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49)[美]保罗·肯尼迪著,劳垅等译:《没有永久的霸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50)程亚文:“欧亚知识传统中‘中国文明复兴’的不同面相”,载《欧洲研究》,2006年第5期,第6-8页。
(51)[苏]N·N·罗斯图诺夫主编,钟石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77-85页。
(52)萨那、孙成木、余定辉等编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91页。
(53)Farred Zakaria,"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Foreign Affairs,May/June,2008,p.43.
(54)Analysis,"Time to pay the bill?" Financial Times,August 29,2008.
(55)Chris Bryant,"China in second place in purchasing power table",Financial Times,April 12/April 13,2008.
(56)"Births of a nation",Financial Times,March 1/March 2,2008.
(57)陈先奎、汤伟:“21世纪不会出现霸权国”,载《环球时报》,2008年9月5日。
(58)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8,pp.23,33; Carla A.Hills and Dennis C.Blair,"Engaging the new China",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April 27,2007.
(59)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8,pp.23-25.
(60)孔华润主编、张振江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册),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41页。
(61)Farred Zakaria,"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Foreign Affairs,May/June,2008,p.26.
(62)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册),第191-1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