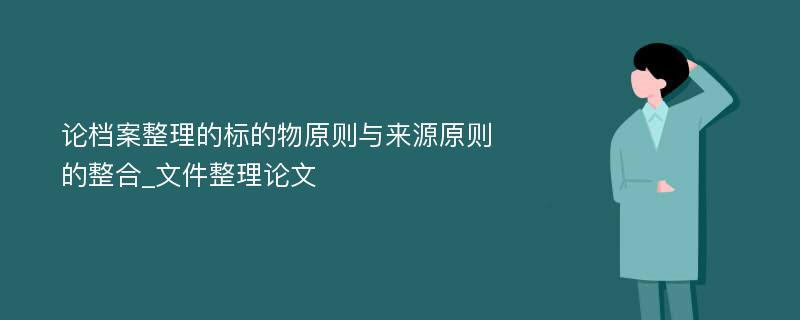
论档案整理的事由原则和来源原则的融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则论文,事由论文,来源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一档案形成主体都处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之中,为实现自己的职能必定同社会的其他部分发生着各种联系,而其实现其职能的整个过程也是按照其内部的各种联系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所积累的文件也必然是相互联系的。“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7页。)档案必须按照文件在机关实践活动中固有的联系进行整理,才能如实地反映历史过程中的人和事,体现出档案自身的价值,也便于后人的查阅利用。因为文件形成过程中联系的复杂性,从而形成了档案整理的不同原则。历史上档案的整理原则基本上有两大派别:事由原则和来源原则。事由原则就是按照事由整理档案的原则,按照该原则的要求,档案按照图书分类的模式,运用归纳与演绎的方法来整理和保管,而不论档案形成的机关。这一原则有很大的局限性,突出表现为混淆了档案的来龙去脉,混淆了形成档案的具体的历史背景,造成查找利用中档案的困难。来源原则就是基于克服事由原则的这一局限性而被提出的。
1841年,法国内政部在省档案馆基本条例中第一次阐述了全宗的概念和全宗不可分散的思想,其核心就是“来源原则”,目的是维护档案进入档案馆之前在机关形成时的本来面貌和有机联系。这一理论的提出在档案事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后又经过普鲁士的登记室原则、荷兰的来源原则的完善,逐渐形成了比较科学的整理档案的原则和方法。我国的档案工作者在整理档案的过程中也从不同方面提出了来源原则,认为“一批档案开始分类以前,必须先明了当时政府的组织、职官的配备、公文的程式,再进一步研究这个藏有档案的机关,在当时政治组织系统上的地位、职责与权利的限度、内部组织及其职掌。”(注:方甦生,《档案整理方法的初步研究》《故宫博物院年刊》创刊号(1936年))。而新中国更是重视全宗理论的研究和实践,规定档案必须按其形成机关为单位整理和保管。1955年国家档案局制定《原大一区级机关档案整理工作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档案材料必须严格地按全宗整理保管。一个全宗就是一个机关在工作活动中所形成的全部档案材料。”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传统理论中,所谓的来源原则的核心依据就是档案形成的主体机关,称为“立档单位”,又称“全宗构成者”。“一个机关就是一个立档单位,一个立档单位形成的全部档案,就构成一个全宗。”(注:陈兆祦,和宝荣主编,《档案管理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99页。)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受生产力及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当时的社会联系相对比较简单,档案工作的范围还比较狭窄,一般只局限于政府机关、团体、个人在政治活动中方面的档案。这些档案形成主体相对比较独立,档案来源联系主要是档案的同一形成主体在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进行活动时的内在联系。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但档案形成主体活动的范围和规模在不断的扩大,从而导致档案数量、门类的增多,档案类型也越来越多样化,而且各部门、机关的联系也日益密切,从而使档案文件之间的联系的表现形式也日益丰富,“比如有些档案不是以同一形成者为核心,而是以同一项工程、同一种产品、同一项科研课题为核心,即以同一活动内容或事由为核心而形成的,如果仍然千篇一律地以形成者为依据组织馆藏档案,在有些情况下就难以行得通。”(注:冯惠玲,何嘉荪,《全宗理论的实质》,《档案学通讯(北京)》,1988年第五期。)现实的发展使传统的来源原则理论受到了挑战,1953年德国档案学家布伦内克提出了“自由来源原则”,第一次从理论上把档案的来源共同性与事由共同性联系起来,认为来源原则应是二者的统一。他指出:“我们的来源思想不是只保持固定的来源,而是要把来源和事由配合成一种相当的比例关系,建立一种在两者之间的综合体。”把自由来源原则解释为“来源共同性基础上的事由共同性。”并且,在某种情况下,“当一个来源机关的变更对于业务继续进行中事由共同性的生长毫无影响时,档案体就完全从原来机关脱离出来作为独立的有机体,虽然在业务机关多次的变换中仍然以旧日的精神继续生长。”
我国的档案学学者敏锐的察觉到了这一实践及理论的变迁,并给出了自己的阐释,如冯惠玲、何嘉荪两位教授在其《全宗理论的实质——全宗理论新探之二》一文中,通过对来源联系和事由联系的崭新解释,认为“档案学理论中曾经以对立面目出现的事由原则和来源原则在新的全宗理论中又合流了,一个半世纪前开始被淘汰的事由原则似乎又回到了我们身边。”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错觉”。两位教授认为:对来源联系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指来源于同形成者档案之间的联系,只是我们传统的理解,是一种比较狭义的理解。另一种是指来源于同一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档案之间的联系。这是对来源联系的比较广义的理解,它把前者包含于其中,而又比前者所指范围更为宽展。对事由联系也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指同一事情、同一个具体活动过程中形成档案所具有的联系,这是有比较严格的限制条件的比较狭义的理解。另一种是指反映同一类事物的档案之间所具有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含义比较广,没有客观的界限,是根据人们的认识加以类聚的,严格地说,这种广义的事由联系只不过是一种事由类同性而已。来源联系(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以及狭义的事由联系都是档案形成过程中所赋予的“天然”联系,因而是内在的本质有机联系,而广义的事由联系则是在档案管理过程中才胜场的联系,因而是外在的非本质的联系,因此,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事由联系不是回到原来的事由原则上,而是对事由联系的含义有了更为确切的认识。档案工作者早就认识到了全宗的实质是同一活动过程,也就是说本来就承认来源联系与狭义的事由联系是统一的,只不过是由于长期以来,同一活动过程采取了同一机关的形式,反而使我们渐渐地淡漠了它的实质。只要把视点从表象移到事物的本质,把同一活动过程所具有的联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档案之间的有机联系作为对来源原则的全面认识和全理论的立足点,就会使全宗理论获得更广泛的,甚至说是对各种门类档案普遍适用的新天地。(注:参阅冯惠玲,何嘉荪,《全宗理论的实质》,《档案学通讯(北京)》,1988年第五期。)
应该说两位教授对于事由联系和来源联系的理解是比较到位的,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把握和认识这一理论变迁的实质。但是,我们认为档案学理论中曾经以对立面目出现的事由原则和来源原则在新的全宗理论中的“合流”不是一种“错觉”,而是客观的事实,把事由原则和来源原则对立起来才是一种错觉。首先,事由原则和来源原则是对于不同的客观对象而言的,事由原则基于档案形成主体的现实实践活动本身,而来源原则则是基于从事特定实践活动的不同主体,对于同一活动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会得出不同的认识,二者并不矛盾。其次,事由原则和来源原则的分和都是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特定主体的实践活动而言的,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以一定的相对独立的主体为单位进行的,这些主体各自体现着相对独立的社会职能和任务,在这些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档案文件自然围绕着产生它们的主体,形成一个内部联系密切、对外相对独立的档案单位。当历史上社会联系比较简单,档案形成主体独立性比较强的时候,整理档案的原则就应以来源原则为主,并且来源的依据主要是一个个职能界限清晰、活动相对独立的立档单位。当社会联系日益复杂丰富的时候,为了完成同一实践活动,就需要不同的主体单位的分工合作,在这些活动中所形成的档案也必然的反映着这些社会联系,假如仍然依照档案形成主体为依据整理档案,就势必要割裂这些内在的联系,影响档案价值的实现。再次,事由原则和来源原则统一的基础是社会实践。任何理论都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只有正确反映客观现实的理论才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同样,要发挥档案的价值,就必须正确反映形成档案的历史活动的内在联系,也就是按照事由原则整理档案,以同一种活动为中心形成档案全宗。而不是脱离形成档案文件的实践活动的人为的理论归类,甚至我们可以对来源原则予以新的解释,即它主要依据不是形成档案文件的活动主体,而是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最后,事由原则和来源原则的结合应以事由原则为基础。任何活动都是主体的活动,活动的内容和目的决定着主体的结构和职能,反过来,主体的结构和职能也影响着活动的特点和要求。为实现一定目的的活动而形成的活动主体随着社会的发展,既存在分工也存在协作,当围绕主体进行的活动过程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连续性,从而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时,在这些过程中产生的档案文件也表现出与档案主体的密切对应关系,这使得档案整理原则既可以是事由原则,也可以是来源原则。当某一活动的完成需要多个或者不定的社会主体共同或者分别完成时,所形成的档案文件的内在联系只体现在活动本身,而与事由背后的机关人格的联系相对松散,这时,如果仍以档案形成主体为依据整理档案,不仅会割裂档案文件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且会造成档案管理和利用的困难。
总之,当我们接受实践的挑战,审视从事由原则到来源原则,再发展到事由原则和来源原则的融合的发展脉络,我们会发现档案整理的事由原则和来源原则在客观上并不存在绝然的对立,二者都统一于档案整理必须反映客观活动内在的联系这一基本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