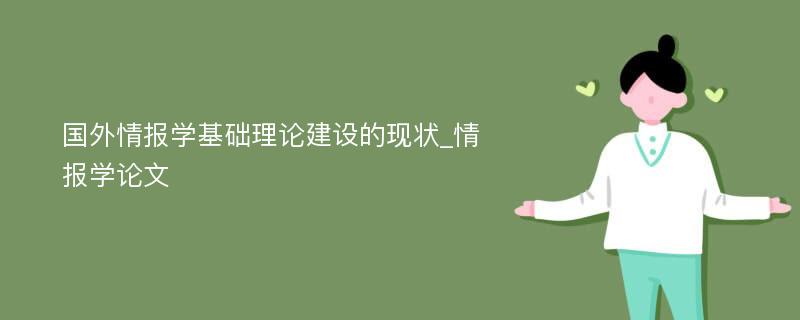
国外情报学(资讯学)学科基础理论建设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基础理论论文,学科论文,现状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外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LIS),在中国台湾被称作图书资讯学,而在中国内地则通常被称作图书情报学,有时也被称作图书信息学,其中图书馆背景下的Information Science通常被图书馆学界称作情报学或资讯学。本文采用这一通行做法,但要特别指出的是,此处的情报学/资讯学与国内基于专业情报机构的情报实践之上的强调以intelligence为中心的本土化意义上的中国情报学是不一样的,尽管两者关系密切。
国际情报学/资讯学界一直比较注重学科基础理论建设,作为本领域最为重要的TOP类学术期刊之一的《美国情报学会会刊(JASIS)》还专门在1997年第4期和第9期以“文献和情报学的历史”、在1999年第11和12期以“JASIS的50周年:杂志、学会和未来的出版;情报学的范式、模型和方法”、在2001年第1期以“还是有待开发的边缘领域:处在千年之交的情报学”为专题来集中探讨学科基础理论问题。此外《图书馆趋势(Library Trends)》在2002年第3期也专门围绕“LIS的当前理论”主题组织刊发了13篇专题论文,其中涉及理论构建的跨学科框架、信息遗传学理论等学科基础理论建设问题。本文主要从认识方法论/哲学基础和学科理论体系建设思路角度对国外现状进行评述。
1 学科元理论建设现状:认识方法论与哲学基础
元理论是关于理论的理论,是指一个学科或实践领域的前提假设,包括学科研究中的一般共识、方法论意义上的原则等。这些前提假设被科学研究者所默认,并以此引发出共同一致的概念,进而产生一些能够为实践所证明的基本原理。因此元理论研究是有着明显的哲学特征的。
情报学的元理论作为情报学学科基础理论的基础,其研究离不开情报研究中的前提假设。情报研究的前提假设通常是隐含的,它主要源于共识或相对缺乏理论性的直觉,在情报学中很少以“假定、假设”或“未加证明而假定某事成立或为公认的事物”(Postulates)的形式表现出来。[1]换句话说,情报学的元理论就是贯穿于其学科理论建设整个过程之中的认识方法论与哲学思想,它与情报学的认识论基础/哲学基础息息相关。推进情报学的元理论研究也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将哲学讨论和LIS的实践这两者结合起来”。[2]
国外LIS界开始直接提出元理论概念并积极从事这方面研究的里程碑式的标志事件,是1997年《元理论与情报学》[1]一文的公开发表,此后对元理论的研究日益关注,直接注明元理论并对此予以探讨的论文日益增多。例如,1998年发表了论文《情报学的理论与元理论》,[3]2001年发表了论文《Dretske的语义信息理论与LIS的元理论》。[2]除了直接围绕metatheory概念来从事元理论研究之外,国外LIS界更多的是围绕philo-sophical、epistemological及其名词以及其他有关的哲学术语的概念来进行元理论研究。例如探讨LIS的哲学基础[4][5]或认识论基础;[6][7]又如将LIS中的科学哲学理论与元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同时进行探索,[8]而从事元理论研究所涉及的具体西方哲学理论或思想有后现代主义、[9]现象论、[10]诠释学、[11]实用主义和新实用主义、[12]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13]扎根理论、[14]构成派,集体主义和构成主义、[15]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16]现实主义[17][18]等;《文献杂志》还专门刊登了一组论文[10-17]来推动元理论研究。
国内情报学界对国外的元理论研究也给予了关注。文献[19]专门阐述了情报学研究中若干哲学理论的引入,指出在研究情报学的认识论基础时,人们比较熟悉的哲学理论包括库恩、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理论,此外,实证主义认识论也被认为“仍然在控制着大多数严肃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者的思维方式与工作的哲学认识论”,实证主义的几个流派,如简约主义和马赫的现象主义等,在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中都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国外还不断尝试运用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或诠释学、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等西方哲学理论来进行LIS研究。文献[20]则沿着国内上述思路,在现有成果基础上对西方LIS中的作为元理论基础的现代哲学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动态分析,主要对西方情报学中的实证主义、认知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语言游戏论、现代诠释学这几种重要的元理论进行了详细评述,探讨了上述五类现代哲学思想对于情报学理论构建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同时也简约地提到近年来兴起的信息哲学与包括后现代哲学思想在内的当代哲学理论也都可以视作是情报学的元理论。
针对文献[20]并没有详细评述信息哲学这一情况,本文将专门谈谈国外利用信息哲学作为本学科认识方法论与学科哲学基础的最新探索。国外LIS学界一直在寻找自身的哲学基础,如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布鲁克斯首次将其引入LIS研究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激烈论争,但时至今日,可以说这一理论并没有能完全解决LIS研究领域的哲学基础问题,也没能很好地推动LIS的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正式地提出应当用信息哲学来作为LIS的哲学基础。
信息哲学是一门正式问世于西方哲学界的以信息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学科。当代信息哲学的创始人、牛津大学哲学家弗洛里迪于2002年在西方哲学界权威性期刊《元哲学》上正式提出什么是信息哲学这一里程碑意义的命题,详细论述了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何以成为可能,指出信息哲学是第一哲学、信息哲学领域涉及信息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包括其动力学、利用和科学的批判性研究,以及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21]他还在其他论文中阐述到信息哲学是研究信息的历史和逻辑动力学问题以及信息的概念性分析,是试图回答什么是信息的一门哲学;并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开放性的,就像路标一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22]还提出了信息哲学的18个基本问题,并将之分别归纳在信息概念分析、语义学、智能研究、信息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价值研究五个方面,如信息本质问题、信息动力学问题、统一信息理论问题、数据基础问题、脑一信息一身问题,等。[23]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其研究纲领首先强调的是信息转向(information turn),即强调信息的基础性地位。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哲学家将其注意力从可知客体的本质转移到客体与认知主体之间的知识关系,因此从形而上学转向认识论。那么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信息圈(infosphere)的出现,已经使信息上升为一个基本概念,与诸如存在、知识、意义等基本概念同等重要。当前理论界将信息哲学的理论旨趣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24](1)核心:寻求统一信息理论;(2)创新:以核心为基础,其主要目的是为各种新老哲学问题提供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3)体系:属于原信息哲学(以创新为基础,为创新目标的各个分支提炼理论分析框架);(4)方法论:以创新为基础,对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及其相关学科中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为其提供元理论分析框架。
信息哲学的提出为完全解决LIS领域的认识方法论与哲学基础问题又指明了一条新的研究方向。也是在2002年,弗洛里迪还在其发表的《论将LIS定义为应用信息哲学》中分析了信息哲学、LIS、社会认识论之间的关系,指出在信息哲学和LIS之间存在一种天生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社会认识论所不能为LIS提供的。LIS研究领域的发展不能依靠某些以前借来的理论。作为一门应用信息哲学,LIS能够在随着信息哲学自身理论研究的发展取得更大的成就同时建立自己的理论基石。[25]可见,弗洛里迪认为LIS可以被看做是应用信息哲学,而信息哲学也就可以成为LIS的哲学基础。而在LIS领域之内,信息哲学也同样引起了瞩目。美国LIS界的Herold在《图书馆人的职位与信息哲学》中指出:[26]“图书馆学是一门应用哲学,它试图发现传统图书馆工作的信息动态阶段性的根源,以设计和实施有效的信息服务为目标”,“图书馆学并不一定要选择一个与信息有关的特别的哲学位置。我们必须认识到信息给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经验共享带来新思路的时代即将到来。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信息哲学的讨论中去”。该文还从图书馆工作的实际经验、权威著作、分类、认识论、逻辑学、存在论、智力等方面分析了LIS与信息哲学的关系。不仅如此,国外LIS学界出于对信息哲学的重视,在《图书馆趋势》的有关LIS中的哲学问题的专刊中还专门发表了弗洛里迪的《作为应用信息哲学的LIS:一个重新评价》一文[22]来推动对于以信息哲学作为LIS领域的认识方法论与哲学基础这一问题的研究。该文指出LIS的理论和实践涉及三个层面:处理图书馆及其内容和服务;LIS的研究层面;第三个层面是基础性的,对LIS而言就是信息哲学,这与其他所有学科的层次是一致的,即应用实践、基础理论、哲学基础。
总之,信息哲学的兴起给LIS领域带来了一个建立自身理论基础的机遇,LIS可以把握好这个机遇,来建立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以有力推动本学科元理论研究实现重大突破,从而有效支撑起整个科学理论建设实现跨越发展。
2 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现状:两种不同的探寻思路
国外LIS界对于情报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探讨由来已久,总的来说,进行探寻时所采用的方法分为两大类,分别是遵循自上而下(Up-Bottom)和遵循自下而上(Bottom-Up)研究思路的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研究。例如,Hawkins就分别运用上述两类方法来进行过探寻。他在2001年利用通过追踪所收录的文献就能识别其所覆盖的学科领域的变化的《情报学文摘(ISA)》,对于什么是情报学这一问题进行了历史考察,并对已有的众多情报学定义予以分析之后,自上而下地在宏观层面上构建了一个情报学地图,通过绘制出学科体系图谱,以此来指导微观层面研究。[27]2003年他又以《ISA》中的数千篇文摘为样本数据,依据2001年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两次确认实验,经过数据分析和对原有学科分类体系的修订,最终基于微观层面上的实际工作记录而自下而上地生成了宏观层面上的一个新的情报学分类体系。[28]现将两种探寻思路的具体应用情况进一步归纳如下。
2.1 遵循自上而下思路的学科理论体系建设
遵循该思路的学科建设研究是指主要依托质的方法,通过思辨以理论演绎的方式在宏观层面上进行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在此基础上为微观研究指明方向和规定范围。国外LIS界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主要有:
英格沃森提出情报学的核心领域由信息计量学、信息查寻、信息检索、信息管理和信息检索系统设计这5个部分所组成。[29]
萨瑞塞维奇指出情报学是一个关于专业实践和科学探索的领域,它提出了知识记录即文献的有效交流问题,以满足社会、组织和个人对信息的需求和利用。在该领域中文献计量与信息检索两个子领域发展不平衡,当这两大部分有机结合时,情报学就会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30]
萨默把情报学理论体系划分为三大部分:[31]情报学核心领域,即信息的生产、采集、评价、组织、存储、传输、检索和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信息管理,即各种组织的信息资源管理;信息技术,即可用于情报学与信息管理的各种技术。
贝茨指出情报学理论研究具有三大问题:[32]物理问题,什么是记录信息世界的特征和规律(法则);社会问题,人与信息如何发生联系、如何搜寻和利用信息;设计问题,如何能最快和最有效地获取信息。
卡洛琳等将LIS理论研究框架在宏观层面上划分为“LIS的四个关键维度”:[33]资源、技术、组织、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来指导微观研究,即如果把每个维度的研究内容用一个圆圈来图示的话,那么代表上述四个关键维度的四个圆圈的集合图便代表了LIS中的关键维度的概念图解(A Conceptual Schema of Key Dimensions in LIS),而上述四个关键维度中不同要素的不同组合也就形成了情报学的各种各样的研究领域。
鲁宾阐述了LIS中十个方面的基础性问题,它们大致构建起了LIS的学科理论体系框架,[34]即信息基础设施;有关情形下的图书馆、情报学;服务的视角、重新定义图书馆、信息政策;利益攸关者与议程、信息政策:智力自由、信息组织;问题与技术、从过去到现在:图书馆的任务及其价值、伦理和标准;LIS领域里的职业实践、作为制度的图书馆;组织机构的观点、图书馆职员的任职资格;一个正在演变发展中的专业领域。
储荷婷在属于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丛书的《图书馆信息学》中所搭建的学科理论体系框架如下:[35]各种形式的信息、变化中的图书馆、信息表述、信息检索、用户服务、信息系统、用户研究、信息伦理和信息政策、图书馆信息学的研究方法、信息技术、信息计量学与网络计量学。
辛斯在澄清数据、信息和知识的含义的基础上,依据《情报学文摘》(2002年)和《情报学和图书馆职业领域辞典》(1998年)中所分别提供的情报学学科理论体系分析框架,对情报学的本质进行了哲学思考,指出情报学关注客观知识的元知识方面或基础问题,尤其是中介的和技术的方面,提出要将情报学的名称由information science重新定义为knowledge science;[36]还对57位国际情报学界的顶级学者进行数轮问卷调查,在汇总这些专家在宏观层面上对情报学的个人评判结论或质的研究情况的基础上,依据大部分专家的意见,认为文化模式代表了当代情报学的主流发展方向,即情报学聚焦于人类社会中的数据、信息、知识和讯息之间的中介转换问题(the mediating aspects of D-I-K-M),[37]并进一步绘制出了情报学的知识地图、[38]提出了情报学的分类方案,[39]这些宏观研究无疑为微观研究提供了有效指导。
2.2 遵循自下而上思路的学科理论体系建设
遵循该思路的学科建设研究是指从对微观的具体数据进行计量和统计来了解并掌握整体意义上的学科结构和所形成的研究范式、学科发展走势以及同相关学科之间的内在关系等,从而把握住情报学的宏观全貌。在该思路中学科建设所用的方法统称为共现分析(Co-Occurrence Analysis),即将各种信息载体中的共现信息定量化的分析方法,以揭示信息的内容关联和特征项所隐含的寓意,它又具体分为共引分析(Co-Citaion Analysis)、共词分析(CO-Word Analysis)、共链分析(Co-link Analysis)。
在整个共现分析方法中,比较而言,ACA方法(作者同被引或作者共引分析)在学科建设中用得较多,所取得的成果较突出,影响也较大。ACA方法被开发的初衷可以说就是用来描述学科结构的,即“通向学科知识结构的金光大道、(ACA Is to Intellectual Structure)”,[40]其原理在于假定两个作者的作品同时被后继作品引用则表明这两个作者之间有联系,共同被引用的次数越多,两者间关系就越紧密;而对一组相关作者的共引频次模式分析能揭示出作者间突出的链接,并能揭示彼此各自或共同代表的主题领域。可见ACA方法就是从特定学科或领域的核心著者的同被引入手,通过对有关数据的统计分析,以此来探讨科学和学术内部的专业知识结构,探讨学科范式和流派等。
ACA方法在我国LIS界运用得比国外少很多,在仅有的少量有限使用中,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是2006年马费成教授用此方法揭示我国情报学学科结构和研究状况,[41]而它在国外运用却较多,最为典型的使用是White H在1981年和1998年所作的两次分析。正因为其代表性,以至于国内甚至还有人专门通过对这两次分析的比较研究来审视近20年间国际情报学发展的新情况。[42]
1981年White选取39位核心著者,以1972-1979年间的SSCI为数据来源,运用ACA方法分析得出了国际情报学的5大分支:科学交流、文献计量、一般理论、情报检索、由齐夫和申农组成的先驱者集团。在所绘制的二维体系图中,文献计量位于中心位置,科学交流和情报检索分别位于其两侧,一般理论处于文献计量与情报检索之间,而体系图下方是先驱者集团。[43]
1998年White选取了1972至1995年间发文被引率最高的前120位作者为样本再次进行ACA分析,发现情报学已有了两个相对集中的领域并又可分为12个专业:信息检索实验研究、引文分析、信息检索应用、文献计量学、图书馆系统分析、科技传播、用户研究及理论、OPAC系统、从其他学科引进的思想、索引理论、引证理论、传播理论。White将分析结论进行了可视化,即对统计分析进行了聚类,并将像一个椭圆的聚类结果形象地说成是“情报学就像一幅澳大利亚地图,它的沿岸在发展,而固定的内陆则人烟稀少”。[44]萨瑞塞维奇则对这一聚类分析结果作出了进一步解释:[30]在海岸的一边包括了这样一些作者,他们研究的问题是文献的分析研究、文献的结构、作为载信体(Contentbearing object)的文本研究、不同人群的交流,特别是科学交流、信息的社会方面、信息利用、信息搜寻行为、各种信息理论及相关论题,这个类被称之为“信息分析”,我们则暂且将其称为“领域类(domain cluster)”,或像White那样称作“基础(basic)”。在海岸的另一边则散布着这样一批作者,他们的研究集中在信息检索理论和算法、实用的情报检索方法和系统、人机交互、用户研究、图书馆系统、OPAC以及相关的论题,这一类我们暂且称之为“检索类(retrieval cluster)”,或用“应用(applied)”来称呼。领域类集中在信息的现象及其在文献中的表现形式;而检索类则集中在理论与实践层次上的各种应用,包括人机界面以及信息检索各个方面的实施、行为与效果。
White所作的上述两次分析属于传统的ACA分析,大量的计算与绘图操作、工作流程中烦琐的数据搜集、计算中存在的复杂问题都增加了它的复杂性,严重阻碍了它的广泛应用。[45]网络寻址定位就是人们寻找新的技术方法来改进传统ACA分析所作出的尝试之一。比起传统ACA方法,该技术方法可直接产生于原始数据矩阵,而不需要再将原始矩阵进行转化,极大地减少了ACA的计算强度,结果更为可信。White于2003年采用该方法对他在1998年所做的那次ACA分析中所使用的同一数据进行了第二次分析,得到了更为清晰的学科结构和研究范式,其分析结果反映了多个学术集团并存的格局,突出了以Lancaster、Carfield等著名情报学家为代表的核心人物,要比以往分析显得更为准确可靠。[46]除了将传统ACA方法发展为网络寻址定位方法之外,国外情报学界所做的另一项对传统ACA分析的改进探寻就是将以ACA为代表的共现矩阵(包括共引、共词、共链矩阵)的应用拓展延伸到网络环境之中。[47]
收稿日期:2008-0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