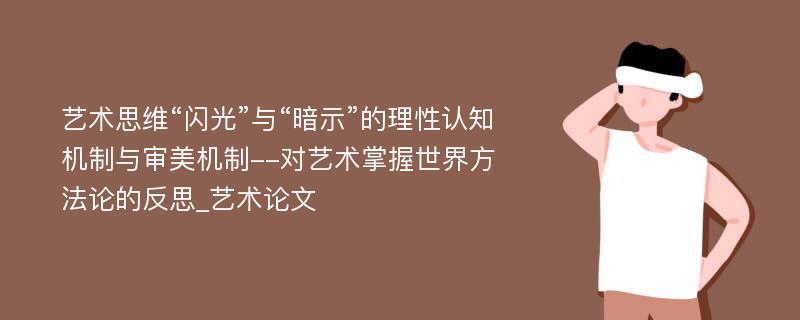
艺术思维“闪现”和“暗示”的理性认识机制及其审美机制——关于艺术掌握世界的方法论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机制论文,理性认识论文,艺术论文,暗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关于对世界艺术掌握或曰艺术掌握世界的本质内涵,我们认为就是艺术地感受、认识、理解并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方式。它是以艺术思维(主要通过想象和幻想)为本质特征的,以能动的文艺反映论为掌握方式的,以“按照美的规律造型”的艺术创造活动为中心的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全部内容的总和。那么,作为对于宏观物质世界的本质特征进行艺术掌握的,艺术思维的微观精神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呢?其间存在着怎样的现象特征呢?艺术思维或曰形象思维能否达到和怎样达到理性认识?它的存在形态和审美形态或者说它的心理形式,与灵感、联觉、错觉和幻觉等心理现象的内在联系及其审美机制如何等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无疑对美学理论和艺术实践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一、艺术思维“闪现”和“暗示”的理性认识机制
艺术思维或曰形象思维能否达到和怎样达到理性认识,或曰其对于事物内在联系及其规律的本质属性的认识何以成为可能,呈现出怎样的心理形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里,我们根据当今思维科学的积极成果,结合审美和艺术实践,来谈一点探索性的意见。
《列子·说符》中记载了一个深启肯綮、发人省悟的故事:伯乐(善相马者)推荐九方皋给秦穆公去寻良骥。三月归来,称说是寻着了。秦穆公问是匹什么样的马,九方皋答道:“牝而黄”。差人牵来一看,竟是“牡而骊”。马的“牝牡(雌雄)”和毛色的“骊黄(黑黄)”都未能分辨,何谈相得良马?!然而,事实证明,九方皋所相得的,确是一匹千里神骏。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咄咄怪事呢?伯乐受到秦穆公责怪后的喟然长叹的一番话,给了我们一种探赜索隐的启迪:“若皋之所现,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者,乃有贵乎马者也。”这便是常用以说明认识事物要摒弃表现现象,抓住内在本质的“牝牡骊黄”的典故。近年来,偶有文艺理论家藉以来状喻艺术创造所进行的去粗取精、去芜存真、删繁就简的典型化过程,不能不说是独具只眼、别出心裁的理论识见。然而,追本溯源,“牝牡骊黄”这一事典的真正价值,正在于它揭示了艺术思维及其理性认识的本质特征。
无独有偶,被格式塔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称誉为“曾以非凡的勇气和天赋描述过他亲眼见到的那些与常识大相背悖的东西”的爱德华·B·铁钦那,以思维心理学家那独特的心理内省体验,描述了在他的心理意象中的“马”:“在我的眼中,一匹马只不过是一条呈跃立姿态的双曲线,周围有鬃毛点缀”。这样的“有鬃毛点缀”的“呈跃立姿态的双曲线”,应该说正是他对类似九方皋所相得的千里良骥那“腾骧磊落”的风神骨气的本质抽象或曰形象概括。那么,这种本质抽象或曰形象概括在艺术思维的过程及至艺术思维本身的思维过程是怎样进行的呢?铁钦那阐发道:“在我的大脑以正常状态活动起来时,它便是一列清晰而又完整的画廊——不是由已定稿的画组成,而是一系列印象式的画稿,每当我读到或听到某某人在虚心地或严肃地、骄傲地、谦卑地和殷勤地做某件事情时,眼前就立即呈现出:‘虚心’、严肃、骄傲、谦卑、殷勤等视觉形象,……一提到一个谦卑的随从,我眼前便闪现出一个弯腰曲背的形象,但这个形象的唯一清晰之处,却是他的弓形的背,虽然有时候还有放置在(未呈现的)脸前方的正乞求些什么的手……。上面描述的这些情景,有时十分确定和明确,有时又象是童话一样的虚幻。”[1]阿恩海姆在援引了关于“视觉形象的闪现和暗示”这段心理内省体验之后强调指出:“这段话代表着新时代的声音。在这段话中,他以最明确的语言告诉我们,种种印象或心理意象的忽隐忽现,并不说明我们对这些事物没有完全把握,也不是心灵对它进行了切割。其实,这种粗略意象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正面的或肯定的性质。正是这样一种性质,才把一个物体的心理意象同它的自然本体区别开来,使我们避免了所谓‘客体—谬误’。所谓‘客体—谬误’,乃是指那些把心灵对外物的解释,错误地等同于客体本身的(或是全部或是部分)性质的错误。”[2]
这段“代表着新时代的声音”的思维科学的新颖阐释,使我们对于艺术思维的思维活动及其理性认识机制的认识和理解,得到了细化和深化:(一)作为思维心理学家的铁钦那的这段心理内省体验的胪陈,是对于艺术思维或曰形象思维所呈现的心理形式的具体而微的科学描述。(二)被格式塔心理学家称之为“心理意象”的表象或印象,是以“忽隐忽现”的“闪现”的方式出现的——这,便是艺术思维或曰形象思维的思维活动所呈现的一般心理形式。没有了“闪现”,也就没有了艺术思维或曰形象思维的思维活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三)艺术思维或曰形象思维的思维活动,由于“心理意象”或曰表象的“忽隐忽现”地“闪现”,使得“心理意象”或曰表象产生了“一系列印象式的画稿”。这“一系列”画稿的产生,正表明了“心理意象”或曰表象自觉运动的嬗替衍变和推陈出新,使得艺术思维或曰形象思维的思维活动,以层出不穷、赓续不断的视象呈现形式得以直接现实。(四)艺术思维或曰形象思维的“闪现”心理形式中,最具认识价值的是它于“暗淡闪现”之中的“清晰暗示”。如铁钦那所作的心理描述那样,在他脑中出现“谦卑”这一概念或意念时,“便闪现出一个弯腰曲背的形象,但形象的唯一清晰之处,却是他的弓形的背。”这种“唯一清晰之处”,即是被阿恩海姆称之为“视觉暗示”的地方。这种对于心理意象或曰表象于“闪现”中呈现的“暗示”,正是通过视知觉所选择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的个别特征的感性形式,来表现概念的内部联系及其本质,从而达到理性认识的心理形式的肯綮。由此推断,九方皋也正是在“牝牡骊黄”的一片“闪现”和“暗示”的心理意象或曰表象中,“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地“视”、“见”了千里良骥之所以日行千里的本质特征。(五)正如伯乐所说的“见其所见”、“视其所视”的“见”和“视”一样,阿恩海姆在他对铁钦那的心理描述的阐释中,在“理解”和“看”的下面,加了重点符号予以强调;表明这样一种在暗淡、模糊中闪现的清晰部分如“弯腰曲背”,则不仅体现了具体事物的个别真实,同时还体现了这类事物内部联系的一般真实——即本质真实。这种本质真实,在心理意象暗淡地“闪现”中被清晰地“暗示”出来,使视觉主体不是通过概念的判断和推理来认识和理解,而是通过视知觉的直接感觉即“看”,来达到理解其规定内涵即本质属性的理性认识的。这对于我们深刻领悟马克思关于“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3]这一美学命题及其直觉对于审美感悟、艺术创造的重要作用和理性认识功能等美学理论问题,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六)这种“闪现”和“暗示”,作为艺术思维或曰形象思维的心理形式,正如阿恩海姆钩元提要所指出的那样:“并不说明我们(的心理意象)对这些事物没有完全把握”,恰恰相反,这种于暗淡中“闪现”、于清晰处“暗示”的“粗略意象”,本身就代表着对事物本质属性的一种正面的或肯定的性质;并且正是通过这种肯定的性质,使我们避免了所谓“客体—谬误”即那种把心灵对外物的解释,错误地等同于客体本身(全部或是部分)性质特别是客观事物的表面现象即非本质属性;而“心灵对外物的解释”,则表明了视觉主体的感觉器官对于外物某种本质属性的抽象——这正是包括视知觉即视觉思维在内的艺术思维或曰直觉思维的理智机制的突出表现。对那些认为艺术思维即形象思维不具有“思维性”,不能达到理性认识的观点——即所谓“主体—谬误”,是一个有力的反拨。(七)艺术思维的“闪现”和“暗示”等心理形式,在铁钦那的心理意象中如同“印象式的画稿”一般,这就使得铁钦那对自己视觉经验这一心理内省的描述,同以往其他心理学家的视觉经验描述,有了根本的区别,使他真正成为“新时代的声音”。这根本区别正如阿恩海姆指出的那样:如同印象派绘画同它以前的一切传统绘画有着根本的区别一样。尽管在莫奈的《日出·印象》之前,西方传统画家们在再现外部客观物体时已经相当随便或者说出现了逸笔草草的画风,但仍未脱离传统绘画观的窠臼——绘画以达到逼真摹仿、再现客观外物为己任。唯印象派绘画勃兴之后,它的艺术实践促使绘画美学理论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认识到绘画乃是心灵生长的精神花朵,而不是外部物理对象的机械复制;“其实,画家真正想要表达的效果或经验,是视觉意象的‘闪现’或‘暗示’。这些‘暗示’会引导我们体验它的大体色彩和方向,而不是物体的具体而又确定的轮廓或物体的某一细部。”[4]因此我们认为,以莫奈的《日出·印象》之“印象”,作为画派名称即印象派的出现,不是一种艺术风格或审美风尚在艺术表现上的偶然展示;因这种以表现画家心灵感受的主观印象为旨趣的画风形成,可谓是艺术家对于艺术思维或曰形象思维的心理意象这一心理形式的主体自觉。特别是初期印象派到后期的“点彩派”的嬗变,以至采用纯度高的原色色点的混杂厾点,来表现迷离朦胧的自然景物(如同“暗淡闪现”)中的明媚阳光(如同“清晰暗示”——表现“印象”中的大自然的外光特别是明媚阳光,是印象画派的永恒主题或曰画旨),这便更加清楚地体现作为主体的心理意象,对自己的“视觉闪现”和“视觉暗示”[5]的心理形式所经历的由自在到自为的心路历程。从某种意义讲,艺术家对自己的艺术思维“闪现”和“暗示”这一心理形式经历的由自在到自为的自觉,正是对于艺术本质的自觉,对于艺术掌握世界的本质特征的自觉。
由艺术思维“闪现”和“暗示”引发和体现的这种艺术本质乃至艺术掌握世界的本质特征的自觉,还存在于其他的心理现象如灵感、联觉和错觉等之中;它们在表现主体心灵的自觉时呈现的心理机制和审美机制是怎样的呢?
二、艺术思维“闪现”和“暗示”在灵感中的心理形式和审美机制
作为艺术思维的“闪现”和“暗示”等心理机制的特殊状态,便是灵感的“心灵烛照”的独特心理现象。所谓“灵感”,早年迻译中国,即鲁迅于《并非闲话》中说的“烟士披离纯”(英语“灵感”(insbiration)的音译)。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这一概念,借用了佛教教义中的“悟”。“顿悟”、“参悟”、“感悟”、“颖悟”、“圆悟”等均归此属。指众生成佛时明心见性的悟觉。此外,“神来”、“神助”、“神通”、“神应”及“契妙”等亦归此属。其侔色揣称,颇类西文。如柏拉图在《伊安篇》中也认为:“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6]这无疑都是囿于人们缺乏对自身认识的自觉,无法解释心灵即思维的这一神奇现象所致。其实,灵感即是人脑在高度亢奋情况下信息纷呈并相互沟通所造成的那种最佳的思维态势。[7]那么,灵感遽发时的具体心理形式或曰心理特征是怎样的呢?然而,这揭示灵感本质特征的重要心理特征却往往被人忽略了。
许多作家艺术家在剀切详明地追忆自己艺术创作时所体验的灵感现象中,都描摹了一种奇异的心灵的火光烛照现象。彼时的意象或表象在这“心灵烛照”之中,显得异常鲜明、清晰。即“思想里活动着最清晰的形象”[8],并闪烁着令人兴奋和激动的绚丽光彩。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早就指出:“没有一种心灵的火焰,(便)没有一种疯狂式的灵感。”[9]巴尔扎克更加具体地描述道:“某一天晚上,走在街心,或当清晨起身,或在狂饮作乐之际,巧逢一团热火触及脑门,……顿时,一字唤起了一整套意念。”[10]周扬指出:“这样酝酿又酝酿,于是突然一下子,完全出你意外地,火从里面着出来了,火舌伸吐着,照得漫天通红。”[11]当代作家王汶石也深有感触:“忽然得到启发(人们通常把这叫做灵感),它就象一支擦亮了的火柴投到油库里,一切需用的生活记忆都燃烧了起来,一切细节都忽然发亮。”[12]根据作家艺术家在文学艺术创作实践中的心理内省经验及思维心理学的有关实证材料,我们认为:(一)所谓“灵感”的“心灵烛照”现象,正是艺术思维或形象思维的“闪现”和“暗示”这一心理形式所表现的特殊形态或曰特殊势态。由于其“闪现”和“暗示”的心理活动处于最佳的“思维势态”,故“思想里活动着最清晰的形象”;而这种“最清晰的形象”又正是“心灵烛照”亦即“闪现”和“暗示”的结果。根据格式塔心理学的实证材料表明,这种“心灵烛照”现象,是视知觉系统即后半部的大脑皮层视觉中心——大脑皮层的电化学力场释放出来的能量,呈现出振荡最佳势态而生发出来的火光幻觉。(二)灵感遽发时的“心灵烛照”的“闪现”和“暗示”心理机制,具有多方面的“串连”或曰“引发开启”作用。灵感的巨大创造性悉生于兹。明代戏剧家汤显祖根据自己的艺术实践体验,谈及灵感偶发时:“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是故善画者观猛士舞剑、善书者观担夫争道、善琴者听淋雨崩山。彼其意诚欲愤积决裂,挐戾关机,尽其意势之所必极,以开发于一时。”[13]这里的“挐戾”之“挐”即牵引,“戾”同捩,转动之意;挐戾意为“引发开启”。“关机”即“机关”,此以控制机械的关键部位而喻心脑之灵窍。将灵感阐释为引发开启心脑之灵窍,不能不说是卓有见地的。物理学家杨振宁的阐释则更为明了:“所谓灵感,是一种顿悟,在顿悟的一刹那间,能够将两个或以上,以前从不相关的观念串连在一起,以解决一个搜索枯肠仍未解的难题,或缔造一个科学上的新发现。”[14]这里所说的“观念”,不能作胶柱鼓瑟的读解。正如金开诚所指出的那样:“要作广义的理解,即指‘意’也指‘象’;广义的‘观念串联’可以概指意与意、象与象、意与象之间的多种多样的‘串连’”[15]。思维科学的积极成果表明,思维活动的一般模式,是一个三项式,即由首项、中项、末项组成。首项为出发知识,末项为结论知识,中项是“接通媒介”。如果接通媒介是抽象形式的知识如概念等,这种思维活动是抽象思维;如果接通媒介是形象形式的知识,这种思维活动是形象思维;如果接通媒介是直觉形式的知识,这种思维活动便是直觉思维。灵感或曰灵感思维即是特殊的直觉思维。[16]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从某同事的双颊潮红,可直觉他(她)感冒发烧了或患有肺结核病等,但这绝非灵感思维。所谓灵感思维,即在以人们的直觉作为接通媒介的思维活动中所得到的结论知识,必须是前所未有的具有社会价值的新知识或及时、新颖、巧妙地解决了重大疑难问题的知识。[17]前者如牛顿见苹果坠地发现万有引力即为典型例证。这些当然是针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而言的。对于文学艺术创作来说,其结论知识则应该是:具有深刻思想蕴意与高度审美价值的崭新艺术形象和巧妙、新奇、圆满地解决了文学艺术创作中的困惑和难题的方法等。前面所援引的自古迄今的“心灵烛照”即艺术思维“闪现”和“暗示”的特殊势态,正是作为接通媒介的直觉完成“串连”或曰“引发开启”之后,所出现的困惑、疑难涣然冰释、迎刃而解,新颖而瑰丽的想象表象或曰意象纷纷攘攘涌跃呈现的灵感思维形态。(三)灵感遽发时的“心灵烛照”的“闪现”和“暗示”心理机制,还具有融合化一客观与主观、存在与意识的作用,以达到“物我一体”的最高审美境界。由于物象和情意在“心灵烛照”即“闪现”或“暗示”下的“串连”或曰“引发开启”,使得客体与主体即客观与主观、外物与情志达到同一,从而产生具有审美价值的意象乃至意境。正如周扬所指出的那样:“这样酝酿又酝酿,于是突然一下子,……火从里面着出来了,火舌伸吐着”,“这个火就是融化了客观的主观,突入了对象的热情。借用王国维式的表现法,叫做‘意境两忘、物我一体’。这是创作的最高境界。”[18]之所以说“意境两忘、物我一体”是创作的最高境界,是因为审美实践中客体与主体,外物与情志确乎常常处于一种物我难分的融合化一的情景中,主体仿佛感到自己化为了对象,或曰对象化了。如庄周梦化蝴蝶,宛如蝴蝶那样翩翩飞舞,自由自在,怡然陶然。就对世界的哲学掌握或科学掌握来说,无疑是荒诞不经的;就艺术掌握或审美掌握来说,却深刻地揭示了审美心理活动中确实存在的“移情”现象。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体的观点来看,这便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所发生的“自然的人化”在主体的情感心理或曰审美心理上的反映。[19]王国维承袭庄周学派把审美当作“物我一体”的境界,表明中国古典美学不仅是单纯从物的属性或形式美如对称、均衡、和谐等方面去寻求美,而且还从我与物、情与景、意与象、主体与客体的精神联系上去寻求美,把美看作是一种诗化的忘我的物我浑一的特定情境或生活境界,不能不说是一种具有审美巅峰体验的最高诗美境界。然而,这种“意境两忘、物我一体”的最高诗美境界的寻得,如同前述的“最清晰的形象”的获得和众多意象纷纷攘攘涌跃呈现的诸审美特征或曰审美机制一样,是始终伴随着灵感的“心灵烛照”即“闪现”和“暗示”的特殊势态而密不可分的。因此,上述诸审美机制,也是灵感思维的“心灵烛照”,即艺术思维特殊势态的“闪现”和“暗示”的心理形式所呈现的审美机制。
三、艺术思维“闪现”和“暗示”在联觉中的心理形式和审美机制
艺术思维的“闪现”和“暗示”心理形式,还同“联觉”这一心理现象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以其诡谲瑰丽、变幻莫测的审美意象及其审美机制,造成艺术表现和审美感兴的深入雅致的独特魅力。联觉是不同的感觉相互作用、相互沟通所产生的一种特殊心理现象。故也称“通感”。它在审美主体的心理意象里,仿佛视觉形态的颜色有了冷暖,听觉形态的声音有了形状,嗅觉形态的香臭有了锐钝等。《礼记·乐记》中的“故歌者,……累累乎端如贯珠”。正如杜预于《注》中所言,“论其声”乃“以耳为目”。堪称联觉范例。陆机《文赋》在探讨艺术思维的思维特征时,便关涉到联觉,殊为难能可贵:“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葳蕤,唯豪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我们认为,联觉与灵感的艺术思维“闪现”和“暗示”的心理形式是大体相侔的,都是“沟通”、“接通”或曰“引发开启”。只不过灵感“接通”的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而联觉则将主体对客体反映的各种不同的感觉器官及其不同感觉形态的反映一并“沟通”、“接通”起来;灵感“接通”的既有感性认识也有理性认识,而联觉“沟通”的则主要是感性认识即感觉或曰直觉。我们须指出的是,联觉这种“沟通”和“接通”所产生的别样感觉形态,其本身便是独具审美特征或曰审美机制的。那么,联觉的客体感性形式和主体心理机制及其关系的谐调统一与否,和审美价值或审美机制的高低强弱、损益亏盈有无联系呢?回答是肯定的。阿恩海姆指出:“有些意象的视觉形态还被约简为某种形状或某些性质的‘暗示’或‘闪现’”[20],因此,“我们的心灵中有可能会出现一种联觉经验”[21],“当一个人倾听某种声音(尤其是音乐)时,会感受到一片特殊的色彩。”[22]“一般说来,这样一种特殊的视觉感受,不会使音乐变得更加悦人和更易于理解,即使在一首曲子自始至终都会唤起同一种色彩感受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当人们使某些动态的色彩形式随着音乐的播放而出现时,便会得到极佳的效果。这时,动作、节奏、色彩、形状、音调等均越过了各自的感觉界限,相互支持和加强。[23]当然,上述各种不同感觉结合起来之后,究竟有益还是有害,主要取决于各种感觉之间在结构上是否相互对应或这种对应是否在感受者心中出现。”[24]这便大大加强了我们对联觉的客体感性形式和主体心理机制及其审美价值或审美机制之间的关系的具体情形的认识和理解:(一)具有审美属性或曰审美特征的“联觉”现象,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发生的;它的发生往往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常常被表现为,主体的心理意象的视觉形态被约简为某种形状或某些性质,即显现出彰明较著的形式美特征而被“闪现”和“暗示”的情况下才成为可能。(二)从审美客体即审美对象来说,无论视觉形态与听觉形态或其他感觉形态的心理意象所产生的一般“联觉”,似乎都不能改变其审美价值或审美机制的高低强弱、损益亏盈——不仅其形式美因素是如此,而内容美因素也是如此。只有当他们如视觉形态和听觉形态的心理意象,产生了诸如“动作、节奏、色彩、形状、音调等”形式美因素的共时性的动态谐调时,其审美价值或曰审美机制,才会产生质的飞跃,极大地激发主体的审美感兴,获得更大的审美怡悦。如宋祁《玉楼春》词的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正是因春意盎然、东风骀宕、杏花枝头、万红攒动的视觉形态的心理意象,与莺啼宛转、燕语呢喃的听觉形态的心理意象,产生了诸多形式美因素的共时性的动态谐调,才于作者濡墨飞翰间跳踉出一个独具审美魅力的“闹”字来,成为联觉的千古绝唱。(三)从审美主体来讲,只有当各种感觉在心理结构上取得对应的相谐关系时,联觉所独具的审美机制,才在艺术思维的“闪现”和“暗示”之中成为美感的直接现实。譬如“热闹”的“热”(温觉)和“闹”(听觉)、“冷静”的“冷”(温觉)和“静”(听觉)在主体感觉的心理结构上取得通同一气、对应相谐的关系,故被约定俗成地牢牢结合在一起。范成大的诗句“已觉笙歌无暖热,仍怜风月太清寒”中的“笙歌”(听觉)、“风月”(视觉)和“暖热”、“清寒”(温觉)是分别通同一气、对应相谐的。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音乐的声调摇曳(the quaveringupon a stop in music)和光芒在水面浮动(the playing of light upon water)完全相同,那不仅是比喻,而是大自然在不同事物上所印下的相同的脚迹。”[25]钱钟书指出:“这可以算哲学家对通感的巧妙的描写。”[26]我们以为,倘将这“巧妙”变得更加“准确”,当是大自然在不同事物上所印下的相同的脚迹,在我们(培根等)心灵上引起的相互通同、相互对应、相互和谐的橐橐回声。而这一切都是以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属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即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27]为前提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享受到联觉给我们带来的云谲波诡、独具魅力的审美愉悦。
四、艺术思维“闪现”和“暗示”中的美学错觉及其他
错觉是客观事物的不正确的知觉现象。但当他被知觉主体或审美主体和创造主体,作为一种艺术掌握世界的方法论,在审美实践和艺术创造的过程中,由于艺术思维“闪现”和“暗示”等心理机制的作用而产生出审美价值或曰审美属性时,便成了“美学错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这一具有艺术掌握世界的方法论意义的范畴:“美学上大大小小的鲁滨逊故事的错觉”[28]。这里所说的“美学错觉”,根据我们的理解,实质上便是马克思在同一文章后面所指出的那种通过“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29],即对世界进行艺术掌握或审美掌握的方式,暂时取代了通过社会实践“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30],从而揭示事物内部联系即本质的对世界的哲学掌握或科学掌握之后,所产生的迷惘或错觉。然而,由于“美学错觉”作为艺术掌握世界的艺术方法论,在艺术思维的“闪现”和“暗示”心理机制的作用下,产生了诸多的存在形态和审美形态,大大地丰富和提高了文学艺术实践的表现方法、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
这里有一个饶有趣味而又发人深省的艺术问题:古代诗人特别是唐代杰出诗人王维、李白、杜甫等,为什么那么喜欢将“大漠”、“长河”、“海上”与“落日”、“初月”、“孤烟”、“孤帆”等风物组合在一起吟咏。这里要特别指出的即是,曹雪芹于他的不朽巨著《红楼梦》中,借香菱之口,言及诗家三昧,所引王维那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几乎句句不离“落日”与“孤烟”。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和“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等不一而足。并言之凿凿地说这“孤烟”之“直”和“落日”之“圆”,“合上书一想,倒象是见了这景的,若是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字,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由于诗中上述意象,在她脑中形成极其鲜明、深刻的印象,遂使她由激赏的审美态度转变为确定的审美判断:“直”、“圆”之妙,洵为不刊。我们认为,这不能不说与美学错觉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于此且举“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试加释析。首先须指出的是,对于具有极其锐敏的“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的画家(南派鼻祖)、诗人(“神韵说”诗宗)王维,运用“大漠”和“孤烟”,“长河”和“落日”营造了一种诗意絪蕴的形式美感,而这种具有均衡、对称等形式美感的风物,不仅易于造成意象鲜明的诗美境界,而且易于产生稳定宁静的心境意绪,足以引起审美注意和审美感兴,于是,“大漠(地平线)”的横线和“孤烟”的竖线、“长河(水平线)”的横线和“落日”的圆形,便分别产生了长度错觉中的横竖错觉(horizontal-vertical illusion)和月亮错觉(moon illusion)。前者表现为视觉主体视域内的知觉映象的竖线(如“孤烟”),比与它等长的横线(如“大漠”)显得长些;后者则是月亮(或“落日”)在接近地平线或水平线(如“长河”)时,比在头顶上的月亮显得大1.5倍。[31]因此,这些错觉现象,对视知觉所产生的视觉形态的冲击力,使得视觉主体的感知映象乃至记忆表象和想象表象,有时在记忆表象的对比下(如同记忆表象中的“中天之月”相对比),生发出印象鲜明、感受强烈且难以磨灭的审美意象来。这便是美学错觉造成千古绝句的独特魅力的个中堂奥。
思维心理学家M·布鲁墨将识认错觉研究的触角,伸向了语言叙事艺术。她指出:“神秘小说作家如阿莎·克里斯蒂和阿瑟·柯南道尔就是这样来构思故事的,他们让读者得出‘错误的’形象,真正的线索则置之不顾。侦探的本领就在于他们能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作家大笔一挥,细节改变了,新的形象——结果——便暴露无遗了。”[32]我们认为,M·布鲁墨所说的“他们让读者得出‘错误的’形象,真正的线索则置之不顾”的所谓文学技巧和奥妙,主要表现在神秘小说亦即侦探小说范式结构的第二构成因素“情节”和第三构成因素“人物关系”上。在“人物关系”上,“受害者”和“侦探”一般是确定的因素。而“罪犯”和“侦探的朋友,牵涉进罪案的好人”,则是作者所施展的布疑手段,“让读者得出‘错误的’形象”即产生错觉。在“情节”上,则是作者有效地利用读者通过视觉表象的“闪现”和“暗示”的心理机制,展示自认为合乎生活逻辑的故事或曰情节,以造成视觉错觉的识认活动。这种视觉错觉实为美学错觉的识认活动的全部审美魅力,都表现在侦缉罪案的故事情节进入戏剧性高潮(即“宣布案件侦破”和“解释破案疑窦”——有时此两环节是“急转直下、合二而一”的)时,所造成一种在“介绍侦探”、“列出犯罪事实及犯罪线索”和“调查”等情节的叙述中,足以使读者产生月迷津梁、雾失楼台的识认错觉,同“宣布案件侦破”时的扑朔迷离一起,产生极其强烈的诧异而又新奇的矛盾心理和心理矛盾。及至“解释‘破案’”时,使得故事情节在进入戏剧性冲突的高潮中,生发出出其不意的“发现”和急转直下的“突转”,使读者产生撄及灵府的内心震撼、浮想联翩地不断追忆回溯识认错觉之所由因缘,通过自觉或不自觉的反思、内省,在重新确认自己的智慧力量中获得喜悦。这便是美学错觉所独有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魅力之所在。
西方现代派造型艺术中,画家常常利用其所描摹对象的感性形式及其背景的“黑”与“白”的重叠,和描摹对象的视觉形式的模棱两可的模糊性,乃至特殊视觉形式的“频闪”动态效果,以造成审美主体在观赏此类作品时,所产生的略带谐谑意味的轻喜剧审美形态的美学错觉。著名作品有《彼得—保尔高脚杯》、《妻子和岳母》和罗格·普莱斯题为《橄榄掉到马丁尼酒杯中或一个穿紧身浴衣女子的特定镜头》和马赛尔·迪尚《走下楼梯的裸体者》等。更有毕加索的《生活的乐趣》、《底座上的静物》等,则于那诡谲离奇和倏忽幻化的特殊造型中,展现出他所谓的“双重肖像画”那种或隐匿或透露的“隐私”与“假象”来,使得他那独具个性的生命意识:挚爱与憎恶,沉实与荒唐、创造与毁灭等相杂糅的崇高与滑稽相交织的矛盾审美形态,在艺术思维“闪现”和“暗示”心理机制所呈现的美学错觉中得到独特的表现;并在同样的心理机制所呈现的美学错觉中被鉴赏者接受。这不仅是毕加索巨大艺术成就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审美精神和艺术方法论的一个鲜明标志。
还要顺便提及的则是,视觉形态的美学错觉在工艺美术和服饰审美文化中的运用,有着极为广阔的天地。正如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所记叙的鲁迅对于服饰审美文化的“错觉”矫正功能及其运用的深湛见解:“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33]现代服装学则从服装款式和造型的廓形线,面料的颜色及条纹等的搭配、对比以及女装花饰的分布与点缀等方面,无不广泛运用方向错觉、角度错觉、对比错觉、分割错觉等多方面错觉原理,以达到利用美学错觉的矫正、美化功能,提高服饰审美文化的艺术含量之目的,从而造成服饰与人体关系的和谐美、个性美和风度美等等。
最后,我们须强调指出的是,思维心理学对错觉特别是视觉错觉的研究和认识,有了新的突破和拓展,按照系统论的观点,错觉是由物理的(光学成分)和生理的(视网膜、皮层)以及识认等多种原因引起的,最终知觉的视觉系统中正常加工的表现形式。我们认为,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那些能感受人的快乐和确证自己是属人的本质力量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34]这说明了作为历史的、社会的、现实的人,以自己全部世界史的审美文化积淀所造成的审美文化心理结构,使得自然性的感受错觉的视觉感官,已经具有了社会性的美学错觉的审美机制,从而表现了人类对世界的艺术掌握或曰审美掌握的自觉。
注释:
[1] 爱德华·B·铁钦那《关于思维活动的试验心理学讲演》第13页,纽约·麦克米兰1916年版。
[2] 鲁道夫·阿恩海姆著《视觉思维》(滕守尧译)第177—17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7月版。
[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版。
[4] 鲁道夫·阿恩海姆著《视觉思维》(滕守尧译)第17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7月版。
[5] 鲁道夫·阿恩海姆著《视觉思维》(滕守尧译)第17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7月版。
[6] 柏拉图《伊安篇》、载《文艺对话录》第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7] 刘锡庆《基础写作学》第185页,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4月版。
[8] 黄药眠《论食利者的美学》、载《初学集》第60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9] 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第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7月版。
[10] 巴尔扎克《论艺术》,载《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0册第97页。
[11] 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之一,载《解放日报》1941年7月17日副刊版。
[12] 王汶石《答〈文学知识〉编辑部问》,载《创作经验谈》第4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13] 汤显祖《序丘毛伯稿》,载《汤显祖集》第10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14] 《杨振宁谈灵感涌现有赖知识积累》,载《文汇报》1985年2月3日文摘版。
[15] 金开诚《文艺心理学概论》第3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9月版。
[16] 田运《关于灵感思维的两个问题》,载《贵州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
[17] 田运《关于灵感思维的两个问题》,载《贵州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
[18] 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之一,载《解放日报》1941年7月17日副刊版。
[19] 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第2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7月版。
[20] 鲁道夫·阿恩海姆著《视觉思维》(滕守尧译)第180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7月版。
[21] 鲁道夫·阿恩海姆著《视觉思维》(滕守尧译)第180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7月版。
[22]鲁道夫·阿恩海姆著《视觉思维》(滕守尧译)第181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7月版。
[23]此试验由奥斯卡·弗舍格(Oskar Fishinger)、瓦尔特·鲁特曼(WalterRuttman)和诺曼·麦克拉伦(Norman Mclaren)等所做。
[24] 鲁道夫·阿恩海姆著《视觉思维》(滕守尧译)第181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7月版。
[25] 培根(Bacon)《学术的进展》第2卷第5章,转引自钱钟书《旧文四篇》第52页。
[26] 钱钟书《旧文四篇》第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版。“热闹”等例亦参见钱文。
[2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8、79、7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版。
[28]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
[2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
[3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
[31] 林传鼎等主编《心理学词典》第56、466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6月版。
[32] 卡洛琳·M·布鲁墨《视觉原理》第4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8月版。
[33] 转引自施昌东《“美”的探索》第37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1月版。
[3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
标签:艺术论文; 艺术价值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美学论文; 视觉错觉论文; 形象思维论文; 思维模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