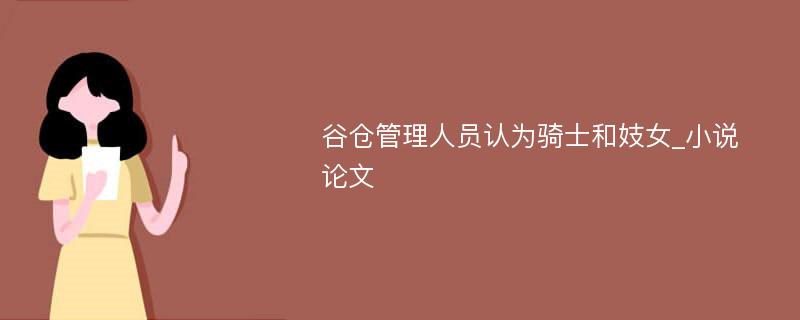
稗官争说侠与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稗官争说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末,当维新派策动思想与文学改良风潮之际,新学泰斗严复、夏曾佑联名在《国闻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文章。文章的主要思想成果表现在它试图完成对以下两个问题的解释:第一,普遍人性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及其与文学永恒性主题的关系;第二,小说文体在表现人性及再现人类行为时所显示出的优长。文章认为:茫茫宇宙,古今中外,凡为人类莫不有一“公性情”,曰“英雄”、曰“男女”。英雄、男女之性相互倚存,支撑人类在物竞天择法则支配之下的社会与自然进化的漫长旅途中,自强不息,繁衍生存,从蛮荒混沌、茹毛饮血走向文明之化。英雄、男女之性与人类文明进化相始终,又自然存在于每个社会个体的血肉之躯中。英雄、男女之性为政教礼乐之本、文章词赋之宗。若将英雄、男女之性形诸笔端,“作为可骇可愕可泣可歌之事,其震动于一时,而流传于后世,亦至常之理,无足怪矣。”至于再现英雄、男女之性,托之于经、子、集等言理之书,莫如托之于史、小说等纪事之书;托之于史书,则又莫如托之于小说。小说与史书相较,史书重在实录,而小说则“凿空而出,称心而言,更能曲合乎人心”,故而“曹、刘、诸葛,传于罗贯中之演义,而不传于陈寿之志;宋、吴、杨、武,传于施耐庵之《水浒》,而不传于《宋史》。”作者据此宣称:“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
《缘起》一文旨在为新民救国运动和小说界革命的兴起而鼓噪,但其视英雄、男女为人类普遍人性,以擅长表现普遍人性、艺术再现人类行为而推重小说,却是超出时论、颇有识地的见解。人类的存在与发展,充满着艰难困厄,也充满着欲望梦幻。对人生进取的渴望,对英雄行为的崇拜,对缠绵情爱的企求,构成了世俗人生最为普遍的情感。而小说是一种重再现的艺术,它力图在实虚真幻之间,展示人类生活场景与行为、情感,再现历史与人生,以满足人类自知、求奇与审美愉悦的各种需求。在世俗人生、普遍人性与小说之间,存在着最为简捷的通道和最为短暂的化入距离。因而,当明清小说超越志怪、讲史的题材范围,以现实世俗生活为主要场景,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注:《今古奇观·序》)为小说写作旨志之时,解人急难的义士侠客、缠绵怨慕的痴男情女,便跃然成为小说中的主角,英雄之性、男女之情遂演绎成为无数人世间悲欢离合故事的主题原型。
19世纪小说最引人注目的创作趋向,是长篇白话作品中侠、妓题材的空前盛行,形成了稗官争说侠、妓的特有景观。说侠者有《三侠五义》(首刊于1879年)、《荡寇志》(首刊于1851年),言妓者有《品花宝鉴》(首刊于1849年)、《青楼梦》(成书于1878年)、《花月痕》(首刊于1888年)、《海上花列传》(结集本初版于1894年)。合英雄之性、男女之情于一身的有《儿女英雄传》(成书于1849年)。其卷帙繁多,蔚为大观,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和创作潮流。19世纪侠、妓小说是英雄之性、男女之情传统主题模式的衍化与畸变。作者分别选取世俗人生中最富有神秘传奇色彩的人物与生活场景,在工笔浓彩、腾挪变化之中,演述着人世间的悲喜剧。19世纪侠、妓小说产生在中国封建社会正在走向土崩瓦解的社会背景下,小说所显现的价值观念与作品所形成的主题模式,带有鲜明的历史与时代的烙印。
一 文化变动与小说观念
中国古典文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发达的审美教化意识。审美教化意识把人类的审美活动与道德完善看作是充满必然联系的过程,它时时提醒文学家在进行美的创造的同时,要给人以善的启示,以唤起人们的反省与良知,从而影响与规范其思想及行为。由真及美,由美及善,终达于德行净化、人格完成。在审美与教化的和谐中,求得生命个体对社会伦理政治的心悦诚服。
审美教化意识源于儒家礼乐文化,它最早表现在诗学观念之中。孔子论诗,以为诗可以“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注:《论语·阳货》)《毛诗·序》论诗,以为诗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种将审美与伦理教化、家国政治紧密连接的诗学观,突出地强调了诗的社会功能。在以治平修齐、安邦治国为人生最高理想的传统价值体系中,诗也因为有裨政教而被以莫大的殊荣,沾溉上高贵气象。继诗学之后,文有载道、明道之说,文取得了与诗并肩的资格。诗裨政教、文以载道之所以被历代文人墨客所津津乐道,除去文化认同的原因之外,其中不无托体自尊以显示高雅优越的心理作祟。
如果以神话寓言作为中国小说的源头,小说的成育年代并不晚于诗文。小说是一种虚构的叙事文体,其虚构的特质与诗文同构,其叙事的体征则与历史毗邻。在传统的文化构成中,小说没有诗文的殊荣,更不能与历史相提并论。在虚构性叙事——小说与记叙性叙事——历史之间,我们的祖先对历史投入了其他民族无法相比的热情。历史对于民族的社会性生存,有着更为直接的作用,它担负着记述严肃重大事件的任务。战争风云、朝代更替、文明进化,其气魄之恢宏,笔力之深厚,篇帙之繁重,令人叹为观止。在优秀的史学著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文学气息。跌宕完备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生动具体的生活场景,使人获得史实之外的审美愉悦,文学记叙被渗透、融化在历史记叙之中。而以文学性叙事为职志的小说则流落于摭拾异闻杂说、志怪志异的地步,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消遣,任其自生自灭。
小说在民族初期文化结构中的位置,是由它自身所显现的价值系统与社会需求程度所决定的。我国封建文化形成的基础,是农业化生产方式及由这种方式所带来的等级文化观念。它所拥有的文化成员,必然与农业社会生产方式的存在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小说文体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被界定为“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浅薄”、“悠谬”的看法,就决定了小说在封建初期文化结构中处于“君子弗为,然亦弗灭”的非中心与游离性地位。对小说功能的认知局限在志怪志异的范围之内,它便很难获得广泛的社会需要,它的“悠谬”特征与所载之异闻杂说,只为少数有闲者所欣赏、解读。
明清两代,随着单一农业生产方式的缓慢解体和市民文化的兴起,传统的文化结构及文化成员之间的排列秩序面临着新的调整,于是,小说借助外力开始不失时机地由文学的边缘向中心地带运动。促成小说运动的直接外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市民文化导向,一是小说家对小说功能的重新阐释。市民文化在晚明人文主义思潮的激荡下,表现出对自然人性和社会平等理想的追求,对普通人命运的关心。市民文化导向促使社会产生对世俗人生与人间故事的消费需求和阅读期待,为小说开辟了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而小说理论家则试图通过对小说功能与价值的重新阐释,从思想观念入手,改变小说的社会形象及在整个文化结构中的地位。
小说遭人鄙夷的重要原因,在于人们普遍认为它不及诗文高雅而不及史书有用。明清小说家推重小说,则试图论证小说兼备诗、文、史之优长,可以补史、劝戒,怡神导情,与圣经贤传同为发愤之作。
补史之说流行最早,此说旨在通过揭示小说与正史之间互补倚存的关系,论述小说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自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列小说家为九流之外的第十家,关于小说价值的争讼便绵延不绝。班固对小说的立论本来是相当谨慎的。他一方面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另一方面又引用孔子“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之说,以为于小说,“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此话的前段,常为轻诋小说者所引用,而后段,则为小说家据为口实。他们试图从“虽小道,必有可观”之处,肯定小说的存在价值。但这种存在是以自轻自贱、自处小道为代价的。至晋人葛洪有以《西京杂记》“补《汉书》之阙”(注:《西京杂记·卷六》)的说法,小说家遂寻找到一种补史的生存理论。明清时期,补史说盛行一时,不但讲史之演义称为补史,而且描摹市井人情、备写悲欢离合故事的小说亦称为补史。补史论者比较史书与小说两种叙事文体的差异,以为史书重实录而传信,小说尚虚幻而传奇。史书为官书,大抵写君主承继、将相踪迹;小说为稗史,可构写世间奇情侠气、逸韵英风。史书写一人一事即是一人一事,小说写一人一事可括百人百事。小说与史书相比,具有独特的虚构性和典型意义,两者尺短寸长,无贵贱之分,不能相互替代,只能倚存互补。
如果说,补史说试图通过揭示小说与历史之间互补倚存的关系,论证小说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尚带有一定迂回性的话,劝戒导情说则将诗文为之崇高的教化功能径直搬来,据为己有,从而心安理得地跻身于文学坛坫。这种“僭越式”行为,正是传统文化结构发生变化的重要迹象。晚明士林中,激荡着崇尚自身灵知的人文精神,除性灵之外,一切思想规范与艺术法度都为时人所鄙夷。同时,在宋代之后即已出现的文化下移总趋势的影响下,士大夫所拥有的雅文学形式——诗、文,在新的文化构成中无力独霸文坛。小说、戏曲等后起成员便乘虚而入,占据了诗文固守不住的地盘,堂而皇之地担负起教化的责任。由稗史小道骤然升迁,小说得到了它梦寐以求的地位,因而便不遗余力地炫耀自身劝戒导情的功能,企求通过这种毫不逊色于诗文的功能显示,巩固其由“庶出”变而为“嫡出”的新贵地位。晚明小说家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中对小说的教化作用有着由衷的赞叹,以为小说可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如是之捷且深矣。”动人观感,起人鉴戒,劝善惩恶,当小说成为新兴文化结构中的重要成员时,它必须同时承担与身份相符合的职责。对道德主题、劝戒导情功能的认同,无疑使小说的存在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小说对诗文之崇高的僭越还表现为它对发愤著书说的移植。发愤著书说是我国文学发生理论的最基本命题。它把文学家的审美创造过程看作是一种忧郁愤懑情绪的宣泄。这种忧郁愤懑情绪的形成,根源于社会与个体、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种种不和谐。宣泄的欲望支配作家产生进行审美创造的冲动,并把个人的忧思孤愤灌注在作品之中。创作者通过这种宣泄达到心灵的平衡与精神的自足,完成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评判与参与。发愤著书说引导人们以审美创造的方式消解怨愤、寄托理想、干预现实,符合传统文化关心社会、和谐人生的基调,因而为历代文人墨客乐道不疲。《论语》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注:《论语·述而》)之说,屈原有“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注《九章·惜诵》)的诗句,司马迁有“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注:《汉书·司马迁传》)之至论,韩愈有“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注:《韩愈集·荆潭唱和诗序》)之名言。但诸人感时发愤之说,皆指诗文著述而言,明清人则把感时发愤之说引入小说理论之中。李贽评《水浒》,以为此传为“发愤之所作”。施、罗二公愤“宋室不竟,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注:《忠义水浒传叙》),故有此作。自李贽以发愤说解读《水浒》, 从书中发见作者之政治感慨与思想寄托之后,“发愤”、“寄托”之说,则常见于小说家笔端。蒲松龄之《聊斋自志》云:“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曹雪芹自述《红楼梦》的写作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蒲、曹均以别有寄托自命,显示出两位小说大家于“补史”、“劝戒”之外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更注重小说作品中展示创作主体对社会生活的感受力、审视力和主观感情。它不再是以游戏笔墨去讲述街谈巷语,也不满足于以旁观说话人的口吻去讲述市井间曲折离奇的故事,而是以饱蘸情感之笔,描摹社会人生,寄寓幽情孤愤。
小说是文学家族中的后起之秀,它的成熟晚于诗歌、散文。明清人似乎在一个早上突然发现历来遭人鄙夷的小说具有如此广阔的重要的社会功能,因而对它推崇备至。小说功能的全面展现是以明清文化结构的变动为依托的,它的崛起促使文化门类内部重新调整诸成员的职责范围。小说以其虚构性叙事的边缘优势分别向与其邻近的文化成员如历史、诗歌、散文的领域内渗透、蚕食,分享或占据它们无法固守的阵地。明清人对小说功能的发现和重新阐释,很大程度上是对历史诗歌、散文功能的攫取和横向移植。新的社会变动及文化结构赋予小说前所未有的功能内涵,而小说在接受这些功能内涵的同时,也在积极地改善自身的社会形象,扩大表现领域,寻求名实相符的存在价值。小说由此步入自身发展的黄金时期。
小说的功能机制与存在价值的全面发现,是明清文学演进的重要成果。这一成果既然是由特定历史时期内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结构所共同赋予的,因而,只要这种生产方式与文化结构没有重大改变,小说的功能机制与存在的价值便会成为一种固定的权威性的符码而为社会所普遍接受。明清时期,演史、神魔、市井、人情小说潮流几经更迭,但补史、劝戒、发愤诸说,却始终是作家与评论家取材命意、抉隐发微的归宿。
19世纪小说是明清小说发展的尾声。当小说家眉飞色舞、津津乐道地讲述着一个个起因结局各不相同的侠与妓故事的时候,他们无不对补史、戏戒、发愤说再三致意,淋漓发挥。小说评论者也总是在有益于世道人心,别寓有寄托怀抱处属意立论。作家与评论家对小说创作宗旨的正面阐发,多集中于小说的序跋之中。小说序跋是我们窥视与了解19世纪小说价值观念和小说家文化角色认同的绝好窗口。
19世纪侠妓小说,多为文人创作。明清小说所显示的实绩和层层文化风潮激荡的结果,使小说家一改自轻自贱、以小道自处的畏缩心理,不断扩大补史说的成果,动辄将小说与经传子史相提并论,比较其优劣。古月先人为初刻本《荡寇志》作序云:“自来经传子史,凡立言以垂诸简编者,无不寓意于其间,稗官野史,亦犹是耳。”(注:《荡寇志·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此语强调稗官野史立言寓意与经传子史者同。俞灥序重刻本《荡寇志》云:“古今来史乘所载,事多失实。忠孝所存,有不能径行直达者,而姑以杳渺之谈出之,固不仅《荡寇志》也。”(注:《荡寇志·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史失于实而忠孝存在于杳渺之谈,稗史则庶几胜于正史矣。半月老人论《荡寇志》有功于世道人心道: “昔子舆氏当战国时, 息邪说,讵詖行,放淫辞,韩文公以为功不在禹下。而吾谓《荡寇志》一书,其功亦差堪仿佛矣。 ”(注:《荡寇志·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将小说之功直比于禹、孟,此种气概怎能为明、清以前之人所可以想见。
小说家气吞斗牛、直率无忌,自有其仗恃所在。小说家的仗恃首先来自于对辅翼教化文化角色的认同和对小说文体独特社会效应的自信。中国封建文化的构成,是以纲常伦理为其内在核心的。在这一内在核心之中,包蕴着对封建皇权政治与社会等级秩序永世长存的理论阐释,也包蕴着对每个社会个体行为规范与心理原则的基本要求。封建文化的各个门类在行使自身职责的同时,以各自的形式与文化核心保持着联结,并履行各自的义务。与文化核心紧疏不同的联结,形成了各个门类文化品位的差异。当小说被视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类时,它只能处于“君子弗为,然亦弗灭”的非中心与游离性地位。当小说随着明清之际文化结构的调整,成功地完成向文学中心地位的移动后,它便逐渐取得了辅翼教化的资格,取得了在社会人生系统中的重大存在意义,同时也具有了和经史子传分庭抗礼的实力。与纲常教化的亲疏,决定着小说的荣辱毁誉。因而,19世纪侠、妓小说作者无不将辅翼教化、整肃人心、有裨世道作为小说创作主旨,小说评论家则把发掘作品中所隐含的思想意蕴、破译它所具有的教化意义视为自己的本分。俞万春积数十年之力写成《荡寇志》,未及刊行而先殁。其子俞龙光作《荡寇志·识语》,明其父著书之意云:“盖先君子遗言,虽以小说稗官为游戏,而于世道人心亦大有关系,故有是作。”徐佩珂序《荡寇志》,以为此书“盖以尊王灭寇为主,而使天下后世,晓然于盗贼终无不败,忠义之不容假借混蒙,庶几尊君亲上之意,油然而生矣。”栖霞居士为《花月痕》题词曰:“说部虽小道,而必有关风化,辅翼世教,可以惩恶劝善焉,可以激浊扬清焉。”(注:《花月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邹弢作《青楼梦叙》,以为“是书标举华辞,阐扬盛俗,为渡迷之宝筏,实觉世之良箴。”(注:《青楼梦》,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观鉴我斋序《儿女英雄传》,以为当今之世,“醒世者恒堕孤禅,说理者辄归腐障。”小说于转移人心,整肃教化,自应当仁不让。“自非苦心,何能唤醒痴人;不有婆口,何以维持名教?”(注:《儿女英雄传》,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众人竞相从转移人心、维持教化的角度揭示侠、妓小说的创作宗旨,这种价值趋同现象,既表现为对小说社会政治功能的强调性认同,也隐含着小说努力保持已有文化品位的苦心。
19世纪小说家对小说文体特征充满着自信。他们认为,小说以寻常之言、不经之笔,托微辞伸庄论、假风月寓雷霆,在悦目赏心之中,劝善惩恶、激浊扬清,其作用于世道人心者,可谓得天独厚,为其他文学体裁所不可替代。观鉴我斋为《儿女英雄传》作序,以为“其书以天道为纲,以人道为纪,以性情为意旨,以儿女英雄为文章。其言天道也,不作玄谈,其言人道也,不离庸行;其写英雄也,务摹英雄本色,其写儿女也,不及儿女之私。本性为情,援情入性。有时诙词谐趣,无非借褒弹为鉴影而指点迷津;有时名理清言,何异寓唱叹于铎声而商量正学,是殆亦有所为而作与不得已于言者也。”于庸行中见人道,在诙谐中寓抑扬,借褒弹指点迷津,寓唱叹商量正学,这正是小说家作用于世道人心的独特手段。钱湘序《荡寇志》,以“不禁之禁”之说概括小说整肃人心世道之功能。其言曰:“思夫淫辞辟说,禁之未尝不严,而卒不能禁止者,盖禁之于其售者之人,而未尝禁之于其阅者之人;即使其能禁之于阅者之人,而未能禁之于阅者之人之心。”而《荡寇志》一书,寓劝戒之意于可资鉴影的故事之中,“兹则并其心而禁之,此不禁之禁,正所以严其禁耳。”以小说息淫辞辟说,戒奸盗诈伪,疏引而非堵湮,导情而非窒欲,可望收到“不禁之禁”的效果,这又是小说的擅场之处。问竹主人序《三侠五义》,以为此书“极赞忠烈之臣、侠义之士”,又能“以日用寻常之言,发挥惊天动地之事”,“昭彰不爽,报应分明,使读者有拍案称快之乐,无废书长叹之时”,也极力从体裁优势的角度称赞小说作用人心之便捷。小说“以日用寻常之言,发挥惊天动地之事”,则可做到雅俗共赏,既可供优雅君子爱好把玩,又使引车卖浆者流喜闻乐见,拥有广大的阅读群体。至于“昭彰不爽,报应分明,使读者有拍案称快之乐,无废书长叹之时”,则庶几近于寓教于乐,与中国传统的由审美而及于教化,终达于社会和谐的政治理想入丝合扣。
除去对辅翼教化文化角色的认同和对小说文体独特社会功能的自信外,19世纪小说家的良好感觉还来自于对发愤著书说的倚仗。如前所述,自明清人将发愤著书这一诗文创作中的古老命题引入小说理论中后,小说创作遂获得了从杂谈补史之初级形态中挣脱,走向更为自由的创造空间的机会。发愤著书理论把小说创作看作是由作者主观情感积极参与的创造性活动。它引导小说家以巨大的热情贴近与反映现实生活,鼓励小说家理直气壮地抒写个人对社会、人生的感触、忧愤与评价,使小说家的目光不再仅仅停留于遥远的历史,而更自觉地面对生活现实。发愤著书说扩大了小说的社会功能和表现领域,小说创作不再满足于充任游戏消闲、诙谐调侃的角色,而是企求有所作为、有所寄托;不再拘泥于据实以录、羽翼正史,而是着力寻求现实世界中足以令人回肠荡气的艺术真实;不再是街谈巷议、杂谈逸闻的辑录搜集,而是饱含着作者人生阅历与主观情感的发愤之作。从诗文理论移植而来的发愤著书说,在为小说开辟更为自由、更为广阔的表现空间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改变着小说的社会形象与文化品位。发愤著书说使得先前拘于名实之辨的文人骚客不复小觑说部,从而毅然下海,操笔着墨,抒写悲凉慷慨、抑塞磊落之气。
发愤著书说作为一种文学发生理论,其最基本点是把文学创作看作是作者怨愤之情的郁结与发泄。而作者的怨愤之情又多由现实生活、人生路途中所遭受的种种穷困阻厄所激发引起。现实与人生的穷困阻厄造就了作者莫可告语的愤慨忧思,其郁结氤氲、积蓄酝酿,一旦喷薄而出,铺泻成文,便是天地间最真实美好的情感,最感人至深的文学。在发愤著书理论中,愤慨忧思被赋予最为神圣崇高的意义,它是点燃作家创作激情的圣火,又是贯穿于作品始终的原型情感。
19世纪侠妓小说的作者与评论者,习惯于从辅翼教化的角度挖掘小说的社会意义,同时,又习惯于以发愤著书理论解读小说的思想价值。辅翼教化与发愤著书,如同他们手中的双刃之剑,批隙导窾,运用纯熟。以发愤著书理论解读小说,需要着意在作者所演述的故事中发现某种感慨与寄托,并努力品咂其所包容的深层意味和人生意义,寻绎其与作者身世阅历的微妙联系。花隐倚装序《青楼梦》,以为此书虽敷写欲河爱海之事,其骨子里都是寄寓“美人沦落、名士飘零”之感慨。“其书张皇众美,尚有知音,意特为落魄才人反观对镜,而非徒矜绮丽为也。”“览是书者,其以作感士不遇也可,倘谓为导人狭邪之书,则误矣。”栖霞居士为《花月痕》题词,以为此书令浅识者读之,不过是怜才慕色文字,其实,作者在怜才慕色的题面下,对比玩味着两种人生。《花月痕》主写韦与刘、韩与杜两对人物。韦痴珠落魄一生,“踯躅中年,苍茫歧路,几于天地之大,无所容身,山川之深,无所逃罪”,刘秋痕“以袅袅婷婷之妙伎,而有难言之志趣,难言之境遇”,韦、刘同病相怜,寂寞不遇。韩荷生、杜采秋与韦、刘同为书生妙伎,却才遇明主,飞黄腾达,享尽人间荣华富贵。遇与不遇,别如霄壤。世态炎凉如此,怎能不令人感慨系之,又怎可仅以“怜才慕色”视之。马从善以馆于作者家最久的身份序《儿女英雄传》,以为文康此书为感慨家道中落之作,“先生少席家世余荫,门第之盛,无有伦比。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时遗物,斥卖略尽。先生块处一室,笔墨之外无长物,故著此书以自遣。”“先生一生亲历乎盛衰升降之际,故于世运之变迁,人情之反复,三致意焉。先生殆悔其已往之过,而抒其未遂之志欤?……嗟乎!富贵不可常保,如先生者,可谓贵显,而乃垂白之年,重遭穷饥。读是书者,其亦当有所感也。”在诸篇序跋中,评论者循着发愤著书理论的思路,要言不繁、轻车熟路地为读者破译小说作品中隐寓的寄托感慨。发愤著书理论为文学批评者提供的是一种释原式思维。它把文学创作过程看作是某种愤慨忧思情绪的郁结发散,因而,批评者的主要任务是用画龙点睛式的语言解释、还原作品的原发性情绪。执著于人生课题,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显著特征。着意在普遍存在、无法消弥的现实与理想、个体与社会诸种冲突、抵牾中寻求植被地带,这是发愤说作为一种文学发生理论源远流长,并由诗文而推及小说的奥妙所在。伤时悯世的忧患,人生际遇的失意,精神的痛苦,心灵的疮痍,永远是构成人类情感生活的重要内容。将作品归属于人生多艰、感士不遇等大而无当、无所不适的类型化主题,以边缘模糊的语言触角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和联想认同,使之在阅读中获得会心释然的快感,这是虽已套式化的释原式批评长期存在流行的重要原因。
当我们回顾明清小说演进历史,对照分析19世纪小说价值观念构成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明清时期文化结构的板块式移动,小说的非中心游离性地位得到改善,其功能机制和存在意义也日益得到丰富和全面展示。19世纪处在明清文化结构变动的余波之中,在摆脱了自惭形秽的卑怯心理,勇于将小说与经史贤传相提并论之后,小说家逐渐将小说文体的文化功能由补史而移重于辅翼教化与发愤著书,旨在扩大小说在社会、人生系统中的存在意义,巩固其社会地位,并期望在诗文词赋中已趋暗淡的理论之光,能在小说文体中重放异彩。但奇迹终于未能出现,19世纪小说并没有能够为中国古典小说作出一个辉煌的结束,侠、妓小说的盛行便是这个时代所收获的一颗酸涩的畸果。
二 侠妓演述的主题模式
侠与妓,是江湖间与风尘中的人物。他们浪迹天涯、漂萍人间,有着不同于常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也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欢乐痛苦和人生感受。侠与妓的生活,构成了独特而神秘的社会风景。侠与妓并非高蹈世外不食人间烟火者,相反,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与尘世保持着割舍不断、千丝万缕的联系。特殊的生活阅历,使他们有比普通人更丰富的侠骨柔肠,有比普通人更耐咀嚼的人生故事。讲述侠与妓故事的作品源远流长,自汉人之《游侠列传》,至明人之《水浒传》,自唐人之《教坊记》,至明人之《杜十娘》,写侠写妓者,精品不断,异彩纷呈,构成了一条五光十色的艺术长廊。
历代作家之所以对侠、妓题材情有所钟,侠、妓故事的演述之所以绵延不绝,其原因是多重的。人类生活的组成以人性作为底蕴。对恶的憎恨,对善的赞美,对美的追求,对英雄之性的崇拜,对儿女之情的迷恋,构成了人类最基本的人性原则和情感指向。侠、妓故事写英雄之争天抗俗,儿女之柔情似水,展示人性中阳刚与阴柔之美的两种极致:写恶者终得恶报,善者终得善果,让人性在善恶美丑的巨大张力中磨砺洗刷,从而启迪人们对人性真谛的领悟。侠、妓故事痛快淋漓地展示人类最基本的人性原则和情感指向,这是原因之一。人类生活是一种社会性活动,其自身充满着对社会公正和人性自由发展的渴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社会公正原则遭到君权原则的压抑,礼教规范束缚着人性的自然发展,人们便把对社会公正和人性自由的期待转移到文学世界,转移到侠妓故事的演述中,在侠之以武犯禁的行为中,寻求正义公平,在妓之青楼歌榭的温柔里,寄托浪漫风流。侠妓故事的演述,有着深广的社会心理基础,这是原因之二。侠妓生活既与世俗社会保持着广泛联结,又具有自身活动的隐秘性。与社会广泛联结,便有许多可以讲述的人间故事,为作家展示特定时代的生活场景、风俗人情,表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活动,提供了莫大的便利。侠妓活动的隐秘性,又给故事本身凭空带来了许多诡秘和传奇色彩,作者可以在较大的自由度上制幻设奇,纵横捭阖,提高作品的可读性与愉悦效应。侠妓故事具有天然而无与伦比的文学禀赋,这是原因之三。
上述仅为侠、妓故事演述常盛不衰的一般性原因。19世纪,继《聊斋》之志怪、《儒林》之讽世、《红楼》之言情之后,侠妓题材骤然成为小说的表现热点,形成了一种长篇纷呈、言侠言妓者双峰对峙、几乎主持说苑的声势。这种“稗官争说侠与妓”现象的形成,又有其特殊的时代与文化成因。
19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在经久不息的动荡中已走向崩溃的边缘。道咸以降,内乱不已,外侮频加,战争风云笼罩海内。封建政权失去往日的威严与灵光,现有的思想信仰堤坝纷纷坍陷,政治文化秩序陷入混乱,整个社会像失去重心的陀螺摇摆不定。面对纷乱的现实,人们的心理上充满着对命运、对未来的恐惧、焦虑、忧患和莫名的失落感。忧道者追忆着逝去的帝国盛世、文治武功,沉湎于补天救世的梦幻,期待着封建秩序的恢复、纲常伦理的重整,渴望仗剑戡乱、澄清乾坤、再振雄威的英雄出现。狂狷者恃才傲世,世遭奇变,更觉英雄末路,既不能为世所用,遂以声色犬马消磨心志,在粉黛裙裾中寻求红粉知己,寄托不遇牢愁。嬉世者游戏人生,值此更以及时行乐苟且偷安为生命宗旨,在游花采美、情场角逐中寻求快慰。世纪之变,影响着一代士人的心理结构、人生情趣,对世纪英雄的幻想和颓废感伤的士人心态,为侠、妓热题的流行创造了适宜的文化氛围。
就小说自身演进的历史而言,明清两代说侠之书,自《水浒》之后,继踵者寥如晨星,康乾年间成书的《说岳全传》问世不久,便遭查禁,此与清代禁忌繁多的文化政策不无关系。侠之以武犯禁与官方统治多有抵触,故命运不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言情之作,则高潮迭起。明末之市井小说,清初之才子佳人小说,清中叶之《红楼梦》及其续书,生活场景由市井而转至家庭,情调由艳冶而渐至优雅。19世纪的文网松弛,行侠者先出现于公案小说中,助官破案,缉盗戡乱。世人对于侠义久别重逢,分外亲切,故而趋之如鹜。言情之作徜徉于后花园与簪缨之家既久,读者口餍耳倦而作者亦意拙技穷。道咸年间,继京都狎优之风盛极之后,海上洋场间粉薮脂林,不胜枚举,狎妓成为时下士林风尚。言情之作把生活场景由后花园转向青楼妓院,主人公由官宦子弟、名门淑媛改换为冶游文人与卖笑倡优,只是举手之劳,侠、妓热题的形成又是小说家适应读者审美时尚的有意选择。
侠妓故事讲述江湖英雄行侠仗义、勾栏妓院男女相悦之事,这是一个司空见惯而永远富有阅读效应的题材。但19世纪小说家面对侠、妓题材,并不感到十分轻松,他们的心理压力来自于题材之外。如何在侠妓故事的演述中,落实劝戒、泄愤的小说主旨,通过故事讲述、人物活动传达作者的政治观念、文化意识,起到整肃人心、泄导人情的作用?如何使侠、妓行为的描写,限制在适宜的“度”内,使之契合于社会认可的思想与道德规范,达到社会效应与题材效应的一致?这些问题,都被小说家有意识地统一消融在主题模式的设计中。主题设计,这是小说家进入创作过程所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作家思想意念渗透故事讲述之中的第一通道。在说侠之作中,作者将侠义天马行空的活动编织在公案故事的经纬中,把传统侠义题材中的侠、官对立模式,转换为侠、官协力,同扶圣主、共戡盗乱的主题模式。侠以武犯禁一变而为侠以武纠禁。在说妓之作中,作者或重写实,敷陈京都海上巨绅名士之艳迹,或重写意,借美人知遇抒写英雄末路之牢愁。无论敷陈艳迹之主题模式,还是抒写牢愁之主题模式,无不在描绘柔情中推重风雅,渲染用情守礼而鄙夷猥亵放荡,总体奉行着情清欲浊、重情斥欲的价值标准。
19世纪写侠之长篇小说主要有《荡寇志》、《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荡寇志》又名《结水浒全传》。作者俞万春出身诸生,曾随父从征瑶民之乱,以功获议叙。俞氏以二十余年之力,写成《荡寇志》一书,书之序言及结子部分言其著书之意甚明。俞氏认为,施耐庵著《水浒传》,并不以宋江为忠义,施氏“一路笔意,无一字不写宋江之奸恶。”而罗贯中之续书竟有宋江被招安平叛乱之事,将宋江写成真忠真义,使后世做强盗者援为口实,以忠义之名,行祸国之实。罗之续书刊刻行世,坏人心术,贻害无穷。《荡寇志》一书,即要破罗续书之伪言,申明“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的话,只有被张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话”,以使“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辨,丝毫不容假借。”俞书自《水浒传》金圣叹七十回删改本卢俊义之噩梦续起,至梁山泊英雄非死即诛,忠义堂被官军捣毁,山寨为官军填平,一百零八股妖气重归地窟,张叔夜、陈希真终成平乱大功,封官加爵处止。
《荡寇志》一书把宋江等人写成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戕官拒捕、攻城陷邑、占山为王的贼寇,他们与朝中奸臣高俅、蔡京、童贯暗中勾结,沆瀣一气。方腊起事浙江之时,朝中曾有招安宋江、借力平乱之议,蔡京极力撺掇促成此事。但宋江贼心难收,为安定梁山人心,羁縻众将,表面欢天喜地应允,暗中却差人杀了使者,自绝了梁山受招安之路。与梁山盗贼对阵的是已告休的南营提辖陈希真、陈丽卿等人。陈氏父女武艺出众、才略超人,因逃避高俅父子迫害出走京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遂与姨亲刘广奔猿臂寨落草,权作绿林豪杰,并收拢祝永清等一批骁将,与梁山作对。他们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时时念叨皇恩浩荡,一心以助官剿匪的行为,“得胜梁山,作赎罪之计。”猿臂寨与梁山多次对阵交锋,使梁山人马损兵折将。最后在朝廷委派大员张叔夜的统领下,一举平灭梁山。
《荡寇志》在故事结构上以叙写陈氏父女活动及猿臂寨建兴为主线。《水浒传》中的官盗、忠奸矛盾在书中虽依然可见,但已退居于事件背景的交待之中。作为绿林好汉对立面的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则杳然无迹。《荡寇志》一书主要展示的是两大江湖集团的争斗厮杀及其不同的命运归宿。猿臂寨首领陈氏父女因受奸佞迫害而走上绿林,这与宋江等人走上梁山并无不同。所不同的是,陈氏父女落草之后,辄以逆天害道之罪民自责,外惭恶声,内疚神明,时时不忘皇恩浩荡,日夜伺机助官剿寇,立功赎罪,将有朝一日接受招安,作为解脱之道;宋江等人则啸聚山野,假替天行道之名,攻城陷邑,对抗官府,桀骜不驯,于招安之事缺乏诚心。陈氏父女深明天理,以有罪之身,助王剿乱,终为朝廷所用,功成名就;宋江等人一意孤行,背忠弃义,倒行逆施,终至人神共怒,身败名裂。陈氏父女报效朝廷,真得忠义之道;宋江等人恃武犯禁,已入盗寇之流。作者正是在一侠一盗、一荣一衰的命运对比中,夸耀皇权无极,法网恢恢,晓告世人,忠义之不容假借混蒙,盗贼之终无不败。尊君亲上,招安受降,是绿林侠义、江湖英雄最好、最理想的归宿。
如果说《荡寇志》一书的思想主旨是尊王灭寇,那么,《三侠五义》的思想主旨则是致君泽民。《三侠五义》又名《忠烈侠义传》,它在民间说唱艺术的基础上,经文人增饰而成。《三侠五义》是一部较为典型的以清官断案为经,以仗义行侠为纬的公案侠义小说。它带有更多的市井细民对清官与侠义行为的理解和愿望。作品前二十七回讲述清官包拯降生出仕,决狱断案,审乌盆、斩庞昱、为李太后伸冤寻子的故事。自南侠展昭得包拯举荐、被封御猫事件之后,引出三侠五义的纷纷登场,他们由互相猜忌,敌视争斗,终至联袂结盟,各奋神勇,各显绝艺,辅助清官名臣除暴安良,为国为民献忠效力。
《三侠五义》是以忠奸、善恶、正邪作为故事基本冲突的。小说展示了上自宫廷皇室、下至穷乡僻壤间的种种社会矛盾。贪官污吏结党营私、诬陷忠良,铸就冤狱;土豪恶霸荼毒百姓,鱼肉乡里;皇亲国戚广结党羽,图谋不轨。这些奸邪丑恶的存在,为清官、侠士提供了用武之地。他们相互辅助,洞幽烛微,剪恶除奸,济困扶危,仗义行侠,为民除害,清官与侠义代表着社会公正与正义。作者致君泽民的思想主旨,也正是在清官与侠士的行为中体现出来的。在作品中,包拯、颜查散等清官名臣,展昭、欧阳春等义士侠客,充当着君主意志与民众愿望的中介。君主的意志通过清官名臣的作为而得能显现,清官名臣的作为依靠侠客义士的辅助而获得成功,侠客义士除暴安良的行为,又体现着民众社会公正的愿望。清官名臣、侠客义士,上尽效于朝廷,下施义于百姓,使民众愿望与君主意志、社会公正原则与君权原则获得和谐统一,这正是作者所期望的致君泽民的思想与行为规范。
《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义士系有产者居多。在归附朝廷之前,大都有过飘零江湖、行侠仗义,甚至以武犯禁的行为。他们归附朝廷并非是屈服于政府的武力,而大多是出于为国效力的愿望、对清官名臣高风亮节的折服及对皇上知遇之恩的报答,他们的归附被视为一种义举。当他们接受清官的统领之后,其除暴安良的行为便不再仅仅具有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的性质,而是一种代表政府意志的活动。侠义之士一旦与江湖隔绝、与个人英雄行为分离,江湖上少了一位天马行空的英雄,而官府中则多了一名抓差办案的吏卒。这也是侠义何以与公案小说合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侠五义》显示出侠义与公案小说的合流,《儿女英雄传》则试图将侠义与言情故事同说。《儿女英雄传》初名《金玉缘》,作者文康在《首回缘起》中借天尊之口揭明此书立意云:世人大半把儿女英雄看作两种人,两桩事,殊不知英雄儿女之情,纯是一团天理人情,不可分割。“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做得出英雄事业。”又谓世人看英雄儿女,误把些使用气力、好勇斗狠的认作英雄,又把些调脂弄粉、断袖余桃的认作英雄,殊不知英雄儿女真性在忠孝节义四字。立志做忠臣、孝子,便是英雄心;做忠臣而爱君,做孝子而爱亲,便是儿女心。由君亲而推及兄弟、夫妇、朋友,英雄儿女至性便昭然人世、长存天地。作者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铺缀文字,“作一场英雄儿女的公案,成一篇人情天理的文章,点缀太平盛世。”
《儿女英雄传》以书生安骥与侠女何玉凤(十三妹)的弓砚之缘作为故事主线。汉军世族旧家子弟安骥携银往淮南救父,路遇强人,为十三妹所救。十三妹本中军副将何杞之女,其父为大将军纪献唐所陷害,玉凤携母避祸青龙山,习武行侠,伺机复仇。十三妹在能仁寺救出安骥之后,当下为安骥与同时救出的村女金凤联姻,并解送威震遐迩的弹弓,让他们一路作讨关护身的凭证,十三妹自己拾得安骥慌乱中丢下的砚台。安骥之父安东海获救后,弃官访寻十三妹于青云峰,告知她父冤已伸,以砚弓之缘为由,极力撮合十三妹与安骥的婚姻。玉凤嫁安骥后,与张金凤情同姐妹,又善于理家敛财,鼓励丈夫读书上进。安骥科场得意,官至二品,政声载道,位极人臣。金、玉姐妹各生一子,安老夫妻寿登期颐,子贵孙荣。
《儿女英雄传》为侠客义士、绿林英雄安排了一条与陈希真父女、南侠、五鼠不同的归顺道路——走向家庭生活。十三妹身为将门之女,自幼弯弓击剑,拓弛不羁。家难之后,凭一把倭刀、一张弹弓啸傲江湖,驰名绿林,血溅能仁寺,义救邓九公,行侠仗义,抱打不平,是何等的豪放威武。但这些在饱读诗书的安学海看来,却是璞玉未凿,“把那一团至性,一副才气弄成一团雄心侠气,甚至睚眦必报,黑白必分。这等人若不得个贤父兄、良师友苦口婆心地成全他,唤醒他,可惜那至性奇才,终归名堕身败。”(注:《儿女英雄传》,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故而决心尽父辈之义,披肝沥胆,向十三妹讲述英雄儿女的道理。十三妹听了安学海的劝解,“登时把一段刚肠,化作柔肠,一股侠气,融为和气”,决意“立地回头,变作两个人,守着那闺门女子的道理才是。”(注:《儿女英雄传》,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向打家劫舍、掠抢客商、称雄绿林的海马周三等人,也听从教诲,学十三妹的样子,决心跳出绿林,回心向善,卖刀买犊,自食其力,孝老伺亲。走向家庭生活的侠女十三妹,将倭刀弹弓尽行收藏,英雄身手只在窃贼入房、看家护院时偶尔显露。
在上述三部写侠小说中,侠义之士或接受招安,或报效朝廷,或步入家庭,无一不走着一条通向自身异化的命运之路。他们由啸聚江湖、逸气傲骨变而为循规蹈矩、世故世俗,由替天行道、仗义行侠变而为为王前驱、以武纠禁,由现行政治法律、伦理纲常的挑战者和反叛者变而为执行者、维护者,这种以表现江湖侠士收心敛性、改邪归正行为为主旨的作品,我们不妨称之为“归顺皈依”主题。这种主题模式的形成,带有晚近期封建皇权政治文化的特征,它建立在一套以忠君观念为核心的价值理论体系之上。根据这种价值理论体系,作者极力寻求绿林英雄与皇权政治妥协调和的方式,而又总是以侠义之士向皇权政治的归顺皈依作为最终结局。作者正是在这种归顺皈依的主题模式下,寄寓着劝戒的意蕴和重整纲常伦理、社会秩序的渴望。
19世纪言妓小说有写实、写意之分。写实者,敷陈京都海上巨绅名士之艳迹,重在描绘繁华乡里、风月场中的闻闻见见,此类作品有《品花宝鉴》、《海上花列传》。写意者,借美人知遇抒写英雄末路之牢愁,重在赏玩潦倒名士、失意文人之落拓不羁、雅致风流,此类作品有《青楼梦》、《花月痕》。
乾、嘉以降,京都狎优之风甚盛。公卿名士招梨园中伶人陪酒唱曲、狎爱游乐,成为一时风尚。虽所招均为男子,与之调笑戏谑,却以妓视之,呼之为“相公”。流风所被,以至“执役无俊仆,皆以为不韵,侑酒无歌童,便为不欢。”(注:柴桑:《京师偶记》)《品花宝鉴》所记述的即京都狎优韵事。作者陈森,道光中寓居都中,因科场失意,境穷志悲,日排遣于歌楼舞榭间,于狎优之风,耳闻目睹,遂挥毫以说部为公卿名士、俊优佳人立传写照,道人之所未道而兼寓品评雌黄之意。
作者认为:“大抵自古及今,用情于欢乐场中的人,均不外乎邪正两途。”(注:《品花宝鉴》第一、五、二十三回)本书之立意,即要写出正者之高洁和邪者之卑污,以作为品花者鉴影之具。故而书中开首第一回,先将缙绅子弟、梨园名旦各分为十类,推之为欢乐场中之正品,又将卑污之狎客、下流之相公分为八种,斥之为欢乐场中的邪类。书中用主要笔墨描写十位“用情守礼”的缙绅子弟与十位“洁身自好”优伶的交往。十位优伶来自于京都联珠与联锦两大戏班,他们聪慧清秀、仪态婉娴,在红氍毹上各有绝技。虽生于贫贱、长于污卑,却自尊自爱、择良友而交结,出污泥而不染。十位缙绅子弟家资丰饶,地位显赫,才华横溢,风流倜傥,他们视“这些好相公与那奇珍异宝、好鸟名花一样,只有爱惜之心,却无亵狎之念。”(注:《品花宝鉴》第一、五、二十三回)其中波折横生,作者极尽曲意的是对梅子玉与杜琴言、田春航与苏蕙芳交往故事的描述。梅、杜之交,形淡情浓、悲多欢少,而重写其缠绵相思之苦;田、苏之交,炽热率直、知己相报,而重写其道义相扶之乐。最终众名士功名各自有得,众优伶脱离戏班,跳出孽海,会聚于九香楼中,将那些舞衫歌扇、翠羽金钿焚烧尽净,皆大欢喜。在描述美人名士好色不淫的交往之外,书中还穿插讲述了奚十一等无耻狎客与蓉官、二喜等“狐媚迎人,娥眉善妒,视钱财为性命,以衣服作交情”的下流优伶的荒淫行径,作为美人名士的对照。作者以为:“单说那不淫的,不说几个极淫的,就非五色成文,八文合律了。”(注:《品花宝鉴》第一、五、二十三回)
《品花宝鉴》对京城品优之风的描述抱着一种猎奇写实、激浊扬清的基本态度,正因为如此,作者在书中序言里一再声称书中所言“皆海市蜃楼,羌无故实”。“至于为公卿,为名士,为俊优、佳人、才婢、狂夫、俗子,则如干宝之《搜神》,任昉之《述异》,渺茫而已。”但不少好事者还能一一寻出书中某人即世人某人的蛛丝马迹。
《海上花列传》问世晚于《品花宝鉴》近半个世纪,但其刊行后的遭遇几同于《品花宝鉴》。《海上花列传》最初连载于《海上奇书》杂志时,作者即在《例言》中声明:“所载人名实俱凭空捏造,并无所指。如有强作解人,妄言某人隐某人,某事隐某事,此则不善读书,不足与谈者。”但读者与研究者仍饶有趣味地索解书中的本身。《潭嬴室笔记》云:“书中人名皆有所指,熟于同、光间上海名流事实者,类能言之。”许廑父为民国十一年《海上花列传》排印本作序,谓此书为作者谤友之作。诸说无须稽考,但作者之罗列众相,点缀渲染的本领,却通过索求本事者积极踊跃这一现象反映出来。
《海上花列传》开篇第一回言写作缘起云:“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盛,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虽有父兄,禁之不可,虽有师友,谏之不从。此岂其冥顽不灵哉?独不得一过来人为之现身说法耳。”作者即是以“过来人”的身份,写照传神,属辞此事,点缀渲染,以见青楼花巷令人欲呕之内幕,繁华场中反复无常之情变,“苟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它年之毒于蛇蝎。也算得是欲觉晨钟,发人深省者矣。”
与《品花宝鉴》中的狎优场面相比,海上烟花生活充满着更多的铜臭气味。《海上花列传》的作者似乎已失去了《品花宝鉴》作者那种欣赏名士作派、玩味品花情韵的雅兴,更多的是以平实冷静而不动声色的笔调描述欢乐场中的艰辛悲苦。书中首回写花也怜侬在花海上踯躅留连,不忍舍去,那花海“只有无数花朵,连枝带叶,浮在海面上,又平匀,又绵软,浑如绣茵绵罽一般,竟把海水都盖住了。”正因为如此假相,畅游花海者才容易失足落水:“那花虽然枝叶扶疏,却都是没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被海水冲激起来,那花也只得随波逐流,听其所止。若不是遇着了蝶浪蜂狂,莺欺燕妒,就为蚱蜢、蜣螂、虾蟆、蝼蚁之属,一味的披猖折辱,狼藉蹂躏。惟夭如桃,秾如李,富贵如牡丹,犹能砥柱中流,为群芳吐气;至于菊之秀逸,梅之孤高,兰之空山自芳,莲之出水不染,哪里禁得起一些委屈,早已沉沦汩没于其间。”花海之绵软其表,险恶暗藏,花朵之随波逐流,命运不能自主,花海、花朵的暗喻表达着作者对海上烟花生涯的理解。
《海上花列传》以赵朴斋由乡下到上海访亲、初涉妓寮起,至其妹赵二宝被史三公子骗婚而惊梦处止,以赵家兄妹的命运照应故事首尾。而中间叙事写人,则采用史书中列传体例与《儒林外史》的规制,加上所谓穿插藏闪之法,描述了三十余位妓女和奔走于柳街花巷中的嫖客、老鸨各色人等之间的恩怨纠葛、风波结局。其中反目成仇、背信弃义者有之,附庸风雅、迂阔痴情者有之,始合终离、始离终合、不离不合者有之,寒酸苦命、淫贱下流、衣锦荣归者也各有之。在这个以叫局吃酒、打情骂俏、争风吃醋、勾心斗角为主要生活内容的社会层面里,充满着人世间的喧嚣波澜。
《海上花列传》曾以《青楼宝鉴》之名刊印。它和《品花宝鉴》之所以同称为《宝鉴》,即含有还其真面、引为法戒的两重含意。两书作者在故事叙述中都以“过来人”的口气现身说法,他们对特定生活场景的描述,遵照“道人之所未道”、“写照传神”、“其形容尽致处,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写实宗旨,以接近现实真实的努力,向读者讲述京都海上欢乐场中的怪怪奇奇、妍媸邪正,为狭邪中人物立传写照。这种以展示狭邪生活场景、描摹梨园青楼世态人情、寄寓警世劝戒之意为主旨的作品,我们称之为言妓之作中的“敷陈艳迹”模式。
言妓之作“敷陈艳迹”模式之外的另一支流是“人生感悟”模式。如果说,敷陈艳迹之写实派承《儒林外史》之笔意,旨在罗列众相、为狭邪者立传、为风月场写照的话,人生感悟之写意派则以发愤说为底蕴,借青楼风月之演述,玩味人生悲欢离合、荣辱穷达之禅机,抒写人生牢愁与感慨。《花月痕》、《青楼梦》的写作之旨,近于后一类型。
《花月痕》为何而作?作者魏秀仁于本书《后序》中云:“余固为痕而言之也,非为花月而言之也。”花之春华秋实,月之阴晴圆缺,其形人人得而见之,而花月之痕,则非人人都能体味。花之有落,月之有缺,人若有不欲落、不欲缺之心,花月之痕遂长在矣。花月之痕,得人之怜花爱月之情而存在,“无情者,虽花妍月满,不殊寂寞之场,有情者,即月缺花残,仍是团圆世界。”人海因缘之离合,浮生踪迹之悲欢,与花月何异?有情者,其合也,诚浃洽无间,其离也,虽离而犹合。此一段庄言宏论,正是作者铺缀文字立意所在。
《花月痕》开首即为一篇“情论”。“情之所钟,端在我辈”,“乾坤清气间留一二情种,上既不能策名于朝,下又不获食力于家,徒抱一往情深之致,奔走天涯。”不遇之士情深不能自抑,无处排遣,故向窗明几净、酒阑灯灺处寻求适情之物与多情之人,借诗文词赋、歌舞楼榭寄情耗奇。“那一班放荡不羁之士,渠起先何曾不自检束,读书想为传人,做官想为官宦,奈心方不圆,肠直不曲,眼高不低,坐此文章不中有司绳尺,言语直触当事逆鳞,又耕无百亩之田,隐无一椽之宅,俯仰求人,浮沈终老,横遭白眼,坐团青毡。不想寻常歌伎中,转有窥其风格倾慕之者,怜其沦落系恋之者,一夕之盟,终身不改。”仕途官场不遇之人,得遇于寻常歌伎;欲为传人名宦不成,而倦归于温柔之乡。《花月痕》开首之“情论”,点明所言之“情”的特殊规定性,又俨然是一篇不羁名士与青楼佳丽天作地合的辩词。
“一夕之盟,终身不改”,作者将名士美人青楼之遇的情感关系推向了一种理想化的极致。“幸而为比翼之鹣,诏于朝,荣于室,盘根错节,脍炙人口;不幸而为分飞之燕,受谗谤,遭挫折,生离死别,咫尺天涯,赍恨千秋,黄泉相见。”(注:《花月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作者正是根据幸与不幸的命运、荣辱与共的情盟来安排情节、设置人物的。《花月痕》主要讲述“海内二龙”韩荷生、韦痴珠与“并州二凤”杜采秋、刘秋痕悲欢离合的故事。韩、韦以文名噪世,以文字相识,同游并州,得识青楼佳丽杜、刘。韩有经世之略,得人推荐,于并州兵营赞襄军务,平回之役中屡建奇勋。后应诏南下,收复金陵,官至封侯,与所恋佳妓杜采秋终成眷属,采秋被封为一品夫人。韦痴珠著作等身,文采风流,倾倒一时,所上《平倭十策》,虽不见用,却享名海内。倏忽中年,困顿羁旅,内窘于赡家无术,外穷于售世不宜,心意渐灰。与并州花选之首刘秋痕情意相投,却无资为其赎身,终至心力交瘁,咯血而死,秋痕自缢以殉。韩、杜与韦、刘,同是情盟似海,结局却是天壤之别。韩、杜之交,是“幸而为比翼之鹣”者,韦、刘之交,则是“不幸而为分飞之燕”者。作者以歆羡之笔写“比翼之鹣”,而以凄惋之笔写“分飞之燕”。幸与不幸的根结何在?韩荷生得遇而位极人臣,故福慧双修、恩宠并至;韦痴珠不遇而穷愁困顿,虽眷爱而不能相保。遇与不遇,是达与不达、幸与不幸的根本。痴珠华严庵求签,知与秋痕终是散局,但蕴空法师告知,数虽前定,人定却也胜天,而痴珠终因不遇而无力赎回秋痕;荷生欲娶采秋,鸨母初亦为难,后闻荷生做了钦差,追悔不及,亲将采秋送迎,韩、杜终得如愿以偿。作者在《花月痕前序》中写道:“浸假化痴珠为荷生,而有经略之赠金,中朝之保荐,气势赫奕,则秋痕未尝不可合。浸假化荷生为痴珠,而无柳巷之金屋,雁门关之驰骋,则采秋未尝不可离。”虽然离合之局,系于穷达,荣辱之根,植于遇而不遇,但若情之长存,离者亦合,辱者犹荣。作者对人生命运、情爱价值的理解于此可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