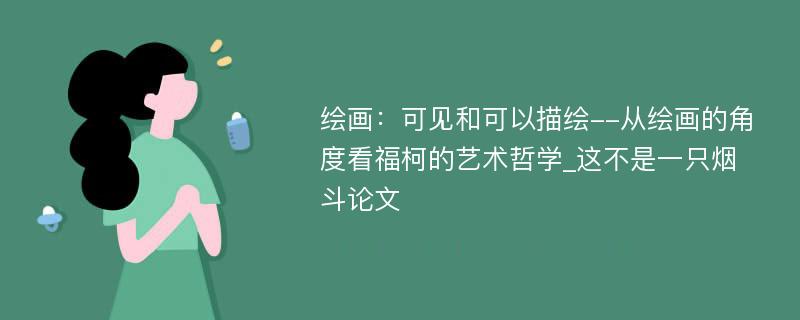
绘画:可见与可述——从绘画看福柯的艺术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艺术论文,看福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曾在给友人埃米尔·波尔纳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欠着你绘画的真理,我就将告诉你。但塞尚并没有明说——也许他认为,光线、色彩才是绘画真正的语言和真理之所在。因为“自然”才是他终生的迷恋,塞尚要让它们自己说话。但这种“自然”或“真理”是什么?绘画中有没有真理?这是一个问题。无数艺术家、哲人都曾试图揭开其面纱,渴望抵达其神秘的本真。海德格尔自然如此:在著名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中,他用极具诗意的语言,揭示了梵高(Van Gogh)那双农鞋中的真理——大地的召唤。在他看来,“真理的本质上就具有此在式的存在方式,一切真理都同此在的存在相关联”(《存在与时间》261)。艺术的本质就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海德格尔,《林中路》21);而艺术作品就是存在之真理的“澄明”或“除蔽”。福柯则认为,“‘真理’是作为一整套有关话语的生产、规律、分布、流通和操作的有规则的程序而被理解的”(The Foucault Reader 74)。显然,福柯的“真理”是不同于海德格尔的。它是一种操作性、实践性的,它与话语操作相关。至于绘画,福柯说:“绘画不是一种应该记录在空间的物质性中的纯粹的视觉形象,也不是一个需要我们用后来的解释阐述其无声的和无比空洞的意义的赤裸的动作。绘画——独立于科学知识和哲学主题——贯穿着知识的实证性”(《知识考古学》217)。在福柯看来,绘画其实就是一种话语实践。那么,它必然关涉真理;也必然要成为哲学和思想关注的话题。于是乎,福柯对绘画中真理的寻求,也许就是一种“话语”(或“非话语”)的真理寻觅。或许,福柯的话语真理连通着他对外部世界认知的考证和想象。
对于绘画或者艺术而言,虽不必用“真理”彰显其意义;但我们还是渴望发现其秘密。福柯对于绘画的描述和探讨,未见得就是正确和不可替代的;但他的述说却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逼近了绘画的“真理”或“秘密”。福柯集中论述绘画的文字主要在三篇作品中:第一篇是对《宫娥》的细腻、神秘而繁复的评述(1966);第二篇是对马格利特《这不是一只烟斗》的分析(见其同名文章,1968);第三篇是对马奈(Edouard Manet,1832-1883)绘画的一个讲座稿:即,《马奈的绘画》(1971)。其中第一篇曾单独发表,后收入《词与物》;而后两篇也都曾以单行本印行。作为福柯对绘画的主要著述,这三篇文章表达了他的艺术哲学理念。可以说,福柯正是通过这三篇文章传达了他的艺术哲学思想;同时也使其与自己的哲学和美学互为表里、相互参证。如果说前两篇福柯谈论的是词与物(或语言与意象)的断裂之问题;那么,关于马奈的评述则显示了福柯试图构想一种“自由空间”的努力。然而究其实,它们谈论的是福柯一直迷恋的和渴望的一种体验:“看”与“说”、“可见”与“可述”的秘密。
在《词与物》开篇,福柯分析了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开兹(Velazquez)的古典名画《宫娥》。在这幅画的解读之中,福柯提出了其著名的“词与物”之关系问题,即:可见与可述之关系问题。因之,福柯事实上“利用该画处理‘画中画’的隐显关系之独特的手法,引导出‘语言’与‘画象’(意象)之间不确定关系”(叶秀山849)。换句话说,《宫娥》的分析只是一个引子,福柯想说的其实是“词”与“物”已然分离,而由此也带来了“知识型”的转化以及社会的转向。①不过,福柯解读这幅画的语言极为诗意、玄妙,甚至曾经引来研究者探索其“微言大义”、“春秋笔法”的猜测。可以说,福柯解读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述”(说);可这种“述”(说)与“见”(看)、与画中之“见”(透视/目光)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福柯没有明说,他制造了玄奥……
此画的中心是小公主和仆人,真正要表现的却是国王和王后,但他们的形象却是通过镜子反射出来的。画面中还有侧面朝向画外的画家本人,以及朝着画外观看的仆人……这些繁杂多样的目光交织在一起,使所有人既是观看者也是被观看者。它制造了这样一种效果,即:“注视者与被注视者不停地相互交换”;而且“任何目光都是不稳定的……主体与客体、目击者与模特无止境地颠倒自己的角色”(福柯,《词与物》5-6)。因此,这幅画反映的是“再现”;问题是这里的“再现”行为没有被表象出来。也就是说,“表征的两端都出场了,但是,将这两端连接在一起的行为却隐而不见”(汪民安66)。遵从福柯,我们可知在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词与物遵循相似性原则。即是说,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系统是这样组成的:能指、所指和“联结”。但在古典时期,同一性和差异性取代相似性——即是说,只剩下了能指与所指,不再有“联结”;而且,“符号不再是世界的标记,符号与相似性分离,成为一种纯粹的表象,并且是复制自身的表象”(刘永谋132)。这样,古典时代的知识型就是词与物断裂的表象世界。即是说,在古典时代,词(语言)与物(实在)分裂——《宫娥》所展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分裂。于是在该画中,“表象着手在自己的所有要素中表象自己”(福柯,《词与物》21);最终,表象将作为纯表象出现……《宫娥》中目光的交织,以及它与观者目光的交织,组成了一个未知的、不确定的网络。然而,这种相互可见性却也潜藏和承诺了无限的不可见性。不可见的需要被寻觅,然而它未见得必须、或能够被寻到——它是一种无限的生成,无尽的虚空。所以,“不是促使那不可见成为可见,而是促使不可见的不可见性源源喷涌其威力,这就是虚构的伟大力量”(杨凯麟19)。这种虚构既是绘画的魅力所在,也是其真理的秘密所在。可以说,福柯不仅展示了“语言”与“表象”不确定的关系;也展示了一种关于“可见”与“可述”之间的隐秘而繁复的关系。
正是因为关注词与物、语言与图像、可见与不可见②的问题,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Magritte)的作品《这不是一只烟斗》③才引起了福柯的强烈兴趣和热切关注。最终,福柯于1968年对这两幅作品进行了评论。这两幅画也被名之曰《意象的背叛》——马格利特解构了传统的、稳固的词与物、图像与表现之间的关系。言下之意,此中所要传达的就是“再现”与“否认”的关系(约斯·德·穆尔198-203)。马格利特的《这不是一只烟斗》无疑暗自契合了福柯的理论;故而,“福柯实则假借马格利特重述他在《词与物》中的主张——语言、图像和事物三者断裂的理论”(赵宪章170-84)。图形与文本的“同构”思想有着长久的传统,它有三个方面的作用:增补文字的不足;不求助修辞学实现重复表达;用双重书写捕获事物(Foucault,This Is Not a Pipe 20)。但马格利特此画(指第一幅)目的却是“使它们[指上述传统]堕落”,“从而打乱了语言和形象的传统关系”(Foucault,This Is Not a Pipe 22)。马格利特的文字显示了一种吊诡:它展现了一种“否定”关系(Foucault,This Is Not a Pipe 23-24)。也许马格利特是故意要显示这种背叛或断裂,但这种被“否认”的“再现”反而引发观者的审美愉悦——这是奇怪的,但又是可以理解的。西方自文艺复兴、甚至古希腊以来,知识系统一直是斯多葛式的三段论:所指、能指、联结;而事物与语言之间最大的特征就是“相似”。即是说,实在与言辞是同一的;表象与被表象物是同一的。然而,马格利特彻底断送了这种“同构”的幻想和期待。这是因为,“画、事物、文字,实际是三种不同的东西(物),它们之间只有某种‘相似性’(similarity),它们是‘相似物(者)'”(叶秀山849)。现代画家要做的就是冲出藩篱、努力创造、开拓疆域:他们既想打破同一性的迷梦,也想建构一种自己的原则——哪怕是一种无意义的意义、无原则的原则。在这一意义上,现代艺术家与哲学家、文学家所做的是同一件事。所以福柯说,在现代,“与其说绘画摆脱形象,毋宁说它已着手摧毁形象”(《福柯集》260)。
福柯认为,有两个原则支配着从15世纪到20世纪的绘画:一是把造型表现与语言表现区分开来的原则;另一是对等原则(即事实的相似与表达上联系的确认之间的对等)。克利(Klee)推翻了图文的空间,反叛了第一个原则;而康定斯基(Kandinsky)拒绝了第二个原则,同时抹去了相似性和表现功能。马格利特在表面上看起来比任何人都远离克利和康定斯基,但福柯认为,他们之间并不遥远——他们以共同体系为基础,组成了一种既对抗又增补的关系(This Is Not a Pipe 32-35)。福柯说,与克利与康定斯基不同,马格利特阻断了相似与确认之间的关系,“建立了它们的不平等性,使一方在孤立情况下运作,保持绘画的属性,排除最接近言语的性质——尽可能追随相似的无限延续,而把延续从任何确认性中删除”(This Is Not a Pipe 43)。于是,语言与表象、词与物彻底断裂,它们之间的“联结”不在了;能指与所指孤独而相对而在。意义变得无限、变得不确定;一切稳定的、僵化的、对等式观念就此消亡。马格利特“使纯粹相似和非确认性的语言陈述,在一种无标记的形体和一种未绘就的空间的非稳定状态中运作”(Foucault ,This Is Not a Pipe 53-54)。而在这一过程中,意义既消亡又再生;既确定又含混;既可见又不可见……然而,“秘密只为了被泄露或自行暴露而存在”(德勒兹,《德勒兹论福柯》56)。于是,图像(意象)本身就成为了语言(或话语)和目光的交迭、传输和生成的新的空间;它是自在的,也是自由的……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有词与物、事物与表现的“同构性”梦想;④但往往被“幻象”所遮蔽——它既可激起人们对世界把握的确信,也能促使人们不断渴望明晰性、同一性。于是,一种中心与边缘、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逻辑时刻缠绕在人们的头脑中。康德虽然打破了人类的幻想迷梦,然而却使人们再次陷入理性的深渊。后结构主义努力破除这种幻象,也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反讽(甚至是以荒诞的、极端的方式)。作为存在之象征的语言,德里达说作为物的、静态的语言始终被压制:即言语压制文字。于是,言语中心主义始终张狂:声音远高于形象,说远胜于写。基于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说”也必然远胜于“看”。这样,语言在古典时代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问题是,陈述和可视的关系并非那么简单。陈述对可视具有优位性——这种至上性正如德里达所言:“通过语言来恢复在场,既是象征性的恢复,又是即刻的恢复”(《论文字学》225)。不过,它永远只是一种“增补”;而增补不可能替代“看”本身。布朗肖认为述说具有作为决定者的至上性,但“言说并非观看”(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 25—32)。他说:“观看只是意味着一种谨慎的和可测量的分离……目光是一个停顿中的不可见活动——在其中,事物隐瞒自身”(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 28)。在这种不可见的“目视”活动中,事物需要揭示自身。于是,语言与形象之间、文与图之间也必然是一种互为增补的关系;而这必然又是古典的原则。马格利特打破了这一窠臼,福柯也肯定了这一点。布朗肖并非要指证二者的不可分离;他其实想说的是:“可视”是一种遥远的目光——它需要被重视、被解释。虽然福柯赋予(语言)话语、陈述以重要作用;不过,“福柯则仍维系着(尽管只是惊鸿一瞥)作为未定形式的观看特殊性与可视不可化约性”(德勒兹,《德勒兹论福柯》64)。福柯虽未见得扭转了“可视”的被动地位,但他毕竟赋予了“目视”一种本源和真实的地位;而这种“赋予”是福柯通过解读马奈的画来实现的。福柯在解读中还原了“目视”本身,极具现象学意味。福柯从13幅画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即,马奈发明了一种“实物—画”。福柯说:“这种油画物质性在被表象物中的嵌入,正是马奈带给绘画变革最核心的价值所在”(《马奈的绘画》16)。福柯认为,马奈的画给予“可视”和“可述”同等的地位;甚至“可视”本身从“可述”中越出,重新回到“看”本身。马奈的画是一种不再抒情的画,而是一种“是其所是”的画。
福柯认为《歌剧院化装舞会》的“空间被堵塞,从后面被关闭”(《马奈的绘画》18),从而景深效果也就消失了。⑤福柯认为这幅画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展现深度和空间,而是要让它成为纯粹的“表面”。这种“表面”既让人惊奇,也让人丧气;不过它却使新的空间得以打开。即是说,这种不可见空间正是“可见”的“不可见性”,或者相反。那么,“福柯寻找一种绘画话语,这种话语针对的是作为文献的画面,不仅仅是可见的画面,更应是不可见的画面,把陈述从可见性的圈套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要确立一种避免单纯用感觉经验进行解释的话语,它介于可见物及其可能性条件之间”(杜小真129—38)。这“之间”就是德勒兹所谓“……之中”,或它本身就是一种“生成”。福柯发明的这种话语并非是要再度到达一种确定性或稳定意义;而是使我们知道,“看”要比“说”重要。最终,“福柯认为……马奈的作品开启了让观者看画的时代,‘看’代替‘读’……看画…就是‘可见性的非话语实践'”(杜小真129—38)。于是,福柯的所谓“真理”也就暗含其间了——或者,福柯的绘画理念(或真理观)是抽离绘画本身的。
在解读《在温室》这幅画时,福柯说:“在这里,我们看到旨在消除、抹杀、取缔景深意义的空间,凸显垂直和水平线条的全部手段”(《马奈的绘画》25)。画中,两位模特都置身于同一平面;画面空间极为逼仄。没有景深、没有空间,甚至连人物也模糊不清。男模特低垂着头、不见目光;而女模特的目光游离,散漫地投射向画外……可以说,这是一幅用极端手段来抵御景深的绘画。在《卖啤酒的女侍》的读解中,福柯终于揭示了他的核心观念:⑥“与其说这幅画表现可见物,不如说它隐藏和掩盖可见物。油画正反两个面的平面不是表现可见性的地方,相反,它是确保不可见性的地方,即被画中人物所看到的东西的不可见性”(《马奈的绘画》27)。不过,这幅画的关键是“目光”:一种外泄与内在的目光。观者与被注视者将在“目视”之间形成空间、制造景深——而非在画面内部。这种“看”不仅使不可见愈加可见,也使得它意义更加多元。这里的“目视”就是“述说”,或者是其隐喻……当然,这种不可见性也与画面的光线或光照有关;所以福柯挑选了马奈的名画《吹笛少年》和《草地上的午餐》(1863)。他认为,《少年》取消了内光;而《午餐》则有两个光照系统——内光与外光。只是,福柯从后者看到了“内在异质性”。⑦这种异质性使马奈的画显现逼人的真实,也显现一种话语或“述说”的可能性。至于那幅惊世骇俗的《奥林匹亚》,福柯说,是我们的目光投向她(或它)并将其照亮。即是说,这里的光线是观者之目光——在这里,目光就是光照(《马奈的绘画》34—35)。这才是重点所在:福柯发现了马奈将光线与观者目光进行了整合——而这无论是古典绘画、还是激进的现代画家都不愿做的。
福柯最推崇的是《弗里—贝尔杰酒吧》这幅画:画面中心的酒吧女侍好像处于一种迷失之中;她周围有为数众多的顾客在座,但都是镜中映像。这些倒置的意象将女侍的可见性离散,使之一劳永逸地走向“可视”的边缘。从观看的角度来说,这幅画没有中心;而“不可见的”不是一种具体物象,而是“不可见性”。福柯认为,这幅画真正提出了“不可见性”的问题。在此画中,观者的位置、画家的在场与不在场、模特之看与被看……都极具象征意义,也都真正再现了一种不确定空间和意义。而这些“正是人们最终可以摆脱表象本身,用油画纯粹的特性以及其本身的物质特性,发挥空间作用的基本条件”(《马奈的绘画》43)。正是因为这样,福柯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马奈发明了一种“物—画”或“实物—绘画”。为此,布朗迪娜·格里热说:“实物—画、实物—绘画的提出就是现象学的,几乎像化学那样纯粹”(《马奈的绘画》146)。所以,逼真地“看”至关紧要。最终,可见与可述在马奈的画中逐渐合一,新的“真理”也自行显现。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说,“看”与“说”只是一种话语或非话语实践操作;它关涉的并非意义本身,而是意义的生成——而这也就意味着“可述的,只用话语形成;可见的,不能用话语形成,它落在一个沉默的空间里,等待话语替它说话”(尚杰5—20)。“可见”与“可述”通过一种实践操作,从而打开新的空间,也使新的意义和价值呈现。然而它又并非一种僵化之线;毋宁说,它是一种生成运动。在此种运动中,可见与可述、看与说相互关联、互通有无,从而真正实现一种对等、交迭和互逆性。在此,可见与可述不再纠缠于对与错、好与坏、真与假的道德判断中,也不再将自身消耗在永无休止的孰优孰劣、孰高孰低的争执中;毋宁说,它将努力整合二者的操作功能,从而实现抽象与生成的意义书写。从这一角度而言,它必将是一个过程。然而,“在说与看、可视与可述之间存在着一种隔离(disjunction):‘被观看之物从不蛰居于被述说之物中’,反之亦然”(德勒兹,《德勒兹论福柯》67—68)。福柯看到了这种断裂:对他而言,这种“隔离”要远比古典时期词与物之间的“断裂”来的重要。因为,词与物之间的断裂仅仅显示为事物自身的关系破碎,它还有弥补和增补的可能——正像中国古代绘画中的题诗画那样;而“看”与“说”的“分裂”却显示出一种人们思想或意识的“分裂”。如果我们不能将这种“可见”与“可述”置放、或布置在一个洽适的位置,那么将会引发更大的裂变。这种裂变将会毁坏我们的感觉,毁坏我们的触感空间,甚至会毁坏“看”与“说”本身。
不过,看与说是一回事,可见物与述说物又是另外一回事。看与说关涉的是一种理念和情感,而后者却只是一种将被揭示的“沉默”。沉默的事物自我隔离、自我断裂,从而也将“看”与“说”的行为本身引向分裂。福柯不仅从《宫娥》和《这不是一只烟斗》中发现了这一点;也从马奈的绘画中深刻印证了这一事实。因此,“在福柯‘看’和‘陈述’的理论中,我们都能看到‘断裂’思想的影子:已成画作的画面与观者‘看画’的陈述之间、画家之‘看’与观者之‘看’之间、画家位置与观者位置之间[……]都存在着‘断裂’或者说根本的改变”(杜小真129—38)。这种断裂在任何“看”与“说”、“可见”与“可述”之中根本不可能彻底弥合;福柯认为我们要做的是去感受和“体验”。然而,问题并不在于去显示这种断裂或不可化约性;而是要去展现它们之间的层次与生成。正因如此,福柯发现了马奈绘画中惊人的创造;而它们正如达龙-于贡所说的那样,福柯展示了马奈绘画的三个方面条件:表现空间的处理;对光的处理;对观者的位置的安排(《马奈的绘画》72—73)。这也就是说,福柯指出了马奈绘画的这样三种突破;同时也将其潜藏进自己的思想之中。事实上,这三个问题可以归结成一个问题:可见与可述。它们直接指示着这样一个问题:感受或体验。
德勒兹说:“就所有艺术而言,应当说:艺术家给予我们感受和视觉,他们因而就是感受的报告者,发明家,创造者”(《什么是哲学?》456)。显然,委拉斯开支、马格利特、马奈都是如此;克利、康定斯基也不例外。现代画家需要展现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而艺术、尤其是绘画需要的正是这种感受性。可以说,一种“感觉”或“体验”就融汇在绘画之中,而画家要做的就是将其展现出来。绘画既是一种“可见性”的艺术,也是一种“可述性”的艺术。更为紧要的是,“可视性并非由视觉所界定,而是行动与激情或是行动与反应的复合联结,它是进入光线中的多元感官的复合联结”(德勒兹,《德勒兹论福柯》61—62)。即是说,绘画的多元感官组合必定会促使“看”与“说”走向合一。即便这种整合或许是暂时的、间断的,但它却会促使新的意义空间得以生成。诚然,作为“物”的画只能沉默,可是作为观者的“可见”与“可述”却会使其走向言说。从17世纪开始,“所见与所读,可见物与可陈述物在其中不停地相互缠绕的那个单一的层次那时也消失了。物与词将相互分离”(福柯,《词与物》58)。委拉斯开支显示了这一点,而马格利特则走向了更极端的悖反。马奈与他们不同,他着力于发掘可见性本身;并且试图用可见性来勾连可述性。即是说,马奈让绘画首先沉默,然后自我呈现。可以说,“马奈要的是‘绘画的沉默’[……]马奈用一种可见的绘画替代了可读的绘画。”(福柯,《马奈的绘画》65—66)。福柯关于可见与可述的探讨显示了其艺术哲学理念:即,让话语出场,实现话语(或非话语)操作,进而发现其秘密。进而言之,“可见”与“可述”、“看”与“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只是福柯真理操作的策略或行为之一。
事实上,福柯终生迷恋的就是“体验”。尤其是阅读了尼采、布朗肖、巴塔耶等人作品之后,福柯的这种体验的欲望更是不可遏制。关键是,上述这些人都昭示着一种“越界”或“外部”的思想。即是说,福柯渴望到达那种神秘的“域外”;而这种域外正是一种如同无尽的目光那般遥远和迷人。所以,福柯一度对于文学、绘画、艺术产生出体验的迷狂;而这种体验都指向外界——他的所有关于文学与艺术的分析和解读,实际上都是这种想念的实践或结果。可以说,“不只是历史,福柯对文学或绘画的分析都只不过是为了再次召唤这种域外的未知力量以寻觅摆脱自我及自我转型的可能”(杨凯麟37)。如果说《宫娥》和《这不是一只烟斗》的解读还有着明显的学术纹理在其中;那么,《马奈的绘画》就完全是一种向外界伸展的手——一只可以任意伸缩、褶曲的手。在这只手的正反两面中,一面是可述,一面是可见;一面是“看”,另一面是“说”……二者无限接近,又无限遥远。于是,在这恍惚迷离、若隐若现之间,福柯给予我们以最深沉的感受。
1.“目视”的考古学
在考察临床医学时,福柯发现了“可见”与“可述”之间含蓄隐秘的历史关联。然而,他在马奈的绘画解读中则更进一步:如果说前者仅仅在于发现;那么后者就有一种构想在其中了。即是说,福柯三次关于绘画的解读实际上都是一种“看”或“可见”思想的描述;重要的是,在这些解读中,福柯不仅给予其以颠覆者的地位,而且努力使其另一面(即“说”与“可说”)参与其中。福柯并没有打算让前者彻底击垮后者;而是试图将二者做出勾连和协调。他的目的其实在于,不仅仅是要“差异”,更要“生成”。对于绘画而言,这种“生成”首要的质素就是“目视”、“看”或“可见性”。即是说,它的光线、色彩、景深、构图等等都是观者可见的“可见物”承载者。这些可见物(或“可见性”)本身实际承载着无限的不可见——但它们始终孤独地沉默着,等待被看与说。同时,“可见性与不可见性在观画过程中的变化和置换给予我们一种关于目光的启示:艺术家的执着和追求,可以建立可见物和不可见物之间的结构,作为光和影的知识永远可以向言语投射原始目光”(杜小真129-38)。于是,目光就不仅仅是一种“看”的延伸,它具有了丰富的言说的动机。现代画家就是要抓住这种遥远而深沉的“目光”,让其回归本真,成为一种“目视考古学”。这就是说,画家以其特定的艺术技巧使可见与可述走向协商和交织,并最终走向一种深度的表面化。这一点在马格利特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而它可能“最伟大的功绩就在于它无限的表面性,而不是深奥”(约斯·德·穆尔218)。
所以,现代绘画并不在于技法的创新,而是在于重新发现目光。就是说,“必须劈开事物,击碎事物,因为可视性既非物体的形式,甚至也非光线与事物接触时所显露的形式,它表现为一种明晰性形式,由光线本身所创造,而且只让事物或物体如闪电、闪光或闪烁之光线般暂存”(德勒兹,《德勒兹论福柯》54)。这种“目视”的考古学,在德勒兹看来是福柯从雷蒙·鲁塞尔(Raymond Roussel)那里汲取的;⑧并且福柯试图从马奈那里得到印证。德勒兹说:“看—说的隔离在关于雷蒙·鲁塞尔的著作和关于马格利特的文章中达到顶峰,它将带来可见和可说的新地位:‘人们说’将活跃陈述的理论;近与远在外的线上的转换,作为生与死的实验,将带来福柯独特的思维行为,带来褶皱(与海德格尔迥异),并终将成为主观化进程的基础”(《哲学与权力的谈判》111)。福柯首先发现了“可见”与“可述”的关系;他也试图改变二者陈旧破碎的对立关系。福柯因此成就了一种“目视”的“考古学”;同时也将思想带到了一个新的场域——德勒兹认为,这是一个“皱褶”(或“褶子”)。然而,“陈述条件(语言)的自发性赋予陈述决定者的形式,并使其具有优位性。而可视条件(光线)的感受性则仅使可视具有未定的形式。因此,即使这两种形式有本质上的差异,决定作用仍可视为总是来自陈述”(《德勒兹论福柯》70)。可以说,陈述(或“可述”)的优位性(或“至上性”)不可能改变。好在福柯并不打算颠倒二者;而是宁愿给二者以平等的地位,并使其共存、共生和共赢。
事实上,巴塔耶也评述过马奈的画。他认为马奈的画是通灵的,都传达出神秘的力量——它是一种“可见物的”艺术。由此可见,巴塔耶的分析和福柯是非常接近的——只是他并未如福柯般赋予“目光”一种更深刻的思考。也许,马奈不像马格利特那样解除了和模特之间的表象关系,“而是显明了表象的诸种条件,就是说显明表象的这个盲点,它只允许在未被看见的条件下去看”(福柯,《马奈的绘画》71)。福柯因此认为,这就是马奈的创新,一种超越印象主义的再创造。而这种创造既是技术上的,也是思想上的。这样,福柯的“目视考古学”也必然带来一个积极的结果:那就是走向新的“自由空间”。
2.自由空间
通过马格利特的画,福柯使我们认识到:正是语言文字的嵌入,现代绘画表现出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它抛弃了相似性和确定性,显示了断裂的碎片或新的空间。而通过马奈的画,福柯则向我们昭示了一种新的自由艺术空间的可能性——正如大卫·玛丽认为的那样,“对福柯而言,马奈的作品是将自由还给观者的绘画”(《马奈的绘画》85)。而在其中,福柯向我们描述了可见与可述之间的缠卷、交迭和衍生;也向我们展示了绘画中的“力”和意义。基于福柯,我们可知:绘画是一种增补和再现;它要展示的是不可见性;它是一种关涉自由空间的艺术。然而,福柯也暗示我们:在绘画中,没有什么确定的意义;重要的是“看”、是“展示”、是让画“自己说话”——而这也和德里达的观点极为相似。德里达曾经认为,绘画是将意义悬置起来的艺术,绘画是一种没有真理的艺术(The Truth in Painting 340-43)。在分析海德格尔关于梵高的鞋的文字和事件时,德里达运用解构的视角和手法告诉我们:绘画中,真理(或意义)已经失落了。于是,需要增补,需要复原。这些既是绘画的古典要求,也是所有艺术的现代律令。然而,马格利特、马奈、塞尚或许就不会这么看。换句话说,他们至少不会就此遵从,因为他们的目标在别处、在“外边”。福柯有这样的兴趣,更有这样的需求。因此,福柯试图构想一个绘画的自由空间:一种关于目视的空间。这一空间既是真理的自行显现或“去蔽”,也是自由思想的游戏、实验和流动。这一自由空间的梦想,实际上早已为海德格尔所昭示——他曾经说:“真理的本质乃是自由”(《林中路》214)。这也就是说,艺术的本质就是自由,这种自由就是真理本身。福柯关于“看”与“说”、“可见”与“可述”的分析,实际上都是这种自由精神的反照。关键是,绘画就是实验、就是创造;而这种说法对于思想而言,显然也并无不可。
德勒兹在解读培根的画时就倾向于体现这种“自由”的“感受”,他倡导一种“力”。即是说,他关注的是“感觉”和“力”:“与感觉紧密相关的不是形式而是力,正如培根的画旨在捕捉力一样”(康斯坦丁·V·庞达斯305)。并且,“绘画的职责被定义为将一些看不见的力量变成看得见的尝试”(德勒兹,《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68)。在他看来,这种“力”就是创造、就是自由精神,它所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必然是一种“自由空间”。德勒兹甚至为此反对透视法和深度:“透视,甚至是深度,都是对于逃逸线的再结域,而只有逃逸线才能创造绘画、将它带向更远”(《千高原》424)。即是说,作为欲望之线和毁灭之线的“逃逸线”既能将绘画带到新的空间,也能使其展现自由的精神。福柯和德勒兹所使用的概念虽然迥异,但二人的思想却是一致的。福柯认为,“画家与其所绘内容的关系处于一种被接替、被帮助和被保护的状态”(《福柯集》261)。这就是说,画家将自己所画的内容与自己的思想密切结合起来。于是,马格利特就要展示一种“再现的否认”或“意象的背叛”;而马奈就要将自己的目光伸向遥远的不可见境域之中……而这些显然都是自由空间的生成。
也许,“对无限的‘意义’的表现正是艺术想象的核心目的”(姜宇辉118)。那么,对于普泛化意义的追寻始终是艺术的根本目标或动机。关键是,这种意义在现代或后现代艺术中已经不再是确定的、不容置疑的了。现代艺术主张寻找差异、寻找未定性的意义;这也就意味着现代艺术必然倡导一种自由的生成与流变——而“‘意义’正是在所有这些差异的要素的‘游戏’之中得以‘表现’”(姜宇辉119)。换句话说,单一的意义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要去感受,去创造。而在这样的情势之下,现代艺术将会在更广大的空间中获取自由和价值。可以说,福柯的三幅绘画的解读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或许就是:我们需要的不是思想什么(或思考某物),而是思想本身。重要的是,福柯给我们开启了一种新思想的可能性空间;同时也展望了一种自由的绘画空间。虽然福柯并没有确实地创立某种规范化、或体系化的艺术哲学理论,而他关于绘画的思考本身就是一次朝向外界的探索之旅或实验。而马奈给予福柯的启发也许就在于——绘画即事件本身;所以福柯说:“绘画重新启动事件,向事件开放”(《福柯集》265)。而这一事件也将开启一个自由的思想和空间。在这里,绘画将会真正自由而成为“其所是”。艺术家也将会在此回到“可见”与“可述”的裂隙之处,进而婉转自由地转跳腾挪。于是,德勒兹认为:“观看,就是思考;述说,就是思考,但思考完成于缝隙中,于观看与述说的隔离中”(《德勒兹论福柯》89)。也正是因为这样,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E.H.Gombrich)才说:“艺术家的倾向是看到他要画的东西,而不是画他所看到的东西”(61)。
注释[Notes]:
①福柯认为存在着三种“知识型”:第一,16世纪文艺复兴知识型(即,“相似性知识型”);第二,17-18世纪古典时期知识型(即,“表象知识型”);第三,19世纪以来的现代知识型(即,“有机结构知识型”)。在第一种知识型中,词与物统一(特征:相似性原则/阐释);第二种知识型用词的秩序再现物的秩序(特征:再现/同一与差异原则/分析);而在第三种知识型里,词的秩序不表示真实事物,而表示人对物的表现(特征:“人”出现/有机结构原则)。并且,福柯认为这三种知识型之间是断裂的、不连续的、不可通约的(此处主要参阅了以下研究成果: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第145页及以下;福柯:《词与物》,译者引语,第3页;刘永谋:《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第130页及以下)。
②事实上,“可见(性)”与“不可见(性)”也是现象学关注的中心。因为,现象学和胡塞尔思想的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我们如何回到事情本身?!后期的梅洛—庞蒂也极为关注这一问题,并为此写出过专著(即,《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眼与心》等)。他从“知觉”和“身体”出发,发现了世界之“肉”;也发现了可见物与不可见物之间的“交织”以及“互逆性”。
③马格利特曾以此为题作过两幅“烟斗”画:一幅画于1926年;另一幅作于1966年。前者就是广为人知的《这不是一只烟斗》:图中,一只巨大的烟斗蔓延在整幅画面里,而底下铭文即为“这不是一只烟斗”;后者图中有两只烟斗:一只同上一幅画(处于画面左上方),另一只是“画中画”——乃是画于画中的烟斗(处于中下方)——这只烟斗就好像上一幅画的复制(包括铭文)(参见Foucault,This Is Not a Pipe,1982)。此外,马格利特为此还曾与福柯通过信,交流关于此画的看法(参见This Is Not a Pipe附录)。
④这种梦想就是:我“所说的”和我“所看到的”是否、或能够是一致的?我所描述的和事物本身是否相同?或者,我“看”与我“说”这种行为本身是否一致?……对于一首“造型诗”(calligramme)而言,其文本与图画、语言与造型、陈述与影像之间,是否具有相同的形式或意义?即是说,它们之间有没有分离、断裂,或存在着交锋?它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德勒兹认为,福柯沿用布朗肖的看法,认为这是一种“非关系”——只是,这种“非关系”也是一种关系,而且还是一种更深层的关系。不过,究其极而言,这种“同构”的梦想是可以被理解和思考的(参见:《德勒兹论福柯》,第64—66页)。
⑤福柯在《这不是一只烟斗》中也曾经认为“空间没有景深”(参见:杜小真编《福柯集》,第129页)。但英文版第54页所显示的词汇是“an unmapped space”——该文的中译者根据语境,将其译为“空间没有景深”;但仅就该短语来看,译为“一种未绘就的空间”似乎更恰当一些。
⑥马里沃尼·塞宗认为,福柯全部讲座都在证明这样一个观点:即,“不可见性是可见的”。而且,他还援引福柯著作(即《言与文》)中的话加以证明:“虚构,不在于让人看到不可见物,而是要让人看到不可见性是多么不可见”(参见:福柯:《马奈的绘画》,第5—8页)。
⑦福柯是纯粹从两种光的表象系统来谈论这种“内在异质性”,即“不平衡性”的。而当年此画之所以饱受抨击,倒不是因为这种哲理因素使然,也不是因为绘画存在着什么技术问题;而是因为卫道士们、或普通的世俗审美心理根本难以接受画面所显露的道德冲突、冒犯、僭越或亵渎。比如:在画面最前方,裸女肆无忌惮的目光,两个正襟危坐男人的旁若无人交谈……都让人不可理解、不堪忍受——而这种“目光”的暴力(或“放肆”的目光)及其显现,更是在马奈的另一幅名作《奥林匹亚》(1865)中登峰造极——它使无数观者大惊失色、惊慌失措;以至于人们最终根本不堪忍受,进而开始群起而攻之。
⑧事实上,它最早源自于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的思考。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Blanchot,Maurice.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Trans.Susan Hanson.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3.
[2]康斯坦丁·V·庞达斯:“德勒兹的几个主题”,汪民安编《生产5:德勒兹机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Boundas,Constantin V.."Some Themes of Deleuze".Producing V:Deleuze's Machine.Ed.Wang,Minan.Guilin:Guangxi Normal UP,2008.]
[3]吉尔·德勒兹:《德勒兹论福柯》,杨凯麟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Deleuze,Gilles.Foucault.Trans.Yang Kailin.Nanjing: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2006.]
[4]——:《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刘汉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Negotiations(1972-1990).Trans.Liu Hanquan.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00.]
[5]——:《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董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Francis Bacon:the Logic of Sensation.Trans.Dong Qiang.Guilin:Guangxi Normal UP,2007.]
[6]——:《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
[---.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Trans.Jiang Yuhui.Shanghai: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2010.]
[7]——:《什么是哲学?》,张祖建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
[---.What Is Philosophy? Trans.Zhang Zujian.Changsha:Hu' 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2007.]
[8]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Derrida,Jacques.Of Grammatology.Trans.Wang Tangjia.Shanghai: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05.]
[9]---.The Truth in Painting.Trans.Geoff Bennington and Ian Mcleod.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10]杜小真:“‘看’的考古学——读福柯《马奈的绘画》”,《文艺研究》3(2011):129—38。
[Du,Xiaozhen."The Archeology of the Vision:on FoucauIt's Edouard Manet's Paintings."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3(2011):129—38.]
[11]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Foucault,Michel.The Order of Things.Trans.Mo Weimin.Shanghai: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1.]
[12]——:《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Trans.Xie Qiang and Ma Yue.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6.]
[13]——:“照相式绘画”,《福柯集》,杜小真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
[---."The Photographic Painting." Selected Works of Foucault.Ed.Du Xiaozhen.Shanghai:Shanghai Far East Publishers,2003.]
[14]——:《马奈的绘画》,谢强、马月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
[---.The Edouard Manet's Paintings.Trans.Xie Qiang and Ma Yue.Changsha:Hu' 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2009.]
[15]---.The Foucault Reader.Ed.Paul Rabinow.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4.
[16]---.This Is Not a Pipe.Trans.& Ed.James Harkness.Berkeley,Los Angeles &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
[17]E.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林夕、李本正、范景中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
[Gombrich,E.H..Art and Illusion.Trans.Lin Xi,et al.Changsha:Hu'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2007.]
[18]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Heidegger,Martin.Holzwege.Trans.Sun Zhouxing.Shanghai: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04.]
[19]——:《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Being and Time.Trans.Chen Jiaying and Wang Qingjie.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6.]
[20]约斯·德·穆尔:《后现代艺术与哲学的浪漫之欲》,徐骆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
[de Mul,Jos.Romantic Desire in(Post)Modern Art and Philosophy.Trans.Xu Luo.Wuhan:Wuhan UP,2010.]
[21]姜宇辉:《德勒兹身体美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Jiang,Yuhui.On Deleuze's Aesthetics of Body.Shanghai:East China Normal UP,2007.]
[22]刘永谋:《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Liu,Yongmou.A Journey into Foucault's Deconstructurtion of Subject.Nanjing:Jiangsu People's Press,2009.]
[23]尚杰:“‘外部的思想’与‘横向的逻辑’”,《世界哲学》3(2009):5—20。
[Shang,Jie."The Thought of Outside and the Transverse Logic." World Philosophy 3(2009):5-20.]
[24]汪民安:《福柯的界限》。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Wang,Minan.Foucault's Limit.Nanjing:Nanjing UP,2008.]
[25]杨凯麟:《分裂分析福柯》。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Yang,Kailin.Schizoanalysis on Foucault.Nanjing:Nanjing UP,2008.]
[26]叶秀山:“‘画面’、‘语言’和‘诗’——读福柯的《这不是烟斗》”,《叶秀山文集》(美学卷)。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年。
[Ye,Xiushan."Image,Language and Poem:on Foucault's This Is Not a Pipe." Collected Works of Ye Xiushan.Vol.Aesthetics.Chongqing:Chongqing press,2000.]
[27]赵宪章:“语图互仿的顺势与逆势——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中国社会科学》3(2011):170—84。
[Zhao Xianzhang."Asymmetry in the Mutual Imitation of Language and Image:A Fresh Look at the Literature-Image Relationship",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3(2011):170—84.]
标签:这不是一只烟斗论文; 艺术论文; 福柯论文; 艺术哲学论文; 文化论文; 德勒兹论文; 词与物论文; 哲学家论文; 马奈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