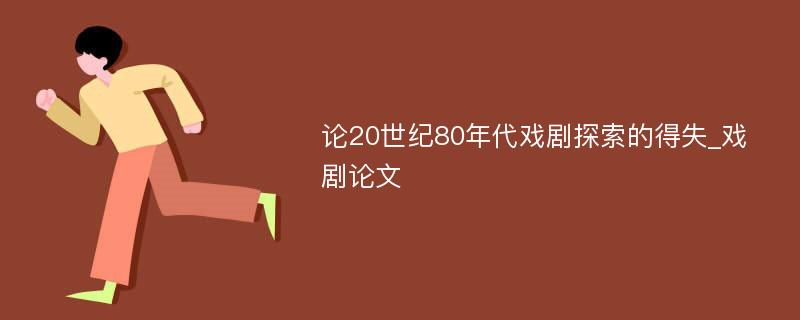
八十年代戏剧探索得失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得失论文,戏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剧坛是令人难忘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刚刚离去,人们对它还记忆犹新,更重要的是它那曲折、独特的发展、演变过程,既令人欣慰、赞叹、倍感兴奋,又让人惊讶、困惑、忧心忡忡:那融入了几代人心血的中国话剧的辉煌以及猝不及防、突兀出现的让人心寒的寂寞与悲凉,始终萦绕在当代戏剧工作者的脑际、心间。的确,中国八十年代沸沸扬扬而又冷冷清清的剧坛上出现的诸多众说纷纭的现象,太值得我们思索、探讨、研究了,真是“说不尽的八十年代”。在此,笔者仅就八十年代中国剧坛的一大景观——戏剧探索热潮的蓬勃兴起与探索戏剧的大量涌现及其功过、得失,谈谈个人的初浅看法。
粉碎“四人帮”后的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政策、思想解放的潮流,推动了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实事求是的作风,民主、宽松的氛围,更给中国人民解除了种种有形、无形的精神枷锁;打开国门、引进先进技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已成为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参预国际对话、参预国际竞争,已不仅仅是企业家的思想动向,而且在文艺界也产生了热烈的反响。正是在这种团结、和谐的政治气候与文化环境的鼓舞下,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自觉地肩负起时代的重任,开始踏上了布满荆棘、又充满希望的探索之路。一时间,当代文坛喧闹嘈杂,令人眼花缭乱。一方面,文学艺术逐渐从“政治工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始更为鲜活地显示出自身独特的品格与规律;另一方面,不少作家在艺术上又八方涉猎、兼收并蓄,广泛地引进外国文艺思潮、借鉴西方现代派创作技法,致使文坛面貌大为改观。什么先锋小说、实验话剧、朦胧诗、意识流、心理结构、忧患意识、系统论、符号学、全知视角、间离效果、非理性主义、非逻辑因素,等等,在短期内大量出现。尽管文艺界对此评判不一——称赞者说: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反对者认为:当今的文艺已陷入无力自拔的误区。但客观的事实是:这些新潮流、新理论、新面孔正以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特有的魅力向传统的文学观念、审美方式、艺术法则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并共同营造了这时期中国文坛“从一元走向多元、从整齐划一走向参差无序、从纯净明朗走向斑驳含蓄”的新局面。
以上状况也正是八十年代中国剧坛戏剧探索热潮蓬勃兴起、探索戏剧大量涌现的气候、土壤与背景。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戏剧界这一特殊景观的出现除了与社会环境、文艺潮流等因素直接关连外,也还与当代戏剧自身面临的困境与挑战紧密相关。当代话剧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短短几年里曾有过令人振奋的繁荣时期,但一经跨入八十年代便骤然跌入低谷,出现了以观众大量流失为主要特征的“话剧危机”。当然,“危机”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仅就目前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而言,就有影视的冲击、业余生活的丰富、个人兴趣爱好的多样与艺术自主权的失而复得等外因,以及话剧艺术自身观念的狭窄、形式的凝固、手法的单一、表现力的贫弱等内因。为此不少戏剧家怀着正视困难、克服“危机”的勇气和决心,开始了新的追求和探索。他们不倦以求的是丰富和拓展话剧的表现手段、强化话剧作为现代艺术的表现张力。他们努力寻找戏剧的优势、寻找戏剧的观众、寻找戏剧的出路,力图摆脱困境,重振昔日雄风。于是,当代剧坛涌现了一批五光十色、众说纷纭的所谓探索戏剧,或称实验话剧、新潮话剧。象《屋外有热流》、《血,总是热的》、《陈毅市长》、《阿Q正传》、《绝对信号》、《车站》、 《野人》、《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挂在墙上的老B》、 《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街上流行红裙子》、《五(二)班日志》、《魔方》、《WM(我们)》、《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等等,则是它们的代表。
说到戏剧探索,笔者以为它是与中国戏剧发展的历史同步,也就是说它始终贯穿于中国戏剧发展的整个历程。 中国话剧的诞生如果是从1906年留日学生成立春柳社算起,至今已有了近百年的历史。近百年来,戏剧界的前辈,象欧阳予倩、田汉、洪深、郭沫若、丁西林、老舍、曹禺、夏衍、阳翰笙、李健吾、陈白尘、熊佛西,以及顾仲彝、焦菊隐、黄佐临、欧阳山尊等等,为话剧艺术的生存与发展,在披荆斩棘、呕心沥血的同时,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他们倾心探索如何将这“舶来品”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土壤之中,探索话剧艺术如何为中国广大普通百姓喜闻乐见,探索话剧如何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伟大斗争相结合,还要探索如何使这一外来的艺术更多地融入民族风格、地方色彩,特别是如何与中国古老的戏曲艺术相结合,使其更具中国特色。这一切都为我们后来者积累了经验、树立了榜样。如果我们有意识地将今、昔的探索加以比较,便会发现:八十年代的戏剧探索既与前辈戏剧家勇于开拓、不懈探求的精神一脉相承,但又有自身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全方位、大力度、开放性、兼容性。如果说过去的戏剧探索更多的是致力于改善、调整话剧艺术与外部世界的和谐关系,那么到了八十年代,探索的着眼点则更为丰富、多样。其中既有对戏剧特性、规律、功能偏狭理解的扬弃,又有对长期以来习惯于政策图解、道德教化的创作思想与模式的否定;既有对作品结构、形式、手法的各种新的实验、尝试,也有对剧场艺术方面不同表演方式、观演关系的重新探索;既有对西方现代戏剧流派、艺术手法的引进和借鉴,又有对我国民族戏剧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此外,我们还发现,前辈们的戏剧探索更注重于建立并完善易卜生的写实主义佳构剧的模式;学习并推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制造生活幻觉的表演经验;而八十年代的戏剧探索则与之不同,它不固守某一不变的法则或单一的模式,而一开始便呈综合包容、兼收并蓄的态势——既力求继承、发展传统艺术的表现力,又努力探索、开拓表现生活的多种可能性。什么写实型、写意型、象征派、荒诞派都能进行广泛的尝试;什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布莱希特体系、梅兰芳体系都能在剧坛上一展风采,因此可以说八十年代的戏剧探索是前所未有的,是规模空前的,它以其自身的广度、力度与实绩影响着中国话剧发展的走向,改变着中国剧坛整体的面貌,在中国话剧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八十年代戏剧探索的主要特点,首先表现在剧本创作上。广大剧作者,特别是一批中青年作家,他们愈来愈不满于建国以来中国话剧封闭、凝固、单一的风气,象直奔主题的戏剧动作、过分凝聚的线性结构、营垒分明的冲突格局、平面静止的性格设计等等,他们力图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冲破固有模式的束缚,给剧坛带来新鲜空气和活力。他们的这种创新与探索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戏剧结构多姿多采。广大剧作者大胆否定了将纷繁复杂的生活矛盾简化为环环相扣、因果相依的线性组合的作法,摒弃了“一对冲突、两股势力、三个回合”的套数,而主张根据现实生活的实际、根据剧本内容的需要,不拘一格、自由灵活地来选择、安排戏剧结构。被誉为“戏剧新潮滥觞之作”的《屋外有热流》便是这样。这出小戏描写了一位为革命工作而献出年轻生命的普通勤杂工赵长康的幽灵,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弟弟、妹妹见利忘义、浑浑噩噩的可鄙生活,决心帮助他们找回失去的“那发光发热有生命的灵魂”,并呼唤他们走出冰冷的屋子,到屋外,到充满热流的生活中去。剧本采用近乎荒诞的手法,通过不合常理的戏剧冲突,以虚写实、以实写虚,虚虚实实创造了一种自由的结构格式来鞭挞丑恶的灵魂。“改变了话剧舞台上长期以来出现的‘传统戏剧’的格局——完整的故事情节、起承转合的戏剧冲突、严谨的时间、空间限制”,不仅给读者、观众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在戏剧界还产生了意外的效果。象《陈毅市长》,剧本打破了以中心事件贯串全剧的传统戏剧结构手法,代之以一个人物贯串始终。十场戏,十个生活片断,既各自独立,又互有联系,在波澜迭起的矛盾中成功地塑造了有胆识、有魄力、有才干的陈毅市长的典型形象,作者称此为“冰糖葫芦式”的结构。而《魔方》则由哑剧、音乐、舞蹈、相声等不同艺术形式组合而成,剧中的节目主持人随时拿着话筒请观众发表感想,这一切打破了“第四堵墙”所造成的幻觉和镜框式舞台的限制,可以说“在任何一本编剧法上都找不到它的归属”,而编导者则给它命名为“马戏晚会式”结构。此外象《街上流行红裙子》的平行结构、《绝对信号》的双重时空结构、《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的散点透视结构、《野人》的开放型网络结构、《狗儿爷涅槃》的意识流式的结构等都是过去未曾见过的。这一切,不仅改变了传统戏剧结构千篇一律的模式化弊端,而且还使得八十年代的中国剧坛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景象。
第二,在人物刻划方面,既注重普通人形象的塑造,又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长期以来,我们的戏剧创作由于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往往只是片面地强调“写英雄、唱英雄”,而多少忽视了作为我国人口最大多数的普通的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或将他们斥为“中间人物”而排斥于戏剧殿堂之外、或只把他们作为英雄人物的“陪衬”、“附庸”、“背景”,这实际上是抹煞了普通人形象在戏剧舞台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直到粉碎“四人帮”,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之后,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才得以根本改变。广大戏剧工作者(还不仅仅是戏剧工作者)总结了“十年浩劫”的教训,开始把自己的艺术目光从虚无缥缈的人造神坛,转向生气盎然的坚实大地。他们真诚地审视了这些自身带有这样那样缺点,或还残留着各式各样包袱的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开始在自己的剧本中描写这些勤勤恳恳、堂堂正正的普通劳动者。象《屋外有热流》、《血,总是热的》、《绝对信号》、《路》、《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街上流行红裙子》、《寻找男子汉》、《宋指导员的日记》、《黑色石头》等剧作都将普通劳动者作为主要的反映对象和描写的主角。既写了他们的弱点、苦恼和困惑,又满腔热情地讴歌了他们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出自己一切的品质。此外,八十年代戏剧探索在人物塑造上还有一大功绩,那就是将老一辈革命家形象搬上了戏剧舞台,象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毅、彭德怀,甚至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马克思、恩格斯等等,这不仅丰富了当代话剧艺术的人物画廊,而且还填补了中国话剧发展史上的空白。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广大剧作家在刻划这些为革命立下丰功伟绩、被人民忠心敬仰的领袖人物时,摒弃了“造神”,而倾力于“写人”——既突出他们作为革命家所具有的胸怀、品格、胆略,又揭示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生活情趣和喜怒哀乐,因而获得真切、感人的艺术效果。再有,八十年代的戏剧探索已不再满足于精细地描绘外部世界、表现生活的外在行动过程和人物的外部行为轨迹,而是将目光投向人的“内宇宙”,致力于人物内心世界丰富性、复杂性的开掘,着重表现特定情境下人物的情绪和心态。特别是人物内心外化、内心活动具象化等艺术手法的运用,使人物的感觉、想象、回忆、思考、闪念、欲望等等内心活动得以在舞台上形象地展现出来。象《路》一剧中,主人公周大楚内心矛盾时,舞台上就出现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人,作为矛盾着的另一个“自我”。修路工杨七贵想到“白衣姑娘”时,这位只是在七贵脑海中浮现的影象,竟也能出现在舞台上。象《绝对信号》、《桑树坪纪事》,人物的回忆与内心活动,都具体地在舞台上得以表演。其他一些剧作也是这样,主人公内心深处看不见、摸不着、猜不透的思维活动都化为视觉形象出现在舞台上,这不仅表达了当代剧作家对人物整体复杂性的评价与思考,而且也有助于读者、观众对人物内心隐秘世界作深入的窥探,当然也造就了当今戏剧舞台表现形式的多姿多采。
八十年代戏剧探索的主要特点,更多的还表现在舞台演出上。所谓的“赞叹不已”或“深恶痛绝”;或人们常说的“为之欣喜”或“为之叹惋”,往往都是在看了演出之后。的确,八十年代话剧表演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其广度与力度都是空前的。粗略审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破舞台界限,强化观演交流。进入八十年代,戏剧艺术陷入困境、遇到挑战。严峻的现实使戏剧家对这一艺术样式的本质特征、生态环境、竞争优势等等进行严肃、认真的反思。他们再次认同,所谓戏剧即是由演员扮演角色当众表演故事情节的一种艺术,演员、观众、剧本是构成戏剧的基本要素。因此戏剧要摆脱“危机”,尤其要在“三要素”中找原因、做文章。他们还认识到戏剧在现代社会中与姐妹艺术,如电影、电视相比有许多不利因素,但它也有自身特殊的优势,那就是观众与演员的现场直接交流。正如北京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是之说的,“比起电视、电影来,话剧是唯一的可以同观众一起创造的艺术。观众喜欢面对面地看到一个活人表演着一个活生生的性格”,“这种创作者与观众的活的交流,是剧场艺术独特的长处”。因此,八十年代的戏剧探索特别注意发挥戏剧自身的这一长处和优势。为了加强这种观众和演员的直接交流,有的戏剧家则对原有的剧场和舞台设计进行了某些改造,如《挂在墙上的老B》变台上演出为平地演出,将观众安排在演区跟前,演员与观众处在同一水平面上,拉近了空间的距离;《母亲的歌》、《路,在你我之间》则采用中心舞台形式演出,观众则围坐在舞台四周;《绝对信号》采取了在小剧场演出的形式,使观众和演员更加贴近。此外,还有的演员坐在观众席中,从观众席向台上对话,或从观众席走上舞台,这一切都最大限度地加强了演出的亲切感。又如《陈毅市长》,导演则致力于创造一种炽热的戏剧氛围,让观众产生一种亲临现场的感觉。演出一开始即让扮演陈毅的演员站在台口讲台上,直接面对观众做报告,仿佛观众席中坐着的就是即将对上海发起总攻的我军干部和战士,这就造成了一种“戏剧环境与现实环境的重迭”,强化了观演直接交流,使台上台下融为一体。再有,为了改变传统话剧台上演员演戏,台下观众看戏的关系,冲破“镜框式舞台”界限,启发观众的参与和思考,不少艺术家引进了文学的叙述因素,增添了叙述者,运用“间离效果”,破除“舞台幻觉”,强化观演交流,收到了感人的效果。象《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作者就专门设置了男、女两个叙述者,他们既在剧中扮演角色,又象晚会主持人那样从中串戏,连贯全剧,还夹叙夹议、画龙点睛,不断启发观众的思考。象《魔方》,也有个“主持人”,他时而在戏内,时而又离开戏剧情景,拿着话筒请观众即席发表感想,引导观众去思索演出中的人和事。又如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阿Q正传》一剧也设有一位“讲解人”,他不时地出现在台上, 或评价人物行为、或揭示内心世界,或介绍剧情发展、或感叹人物遭遇,时而将观众引入戏内,时而又将观众拉出戏外,这显然是对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的借鉴和运用。这种人物串演剧情与“间离效果”的巧妙结合,既增添了作品的哲理性与抒情性,又造成了剧作特有的艺术魅力。
第二,打破传统分幕、分场整一概念,扩大舞台时空领域。众所周知,戏剧艺术是显现有形事物一段相对完整的运动过程,它和生活本身一样是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中延伸,是典型的时空艺术,因而也必然受到舞台时空的制约。在这方面八十年代中国的戏剧家也作了不懈的努力。他们不满于为顺应这一制约而产生的所谓“时间整一、地点整一、事件整一”的剧作法,而试图借助于戏剧的假定性与想象力来扩大被制约的时空,努力把观众引导到更为广阔自由的情境中去。其具体做法为:一是突破传统戏剧四、五幕,二、三场的大段结构,而增加剧作的场次,使演出的时间、地点的变换加快,幅度扩大。象《迟开的花朵》演出时,场景更换就有十一次之多;象《原子与爱情》采取了大跨度(前后十五年)、多场景(近三十场)、大段回述的结构方式;象《血,总是热的》全剧共分十七段,完全打破分幕分场、场景集中、顺序发展的传统法则;象刘树纲改编的多场景舞台剧《灵与肉》,“试图打破传统的分幕分场和时空观念,在场景的变幻上要求有更大的跳动自由,全剧场景竟有好几十场”。就连老剧作家陈白尘改编的《阿Q正传》, 也一反传统剧作集中、凝聚的法则,而“向小说靠拢”,“依照原著的章节次序,大致不变地转换成多场景。”二是分割舞台、增加演区,扩大舞台空间,甚至几个演区同时表演,使时空更为经济。象《屋外有热流》用灯光处理、切割演区,使现在与过去,现实与梦幻,人与鬼魂,具象与抽象,做到变化自如、衔接流畅。象《血,总是热的》剧中的段落、场景的连接与转换都用灯光的明暗手段来实现,有的段落(如第十段)场景转换竟达十多次,有时戏还在三个演区同时进行。特别是《绝对信号》、《野人》、《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等剧作,充分运用了灯光切割的手段,使同一舞台出现时间与空间各不相同的多种表演区,使舞台的时空由固定变为流动、由狭小变为广阔、由单一变为多层次。正由于这种纵向的时间和横向的空间巧妙的交织变幻,充分利用戏剧的假定性,使看来简单的场景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层次来。三是学习西方现代派技法,借鉴中国传统戏曲假定性、虚拟性手段,不注重幻觉性时空的营造,而崇尚非幻觉性时空的运用。象戏剧舞台废除巨型、豪华、维肖维妙的自然主义布景,而代之以中性舞台的装饰,象用空台让演员表演;象在舞台上只安置高低不等的平台、积木块,结合表演指示情节空间;象用图案、文字来表示空间等等,这一切都使得舞台的表现力获得了极大的扩展。此外,角色心理时空形式的引入,即人物内心活动,诸如回忆、梦幻等在戏剧舞台上的直观展现,也极大地丰富了戏剧艺术的创造力。戏剧家可以根据人物心理状态及时地插入戏剧动作,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外化为可见的实体,而这一切又可以不必受到日常生活中事物发展的时空逻辑的束缚,而只要根据人物的意识流动或潜意识、无意识等活动方式来组合,因而享有更大的自由度。
第三,加强戏剧的综合意识,丰富话剧的表现手段。“戏剧是一种综合艺术”,这是中外戏剧家约定俗成的一种说法。因为从它的活动过程来看,是剧作家、导演、演员、舞台美术设计家、舞台各部门技术人员,剧场管理人员和观众共同创造的产物;从它的构成来说,又是文学、造型艺术、音乐及演员表演艺术等多种成分的综合。可以说综合性是戏剧艺术固有的天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古希腊的戏剧是诗歌、雕刻、合唱、舞蹈、动作的综合体,我国的传统戏曲更将歌、舞、杂技、滑稽、说唱等多种艺术门类融为一体。但是,不知何时、何故,中国话剧逐渐丢失了综合性的特点,最终竟成了“对话”主宰一切的艺术。这么一来,戏剧的面貌日益单一、板结,表现力也日趋衰竭。为了改变这种颓势,八十年代的中国戏剧工作者决心重新“捡回它近一个多世纪丧失了的许多艺术手法”,主张“原始宗教仪式中的面具、歌舞与民间说唱、耍嘴皮子的相声和拚气力的相扑,乃至傀儡、影子、魔术与杂技,都可以入戏。”(《高行健戏剧集》)因而使剧坛出现了熔歌、舞、诗、剧于一炉的发展态势。例如《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魔方》、《野人》以及《黑骏马》等剧就大胆地吸收并运用了音乐、舞蹈、电影、曲艺等艺术成分,作为自己的有机表现手段;又如沈阳话剧团的《搭错车》,演出上千场而盛况不衰,造成轰动效应,人们称之为“《搭错车》现象”,其重要原因之一则是他们充分重视、发挥戏剧“综合性”的特点,将歌、舞、话三者有机结合的结果。特别是《桑树坪纪事》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出戏之所以倍受欢迎与称赞,并被誉为“十年探索的崭新收获”,除了与剧本着力于对中国农民生态与心态的深入开掘,在艺术上“东张西望”、兼收并蓄有关外,也还与广大戏剧工作者强化戏剧综合意识,拓展话剧艺术表现力的追求分不开。剧本演出中,那身着鲜丽服装的现代舞队的“间离效果”以及“东方的巨龙何时才能猛醒”的主题歌的萦绕与渲染,不仅促人深思、启入遐想,而且还给这部作品增添了无穷的诗意与魅力。
八十年代的戏剧探索其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拓展了戏剧家、理论家想象的领域和思维的空间,而且还给整个剧坛带来了锐气和活力。它敢于突破固有的模式、敢于否定传统的法则,它逼迫这被视为“黄昏艺术”的戏剧在文化反思的氛围中去寻找自身现代的品格。它不仅以自身的实践告诉人们:话剧是什么样的,更重要的是还告诉人们:话剧可以不是什么样的。这显然有助于打破当今剧坛沉闷的局面,开拓话剧生存、发展的多样空间,丰富话剧艺术的表现力。这种勇于创新、勇于探索的精神理应受到崇敬和称赞。著名戏剧理论家陈恭敏对探索者们的这种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一是胆略:他们敢于面对‘危机’,探索出路,不抱残守阙,因袭陈规;敢于排除世俗偏见和庸人哲学。二是见识:他们从历史的呼唤中,意识到肩上的责任和使命。与时代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能对戏剧的现状作出清醒的判断,对发展的前景作出明智的抉择。三是才智:如果挑毛病的话,每部作品和每台演出,都可以找出许多缺点,但探索者们的最大优越之处,在于‘有我’。有我的思考和判断,有我的独创与想象……他们既善于借鉴,又善于消化,为我所用。”(《探索戏剧集·序》)这正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同志对八十年代戏剧探索价值、意义的整体认识。
八十年代戏剧探索的成就不仅仅只表现在那极可宝贵的探索精神上,这当然是我们时代的骄傲与财富,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保证;而且还表现在这种探索所取得的具体实绩上。以上列举的探索戏剧,它们不仅为中国戏剧的发展探索了新路,而且还为中国当代文坛增添了光彩。特别象锦云的《狗儿爷涅槃》、李龙云的《洒满月光的荒原》、陈子度等的《桑树坪纪事》等剧本的创作与演出,不仅标志着八十年代中国戏剧探索已经走向成熟,也不仅标志着写实与写意、再现与表现、戏剧性与叙述性、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制造生活幻觉与破除生活幻觉等等,已不再是水火不容、互相排斥、永远对立的东西了,而且还标志着和谐的多元并存的格局、良性的综合、兼容的动向,由此带来的开创性、丰富性与深刻性,正为处于困境的中国话剧迎来希望的曙光。
但是,八十年代戏剧探索的缺点与不足也是明显的。1989年8 月《中国文化报》上曾有一篇文章这样指出:“几年过去了,各种各样的探索性话剧也出现不少,形式多样:荒诞派、先锋派、生活派、意识流;哲理戏剧、贫困戏剧;存在主义、未来主义;散文式结构、情绪辐射式结构等,令人眼花缭乱。然而,话剧在总体上的危机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观。究其原因,我以为主要是这种探索相当多地是一种自我表现,是少数人能够欣赏的艺术,是在沙龙里的探索。因为“‘新潮’话剧的出发点往往是‘表现自我’,很少涉及到它的审美对象——广大观众。‘新潮’话剧不少是照搬西方人的‘玩话剧’,大多数中国观众对此因看不懂而难以接受”(《话剧——走出沙龙的误区》)。这篇文章的某些观点、提法不够周全,似可商榷,但所揭示的现象,即八十年代的戏剧探索未能使中国话剧摆脱“危机”;所总结的戏剧探索的不足:一是生硬照搬西方的经验,二是忽视中国百姓的需求,倒是言之成理,说到了问题的要害。我们发现在八十年代戏剧探索热潮中,有的剧作家或多或少存在着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误解,或将现实主义与公式化、概念化等同,或视传统手法、形式为陈腐、僵化的同义词,甚至认为,斯坦尼——易卜生模式在中国已经走到了尽头,于是更乐意于向现实主义之外的现代主义寻求出路。而就在这寻求过程中又存在着“生吞活剥”、“消化不良”的现象。有的作家刚从生活中发现一点小素材、遇到一阵小挫折、萌发起一丝小感触,还没来得及寻找到自身独特的体验与感悟,更没能挖掘客观现象的底蕴与意义,便匆忙地套用西方现代主义的技法,将这一切搬上了舞台,其直接后果便是造成剧作形式上的创新与内容的单薄的反差。这不仅无助于克服“危机”,而且还冷淡、疏远、甚至吓跑了观众。此外,理论上的偏颇与误导多少也影响了戏剧探索成就的取得,并直接导致当代话剧始终未能摆脱“危机”阴影的缠绕。长期以来,戏剧被认为是极富“群众性”的艺术,但是,随着电影的发展,特别是电视的普及,戏剧这一“群众性”的优势越来越受到冲击与挑战。为此有人提出:戏剧既然在文化消费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不妨干脆把“群众性”这项桂冠拱手相让,而以“少数人的艺术”自满自足。于是乎理论界亦大谈所谓的“高雅艺术”、“精英艺术”等等,认为戏剧不必在争取广大普通观众上煞费苦心,而应在大城市品位高的知识阶层中寻觅知音。甚至鼓励戏剧探索可以淡化主题、淡化情节、淡化人物,可以忽视大众的趣味和习惯,而去单纯追求多元化的审美效应、多变性的戏剧结构,多层次的舞台时空,多声部的演出效果;鼓励作家去挖掘、表现深邃的哲理、去努力发现自我、表现自我。这种远离国情、脱离本土、不顾客观现状,无视审美对象的理论误导,其后果只能使本来就“门庭冷落车马稀”的剧院变得更加萧条、凄清了。
美国著名美学家桑塔耶那曾经说过:“一千种创新里,九百九十九种都是无才的制作,只有一种是天才的产物。因为在美的追求中,正如在真的追求中一样,有无数的途径通向失败,只有一条道路通向成功。”(《美感》)如果对这段话的含义不作机械的理解的话,它倒是道出了艺术探索的艰辛。的确,勇于探索的戏剧家是令人敬佩的戏剧家,却不一定是成功的戏剧家。探索是求得成功的手段,甚至是必备的手段,但是探索之于成功的概率是很小的。失败的探索是由于为后来者提供了引以为戒的经验而获得价值和意义。从这一点认识出发,笔者以为评价八十年代的戏剧探索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只要探索者从繁荣中国社会主义话剧的总体目标出发,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主动调整探索的方位和步伐,不固执、不懈怠,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成也英雄,败也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