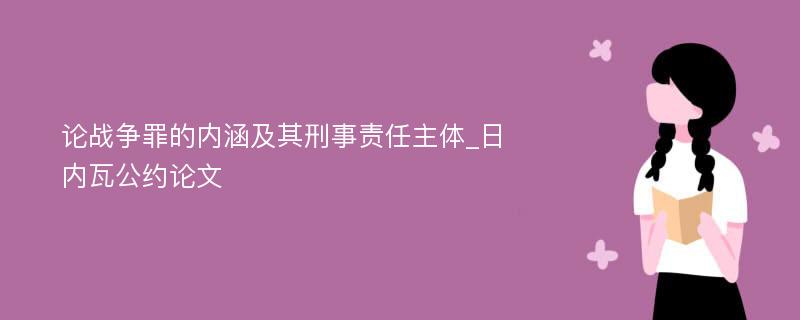
论战争罪之内涵及其刑事责任主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刑事责任论文,内涵论文,主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 (2001)02—0013—09
战争对人们来讲并非陌生的概念,甚至早在原始部落或集团之间便存在着仇杀或复仇的行为——原始人的战争。著名的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勃郎在描绘原始澳大利亚人之间的战争时指出:“在某些共同体中,如在澳大利亚游牧部落中,进行战争通常是由一个集团对应向所遭受的伤害负责的另一集团所实行的一种复仇行为,而其程序则由等于现代国家的国际法的一批公认的习惯来加以调整。”[1](P368)
国际法理论关于战争的认识主要有三种:一是认为应予以系统地谴责;二是认为应毫无保留地对战争大加赞赏;三是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战争是一种必要的坏事。对国家社会主义学派的作者来说,战争是一种高于法律的现象;对许多实证主义作者来说,战争是一种处于法律范围之外的现象[2](P11-12)。但是,自1928年8月27日美国、德国、比利时、法国、意大利、日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包括英联邦7个国家)等15个国家在巴黎签订了非战公约——《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又称白里安——凯洛格条约或巴黎条约)后,在国际法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则认为,战争是一种与法律相违背的现象。战争的主要特点是,它既不是超法律的,也不是在法律之外的,而实在是违反法律的(注:但是,在国际法关于正义战争的理论中,通常将《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1919年的《凡尔塞条约》和1919年的《国际联盟盟约》视为是国际法关于正义战争的重要法律文件。其理由是从该3个法律文本的有关规定中得出的结论。)。
特别是近代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仅没有达到战争发动者所欲追求的结果,反而进一步暴露了战争的残酷性,也发展了涉及战争行为的国际法律文件,以及对战争犯罪的国际刑事审判。1919 年6月28日《凡尔塞条约》第27条成为建立国际特设刑事法庭,审判德国凯萨·威廉二世、德国战犯,以及实施“违反人道主义法罪行”的土耳其官员的法律依据。虽然对凯萨·威廉二世和战犯们的审判最终化为泡影,但战争罪在国际法理论上和司法实务中被广泛认可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一、涉及战争罪的国际法律文件
自1854年7月22 日美国和苏联在华盛顿签署了《关于海上中立权公约》(该公约对战争行为不具有刑事罚则的特征),至1998年7 月罗马国际外交代表大会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明确界定了战争犯罪的概念及法院的刑事管辖权),目前国际社会共有70多个相关法律文件包含了战争行为或战争罪的内容。而且,自1868年到1998年,依据划分罪行类别的方法,另有30多个法律文件可适用于战争罪,如1949年8 月12日在日内瓦签订的《关于战时平民保护的日内瓦公约》。
考察所有关于国际犯罪的法律文件,包含着战争犯罪的禁止性规定或规则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且规定的内容也较为详尽,其中还包括违反这些规定或规则将受到起诉和处罚的具体内容,如1945年8月8日在伦敦签署的《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又称《伦敦宪章》),以及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都具有明确的刑事处罚特征(注:《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6 条规定:“……对此等犯罪,犯人应负其个人责任……战争罪,是指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此种违反包括谋杀。为奴役或为其他目的而……凡参与犯上述任何一种犯罪之共同计划或阴谋之决定或执行之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与共犯者,对于执行此种计划之任何人所实施之一切行为,均应负责。”)。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涉及战争犯罪的法律文件大多由习惯国际法所涵盖,并成为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如1899年7月29 日第一届海牙和平会议第二公约《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公约》、《关于陆战法规和陆战习惯的规则》;1907年10月18日第二届海牙和平会议《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的公约》、《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规则》。在国际刑法的历史上,虽然这些禁令的施行仅涉及战争罪的有关问题,且并非统一或一致,但已成为起诉和惩治战争犯罪之违法者最可靠的根据。
从规定战争罪的国际公约或法律文件来看,1949年的四个日内瓦公约(注:1949年8月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分别为:《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难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关于战浮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及其两个附加议定书(注:1949年8 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的两个附加议定书分别为:《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二议定书)。)的规则或规章是可适用于战争犯罪的最明确、广泛和综合的法律文本。之所以将“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视为关于战争罪较为详尽的一般性规定,是因为“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不仅吸纳了“海牙公约”(注:《海牙公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其一,1899年7月29 日第一届国际和平会议形成的以下公约及宣言:《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陆战法规和习惯公约》、《关于1864年8月22 日日内瓦公约原则适用于海战的公约》、《禁止从气球上或其他新的类似方法投掷投射物和爆炸物宣言》、《禁止使用专用于散布窒息性或有毒气体的投射物的宣言》、《禁止使用在人体内易于膨胀或变扁的投射物,如外壳坚硬而未能全部包住弹心或外壳上刻有裂纹的子弹的宣言》;其二,1907年10月18日第二届国际和平回应形成的以下公约和宣言:《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限制使用武力以索偿契约债务公约》、《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的公约》、《中立国家和人民在陆战时的权利和义务公约》、《关于战争开始时敌国商船地位公约》、《关于商船改造为军舰公约》、《关于敷设自动触发水雷公约》、《关于战争海军轰击公约》、《关于日内瓦公约原则适用于海战的公约》、《关于对海战中行使拿捕权的某些限制的公约》、《关于建立国际捕获法院公约》、《关于中立国在海战中的权利和义务公约》、《禁止从气球上投掷投射物和爆炸物宣言》。)构建的规范内容,还弥补了“海牙公约”内容上的缺失,因而“日内瓦法规”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国际惯例。
通过多年来对国际犯罪行为(其中包含了战争罪)相关问题的摸索,可见原有那些涉及国际犯罪行为的国际公约基本不含有刑罚特征,而现在的国际公约已逐步发展为详尽规定刑罚适用中的有关问题,如根据《伦敦宪章》建立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所确立的个人刑事责任原则,现已成为广泛使用的“纽伦堡原则”(注:“纽伦堡原则”,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全体一致确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险症及该法庭判决书中所包含的国际法原则(即纽伦堡原则),”并于通过该原则,其内容如下:其一,任何人凡从事构成国际法上的犯罪行为者,应对此行为负责并受到处罚;其二,国内法对构成国际法上的犯罪行为不处以刑罚的事实,不能免除从事该行为的人在国际法上的责任;其三,从事构成国际法上犯罪行为的人是作为国家元首或政府负责官员而采取行动的事实,不能免除其在国际法上的责任;其四,根据政府或上级命令采取行动的事实,如属此人实际上可能进行道义上的选择者,不能免除其在国际法上的责任;其五,任何人由于犯了国际法上的罪行而被追究刑事责任时,有权受到依据事实和法律的公正审判;其六,以下规定的罪行应作为国际法上的罪行受到处罚……乙、战争罪,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其七,犯有原则六所规定的反和平罪、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的共犯,是国际法上的犯罪。)。特别是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国际罪行法典草案》,明显地体现了国际公约所具有的刑罚特征,即:(1)构成国际罪行禁止性行为的明确规定,或依照国际法构成的国际犯罪;(2)通过确立禁止、预防、起诉和惩罚,及类似的义务,来间接认可行为的刑罚性;(3)禁止性行为的犯罪化;(4)起诉的义务;(5)惩罚实施禁止性行为的义务;(6)引渡的义务;(7)在起诉、惩罚(包括刑事诉讼程序的司法协助)方面的合作义务;(8 )刑事管辖根据的建立(刑事管辖的理论或刑事管辖的优先);(9 )论及具有刑罚特征(或者特权法院)的国际刑事法院或国际刑事法庭的建立;(10)取消上级命令的辩护理由[3]。
最后,上述关于战争罪的习惯国际法、公约及附加议定书所规定的原则或规则,不仅在以后的国际刑事法庭规约中有所体现,而且在国际刑事司法实践中都加以具体地运用。无论是针对国际性的武装冲突(如前南斯拉夫境内发生的冲突即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还是针对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如卢旺达境内发生的武装冲突),均可通过国际特设刑事法庭(前南斯拉夫国际特设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特设法庭)以及常设国际刑事法院按照国际规约的规定,将这种性质的犯罪作为国际性刑事法庭的管辖罪行。
二、战争罪的内涵
战争罪被认为是由强制性法律规范调整的一种犯罪[4]。 所谓“强制性法律规范”(或绝对法Jus Cogens),是指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允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5]。著名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教授认为, “强制性法律规范”的适用是那些义务的遵循,而不是选择权利的使用,否则“强制性法律规范”不可能构成国际法的绝对规则,因而“强制性法律规范”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都是不容贬损的。将某种国际犯罪的含义视为“强制性法律规范”调整的一部分,就是履行或引渡或起诉的义务;对某些罪行不适用诉讼时效法规;对某些犯罪无论于何地实施或何者实施(包括国家元首),被害人是谁,以及行为实施的背景如何(战时还是平时),均应适用普遍管辖原则。上述某些犯罪的特征作为“强制性法律规范”调整的一部分,对那些违反置于国家各项义务者均不享受豁免权[6]。
从战争罪应受“强制性法律规范”调整的这一事实分析,可见战争罪在国际法治发展历程中所受的重视程度。早在1854年的《关于海上中立权的公约》中就已涉及战争行为,但国际社会公认战争行为是一种国际性犯罪,并赋予其明确的内涵,则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两届和平会议虽然就战争行为制定了较为详尽的规则或章程,但关于战争罪的刑罚性全面、清晰的规定,应当说是在1949年的日内瓦四公约及其两个附加议定书的战争罪适用规章和规则中得以明显体现,然而遗憾的是,战争罪的内涵并未得到明确。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特设军事法庭,如纽伦堡军事法庭和远东军事法庭分别在其章程中将战争罪定义为:“战争罪,系指违反战争法规或战争习惯的罪行。这种违反包括(但不限于):屠杀或虐待占领区平民,或以奴隶劳动为目的、或为其他任何某种目的而将平民从被占领区或在被占领区内放逐,屠杀或虐待战俘或海上人员,杀害人质,掠夺公私财产,恣意破坏城镇乡村,或任何非属军事必要而进行破坏”;“普通战争犯罪,是指违反战争法规或战争惯例之犯罪行为。”著名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教授认为:“战争罪,是指在国际协约中规定的适用于武装冲突的规则,以及普遍认可的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所禁止的作为或不作为。”[7]无论是两个国际特设法庭所界定的战争罪,还是学者所理解的战争罪,其本质都是将违反战争法规或战争惯例的行为视为战争罪。
由国际法委员会起草的1998年《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将先前战争罪的笼统表述改为详尽的说明,战争罪是违反有关具体战争法规或战争惯例,以及战争行为的客观具体行为,即:“战争罪,是指:第一,严重破坏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公约》的行为, 即对有关的《日内瓦公约》规定保护的人或财产实施下列任何一种行为:(1)故意杀害;(2)酷刑或不人道待遇,包括生物学实验;(3 )故意使身体或健康遭受重大痛苦或严重伤害;(4)无军事上的必要, 非法和恣意地广泛破坏和侵占财产;(5)强迫战俘或其他被保护人在敌国部队中服役;(6)故意剥夺战俘或其他被保护人应享有的公允及合法审判的权利;(7 )非法驱逐出境或迁徙或非法禁闭;(8)劫持人质。第二, 严重违反国际法既定范围内适用于国际武装冲突的法规和惯例的其他行为,即下列任何一种行为:(1 )故意指令攻击平民人口本身或未直接参建敌对行动的个别平民;(2)故意指令攻击民用物体,即非军事目标的物体;(3)故意指令攻击依照《联合国宪章》执行的人道主义援助或维持和平行动的所涉人员、设施、物资、单位或车辆,如果这些人员和物体有权得到武装冲突国际法规给予平民和民用物体的保护;(4 )故意发动攻击,明知这种攻击将附带造成平民伤亡或破坏民用物体或致使自然环境遭受广泛、长期和严重的破坏,其程度与预期得到的具体和直接的整体军事利益相比显然是过分的;(5 )以任何手段攻击或轰击非军事目标的不设防城镇、村庄、住所或建筑物;(6)杀、 伤已经放下武器或丧失自卫能力并已无条件投降的战斗员;(7)不当使用休战旗、 敌方或联合国旗帜或军事标志和制服,以及《日内瓦公约》所订特殊标志,致使人员死亡或重伤:(8 )占领国将部分本国平民人口间接或直接迁移到其占领的领土,或将被占领领土的全部或部分人口驱逐或迁移到被占领领土内或外的地方;(9)故意指令攻击专用于宗教、教育、艺术、 科学或慈善事业的建筑物、历史纪念物、医院和伤病人员收容所,除非这些地方是军事目标;(10)致使在敌方权力下的人员肢体遭受残伤,或对其进行任何种类的医学或科学实验,而这些实验既不具有医学、牙医学或住院治疗有关人员的理由,也不是为了该人员的利益而进行的,并且导致这些人员死亡或严重危及其健康;(11)以背信弃义的方式杀、伤属于敌国或敌军的人员;(12)宣告决不纳降;(13)摧毁或没收敌方财产,除非是基于战争的必要;(14)宣布取消、停止敌方国民的权利和诉讼权,或在法院中不予执行;(16)抢劫即使是突击攻下的城镇或地方;(17)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18)使用窒息性、有毒或其他气体,以及所有类似的液体、物质或器件;(19)使用在人体内易于膨胀或变扁的子弹,如外壳坚硬而不完全包裹弹芯或外壳经切穿的子弹;(20)违反武装冲突国际法规,使用具有造成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的性质,或基本上为滥杀、滥伤的武器、弹药、装备和作战方法,但这些武器、射弹、装备和作战方法应当已被全面禁止,并已依照第121条和第123条的有关规定以一项修正案的形式列入本规约的一项附件内;(21)损害个人尊严,特别是侮辱性和有辱人格的待遇;(22)强奸、性奴役、强迫卖淫、第7条第2款第6项所界定的强迫怀孕、 强迫绝育或构成严重破坏《日内瓦公约》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性暴力;(23)将平民或其他被保护人置于某些地点、地区或军事部队,利用其存在使该地点、地区或军事部队免受军事攻击;(24)故意指令攻击依照国际法使用《日内瓦公约》所订特殊标志的建筑物、装备、医疗单位和运输工具及人员;(25)故意以断绝平民粮食作为战争方法,使平民无法取得其生存所必需的物品,包括故意阻碍根据《日内瓦公约》规定提供救济物品;(26)征募不满15岁的儿童加入国家武装部队,或利用他们积极参与敌对行动。第三,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严重违反1949年8月12 日四项《日内瓦公约》共同第三条的行为,即对不实际参加敌对行动的人,包括已经放下武器的武装部队人员,及因病、伤、拘留或任何其他原因而失去战斗力的人员,实施下列任何一种行为:(1)对生命与人身施以暴力,特别是各种谋杀、残伤肢体、虐待及酷刑;(2)损害个人尊严,特别是侮辱性和有辱人格的待遇;(3)劫持人质;(4)未经具有公认为必需的司法保障的正规组织的法庭宣判,径行判罪和处决。第四,第2款第3项适用于非国际武装冲突,因此不适用于内部动乱和紧张局势,如暴动、孤立和零星的暴力行为或其他性质相同的行为。第五,严重违反国际法既定范围内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规和惯例的其他行为,即下列任何一种行为。(1 )故意指令攻击平民人口本身或未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个别平民;(2 )故意指令攻击按照国际法使用《日内瓦公约》所订特殊标志的建筑物、装备、医疗单位和运输工具及人员; (3)故意指令攻击依照《联合国宪章》执行的人道主义援助或维持和平行动的所涉人员、设施、物资、单位或车辆,如果这些人员和物体有权得到武装冲突法规给予平民和民用物体的保护;(4 )故意指令攻击专用于宗教、教育、艺术、科学或慈善事业的建筑物、历史纪念物、医院和伤病人员收容所,除非这些地方是军事目标;(5 )抢劫即使是突击攻下的城镇或地方;(6)强奸、性奴役、强迫卖淫、第七条第2款第6 项所界定的强迫怀孕、强迫绝育以及构成严重违反四项《日内瓦公约》共同第三条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性暴力;(7 )征募不满十五岁的儿童加入武装部队或集团,或利用他们积极参加敌对行动;(8 )基于与冲突有关的理由下令平民人口迁移,但因所涉平民的安全或因迫切的军事理由而有需要的除外;(9)以背信弃义的方式杀、伤属敌方战斗员; (10)宣告决不纳降;(11)致使在冲突另一方权力下的人员肢体遭受残伤,或对其进行任何种类的医学或科学实验,而这些实验既不具有医学、牙医学或住院治疗有关人员的理由,也不是为了该人员的利益而进行的,并且导致这些人员死亡或严重危及其健康;(12)摧毁或没收敌对方的财产,除非是基于冲突的必要。第六,第2款第5项适用于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因此不适用于内部动乱和紧张局势,如暴动、孤立和零星的暴力行为或其他性质相同的行为。该项规定适用于在一国境内发生的武装冲突,如果政府当局与有组织武装集团之间,或这种集团相互之间长期进行武装冲突。”[8]
从形式上看,《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设置战争罪的概念似乎颇为冗长,缺乏概念本身的精练要求。但这种规定方式的优势在于突出了追究战争罪犯刑事责任的可操作性,特别是针对国际社会中多元国家、多种法系并存,以及各国刑事司法活动各不相同的特性。《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关于战争罪的详尽规定囊括了各种涉及战争犯罪国际公约、国际法理论和国际上审判战犯的经验,如此规定既可以满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遵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同时,又能使国际或国内的刑事审判机构在审理有关战争罪案件时,可以直接援引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规定内容。就目前而言,这一规定基本上缓解了国际社会惩治战争犯罪的当务之急。
从国际犯罪角度看,国际公约、条约等国际性法律文件所罗列的25种国际性犯罪,无论其实施的方式如何,但其所造成的结果都在不同程度上危害着人类。特别是侵略罪、危害人类罪、种族灭绝罪等残酷、野蛮违反人道主义法的国际犯罪,其犯罪行为特征和客观危害结果都与战争罪具有一定的重合性。而《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对战争罪的繁缛规定,则是辨别这些相近犯罪的最好方式,同时更有利于准确适用国际刑事法律规范,正确定罪和公正审判。
三、战争罪的刑事责任主体
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对刑事责任主体范围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分歧,这一问题在国内法中的反映最为明显,国家不能将由自己组成部分之一制定的禁止性法律规范施加于其整体之上(注:国家的存在必须有四个方面:一是人民;二是领土;三是政府——要求有一个或更多人为人民并且按照本国的法律进行统治;四是主权(参见:[英]詹宁斯、瓦茨修订,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际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如果政府用国家制定的强制性法律作用于国家的身上,只能说明国家制定的法律缺陷甚大,或国家只是一个非完全主权的国家。),否则刑事管辖权的行使将产生困惑;在国际法中,如果通过国际性审判机构(直接的实现方式)实现国际刑事责任(注:在1998年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上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之前,国际社会已经尝试性地建立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也主要是追究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但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对德国、日本、意大利国家所采取的制裁能否理解为是国际社会对该三个国家所实施的战争罪行的结果承担的国际刑事责任,这个问题虽然至今仍有争议,但我们认为,国际刑事责任的具体内容与国家法律规范所确定的刑事责任的内容是不同的,国际刑事责任如同国内的刑罚种类只能通过惩罚个人才能体现出来,对于国家的惩罚,国际性的法律制裁或经济制裁,也可理解为是国际刑事责任的内容之一,这种刑罚方法也可以理解为如同国内刑罚体系中的罚金或没收财产一样的作用。),确认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尚可以探讨;如果国际刑事责任是通过各个国内的刑事司法系统来实现(间接的实现方式),则同样会遇到刑事管理权行使上的难题。其次,就团体或组织的刑事责任来说,国际刑法和国内刑法存有不同的认识,各法系与各主权国家之间亦有不同的见解。在国内法体系中,刑事责任的承担已由单一的个人刑事责任向“法人”或“单位”等组织、团体延展,而且已经成为刑事法律发展的一种新趋向(注:现代国内立法中有关于“有组织犯罪(organized crimes)”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规定(参见《意大利刑法典》犯罪之结社,第416-418条;颠覆之结社,第270条;黑手党之结社,第416条。参见《法国刑法典》第265-267条)。我国刑法不仅在刑法总则第30条明确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我国刑法在分则规定的具体罪名和刑事责任上也体现了单位、组织的刑事责任条款,如第191条规定的洗钱罪、第151条规定的走私核材料罪等。);在国际法领域中,认定组织或团体的刑事责任,虽然曾在个别场合中有所体现,但却未能像个人刑事责任原则那样得到广泛的认可。由此可见,无论是历史的法律规范还是现代的法律规范(注:依照古罗马——民法的法律体系, 法律实体(les personalities morales)是不能承担刑事责任的,只有个人才可以。),不管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注:在国际刑事法律规范中规定个人刑事责任的款项比较普遍,自1907年的《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的海牙公约》明确指出该公约适用于居民和交战者个人时起,国际社会惩治个人国际犯罪行为便有了法律依据。至1945年的纽伦堡审判,正式确立了个人刑事责任原则,1998年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将个人刑事责任原则予以法典化。),对于追究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都毫无争议。故本文将团体、组织以及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作为主要探讨的对象。
(一)团体或组织战争罪的国际刑事责任主体。
在国际刑法理论中,关于团体或组织刑事责任的研究发展得较为迟缓。从上述战争罪内涵中可见,战争罪明显属于一种带有组织性或团体性的国际犯罪,这种犯罪组织或团体不可能是由若干人临时性纠合在一起的犯罪团伙,而是由具有共同犯意的多元个体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这种团体或组织实施的国际犯罪行为,其恶劣性和危害程度远远超出个人实施的国际犯罪行为,更应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国际军事法庭在比较犯罪团体或组织与阴谋集团时指出,犯罪组织是具有严密结合在一起的,并为某一共同的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团体,且该团体的形成或对其适用法律必须与宪章规定的罪行有关,战争罪即是与宪章相关的罪行之一。
目前,虽然国际刑法理论尚未认同团体或组织实施战争罪应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在国际社会的司法实务中已逐步认识到团体或组织的犯罪性。特别是德国的纳粹党政治领袖集团、秘密警察、党卫队保安勤务处、冲锋队、党卫队、德国内阁、以及参谋总部和德国国防最高统帅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施的种种暴行,足以表明有组织犯罪的危害性。为此,《纽伦堡宪章》第9条和第10 条分别规定:“在对任何集团或组织的个别成员进行审判时,法庭可以(在被告被判决与该集团或组织的任何行为有联系的情况下)宣布被告所属的集团和组织为犯罪组织”;“如果某一集团或组织被法庭宣布为犯罪组织,任何签字国的国家主管当局均有权将从属于某一此类犯罪组织的人员交付其国家法庭、军事法庭或占领区法庭提出诉讼。在此类情况下,该集团或组织的犯罪性质应被认为已经证实,而不应有所异议。”依照《纽伦堡宪章》的规定宣告上述犯罪组织的有效性,在德国管制委员会第10号法案(
Control Council Law No.10)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说明:“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均为犯罪:……(一)凡参与经国际军事法庭宣告为犯罪的犯罪集团或组织的成员。……三、任何经判定有上述罪行之一者,可于定罪后判以法庭认为公正的刑罚。……。”[9]
需要说明的是,《纽伦堡宪章》强调了团体或组织的犯罪性质,同时强调个人对组织犯罪所应承担的责任。如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明确指出:“经法庭宣告有罪的某一组织成员,以后可因其以该组织成员身份所犯的罪行进行判决,并可因此被判处死刑。”[10](P225)那么,被宣告为犯罪集团或组织中的所有成员是否都应无一例外地承担刑事责任呢?仅仅凭借某一个人是否具备组织成员的身份,或者对组织犯罪性质处于不明知的情况下,而要求其承担个人刑事责任是否有失公平呢?国际军事法庭在审判过程中,将犯罪集团或组织定义为:“宣告犯罪组织和集团性质将决定于它的成员的犯罪性质,因此,宣告集团或组织的犯罪性质时,应不包括那些对该组织的犯罪目的或犯罪行为并不知情的人,也不包括被国家吸收为各该组织的人,但如果以各该组织成员的身份参与本条第6条所规定的犯罪行为的人除外, 单凭成员资格并不足以被列入法庭宣告之列。”[10](P226)
因此,如何认定组织或团体实施战争行为的犯罪性质,怎样透过团体或组织的外衣使有罪者接受恰当的刑罚,使无罪者避免承担组织犯罪的集体刑罚,《纽伦堡宪章》第9条规定的“法庭可以宣告……”方式,恰如其分地解决了个人与组织有罪性和可罚性的问题。该规定强调法庭是否宣告一个组织为犯罪组织,应依照公允原则进行判断,而这种判断过程便是司法的职责。如果法庭确信一个组织或集团犯有应受处罚的罪责,那么法庭诀不会因为“集团犯罪”概念属于新的理论,或者因为这种理论可能被以后的法庭不公正地使用,而对宣告该组织或集团为犯罪组织有所迟疑;另一方面,法庭在宣告一个组织具有犯罪性质时,应尽可能保证无罪的人不受惩罚[10](P225)。事实上,国际军事法庭在确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及组织或团体的犯罪性质时,要求既有以个人身份实施的犯罪行为,也要求其明知自己是实施犯罪行为组织中的成员。如果法庭仅仅根据某一个体在组织中的成员身份,而强加其国际刑事责任,不仅延伸了大部分法律体系中已被普遍接受的刑事责任原则,而且易于招致大多数法律体系反对将单纯结伙认定为犯罪的这种不公正的现象。
最后,由于战争罪具有明显的组织性和团体性的特征,故而需要国际社会进一步探讨是否有必要构建组织或团体国际刑事责任的理论。假设可以将组织或团体理解为介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一种集体形式,那么,团体或组织的刑事责任则既可以由组成该集体的若干个人分担刑事责任的实体,也可以由授权其成立的国家代为承担宣告式的罪责,如果这样,则没有必要确立团体或组织的国际刑事责任。但是,就团体或组织与国家的关系来讲,其成立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国家授权成立的团体或组织,完全执行国家的政策,没有自我的决策权。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宣告组织或团体有罪,首先,其刑事责任的实体仍由个人承担;其次,作为国家授权的团体或组织,也只是替代国家的刑事责任,如果将组织或团体的罪和责分别由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和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分担,则没有必要建立组织或团体的刑事责任。二是该组织或团体非经国家特殊授权,依照本国法律成立的组织或团体,该组织执行自己机构的决策,实施了危害国际社会的行为,如跨国环境污染(污染转嫁)构成环境犯罪时,该组织或团体、法人除承担组织或团体、法人的刑事责任外,其决策者和执行者也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由此可见,团体或组织的国际刑事责任不仅不能为个人刑事责任理论所替代,而且不能包含在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之内。只要国际社会存在一种法人、团体或组织应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可能性,就非常有必要于国际刑法理论中探讨确立法人、团体或组织的国际刑事责任问题。
此外,国内刑法或国际刑法通过对团体、组织或国家这种法律意义上“拟制人”违反刑事法律规范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恰好弥补了传统个人刑事责任理论滞后于国际社会惩治犯罪的需求,以及追究国际的刑事责任上的不足(注:在国际犯罪的诸多种类中,不乏一些以抽象的实体——团体或组织、国家的名义,或者为了这些抽象实体的利益,或者为分享该这些抽象实体的利益而通过个人的行为实施的危害国际社会的结果。)。
(二)国家战争罪的国际刑事责任主体。
1907年的《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的海牙公约》第3 条规定:“一个国家应为它的武装部队的一切行为担负责任。”1912年11月11日国际常设仲裁法院在制作土耳其对俄国的战争赔偿案的裁决中表达方式是,战争构成“一个国际行为”即一个国家间的行为(仍有分歧)。从战争罪的定义上分析,战争罪不仅仅具有其客观的要素——在国家间存在着武装斗争;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冲突中国家的意志产生的结果。1987年国际法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治罪法草案》第3 条规定:“对犯有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的个人进行追诉,并不免除一个国家对归因于它的某一作为或不作为依国际法应负的任何责任。”
在论及国家战争罪的刑事责任以前,应首先明确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正如卢梭所说:“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一瞬间,这一结合行为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组成共同体的成员数目就等于大会中所有的票数,而共同体就以这同一个行为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而以之和它的同类相比较时,则称它为政权。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就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但是这些名词往往互相混淆,彼此通用;只要我们在以其完全的精确性使用它们时,知道加以区别就够了。”[11]( P25-26)由国家与国民之间概念的界定上看,国家是一种集合性概念;同时,国家作为当代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承受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又是国际法的主要主体(注: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是从国家的法律性质本身产生出来的,意思是说,国家本身就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在它的上面再没有任何最高机关。参见[苏]柯热夫尼科夫:《国际法上的主体问题》,载《现代国际法上的基本原则和问题》(国际法论文集第一集),法律出版社1956年版,第67页。)。是国际社会中直接、独立和全面地参加国际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社会等关系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实体[12](P65)。国际法为国家设定义务的事实, 实质上与国家对违反这些义务而在法律上负责的事实是联系的。如果国家因为主管机关没有按国际法所规定的那样行为,或者是如果国家违反了国际法,那么,国际法所规定的制裁并不是针对以国家机关资格负有义务应这样行为但却未这样行为的个人[13](P389)。
透过国际刑事法律规范(国际公约、条约涉及刑事罚则部分的内容,以及罪行法典草案)所列举的25种国际性犯罪(注:1996年统计的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国际犯罪的种类为:侵略罪,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危害联合国及其相关人员的犯罪,非法持有、使用武器罪,核材料犯罪,充当外国雇佣兵罪,种族隔离罪,奴役及与奴役相关的犯罪,酷刑及其他残酷方式的犯罪,非法进行人体实验罪,海盗罪,劫持航空器和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的犯罪,危害航海和公海平台安全犯罪,威胁和使用武力危害国际被保护人员的犯罪,劫持人质罪,破坏国际邮政秩序罪,国际贩卖毒品及与毒品相关的犯罪,毁坏兼及偷盗国家珍贵文物罪,危害环境的犯罪,国际贩卖淫秽出版物罪,伪造、仿造货币罪,非法干扰国际海底电缆罪,贿赂外国官员罪。)分析,有些罪行明显为国家或国家政策驱使的结果,战争罪即为其中一种。正如卢梭所指出的:“战争绝不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而是国与国的一种关系,在战争之中,个人与个人绝不是以人的资格,而是以公民的资格,才偶然成为仇敌的;他们绝不是作为国家的成员,而只是作为国家的保卫者。”[11](P18)著名国际法学家奥本海将国家刑事责任与个人刑事责任之间的关系表述为:国家的刑事责任是附加于违反国际法实施犯罪行为的个人所担负的国际刑事责任之上,而并不排斥个人所担负的国际刑事责任(注:奥本海认为,个人并不单纯以权利享受者作为国际法的主体。他们也必须承担国际义务,他们不仅在特殊情况下为充当封锁破坏者、海盗或战犯时,承担国际义务,而且更一般地以国家机关的资格承担国际义务。现代把个人视为国际法主体的倾向并不等于片面地强调个人享受国际法所产生的权利相等同。同时,明显的是,除非国家的刑事责任在法律上成为毫无意义,否则国家刑事责任必须交给有政治组织的国际社会的公正国际机构去执行。参见[英]詹宁斯、瓦茨修订,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际法》(第1卷,第1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9页。)。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战犯期间,苏联首席起诉人R.A.卢登科在其总结性发言中指出:“在当前情况下,不只希特勒的国家破坏了国际法的准则,从而导致了对某些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具体的个人也破坏了国际法的准则,由于他们所干的这些破坏行为,他们也犯了个人应受惩罚的罪行,根据法庭条例,他们在国际军事法庭上对这些罪行负有责任。”[10](P127)国际犯罪是国际刑事责任承担的前提,具有国际犯罪主体资格者应具备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能力。也就是说,不仅个人、团体或组织可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国家同样也应对其实施的国际犯罪或由其政策促使实施的国际犯罪承担国际刑事责任。
可以说,由于战争罪的出现,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国家是否应负刑事责任问题的探讨。传统国际法认为,国家在国际上不负刑事责任,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所作的国家行为,个人也不负刑事责任,因为他们的行为一般被认为是代表国家的行为[14](P66)。然而,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罪行的残酷现实表明,传统国际法关于国家不负刑事责任,以及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也不负刑事责任的观点已经过时。当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犯时,战犯们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提出不应由具体的个人来对战争行为和战争罪行负责,而应由德国和德国人民对此负责。辩护人雅尔赖斯曾辩护到:“当德国在个别情况下不得不违背一份仍然有效的互不侵犯条约而发动进攻时,它是干了违反国际法犯法行为,而且根据国际法的有关触犯国际法的条文,对此负有责任。但对此负有责任的只是德国!而不是个人……。”[10](P126)当然,这些只是战犯将其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推卸给国家的一种借口,但也说明国家在某些国际罪行中具有不可推卸的国际刑事责任。虽然国际军事法庭没有明确国家国际犯罪的有罪性和可罚性,但国家是否应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问题,值得国际社会、国际公法学家和刑法学家重新认识与思考。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79年7 月拟定的《关于国际责任的条文草案》,不仅明确了一国应负的国际责任,还在第19条“国际罪行和国际不法行为”的规定中,明确了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主因:(1 )一国的行为如构成违背国际义务,即为国际不当行为,不论所违背的义务主题为何。(2 )一国所违背的国际义务对于保护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至关紧要,以致整个国际社会公认违背该项义务是一种罪行时,其因而产生的国际不当行为构成国际罪行。(3)在第2款规定的限制下,并根据现行国际法规则,国际罪行除了别的以外可以由于下列各项行为而产生:1)严重违背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国际义务, 例如禁止侵略的义务;2 )严重违背对维护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利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国际义务,例如禁止以武力建立或维持殖民地统治的义务;3)大规模地严重违背对保护人类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国际义务,例如禁止奴隶制度、灭绝种族和种族隔离的义务;4 )严重违背对维护和保全人类环境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国际义务,例如禁止大规模污染大气层或海洋的义务。(4)任何国际不当行为之按照第2款的规定并非国际罪行者均构成国际不法行为[15]。
国际法律规范援用国家的国际责任,可以作为一种补偿性和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方法,同时威慑国际上的违法行为,抑制刑法中未然犯罪行为的实施。但是,国家这种“集合性”的国际法特殊主体,其承担国际责任的方式不过是对所造成的损失进行损害赔偿,而这种损害赔偿完全可以通过国家民事责任的承担予以解决,是否还有创设国家刑事责任的必要呢?肯定者认为,尽管《国家责任条文草案》已经规定了补偿性和惩罚性的损害赔偿,而且民事责任的裁决似乎比刑事责任的裁决更容易做到。但是,国家刑事责任的援用虽然只是象征性的对策,是通过国际社会谴责那些从事国际性禁止行为的政府,而不考虑这种指责在改变国际性禁止行为的实际效果,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这种方法威慑了其他政府从事近似的或其他的犯罪行为,但是,国家刑事责任的预防和威慑作用从来就是难以评价的,其作用的设想肯定是有效的[16]。否定者认为,将刑事责任归属于国家,忽视了刑事合法性的基本原则,刑事责任的必然结果是将责任适用于那些由于其共谋、策划、执行、煽动和教唆或实施了禁止行为的具有共同责任的人。而将刑事责任归属于国家则违反了合法性的基本原则,因为,这种归责的结果是将刑事责任降临到无辜者或未来无辜者的身上,或者至少是那些依据法律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的人身上[16]。我们认为,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即使只是宣告性的,仍有规定的必要,至少使国际社会意识到国家实施某种行为是具有犯罪的性质且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无论其预防和威慑作用的程度有多大,仍对该国家的国际形象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国际公法学家和刑法学家应探索一种通过其他国际法渊源创设国家国际刑事责任的理论基础(注:由于目前没有国际公约规定国家刑事责任的基础,就更别提该责任的确立,唯一与该责任有关的法是习惯国际法。根据该法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国家责任的建立应当是完善的,但却远不及,他们没有包含国家的刑事责任。)。
著名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教授在《国际刑法典草案》一书中指出,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行为主要有:(1 )代表国家或以国家名义行事的权威人士实施的任何犯罪,不管其行为按其国内法是否合法,国家应对此负刑事责任。(2)如果个人或团体以官方资格, 即这些人按该国国内法有权作出关于国家的政治性的决议,或拥有该国机关、代表的地位或该国家的手段或政治之类的手段,由他们所实施的行为应归咎于国家;上述人等以这种资格所作的行为,即使其行为超出了其实体权利范围也应归咎于国家。(3 )国家不履行国际刑事法律规范规定的义务,这种不作为构成犯罪,国家应对这种不作为负刑事责任;新国家、新政府有责任逮捕、引渡、起诉、惩罚国际罪犯而不为此行为者,应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国际法委员会一致认为,国家的责任不限于恢复原状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由于某些国际不法行为所违反的义务内容特别重要,所以会引起特殊的甚至更为严重的国际责任。如果国家以及代表国家行使行为者实施了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而这种行为由于其严重性、残酷性和对人类生命的蔑视而被列入文明国家的法律公认的犯罪行为一类,国家及其代表国家实施行动的人就应担负刑事责任[17](P417)。于是,便出现了国家因自己的不法行为而承担责任——原始的国际责任(直接责任original responsibility), 或者因其他个人或机关的不法行为而承担责任——转乘的国际责任(间接责任
vicarious responsibility)。而台湾学者汤武则认为,从国家的立场上看,损害行为的开端,可有直接与间接之分;从国际法的观点讲,国家责任的性质原无直接与间接之别[18](P424)。我们认为,无论国家有无实际执行国际刑事审判机构所作的非财产性刑罚的能力,仍应区分国家的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这样不仅使承担直接责任的国家和参与犯罪行为的被告人无可辩驳地承担各自相应的责任,而且还有利于警戒国家对其国民或官员的私人行为加强管理和监督。
应当说,战争罪是“国家行为”,或者“国家政策支持”实施的犯罪行为。作为国家成员的一些个人肯定参与了实施战争犯罪的行为,即便是“国家行为”或“国家政策的支持”(注:“国家行为”和“国家政策的支持”,是指由制定政策,或实施政策,或在国家职权掩盖下实现构成国际犯罪行为的若干个人,集体制作的决定和采取的行为。),也离不开一个或更多的煽动者的事实。虽然与国家全部统治机器相比,特别是与国家的全部人口相比,决策者通常是少数,例如独裁政府中某一个人(如希特勒),但其却有代表整体国家作出决定的独有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单独适用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即使该原则足以使这类人受到应有的国际性惩罚;但是,如果将国家的直接刑事责任转嫁给个人,该个人不仅很难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反而会赢得其国民的同情与支持,如此便失去了刑罚惩戒和预防犯罪的作用(注:纽伦堡审判的结果是使那些被指控或认定为战争罪犯的大多数德国人成为他们社区中受到蔑视的人;而与此相反的是,日本不仅不将这些人视为罪人,反而视为受害者,在日本国人看来,受到审判的战犯是胜者用审判的措辞掩饰胜者复仇的行为。参见M.Cherif Bassiouni,From Versailles to Rwanda in Seventy- five
Years:The Need to Establish a Permanent Intemational
Criminal Court",Harvard Human Rights Journal,Vol. 10, Spring 1997.)。而即便该行为者受到应有的惩罚,由于该国家的无罪性,国家可运用其固有的权利宣布对该罪行的实施者予以赦免,仍然没有起到对刑罚预期达到的效果。如果国家承担直接的刑事责任,同时煽动、参与实施国际性犯罪行为的个人也相应地承担其应有的个人国际刑事责任,那么,国家作为同一犯罪行为的责任主体就无权去赦免同一罪行中的任何个人。
遗憾的是,纽伦堡审判虽然牵涉团体或组织的刑事有罪性,但仍未得到国际特设刑事法庭和常设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认可。而且,虽然国际法委员会自1947年以来一直酝酿着《关于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行法典草案》,并在1991年草案文本的第4条中设置了“国家责任”的称谓,即“现行法典规定个人承担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行责任的事实,无损于依照国际法规定的国家责任的任何问题。”但由于该项内容引发国际社会的普遍争议,从而使1996年的《罪行法典草案》“合理化”地回避了国家刑事责任的内容。在常设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起草过程中,有的代表团认为,“还要说明的是,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中应提出的基本问题是,是否需要一些保障条款,确保个人刑事责任在规定的情形中不会解除国家的任何责任。”[19]这些在国际刑事法院建立过程所作的关于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的倡导,并没有起到主导的作用。常设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拒绝了团体或组织的刑事责任以及国家刑事责任的观念,这不能不说是国际刑法理论发展中的缺憾。
收稿日期:2000-11-15
标签:日内瓦公约论文; 法律论文; 国际法论文; 战争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刑事犯罪论文; 国际刑事法院论文; 犯罪主体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