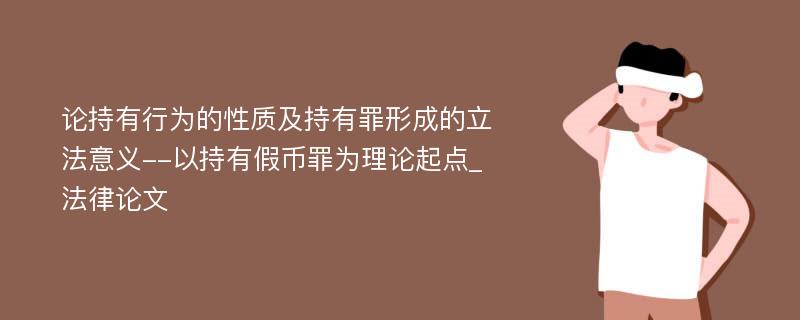
试论持有行为的性质及持有型犯罪构成的立法论意义——以持有假币罪为理论起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假币论文,试论论文,性质论文,意义论文,起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043(2001)06-0022-03
一、持有假币罪概述
持有假币罪,是指明知是伪造的贷币而持有,数额较大的行为。该罪在我国刑事立法中最早出现于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第四条,与该条规定的“使用假币罪”构成选择的一罪。1997年修订刑法基本保留了该《决定》第四条的规定。
持有假币罪的犯罪客体是国家的货币流通管理制度;犯罪对象是伪造的人民币和外币;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持有伪造的货币,数额较大的行为;犯罪主体是自然人;犯罪主观方面是故意。[1]
在现行刑法所规定的数百个罪名中,持有假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非法持有国家秘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等犯罪共同构成一类较为独特的犯罪——持有型犯罪。该类犯罪的独特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行为方式具有独特性,“持有”既不同于“作为”,也不同于“不作为”,而是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种行为方式”;二是持有型犯罪构成在立法论上具有独特的意义,是刑法规范模糊性的具体体现,是保障刑法规范实现精确性与模糊性之平衡的重要一环。
二、持有行为的性质
(一)犯罪行为方式发展简史
人类刑法史上,对于犯罪行为方式的理解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逐渐提高、犯罪态势的不断变化而不断更新。在西方国家,十九世纪初期,个人主义思潮大行其道,自由主义备受推崇,当时所谓的犯罪是指对于法益或权利的侵害,所以刑法只注重“作为”这一种犯罪行为方式,而鲜有论及“不作为”。十九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诚实信用原则被普遍认识并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之中,团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思潮日益盛行,“不作为应构成犯罪”、“不作为亦是一种犯罪行为方式”,才逐渐为学者与刑事立法者所认识。[2]二战以后,又一种崭新的行为方式——持有——迅速走进了许多国家的刑事法律中,比如日本、法国、新加坡、丹麦、美国等等。1961年联合国《麻醉品单一公约》也将持有毒品的行为与“种植、生产、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等行为并列规定为一种犯罪行为,从而标志着“持有”已成为一种为国际社会所公认的犯罪行为方式。至此,犯罪行为方式演化成作为、不作为、持有三足鼎立之势。
(二)英美学者关于“持有”行为的理论探讨
关于“持有”行为方式的性质、特点等基本问题,英美法系国家的刑法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讨。英国有学者认为:“有时,犯罪定义与其说是涉及到一个作为或不作为,还不如说是仅仅涉及到一个外部事件。只要有事件就可以构成的所有犯罪,都是由制定法明文规定的。1968年《盗窃罪法》第二十五条为此提供了一个例证。按照这一条的规定,如果一个人在其住所之外携带有用于夜盗、盗窃或欺诈或与此有关的任何物品,此人就构成了犯罪”。[3]
美国学者拉菲夫和斯科特认为:“一些持有行为被规定为犯罪,如麻醉剂、制幻剂或伪造印模的持有,或持有夜盗工具,都可能构成犯罪。虽然从严格意义上看,持有不是作为(身体的动作),也不是不作为,但持有犯罪受到普遍地赞同。”[4]
另外,美国《模范刑法典》的行为条款除规定了“作为”外还规定了“不作为”和“持有”,“如果持有人有意识地获得或接受了该持有物,或者在能够终止其持有的充分时间内知道自己控制着该物,则此种持有即为一种行为”。[5]
由此可知,无论是美国刑法,还是英国刑法,无论是在其理论研讨中,还是在其刑事立法中,关于犯罪行为方式,除了认为有作为与不作为这两种基本方式之外,都承认“持有”这种行为方式的存在及其犯罪论意义。
(三)我国刑法学界对于“持有”行为的认识
我国刑法理论中犯罪行为方式的划分方法,经历了一个从“二分法”到“三分法”的演化过程。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颁布是这一变化的分界碑。此前,学界普遍认为,犯罪行为方式只有作为与不作为两种。而此《补充规定》中“公务人员持有超过合法收入的财产罪”的设立,标志着该观点的通说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和质疑。
储槐植先生最先对犯罪行为方式“两分法”提出质疑。他认为“持有(Possession,亦译占有)是一种状态,不是作为,但其起始点常是积极的作为;状态本身更近似不作为,而刑法上的不作为却总与不履行特定义务相联系。‘持有’状态是作为与不作为的特殊结合,日益被刑法理论认为是‘第三’犯罪行为形式。”[6]“持有既像作为又似不作为,既不像作为又不似不作为,应是与作为和不作为并列的一种犯罪行为形式”。[7]
此后,在学界,持有行为的法律性质是什么?它是否应作为与“作为”、“不作为”并列的第三犯罪行为方式?一度成为学者们所关注、研讨的热点问题。主要观点无非有两种:“非独立行为方式说”与“独立行为方式说”。我们同意后一种观点,认为将持有作为第三种行为方式,既是必要的,又是合理的。至于理由,曾有多位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为避免重复,我们只补充、强调以下几点。
1.持有行为的本质是一种状态性行为,持有型犯罪既非状态犯,又非持续犯。
状态犯指行为产生了危害后果、构成犯罪既遂之后,行为所造成的不法状态仍继续存在,但这种状态本身不认为是犯罪。显然,状态犯中行为与不法状态是先后相继产生的两项可以完全分离的不同因素;并且这种单独存在的状态不同于犯罪构成意义上的行为范畴,不具有刑罚可罚性,因此,“状态犯称不上‘犯’”。[8]持续犯,亦称继续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虽已构成犯罪既遂,但犯罪行为与不法状态仍同时继续存在着的犯罪形态。其中,不法状态是刑法评价的一部分,且行为与不法状态是可以清晰界分的两个因素。比如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罪中,犯罪行为是行为人采取捆绑、禁闭等方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一系列动作,不法状态指受害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或剥夺的状态,显然,行为与不法状态是两项先后发生的行为要件,是易于剥离或区分的。
2.持有行为不同于作为,具有消极性与静态性。
作为,指行为人通过身体的外部动作积极实施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因而,作为具有积极性与动态性。而持有行为中,行为人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内相对静止地维持着对特定物的支配控制力,并没有以特定物为行为对象积极实施刑法所禁止的行为,也就是说,行为是通过消极的不行动来侵犯犯罪客体的,因此,持有行为具有消极性与静态性,这是持有行为与作为的主要区别。
3.持有行为不同于不作为,其区别表现在:第一,就刑法评价的基点与核心而言,不作为犯罪中,特定的积极行为义务是不作为犯罪中刑法评价的基点与核心。而持有犯罪中,“行为人与持有物之间存在着的事实上的支配与被支配状态”是刑法评价的基点与核心;持有行为人仅负有一般法律意义上的不得非法持有特定物的消极行为义务,而不负有构成不作为犯罪所必需的积极行为义务。第二,就行为与行为造成的不法状态之关系而言,不作为犯罪中,行为人的不作为行为与这种行为所造成的不法状态(或曰危害后果)是两项先后相继产生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可以截然分离的不同因素。在持有型犯罪中,是二者合一,行为即状态,状态即行为。第三,就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的形态而言,不作为犯罪中,危害后果都是具体的、明确的、甚至是可计量的。而持有犯罪中,危害后果是行为人非法持有特定物品的一种非法状态,因而不可能是具体、明确的。假如行为人因非法持有特定物而客观上产生了其他明确具体的危害后果,那么构成相关的其他犯罪,而不再以持有犯罪认定。[9]
三、持有型犯罪构成的立法论意义
(一)精确性与模糊性之平衡是刑事立法的基本目标
1.在刑事立法过程中,精确性是法律规范的理想追求。
第一,精确性是由法律规范的形式结构所固有的刚性因素决定的[10],是法律规范的基本属性。第二,精确性是法律稳定性的逻辑前提,是法律真正发挥功用的首要因素。第三,刑法规范的明确性是有效地限制刑罚权的随意发动、保障公民权利的锐利武器,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刑罚权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权利(即公权力),本质上具有先天的扩张性与侵蚀性,除非它遇到强有力的阻碍,否则便会无限扩张下去;而作为刑罚作用对象之公民私权利则具有先天的脆弱性与内敛性,因而极易受到公权力的侵害。这便决定了“整个刑事责任基本原则的核心是限制国家当局滥用刑罚”,[11]假如不对刑罚权实施有效控制,那就意味着刑事法律会变成凶猛的怪兽,随时都有可能露出狰狞的面目与尖利的獠牙,吞噬人们的自由、生命与财产。而刑法规范的精确性恰如圈定刑法怪兽的藩篱,是控制刑罚权之发动的基本手段,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坚实盾牌。
作为近现代刑法之根基的罪刑法定原则,其斗争矛头正是针对封建制法律的不明确性与含混性;其基本要求便是法律条文必须“意思确切,文字清晰,不容稍有混淆”[12],我国现行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标志着中国已经启动了法治列车。然而,制度化、条文化毕竟仅仅是个开端,其观念化、现实化尚需一段漫长而艰苦的路程,因此当前条件下,强调并切实加强刑法规范之精确性的意义犹为深远。
2.模糊性是刑法规范的又一基本特征,模糊性在刑法规范中的存在既有必然性,又有必要性①。
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模糊性是由语词的基本特性所决定的。英国学者哈特认为:语言具有空缺结构(open texture)的特征——每一个字、词组和命题在其“核心范围”内具有明确无疑的意思,但随着由核心向边缘的扩展,语言会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在一些“边缘地带”,语言则根本是不确定的。因此,“消除一个给定术语的模糊性,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我们所希望作到的,至多是渐渐地接近于消除模糊性”。[13]第二,模糊性是立法者基于“刑法规范的精确性”追求之困难及其副产品之巨大而不得不作出的次优选择。根据模糊论可知,法律的“精确性”是个相对概念,是法律的“永恒追求”,绝对的“精确性”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法律规范的“精确性”是一柄“双刃剑”,其弊端即刚性太强而灵活性欠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亦令人们大伤脑筋:一旦出现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执法者和公民便无所适从。既然如此,法律规范的模糊性便成为立法者的“次优”选择。第三,模糊性是立法者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而有意作出的积极选择。从价值取向上讲,如果说刑法的精确性旨在限制刑罚权的发动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着重体现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那么,刑法的模糊性则有利于推动刑罚权的发动,重在体现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人权保障固然重要,社会保护同样不可轻视;特别是在社会治安比较严峻,各类犯罪特别是有组织犯罪、跨国犯罪日趋严重的形势下,适度设立一些空白罪状或者模糊性、柔软的、概括性的规定,对于强化刑法的适时性、灵活性与超前性是很有必要的。适度的模糊性也是刑法规范保持其生存所必要、合理张力的必要条件。
总上所述,精确性与模糊性是法律规范的两个基本属性。我们必须在立法实践中努力谋求精确性与模糊性之间的和谐与平衡,设计并完善实现刑事规范精确性与模糊性之平衡的具体运行机制。在刑事规范精确性与模糊性趋于平衡的天平上,持有型犯罪构成是模糊性一端的砝码。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
(二)持有型犯罪构成是模糊犯罪构成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第一,就持有型犯罪构成的最初起源来讲,它是立法者在无法证明“持有”行为的先前行为或后续行为构成犯罪的情况下,为了严厉打击相关犯罪而作出的选择。
对于立法者而言,持有型犯罪构成的出现起源于对“不罚预备”刑事原则的补救。②详言之,对于某些以诸如伪造的货币、毒品、枪支弹药等特定物品为行为对象的犯罪而言,其犯罪行为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具有极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都有必要严厉地予以刑法规制;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对于那些单纯持有特定物品的行为人而言,司法机关无法以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先前行为或后续行为构成犯罪。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违背“不罚预备”这一总则性的刑法原则,又不能让犯罪人逃脱法网,两难之下,立法者将“持有”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行为方式予以单独规定,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然而,究竟行为人之“持有”行为的先前行为与后续行为具体是什么?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与刑事可罚性?对于立法者来讲显然是不明确的、模糊的。由此可知,在发生学意义上,持有型犯罪构成是刑事规范模糊性的具体体现。
第二,从价值取向的角度而言,持有型犯罪构成与模糊性刑事规范都是立法者严密刑事法网、严格刑事责任的重要手段,都重在体现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
如前所述,精确性犯罪构成以其精确性、具体性、非此即彼性体现着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而模糊性犯罪构成则以其概括性、模糊性、亦此亦彼性体现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而持有型犯罪构成恰恰以其模糊性与不尽明确性体现着对于犯罪人的打击与惩治。具体言之:
持有型犯罪在我国现行刑法中的出现与持有行为作为第三种行为方式之地位的确立,绝非我国立法者盲目追崇、简单模仿外国刑事立法最新潮流的结果;而是立法者深层价值取向的生动体现与反映——简言之,它反映了立法者严密刑法法网、严厉打击某些严重犯罪、充分发挥刑法社会保护功能的价值追求。对于司法机关而言,在持有型犯罪构成中,对于犯罪构成客现要件的要求标准较普通犯罪要低,司法机关只要有证据证明“持有”这种状态性行为的现实存在,便可以认定犯罪的成立。而“持有”是一种现存客观事实,是容易证明的,发现了“持有”这个事实便等于证明了这个事实。由此可见,持有型犯罪的设立实际上减轻了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从而有利于更有效地打击某些多发性、危害巨大而且难以用传统犯罪构成惩治的犯罪。
总上,持有型犯罪构成作为模糊性犯罪构成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保障实现刑法规范精确性与模糊性之平衡的重要手段,在立法论上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