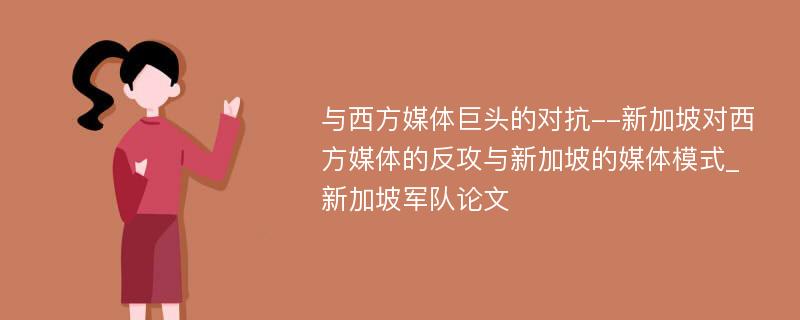
与西方传媒巨人的对抗——新加坡对西方媒体的反击与新加坡的媒体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媒体论文,巨人论文,模式论文,传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今日西方媒体的力量有多强、势力有多大,相信大家心里有数。它们霸占着世界传播市场,控制着国际舆论,是无论如何招惹不起的。可是,新加坡这个经济发展极为成功的小国却偏偏不向它们低头,甚至胆敢公开与之对抗。这场对抗愈演愈烈,已经引起了国际间的重视。
这场对抗具有重大的政治与文化的意义,其重要性必将超越时空,引起巨大的反响。它引发了几个问题:一个国家采取开放政策、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走向现代化等等,非采纳西方媒体的模式不可吗?新加坡为什么对西方媒体抱着这样大的戒心?它本身的媒体模式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在“世界华文报刊与中华文化传播”这样的研讨会上讨论,我认为是有意义的。各个华人社会都处在不同阶段的现代化道路上,它们或迟或早地会遇到这个问题。
西方媒体所向披靡
在强大的西方经济、政治、军事势力的支持下,在日新月异的通讯科技的推动下,近年来纷纷进行“环球化”的西方媒体,今天的影响力可说是铺天盖地、无远弗届的。无论哪一个国家,无论多偏远的地区,哪怕是不对外开放,技术上说,都在西方媒体的通讯网、广播网和发行网的笼罩之中、覆盖之下。英国广播公司(BBC)、 美国电缆新闻网(CNN)、《国际先驱论坛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 《经济学家》周刊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而近年来异军突起的电脑网际网络(Intemet),更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了!这一巨大无比的力量, 对全世界所造成的巨大冲击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长期在国际上处于支配地位,西方媒体一般而言习惯于将它们本身的价值观强加于它们所到的世界各地,而往往不考虑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情况与西方社会究竟有多大的差别。这些价值中,最重要的就是新闻自由至上的观念。在新闻自由的大前提下,报章崇尚对抗而不是社会和谐,重视争论而不是求取共识,鼓吹极度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而不是社会整体的利益和自由;报人自以为代表真正的民意,对一切权威,包括民选的政府,采取不信任、挑战,甚至破坏的态度。以美国为例,所谓“新闻自由”获得宪法的明文保障,神圣不可侵犯,新闻媒体因此自认为拥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等三权以外的“第四权”(Fourth Estate)。
这些价值被认为是体现西方言论自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但它们是否能被移植到一片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土壤,适应不同的环境和气候条件,与当地的花草共同生长,开花结果呢?还是会带来一些当地植物没有免疫能力的病毒,将原有的生态环境破坏,进而消灭一切土生土长的生命呢?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很快找到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至今为止,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恐怕还没有找到一个禁得起验证的成功例子。
然而,这些重要的问题显然是西方媒体所不感兴趣的,它们自认为负有“替天行道”的神圣任务,认为接受西方那种自由至上的新闻模式是理所当然的。它们要那些和西方国家没有共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中国家也加以采用,认为这样才会真正给各国带来好处。
这种情形,在东欧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尤为明显,因为在全球的基础上足以和西方势力抗衡的唯一一股势力在一夜之间忽然瓦解,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时之间,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与之共生的放任式新闻自由,似乎已成为普遍的真理,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了。有人甚至因此而宣告“历史的终结”〔1〕,西方之道从此将统治人类。 而西方媒体作为这股似乎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开路先锋,更是意气风发,几乎所向披靡了。
在亚洲,这股西方的激流更是波涛汹涌,征服了一片又一片的海岸,并进一步建立了桥头堡。选择西方模式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有些是因为眼前的政治利益而心甘情愿地采纳,有些则由于种种政治、经济或外交的因素不得不听命或受制于西方,无可奈何地被迫接受。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西方媒体以一种高人一等的姿态加以表扬,称赞它们对“民主与自由”作出贡献;而那些不愿萧规曹随的国家,则被它们贴上“压制新闻自由”、“违反人权”、“不民主”等标签,受到排斥和攻击。这种攻击行动不再只是出现于西方媒体的报道内容,而逐渐以国际论坛的形式,有组织地进行了。例如,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美国的一个新闻业组织“自由论坛”(Freedom Forum )和香港的外国记者俱乐部联合在香港举行了一个称为“亚洲新闻论坛”的国际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几乎是冲着新加坡而来的,对新加坡的新闻模式和它所提倡的“亚洲价值观”进行了猛烈的攻击〔2〕。此外,在一九九五年五月, 国际报业协会(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 在韩国首都汉城举行第四十四届全体大会上,通过了几项决议,要求朝鲜、缅甸、印尼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其他几个地区改善媒体的处境〔3〕。
打到了巨人的痛脚
新加坡为什么会被西方媒体和西方新闻专业组织挑出来作为攻击的对象?原因很简单:正当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接二连三地采取迎合西方媒体的姿态,随着它们的指挥棒起舞时,新加坡和另一些国家却对西方媒体采取了不妥协的姿态。其中,新加坡不但毫不屈服,还进行了反击。西方媒体势如破竹的攻势来到东南亚,却遭到这个小国的顽强的反抗,不但完全无法影响新加坡的媒体,它们的进程还因此受到了阻挡。因此,它们将新加坡视为眼中钉,不放过任何攻击它的机会。
的确,新加坡政府对西方媒体的反击行动早已闻名于世。这种反击主要有三种方式。
首先是新加坡的政治领袖,特别是李光耀资政,在国际场合上对西方媒体的严厉批评。他们对西方媒体那种自以为是、爱干预别国内政的作法,以及那种喜欢带着西方优越感、以高人一等的姿态教训第三世界的作风,感到深恶而痛绝之。任何西方媒体若没有掌握充分的事实,缺乏有力的论据,却试图以这种姿态向新加坡“训话”,告诉新加坡领袖如何治国的话,必然会遭到毫不留情的公开反驳或反唇相讥。在国际论坛或记者招待会上,西方记者若以不敬或对抗性的语气,或试图以一种话中有骨、不怀好意的态度向李资政发问题的话,也必然会遭他毫不客气地驳回,甚至教训一顿。由于李资政是一位受尊敬的国际闻名政治家,常有机会在国际论坛上发言,也常接受国际媒体访问,他的这种姿态早已闻名遐迩,也连带使到新加坡反对西方媒体的声量特别高,这方面的形象特别突出。
其次,新加坡政府要求在它国土内发行的外国报刊必须同当地媒体遵守同一套规则,特别是给予它答复的权利。西方报章向来把最后的发言权保留给自己,而不愿自动给予不公正批评的受审者答复的权利,有时甚至对事实上的错误也不愿给予更正。由于新加坡以英文为行政语文和学校教学的第一语文,通晓英文的人口占大多数,特别是年轻人。一些英美媒体公司所办的国际性英文报刊看准这一点,常常以刻意批评新加坡政府或其政策的作法制造舆论,引人注目,以便吸引新加坡读者,开拓在新加坡的销路。当政府认为一些批评缺乏事实根据或有欠公正而作出答复时,它们却对答复信置之不理,认为答复的权利并不是当然的;有时即使将答复信登出来,也改得面目全非,完全失去原意。新加坡政府对此自然感到非常气愤,认为这些报刊已超越了媒体的角色,而进入了明目张胆干预它的内政和参与它的国内政治的地步;而不给予政府答复澄清的机会和权利,更是一种极为傲慢和不公平的态度。
在与这些西方报刊进行了长期交涉不果后,政府只好通过立法,授权它限制这类报刊在新加坡的销量。在新加坡的《报章与印刷厂法令》下,新闻及艺术部长有权通过宪报宣布任何在新加坡发行的外国报刊为“参与新加坡国内政治”的报刊,而限制它在新加坡的销售或发行量〔4〕。采取限制销量,而不是完全禁止发行的手段, 除了不让西方媒体有机会给它贴上“关闭传媒市场”这个更严重的标签之外,也考虑到新加坡是个国际大都会及区域性的工商业和交通枢纽,有无数外国公司在这里营业或设立总部,有一大批真正需要国际资讯的外籍工作人士和旅客,若不让他们看这些他们所熟悉的刊物,可能会引起对新加坡经济不利的后果。大幅度限制销量而不是全面禁止的好处,就在于一面使有关报刊中的资讯能继续在新加坡流通,但另一方面却使它的广告收益因发行量大减而大受影响,使它的商业利益受到打击。自从一九八六年采取这种手段以来,已有多家外国报刊先后被宣布为“参与新加坡国内政治”的刊物,包括《亚洲华尔街日报》、《远东经济评论》、《时代》周刊、《亚洲新闻》(Asia week)、《经济学家》等, 其中大多数的销量曾被限制,有些从每期高达万多份限制为仅三百份。
新加坡政府使出的这一打击西方媒体的绝招果然奏效。这些报刊禁不起长期的经济损失,在报刊老板的坚持下,编辑部尽管万分不情愿,也只好接受新加坡政府的原则,将答复的权利还给它,即使要删改答复信也得征求它的同意。现在,虽然其中一些的限制令还没有解除,但销量顶限已经获准大幅度提高,有些甚至已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在这一回合中,新加坡打到了巨人的痛脚。
新加坡对西方媒体进行反击的第三种手段是采取法律行动,毫不犹豫地将触犯新加坡法律的西方报刊告上法庭,迫使它们尊重新加坡的法律,为本身的言论负责。这一反击行动的最佳例子,莫过于最近刚下判的《国际先驱论坛报》诽谤新加坡国家领袖的案件了。
非美国式的处事方式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日,该报刊登了专栏作者菲利普·鲍林(PhilipBowring)的一篇文章,题为《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往往是禁不起考 验的》〔5〕。这篇文章对近年来逐渐被普遍认可的、 以李光耀资政为其中一个主要提倡人物的“亚洲价值观”进行了攻击。这种攻击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方面的论争在新加坡也经常发生。但是,文章却超出了正常讨论的范围:它进一步声称,新加坡目前也存在着中国传统的“王朝政治”。
这里的“王朝政治”是何所指,不言而喻:李光耀从一九五九年新加坡开始自治以来,就一直担任新加坡总理,前后三十一年,到一九九○年才卸下这个职位。接任总理职位的吴作栋,他委任李光耀为内阁资政,并委任李资政的儿子李显龙准将为副总理。同时,他也曾公开表示有意推举李显龙为接班人。因此,任何对新加坡政治有起码认识的人,都能一眼看出,鲍林的所谓“王朝政治”就是在影射这一情况。
这篇文章当然引起当事人的强烈不满。虽然《国际先驱论坛报》在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刊登了一则道歉启事,声明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吴作栋、李光耀和李显龙三人还是以诽谤罪名对该报进行了起诉。这个案子今(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新加坡高等法院判决,承审法官在八月二十二日发表的书面判词认为,这篇文章影射李资政和李副总理行为腐败,搞裙带关系,而吴总理则在李资政的指示下,对这些行为给予协助,并成为他们的同谋,是对他们作出了“导致严重伤害的攻击”。他指出,这篇文章已影响到起诉人执行公职和治理国家的能力,使他们感到气愤,并攻击了他们所坚持的政治信念的核心〔6〕。 法官宣判此案的三名答辩人得赔偿吴作栋总理三十万元、李光耀资政和李显龙副总理各三十五万元,赔偿总额为九十五万元(约六十五万美元),是历来在单一诽谤案中最高的赔偿额〔7〕。
《国际先驱论坛报》案件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对西方媒体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因为这是新加坡对它们所进行的一次非常强有力的反击。向来唯我独尊的西方媒体被逼必须向一个第三世界的小国道歉又赔款,其意义的确非比寻常,它自然引起了西方媒体和新闻专业组织的愤怒。它们对新加坡法庭的判决展开了攻击,更对《国际先驱论坛报》接受新加坡法庭的判决而不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
小国与西方媒体抗争而最终取得胜利,哪怕是在本国领土,也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菲律宾《马尼拉纪事报》的一专栏作者对《国际先驱论坛报》总裁西蒙斯(Richard Simmons )决定不对新加坡法庭的判决进行上诉以及继续在新加坡印刷和发行的事〔8〕发表了评论。 他写道:“对一个像《国际先驱论坛报》那样势力强大,又是由美国两份势力最强大的报章,即《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所拥有的机构来说,采取这样的立场是很不寻常的。它已经接受这样的原则:只要它继续在新加坡保留一个办事处,继续在新加坡营业,那它除了尊重和服从新加坡的法律和传统之外,别无选择。这根本就是一种非美国式的处事方式。”〔9〕
这段话很准确反映了一个重要事实:美国媒体尊重别国法律是很不寻常的、很“非美国式”的。由此可见,新加坡领袖赢得这场官司,而法庭的判决又为美国最强大的媒体接受,其象征意义是何等重大!
新加坡在反抗巨人的战斗中,又取得了另一回合的胜利,而这一回可说是击中了巨人的要害。
新加坡的这些高姿态的反击西方媒体的行动,使它成为一个反西方媒体的突出例子,在许多人心目中,它似乎已成为国际上反西方媒体的急先锋。其实,新加坡政府并不是、也没有能力在国际场合向西方媒体的行为挑战,它根本无意这么做。它所要争取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只不过要求那些在新加坡发行、以新加坡读者为对象的外国报刊,在报道有关新加坡的新闻和评论新加坡的问题时,尊重它的主权,遵守它的法律和媒体政策,并接受新加坡媒体所遵循的同一套规则罢了!
否则的话,它们将使新加坡的媒体面对不公平的竞争。李光耀资政一九九五年六月十四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访问时,对这一点就有很清楚的说明。他说:“如果外国媒体要报道新加坡的新闻,那就得据实报道,因为我对于本地报章和外国报章是完全一视同仁、绝对公平的。……如果我允许外国报章来拉我的尾巴,掐我的颈项,而且又没有受到惩罚,那新加坡媒体也很快的就会加以仿效。”〔10〕
负责任的新闻自由
那么,新加坡的媒体模式是什么呢?答案其实很简单:负责任的新闻自由。
新加坡政府对本国报章的要求,在吴作栋总理于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五日发表的一篇演讲中有清楚的说明。他是在庆祝《海峡时报》(新加坡的主要英文日报)一百五十周年晚宴上,发表这篇题为《新加坡报章——好政府和好社会良性循环的一部分》的演讲,对宴会上以新闻从业员为主的听众说:“新加坡报章不能因为其他国家的新闻机械接纳了对抗性的角色而这样做……
“你们对新加坡人的最佳服务,就是准确地报道,清楚地分析,以及从新加坡人的角度、为新加坡明智地诠释事件与事态的发展;澄清问题,清楚地说明各项选择,因为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每一个解决方案都要付出代价。……
“报章的任务是促进共识,而不是挑起对抗;是促进建国,而不是损害社会组织。……
“别滥用给予你们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应等于可以不查明事实便报道谣言,或可以恣意伤害无辜者,或可以不顾权威体制及对外关系会因为不够敏感的报道而受到伤害。约束新加坡报章的自由比让它们像在一些国家里那样撒野胡闹来得好。”〔11〕
吴总理的这番话清楚地说明了政府为媒体所定下的“游戏规则”:新闻自由可以享有,但这种自由必须受到社会和政治责任约束;媒体的角色是促进共识,协助建国,而不是挑起对抗,破坏稳定。但与其说他是在对新加坡报章提出新的要求,不如说是一种对官方新闻政策的重申,对现状的陈述,因为这些规则其实是新加坡已经接受了的。
事实上,除了这些“游戏规则”之外,过去这些年来,新加坡政府还划定了一些明确的“界限”,不准媒体逾越。
这些界限之所以会定下来,主要和新加坡的社会结构及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关。新加坡是一个面积只有六百多平方公里的城市国家,人口不到三百万,种族、语文、宗教的成分却很复杂,处在一个关系微妙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中;没有天然资源,连食水也得靠邻国供应,飞机一升空就进入邻国的领空,军队必须出国才能演练……。无论从狭义或广义的角度来看,新加坡的生存空间都是很小的。
面对这种种局限和不利的条件,新加坡政府绝对不允许媒体玩弄种族、语文、宗教等问题,或突出这方面的矛盾,煽动敌视和仇视的情绪,当然也不能采取种族或文化沙文主义的立场——这类文字不只会引起国内的种族冲突和社会动乱,也会严重影响与邻国的关系。此外,对于任何可能损及与邻国关系的报道或言论,它也要求报章采取最谨慎的态度。
这些界限并不是一夜之间定下来的,而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中间夹杂着一些痛苦的经历,根据实践经验逐渐演变出来,并逐渐明朗化的。其中一些重要事件是:一、新加坡在一九五○年曾发生一场穆斯林和欧裔人士之间的种族/宗教暴乱, 一九六四年则发生一场马来族和华族之间的种族暴乱,对社会安全和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两场暴乱的起因都与宗教、种族和政治问题有关,背景和过程相当复杂,但直接的导火线却是马来文报章的煽情报道〔12〕。(引起一九六四年那场暴乱的紧张种族关系后来终于导致新加坡于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被逐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在新、马分家后,两国签署了一项协定,同意彼此的报章不在对方国土发行,其中一项主要的考虑因素就是不让本国的种族关系受对方报章影响。)二、一九七一年五月,政府援引内部安全法令,逮捕了华文大报《南洋商报》的四名管理层及编辑部高级职员,罪名包括煽动华人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政府怀疑该报一些主要负责人涉及国外敌对势力所搞的、目的在于颠覆新加坡社会的“黑色活动”〔13〕。三、一份不断在新闻和评论中抨击国民服役制度及鼓吹放任思想的英文报《新加坡先驱报》(Singapore Herald),由于在营业严重亏损之下,仍然源源不断地从国外来历不明处获得资金,也被怀疑涉及“黑色活动”,终于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被政府吊销出版准证〔14〕。
媒体不过是社会的一环
新加坡媒体对这些事件有相当深刻的记忆,了解到本身过去的一些作法已经危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因此认可了定下这些界限的动机和必要性,并已经完全加以接受,也完全放弃了对抗性的作法。
然而,无论是“游戏规则”或“不可逾越的界限”,都不是明文规定下来的。就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新加坡也有一套约束报刊的法律条文——就是前面提到的《报章与印刷厂法令》。这项法令除了授权政府在必要时限制外国报刊在新加坡的发行量外,主要还是对新加坡报章出版公司的股份结构和管理权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其中一些主要规定包括:报刊必须有新闻及艺术部长发出的准证才能出版,准证必须每年更新:报章出版公司的董事必须是新加坡公民,任何个人或机构不得拥有超过百分之三的股份;股份分管理股和普通股两种,管理股占总股份的百分之一,只能发给那些获得部长批准的新加坡公民或机构,在有关委任或开除任何董事或报馆职员的投票表决中,每份管理股拥有二百票的表决权;外国人不得拥有超过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任何新闻从业员若因发表某则新闻或文章,或因对某则新闻或文章采取某种立场,而获得来自国外的酬金的话,必须在七天内以书面向报社的董事经理报告等等〔15〕。
其中对外国人、个人及机构所能拥有股份总额的限定,对获取国外酬金申报的规定,以及对有关管理股的规定,反映了新加坡政府对“黑色活动”的戒备心理,显示了它不让外国人有任何机会控制、操纵或影响新加坡媒体的决心。
除了《报章与印刷厂法令》外,其他有关法律条规,如诽谤法、官方机密法令等,也对媒体的行为形成了直接和间接的约束。
从这些法律条文、界限和规则看来,新加坡政府对媒体的管理的确是相当严密的。但必须指出的是,新加坡由于长期面对生存的问题,本来就是一个管得很严的社会,在每一方面都是如此,媒体只不过是其中一环罢了。最重要的一点是,新加坡的媒体承认如何治理国家是民选政府的权力,报章不应越俎代庖。它们也同意:由于媒体具有传播信息和引导舆论的重要功能,对人民有巨大的影响力,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体制,政府对它们实行严密的管理并非不合理的事。
事实上,新加坡有今天的成就,多少可以归因于政府管理得严。假如不是严密的管理,没有严格的纪律和秩序,没有咬紧牙根的励精图治,新加坡以一个毫无天然资源的小岛,一个一无所有的前英国殖民地,是不可能在短短三十年内发展成为一个人均收入高达三万一千一百八十七新元〔16〕(约二万一千五百美元)的富足社会。但是,今天的成绩并不是理所当然能保证明天的生存,更不能保证明天的繁荣。尽管由瑞士的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和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出版的权威性的《世界竞争力报告》,今(一九九五)年连续第二年将新加坡列为全世界竞争力第二高的国家〔17〕,尽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决定从一九九六年起将新加坡升级为“发达国家”〔18〕,这些成就仍然改变不了一个基本而残酷的事实:新加坡先天不足,生存环境又恶劣。
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新加坡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各方面的政策都不可能有太多的选择;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社会必须保持高度的凝聚力,人民必须高度团结,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才有可能继续生存和发展。媒体必须协助政府将这些重要信息传达给人民,让人民了解在今日的国际环境中,特别是在新加坡“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不断保持甚至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性,因为只要一不小心,松懈下来,失去经济竞争能力,新加坡的生存就会面对问题。假如新加坡媒体不但不这样做,反而采用西方的媒体模式,一味制造无休无止的争论,向民选的政府、国家领袖或代表他们执行政策的各级行政单位采取对抗的态度,使他们的权威地位在人民心目中动摇,使公众对政府的能力和信心产生怀疑,那肯定是招惹灾难、自取灭亡的不二法门。
可以这么说,今天新加坡的报人已经不只是消极地接受上述那些法令、界限或规则而已,而是已经更进一步,和政府对许多重大的问题取得高度的共识,积极和主动地采取与政府合作的态度,在提高社会凝聚力、协助政府达到政策目标、从而促进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有利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
以国家利益为依归
约束报章行为的各种条例和规则可说是管制媒体行为的硬件,但使得这样的一个传媒体系能更顺利运行的却是媒体中的软件——新闻从业员的价值观。新加坡的媒体和政府对于传媒的角色有高度共识,官营的电视台和电台自是不在话下,即使是私营的报章也是如此,这也许是因为大家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同一套亚洲价值观。其中,华文报的新闻从业员更明显地具有那种以大局为重、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以和为贵、尊重权威等价值观,并且较具有高度自律的精神。这也许是他们曾接受华文教育和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薰陶的缘故,心中已有一个亚洲价值参照体系,因此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比较能够有所判断和筛选。在华文报工作的人,认为维护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支持廉洁贤明的政府和尊重被普遍接受的权威是理所当然、无须辩解的。在这方面,新加坡主要华文报《联合早报》的表现相当有代表性,而它的编辑方针就清楚写明“必须以维护新加坡国家利益为依归”。相对于英文报同行来说,华文报的新闻从业员更加没有那种“报章或报人必须挑战政府的权威才能建立本身的威信”的心理负担。华文报的这些特点,显示了即使在新加坡的宏观模式下,不同语文的报章也因为受西方影响程度的不同而有微观的差别。
但无论是华文报或英文报,都采纳了支持政府的立场。按照西方的标准,一份与政府关系太好的报纸必然值得怀疑,它的可信度必然会大打折扣,但新加坡的报章却证明这种标准是大有偏差的。它与政府关系良好,却维持了很高的可信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大众传播学院讲师郝晓鸣博士今(一九九五)年八月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加坡报章及公众信任》的论文,提供了具体调查数字,显示了新加坡公众对当地报章的信任程度相当高。根据他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所进行的一项有关公众对报章看法的随机抽样调查,有多达百分之七十的人认为新加坡报章的素质“好”或“很好”,认为“坏”或“很坏”的低于百分之四;至于对报章的信任程度,“很信任”的占百分之三十六点五,“有某种程度信任”的占百分之五十三点六,“信任程度很低”或“完全不信任”的加起来还不到百分之十〔19〕。这些调查数字强有力地说明了“支持政府”和“可信度”并非互相排斥的。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公众对该国报章的信任程度要比新加坡低得多。吴作栋总理在上述演讲中引用了美国“盖洛普,哈里斯及国民意见研究中心”(Gallup,Harris and the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re)今(一九九五)年二月发表的一项广泛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一九九三年,对报章很信任的美国公众只有百分之十一,几乎完全不信任的高达百分之三十九〔20〕。
事实上,要办好一份既支持政府又获得读者信任,既替政府解释政策却充分反映民意、对政策提供建设性批评的报纸,比起办一份一味强调新闻自由而不注重社会责任、为了讨好读者而哗众取宠、靠贬损别人抬高自己的报章,难度更高、挑战更大,需要报人具有更高的专业能力,以及丰富的学识和高度的纪律。
当然,要办好这样的报纸,要避免与政府对抗,客观因素和条件也是很重要的。新加坡报章能做到这一点,也应归功于下面几个重要因素:有一个廉洁、贤明、公正、有效率的政府,有高瞻远瞩、开诚布公的政治领袖,有高度透明的法律制度、行政系统和司法过程等。此外,政府领袖尊重和信任报章的主要负责人,与他们保持经常的联系,并愿意与他们分享一些重要消息和政策背景等,都是对促进政府与报界良好关系的有利因素。
结论
新加坡的发展过程的一大特色是:能够在不断取得高经济增长、大大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维持社会秩序和纪律;在吸收和利用西方的管理及科技知识的同时,杜绝西方的一些政治和社会弊病,保留亚洲社会的特性和本质,也避免了其他国家或地区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种种社会问题。这些普遍可见的弊病和问题包括:社会失序、价值解体、道德沦丧、家庭崩溃、毒品泛滥、罪犯横行、政治腐败、官员贪污、贫富悬殊、环境污染、交通阻塞等等。
这样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新加坡的发展经验的确有其吸引人的地方,它作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一个模式,已经引起了国际间的广泛重视和兴趣。
新加坡的独特媒体模式,其实是它的整个现代化模式的一个构成部分。它和其他因素互相配合,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新加坡的成功,对新加坡今日的成就有很大的贡献。
也许就是新加坡的成功传达了“现代化不一定要西化”这个重要信息,西方传播媒介对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大多数持否定的态度,更因为新加坡胆敢反抗它们而对它完全没有好感。它们在报道或评论新加坡时,对它的成就总是轻描淡写,要不然就是认为这些成就是在付出太大的代价下取得的。在西方媒体的描绘下,新加坡的形象总是负面的,它被形容为一个独裁、专制、缺乏自由、违反人权、过度管制、枯燥乏味的社会。
西方媒体不但不愿肯定新加坡的模式,还一直贬低它,希望制止它的散播,甚至很想改变它。它们不但试图运用本身的强大影响力达到这个目的,也试图通过迫使新加坡采用西方的媒体模式的作法,使新加坡面对来自内部的要求改变的压力。
新加坡当然不能让它的制度被颠覆,不能让它辛辛苦苦取得的成绩付诸东流,不能让它的重要议程由外人决定,更不能让它的发展前景甚至生存能力受到威胁。它不但没有向西方媒体这个巨人低头,反而对它的压力和干预行动进行了坚决的抗拒和反击。新加坡一来不允许西方媒体操纵它国内的舆论,二来坚决不接受西方媒体的游戏规则,从而使西方媒体或它们背后的势力或利益无法通过新加坡媒体,达到它们本身所无法达到的目的。
新加坡政府反抗西方媒体的行动,得到了新加坡媒体和新闻从业员的支持。他们认为,媒体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体制,应该以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为依归,而不是向一种抽象的、基本上源于不同社会的“新闻自由”观念负责,何况这种观念已经给西方社会以及有样学样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来了许多弊病。
新加坡在本国领土上战胜西方媒体巨人,迫使它遵守新加坡的法律和规则,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制止了一场对它的主权的侵犯行为。由于新加坡是个非常开放的国家,为了经济发展必须让资讯自由流通,它的胜利就更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证明了,即使在开放的环境下,即使让资讯、消息自由流通,也不一定就得采纳西方的媒体模式。新加坡报章能够在与政府合作的同时获得民众的高度信任,使它们能在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充分发挥了传媒这一重要体制的积极功用。
新加坡媒体模式的产生自然有其特殊的生态环境,但这里面是不是可以提取一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元素呢?假如这种模式是可取的,它能不能适用于其他社会,特别是那些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前进的社会?最低限度,它的一些内容是否有值得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参考的地方?长远不说,这样的一种媒体模式在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利益方面,是否会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注释:
〔1〕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一九八九年在《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 )夏季号发表了他那篇引起争论的著名文章《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roy?)。文章的主要论点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已经结束,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将普及全世界,成为最终的政治形式。
〔2〕当时许多以香港为基地的国际报刊和一些港台报刊都有这样的报道,台湾《新新闻周刊》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八日那一期的一篇文章《李光耀的“亚洲价值”在公审下被瓦解了》是个典型的例子。
〔3〕见"IPI Calls for Freedom in P'yang " ,Korea Newsrev-iew,20 May 1995.
〔4〕详见 Singapore statutes,Newspaper and Printing Pr-esses Act,(Singapore:Singapore National Printers,1991)。
〔5〕Philip Bowring,"The Claims About 'Asian' ValuesDon't Usualy Bear Scrutiny",Intemational Herald Tribune,2August 1994.
〔6〕《联合早报》,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7〕《联合早报》,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8〕详见 William Glaberson,"IHT's President Says Newspaper Won't Contest Singapore Award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7 August 1995.
〔9〕J.V.Cruz "IHT needs Singapore but not vice versa",Manila Chronicle,12 August 1995。
〔10〕《联合早报》,一九九五年六月十六日。
〔11〕一九九五年七月十六日《海峡时报》,(The Straitstimes)和七月十八日的《联合早报》都刊登了吴作栋的演讲全文。原文英文题目是"The Singapore Press:Part of the Virtuous Cycl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Good Society"。
〔12〕见Tan Yew Soon and Soh Yew Peng.The Development ofSingapore's Modem Media Industry (Singapore:Times AcademicPress,1994).PP.46.
〔13〕见《南洋商报》,一九七一年五月三日。
〔14〕见Tan Teng Leng,The singapore Press:Freedom,Responsibility and Credibility,IPS occasional papers No.3.(The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Times Academic Press.1990),P6.
〔15〕同注〔4〕。
〔16〕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Republic of Singapore.Economic Survey of Singapore 1994 (Singapore:SNP PublishersPte Ltd,February 1995),P Viii.
〔17〕《联合早报》,一九九五年九月六日。
〔18〕《联合早报》,一九九五年五月六日。
〔19〕详见Hao Xiaoming,"Singapore Press and Public Trust," Presented to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s in Washington D.C.August 1995.
〔20〕同注〔11〕。
(原载1996年2月《海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