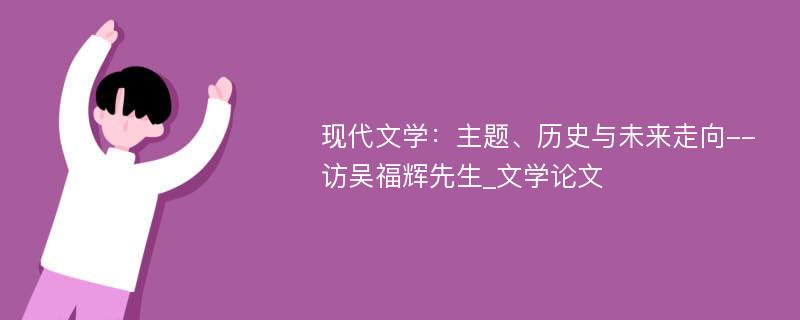
现代文学:学科历史与未来走向——吴福辉先生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学科论文,访谈录论文,走向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6)01—0027—07
吴福辉:著名学者、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三四十年代文学、左翼文学与京海派文学、现代讽刺小说等。主要著作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钱理群、温儒敏合著)、《沙汀传》、《带着枷锁的笑》、《深化中的变异》等。
邵宁宁: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邵:吴老师,您好!近一个时期,受《甘肃社会科学》主编董汉河先生的委托,我一直在做有关文学研究的学术访谈,想通过对一些有成就的学者的访问,以一种比较贴近个人体验的方式,探究和反思我们的学术传统。从80年代起,您就是现代文学界的知名学者,您与钱理群、温儒敏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目前大学中文系使用最普遍的教材;同时,您又长期担任着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副馆长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主编。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有理由认为,您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最具全局了解力的人之一。因而,在这次谈话中,我希望您能对这门学科的历史和现状作一番论析,以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它曾经具有的意义和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吴:我看了你的提纲,你的提纲还挺深的,要求也很高。原来我以为只是谈谈自己的学术经历,便答应了你,没想到你根据我多年做《丛刊》的主编,又是《三十年》的作者之一的身份,要求我从学术史的角度,谈我们学科的过去、今天和未来等等,而我的学术自述已属于你所提的五个问题之一了。我希望今天我们能够对谈,不希望自己一个人成本大套地谈什么东西。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下,写了几个字,今天我们随便谈,我基本上围绕你的问题,能谈多少谈多少吧。
1.有关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性质和意义
邵: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现代文学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在50~70年代,它的建立和发展都和当代意识形态建构存在着紧密关系,用一位前辈学者的话说,它可以被看作是“第二革命史”。这既给它带来了许多局限与问题,同时也赋予它当代生活中的显赫地位。就是到80年代以后,它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和引起的社会关注,也和该时期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认为,在当时,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每一重要突破,其最终结果都指向了某种现实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氛围的变化,现代文学研究与整个人文学术一道被边缘化,同时,由于新一代学者的出现,以及学位、职称制度对学术工作性质、方式的潜在影响,这一学科在当代生活中的意义变得多少有些模糊,随着现代文学意识形态建构功能的降低,这一学科似乎面临着一种被“古典化”、书斋化的命运。现代文学在当代知识生产中还能产生出些什么,它的内部生长空间究竟有多大,逐渐成为一个问题。在一次有关学科“生长点”的讨论会上,您曾说:“讨论清楚到底有哪些‘生长点’可能还是次要的,进一步认识我们这个学科的性质特点,才是重要的。”我很赞同您的这种看法。现在,能否请您就现代文学学科的性质、特点,以及它对当代生活所可能具有的能动意义,做一点解说?
吴:这个“学科”的历史,现在来说,算多少年呢?过去樊骏老师说我们这个学科正年轻,他发表过这样的文章。近几年又说,这个学科现在已不再年轻了。这个学科也正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这个学科,过去有的人说,它是1949年以后才正式确立形成的,这个当然说得过去,这也就是以王瑶先生的《新文学史稿》作为标志。但我们这个学科的历史,严格地说,应该从几方面来看。譬如最早开始研究现代文学作家,研究鲁迅——这就比较早了。我查了一下,比较大的人物,像茅盾,发表《读〈呐喊〉》是1922年,这就离“五四”运动没有多远。在1922年以前,他还谈过鲁迅的《阿Q正传》,但没有成篇的文章,是与别人交谈的,不是长篇的论述。但《读〈呐喊〉》是成篇的文章。这就是说从1922年,现代文学作家自己研究自己的历史就已经开始了。这是一个标志。同样也是1922年,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也谈到了现代文学——这是典型的、黄修己老师说的“附骥式”的文学史,前面是古代的或近代的,后面附上一些近十年的。这样的文学史有一大批,以胡适的名头最响,《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篇文章最重要。再下来就是朱自清了。朱自清1929年开始在清华讲新文学,这个东西当时没有发表,手稿一直保留到解放后,等到我们上学的时候,王瑶先生把它拿出来,交给赵园去整理,赵园整理出来以后,发表在上海的《文艺论丛》上。这个新文学史——后来叫做《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我们看了以后还是挺受刺激的,它和解放以后我们读的,像张毕来的、叶丁易的,都有很大的不同。朱自清先生的论述,比较接近现代文学的原生状态,而后来的经过什么整理呀,提炼呀,按照某种观念归纳呀,越来离文学的原样越远了。朱先生的那个纲要,还是很生动的(当然,后来又有人整理周扬的,周扬在延安讲新文学,这已经很晚了)。这算是一个标志吧——在大学里开始讲新文学,这是1929年。然后就是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写。今天说来,赵家璧的功劳确实是很大的。蔡元培作总主编,下面每一个主编,现在看来都是不得了的人物,鲁迅编了小说二集,其他胡适、茅盾、郁达夫、朱自清、郑振铎他们每人编一本,前面均写有导言——当然水平有高有低,但总体来说,对新文学是一个很好的总结。这就是说,我们的新文学学科,从1922年算,有80年之久了;如果从1929年算,从1935年算,也有相当长的时间,起码有半个世纪了。所以我同意樊骏的观点,还年轻,但也不年轻了,慢慢不年轻了。
你在提问中说,你很同意我在清华谈“生长点”时的发言,认为讨论清楚到底有哪些“生长点”还不是最重要的,认清学科的性质和特点才是更重要的。我今天仍持这个看法。这个学科的性质和意义,我自己概括起来是这样的:第一,这个学科结束了中国文学的古典状态,开启了现代状态。这个意义可能永远不会变,会长期存在下去。尽管现在对它的分期、内涵,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大家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意见,也就是说,这个学科还在变动当中。但是不管怎样,它结束了中国文学的古典时期,这毫无疑问。你不管从哪个地方算起,从鸦片战争、戊戌变法、还是甲午战争算起都行,它结束了中国文学的古典状态,开启了现代状态,这个学科的意义就在这儿,它的所有意义都要从这儿生发出来。
邵:这也就是说,您说的现代文学是一个有更大包容性的概念,不是1949年就结束的那个“现代文学”,而是和“古典”相对的“现代文学”。
吴:对,这个观点大部分人都能同意。分歧就是看它的准备期有多长,但准备期再长,也就是鸦片战争,有政治事件做标记的。文学性的标记很难找,我曾经试着找,晚清时候,到底哪一年,对我们中国现代文学是最典型的一年呢?从1897年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算起,或者从梁启超1902年创办《新小说》算起,都是一说。大家知道,北大出的那一套书“百年中国文学总系”,谢冕、钱理群主编的,其中程文超那本谈的是1903年。其实1903年谈“谴责小说”最好,所有重要的“谴责小说”都在1903年的报刊上发表,这就很集中啊!特别是鲁迅先生说的“四大谴责小说”,都在这一年的期刊上发表了。1903年的意义就在这儿。当然,其他方面也能找出一些标志,比如邹容的《革命军》的写作时间、发表时间,以及“苏报案”出事都在这一年。但不管怎么说,现代文学从晚清什么时候开始,它结束了中国文学的古典状态,开启了现代状态。
现代文学的性质——多年来我常谈的——是一个政治性、社会性很强的学科。现在我们谈内在矛盾性,这个内在矛盾性很难得到解决。比如说我们说让“文学史回到文学”,不管现代文学的整个过程,这是不可能的。就是把政治甩得远一些,还得进入文化视野,不进入思想史,还得进入文化史。研究教育呀,出版呀,期刊呀,社会经济包括物价呀,市民的日常生活状态呀,通过这些来研究现代文学,这还不是还没有完全回到文学本身吗?完全回到文学本身就不是中国现代文学了。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特点就是社会性、政治性很强。它的思想史的特点,文化史的特点确实非常强。这当然也给它带来了一些问题。其次,它显然是多元的。像许子东,像我,还有一些人,基本上同意现代文学有五种文学形态,像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通俗文学……,有提四种的,有提五种的。这个多元性不稀奇,但过去很少将它贯穿始终来考虑现代文学。很多人都说“五四”当时怎么多元性,到30年代又怎么个多元性,现在我们应当慢慢地将它提升到整个文学史来考虑。这种思考容易僵化,但有个好处,可以把整个文学史提纲挈领地提起来看。整个现代文学这一百年,有哪些文学形态,它们互相怎么影响,比如左翼文学有没有受鸳蝴文学的影响?这个很少讨论。但所有人都说,茅盾有点像鸳蝴。他生活的地域也像。茅盾生活的地方杭嘉湖地区前后左右都出鸳蝴作家,中国的文学现在要打开来看,多元性要提到一个高度,俯视整个现代文学。我们可以研究鸳蝴作家与左翼作家的关系,也可以研究京派和海派之间的关系,他们都是同时代人,你把它放在同时代去考虑,互相之间肯定有影响,他们有很多相同点,互相渗透,互相刺激,文学是这么往前走的。这个多元性,我们过去只是分作两类,一部分人是社会性很强的,一部分人是个人主观性很强的,实际上还可以把眼界放得更宽些。
第三个呢,现在有人主张还应该给现代文学定一个性——“五四性”。现代文学有一个特点,它产生的年代同时给自己形成一个理论的构架,“五四”本身形成了一个怎么看“五四”文学的问题。“五四”时期思想流派多样,文学也多样,完全不像30年代,到30年代就有一种对垒,两三种文学互相对垒的感觉。“五四”没有这种感觉。甚至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你也分不清的。你看《灭亡》,看巴金早期的著作,看《爱情三部曲》,谁是社会主义者,谁是无政府主义者,你是分不清的。我小时候看巴金的早期作品,只知道这些人都在革命,不知道他革什么命,实际上到处都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时候你也分不清的。无政府主义者很容易演化为社会主义者,所以才有蒋光慈、胡也频那些小说,写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怎么争论。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差不多的人。毛泽东、茅盾早期也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后来演变为社会主义者。现代文学和这个情况是比较相近的,到30年代才真正对垒起来。
比如王富仁谈的那个问题,说各种传统都向我们现代文学渗透,欧美文学的渗透,俄国文学的渗透,都是可以理解的,但说新儒学的渗透,就是大家不能同意的。为什么?这就是从它的“五四性”出发,我们的现代文学一开始是从反儒反孔发展而来的,反儒反孔给我们现代文学定了一个什么性?你本来是反儒的,现代文学是不能与新儒家、老儒家共存的,和它一共存,现代文学性质就变了。现代文学从“五四”产生,同时便带着一个“五四性”,好多人都谈过。新文学有很多传统,但不要忘了“五四”文学传统。“五四”作为一个新传统,基本上是批儒的。但是不是说中国现代文学就一定是批儒,没有崇儒的传统?这我也有点不同意,但现在也很难说“学衡派”就是崇儒,这可以研究,首先你不能封闭起来。“五四”文学这个新传统是存在的,和这个新传统共同存在的还有没有别的?我想还有。这还要回到多元性上来,讲“五四性”不要和多元性矛盾起来,“五四”本身就是很丰富、很阔大的,它应该包涵,它和多元性是可以互相补充的。
第四个,就是经典性。现代文学到了现在,它的经典性问题也就慢慢出来了。我专门讲过这个问题。这个学科开始经典化和没有开始经典化不一样。本来经典化这个学科应该更纯粹,提炼的更厉害,可惜的是解放以后我们这段弯路走得太大了,所以我们现在要不断地“重写文学史”。“重写文学史”和经典化的过程合在一块儿,这可能是这个学科的一个特点。古代文学不会这样,古代文学你要说“重写文学史”,肯定越写越少,文学史应该越来越薄吧?把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家提炼出来以后,其他次要的作家都分散掉了。总不能越写越多吧?我们现代文学,结果越来越多,我们主张研究期刊,原来不注意的作家也被注意了,原来不注意的现象也被注意了。这和我们所走的弯路有关。经典化开始的时候,这个学科已经产生了将近一百年了,20世纪文学的概念都提出来了。现在20世纪文学已经离我们而去了,纪念作家100年的高峰也过去了。经典化开始的时候, 你开始考虑文学大事表怎么排——这种考虑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就是经典化的东西。20世纪过去了,然后评选,很多报纸都搞过,人民文学出版社评选百年百部作品,我也参加过。一般的话《阿Q正传》是第一位是没问题的,第二部标准就完全不一样了,各种报纸、 杂志标准完全不一样。那几年《围城》排得很前,这几年电视剧不放了,就不那么靠前了。这种调查本身都是经典化的开始。经典化会带来很多问题,文学史写得薄啊,写得厚啊,文学现象是写得越来越丰富啊,还是写得越来越单纯啊,哪些作家可以进入文学史,哪些作家不能进入文学史。现代文学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些人离刚刚发生的文学很近,哪怕隔了一代,也很近,很容易参与进去。经典化的过程是一个读者、作者、编者都能参与进去的一种活动,这也很明显。我到南京的东南大学讲课,他们就和我争论,对现代文学到底有没有经典性就很怀疑,一百年的中国文学,到底有没有经典作家、经典作品出现,理工科的同学表示怀疑,他拿出世界上最有名的作品来比,这也是一种观点。我有次听一位学者讲话,她说(现代文学)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东西可看?现在还有人说,除了鲁迅和张爱玲,还有什么可看?这已经极而言之了——只有两个经典作家。这一百年里面没有稍多些的经典作家、没有经典作品,这是不可能的。怎么来经典化,怎么来认识经典性,这个可以讨论的,但这个文学史已经过去了,需要后人来总结,从它的影响程度,当时怎么接受,后来怎么接受。当时再红,但后来没有影响,一个文学作品没有影响,没有承传,你怎么说它是经典?有永久性、有代表性、有承传性,这都是经典化的标准。
第五,就是我们学科的内在矛盾性。它从一开始产生,内在的矛盾、不可解的矛盾,就一直是存在的。这个矛盾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考虑。可以从文学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从文学的思想文化研究——传统如何渗透,文本研究的资源如何缺乏;从文学的时空边界——确定性、模糊性;可以从现代化——眉目我们还没有把它描述清楚呢,现在又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了。还有在理论方法上,外来的理论方法和内在的理论方法的冲突,和整个理论方法的滞后,等等。这个需要做很多的梳理,抓住了这个矛盾性,也就抓住了现代文学的特点。
至于你的问题中问我,这个学科对当代知识生产还能产生什么东西,到底有多少成长空间?我自己总结起来,现代文学它确实还是我们研究现代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学科。最重要的地方还在于我们通过它,可以了解现代人的生长过程,他的生命过程和他的想像。通过现代文学,可以对当代知识产生什么——永远的人的现代性的研究,都离不开它。我们可以从现代文学去研究现代的人,他怎样活在现代性这个矛盾当中,在现代性和反现代性,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个矛盾当中,现代人的生存状况,他所有的生命过程和困境,它能提供给我们最重要的知识。而这个知识永远可以存在。
有的人说现代文学是很贫困的,有几个作家,有几个作品能流传下去?这完全可能。我长期生活在东北,就像这个铁矿,本身是富矿,含量肯定高,如果是个贫矿,就要想办法把它变成富矿,选矿的过程可以把任何的贫矿转化成富矿。
邵:我是这样想,经典性的东西不一定在文学性上非常有价值,就像我们去读中国最早的经典之一《尚书》,它也没有什么文学性,但它就是经典,因为它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是奠基的东西,就像您刚才讲的,我也感觉到现代文学最大的价值可能不一定是我们说的“纯文学”,“纯文学”可能是一个太狭隘的概念。就是我们将文学当作一种语言艺术看待,这本身就是小看文学了。文学可能还是中国本来意义上的那个文学——人文之学。我觉得现代文学从这个意义上,像您说的,它作为现代的起点,现代文化的起点,所以是我们不断要返回去的地方,就像研究古代要回到诸子时代一样,研究现代要回到鲁迅的时代。
吴:这我完全同意,现代文学就是这么个东西。文本细读最后读出些什么东西?结果还是读出了很多有文化意味的东西。你完全离开了要搞纯文学研究,那只是一种设想。理论可以把一种东西推到极端,但要进入文学史就很难了。我想写一本纯文学史很难,写一本形式文学史也很难,我都想像不到怎么来写这个文学史。陈平原那个时候,这个话还好说,毕竟是第一次研究叙事的转化,他可以说哪个人称多了就是一种标志。这个话说一次还可以,再说就难了。假如说到30年代,又有一批人放弃第一人称了,全都搞第三人称了。你说这到底是更现代了呢,还是又复古了呢?怎么说这个事?下次这种事产生以后是不是又是一个标志?所以说形式的问题,加上文化的含义,思想的含义就可以,你把文化思想加进去,就可以了,完全纯形式研究,很多结论就很难下。
2.有关80年代以来的学科走势和未来方向
邵:在现代文学研究中,80年代是一个令人怀念的时代。尽管此前这一学科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但我们今天对它的基本认识,主要还是通过80年代的工作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您和您的同辈学者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作为一个受惠于这一学术成果的后辈,在我的经验和印象中,那仿佛是一个新的启蒙时代,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洋溢着一种启蒙的激情,而你们的工作,也确实为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了贡献。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回望80年代学术,在欣羡它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禁会问,这一学术传统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它所取得的主要突破在哪里?如果说它仍存在某种不足,那又是什么?作为过来人,您能否就自己的体验和思考谈谈对这类问题的看法。
吴:我们都是80年代毕业的。像我、杨义、钱理群、温儒敏、凌宇、赵园,以及上海的一些学者——上海还有一些78届的大学生。80年代初毕业的研究生和大学生,构成了当时的青壮年研究力量。80年代怎么评价?拉开点距离来看,我还是很看重“重写文学史”。我认为,认识近二三十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抓住80年代中期的“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也是那时提出来的,90年代等于是再一次“重写”。1985年、1984年以前的那个阶段可以算是“重写”的一个准备。围绕“重写”,可以把这段研究分成“重写前”、“重写中”、“重写后”,但这样分还是太细。“重写”可以作为理解80年代现代文学的一个核心。而杨义提出的“文学地图”的问题,现在我们好多人都在考虑,当然不一定用“地图”这个名称,严家炎老师说要恢复文学的生态,也是这个意思。杨义提出文学地图问题,主要是说我们要重新考虑现代文学研究的空间,不平面化,要立体化,把现代地理学的概念用进去,要形成一个立体的文学空间。到底空间怎么构成的,现在说法很多。还有回到历史原点的说法,就是说文学如何发生。因为发生以后的情况被我们接受了以后,再返回去,有点“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味道,按因果论返回去,文学的状况就变了。不像以前那么做,才能真正回到原点,回到原点的目的不是为了复古,是为了更了解文学史。所以我们提倡文学生态学、发生学,最近期刊研究这么热闹,都是相配合的。这些都说明现代文学研究正在形成新的突破,我是很乐观的。你们这一代应该认识到这一点,现代文学正在酝酿新的突破,就是说文学研究的边际、空间都可能有大的改变,这种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又一次“重写”开始了。这次“重写”的意义可能比上次“重写”的意义更大。那次重写有点“拨乱反正”的味道,把一些污泥甩掉,从原来完全政治化地认识作家、作品到更人文化。这次是要真正建立起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的立体空间。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这次酝酿的突破是从80年代来的,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80年代的意义,把“重写”作为一个核心,那一次的“重写”有点像恢复“五四”精神的味道,把被我们丢掉的重新恢复起来,再往前走,走到现在,另外一个性质的“重写”又要开始了。现代文学史要不断地“重写”,80年代是第一次“重写”,一切意义都可以从“重写”上出来。
邵:在一篇旧文中,我曾将50~7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所做的主要工作概括为“选择与安排”,80年代的主要工作概括为“发现与辩护”;对于90年代及其以后,我现在倾向于将其概括为“解构和还原”。这当然只是一个大体的概括,而只要是概括就不免有所遗漏,有所遮蔽,但三个时期学术的不同毕竟是存在的。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不知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尤其是,您是如何看待现代文学学科的未来走向的?
吴:未来的学科方向是什么呢?我已经谈出来了,再一次“重写”就是未来的方向,建立新的文学空间。这一次“重写”,基本上是基于对80年代研究的一种反思,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有些什么问题呢?这几年大家也在不断地反思,现在提出来的问题有这么几个:一个是认识到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学院化,脱离大众,脱离人,脱离老百姓。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五四性”,本身就是联系社会现实的,是引人共鸣的东西。现代文学研究是不是越来越学院化呢?——我觉得我们的现代文学与现实的联系还是比较紧的,比如说,鲁迅评价的一再被提起。像王朔几年他不出来,出来他不是骂老舍,不是骂金庸,就是骂鲁迅,否则他觉得寂寞——但并不能说骂得全无道理。在上海,有几个作家也认为鲁迅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认为鲁迅不需要捍卫,但随意贬低他也是做不到的。还有当代作家,急于摆脱阴影,就贬低现代文学。我看过一本南京出的书,所有人回答受没受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的问题时,80%的年轻作家说没有受过现代文学影响,谈到受外国文学影响就来劲了,外国作家他愿意说我受哪个作家影响了,但现代作家他不愿意说。这也有他的道理,每一代作家都想独立成长,独立成长就要摆脱阴影,每个青少年都要摆脱父母的影响,都有些叛逆——才能长大啊,可以理解。评价不断被提起的本身,一方面是青年一代的需要,一方面就正说明鲁迅仍有活力,要摆脱鲁迅的影响并不容易。第二,我们还是不断提出文学史的一些新概念,也比较多,像“二十世纪文学”的概念,像陈思和的潜在写作,广场、民间,我们现代文学还是能提出几个理论概念的一个学科。从这些角度说,现代文学还是一个比较有活力的、能够联系现实的学科。除学院化的问题之外,王晓明还提出一个思想弱化的问题,这也存在。现代文学研究思想弱化,这当然和商业化的腐蚀是有关系的。但我觉得还不是非常严重。
对于现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和未来方向,邵宁宁你提出的观点是,将来是“解构和还原”?
邵:我是觉得现在——这几年,有这样的倾向。
吴:但我总感觉现代文学学科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空间,新的一套理论方法,这是有可能的,不是凭空产生的,从现在的基础上往前走,是有可能的。整个文学被边缘化了,文学研究怎么能不边缘化?除非我们还愿意再一次被政治利用。但边缘化以后的文学研究会怎么样,我想,还是有它的存在空间,大众文化在工商社会越来越流行以后,虽然有各种假冒伪劣,但这个趋势不可避免——你从电视里看——现在什么事都得专家讨论,电视文化是非常大众的,可电视里头老是让专家给大众讲。有些东西也许是伪的,伪学术、伪科学,但这个现象本身是很明显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距离,转化越来越快。通过大众媒介,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距离在拉近,所以,我想现代文学和大众的关系,界限不会像以前那样分明。
3.有关“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目标
邵:“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目标是什么,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然而在很多时候,它却潜在地困扰着我们的文学研究。有一个时期,“文学史”书写不过是整体革命史的一个章节,其后,随着思想解放潮流的演进,它又日益与思想史难解难分,以致有文学史家,如温儒敏先生,发出了不要以思想史取代文学史的呼吁。然而,一种深入的文学研究,又很难不进入思想史或精神史的领域,在实际中,我们一不小心,仍然不是为思想史就是为文化史所俘获,这里的界限似乎并不好把握,因为说到底,文学毕竟是一种精神现象,传统的传记批评,固然是“外部”研究,形式—结构主义的文本分析,又何尝真正进入到了它的“内部”?早在80年代初,王瑶先生就曾指出,文学史既是文学,又是史学。他这样说,针对的大概主要是当时存在的非历史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后来一点一点得到克服,现在想起来,真正让人感到为难的倒是前一点,因为如何使“文学史”成为“文学史”,似乎不是一个只用以文学为研究对象就可以打发得了的问题。文学史研究的本己目标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很难简单作答的问题,但我们常常又不得不面对它。作为一个文学史家,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吴:有关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目标,我认为,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就像我们小时候讲政治经济学,说马克思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最小的一个单位:商品。我们现代文学研究的最小单位是什么呢?王瑶先生说,最小的单位是文学现象。他把文学现象作为文学研究的最小单位,不能再分割了,再分下去不叫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文学史研究的最小单位就是文学现象。但什么是文学现象?过去基本是作家、作品。因此我们过去的文学史都是建立在分析作家、作品之上的,把作家、作品拿过来,再分成几个时期,抓住主要作家、主要作品,这就完了。这个文学史模式基本上是从欧洲来的。现在我们还是把文学现象看作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但这个文学现象不只是作家、作品——作家、作品也是,但还包括,比如说文学是如何产生的,如何传播的,如何被接受,如何发生影响的,这都可以看成是基本的文学现象。从人来看,包括作家、编者、读者,都把它看成一个整体。当然,过去还有研究文学的外部和内部这样的提法。在我看来,抓住了文学的基本现象,注意文学的内部和外部,注意文学的和文化的,注意形式的和精神的,这样来研究。像我这样年龄的人来看,觉得未来的文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和方法,还是应该这样。——我想请教一下,前几年那个热烈的方法论讨论,在你们这一代研究生身上还有些什么体现?有几年,每个研究生一进校就先看一年西方的东西,然后每个人根据自己接受的理论形成一个框架,再找现代文学组织一个东西。这种风气现在影响还大不大?
邵:这种风气现在应该说还有,但不像前几年那样突出了。不过,那种向西方寻找理论资源的冲动,还是普遍地存在。像“现代性”一类的抽象问题,似乎没有前几年那样讨论得多了,这几年好像是更多地转向了某些具体的问题。
吴:应该是成熟了一些。真正抓住一个中国式的问题来分析,就比较好。我认为,现在是到了西方的理论资源逐渐被我们消化的时候了——虽然还没有完全消化,但正在消化。我们都离不开那一阶段——西方的理论大量地引进来,那么倾盆地下下来——到现在慢慢地在消化。
4.有关文献学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意义
邵:经历了80年代、90年代以来的发展,现代文学在许多方面都显得更为成熟,表现之一,即是人们愈来愈将其置于一种具体的历史情境里去处理。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文学史料学或文献学的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加强。近年,除一些重要学术期刊(如《丛刊》)上有关文献研究的文章越来越多外,一些院校和学术组织还连续召开了多次会议,就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在这方面,中国现代文学馆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能否请您谈一谈您自己对这一学术动向的看法。
吴:对文献学的研究,可以放到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进程中去理解。因为你要回到“原生态”也好,“现场”也好——尽管我们回不了,怎么回得了呢?过去了就是过去了——现在大力提倡进行文献研究也好,都是要在我们要重写文学史,更进一步地重写文学史,在这么个背景下来理解的。另外,我们现在的学风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察一下现在的研究生,有几年,特别是前几年的研究生,根本不读作品,不读杂志,全都在读理论。这怎么行?还有就是抄袭。我认为有些人的抄袭,不是有意抄袭,有两种情况,特别是有了电脑以后,有一种人,什么东西都摘,写东西就靠拼凑,他一块一块往一起拼,拼出一篇论文来。他的材料原来从哪儿来,他自己都忘掉了。现在提倡文献学研究,除了符合我们当前的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的理论之外,和我们当下的学风需要做某些纠正也是有关系的。但从根本上来说,比如你看陈寅恪的研究,他都是把新材料的发现和新观点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一本20万字的研究生论文,如果全是理论发现,没有什么材料的发现,我就不相信这是一篇很成熟的论文。所以我们重视新材料的发现,一篇像样的博士论文,如果有三成到六成是材料的发现,然后再加上五六成,或三四成理论的发现,就是一篇很好的论文。如果是理论基础较弱的人,如果有七八成的材料发现,那就站住了。材料的发现和意义的发现,对我们做学术来说,永远是同等重要的。
5.有关个人经历和学术道路
邵:最后,我想问的是与您个人的经历与研究有关的问题。在我看来,一个人的学术个性,往往与他的个人生活史有关。那些属于个人生活的早期经历,虽然未必直接作用于他的学术选择,但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展开为它的深度背景或思想动力。听您说,您在考入北大做王瑶先生的研究生前,并没有读过大学,您的童年生活与上海有很深的关系,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最先挑选的对象似乎是沙汀,其后又转向有关30年代京派、海派及左翼文学的研究,请问,推动您做出这些选择的深层动力是什么?目前的文学研究,似乎越来越学院化、职业化,一个人从事学术研究,往往只是出自职业的需要,而这很可能使现代文学研究失去真正的学术兴趣和思想动力,不知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能否谈谈您的早年人生经历与您的学术研究的关系,特别是它对您学术追求和学术个性的影响?
吴:关于我自己的研究情况,我看你们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们这一代人,像钱理群、赵园、温儒敏,我们一入学,首先是兴奋,因为我们赶上最后一班车了。当时杨义、刘纳、刘玉山、蓝棣之,他们都住在北师大(按:当时社科院研究生院借址北师大)。这些人原来都以为自己要离开文学研究了,突然又回到文学研究的岗位上,也知道将来还可以继续做下去,因此学习抓得很紧,有人一进校,发誓三年不看电影,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发誓三年不谈恋爱(笑),但好多人都发这种誓:三年不看电影,三年不看戏。我中专毕业没上过大学,有长期自学的经历,自学经历给我带来了什么?我搞文学研究,从生命流程来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我的同代人,即使没有我这种自学经历的,往往也都有这种特点。我们六位研究生里面有五个都是中学教师,只有温儒敏不是——他从人大新闻系毕业,跑到广东去做记者,分配得不错,其他的都是中学或中专教师,赵园、钱理群都是,王富仁也在中学呆过,做过教导主任。我在一个普通中学里也做主任,从初一到高三,任何一个年级我都教过。这种经历是差不多的。前两批考上的学生,大部分都是这样。我们当年考北大,100个人取一个。人人都是经过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积累来考。这些人都是中学教师,都是经过自学。我们12个人复试,其中有一个姓杨的,是四川一个偏僻山村三线工厂里的工程师,也是工大毕业的。他也是从600人里面进入复试的。 后来袁良骏老师告诉我,参加判卷的,一天没判出一张50分的卷子,他问我,你们这里面第一张50分以上的卷子是谁的,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是凌宇。当判出第一张50分以上的卷子时,全场轰动,大家都来看。那是很戏剧性的。老钱收到复试通知一看,糟糕了,要考不上!因为他专业成绩70多分。他想这怎么办?他不知道他的考分全国第一。当然题出得非常好,严(家炎)老师出的,再加上王瑶先生。有些题都没办法想象怎么回答,完全懵住了。有一道题出《新民主主义论》,一道题包括五个问题,每个问题环环相扣,有一个环节堵死了,你就根本不知道如何去答。你没有读过《新民主主义论》,你还能答题吗?这道题是谈《新民主主义论》的,实际上谈的是“五四”文学的性质。它先问你:“五四”文学是什么性质呢,在30年代有不同作者、不同的文人对“五四”文学性有不同的看法,你同意谁的看法?你认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对“五四”文学性质的看法有什么作用?这一道大题问下来,你如果从开始就不知道谁谈过“五四”新文学的性质,你就完了,你怎么答呀?我脑子中的印象,瞿秋白、胡风好像都谈过“五四”文学,他们认为“五四”文学是市民文学,我就从这个往下答。到《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高中课本里有有关文化的那段的节选。我教过高中语文,我就根据那段将题答完。题出得相当有意思。我们这些人是当过中学教师的,当教师,当学生,是不一样的。“书到用时方恨少”,“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任何道理和它都是相通的,你当了老师了,你的知识不扎实不行。我有自学经历,最重要的一点,我读作品读得多,读任何作品都有很多的感受,读作品的基本功,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赵园和我一样,都非常重视读作品的第一感受,她读后马上把第一感受写下来,有什么印象、直觉,说了什么东西。她记,我不记。她一块一块的记,像札记。她的论文就在这个基础上写出来的,有感受、有想法。这种天才成分越多的人,想法就越多。看一部作品就五个想法和有一百个想法,那能一样吗?阅读作品的基本功,对文学现象的感受能力,包括直觉的感受能力,是我们作为文学研究生的一种基本功。而我们这代人,在这方面都是特别强的。通过教中学的训练以后,任何知识你都要讲到实处,都要找到源头。我的自学经历给我三点,第一点就是基本功,研究文学的基本功。第二就是独立的自由的读书习惯。我们中国人很多人读书啊,不是自由的、独立的,而一个中学老师就没有人管你了,你到了中学老师这个程度,就要自己弄,没人管你了。因为好多老师已经是大学本科毕业的了,知识已经够了,只有在教的过程中去学,这个学习是独立自由的学习,长期的独立自由的学习,是我们第一批、第二批研究生,1981年、1982年之所以能考上的原因吧。当中学教师的时候,每个礼拜天我都不回家,我一个人呆在教研室读书,想看什么看什么。有一段我还管过图书馆,这整个图书馆都是我的,我的床就铺在图书馆里。那时好多中学图书馆都很好,全体学生都可以到这个图书馆借书,每人最多借两本,1958年以后批判走白专道路,越批越不读书,中学图书馆就垮了。我们那时候一个图书馆的证都不够用,我有学校图书馆的证、区图书馆的证、还有工人俱乐部的图书证、市图书馆的证,还显得不够用呢。第三,就是我们的职业和我们的兴趣爱好是一致的。有些人职业和品性是不一样的,他喜欢的不是每天要做的,下班回来以后,去做的一件事是自己喜欢的。我们馆里有20多个义工,非常热心,都是理工科的,学历很高,他们本来应该是学文科的,但一辈子搞外贸、搞经济,退休以后才找上文学馆。可见人将兴趣和职业结合在一起是多么不容易!我的自学经历就给我带来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后来就都转化为文学研究的动力和资源。另外,就是在研究当中要不断寻找自己,发现自己,让自己与研究对象契合,这一点非常不容易,但我想我们基本都找到了。我当时开始作张天翼和沙汀,很多人都不理解,你为什么去写《沙汀传》,为什么不挑一个更有名的?
邵:这我也想问您,为什么挑沙汀?
吴:是啊,很多人都这样问,为什么不挑一些比沙汀更有名的作家,你作一个非左翼作家的传,外面就会有翻印,《沙汀传》写得再好,台湾也不会翻印,宁肯翻印《朱自清传》,也不翻印《沙汀传》。可我最喜欢沙汀的小说,一个人物,一个小故事,语言充满了一种幽默智慧,人物都是真正现实里面的人。你要问我最爱读的小说,沙汀的一类。我写他就是因为我喜欢他。他写一个人偷了东西,关在监狱里,今天放出来很高兴,去割点肉做肉,花椒忘了,给佣人点钱去买。买回来以后说怎么买这么一点花椒,怎么不买磨好的,他说你这点钱到哪儿买磨好的,就买了几颗,把这几颗放嘴里嚼嚼,“啪”——往肉罐里一吐,小说就完事。这个小说绝对有思想。当时我做讽刺文学,我做的硕士论文虽然是30年代,实际我20年代的都看了,看完才定位,上下看完才能定位,特别要看上面的。所以一进校,北大老师就说,你们搞古代文学的,你搞先秦的,可以不看唐宋、明清的。你搞明清的,你要看先秦、唐宋的。你搞明清的文学,前面怎么来你能不看吗?你搞30年代讽刺文学,前面你不能不管,都得管,都得彻底研究了。当时我的兴趣在左翼文学的原创性比较强的,我认为张天翼和沙汀都是有原创性的作家。当时王瑶先生认为我可以研究茅盾。毕业后我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一开始我分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那时认为我政治比较可靠,人也没什么大毛病,起码那时候没有看出什么大毛病(笑)。到那里去肯定生活待遇好,当官也快,但我得把现代文学放弃。我说能不能让我搞现代文学,就这样我才分配来中国作家协会。我参加文学馆的筹备,文学馆1985年才成立,1981年筹备时我就到了。当时我搞左翼时,没想到要搞茅盾。王先生却说你能搞茅盾。王瑶先生分析每一个研究生能搞什么,给他指路,有两个观点:王瑶先生认为每个研究生应当背靠一个大家——大到什么程度?和现代文学三十年哪一年都沟通,和很多作家都有联系。他认为大作家像一棵树一样,你抱住这个大作家,就把文学史的实体抱住了,其他都是空的,你老看文学史不行,你看来看去都是空的,都是人家这么分析那么分析。你的认识需要抱住大作家,能通、能连起来,他认为茅盾就是这样的作家,别人去搞鲁迅了,你就去搞茅盾。他没有安排我们谁去搞郭沫若,他自己写过郭沫若,但他没有要求我们接着搞。第二,他看我出身、工作一直都在城市,从上海,到东北,到沈阳,到鞍山——
邵:您是上海人,怎么50年代就到了东北?
吴:这跟历史有关。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共产党就派了一部分人占据东北。东北作为工业基地,打仗这个地方要支援,建设也是。东北要建立工业基地,我父亲是会计师,被招聘到东北,这样我们全家就到东北来了。
我11岁以前都在上海。我是1939年生的,没经过30年代,是从40年代去体会上海30年代最繁华的时候,是按上海沦陷时期的体验。“孤岛”时期还是繁华的,柯灵改编《大马戏团》,高尔基的《底层》《夜店》,人们都能接受。《一江春水向东流》上演的时候,我的亲戚都从无锡坐火车来上海看,看一整天。所以上海消费文化的状况,在我记忆里非常清晰,它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全国没有办法理解上海,不仅是政治上、文化上、物质生活水平上,各方面都是“孤岛”。这段童年记忆、生命经历和我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决定了我的研究的特点。王(瑶)先生看出来我能搞这个——搞茅盾。虽然我没有搞茅盾,但1981年到作协以后,好多工作都和茅盾有关。当时文学馆没多少事,成立茅盾故居,编茅盾全集,建茅盾协会,作家协会都交给我了,所以我那时候没有搞茅盾,但在做茅盾的工作。我感觉茅盾的上海太政治化了,他那个上海我没法理解。但张爱玲那个上海我能理解。我到我同学家去,同学家很有钱的,家里面客厅有两间。在上海这个现代化很高的城市里,他们家的中式客厅古色古香的,中式的客厅。旧的家族在上海衰微的状态,和我的切身的经验都能契合,所以我觉得茅盾就没有把上海写清楚,他只是写了上海的一部分。再加海派其他作家——把予且加进来,把张爱玲加进来,把苏青加进来,这才像上海。上海1/5的人都是宁波人。所以我还了解上海这个城市有不同社区,按我体会,虽然上海的现代化程度非常高,但都市里的乡村性很强。我们小时候在家里,都听长辈说宁波话。上海人就由宁波帮、广东帮、苏北帮、苏南帮组成,人数最少的是本帮。我一看苏青就知道她是宁波人。每一个人都得寻找自己的研究对象,能与自己生命契合的对象,与自己的兴趣结合。
我们这一代外语不好,理论有偏颇,但基础是扎实的。理论太旧,都是苏联的东西,与欧美隔绝,东方西方是不通的,贯通不了,和胡适、鲁迅那一代人比,人家是中西贯通的,到了你们这一代,西的方面好了,也比较全面了;中的方面,传统的方面可能更不行了。我们每一代人都要发挥自己的特长,需要扬长避短,你们有你们的,我们有我们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研究,不是空中楼阁。包括钱理群为什么搞中学教育去了?他要与现实结合。我也参加了。这是我们这代人的特点。所以我们不可能搞纯文学研究,但我理解。我的研究生如果能搞,我一定会支持。形式主义不是不能搞,文体史也可以搞。但将自己熟悉的东西扔掉,把生的东西捡起来,对于五六十岁的一群人很难。文体史应该是你们这一代人搞。
邵:您写了这么多书和文章,自己最满意的东西是什么?
吴:比较满意的还在《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那本书写得也不深,但当时还算是一个开创性的东西,在此之前,谁是海派作家也没有划定,我划定出来了,现在也没有大的突破,虽然可以增加几个,减少几个,但没有大的突破。基本上,谈起海派来,作家都在这里面,而我当时划定的海派作家,一半以上都是原来不谈的。后来大谈海派。我还看到有人大谈“东吴女性作家群”,是我那本书最后结尾的东西。后来把它扩大了——“东吴女性作家群”,以前都是没人谈的。冯亦代先生专门为我这本书写了书评,发在一个民主党派的刊物上。他说自己不知自己是“海派”,看了吴先生的书,还真正服气,找到了自己的根,这真是我作研究工作以来获得的最大光荣。
标签:文学论文; 现代文学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作家论文; 古典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