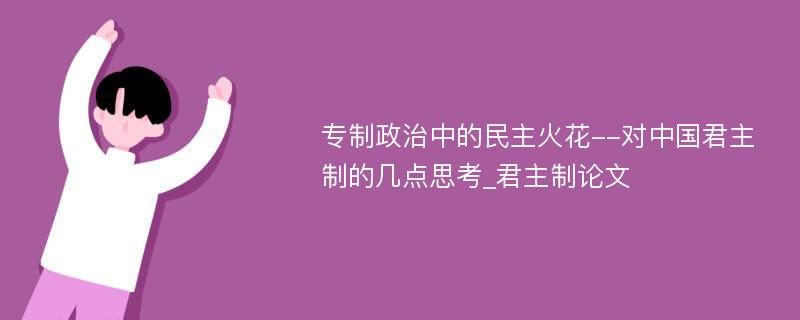
专制之中的民主火花——对中国君主制的一些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君主制论文,中国论文,火花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自从宣统皇帝被赶下台,“君主制”就成了“专制”与“独裁”的代名词,非但乏善可陈,简直成了人人见而啐之的落水狗。宣统之前的中国政治自然也就变成了一团漆黑。鲜有把君主制与民主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与探讨者。
其实,在中国的君主制中,除专制与黑暗之外,也蕴藏着一些民主资源,其中的精萃还被许多发达国家借鉴过。作为遗产,它是中国甚至是世界的骄傲。
说到民主资源,首推科举制。中国的科举制乃世界文官考试制度之嚆矢。它源于隋,兴于唐宋,终于清。这个制度赋予了多数人(极少数从事不道德、不体面职业者除外)从政的权利。只要考试合格,即便叫化子也可能入阁为僚。这使得大臣与官僚中,总能保持一定比例的“新生代”,防止了因“世代为官”而产生的惰性与腐败。中国的科举制的最大特点是,不承认“同等学历”(同等学历很容易为舞弊提供口实),人人都要走文童而秀才、秀才而举人、举人而进士、进士而翰林(明清时,在科考中选一部分人入院为翰林官)的路,这样就基本保证了在考场面前人人平等。考试中举的阁僚,书生气极盛,加之不谙官场世故,多有犯颜直谏者,故而往往能激发出些许民主的火花。最主要的是,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公正的原则,对整个社会起到了较好的示范效应。西方最早实行文官考试制度的是英国,而英国人说,他们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引进的。日本又是从英国引进的,算起来,在文官考试制度方面,日本当属小子辈。当然,明清八股文的考试形式不无弊端,但这丝毫无损于科举制的价值。科举制好比美食,八股文好比骨鲠,只要吐出鲠骨,美食尽可享用。
在中国的君主制政体中,还可以窥到些许制衡机制的雏形。在某些方面,甚至与现代共和制的制衡机制庶几近之,令人惊叹。比如,西汉设置不定员的谏大夫,东汉改称谏议大夫,宋朝还设置了谏院,谏议大夫的本职工作就是规谏朝政缺失,提出意见建议。报喜不报忧是一种失职,要受处罚。中国人也许会掩饰自己亲属的过失,但大臣,特别是谏官,一般不会掩饰君主的过失。正所谓,“君有过则谏,父有过则隐”。重大决策,君主可以召集心腹,策划于秘室,但不一定能在朝廷上获得通过。朝廷对于君主具有一定的制约力。一般来说,君主总要受到来自三方面的制约:一是来自臣僚特别是谏官的制约;二是来自法典的制约;三是来自“祖制”(惯行)的制约。即使是最专制的君主,也不可能完全无视这三方面的制约。
我国从明开始,吏部尚书(负责军事的最高官员)一职就由文官担任,一直延续到清末。这对于防止军权凌驾行政权,防止军队干预政治,保持社会稳定颇为有效,至今为许多国家所效法。而且我国很久以前就有了避嫌制度,基本上做到了本省人不做本省的官,在审案等场合,与案情有瓜葛的官员还要进行回避。
民主的政治必须以“简”为本。如果官制设置叠床架屋,官员人浮于事。就不可能奢望廉洁的政治。我们的先人在这一点上,同样给世人上了生动的一课。明朝,以我泱泱大国,全国文职官员却只保持在区区12500人左中的水平。套用现代的话,这是不可思议的简政。 不仅让今人自豪,恐怕也会令今人汗颜。
按民主含量的多寡,可以把政体分为三类:寡头政体、君主政体与共和政体。君主政体自然不如共和政体民主含量高,但远远强于寡头政体。寡头政体的最高统治者,以一己的智慧与意志实施统治,视法律、监督、制衡等限制自己的因素如草芥。臣与民都不过是寡头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寡头政体距离理想的民主境界,比君主制政体远得多。寡头政体是对君主政体的一种反动。我国传统的君主制政体中,有一种自发地抵御寡头倾向的机制。这种机制就是合谏与附议。在谏官势单力薄时,君臣置个人利益于不顾,纷纷喊上一句“臣请皇上三思”,这对皇帝极具威慑力。这一点,在今天仍然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
比起共和制,君主制算是专制的,落后的。但共和制的大厦绝不可能凭空而起,它需从君主政体中汲取营养。我们在批评延续了两千年的君主制的同时,也该承认其中的合理因素,同时褒奖它对人类的积极贡献。如果我们对先人的文明成果不屑一顾,甚至弃之如弊履,就不仅仅是对先人的不负责,说重些,则有民族虚无主义之嫌。
(二)
学者中多有热衷科举制话题者,叙辨考论,酣畅淋漓。
科举制乃选择官僚的一种机制。大凡机制都有客观(如“看不见的手”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与主观之分。科举制自然属于主观的机制。在科举制之前,没有官僚选择机制,随机地确定官僚,偶然性大,不规范,不公平,质量也无从保证。有了科举制,情况就变了:由无序选择到有序选择,偶然性减少,且规范,公平,质量也有了保证。她体现出中国人深邃的智慧与对公平的孜孜追求,让人不由得为之击节,这或许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
现代政治学把治理国家的人员分为两类:政治家与官僚。世界通行的分法是:职务高于部长或第一副部长的,称作政治家;这一界限之下的称作官僚。这种分类方法基本也可套用古代的君主制。皇帝、王侯及重臣为政治家,其余受禄为官的都算作官僚。古代君主制,受历史局限,不可能建立政治家的选择机制,因为那样做,也就不称其为君主制了。但建立官僚的选择机制并不会改变君主制的性质。于是,聪明的古人就把政治家与官僚严格地分开了。这是当时的人在政治领域力所能及的极限了。确定政治家,采用世袭、君主钦定、竞争等多种手段,而选择官僚主要依靠科举考试(部分官僚通过科举制选出,另一部分通过其它方式选出)。
由于中国历代都不承认同等学历,加之科考制度森严,科举制的规范性与公平性基本可以保证。对此质疑者也并不多。这里仅想对科举制之可行性稍施笔墨,说明科举制(包括八股文)思路包含理性成份,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道风景线。
对科举制之科学性提出訾议者并不少。“考试反映不出真才实学”论古已有之,且至今未泯。这种看法过于求全责备了。真才实学永远也不可能被精准地量化出来。李白与杜甫孰高孰低,谁人知晓?我们只知道他们都是饱学之人。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给他们分出上下来。科举制是一种选官的机制,最终鹄的,是网罗一批精英,并任用之。科举制不是分辨才学的机制,它不可能精准地鉴定每一位应考者的才学。如果“只有文化人才可能考中”的前提成立,那么,考中者与落选者谁的文化水平更高的诘问就成为了多余。关键在于,不能让没有文化的人混入最后成功者的行列,显然,这一点并不难做到。
如果大的侯选群有了质量上的保证,那么,剩下的就是如何保证公正筛选的问题了。公正筛选对考试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评判时有标准的范式,使评判者的主观好恶难以起作用;第二,考试的格式要复杂到很容易制造出差别。八股文就是这一思考方法的产物。它把文章的鉴别取舍规范化甚至定量化了,从而解决了文章难以统一评定的难题。它繁复的程式又极易制造出差别。而且还有防止舞弊之效。八股文确实反映不出真才实学,但无真才实学却绝对做不出好的八股文来。从许多现代社会的考试方法中都能看到八股文的窠臼。国外的,如托福考试;国内的,如对各种科研基金申请的考评(申请科研基金所不可或缺的“开题报告”,简直就是现代八股文,这个报告对于申请成功与否至关重要)。我们不妨设想:如果没有八股文,作文时任凭考生信马由缰,岂不难坏了判官。让评判者如何判卷?家鸡野鹊,各有殊音。有爱家鸡者,有爱野鹊者,公婆之争,岂有终日?最终还不是落得个“以权选官”的结局。所以我说,作为一种思路,八股文是科举制的一个有机部分,同样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它不愧现代考试范式之滥觞。当然,作为一种文章体裁,八股文蹩脚得很,早就该由更好的东西取而代之了。但无论多好的形式,都只能落在八股文思路的延长线上,而不可能另起炉灶,完全脱离与八股文的干系。
现在,由科举制演化而来的文官考试制度已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广为采用。她意味:国家官僚来源于普通民众,意味入阁为官简单到只需让人家考一考,基本没有其它附加,意味官级的晋升不再取决于上司个人的好恶(文官考试不仅解决官僚的初任问题,也解决晋升问题),意味着“官”字并不一定非要与那个“脏”字相伴相随。……而这一切奇迹,都是受科举制(包括八股文)的启示后发生的。可以说,中国人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可惜,我们自己久居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并没有珍惜它,没有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
(三)
中国的君主制,能形成超稳定的体系,载沉载浮,安度劫波,主要是得益于存在一个超越个人——包括君主——的机制。唐宗、宋祖、康熙、乾隆等有为之君尚且动摇它不得,遑论一般的君主。中国的皇帝生杀予夺,大权在握,但他们无力改变自己也必须遵守的制度。皇帝也是人,也有个性,他一定事事都想按照自己的意志做,然而谈何容易,他必须遵从中国的逻辑;最高的权力是以服从权力规则为代价的。皇帝管臣民,规则管皇帝。
这个规则最主要的内容是,不允许皇帝独来独往。臣僚与皇帝形影相吊,难舍难分。皇帝实际上被置于臣僚的“众目睽睽”之下,皇帝与臣僚一起做游戏,欲罢不能。皇帝做出过分之事,实难堵臣僚的攸攸之口。就连皇帝的起居与私生活也被记录在案,皇帝难言有什么隐私权,甚至瞒着皇后与嫔妃偷情都是件很困难的事。如果皇帝越过了雷池,臣僚会立即给以颜色,反复规谏,直到皇帝“就范”。汉高祖多次欲立如意为太子,由于多数臣僚劝阻而未果。唐玄宗十分想保住爱妃杨玉环之命,但面对一片跪倒在地的文臣武将,顿时语塞,不得不眼睁睁看着心上人归西。皇帝若一意孤行,拒谏饰非,也有“死谏”或“尸谏”的。王累谏刘璋不要让刘备入川,刘璋不听。王累就把自己用绳索倒吊于城门之上,见刘璋无意改弦,遂断绳坠地而亡。死谏是很厉害的,等于把昏君的骂名留给皇帝,把忠臣的美名留给自己,固而对皇帝威慑力极大。有时皇帝也拒谏,但多成为“反面教员”。刘备不听诸葛亮之言,兴师伐吴,为关羽报仇。结果不但损兵折将,而且上演了白帝城托孤的悲惨一幕。刘备如此执坳,堪称异数。这个故事似乎就是讲给皇帝们听的。
臣僚对皇帝的制约,是中国历史上较少出现寡头政治家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中国很早就崇仰教化,不太迷信个人的能力。皇帝一般并不觊觎军事家、思想家、学术泰斗等身份。刘邦就说,论运筹帷幄,朕不如张良,论知人善用,朕不如肖何,论带兵打仗,朕不如韩信,论聚款筹粮,朕不如陈平。刘邦讲这些话丝毫动摇不了其天子的地位。因为皇帝就是皇帝。皇帝当然也需要证明自己统治有理,但这个工作是由兖兖圣崽们做的。既然皇帝在许多方面并不一定比臣僚高明,听一听臣僚的意见也就顺理成章了。皇帝在权力上是绝对集权的,但在决策时,更多地依靠群体的智慧。
总有臣僚唠唠叨叨的,皇帝也不痛快,但江山稳固比心里痛快更重要。所以皇帝能够自觉地把自己置于臣僚的监督之下。这确实是专制之中的民主的火花。
但对这个“火花”也不宜评价过高。臣僚的监督终究建立在维护皇帝专制的基础之上。况且,如果说皇帝给了别人批评自己的权利,也仅仅是给了臣僚而已,百姓无缘沾此皇恩。在中国几千年君主制的历史中,百姓始终没有丝毫的发言权。中国人之所以千军万马一齐奔向仕途的独木桥,就因为做了官,不仅名利双收,而且取得了弥足珍贵的特权——“发言权”。
由于臣僚有一定的发言权,也产生了弊端。洞开臣僚的言路,并不意味仅仅是臣僚可以向皇帝提意见了,臣僚也可以假公以济私,利用这个权利攻击、诽谤与自己不和的其它朝臣,挑起“窝里斗”。皇帝给予臣僚的发言权越多,臣僚借此互相攻讦的机会也就越多。苏东坡早就有所察觉,才叹息道:“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廓庙,则宰相待罪”。于是,养成了“打小报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等恶习。特别是谏官,身显言重,常常会挑起臣僚之间的内讧。
康雍乾时的文字狱,多起都是因告发而罹祸。如庄廷钺明史狱、戴名世《南山集狱》、查嗣庭试题狱、吕留良文选狱等,都是在臣僚告发之后做成的。告发正好给了皇帝以最好的口实:不是我非这么做,是臣僚在逼我做,臣意不可违。
聪明的皇帝往往可以利用臣僚的互咬,坐收渔翁之利。而臣僚“阋于墙”,又大大削弱了国家的实力。北宋,苏东坡就险些死于谗言之下,虽得偷生,作为谪官逐臣,终生落魄。一个杰出的人才就只得终生与诗赋为伴了。甲午战争,战端未开,我内部方寸已乱,与其说中国人输给了日本人,不如说,中国人输给了自己。
看来,世界上的事,有其一利,就得防其一弊。
(四)
中国古代,有因官制冗赘而致祸的先例,宋朝为最,最甚时有过一官百人为之的事情,最后导致了宋的倾覆。东汉灵帝时,宦官张让等十二人同任中常侍,封侯。造成“十常侍之乱”。但也有不少朝代贯彻了简政的原则。
刘邦就深谙简政之道,下了非刘姓不封王的诏书。当然,这是为巩固刘氏江山,但也有消肿之效。乱封王的朝廷几乎都没有好结果,太平天国的“王”动辄以百位计,国力要承受多大消耗,可想而知。
中国多数王朝的官职,是一主一副,或不设副职,鲜有两个以上的副职或并职。官制精简,以清为甚。雍正九年,设置了“协办大学士”一职,从六部尚书中选任,辅助大学士管理内阁事务,初无定员,到乾隆十三年定为满、汉各一员。乾隆十年,对大学士进行定员:大学士专以三殿(保和、文华、武英)三阁(体仁、文渊、东阁)入衔,满汉各二员,为正一品官。明清大辟之年的科举主考官也都是两名,一正一副。
为避免官制臃肿,很早以前就已兴兼职。如两汉设给事中,顾问对应,讨论政事,其性质如清代的“内廷行走”。元代时,给事中兼修起居注,不再另置专门负责起居注的员官。我国战国时设尚书,魏晋以后尚书事务益繁,开始分曹治事。隋代始分六部,唐代确定为吏、户、礼、兵、刑、工。从隋唐开始,中央首要机关分为三省,尚书省即其一。明代,不设尚书省长官,六部尚书兼“国务大臣”,清代沿袭未变。就连官满为患的北宋,也常以执政大臣兼中书侍郎,代行中书令之职。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八旗官平时管理民政,战时充当将领,一身而兼二职。日后,八旗腐化,应当别论。至于一地长官(县或知府)兼管行政、司法与财税工作,更是妇孺皆知的事实。
中国多数王朝都重视调节官职,以需定职。以至于各朝代不但官职名称不一,而且实质内容也鲜雷同。如奉朝请,本为贵族官僚定期朝见皇帝的称谓,属闲官。南朝时奉朝请逾六百。隋初改奉朝请为朝请大夫、朝请郎。朝请郎在元代时被废除,朝请大夫在清朝时被废除。清顺治十一年,顺治在宦官吴良辅的怂恿下,设立了并无大用的所谓十三衙门(司礼监、御用监、御马监、内宫监、尚衣监、尚膳监、尚宝监、司设监、尚方司、惜薪司、钟鼓司、兵仗局、织染局等),在宫廷内侍奉皇帝及皇族,由于人浮于事,自相勾斗,顺治十八年被裁撤。
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对明清的有关文官的情况做了如下的描述:晚明,全国共有约12500个文职,一半人在京城, 另一半分布在十五省和大约1500个地方机构中。张仲礼曾计算过在19世纪差不多有20000个文官职位,亦是半数在京, 半数在十八行省与府州厅县的机构中,尽管此时全国人口增加了两倍,但政府官员只增加约60%。清朝文职官员平均每县五人,管辖人口却达250000人之多。
中国一些朝代官制之简,连外国人都为之击节,然而其缺失亦于此肇端。朝廷对地方官员名额控制甚严,也有居心叵测的一面,朝廷压缩地方文官的支出,是想将节省下来的银两充实中央财政。地方经费拮据,由其自行解决。这实际上等于授给了地方官以不轨的借口。京城官与地方官的比例失调,这主要是因为皇帝为了“安全”,往往以甲牵制乙,编制无形中就膨胀了起来。又如,地方官员兼管行政与司法的作法,也产生许多流弊。行政官员身兼二职,又没有其它独立的评定或裁议机构,很难保证司法的有效性与公正性。司法诉讼往往与地方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冤假错案,叠床架屋。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平反冤狱案,皆不是通过有效的机制,而是由于在官员互咬中,冤狱才侥幸得以矫正的,如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中国历代皇帝都没有考虑过通过司法保证人权的问题(哪怕是浅层次的思考),将“爱民”作为口头禅的皇帝并不在少数,然而,没有一个皇帝想到过,司法诉讼,人命关天,应扩大司法官员编制,多投入些人力、物力,更遑论建立公正司法的机制了。历代王朝一直沿用逼供信等迂腐不堪、于公正客观等原则背道而驰的方法。逼供信成为了中国的一个难堪的遗产。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准则是,行政、司法分立,互不逾越,互相制约,实现效率与公正的最佳结合。西方早在数百年前就开始将这一准则付诸实施。所以,到二十世纪初,司法已成为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差距最大的领域之一。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