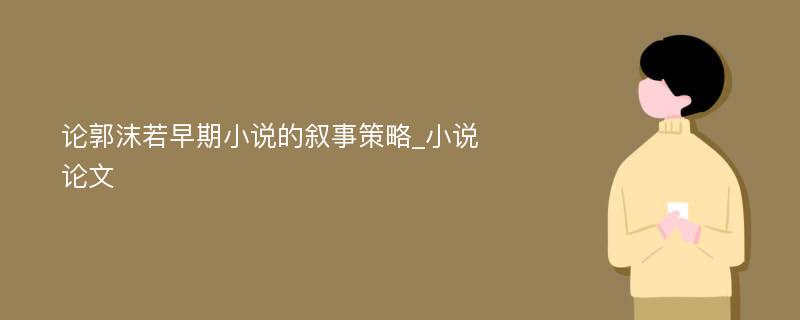
论郭沫若早期小说的叙事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策略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郭沫若生前出版的作品集中,《沫若文集》要算作者本人经手编辑的最后一套、也是收录作品最多的一套作品集。该文集第5卷辑录的38篇小说中,早期创作的小说占23篇(内含历史题材小说2篇),其中至少有15篇明显属于作者对自己日常私生活片段或情感经验的写实。笔者认为研究此类小说时,避免照搬“私小说”一类日本文学中带有特定含义的固有名词而采用“自叙小说”这一说法比较妥贴。为了使论考更具说服力,本文选择了《牧羊哀话》①《残春》②《梦与现实》③《昧爽》④和《喀尔美萝姑娘》⑤等1924年11月告别留日生活归国以前的一批代表作品为考察对象。
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郭沫若的自叙小说并不像日本大正时期盛行的“私小说”那般刻意忠实于对作者私生活的“平面描写”和“客观描写”。他的自叙小说所表现的写实空间里,几乎毫无例外都编织有以梦境这一形式出现的虚构时空。究竟这种梦境的设定对要求写实的自叙小说有何意义?笔者认为回答这个问题有助于正确解读郭沫若乃至其他早期创造社作家的文学叙事。
应该说最普遍反映郭沫若自叙小说个性特征的是梦境的设定。相比之下,其他虚构手法如人称的假借替换等都显得无足轻重。郭沫若在1923年写下的评论《批评与梦》中坦率地谈到过他自己受到荣格心理学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深刻影响。荣格心理学认为所谓梦,不外乎是一种人的自然调整的心理过程。它酷似人的身体机能所拥有的补偿功能。从这一意义上讲,梦具有三种补偿功能。其一是能够对自我结构引起的目前的歪斜进行修正,并能引导人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去理解自己的态度和行动。其二,梦作为人内心的自我表现,它能够让个性化过程中出现的必然与现实中的自我发生碰撞。其三,由于梦中自我的同一性是觉醒状态下的自我的同一性的一部分,故梦亦是呈原始形态的自我在某种程度的意识水平上欲对其同一性所依据的劣等感觉结构进行直接改造所做的一种尝试。⑥
依循梦这一线索对郭沫若早期小说群进行梳理,很容易发现自处女作《骷髅》⑦开始,郭沫若在《牧羊哀话》《残春》《喀尔美萝姑娘》等较为成熟的早期作品中插入了梦的场面。如果对梦的描写仅止于一般意义上的情节渲染,那倒也无须小题大作。然而郭沫若小说中的这些梦却并非点缀性插曲,而是出于作品本身结构上甚至思想表述上的绝对需要。而且,尽管同样是梦,作者早先作品中的梦和后来作品中的梦竟然意趣迥异。笔者认为:这是作者有别于“五四”主流启蒙叙事、始终置身于与“现在”的潜对话中的一种浪漫主义文学叙事策略。
处女作《骷髅》和《牧羊哀话》中主人公“我”的梦境,多少属于猎奇性故事情节的需要。《骷髅》中作者梦见自己从美女死囚身上割下的人皮复苏,听得耳畔有声音在叫:“喂,快还我的爱人来!”睁眼一看,门口站着一具让人毛骨悚然的死人尸骨。《牧羊哀话》中的“我”梦见羊群、狮、豹、虎围着一对身体赤裸的少男少女在墓地翩翩起舞,突然一个矮壮的凶汉出现,手持利刃迎面刺来……从梦的荒诞性上看,与这两篇猎奇故事所显示的浓厚异域风情和斑斓刺目的色彩不无相配。尽管未见得表现了作者的深邃的思想情感,但无疑在假借故事的传奇性来构建怪谲而神秘的欲望叙事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在后来创作的《残春》《喀尔美萝姑娘》以及《昧爽》和《梦与现实》这样一批作品中,梦的叙述本身就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或者说梦的设定即是某种观念的折射,故带有一般性直叙所不具有的深层意蕴。梦里的主人公成为挣脱了家庭、义务、责任以及社会道德等现实束缚而获得了解放的“自由的存在”。这样的梦的穿插实际上为我们把握作者的深层意识结构提供了某种较为可靠的暗示和参照系。
二
郭沫若最早在小说《残春》(1922年4月作)里描写人的潜意识。本文先对这篇小说里的梦进行解析,以考察作者设置梦境的原始动机。
小说《残春》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第一人称“我”是日本某帝国大学医学部的中国留学生,与妻子和几个孩子同住福冈。一天,友人贺君因自杀未遂被送进了门司港的医院。“我”随前来报信的白羊君前往探望。在医院里,“我”与萍水相逢的年轻S护士一见钟情。然而白羊君也倾心于她。为此“我”在跟S护士的交往中时常为一种莫名的罪恶感所困扰。尽管如此,“我”依然做着夜里与她在门司笔立山幽会的梦。梦中,主人公的妻子觉得自己已被丈夫所弃,悲伤之余精神失常,亲手杀死了两个年幼的儿子。
关于《残春》的创作,郭沫若在《批评与梦》一文中吐露:“我那篇《残春》的着力点并不是注重在事实的进行,我是注重在心理的描写。我描写的心理是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这是我做那篇小说时的奢望。”⑧
笔者认为,就《残春》而言,郭沫若所说的“心理描写”和“潜在意识的流动”都是靠梦境呈现出来的。在此,梦不仅是作品的构成部分,且为小说全篇之高潮。很明显,作者把《残春》这篇作品当做了表现潜意识流的实验台。然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流,而且故事里的梦又意味着什么呢?
关于以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的潜意识流,《批评与梦》一文已经显露出郭沫若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荣格心理学的理解。他认为,前者“是主张梦是幼时所抑制在意识下的欲望的满足”。精神分析学家们对梦所作的解释是“梦是昼间被抑制于潜在意识下的欲望或感情强烈的观念之复合体,现于睡眠时监视弛缓了的意识中的假装行列”⑨。
主人公爱牟钟情于S护士。S护士亦为这位风度翩翩的医科大学生所吸引。然而爱牟是有妇之夫。这番恋情自然不会有皆大欢喜的结局。其实,由于这场恋爱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了结局,所以处于觉醒状态的主人公一直将感情抑制在潜意识之下。这种人为的欲望压抑直接导致了梦中潜意识层面的活跃。凭心而论,爱牟喜欢S护士,而且渴望与她幽会。现实中的爱牟因为受到道德观念的制约不能将自己的愿望付诸实现。然而,实现不了并不等于不想实现。在梦里,道德观念的监视和制约被解除,人的欲望便还原为原始自然状态。小说中爱牟在梦中与S护士幽会于笔立山,这一场面可以说是主人公昼间未能得到满足的欲望的宣泄。S护士诉说胸部不适,爱牟为她诊察时看见了她美丽的胴体。一种对美的占有欲因此而蠢动。在意识呈解放状态的梦幻空间里,昼间的罪恶意识也以另一种姿态凸显了出来。正当爱牟和S护士肌肤相亲之时,同样有心于S护士的留学生白羊匆匆赶来告知爱牟家中发生了母杀亲子的惨案。白天的爱牟已视白羊为情敌,梦里白羊在微妙时刻出现阻止爱牟和S护士的关系实质性发展。在潜意识中,对爱牟来说,家庭、孩子、特别是妻子的存在成为他爱情自由的障碍。白昼间的罪恶感在梦中以遭受天罚的终结形式出现这也不难理解,但妻子的疯狂和亲子的被惨杀不能不说是这篇小说始料未及的结局。“由贺君的发狂而影到妻的发狂,由晚霞如血而影到二儿流血,Sirens的联想而影到Medea的悲剧,由Medea的悲剧而形成梦的模型。”⑩作者在创作时由此及彼的奔放联想,最后让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美狄亚为报复丈夫对自己的遗弃而亲手杀死自己的两个儿子的惨案作为自己寻求性爱自由的高昂代价。这种由此及彼的联想同样适合思考对文学的执著追求和受到现实家庭生活束缚这两者的关系。在此,我们可以观察到作者在梦境里将理想与现实极端地对立起来的生存焦虑和人生观。
接下来考察写于1923年的《昧爽》和《梦与现实》。我们将会看到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对梦境的安排以及暗示性的运用等方面呈现出来的明显变化。
《昧爽》这篇作品可以说是作者用幻听和幻觉的荒诞叙事手法展现给读者的作者私生活片断。主人公“我”夜晚孤零零地睡在床上,梦中听见几只臭虫像幽灵一样在聊天。它们吸饱了“我”的鲜血,口口声声高喊着它们是热爱和平的种族,不应该遭到人类的戕害。“我”愤愤不平地找到这些吮吸人血的饶舌家伙,并毫不留情地将它们歼灭。
故事的怪谲荒诞让人联想到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的《变形记》,而叙事方式以及在幻想世界中描写现实的手法又让人不禁想起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这篇貌似荒唐的小品无疑暗示了上海这所冒险家乐园中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对立。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的象征性意义上观察到作者的煞费苦心。第一是小说主人公“我”在故事中扮演伸张正义的角色;第二是让靠吸人血活命的臭虫们以伪善者的面孔粉墨登场;第三是让第一人称从梦中醒来把它们赶尽杀绝。
我们看到,郭沫若在试图给某种观念赋予梦的形态并使之具象化。梦幻与现实之间,有如不可逾越的“天堑”。正是由于现实之中欲望得不到实现,梦幻才被作者当做了实现和宣泄其欲望的舞台。笔者认为,这就是郭沫若凭借现代文学想象对生活进行诠释或干预的谋略。
《梦与现实》这篇作品不乏作者思想的闪光。作品的内容正如它的题目所示,由两幅画面呈现出鲜明的对比。一幅为梦境,另一幅为1923年上海的现实。梦中出现的是:明媚的阳光纷飞的蝴蝶,美女们在花园里向诗人泰戈尔赠戴花环;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23年上海滩的现实:灯红酒绿的街头衣衫褴褛的盲女乞丐,穷人饥寒交迫而浮肿的面孔……
笔者认为,这篇作品最大的成功,就在于作者意识到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并通过文学的手段使其具象化。然而,作者并没有将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直接抛给读者。如果说作者通过梦幻与现实的对比醒悟到了什么,那么它就是文中作者所指出的: “人生的悲剧何必向莎士比亚的杰作去寻找,何必向川湘等处的战地去寻找,何必向大震后的日本东京去寻找呢?”这段话对探索这一时期郭沫若的思想变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留学时期的郭沫若通过诗歌对自己的祖国表达出强烈的眷恋之情,从很大程度上讲,是由于他作为海外学子与祖国的残酷现实之间存在的物理距离。换言之,以《女神》和《星空》为代表的一批给同时代新诗坛带来巨大震撼的诗歌之所以诞生自生活在日本博多湾的留学生郭沫若笔下,除了作者的非凡胆识和新颖的表现手法等诸多因素外,恐怕更重要的还多亏了他那种与众不同的边缘视角。
1923年3月学成归国所见国内的腐败和百姓极端贫困使得郭沫若的思想发生了巨变。之前,他对社会的认识止于对穷人的同情和对富人的憎恨的感性层面。1923年4月以后的他通过对国内社会现实的体验而对好感情冲动走极端的故我进行了否定。1924年研读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事实上为他创造了一种契机。他的思想由此开始向社会主义急遽倾斜,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前的感性认识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质变,即嬗变为一种阶级意识。这一时期创作的《梦与现实》可以说恰好从侧面反映了这种思想濒临质变的前兆。
通过对《昧爽》和《梦与现实》这两篇作品的观察分析,我们发现郭沫若这一时期在小说中的梦幻叙事表现出三大特点:第一是观念性强;第二是极富象征性;第三是缺乏具体性。这种夹带几分浮躁的创作状态到了《喀尔美萝姑娘》中才有了明显的改观。
三
《喀尔美萝姑娘》可以说是郭沫若1924年8月写下的一篇双重人格者忏悔录。与同一时期其他自叙小说一样,它也是基于日本大正末年作者留学九州帝国大学私生活的写实。
小说仍然从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角度展开。“我”是位于日本福冈市某工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与妻子瑞华和两个孩子一起生活在日本。自从听妻子说附近街巷里有一位眼睛长得非常美丽的卖糖人儿的姑娘那天起,“我”那平静的生活水面就掀起了波澜。先是好奇心作祟前去窥视。不料一见钟情,坠入情网后不能自拔。现实之中“我”的人格逐渐开始分裂,白天放弃学习偷偷在她身边转悠,夜里和妻子同床共衾, “抱着圣母的塑像驰骋着爱欲的梦想”。然而,由于害怕暴露自己中国人的身份,怎么也不敢向日本姑娘袒露心中的爱恋。就这样,“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扮演着两种人格截然不同的角色。时而是爱家的好丈夫和慈父,时而是美的疯狂追求者。虽然偶尔也有经受不住良心苛责的时候,但到了必须在义务、责任与爱情之间作出选择时,“我”选择了后者。事态发展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我”变得像变态妄想狂似的羡慕医生可以随心所欲地“扪触女人的肌肤,敲击女人的胸部,听取女人的心音,开发女人的秘库”,甚至想象着自己是医生,去“摸她的眼睛,摸她的两颊,摸她的颈子,摸她的乳房,摸她的腹部,摸她的……”“我”在一种严重变态的单恋式爱欲泥潭里越陷越深,甚至到了置家庭和学业而不顾的地步。妻子越是温柔体贴, “我”越觉得她和孩子们是爱情的累赘。
然而,卖糖人儿的姑娘有一天突然失踪了。“我”像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病一样丧魂落魄。眼看就要大学毕业,可实验总是做不成功,毕业论文也提交不出。感到幻灭的“我”这才略微有所醒悟,并开始为自己有愧于妻儿的行为感到羞耻和悔恨。“我”终于无法面对自己,于是形单影只地走向大海,欲自绝于人生。
苏醒过来的“我”才知道自己被渔民救了起来。面对温柔地守候在旁的妻子,“我”终于如实地吐露了深藏在心底的秘密。妻子善解人意,让“我”重新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
大学毕业以后,“我”携家眷回到了祖国。不久,“我”得知自己心中深恋着的那位卖糖人儿的姑娘在日本某地当酒吧女郎后,又以实习为借口重返福冈。“我”打听到她给某商人做妾去了大都会东京,于是又找人借了钱,买了一把手枪和一包毒药,匆匆登上了开往东京的火车。
如果说《喀尔美萝姑娘》这篇小说与郭沫若其他早期小说作品相比有什么重要的不同的话,那么应该说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这篇作品的故事情节的完整性上。然而,笔者想论述的并不是它那异想天开的情节,包括以上介绍小说梗概在内,其目的都是为了验证作品的虚构性。
毫无疑问,小说的主人公“我”的人物原型即作者郭沫若自己。妻子瑞华的原型即佐藤富子(在作品中被虚构为中国人),其他的登场人物如卖糖人儿的姑娘、“我”的长女、S夫人以及“我”与S夫人之间的那段离奇的暧昧遭遇等都属于虚构。
作品中有这样一个场面:主人公“我”由于白天对卖糖人儿的姑娘追逐不舍,夜里便梦见了与这位美丽的少女密会。这个由梦幻构成的虚构世界又是怎样地层开,而这个梦本身又具有何等深刻的含义呢?
首先,小说情节的展开是作者浪漫情感的演化。在梦中失去了自控能力的“我”对卖糖人儿的姑娘朝思暮想,白天为了见她一面不惜逃课追到几公里以外的公园。公园的密会,使“我”那种病态的单恋急遽地转化为男女彼此的相爱。在那里,卖糖人儿的姑娘第一次袒露胸怀。原来她早就知道“我”这个大学生是有妻室的,尽管如此她还是愿意接受“我”对她的爱。姑娘和“我”深切地亲吻,向“我”表明了她也同样地爱“我”之后,突然间纵身跳下悬崖,投向翻着白沫的大海。
仅从以悲剧性结局这一点上看,这场梦与其他作品中安排的梦境并无多大差异。然而,必须指出的是,郭沫若早期小说中主人公对理想爱情的执著追求如愿以偿这还是第一次。根据这一独特之处,笔者认为把《喀尔美萝姑娘》视为郭沫若同类作品群的终极之作绝对不算过分。我们看到,在自由和责任的冲突之中,主人公一边采取逃避责任的方式而同时又试图使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正当化。他在选择爱情的自由之前首先对受道德约束的婚姻进行了清算。小说主人公说:“我爱我的瑞华,但是我是把她爱成母亲一样,爱成姐姐一样。”(《喀尔美萝姑娘》)对他来说,妻子是时常在一种“圣光”中生活着的人,就像“圣母玛利亚和永远的女性一样”(11)。妻子额头上的那种光辉对他来说,不啻“苛责的刑罚”。他在妻子面前总觉得不自在,甚至觉得痛苦。他认识到自己的婚姻“要算是别一种意义的一出悲剧”。然而,自从对卖糖人儿的姑娘一见钟情的那一瞬间,便“尝着了一种对于异性的爱慕了”(《喀尔美萝姑娘》)。此时此刻,在作品中的主人公眼里,妻子献身的爱与维护家庭的母爱完全属于一种与男女情爱截然不同的神圣而永恒的情感。比起那种神圣之爱(以妻子额头的“洁光”为象征)来,主人公梦寐以求的是自由奔放、有时甚至可能爱不成则转变成恨的惊心动魄的男女情爱。他羡慕那些未婚和没有子女的男人,感到自己像“是在茧中牢束着的蚕蛹”(12)一样被婚姻和家庭禁锢了自由。
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主人公这一系列复杂的潜意识活动都是在梦里,换言之即是在一种虚构的时空里进行的。现实中的作者并没有像在梦里那样将自由和责任极端地对立起来,或者毋宁说现实中作者的人生观由于本质上属于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断对自由和责任这两者进行调和的人生观,故他不可能作为真正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在现实中追求获得形而上的自由和超世脱俗的高洁。正因为如此,作者才会在人为构建起来的空想世界里追求这种欲望的实现。
郭沫若自叙小说中的人生叙事和理想叙事始终都融入了作者对生命的切身体验,始终都能看到作者自我的影子。根据这一特殊现象我们可以得知,郭沫若的自叙小说里的客观描写所表现的只不过是他思想的表层结构,而其深层结构则毫无遮掩地袒露在梦幻——这一虚构世界的层面。
《喀尔美萝姑娘》的问世显示出郭沫若自叙小说实验的终结迹象。在这篇小说里我们可以观察到他的早期自叙小说比较完整的形态。综观其主要创作风格,我们会发现,它们既不同于同时期国内主流现代文学叙事风格,又异于其他创造社同人对留日生活的描写。在1918年至1924年深秋的小说创作探索过程中,郭沫若随着自己的不断成熟而对自己的创作轨道不断进行了修正,并在自己的小说不为文坛所认同的逆境之中锲而不舍地探索着符合自己文艺观念的最佳创作方法。从这个角度讲,《喀尔美萝姑娘》堪称他早期实验小说的集大成之作。
在自叙性告白小说中巧妙地构筑起一个理想的梦幻时空,在这个虚构的世界中大胆地实现自己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欲望。在现实和梦幻、真实和谎言、写实和虚构的空间自由无阻地穿行来往,并借此向读者展现出作者最真实的思想和姿态。笔者认为,这种创作方法应该说是郭沫若早期小说创作探索的最终结果。
四
20年代前半期,也就是中国文坛上如实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占绝对优势的那段时期,对郭沫若来说,小说创作只是自我表现的手段之一罢了。郭沫若是在20年代初向中国新诗坛推出了划时代诗集《女神》并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开始向小说领域发展的。小说创作初期并没有固定的模式,甚至其小说观念都在频频发生变化。在写法上他总是不断地探索,总是在力求寻找一种最适合自己的创作方法。郭沫若早期小说观念的变化显示出一种逐渐成熟的进化过程。他从注重猎奇素材的现代怪异传奇小说开始起步,直至发展为自叙小说这一较为稳定的创作模式,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笔者认为,郭沫若的自叙性告白小说最大的特征应该是有意识地在写实性小说这一真实世界里设定一种虚构的时空,并在梦境中谋求自己理想的实现。
就郭沫若的一生来说,1914年1月至1924年10月的10年属于他留学日本的时代。在这期间,他与创造社其他同人一样生活在异国他乡的日本。他不仅亲身接触和体验了20世纪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同时还受到了来自于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之精神和尊重自我与个性的思想的熏陶和淬砺。然而,由于留学生这一身份的局限,他不可能对外部世界有更细致的观察。既然不能了解国内各阶层的生存方式与现状,自然就无法对他们的语言风格、喜怒哀乐以及感情的表达方式有所把握。想必此乃为何郭沫若最终选择自叙小说作为最适合自己的表现形式的原因。郭沫若对在同时代日本被称为“私小说”的自叙性告白小说进行了多种改造,而这种改造显然是为了克服日本“私小说”的致命硬伤——无社会性和无理想性。仔细想来,他的这些努力并非没有意义。郭沫若笔下的“我”这一人物形象,可以说也就是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者的放大了的自我形象。透过这种放大了的自我形象,我们还可以看到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无比憎恨和对理想王国的无限憧憬。
注释:
①1919年11月15日发行的文艺杂志《新中国》1-7卷。
②1922年8月《创造》1-2卷。
③1923年12月23日《创造周报》第32号。
④1923年9月30日《创造周报》第21号。
⑤初出1925年2月《东方杂志》第22卷第4期。
⑥James A.Hall著,氏原宽译《荣格派关于梦的解释——理论与实际》,第38-39页。此处引自日本创元杜昭和60年11月10日初版,汉译笔者。
⑦据《创造十年》第2章记述,郭沫若创作了处女作小说《骷髅》之后将之投向了国内的《东方杂志》。由于没被采用,退回的原稿被作者愤然付之一炬。
⑧⑨⑩1923年上海《创造》季刊第2卷第1期。
(11)郭沫若小说《歧路》,初出1924年2月《创造周报》第41号。
(12)郭沫若小说《炼狱》,初出1924年3月《创造周报》第4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