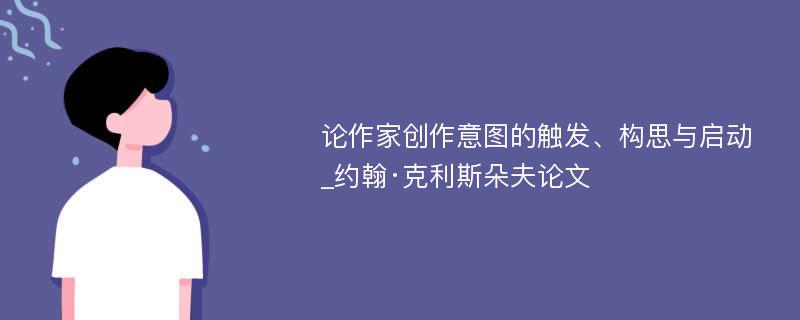
论作家创作意图的触发、受孕与萌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图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任何作家的创作都是从一个最原始的念头,最简单的意图开始,而后经创作主客体一系列复杂的内外信息交流、融合和建构才最终生成一部文学作品的,作家的创作意图从原始触发到交感受孕,至最后萌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生成过程,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具有着深潜隐伏的本质原因。
关键词 创作意图 原始触发 交感受孕 萌生 生成
如果我们把文学作品视为一种生命物,对它的最早的追索,就应该是去探究这个生命物是如何交感受孕,是怎样获得生命的。如果我们把文学创作视为作家艺术家多种心理活动吹奏出的一曲复杂多彩的交响乐,那么我们对它最早的追索,又应该是去寻找它的第一个音符是怎样诞生和吹响的。从追根溯源的角度来说,作家进行任何一部作品的创作,都必有一个最原始的念头、最早的契机和最初的打算,或可称之为“最初本心之一念”。这最原始的念头是从何而来,最早的契机是怎样形成的,最初的打算是怎样产生的?换句话说,作家是从哪里开始孕育他未来的作品的呢?他的创作意图是如何触发、受孕与萌生形成的呢?这便是创作发生论首先要探究的一个问题。
一、创作意图的原始触发
许多作家在回忆他们的创作经历时,往往谈到他们最初的触发冲动:罗曼·罗兰创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最早的触发是在1890年春天,其时他站在罗马郊外的霞尼古勒山上,“夕阳照耀,罗马城上红光闪闪。围绕着城市的田野如同一片汪洋,天上的眼睛吸引我的灵魂。我立足不定,失去了时间概念。忽然间,我将闭着的眼睛微微张开。在远处,我望见祖国,看到我的那些成见和我自己,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生命,自由的、赤裸裸的生命。这是一道闪光。……就在这儿《约翰·克利斯朵夫》开始被孕育。当然,他那时还没有成形。可是他的生命的核心,已经下了种。”①
司汤达写作《红与黑》是由于看到一份《司法公报》上的一桩案件,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是听朋友讲了一件普通的风流韵事,雪莱创作历史名剧《沉西》是由于看到一幅令他激动赞赏的贝特丽采的画像,巴金写《春》是在日本时从一四川女学生嘴里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杨沫写《青春之歌》是早在抗日战争时看到一本名叫《牺牲》的书,上面印有大革命失败后,许多烈士的照片、生平和遗书……
这些作家受偶然因素的触动而生发出创作欲望,创作冲动的情形是各不相同的,能够牵引和触发作家创作意图萌生的情况是多种多样随机而生的,这意味着,创作意图的触发是一种机会,并不具有什么确定的必然性,而是显示发生的倾向,谁也无法预知它将在什么时间地点,需要什么条件和将以什么方式产生,不但理论家无法预言,就连作家艺术家本人也无法确知,甚至于事情发生之后依然说不清自己的创作意图是因何而起,何时诞生的。
譬如鲁迅创作的《阿Q正传》惊世骇俗名满天下,但他在讲创作的成因时,述及“阿Q的影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指孙伏园编副刊约稿催促——作者注),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一点,就是第一章:序。”②他似乎对何时心中产生阿Q的影象、怎样产生的,从来也没在心,因此说不出一个明确的触发情况。曹禺在谈《雷雨》的创作时,也是说“自己也莫名其妙”,说不清为什么而写的,汪曾祺在回忆写作获奖短篇小说《受戒》时也说过。他感觉奇怪:“怎么会在43年之后,在我已经60岁的时候,忽然会写出这样一篇东西来呢?这是说不明白的。要说明一个作者怎样孕育一篇作品,就象要说明一棵树是怎样开出花来的一样困难。”③不过即便是这样的情形,我们也不能就认为作家创作意图的萌生是不需要任何事件的触发、信息的刺激的,而宁肯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无论它是洋洋百万言的鸿篇巨著,或是五、七言的一首小诗,最初皆是由一丝感触、一个意念、一件小事、一次遭遇、一个人、一句话、一物一景等触发而生,然后开始它酝酿构思、创作生成的历程。古人所谓:“夫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是极有见地的。
对于一个敏于感受的作家来说,创作意图触发的机会很多,以致于很不在意,未能一一觉查和记住。艾芜在回答《文艺学习》编辑部的问题:“你的创作冲动是由什么引起的?是由一件事、一个人、或者由于其他?”时,他回答:“关于创作的冲动,可以说随时都有的。”只是有些冲动被自己压抑下去了,因为觉得价值不大,而有的则“象一颗种子似的,种在我的心地上了,必须培养它发芽生叶,开花结果,达到可以收获的程度……把他写在作品里了,才能罢手。”④
对触发引动作家创作意图萌生的触发物细加考察不难发现,具体触发物虽然纷繁杂多,各不相似,但归纳起来不外两类,一种是来自生活来自外界的感性事物,比如一本书、一件物、一个人、一个故事、一个地方或是一种声音、一段乐曲等,它们大多具有客观实在性,同时还具有审美的价值属性,因而能够与作家的心灵相激相撞、协调共鸣,我把这类事物称为具体的感性触媒。另一种是来自心灵中的具有主观性的事物,如某些思想、情感、概念、观念、理性之类的抽象物。它们存在于心中,是内在的观念,而不是外在的感性事物。它们是主观的,但基础和原因也是来自客观世界的。作家主观的思维活动触动了它们(具体的诸如回忆、联想、顿悟、心血来潮等),使它们一下子豁然贯通,仿佛长了腿脚,找到了灵魂似地活跃起来,催引作家进行思考和创作。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心灵观念触媒。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离不开少不了这两类触媒的刺激、勾引、诱发和召唤,否则就变成了一种神秘的无源之水。
原始触发的方式千奇百怪,综合起来也大致就是两类。一种是睹物兴情、触景生情、闻讯生思、触物而成等。如鲁迅的《狂人日记》、茅盾的《青蚕》、杨沫的《青春之歌》、冯德英的《苦菜花》等是从读书读报中受到启示,获得创作意图的。马尔克斯写作《百年孤独》、《残枝败叶》、《星期二的午睡》等是由一个目睹的形象激起了创作欲望。这种触发通常由于有外界因素的作用,找得到具体的触发物。另一种是直觉顿悟、触感而兴,它似乎没直接受什么外界物质的刺激,找不到具体的触发物,而是在散步、洗澡、睡梦中或干其他劳作时,头脑中突然闪现一个主意、一种念头、一种思路,意识中突然看到了一种新颖的画面或发现了一种崭新的关系,于是令作家妙意萌心,兴发意生,激情难抑,打开了创造力的闸门……。
触发作家萌生创意的不论是一个人、一件事、一句话、一个形象、一种思想、一个念头,它们本身往往有一种突出的行为或特征,有一种值得玩味深思的内涵和意蕴,或是有一种特别鲜明生动的形象、一种异乎寻常的审美价值。这就象天河里面的无数群星,都在闪烁发光,又都转瞬即逝。它们对于普通人一闪即过交臂失之,却被有心的作家艺术家灵眼觑见,灵手捉住,成为一种启示、一种酵母,照彻了作家的心胸。作家由这触动自己的平凡事物中看到了不平凡的东西,或从不平凡的事物中又找到了平凡的东西,它们因此激活了作家沉睡的感情,沟通了心灵中潜存的信息和材料,使之精神焕发,欢欣鼓舞,一切变新,犹如诗人布洛克在其作品中所说:“偶然在小刀上/找到一粒遥远国度的微尘——/世界又重新显得奇异神妙/迷离于缤纷的彩雾中。”
二、交感受孕
生活中刺激触动人们的情绪情感,引起喜怒哀乐各种不同反应和表现的事实在是太多了。触发作家引起他情绪波动、思潮起伏、浮想联翩的事也同样多不胜数,无法细述。但大多时候,兴奋激动、感动感叹一阵也就过去了,未必会留下什么后果。然而有时的触发却非同小可,它深入人心,或引发一场情感世界的燎原大火,或促使思想产生一种奇异的飞跃巨变,或导致一种新事物的形成诞生,因此再也难以让作家艺术家忘怀。
罗曼·罗兰说:“……这是一道闪光。……就在这儿,《约翰·克利斯朵夫》开始被孕育。当然,他那时还没有成形。可是他的生命的核心,已经下了种。”这里说的孕育下种就颇为传神地道出了一种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的现象:即作家受环境和外界事物的作用和刺激,主客体在一瞬间交相感应,从而孕育了新的、最初的艺术胚胎。
当代作家杨沫也谈过相似的体会:“……这次的创作,使我明显地感到,创造一个人物,正如女人怀孕一样:要受精,要慢慢地孕育,要孩子在母腹中渐渐生长……而这受精,正是生活感受的精华和作者创作欲望的结合。”⑤她的此番话与罗曼·罗兰的话正好互相补充发明。其要旨在于:生命的胚胎取决于精子、卵子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有两者实际相交—一受精,新的生命才能从此生成孕育。作家的受外物触发萌生创作意图正深同此理。
创作意图的触发受孕,古人把它叫做“兴发意生”、“妙意萌心”、“应感之会”、“神思方运”等等。今人则把它称为创作主客体最初的遇合、契合、创作动机的发生或构思的触发等等。若用例子作比,则它类似植物的一粒种子落入大地,胚芽开始萌生,或者类似于生物的雌雄交体,形成了受精卵。
创作主客体之间的交感受孕往往只是一瞬间的事,但就在那一时刻里,作家的整个精神情感世界犹如被一道闪电所照亮,内心发生一种激烈的震荡和剧变,创作主体忘却了物与我的区别,抛开了任何人世间的牵挂,感觉到物(客体)进入了我之体内心内,我(主体)又进入了物之境界,物我相交,物我融合,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界限完全消散,两个世界重迭交合为一体。仅仅是短暂的一瞬,物的因素溶入了人心,人的因素投射进物体,心灵把一切材料融汇、消化和转化、重组了,于是一些细微的,新鲜的,前所未有的东西——艺术胚胎从中产生了。
这是创作主客体双方的第一次交配感应,是两者最初的神圣结合。经过这一次感应交合,主体客体从此失去了各自的童贞圣洁,不再维持过去那种单纯单一的状态而开始孕育新的生命了。没有交感,人和物各自分离,彼此疏隔,有了交感,物人相亲相爱相交相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神圣而富于创造性的结合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映过程,因此有关反映的理论是无法涵盖和说清它的。
交感受孕是作家与外界事物的一种无比调谐、无比欢快的遇合。巴尔扎克谈到过:“某一天晚上,走在街心,或当清晨起身,或在狂欢作乐之际,巧逢一团热火触及这个脑门,这双手,这条舌头:顿时,一字唤起了一整套意念;从这些意念的滋长、发育和酝酿中”,诞生了悲剧、绘画、雕塑、喜剧等的创思,令他“感到无上喜悦”⑥。罗曼·罗兰在《〈母与子〉订定本导言》中写道:他“开始写一部新的小说:《安乃德和西尔薇》,极大的乐趣。一个不相识的生命潜入我的生命,它把自己的血液、思想和命运、灌注给我”。这种无上的喜悦和极大的乐趣,全是由于孕育了一个新的艺术生命。它诱导、激励着作家从此开始新的征战——投身伟大的创造工程。
交感受孕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体验。当它发生时,创作主体的身心皆会产生一些奇异而亲切的感觉,根据一些作家的体会来看,大体会有:(1)陌生惊奇感。心灵受到触动往往是由于一个陌生人突然闯进作家的生活,一件从未听过的新鲜事忽然灌入耳内,一种从未知晓的观念猛然醒悟,一种纯然陌生的东西突然呈现在作家眼前,引起他的心灵悸动、震颤、感奋和惊喜。这神奇的邂逅,使作家在顷刻间明白了生活的意义,找到了百思不解的答案,陌生的事物变得亲切,遥远的东西显得昵近,隐秘的东西也变得甜蜜。古人所谓“遇事有得,遂造神妙”⑦。平日神秘莫测的东西此刻清晰地在作家的审美知觉中呈现,并结成一种崭新的审美关系,引导作家进入一种冥漠恍惚之境。
(2)光明欢快感。罗曼·罗兰提到的“一道闪光”约翰·克利斯朵夫被孕育,巴乌斯托夫斯基提到的:“朝朝暮暮在空中聚集着电,当它弥漫于大气中到极限时,一朵朵白色的积云便成为叆叆的阴云,于是在云层中,这浓密的电,就迸发出第一道闪光——闪电”⑧。皆清楚地表达了创作主客体交感受孕那一刻的愉悦心境。即心灵被一道强光照亮,主体沐浴在一片灿烂光华之中,进入一种豁然开朗、透彻体悟的高峰体验。仅此一刻,创作主体顿感“万象冥会,呻吟咳唾,动触天真”⑨。“处处通情,处处醒透,处处脱尘而生活。”(石涛语)平日“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叶燮语)
(3)倏忽短暂感。许多作家诗人谈到触物在先,交感随后,兴会神到的情形时,常感叹文思创意的来去匆匆,遽生旋灭,难以捉摸。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就谈过这种妙境:“神动天随……精凝思极,耳目都融,奇言玄语,恍惚呈露,如游龙惊电,掎角稍迟,便欲飞去。须身诣其境知之”。清代王士祯则说:“当其触物兴怀,情来神会,机括跃如,如兔起鹘落,稍纵即逝矣”⑩。不少作家诗人都感叹过这种遭际兴会,匆匆相遇,得之在倾俄的创作经历,强调“须在一刹那上捕捉揽紧,迟则失之”。
(4)神秘莫测感。由于叩击人心的事物让作家感到陌生惊奇,由于心灵突然被一道明晰而粲然的光芒所照亮,由于这一切又来不可遏,去不可止,不期而遇,不思而至,一切便总带有一种神秘的意味。许多作家创作之初都经历过这种不知何时产生,不知为何产生,不知为何来去匆匆毫无规律的境况。凡此种种,自然会使作家艺术家归之为“神的昵近”、“幸运的遇合”、“神灵的光顾”、“缪斯之青睐”。
总之,交感受孕是主体生命与客体自然的协调呼应,它可能只是短暂一刹那的事,但就在那一刻里,创作主客体结成了一种异常亲昵的审美关系,物似乎消融了我,我亦消融了物,物通过我存在,我通过物得以体现,双方息息相通,同跳着一个脉博,同击着一个节奏,微微的不安,甜蜜的战栗,“不知从何而来的源源不绝的词汇,以及突然出现的能统驭人类心灵的诗的力量混合在一起。”正好象“一个古老的魔箱,盖子砰地一声飞起来了,里面藏着神秘的思想和沉沉欲睡的感情,还藏着所有大地的魅力——大地的一切花朵、颜色和声音、郁馥的微风、海洋的无涯、森林的喧哗、爱情的痛苦、儿童的咿呀声”(11)。
三、创作意图的萌生
诗人写道:“一粒小小的种子,植入了我的身体,我明白了大地所有的涵义。一个孕育了生命的女人,便是一片丰饶的大地。”(12)。
作家艺术家在生活中受特定事物的触发、交感、受孕后,一颗种子入心,从此一个弱小但却有着顽强生命力的艺术胚胎便渐渐吸吮雨露,发芽破土,伸枝展叶,企盼着开花结果。
或许这一切只是在短短一瞬间便全部完成,或许它较为缓慢,得经历一个从混沌朦胧状态经细细思考体味才变得明朗清晰,渐具雏形的生成过程。但不论怎样,作家艺术家对它是充满惊喜、欢欣之情的。因为他读懂了这一触动交感的意义,从内心看清了它发送出来的美丽信号,他明白一个新的生命已被孕育、一种诗思已形成、一种新的创作意图已诞生,此后便得围绕着它去苦心孤诣地劳神运思,精心调养,使其能够顺利出世。
当代作家冯骥才在其创作的一幅题为《构思的过程》国画的题记上写道:“辛未一日心有小说意念萌生如筑起一个鸦窠渐渐便有情节细节妙语佳句若双双鸦穿云破雾款款飞来其感觉甚美妙也因作是画以记当时心态……”此话虽短,却顺序记述了作者交感受孕,意念萌生时那种心神愉悦感觉极妙的心理状态:一切都是轻盈漫起,渐渐生出,款款飞来优美地流淌的。此为一种情形。
俄国作家果戈理则这样描述艺术胚胎诞生时的情形:“我感到,我脑子里的思想象一窝受惊的蜜蜂似地蠕动起来;我的想象力越来越敏锐。噢,这是多么快乐呀,要是你能知道就好了!最近一个时期我懒洋洋地保存在脑子里的,连想都不敢想写的题材,忽然如此宏伟地展现在我的眼前,使我全身都感到一种甜蜜的战栗,于是我忘掉一切,突然进入我久违的那个世界。”(13)象受惊蜜蜂似地蠕动,挤嚷着往外奔,这又是另一种情况。
清代叶燮则在《原诗》中说:“当其有所触而兴起也,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出而为情、为景、为事,人未尝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与闻其言者,诚可悦而永也。”劈空而起,恍如惊雷闪电,这又是一种情形。
当代作家何立伟在介绍自己写作全国获奖短篇小说《白色鸟》的经过及创作过程间的审美心理时说,这创意是如何萌生的“实在是不好准确回答的问题。一件作品从最初的萌想到末了的完成,因为种种的缘故,并不都是明晰可言而尽胜言传的。”他之所以写这篇小说,起因是1984年夏初的某日黄昏,“我心曾为一支从旱冰场远远扬来的日本民歌改编的轻音乐深深持久的颤栗,从而陡起了少年时代往事的追想,及因之同血液而沸郁的创作情绪方面的萌动。”(14)而后他意绪沸腾不能自己,遂写了那如同绝句式的优美短章。闻乐声而起颤栗,触景生情,音乐打开了作者敏感的审美意识阀,这就是《白色鸟》创作意图萌动的最初成因,它又是另一种情形。从这一刹那起,善感之心与多情之物交配了,它们共同孕育了这篇小说的最初创作意图,一部小说由此而生。应该说在何立伟听歌之前,无论是世间或是他的脑子里尚不存在任何的创作之源的。虽然作者有少年时代亲历的往事,有许多积累已久的素材,但它们是否有用,何时被用,怎样使用,全是未知数。它们也可能永久沉睡不醒,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另一篇作品中,这往往连作者本人也是心中无数没法先知的。触发感生小说创作意图的这个过程是随机而生的,既不可强求,也不可能事前预测。它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必然借助偶然,偶然帮助必然。两者共同作用这才触发了创作意图,唤生了灵感,以往积累的材料也才会象找到了一个灵魂似的活了起来,被派上了用场,并焕发出了生命和光彩。
但是上述我们谈论的创意萌生仅只是作家艺术家创造精神、生命能量的初始展露,是其创造力的第一次迸发,它距离作家构思酝酿、挥笔倾洒的成熟还差距甚远。对于创作一首短诗来说,一切也许就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但对于创作一部小说、一部长诗、一部戏剧、一幕电影等规模稍大的文学作品来说,则仅仅只是一个开头、一个起点。从起点出发欲到达目的地尚有千难万险、遥远途程等待艺术家去征服跨越。
四、成因分析
从上述所举的各种例子看来,创作意图的触发受孕似乎正好符合传统的“刺激—一反应”的理论公式,因此许多人特别容易接受反映论的原理,特别容易相信是生活决定了文学是否得以诞生和以什么面目诞生的传统理论。然而,事情往往并不象它所直接呈露在表面的那样简单,假若我们忽略或不去揭示深潜隐伏在这一过程内里的更为本质的原因,则永远也休想解开创作意图受孕萌生的真正成因。
在发生论看来,一个刺激之所以能够诱发一个反应,只有当有机体本身对这个刺激能够有感受时才有可能。具体而言,生活中的某一事件、某种信息之所以能够触动并感生作家的创作意图,这本身就必须具备许多复杂的、多方面的条件。诸如主体方面要有一颗多情善感的心、一定的知识结构、丰富的联想能力、某种特殊的情绪和心境;客体方面要有特定的触发物、刺激物,适宜的环境、自由的空气等等。这也就意味着创作意图的触发受孕萌生虽然可能只是产生在一瞬间、仿佛只是一种豁然形成的事物。但真正决定它的却是一系列复杂的甚至苛刻的条件和长时间的积蓄积累。它从来就不光是客体主体任一单个方面的行为所能引起和决定的,而是需要主客体两方面的碰撞、契合、交流才可能产生的,正所谓:景以情合,情以景生”(王夫之语)。
从客体方面来说,大千世界存在着无数事件和超量信息,并非凡信息凡刺激皆有用,而是只有极少的部分信息能够有效地刺激触发创作主体。能够激发创作意图的偶然事件和信息通常可以是非常重大的特异的,也可以是平凡的微不足道的,但却必须是蕴含着某种特别的意义,蕴藏着某种特别的情思或一个小小的真理(这至少是对创作主体而言,而它对别人则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如同果子内藏着一个果核一样。果子可以吃完后很快消失,事件可以勾取引发创作主体的意念情思之后便被人弃置忘却,但其内核却留在了作家的意识或潜意识内,它也许即刻便点燃创作主体思维和情感的燎原大火,也许要潜伏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慢慢地发芽和拱土而出。前述汪曾祺在几十年后突然重写儿时经历的事就说明他过去的经历虽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渐渐淡忘、飘散了,但仍有一些已由意识转入无意识而不自觉地被存储下来。作家虽平日早已忘记了它们的存在,但遗忘并不等于不存在。一朝由于某种机缘的凑合或某种东西的刺激触动,又会勾起回忆,引发联想,使它们重又浮现于脑际,唤起作家的创作表现欲望。
从创作主体方面来说,特定的事件和信息能否刺激并引起作家内心各种信息的激荡振动奔涌,这不仅因人而异,而且因时而异,因心境情绪而异。也就是说,同一的事件对作家甲是令他兴奋不已的,对于作家乙则可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同一信息令作家丙如获至宝,灵感顿生,但对于作家丁则完全可能会漠然置之,不理不睬。即便是对于同一个作家,他想看什么或不想看什么,想听什么或不想听什么,以及由看和听而引起的心理感受和活动本身也具有很大的自由性、自主性。今日以此心情此知识积累听到此事可能无动于衷的,彼日以另一心情另一知识积累听之则可能心领神会,大受感动,判若两人。这就昭告人们,看似十分偶然的创作意图触发萌生事件,必须联系着创作主体及其个性、心向、情趣和生活积累、情感积累、知识积累等更深厚的原因来考察与研究。特定的事件与信息之所以对某一创作主体成为了有用的刺激,这除了此事件和信息本身蕴含有某种意义的成分在内,很大程度须依赖于主体自身的心理格局和审美图式。能为主体的格局图式所接纳同化整合的信息才有可能被接受并触发创作意图,不能为主体的格局图式所接纳同化整合的信息便可能一无用处。而这格局图式简单来说,就是创作主体在此之前所有的经验、感受和知识之总和之积淀。因此,英国学家阿诺·理德指出:“究竟是什么东西推动艺术家进行创作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所有的一切。艺术家进行创作的动因,这包括他过去所有的生活状况,他在创作时的身心状况,意识和气质。包括所有能引起灵感现象的一切情况。这些情况严格说来可以包括直到艺术家所描写的那件事情为止以前的全部宇宙的历史”。王蒙也说过:“只有一个小小的触发能触动你毕生造就的那根心灵的主弦的时候,你才能写出有分量、有深度的作品来。”这些无疑是很精辟的见解。
进而言之,作家所以能在有了刺激之后便能萌生创作意图,他的审美创造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有了这种能力,外界刺激原始触发才会有用,才会给作家带来幸运的机会;没有这种能力,再碰上些什么奇遇良机,也可能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白白错过,或者会导致力与心违,徒怀虚愿却无所作为的深深遗憾。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创作意图的触发受孕与萌生,并不是仅靠创作主客体哪一方就可以单独起作用的,它首先是取决于主客体双方自身的条件与内涵的、其次又须双方实际地碰撞、契合、交流并相互作用,故它既是随机的,又是必然的;既有偶然性,亦有必然性。唐代诗人王昌龄早在其《诗格》里提到诗的诞生时就提出了“生思”、“感思”、“取思”三种方式,生思即“心偶照境,率然而生”;感思即“感而生思”;取思即“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这三种情况也可移用作对创作意图触发萌生的一种概括和描述,当然实际情况要比这还更为复杂多样。
总之,创作意图的触发、受孕与萌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犹如一星爝火将引爆巨大的火药库一样,又如一盏明灯烛照了一大片过去根本看不清的“禁地”一样,它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它既是整个艺术创作的起点,又是此后创作过程中的酵母。靠了它,才能诱发作家内心的生活体验与积累,催生作家的联想和想象,激活作家的创作情思,点燃作家沉潜的热情和创造力,使过去各自相对独立的创作主客体开始进行一系列复杂的内外信息交流、重组和建构。缺少了这一最初的动因和感发作用,便不会有任何文学作品的问世。
注释
①转引自杜书瀛:《文学原理—一创作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
②《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上册,第11页。
③汪曾祺:《关于〈受戒〉》,见《新时期作家谈创作》,第120页。
④艾芜:《回答〈文艺学习〉编辑部的问题》,见《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上册,第525页。
⑤杨沫:《自白—一我的日记》
⑥巴尔扎克:《论艺术家》,见《文学艺术家智能结构》,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⑦[宋]吕本中:《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
⑧《金蔷薇》,第38页。
⑨[明]胡应麟:《诗薮》。
⑩王士祯:《师友诗传录》,见《清诗话》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1)《金蔷薇》,第179页。
(12)姜华:《生命的诗》,见《母爱集》,海燕出版社。
(13)[苏]魏列萨耶夫:《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页。
(14)何立伟:《关于白色鸟》,见《小说选刊》198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