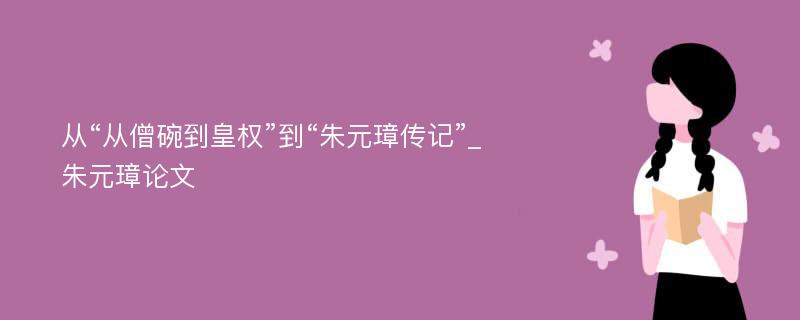
从《由僧钵到皇权》到《朱元璋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皇权论文,朱元璋论文,僧钵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7)01-0055-07
吴晗是朱元璋研究的拓荒者,他的代表作曾经多次改写,由抗战时讽喻时政的通俗读物《由僧钵到皇权》发展成为新中国的学术性史学名著《朱元璋传》,在明史研究以及中国政治史、史学史上都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这部著作曾经得到毛泽东的关注而引起人们的瞩目,然而吴晗最终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首位祭旗人物。吴晗的《朱元璋传》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写成的,又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改写的?产生了怎样的社会效果,存在着哪些问题?这部著作的写作和修改,给后人留下了哪些经验与教训?这些都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由僧钵到皇权》的写作
吴晗于1929年夏考入杭州之江大学预科,一年后之江大学停办,又到上海考入中国公学大学部预科,1929年秋升入该校社会历史系。 1930年夏,他来到北平,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作馆员。1931年三四月,写成《胡应麟年谱》,这是他的第一部明史著作。当年七月,吴晗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为二年级插班生,史学系主任蒋廷黻建议他专攻明史,胡适也给他写信,称“蒋先生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要他“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从这一年开始到1948年,吴晗陆续发表一系列有关明史的论文,至1956年辑成《读史札记》一书,由三联书店出版,代表了吴晗明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就在研究明史的过程中,吴晗萌生了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作传的想法。1943年,战国策派的林同济由重庆来到昆明,约请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吴晗写作《明太祖》。此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工资贬值,吴晗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在叙永分校来回(指1941年秋携家眷由昆明西南联大至叙永分校任教,翌年 9月叙永分校结束,又由叙永返回昆明西南联大)路费弄得倾家荡产之后,家乡沦陷了。老母弱妹衣物荡然,无以为生。加以物价天天飞涨,实在没有办法支持下去了。”[1]林同济答应付给一笔万元的稿酬,并可预支3000元,解其燃眉之急。更为重要的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全国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而蒋介石却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用法西斯手段残酷镇压抗日群众和师生。这激起吴晗的极大不满和痛恨,“讲历史一抓到题目就指桑骂槐,也开始参加一些政治性的社会活动了,走出书房,进入社会了”。写作《明太祖》,吴晗认为正好可以借古讽今,用来抨击蒋介石,于是便慨然应允下来。
当时的昆明,能够找到的参考资料少得可怜。吴晗“过去所曾读过的有关史籍,如《明太祖实录》、《高皇帝文集》、《皇明祖训》、《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御制皇陵碑》、《世德碑》、《纪梦》、《西征记》、《平西蜀文》、《周颠仙人传》、《皇朝本纪》、《天潢玉牒》、《国初礼贤录》,和陆深《平胡录》、《北平录》、《平汉录》、《平吴录》、《平蜀记》、黄标《平夏记》、张紞《云南机务钞黄》、高岱《鸿猷录》、唐枢《国琛录》、王世贞《名卿绩纪》、顾璘《国宝新编》、徐祯卿《翦胜野闻》、王文禄《龙兴慈记》(从皇陵碑以下有沈节甫《纪录汇编》本)、叶子奇《草木子》、孔齐《至正直记》、何乔远《名山藏》、谈迁《国榷》、刘振《识大略》、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夏燮《明通鉴》诸书,都因无法找到,不能利用。甚至像郎瑛《七修类稿》之类的普通书,也百计访觅而不可得”[2]91。但是,吴晗写这个传记的主要目的既然是为了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用以影射、痛骂蒋介石,他还是凭借自己手头的《元史》、《明史》、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权衡《庚申外史》、陶宗仪《辍耕录》、陆容《菽园杂记》、钱谦益《太祖实录辨证》、潘柽章《国史考异》等有限的几部著作和自己过去所发表的几篇论文,从1943年7月7日动笔,同年9月9日杀青,用60多天的功夫写出了8万字的稿子,1944年 6月由重庆在创出版社出版,书名叫《由僧钵到皇权》,随后又被重庆胜利出版社收入由潘公展、印维廉主编的《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第一辑,书名为《明太祖》,在书末加了一个附录年表。
这部一书而两名的朱元璋传记,共分《流浪青年》、《从士兵到统帅》、《开国皇帝》、《恐怖政治》、《家庭生活》五章,记述了朱元璋一生的经历和功过。尽管由于时间匆促,写得极其粗疏,存在“材料不够”[2]91、不少史实弄错的问题,但它却达到了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的预期目的。特别是第四章《恐怖政治》,更是以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借记述朱元璋在洪武建国后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特用严刑治国,诛杀屠戮,几无虚日”,以抨击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在这一章作者写道,朱元璋屡兴大案,“从开国元勋到列侯、裨将,诸司官吏到州县胥役,进士、监生,富人、地主,僧道、屠沽,甚至亲侄、亲甥,一有不是,立刻丧家灭族”,“杀得全国寒心,人人战战兢兢,不知命在何日”,“洪武一朝的历史可以说是血写的”,处处充满着血腥。在这一章作者还着重揭露朱元璋利用锦衣卫实行特务统治,指出“在旧式政体之下,皇帝只是代表个人和家族,以及外环的一特殊阶级的利益,比较被统治的万民,他的地位,不但孤立,而且永远是在危险的边缘,尊严的、神圣的宝座之下,酝酿着待爆发的火山。为图权威和利益的持续,他们不得不想尽镇压的法子。公开的律例和刑章、公开的军队和法度不够用,他们还需要造成恐怖空气的‘特种’组织、‘特种’监狱和‘特种’侦探,来监视着每一个可疑的人和可疑的官吏。他们用秘密的方法侦伺、搜查、逮捕、审讯、处刑。在军队中,在政府机关中,在民间,在集会场所,甚至交通孔道,大街小巷,处处都有这样的人在活动。执行这些任务的‘特种’组织,在汉有‘诏狱’和‘大谁何’,在唐有‘丽景门’和‘不良人’,在宋有‘诏狱’和‘内军巡院’,在明初则有锦衣卫”。这一章还利用一些野史笔记的材料,描述朱元璋“以文字疑误,发脾气杀人”的“文字狱”,以致“举国上下都诚惶诚恐,拱手听命”[2]171-188。这些描述,极易使人联想到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新闻检查和蒋帮特务对人民的镇压、逮捕及屠杀,激起人们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统治的不满和仇恨,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推动人民民主运动的积极作用。
《朱元璋传》的多次改写与三次呈送毛泽东审读
《由僧钵到皇权》原是一本讽喻时政的通俗读物,不是纯学术的史学著作,书中使用的材料一概未注明出处。书稿写成后,吴晗曾请孙毓棠修正,孙毓棠的批评是“这本书最好叫《大明帝国开国史》。因为书中讲明太祖的地方实在不够多,文字也有点演讲派头,想是教书习惯了的缘故”。他自己觉得,“除了孙毓棠兄所说之外,文字的拙劣和材料的不够,也是这本小书的最大弱点”[2]91,“加之,一书而两名,更感不快,决定回北平后,多读史料,把它作废,重新写过”[2]443。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于1946年5月 4日宣告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分别迁回北平、天津。吴晗于当年8月返回北平,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于是,从1947年暑假到1948年暑假,他花费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对这部著作进行改写,改称为《朱元璋传》。这个本子于 1949年4月由上海新中国书局、三联书店和香港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起到了呼应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的积极作用。
这次改写,吴晗补充大量的史料,从原来的 8万字扩充到十五六万字,篇幅差不多增加一倍。并逐一注明材料的出处,还增加500多条小注,许多问题也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不过,全书的基本框架仍然未变,只是将章节标题作些文字上的改动,并将原来的第二章《从士兵到统帅》拆成两章,变为第二章《红军大帅》和第三章《从吴国公到吴王》,第四章《大皇帝的统治术》 (即原来的第三章《开国皇帝》)由原来的4节扩增为7节。而且,由于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经过精心的策划,悍然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作者借朱元璋痛骂蒋介石的想法也更加强烈。书中不仅在《恐怖统治》一章中增加了大量材料,把朱元璋诛杀功臣、搞特务网、兴文字狱,写得淋漓尽致,而且还将第一章的标题由原来的《流浪青年》改为《小流氓》,使影射的色彩更加浓烈。
1948年夏,吴晗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离开北平绕道天津进入解放区。在石家庄,吴晗将刚刚改写完毕的《朱元璋传》稿子呈送毛泽东审读。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抽空读完全稿,约吴晗晤谈两次,对书稿中关于西系红巾军首领彭莹玉在起义成功后“功成身退”,回到人民中间去了的描述提出疑问,认为彭和尚是个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后来,毛泽东在退还原稿时,还给吴晗写了一封信,信中除泛泛称赞“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之外,还着重指出:“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工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3]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吴晗返回北平。 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后就任北京市副市长。不过,他始终记着毛泽东对《朱元璋传》所提的意见,“决意重写,改正错误。但是因为工作较忙,总抽不出比较完整的时间,蹉跎了五年,到一九五四年四月,才下定决心,挤时间再写,有空就写一点,断断续续,经过一整年,才写完第三个本子”[4]1。这次改写,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着重作了三方面的修改:一是纠正以“超阶级思想来叙述坚强不屈的西系红军组织者彭莹玉和尚”的错误。1949年2月回到北京后,吴晗“发愤重新读书,果然发现过去所没有注意的史料,彭莹玉是战斗到底,被元军所杀的”。二是纠正把明朝官僚机构和军队“比喻为封建皇权的两个轮子”的错误说法。因为在学习列宁关于国家的学说之后,他认识到国家机器不只是官僚机构和军队,还有其他的东西。三是去掉影射色彩,力求给朱元璋以公正的评价。新中国建立以后,一些在40年代曾以历史作为影射、抨击蒋介石法西斯独裁统治手段的进步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都曾做过自我批评,承认那种做法并不科学。吴晗也认识到“由于当时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以过分的斥责,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4]1。为此,他除将第一章的标题由《小流氓》改回《流浪青年》,并去掉那些直接影射的词句外,还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论述评价朱元璋一生的活动和功过,特地增写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章,讲述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结束之后所采取的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以及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使读者看到朱元璋除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的残暴一面外,还有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功绩的另一面。这样,全书就由六章变成七章,篇幅也由十五六万扩充至17万字。
1954年写成的这本《朱元璋传》,吴晗没有马上交付出版,而是油印了100多本,分送给各方面的朋友征求意见,并再次呈送毛泽东审阅。他说,这是因为“自己明白理论水平低,没有自信心”[4]2。过了一年多时间,收到许多来信,认为“第三个本子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是阶级关系、阶级矛盾、阶级分析注意不够,对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不够全面”[4]2。毛泽东的意见则是:“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5]。这些批评,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因此,吴晗没有马上动手修改书稿,而是先沉下心来,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经过九年多的学习,他觉得“有些问题比以前认识得似乎清楚一些了,特别是关于阶级、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和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学习得比较用心一些,也写了一些文章”。加上一些读者来信,询问《朱元璋传》早已绝版,何时可以重版?“为了纠正在读者中曾经散布的错误论点,还给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4]2,1964年遂决定利用病后半休养的机会,作第四次的改写。从当年2月初开始,花了两个月时间,写出《朱元璋传》的第四个本子,于1965年2月由三联书店出版。
这次改写的本子,除恢复第三个本子删去的《朱元璋年表》外,在章节的安排上作了些小的调整,将第三个本子第四章《开国皇帝》拆开,其中的第一、二、三节组成第四章,仍称《开国皇帝》,而把第四、五节与原第五章第三节合并,组成第五章《政权的支柱》,这样全书就由原先的七章变为八章,篇幅也由原先的17万字扩增至21万字。
第四个本子进一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元末明初的史事,特别是加强对明初阶级关系、阶级矛盾的分析,除开辟专章《政权的支柱》论述明初的地主、官僚和人民的义务及常备军、特务网的作用外,还在第六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叙述朱元璋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时,加进了这样几段文字,以突出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元末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结果,它大大打击了元末的大地主阶级,并且大大地教训了新统治者朱元璋,迫使他对农民作出了一些让步。这些让步的结果首先表现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上面。”“移民屯田,开垦荒地,承认自耕农开成熟地的产权,旧地主复业只能依丁拨田,和兴修水利是增加谷物产量,增加皇权租税收入,强化国家机器的主要措施,也就是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阶级斗争以后,新皇朝不得不稍为对农民让步的具体表现。”[4]212,218对于朱元璋的评价,则在全书的末尾加了1000多字的概述,着重指出:“和历史上所有的封建帝王比较,朱元璋是一个卓越的人物”。他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结束了元末20年战乱的局面;在于能够接受历史的教训,对农民作了一些让步,大力鼓励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推广棉花和桑枣果木的种植,允许农民尽力开垦,大大增加自耕农的数量;在于解放奴隶,改变了元朝贵族官僚大量拥有奴隶的局面;在于大力清丈田亩,相应地减少了一些赋税负担不均的情况;在于保护商业,繁荣了市场;在于吸取元朝对外战争失败的教训,强调既要抗击外国侵犯,也不可轻易犯人;在于改变元朝匠户制度,推进了民间手工业的生产;在于不信符瑞,不求长生,讲究节俭;在于限制僧道的数量,减少了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但他也有许多缺点,第一,由原来的农民革命领袖变为地主阶级的头子,反过来镇压农民革命;第二,实行以猛治国的方针,过分地运用特务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第三,定下《皇明祖训》,不许子孙改变,束缚了此后政治上的任何革新;第四,他所规定的八股文制度,严重地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进步的有害作用;第五,他大肆宣扬荒诞的神迹,欺骗、毒害人民。总而言之,“朱元璋有许多功绩,也有许多缺点,就他的功绩和缺点比较起来看,还是功大于过的。他是对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起了推动作用的,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此外,他还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4]300-301。这个评价,显然比第一个本子称朱元璋为“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2]187的带有大汉族主义色彩的评价,更加接近历史实际。
第四个本子是《朱元璋传》的定稿本,也是我国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朱元璋传记,成为朱元璋研究的奠基之作。书出版前,吴晗曾再次呈送毛泽东审阅。不过,这个定稿本改定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难免带有那个年代史学论著的通病,即过分突出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从而削弱、冲淡了历史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掌握和运用并不完全到位。比如对朱元璋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书中就只讲到它是“阶级斗争的结果”[4]163,着重强调它的残暴、血腥和恐怖,揭露其对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消极作用,却忽略了明代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归根到底是宋元以来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制普遍发展的产物,在客观上含有某些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因素,因而对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的另一面。而且,由于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吴晗对朱元璋的评价也已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书中对朱元璋的评价也就基本沿袭第三个本子的观点不变,继续以很大的篇幅,大写特写朱元璋以猛治国,搞特务网,诛杀功臣,兴文字狱,迫害知识分子,等等,未能达到毛泽东指示的对朱元璋“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的要求。毛泽东对此自然很不满意。具有政治野心的江青,读到书中所写的朱元璋“不许后妃参与政事”,“规定皇后只能管宫中嫔妇之事,宫门之外不得干预。宫中不许和外边通信,犯者处死”[4]168-169,当然也很不高兴,打定主意要进行批判。事后她曾回忆说:“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果然,就在当年春天,江青即奉命秘密前往上海,组织写作班子,令姚文元执笔炮制批判吴晗另一部作品《海瑞罢官》的文章。当年11月,此文在上海《文汇报》抛出,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吴晗从此受到残酷的迫害和折磨,至1969年终于惨死于现代文字狱的囚牢之中。
经验与教训
吴晗的《朱元璋传》,从抗战时讽喻时政的通俗读物发展成为新中国的学术性史学名著,经历了风风雨雨,为后人留下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1.唯物史观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理论
吴晗在学生时代的治学深受胡适的影响,曾将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写在毕业照片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此外,他还受到在清华任教的蒋廷黼、雷海宗概括、综合研究方法和张荫麟清新活泼文风的影响。1935年负责编辑天津《益世报》的《史学》双周刊,还在《发刊词》中打出“新史学”的旗号,宣称“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学当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强调要研究社会的、民众的历史,并在《益世报》上发表过《明代之农民》、《元明两代之匠户》等论文,表明他受到当时刚在史坛流行的唯物史观的影响。但是,吴晗早年走的还是胡适为他指定的把自己训练成“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的路子,除了从事一些史料的整理和汇编工作之外,发表的多是些考证性质的文章,说明他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跳出旧史学的窠臼。正因为如此,吴晗最初几篇与朱元璋有关的论文如《胡惟庸党案考》、《明成祖生母考》,就都是考据性的文章。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晗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消极抗战、黑暗腐败感到无比憎恨,对共产党的坚决抗日、政治清明感到由衷敬佩,因而积极投身于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不仅经常在学生集会上发表演说,而且撰写了《论皇权》、《论贪污》、《明代锦衣卫和东西厂》等一批文章,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由僧钵到皇权》一书,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旨在借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吴晗更以勇猛无畏的精神,向蒋介石国民党展开斗争,并将《由僧钵到皇权》加以扩充,改写成《朱元璋传》,以配合民主运动和人民解放战争。不过,直到此时,作为著名民主战士的吴晗,也尚未接受历史唯物主义。所以,《朱元璋传》的前两个本子尽管由于痛骂蒋介石而产生积极的政治影响,但都未能对朱元璋一生的活动作出科学的说明,无法对朱元璋的是非功过作出客观的评价,不具有多少学术价值。新中国建立后,吴晗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先后两次对《朱元璋传》进行改写,问题才有所解决,使这部著作由讽喻时政的通俗读物变为学术性的史学著作。《朱元璋传》20多年的写作、修改过程,再次证明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史学研究包括朱元璋研究的科学理论。
2.影射史学不能真正起到为现实服务的作用,是没有生命力的
《朱元璋传》的写作,最初是为了抨击蒋介石,不可避免地带来两个致命的弊端。
一是强调实用性而忽略科学性。史学著作为现实服务,必须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这样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有生命力。《朱元璋传》的前两个本子,以朱元璋比附蒋介石,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因为朱元璋毕竟不同于蒋介石,两者之间阶级性质不同,时代环境也迥然有别。而且,为了突出朱元璋的残暴,这两个本子不仅都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洪武年问的“恐怖政治”,而对朱元璋其他的政治、经济、文化举措却一笔带过,并把朱元璋所强化的皇权说成是历史的“极峰”、“最高峰”[2]184,393,从而违背了历史事实。中国封建专制中央集权高度强化的“极峰”,出现在清代而非明代。清代君主权力之膨胀,专制手段之残暴,比之明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明代的君主虽集大权于一身,但总还有廷议、廷推制度的存在,朝中大臣可以通过廷议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吏部还可以通过廷推参与高层人事安排的决策。为了突出朱元璋的残暴,《朱元璋传》的四个本子,还把朱元璋的治国方针概括为“用严刑治国”、“以猛治国”。其实,朱元璋的治国方针是“教刑并用”、“宽猛适中”。他不仅“定律以绳顽”,也“明礼以导民”[6]卷253,倡导儒学,施行德治,普施教化,移风易俗,并非一味强调刑罚。就刑罚而言,也是按照“世轻世重”的原则,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的。以《大明律》的制定为例,就经历了由轻(洪武七年、九年律)到重(洪武二十二年律)再到减轻(洪武三十年律)的演变过程。况且朱元璋施行的严刑,主要是针对勋贵官僚、贪官污吏和不法豪强,从不滥杀无辜的百姓。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明初的社会伺以会迅速由乱至治,生产也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被清康熙帝誉为“治隆唐宋”的。
二是导致历史评价的失准。评价历史人物,既有道德价值标准,又有历史价值标准。能够完全符合这两个标准的堪称完美的历史人物,当然值得景仰和称赞,但毕竟少见。在历史上,由于阶级和时代条件的限制,更多的是存在这样那样缺陷的人物。首创我国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秦始皇,不也有实施严刑酷法、焚书坑儒、滥发徭役、横征赋税的暴行吗?手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不也有过诛杀同胞兄弟的举措吗?被誉为“盛世之君”的清世宗,登基之后不也对自己的亲弟弟八、九阿哥和他父亲宠信的一大批官员狠下毒手,并迭兴文字狱,屠杀过大批汉族士人吗?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不仅要用道德价值标准来衡量,更重要的是要用历史价值标准来衡量,看他对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究竟起了促进还是阻碍的作用。《朱元璋传》前两个本子对朱元璋的评价,更多的是使用道德价值标准,着重记述并谴责、抨击其暴行,很少顾及其对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贡献,显然有失偏颇。
3.粗疏的学风是史学研究之大忌
史料是进行历史研究的依据。研究历史,首先应该尽可能广泛地搜集、阅读有关的史籍,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资料,并进行认真细致的审核考订,去伪存真,然后进行归纳整理,分析研究,才能拨开层层迷雾,探知历史真相,得到符合实际的结论。吴晗虽然深受胡适考据学的影响,他的史学研究起步于史料的整理。但当初在昆明着手撰写《朱元璋传》的第一个本子《由僧钵到皇权》时,限于客观条件,能够找到的史籍少得可怜,只能根据手头有限的几部常见史书和自己过去发表的几篇论文来进行写作,自然不免显得过于粗疏。抗战胜利后,吴晗返回北平,清华、北大和北平图书馆的藏书非常丰富,查阅并不困难,但此时他已是北京市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正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没有多少时间去广泛涉猎、查阅有关朱元璋的史书。新中国建立后,他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公务十分繁忙,更难得有大块时间可以坐下来阅读大量史籍。因此,《朱元璋传》虽重新改写了三次,史料有所增加,篇幅有所扩大,但其粗疏之风仍未改变,存在许多硬伤。不仅许多重要的史籍未曾查阅,导致一些重要史料的遗漏和重大史事的空阙,而且对一些史籍录载的史料也疏于辨析考订,拿来就用,导致史事的失真。如《明史·叶兑传》记宁海儒士叶兑上书朱元璋言取天下大计,建议攻取平江时曰:“城固难以骤拔,则以销城法困之。于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别筑长围,分命将卒四面立营,屯田固守,断其出入之路,分兵略定属邑,收其税粮以赡军中。彼坐困孤城,安得不困?”“别作长围”、“断其出入之路”显然不是“销城法”,查《明史稿·叶兑传》及《献征录·布衣叶·公兑传》,所谓“销城法”实为“锁城法”之误。《朱元璋传》却据《明史》的记载,仍写作“销城法”。为了突出朱元璋的残暴,《朱元璋传》的四个本子还不加审核地使用一些明中后期野史稗乘记载的逸闻,专门写了一节“文字狱”的暴行,导致史实的失真。这些传闻皆不见于官修的史籍,而且往往互相抵牾,漏洞百出。如徐祯卿《翦胜野闻》等书记载,洪武年间徐一夔任杭州府学教授,尝作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阅后大怒,说:“‘生’者,僧也,以我从释氏也;‘光’则摩顶之谓矣;‘则’字近‘贼’”,乃“罪坐不敬,命收斩之”。但据光绪年间编校的《始丰稿》跋的考证,徐一夔实际死于建文元年,年逾八十,并非为朱元璋所杀。又如赵翼《廿二史札记》引黄溥《闲中古今录》的记载,说高僧来复写了首《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被朱元璋斩杀。但据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及释元贤《继灯录》的记载,来复是在洪武二十四年涉嫌胡惟庸案而被杀,并非触犯文字禁忌而被斩。再如郎瑛《七修类稿》载,四明高僧守仁、德祥分别以《题翡翠》、《夏日西园》的诗作而遭朱元璋的嫉恨,“皆罪之而不善终”。但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却明确记载,这两位高僧都和朱元璋有着良好的关系,并皆善终天年,德祥还活到永乐中期才“谈笑而逝”。可见这些野史稗乘记载的逸闻并不足信。退一步说,即使这些野史稗乘所载逸闻全部属实,它们的性质与触犯封建避讳的案件相似,也不属于文字狱的范畴。所谓文字狱,是用以治思想罪的,应指因文字著述含有触犯统治者利益的政治思想内容而遭受迫害的文字狱案。野史稗乘所载的那些逸闻并不具有这种特征,称为文字狱显然也是过于牵强。
在书稿修改定稿后,作者疏于校核,又导致一些不应有的讹误。如《朱元璋传》的定稿本,第226页记全国的人口,“(洪武)二十六年的数字为户一千六百五万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比之元朝极盛时期,元世祖时代的户口:户一千六十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一,口五千三百六十五万四千三百三十。户增加了三百四十万,口增加了七百万。”下注明、元两代的数字分别出自“《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一《户口》”与“《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但《明史·食货志》所载洪武二十六年户数并不准确,因为成书更早的明朝官方修撰的政书《诸司职掌》及《大明会典》所载的户数是“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而《元史·食货志》载终元世祖之世全国的户数为“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一”。由于口数正确,户数有误,这样一来,口数虽然增加了七百万,户数却减少了九十八万。又如第268页的脚注“《大诰二编》《苏州人才》第十三, 《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查《大诰续编》(即《二编》)第十三条为《戒吏卒亲属》,《苏州人才》第十三则出自《大诰三编》。类似的错误,还可以举出不少。
正是由于这种粗疏之风,使得这部著作存在明显的缺陷,论述的广度不够,深度也有限,对朱元璋的评价也就难以完全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