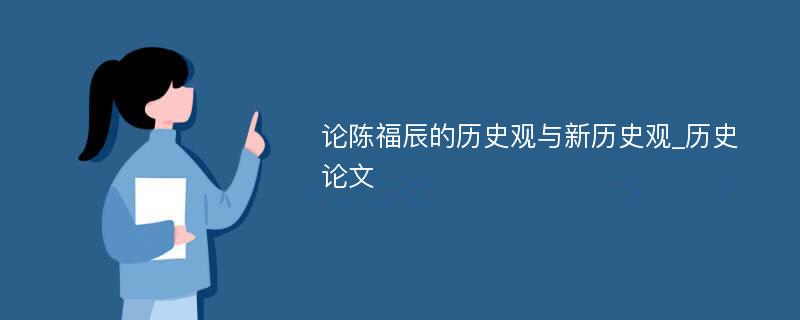
略论陈黻宸的历史观和新史方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陈黻宸论文,史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2)02-0086-04
一、陈黻宸的历史观
什么是历史?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吗?这是每一个史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厕 身于“千古未有之变局”中的中国历史学家来说,回答这两个问题颇为重要,也殊为不 易。他们必须赋予历史以新的涵义,以期能激扬民气,催生民众的爱国激情,救中国于 危难之际。众多的史家对历史作出了新的诠释,陈黻宸就是其中之一。
陈黻宸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是“人心中天然自有之 物,而但假于学士文人之笔以传者也。无天地则已,有天地即有史;天地间无一物则已 ,有物即有史。”[1](p568)可见历史是天地间万物的历史。若细而分之,历史也就是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虽然历史凭借学士文人的笔流传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 的开始,历史在文字产生以前就已存在。他说:“余尤以为自结绳而有文字,可谓史学 之进步,而不可谓史之轫始……是故未有书契以前,自有未有书契之史……史不可以文 章语言尽也。”[1](p675-676)在这里,陈黻宸已经对客观存在的历史和史家记录的历 史作了区分。他认为,客观的历史不会因为人类的是否产生和文字的是否形成而出现变 化,它是一种客观存在;而记录的历史则只能是在文字产生以后才能形成。
和当时的一些进步史家一样,陈黻宸也认为历史只能是人民的历史。“史者天下之公 史,而非一人一家之私史也。”[1](p675)尽管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绝大多数民众都不 能书写,但这并不能否认历史是人民的历史。因为“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 词客所能专也。”[1](p674)他同时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而且是综合了一切科学, 包括政治学、法律学、舆地学、兵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 物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他说:“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 自为一科者也。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1](p675) 而当时中国的科学并不发达,国家也不强盛,是故陈黻宸“窃谓科学不兴,我国文明必 无增进之一日。而欲兴科学,必自首重史学始。”[1](p676)把史学与本国的前途联系 起来,历史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在当时实起到了振聋发聩之效,尤其是对那些接受过 陈氏教育的学生而言更是如此。尽管史学是如此重要,但亦并非人人可以谈史学。陈黻 宸认为,“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 学”。[1](p675)
同时,陈黻宸也认识到历史中有规律存在。他认为历史学是重视因果关系的,因为“ 一物之始,而必有其理焉;一人之交,而必有其事焉。即物穷理,因人考事,积理为因 ,积事为果,因果相成,而史乃出。”[1](p675)所以,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应注 重对历史因果律的探求。
在历史的动力问题上,陈黻宸认为是人力而非天然力决定了历史的发展。天然力能征 服人力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但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不为天然力所压服 ,而常有征服天然力之大权”[1](p581)。他以中国和欧洲为例,中国和欧洲皆为滨海 之国。但自海通以来,欧洲列国“殖民欤,通商欤,电激风驰,绝境四鹜,数万里重洋 ,如挈家人而走之,往来络绎,经营不遗余瘁,而其膨胀力之出于亚美非澳诸区域者, 臣属殆及强半矣”;而中国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重门洞开,让形便以予敌,出四境而 遥望,鼾睡之声彻卧榻矣”;其原因只能是“海者所以开拓人意志,鼓荡人性情,而大 发泄其原动力者也”[1](p582-583)。即地理环境并不起决定性作用,真正起决定性作 用的是人本身,因而其主张“任天者败,任人者胜”。[1](p580)
在历史的发展趋势问题上,陈黻宸认为历史是向前进化发展的,而且是后代必胜于前 代。他说:“自辟为大宇而人类以成,其始也兽化人,其进也人胜兽,其进也人胜人。 相维相系,相感相应,相抵相拒,相竟相择,历数十年数百年数千年数万年之递相推嬗 ,递相淘汰,莫不优者胜,劣者败。”[1](p679)
陈黻宸还注意到历史学与时代环境的关系问题,认为历史是与时俱变的。如陈寿生于 西晋,《三国志》就以曹魏为正统;习凿齿生于东晋,《汉晋春秋》就以蜀为正统。可 见时代环境对史家的影响是很大的,而这影响到他们记录的历史的真实性。所以陈黻宸 慨叹:“时之于史大矣哉!得其时则传则显,则宝于后世,失其时则亡则轶,则藏之名 山,则投之水火。”[1](p687)
综观陈黻宸对历史的论述,其中不乏闪光之处,如他对客观存在的历史和记录的历史 作出了区分;但他的理论还不是很系统,对一些问题的论述也不够充分。没有充分展开 。尽管如此,陈黻宸对历史的论述仍反映了二十世纪初部分史家对历史概念的认识,反 映了当时的史学理论研究成果,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有着比较重要的地位。也正是 在这样的历史观的指导下,陈黻宸提出了他那较有特色的新史方案(当然,陈黻宸的历 史观有个形成的过程,但大体上在提出新史方案时已经初步成型)。
二、有独创见解的新史编撰法
关于新中国通史的编写方案,首推章、梁。章太炎在1900年手校本《訄书》所 增第五十三篇《哀清史》后附有《中国通史略例》一文,欲以“表”、“典”、“记” 、“考纪”、“别录”五体来完成新《中国通史》的撰述。梁启超于1901—1902年也酝 酿写一部《中国通史》,其体例由“年表”、“载记”、“志略”、“传志”四部分组 成。[2](p861)章、梁二人还曾专门就此问题讨论过。(注:1902年,章太炎致书梁启超 :“酷暑无事,日读各种社会学书,平日有编《中国通史》之志……知公于历史一科, 固振振欲发抒者。鄙人虽驽下,取举世不为之事,而以一身任之,或亦大雅所不弃乎” 。见汤志均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97年,第167—168页。)总的看来 ,章、梁二人都力图在吸收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优点的基础上加以创新。[3]而陈黻宸 并不受在学界素负盛名的章、梁所定新史编撰方案之囿,提出了有独创见解的主张,这 主要见于陈黻宸发表于《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2期的《独史》一文。
在撰新史的缘起上,陈黻宸感到“中国之无史久矣”,且“国而无史是谓废国,人而 弃史,是谓痿人”,所以陈黻宸欲作一新史。[1](p569)他明确地指出作新史的目的: “我意谓史于古今理乱,中外强弱,宜求知其所致此之故,而作一比例以发明之。”[1 ](p563)这与梁启超认为近世史家之本分异于前代史家,“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 关系,与其原因结果”颇为契合。[4](p1)他又认为,作史之人要有“独识”,这样才 能成“独例”,而这又贵在有“独力”来完成。
在史书的体例上,陈黻宸批评班固以纪、传分君臣尊卑,认为“后世以本纪、世家为 君臣尊卑之分,是班史之作俑也”;批评刘知几不知本纪之通义,误以为“适以天子为 本纪,诸侯为世家”,以致“令后之学者,罕详其义”;批评郑樵不废本纪,因为“纪 非尊称也”,而且“纪亦犹传体也”;故其主张后世的史家效法陈寿《三国志》废本纪 的史例,以列传代本纪,反对他们“于本纪列传一字之辨”。他说:“其君之矫出者与 其不德之尤者,效《穆天子传》、《汉武外传》之例,为之作传,此亦史家之独例也。 ”[1](p561-562)在陈黻宸看来,“世表、年表、月表以人事为经,岁月为纬”,读史 之人“于表可明盛衰治乱之故”[1](p560-561),盛赞史迁之作帝王年月表,认为修史 时就应仿效史迁所创的“表”这种体例。正因为如此,当他发现“东西邻之史于民史独 详”[1](p562),反顾“中国自秦以后,而民义衰矣”,故其主张“今宜效泰西比较史 例,而推太史公、郑樵二家之意,作平民表”。[1](p563)此外,陈黻宸相当地推服郑 樵及其《二十略》。他说:“郑樵生史迁千余年后,破万古之屯蒙,树独职于乙部,首 作《氏族略》,而终于昆虫草木,大哉后儒之蓍蔡。”[1](p563)认为“郑樵之作二十 略,乃其独力之尤著也。”(p563-564)故其欲效郑樵之“略”作“录”,首录即为“氏 族录”。另外,他认为读史者“于志可识宪令法度之详”。[1](p561)(“志”即“略” ,称呼不一而已。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 说,欧阳修曰考。)由此可见,陈黻宸意把史书体例确定为“传”、“表”、“录”。
在确定了修史的体例后,陈黻宸意欲“据我中国古书,旁及东西邻各史籍,荟萃群言 ,折中贵当,创成史例。”[1](p569)新史的断限上自五帝,下迄于清,共约四、五千 年事,由八表、十录、十二列传来概论。八表为:帝王年月表(邻国附)、历代政体表( 邻国附)、历代疆域表、邻国疆域表、平民习业表、平民户口表、平民风俗表、官制沿 革表;十录为:氏族录、礼录、乐录、律录、历录、学校录(选举附)、食货录、山川录 、文字语言录、昆虫草木录;十二列传为:仁君列传、暴君列传、名臣列传、酷吏列传 、儒林列传、任侠传、高士列传、列女列传、一家列传、义民列传、盗贼列传、胥吏列 传。其中,“十录、十二列传,皆先详中国,而以邻国附之,与八表并行,盖庶乎亘古 今统内外而无愧乎史界中一作者言矣。”[1](p574)
陈黻宸诚然无愧于一有独识之史家。在史书的体例上,他与章、梁一样,皆是欲在糅 合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基础上突破原有的修史体例;虽未创立新的史书体例,但却反 映了当时史学界要求确定新的修史体例,以期能写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史书的呼声,同 时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真正有所突破的是后之夏曾佑)。尽管如此,陈黻宸的 新史方案仍是较具特色的。
三、颇具时代特色的新史方案
在新史内容上,陈黻宸主张不应只记载本国之事,还应参考“东西邻各史籍”,择其 要者而述之,或在正文,或在附录。他说:“五洲通道,各帝一方,例无高卑,义殊华 狄,史固不能详中而略外,为年月以统之,而以外从中,庶几次第秩然。案籍可索。若 夫华盛顿、林肯、威廉、维多利亚诸君,功施当时,泽流后裔,其德可称,其名可贵, 亦附之列传之中。”[1](p562)如此,既注重了外部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又有助于开拓 国人的视野,使他们不再局限于中华一隅;(注:当时的许多中国人都不能意识到中国 只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中的一个,如陈独秀在1901时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 国一国,此疆彼界,各不相下。”参见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 版社1988年版,第17页。)而且,他突破了章、梁所确定的新史范围。以梁启超确定的 新史为例,其范围为:中国本部、新疆、青海西藏、蒙古和满洲;而陈黻宸“详中略外 ”、“以外从中”的修史体例,大大拓宽了史书的记载范围。与章、梁一样,陈黻宸也 提倡“民史”。他认为,“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1](p5 74)故在其所拟定的新史目录中,专门辟有“平民风俗表”、“平民习业表”、“平民 户口表”、“义民列传”四项,此皆为陈氏首创,且占了整个篇幅的2/15。现在看起来 ,这数字似乎比较小,但在当时而言,相比“一人一家之谱牒”的旧史实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陈黻宸是三者中唯一完成《中国通史》撰写工作的史家,他的这种“民史”思 想也得到了深入贯彻。其1905年《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就因“清臣劾其提倡民权焚 毁殆尽”[1](p1192),1915年完成的二十卷《中国通史》也举目可见“民史”之踪迹。 另外,他的“邻国疆域表”、“官制沿革表”、“学校录”、“文字语言录”、“列女 传”、“一家列传”、“胥吏列传”亦颇具特色。如“文字语言录”是在“撷欧亚之精 华”的基础上而作,“列女传”则是希图改变女子以往卑微之境况,“一家列传”则是 记述有一艺之长的人。
在修史的方法上,陈黻宸主张学习并采取“泰西比较史例”。有比较方有鉴别。他认 为,史实的比较做的好,就可知“民人社会之进退,国家政治之良否”,最后能成“弥 纶一代之巨作”。[1](p563)把比较研究的重要性提升到一相当高度,它简直成了一著 述能否成功的关键。这种主张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态度在20世纪初年是颇为少见的。
陈黻宸还主张在修史时,史家应有实录精神。他提出了史家的“大例”和“公理”。 他说:“史家有大例焉,于强国不加益,于弱国无加损,于真王不加褒,于伪统不加抑 。抑我又闻之,史家有公理焉,斧钺不能威,章服不能奖,天子不能争,朝廷不能有。 ”[1](p573-574)总之,史家在叙述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时要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即 实事求是。
此外,陈黻宸随后撰写了《地史原理》一文,以作为对新史方案的补充。在该文中, 陈黻宸提出了“调查贵实”、“区划贵小”、“分类贵多”、“比例贵精”等体例,主 张在此基础上作一新地理史。内容应包括:户口表、宗教表、族类表、学校表、职业表 、疾病表、罪人表、儒林表、文明原始表、历代君主表。从陈氏在此际的论述来看,在 如何看待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问题上,他的态度是科学的,不同于梁启超。梁是一 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认为“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 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其相关之要,恰如肉体与灵魂相待以成人也。”[4](p5) 而陈黻宸则不这样认为。他主张发挥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任人说”,认为“人类所由群 进于文明者,不为天然力所压服,而常有征服天然力之大权”,故最终的结果必将是“ 任天者败,任人者胜”。[1](p580-581)同时,他也不否认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的“种类 ”、“习俗”、“性情”、“德行”、“学术”有重大影响。可见,陈黻宸在学习西方 先进的社会科学思想时,并不是盲目地接受,而是有所抉择。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陈黻宸积极探索符合时代要求的史书体裁,在继承中国传统史 学遗产,汲取西方(包括日本)资产阶级史学优点的基础上,继章、梁之后,独辟蹊径, 提出了一个较具特色的新史方案,代表和反映了20世纪初的中国史学。
陈黻宸的历史观在1905年前后定型,以后似乎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而且还有倒退的 迹象,这主要表现在他1915年编撰完成的《中国通史》上。自从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 科书》出版以后,章节体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学界最佳的编撰体例,学界同人纷纷仿效。 但陈黻宸对此似不甚重视,在其新编《中国通史》中仍以朝代为纲,而没有采用新兴的 先进的章节体,这不能不令人为之扼腕叹息,但我们不能就此苛求陈黻宸,毕竟他做了 他能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