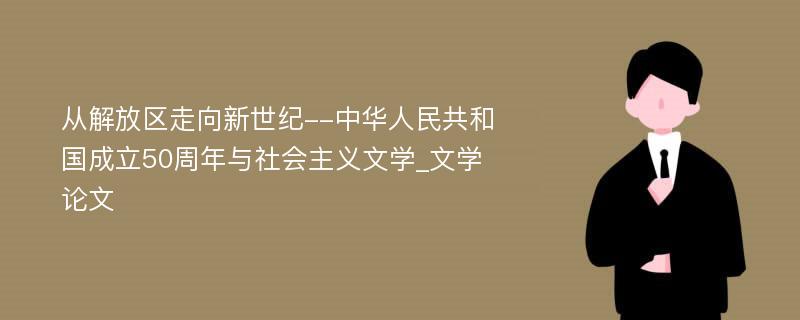
来自解放区,走向新世纪——建国五十周年与社会主义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放区论文,新世纪论文,走向论文,五十周年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年了。当我们分析和总结这五十年的文学工作时,必然要满怀深情地回顾解放区文学,因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前者是后者合乎逻辑的发展,后者是前者新美深广的渊源。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奇谈怪论层出不穷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充分肯定解放区文学的历史地位,正确总结新中国文学的利钝得失,在此基础上展望我国文学应以什么样的面貌跨进21世纪。
充分肯定解放区文学的历史地位
解放区文学是中国历史上崭新的文学。她继承了我国古典文学的优秀的美学传统和五四以来以鲁迅为旗帜的革命文学传统,但又有新的质的飞跃。从总的来说,她是人民以历史主人翁的姿态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文学与人民相结合,作家与群众相结合的结果。她不仅是一个地区和历史的概念,即指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学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的文学,更重要的是一个美学的概念,即指代表了一种新的美学思想和美学成就的文学。
解放区文学的新,突出地表现在人民群众以历史创造者的面貌进入文学作品。古往今来,我国文学史上曾产生过许多艺术精品,它们至今仍是宝贵的精神财富,给我们以智的启迪和美的享受。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人民群众很少表现为改造世界的主导力量,至少只是被当作怜悯和同情的对象。这毫不奇怪,因为它们不可能不受到当时的现实生活和作家的世界观的限制。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才第一次把人民群众的解放斗争引导到胜利的彼岸。这样可歌可泣的斗争和翻天覆地的变化必然使作为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的文学产生新的特点。这种新的特点首先体现在以高尔基的《母亲》等作品为代表的苏联文学中。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文学。中国解放区的新的人民的文学,正是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区文学有一个优点,就是她得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堪称划时代的新美学的指导,因而能够比较顺利地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呈现出新人佳作迭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兴旺景象。在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品中,来自生活低层的人民群众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叱咤时代风云,主宰大地沉浮,用自己忘我的劳动和斗争改造着周围的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在他们身上,再也看不到过去那种逆来顺受、听天由命、自惭形秽、低人一等的奴隶相,取而代之的是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人性美。因此,这些作品使当时的文坛大师几乎达到欣喜若狂的地步。郭沫若读了赵树理的小说后写道:“我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素朴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这种感受很有代表性。有人指责解放区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扁平”、“单一”,没有“内宇宙”的丰富性。这是毫无根据的。任何不存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到,在解放区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中,主要人物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个性鲜明而不失之简单。他们有血有肉,有情有意,有战胜自己身上弱点的成长和发展过程。这正是这些作品能够征服广大读者的重要原因。当然,从这里找什么“性格的二重组合”(如恩格斯所嘲讽的:“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找什么“精神奴役的创伤”,那是徒劳的。但这不是解放区文学的缺点,恰恰是解放区文学的优点。
解放区文学的新,突出地表现在描绘了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壮丽画卷。从《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李勇大摆地雷阵》、《荷花淀》、《边区自卫军》等作品里,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懂得了为什么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由危亡走向胜利的历史转折点。从《小二黑结婚》、《我的两家房东》等作品里,我们看到了革命斗争给社会生活各方面带来的深刻变化,目睹了在解放区农村中封建思想的节节败退和新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初步确立。从《白毛女》等作品里,我们看到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正义性。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里,我们看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这场铲除封建制度的根基的伟大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领略了农村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在这场变革中的立场、态度和表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总体上看,解放区文学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史诗。这些对于鼓吹“告别革命”的人来说当然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近来又有人指责说,解放区文学中抗战题材的作品缺少“宽阔的视野”和“宏大的胸襟”,因为“几乎没有什么作家愿意将他的作品的视角放在整个人类生存状态和人类生命形式的人文关怀上”。这种论调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当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怎么能够设想我们的作家不去用自己的笔表现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而去描绘什么“整个人类生存状态和人类生命形式”?人们有理由怀疑,这是不是在痴人说梦?任何一个没有丧失起码的是非判断能力的人总应该知道,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我们要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它是一种抗毒素,不但能排除敌人的毒焰,而且能清洗自己的污浊。解放区文学之所以新,就在于她真实地揭示了这个过程,因而决非那些以和平主义的观点来表现战争的作品所能望其项背。
解放区文学的新,突出地表现在作品具有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在民族化和群众化上作了许多努力,但是总的说来,欧化的倾向和学生腔的语言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解放区的作家除学习古人和外国人语言中有生命力的东西外,着重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反映实际生活的。这种极富表现力的语言,使作品的面貌为之一新。文学的民族化和群众化还体现在情节、结构、题材等各个方面。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民族化和群众化是解放区文学的共性。每个作家体现这个共性并不是千人一面、千部一腔,而是各具个性、丰富多彩的。拿小说来说,赵树理、丁玲、周立波、孙犁等人的作品个性鲜明,决不会使人把他们相互混淆,但他们又都共同阔步前进在民族化、群众化的康庄大道上。如今有人企图把解放区文学的这个显著的优点说成是缺点。有的拜倒在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脚下,根本否认文学民族化的必要。有的则把民族化同群众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说什么“四十年代中后期的根据地作家试图以对民间形式的回归和对外来文化的拒斥,去获取文学民族化道路的通行证,但是,这种用几乎隔绝的目光去追寻民族化的方式,最终只能是对民族化的曲解”。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文学的民族化总是同文学的群众化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文学的民族独创性,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的集中表现。劳动人民的民间文学尽管往往处于萌芽状态,但却是生长在人民生活这棵常青树上的。它贴近生活,贴近时代,刚健清新,生动活泼,显示了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为专业作家的创作输送着宝贵的营养。离开了群众化来追寻民族化,那只能是路越走越窄,最终走进死胡同去。解放区文学从来没有“拒斥”外来文化,“拒斥”的只是对外来文化的机械模仿。那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说穿了,一些人对解放区文学的不满,主要是她没有照搬如今被他们奉若神明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这种文学以主观唯心主义、非理性主义、自我中心主义为基础,以形式的扑朔迷离、杂乱晦涩为特征,同中国老百姓的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格格不入。如果说在当时紧张的斗争环境中,解放区文学对这些东西加以“拒斥”,那决不是她的所短,而恰恰是她的所长。
解放区文学的新,突出地表现在作家的思想感情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了一片。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特别是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虽然曾经提出过“到民间去”的口号,但是由于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的阻隔,加之一些文艺工作者自身存在的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作家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从亭子间到根据地,客观条件起了根本的变化,加之毛泽东《讲话》的大力提倡,许多作家深入到群众中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不仅获得了无比丰富的创作素材,而且在思想感情上同群众打成了一片。文学艺术“贵在有我”。解放区文学也不例外。由于作家的思想感情同工农兵打成了一片,解放区文学中的“我”,就不仅是作家自己,而且是人民的感情、愿望和理想的代言人。这是文学史上的伟大变化,是空前的、值得大书特书的艺术特色。现在有人根本否认作家向工农兵学习的必要性,说这“意味着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之间的教育关系的倒错”,是一种“逆转”,即“由对大众启蒙到向大众认同”的“逆转”。持这种观点的人对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样的唯物史观一窍不通,对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先当群众的学生,才能当好群众的先生”这样的唯物辩证法茫然无知,有的只是高踞于人民之上的旧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和自大狂。其实,虽然在社会大变动中,进步的知识分子可以起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但是在其未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视自己为民族“精英”,视群众为芸芸众生,实在太缺乏自知之明了。至于有人说作家一旦同工农兵相结合,他们便“丧失”了自我,乃至出现了两个自我,即所谓“真实的自我与佯装的自我总在较量”。这除了说明他们的“真实的自我”是完全同群众相隔绝、相对立的士大夫的孤芳自赏而外,又能说明什么呢?现在他们提倡要“回归”自我,这才是极大的“逆转”,只能把新文学“回归”到旧文学去。
解放区文学的这些新,确立了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她是举世瞩目的文坛奇葩,是新中国文学的先声,是中国作家和中国人民对于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宝贵贡献。然而,近年来贬低和否定解放区文学的思潮却甚嚣尘上。有人用“解放区文学没有传世之作”一句话,对解放区文学投以轻蔑的一瞥,就此横扫了一切。有人大搞什么《百年中国文学经典》,而在其遴选的“经典”之中,1937至1949年部分,一些足以传世的优秀的解放区文学作品,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均被排斥,而《蜀山剑侠传》、《鬼恋》等武侠言情小说却赫然在焉。这不禁使我想起鲁迅的一首诗《教授杂咏之四》:“名人选小说,入线云有限,虽有望远镜,无奈近视眼。”一位文艺界老前辈谈他自己的经历时曾感慨地说起,他从十岁左右就开始接触旧小说,主要是武侠言情小说,后来到了十七八岁才热中于新文学,提笔从事新文学活动,并由此走向革命。他尖锐地提出:“今天的青少年是否还一定要走我们那么漫长的弯路,必须经过自己的长期摸索再接近新的文学?”这个问题提得好。遴选“经典”的教授,似乎不仅先得治一治自己的眼睛,而且也应该稍稍替青少年着想一下,以免他们在自己的误导下走“漫长的弯路”。遴选“经典”的教授声称:“文学为适应生长它的特殊环境而付出代价”,这就是“不得不在较之艺术和审美更为急切的社会功利面前,不同程度地削弱以至在某一时期排挤文学自身的品质”。解放区文学大概便是这里所说的“某一时期”的文学,因此她被高贵的教授“排挤”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但教授振振有词地提出的“审美与非审美,功利与非功利的矛盾、对立”压根儿便站不住脚。从美的起源来说,大量人种学、考古学的材料证明,事物的功利价值先于审美价值,功利价值不仅不与审美价值相矛盾,而且是审美价值的内在要求。从作为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的文艺来说,一部文学艺术史,特别是其中举世公认的若干文艺高峰证明,文艺为先进阶级的社会使命服务,不仅不会损害其审美价值,而且会大大提高其审美价值。其实,高贵的教授在侈谈“审美”时,何尝摆脱过功利主义的纠缠?不过不是革命的功利主义,而是另一种功利主义罢了。
今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如何认识解放区文学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这也是人们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有人认为,解放区文学是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是文学发展的“断层”。谬哉斯言!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这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的领袖人物那里,民主和科学主要是指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然科学。此后,随着运动的发展,原有的队伍分化成了两个潮流。一个潮流是继承五四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民主不再是指资产阶级少数人的民主,而是指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绝大多数人的民主;科学已不限于自然科学,而首先是指科学的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另一个潮流则坚持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乃至同国内外敌人相妥协。我们必须分清这两个潮流。解放区文学是前一个潮流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在解放区,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了主人,党领导人民按照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必由之路开展民族民主革命。这难道不是在空前的深度和广度上实行的启蒙?真实地反映了这个过程的解放区文学,难道还不是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的真正的弘扬?当然,这在属于后一个潮流的人们看来,便是不折不扣的“失落”和“断层”。这决不是解放区文学的耻辱,而是解放区文学的光荣!
正确总结建国五十年的文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学是解放区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凡是继承和发扬了解放区文学传统的,坚持贯彻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反之,就苍白无力,甚至与社会主义文学背道而驰。
由于人民政权在全国的建立,新中国文学的表现对象和服务对象较之解放区文学大为扩展。由于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于党所领导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乃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改变中国面貌的伟大实践,创作的题材有了新的开拓,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了新的发展,作品的艺术风格和形式有了新的突破。由于在丰富生活积累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精心的结撰,一批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更为成熟,堪与世界社会主义文学中的不朽之作相媲美的艺术精品得以问世。这些成就是客观存在的,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毋庸讳言,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曾经犯过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这使我们的事业遭受令人痛心的挫折,未能取得本应取得的成就,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不仅表现在经济建设上,也同样表现在文艺工作上。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使今后的事情办得更好,正视这些错误和挫折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过分地加以夸大,把建国以来的文学说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那是背离事实的,是无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今后的发展的。
我们在总结建国五十年文学的时候,似应注意以下几个区别:
要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同“文化大革命”区别开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广大文艺工作者横遭迫害,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文坛一片荒芜,艺苑万马齐暗,正如毛泽东所说:“百花齐放都没有了。”“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教训至痛至深。但是,此前的十七年却不能同“文化大革命”等同起来。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这是对全党工作的估计,同样也适用于文艺工作。在十七年中,出现了几个文学创作的高潮,产生出《谁是最可爱的人》、《李双双小传》、《创业史》、《红旗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日》、《红岩》、《李自成》第一卷、《致青年公民》、《放声歌唱》等脍炙人口的佳作。现在有人把这些作品贬之为“计划化文学”,说:“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创造了符合意识形态理想与标准的新道德、新价值观念的‘新人’,国家、社会及政党则动用一切有组织的力量,通过一切传播渠道将这些‘新人’形象在最广大群众中普及,进而直接影响与支配亿万人的思想与行动。”如果说这叫“计划化文学”,那她又有什么不好?这正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强大生命力的表现,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的证明。文学真正成了人人乐用的“生活的教科书”,岂不是应该以这种造福人民的崇高而美好的功用而自豪?在十七年的评价上,如今突出的倾向是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年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捆在一起,统称之为二十年“左”。更有甚者,有的连建国头七年的成绩也一概否定。这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也是直接违反中共中央的决议的。
要把真理同对真理的误解和曲解区别开来。解放区文学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讲话》,它同时也是建国五十年文学的指导思想。它同邓小平在中国文联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和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毛泽东《讲话》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分析文艺创作中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它既肯定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又提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既要求努力表现工农兵,又指出要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既要求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求得一致,又指出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既号召学习马克思主义,又指出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又反对没有艺术力量的“标语口号”式的倾向;等等。《讲话》就是这样坚持了辩证法,防止和反对了形而上学。但是,后来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有人片面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使本来是正确、全面的命题被歪曲和片面化了,以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列宁曾经指出:“使一种新的政治思想(不仅是政治思想)声誉扫地,受到损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维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以《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被歪曲的情况正是这样。但是,对真理的误解和曲解不能毁灭真理本身。现在有人批判《讲话》的“左”,以此全盘否定解放区文学和建国以后前三十年(主要是前十七年)的文学,这是极不客观和公正的,是极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和繁荣的。
要把学术批判中问题本身的是非同对问题的处理方式区别开来。本来,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但是,现在有些人也要加以否定。其根据何在呢?从经济上来说,就是声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全搞错了,这在理论界已经遭到了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评。从文艺上来说,就是认为建国初期的几次学术批判完全搞错了,这种说法还有待澄清。毋庸讳言,当时采取的一边倒、一窝蜂的批判确有弊病,特别是混淆两类矛盾,造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冤案尤属悲剧。我们要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但是,能不能反过来说,《武训传》赞美以行乞兴学来取得宣传封建文化的权利是对的,《〈红楼梦〉研究》所代表的新索引派的研究方法是对的,胡风思想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宗派主义也是对的呢?显然不能。然而,有些人却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如今,“武训热”在许多地方已经成为时髦;《〈红楼梦〉研究》以及类似的著作被捧上了天,而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独具慧眼的真知灼见被弃置一旁,不屑一顾,新出现的新索引派比老的走得更远,用同《红楼梦》本身毫无关系的烦琐考证来代替对这部名著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研究;胡风的文艺思想被全盘肯定,说得客气一些的,是声称毛泽东是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文艺,胡风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文艺,一贬一褒,昭然若揭,说得不客气一些的,则径直用胡风文艺思想来批判毛泽东文艺思想,以致造成新时期文艺思想的混乱,例如人们就不难发现那个把“内宇宙”夸大到无以复加程度的“文学主体性”论同“主观战斗精神”论的内在联系。脏水和小孩子被一同泼出去的做法是不足取的,还是让我们把重大的理论是非同对问题的错误的处理方式区别开来吧!
要把真正的思想解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影响下的错误思潮区别开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标志着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告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文艺界和全国各条战线一样,从沉重枷锁下获得解放,从一片死寂中恢复生机。许多敢于直面人生的文学作品陆续问世。如《周总理,你在哪里?》、《于无声处》、《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寻找回来的世界》、《高山下的花环》等,都曾以其独特的思想深度和崭新的艺术表现,不胫而走,赢得广大的读者,产生强烈的反响。这些作品充分表达了人民的心声,深刻揭露了“左”的思潮对人们的伤害,着力塑造了一系列高尚的灵魂。他们身处逆境,虽九死其犹未悔。他们面临“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和灾难性的后果,或披荆斩棘,或默默奉献,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前进杀出了一条血路。这样一批作品给了人们以有力的教育和鼓舞。一些从解放区到建国后在文坛上卓有成就的作家,宝刀不老,为文学宝库增添了若干史诗式的作品,如魏巍的战争三部曲《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东方》,刘白羽的《心灵的历程》、《风风雨雨太平洋》,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等。它们体现了新时期以来创作的成果,也体现了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国现代文学主流的一脉相承的关系。什么叫思想解放?邓小平曾经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在真正的思想解放高歌猛进之时,另一种同它相对立的噪音也乘机表现出来,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影响下的错误思潮。从1978年冬西单墙和1979年初理论务虚会上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观点的抬头,到1983年精神污染的蔓延,到1986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的发生,我们可以听到这种声音时起时伏,乃至瓦釜雷鸣的发展过程。它借“思想解放”之名,行思想和实际相脱节,主观和客观相背离之实。应当承认,文艺界是这种错误思潮泛滥的一个重灾区。众多奇谈怪论,诸如“告别革命”论,“躲避崇高”论,“只要横的移植,不要纵的继承”论,“文学主体性”论,“非理性主义”论,“功利与审美不相容”论,“文学回归自我”论,“为艺术而艺术”论,“远离政治,淡化生活”论等等,不一而足,风靡一时。同理论上的迷误相呼应,创作上出现了某些不好的甚至很坏的倾向。有的丑化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或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描写成杀人放火,不讲道理,奸淫抢掠,共产共妻的十恶不赦的坏人,而国民党顽固派乃至日本鬼子却较为“仁慈”;或把从辛亥革命到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都说成是在鏊子上翻烧饼,其结果是把个好端端的世外桃源折腾得不得安生;或在以土地改革为题材的作品中把地主描写成无辜的受害者,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则是违反人性、违反人道的加害者。有的照搬西方现代派,在支离破碎、不知所云的形式下宣传存在本身的荒诞,人类本性的丑恶,世界末日的来临。一些年轻人写的这一类的古怪诗被吹捧为美学的“新的崛起”,实际上,“崛起的不是青年诗人,‘崛起’论者借‘崛起’崛起自己”(艾青语)。有的把文学完全商品化,一味迎合低级趣味,所谓“拳头加床头,财源滚滚流”。还有的把照搬西方现代派同文学商品化结合起来,例如,一方面宣传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废都”,散布“世纪末”情绪;一方面又在作品中穿插大量的色情描写,庸俗下流。文学上的这些倾向起了毒化人们灵魂的作用,同作家所应担负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崇高使命背道而驰,同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截然相反。你对此类文学现象提出异议吗,那就是“左”,是“思想解放和不解放的争论”!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真正的思想解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影响下的错误思潮区别开来,如果不在这样的问题上分清是非,中国文学将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21世纪?我们在总结建国五十年的文学时,对此决不能熟视无睹,报喜不报忧。
由此展望21世纪我国文学应有的品格
毫无疑问,我国21世纪的文学应当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特别是解放区文学和建国五十年文学的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里,最重要的是政治上要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文化、文学上要坚持其社会主义性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吸取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指针,当然也是繁荣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指针。
总结解放区文学和建国五十年文学的经验教训,我们在展望21世纪文学应有的品格时,似有必要强调几点:
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真实性是艺术的生命。真善美三者,真是基础,不真,就谈不上善,谈不上美。很难设想,一部作品没有真实性甚至歪曲了生活,却能包含某种人生的真谛;也很难设想,一部作品不能给人以真实感,却会给人以美感。艺术的真实从何而来?归根到底来自对生活的熟悉。凡是感人至深、传之久远的作品,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即“来自生活的恩赐”。因此,深入生活,首先是深入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的生活,深入社会主义事业第一线的建设者和保卫者的生活,这是作家的永恒的课题。但是,有人却认为人人都有生活,处处都有生活,强调深入生活纯属多此一举。于是,深居于高楼深院,埋头于闲聊神侃者有之,出入于宾馆舞榭,沉溺于酒绿灯红者有之,忙碌于评奖包装,热中于相互吹捧者有之,长此以往,要创作出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作品,不亦难乎?值得庆幸的是,一些中、青年作家在经受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可疑思潮践踏一通之后,通过反复比较、鉴别,还是选择了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的道路。例如,张平的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反腐败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抉择》,谈歌、何申、关仁山等直面工厂、农村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的一系列小说,王怀让的揭露丑类和歌颂大写的人的长诗《中国人,不跪的人》、《中国是咱的!》等,便是这种文学倾向的代表。张平说得好:“作家不是救世主,但作家绝不可以远离时代和人民。不关注时代和现实,没有理想和责任的作家,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时髦的作家,但绝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如果我以前没有真正想过我的作品究竟是要写给谁看的,那我现在则已经真正想过和想定了,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底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将为他们而写作!”从这些作家身上,我们看到了21世纪中国文学的希望。
在社会主义文学中,真实性和倾向性是应当而且可以统一起来的,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完全一致的。恩格斯在论述理论的科学性和阶级性的关系时曾经说过:“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据此,关于文学的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说,文学越是直面人生和追求真实,它就越符合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社会主义文学的真实性是指丰富的社会生活及其本质在作品中的真实反映,社会主义文学的倾向性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生活。面对同样的社会生活,作家的政治立场、人生阅历和艺术修养不同,其关注的方面和形成的作品会大相径庭。人们不是强调文学的主体性吗?这就是文学的主体性!毛泽东《讲话》向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任务,这个号召今天并没有过时。然而,有人却根本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他们声称:“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的主流是人道主义。”“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的主流是自由主义,这个思潮将在二十一世纪的一百年间‘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引进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这里说的“自由主义”,不是指革命队伍中取消思想斗争、搞无原则和平的错误倾向,而是一种资产阶级学说。它在经济上主张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对市场的绝对的自由放任,在政治上主张西方的议会民主和多党对立,在意识形态上主张个人主义,以个人为目的,把社会、集体、国家和他人视为达到个人目的之手段。这不过是从五四运动发展中分化出去的资产阶级右翼的沉渣泛起。如果21世纪的中国竟然以自由主义为指导,那么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将完全资本主义化,并丧失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沦为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彻头彻尾的附庸。有的宣传自由主义的人还摆出一副虚伪的排斥任何倾向性的姿态,把根据一定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生活贬之为“意图伦理”,并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之际,公然列出五四运动的四大罪状,即:意图伦理,激进情绪,功利主义,庸俗进化论。这难道不是一种十分明确而又荒谬绝伦的倾向性吗?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是以自由主义为指导,将决定21世纪的中国向何处去,也将决定21世纪的中国文学向何处去。
时代精神与民族风格的统一。什么是我们的时代精神?邓小平指出:“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便是我们的时代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共产主义渺茫论”、“社会主义失败论”颇为行时,在许多人的文章里不仅不提共产主义,连社会主义讲得也很少。他们提倡的是抽象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是同西方国家“接轨”,同资本主义“趋同”,搞所谓“全球化”,不仅是经济全球化,而且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全球化。这种“现代性”决不是我们需要的时代精神。邓小平着重指出:“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他又说:“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这充分说明,离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谈什么“现代性”,来讲什么“时代精神”,实在是南辕北辙。至于把“现代性”与现代派扯在一些,说什么“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带来现代派文学”,那更是极大的曲解。文学并不是直接由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的有机构成包括如下的层次:生产力状况——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社会心理——意识形态。生产力状况同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之间隔着很多复杂的中间环节。西方现代派文学并不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的一种曲折的反映。这同我们的时代精神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时代精神一定要同民族风格统一起来。一个民族由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特殊性,在长期的审美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我们的文学应当尊重民族的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形成自己的民族风格。当然,随着民族生活内容的变化,民族的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也会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归根到底还是离不开几千年来优秀的民族美学传统,离不开几十年来珍贵的革命文艺传统。我们的文学只有体现鲜明的民族风格,才能为今天中国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否则文艺为人民服务便成了一句空话。反过来,也只有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汲取营养,民族风格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此外,我们还应当吸收外国文学中一切优秀的于我有用的东西,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丰富和发展自己,而不是丧失和抛弃自己。文学越有民族性,才越有世界性。如同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是由各具个性的作家、作品构成的一样,世界文艺的宝库是由各具个性的民族化的文艺构成的。一个国家的文学是否具有民族独创性,这是衡量它是否成熟的标志。解放区文学和建国以来的文学在形成新的民族风格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毋庸置疑,21世纪的中国文学应当循此前进,而决不能倒退回去或改弦更张。但是,这些年来,西方现代派“反传统”的一套竟然被我国的一些人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否定民族风格固不待言,连艺术规律以至语言规范也统统在扫荡之列。如此打倒一切,真是“左”到家了,而提出此类主张和从事此类实践的人却以反“左”英雄自居,黑白颠倒,叹为观止。时代精神和民族风格是相辅相成的。离开了时代精神,“民族风格”有可能变成抱残守缺的国粹主义;离开了民族风格,“时代精神”也有可能流于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我们需要的是时代精神与民族风格的统一,标社会主义之新,立中华民族之异。
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的统一。毛泽东《讲话》中提出的“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实际上是建国后他提出的“百花齐放”的方针的滥觞。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在这个前提下,不论在内容和题材上,在形式和风格上,都应当是多样化的。既有主旋律,又有多样化,这样才能满足人民不同层次的、多方面的、丰富的、健康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单调贫乏,整齐划一,标准化,定型化,从来是文学工作的大忌。在百花齐放之中,通过比较、鉴别、竞争、淘汰,合乎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文学就能更好地得到发展和繁荣。自从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以来,凡是贯彻得比较好的时候,文学就欣欣向荣,富于生机;凡是贯彻得不好的时候,文学就萧条衰落,杂草丛生。最近有位曾在颐年堂亲自聆听毛泽东谈“双百”方针的人撰文说:“遗憾的是,他(按:指毛泽东)在1956、1957年提出这个方针后,从来不曾实行过。”这恐怕说得太绝对了吧,倘若果真如此,“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年中那些至今仍属上乘之作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倘若果真如此,当时担任文艺界领导职务的此文作者又是怎样贯彻“双百”方针的呢?自己又该负些什么责任呢?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这样的风格是不是太低了一点呢?
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是紧密联系的。对于文学来说,不仅有个各种各色的艺术品自由发展的问题,还有个对于艺术品的不同看法相互争论的问题。后者也就是文艺批评。从文学发展史上看,凡是一个文学兴旺发达的时代,总是既有文学创作的繁荣,又有文学理论批评的活跃。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这样。所以,在文学领域,既要百花齐放,又要百家争鸣。“双百”方针的要义,一曰“放”,二曰“争”,就是说要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鼓励人们创作内容和形式各异的文学作品,发表各种各样的理论见解,同时又要充分展开各种意见之间的讨论、争论,进行对各种作品的批评和反批评,以求得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文学创作水平的提高。“放”和“争”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有“争”无“放”,结果可能是万马齐喑;有“放”无“争”,结果可能是一片混乱。回顾过去,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曾经犯过放得不够甚至不允许放的毛病,给文学艺术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严重损失。这些年来,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有些人又犯了“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的毛病。那些有严重错误的理论见解和文艺作品畅行无阻,广为流传,而人们只要稍持异议,提出批评,立即遭到围攻,被斥为“大批判”、“打棍子”。本来应当具有科学性和战斗性的文艺批评变成了庸俗捧场和廉价广告。这种状况,极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我们痛心地看到,一些有才华的作家,以前曾经深入到沸腾的生活中去汲取创作的素材和灵感,写出了一些具有浓郁生活气息和较高认识价值、审美价值的好作品,但由于受到错误思潮的影响和庸俗捧场的误导,写出的作品越来越糟。真是曾几何时,而作者不可复识矣!有人说,错误的东西本来影响不大,你一批评,反而扩大了它的影响。这种看法不符合事实,也是对真理、对群众缺乏信心的表现。错误的东西是客观存在,装聋作哑,实行鸵鸟政策,挂出免战牌,并不能缩小它的影响。只有开展摆事实,讲道理,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评,才能让真理掌握群众,从根本上消除它的影响。必须指出,文艺批评并不是专指指摘缺点、错误,而是对一定的文艺现象进行分析、研究、评价、判断的科学活动。实事求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是它的基本要求。这对于推动创作、指导鉴赏、丰富理论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正常的文艺批评开展不起来,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不幸,但愿不要把这种状况带到21世纪去。
21世纪已经在向我们走来,足音咚咚,清晰可闻。让我们用辛勤的劳动和扎实的工作去迎接它,让21世纪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姹紫嫣红、大放异彩的世纪!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文革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