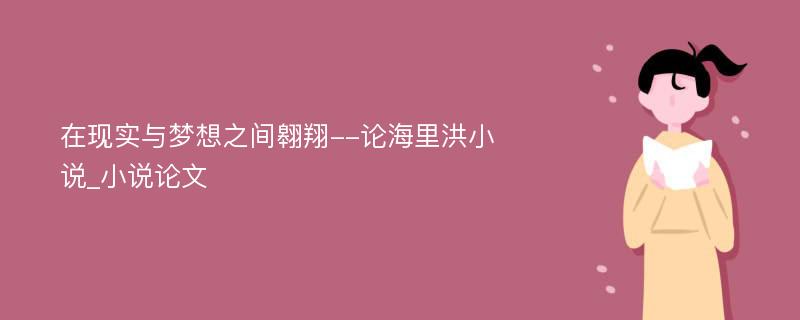
飞翔于现实与梦幻之间——海力洪小说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论文,梦幻论文,小说论文,海力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说作为一种虚构的叙事艺术,一直与现实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关系。即使是那些从故事表层来看与现实似乎毫无关系的作品,实际上也是通过各种隐喻和象征的手段来与人类自身的生存保持着紧密的关系。我们且不说《西游记》之类是如何通过神人之间的争斗来演绎人类真实欲望的奔突,卡夫卡的《变形记》之类又是如何借用人的异化来表达作家对普通平民生存困厄的隐喻,单就马尔克斯这样终生执着于表达魔幻与奇谲的作家来说,他也从来都不肯承认自己的小说是一种纯粹的虚构产物。最近,他在写作回忆录《活着为了讲故事》时又一次强调:“写作中,我力图不运用任何想象;像我这样的想象,我总信不过,因为实际上,我写作时只是进行回忆。”“问题是,我回忆时采用了一种十分严格的标准,即讲述的事情看上去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赢得了杜撰故事的大作家的名声,其实我什么也没杜撰。”(注:见《外国文艺》1998年第5期,第3页。)这种说法在我看来实在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狡辩。这位曾让“俏姑娘雷梅苔丝飞上天空,黄蝴蝶缠着毛里西奥·巴比洛尼亚打转转”(《百年孤独》中的情节)的作家,居然死活不肯承认自己的小说中存在着杜撰的成分,而且对自己被称为“杜撰故事的大作家”很不满意,这其中唯一的理由,我想就是他非常害怕自己的写作被人们视为与现实无关。
事实上也从来就没有作家曾公开坦言:我的小说与现实绝对无关。相反,许多看似写着一些与现实无关的小说的作家,总是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创作寻找着现实的注解,譬如余华就曾为他的一系列先锋作品提出过一个“心灵真实”的命题。(注:关于此点,请参见余华《虚伪的作品》一文,见《余华作品集》第2卷,第2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马尔克斯很不情愿用“想象”这个词汇而更乐意用“回忆”来描述自己的创作,在本质上也是企图证明自己的写作是指证现实的。因此,如果从创作主体的本源上看,所有的小说都是在试图以自身特有的方式介入现实、表达现实,都体现着作家认识现实、理解现实、处理现实的方式方法。正是由于他们对现实的认识、表达的不同,构成了多种多样的小说风格。
这也给我们洞悉一个作家的写作意图和审美理想提供了一个解读的切入口。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体察现实、表达现实,不是只表明一个作家与现实的关系,而是直接袒示着作家的审美追求,折射着作家在从事虚构艺术创造过程中的艺术能动性。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审度海力洪的小说创作,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作为一个在小说领域中活动时间还并不长久、写作成果也并不很多的年轻作家,海力洪几乎从一开始进行小说叙事时就非常注意处理自己与现实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不轻而易举地将自己的叙事资源定位在单纯的现实或是理想的层面上,而是试图通过更为灵活的方式来处理叙事与现实的关系,从而使他的小说始终飞翔于现实与梦幻之间,既保持着对某些生存状态的密切关注与再现,又不断地促动着小说灵性的生发与铺展。尽管在这种梦幻与现实的协调过程中,海力洪更侧重于小说的诗性品质,更倾心于对故事的灵动性、虚拟性的探求,但是在文本的内在追求中,他还是努力地表达着自己在这个时代的一种绝非纯个人化的生存感受,凸现着自身对存在的某些思考。
在这种对存在的思考中,面对种种现实的生存经验,海力洪不愿意屈从于对现实生活的直接表达,也不愿意在纯粹的个体生命内部享受叙事的快乐,他的写作目标几乎不针对个人的记忆,更不触及生存现实中那些表层上的焦点问题。在他的身上,我们很少能看到某种社会使命意识的制约,也无法明确地感受到他对自身知识分子角色的某种担忧。那些在六十年代作家群中共同体现出来的对物质现实的激愤与体恤、对个人欲望的沉迷与狂欢、对现代文明的景仰与缱绻等等复杂心态,在他的身上都没有任何鲜明的体现;而对七十年代作家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骄狂与虚妄,那种对世俗生活的投入与肯定,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特别的热情。也就是说,他非常清醒地将自己游离于社会群体之外,在叙事中剔除自己作为社会整体的人有可能会作出的带有社会主体价值性的大反应,摆脱小说家与社会学家在角色上可能产生的混淆。在他看来,小说家就是写小说的,只对小说的艺术形式负责,只表达自己对人和人的生活的认知,所以他很少选择大命题的社会叙事,而只专注于讲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审美考察。就现实生活而言,他似乎只注重那些能构成某种紧张关系的人与事,他不断地截取那些带有紧张成分的现实片段,然后将之融入故事之中,以此表达自己对待现实的态度。也就是说,他在处理现实与艺术的关系时,不是想从整体上把小说还原到“生活就是这样”,而是通过对生活中某些有意味的东西的开发与改造,表达“生活可能是这样”。
因此,在他的小说中,现实生活里那些看似非常亲密的、具有明确的社会伦理意味的人与事却始终处于种种非常特殊的紧张状态中。譬如在《药片的精神》中,是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在情感上的微妙紧张;《丧与殇》里,是父子之间、兄妹之间、夫妻之间、母子之间在血缘亲情上的紧张;《复仇记》中,是兄弟之间、母子之间在道义与责任上的紧张;《白雪》中,是夫妻之间、亲友之间在功利现实和人生价值上的紧张;《水淹动物园》里,是上下级之间在生与死上的紧张;《巨人》中是夫妻之间、梦幻之人与现实之人之间在理想和信仰上的紧张;《大风》中是父子、朋友之间在物质欲望上的紧张;《苦埃咒》中是亲戚、人与魂之间在实利与情欲上的紧张,《流感场》中是上下级之间、夫妻之间在生理疾病与心理疾病上的紧张……这些紧张不断地解构着一切惯常的社会秩序和伦理温情,在一种相当尖锐的叙事氛围中体现创作主体对现实社会和人体本质的种种拷问。
剥夺温情,在父母、夫妻乃至亲朋密友中设置种种互不信任的精神屏障,促动他们站在各自的价值立场上进行心理对抗,甚至在行动上彼此伤害,是海力洪津津乐道的一种叙事模式。尽管从文本上看,这种模式只是他在叙事上的一种策略,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也同样体现了他对现实生存内部关系的一种理解,尤其是对在传统伦理面纱笼罩之下的现代人际关系的某种感悟和质疑。他似乎不太相信那些庸常状态下的生存逻辑,对那些世俗性的外在生存状态显得相当冷漠,而更看重个体生命中那些隐秘的、带有对既成生存模式强烈抗拒意味的生活部分。我们说,人的生活实际上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现实生活、私生活和隐秘生活。现实生活构成人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的生存方式;私生活是确保人作为个体生命独立于社会群体之外、具有相对完整性的生存方式;而隐秘生活只存在于人的心理之中,带有理想的成分,是平衡现实生活与生存愿望的一种方式。海力洪着力于那种隐秘生活的发掘,集中展示着人在精神深处与凡俗生存关系的对立,实际上正是体现了他对现实的某种审美理解。这使他的小说很难在故事层面上直接给人带来某种震撼人心的审美效果,但在细节的内部却常常让人玩味再三。在《药片的精神》里,阿三和卢俊、吴童和林红这两对夫妻就故事表象而言并没有多少新奇的地方,但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却辐射出很多隐秘的生存方式。阿三和卢俊由同居而结婚,不是情感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由朋友吴童和林红所构成的情感胁迫所致。他们彼此之间都是亲朋密友,但在许多细微的言行中又透射出情感上的相互引诱、夫妻间的忠贞性的相互怀疑,而这一切又是非常模糊的、不确定的和极为暧昧的,无论是卢俊怀疑阿三与林红的关系,还是阿三怀疑卢俊与吴童的关系,都没有事实依据,因此这种怀疑就不可能被认定,人物的情感伤害只能处在一种难以言说的隐秘状态,彼此之间的矛盾也就无法转化成外在的冲突,而只能处在心灵内部的紧张状态之中,纤细、烦杂而又无法爆发,像炉膛内炽烈的炭火,虽看不见呼啸的火苗和烈焰,但内部的温度却可以灼穿任何一种物体,整个小说的叙事张力也就维持在这种状态中。
《丧与殇》虽然明显地体现出作家理念干预叙事的倾向,使故事显得有些坚硬生涩,丰韵不够,但在人物之间的关系处理上仍是值得称道的。小说围绕着母亲叶英的病重和死亡,将缪氏家族中的子女聚拢到凤城,让他们在这种特殊的短暂聚会中,衍生出彼此之间极为可怕的人性冷漠。这里,我们无法看到任何一点血缘上的情感亲密性和人伦上的温馨感,充斥于叙事的都是人物之间的不信任、不理解以及现代生存意义上的冷漠。缪印看到缪玉不正常的呕吐,没有兄妹之间的体恤,只有情感上的蔑视和嘲讽;母亲即将死亡,无论是父亲还是子女都没有多少心灵上的巨恸,只剩下伦理上的义务与责任;弱智的缪泥,从一开始就以一个被忽略的对象存在于这个家庭之中,到最后又被父亲当作累赘而扔来扔去,没有任何人伦上的关怀;母亲死去之后,面对孤老的父亲和弱智的弟弟,缪玺、缪印、缪玉这三个兄妹依旧无所牵挂地各奔东西。从整体上说,缪家的这次聚会只是一次奔丧,然而在这种“丧与殇”的过程中,他们失去的并不只是一位勤劳的母亲,一位至亲至爱的亲人,还有在那种生与死的诀别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亲情力量,人类应有的血缘情感也因此被消解得一干二净。海力洪正是通过这种特殊的故事营构,在尽力确保家庭外部平静的叙事状态下,使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处在情感的紧张状态之中,以种种细微的心理纠葛凸现出作家对现实的某种怀疑和感伤。
对这种亲情的怀疑与肢解,还体现在他的《寻仇记》、《白雪》等一系列作品中。《寻仇记》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在讲述一个为父报仇的亲情故事,但是由于仇人本身就是一个无法确定的对象,因而所谓的为父报仇也就不具备任何现实意义。小说的真正目的仍在于怀疑和质询亲人之间的情感强度。父母亲在生前看不出有多少情感上的疏离,但父亲死后,风华正茂的母亲却“从男人们的调情和麻将桌上的输赢中忘却丧夫之痛”;当自己的亲生儿子小华因为逃难而从寄养的兄长家回来,母亲和“我”立即表现出排斥的态度;当小华提出要为父亲报仇,母亲非常乐意地利用这个借口把他“打发”出家门;“我”与小华虽是亲兄弟,然而从小华回家的那一天起,彼此之间的紧张状态就从未消失。尽管在整个寻仇过程中,兄弟俩表示出某些愿望上的一致性,但那不是基于真正的“报仇”,而是出于一种少年式的对家庭规囿的摆脱心理,所以小说中的“寻仇”只是某种道具,真实的是“我”与小华对新生活的冒险。在这种冒险历程中,“我”总是离不开利用小华的念头,即使小华对“我”亲同手足,最后甚至送“我”一套房子,也没能激起“我”内心深处的亲情力量。《白雪》非常巧妙地用一个劳改释放犯的亲戚作为突破口,将一个濒临于死亡的婚姻家庭重新激活。对于“我”和阿琳的情感生活,伴随着阿琳演唱事业的一步步成功和“我”的命运不济,夫妻之间的隔膜渐渐地化作了内心深处的冷漠,在这种死水一潭的婚姻生活中,曾与妻子在幼年一起生活过的表兄曾宪出现了。面对这个出狱的劳改亲戚,阿琳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麻木和厌烦,仅仅是出于一种伦理和道义作了接待。而在这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包括“我”和周宪一起去贩毒到最后自己吸毒,表面上体现的是一种命运不可把握的状态,实则是人物对现有的冷漠而又紧张的家庭关系的绝望式反抗或者说是自戕式反抗。白雪,“我”心中所渴望的那种纯洁而又亲密的亲情,最后化为纯度极高的海洛英,为罪与恶所替代。而导致这一悲剧的根源,却在于现代社会中那种人的温情的丧失,情感纯度的大幅度退化。《流感场》以一场大面积感染的流感作为叙事动力,借助生理疾病与心理疾病的相互催发,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一轮叙事界定。其中既有一般同事之间由于对流感的恐惧而产生的相互疏离和戒备,也有夫妻之间、上下级之间因为流感的到来而衍生出许多颇具人性意味的言行。《大风》以欲望之间环环相套的叙事方式,把人性的内部图景表现得别有一番情趣。王强因为一场情
欲的呼唤失去了为父亲送终的机会,接着又在一封无法推证的父亲来信中,嗅到了金钱的气息。于是,物质上的引诱终于催发他踏上了远去的征途。而当他来到写信人的家中,意欲获取那份想象中的金钱,却不料被另一种欲望——杨爱武的偷窥欲和梦游症而击碎……
这就是海力洪对现实生存的一种理解。他总是试图撕裂一切缠绕在人与人之间外在的道德之衣,揭去那些伦理温情掩盖下的虚假人性,而将笔触直入人类内心深处的隐秘生活,小心翼翼地剥开它的外壳,既不对它进行过份的张扬,又不轻描淡写地展现它。他极力地维持着它们在人物内心中的潜在状态,使它们以一种看又看不出、说又说不清的方式占据各自人物的内心世界,构成人物彼此之间的内在张力。这种隐秘的生活如果表现得过于透明,无疑会使别人找到道德讨伐的依据,激化人物之间的公开冲突,那样虽在情节上可能更富有戏剧性,但是对于这种是非感过于明确的冲突,从小说自身的表现形式上说,并没有多少审美价值。海力洪好就好在对“度”把握得很难,用一种欲说还休的暧昧方式恰到好处地叙述出来,从而给人以某种苦涩的反刍。
现实生存作为海力洪小说创作的有限资源,只是为他提供了表达生存困惑的某种切入口。当这种现实本身的紧张关系不能推动叙事的发展时,他开始动用他的梦幻资源,不断地使用各种带有梦幻气质的人与事,激活叙事中的现实成分,拓展小说内在的审美空间,使小说文本恢复它的艺术灵性,展示它的诗性品质。
梦幻资源作为现实生活的对立面,是人类生活可能性状态的某种预示,它超拔于现实本身的实证性,只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在审美上具有某种灵动的怀想氛围。但是,如何将种种非现实性的梦幻融铸在现实性的叙事之中,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从而带动整个叙事进入更有意味的审美结构之中,就需要作家对叙事技术有着独到的把握。海力洪在往返于现实与梦幻之间时,非常注重对叙事过程的诗性培植,强调叙事本体的隐喻力量,力图通过各种虚拟化的手段达到空灵的审美效果。在这种审美追求中,最为突出的也许就是短篇小说《巨人》。这篇小说通过对故事的两次重构,以一种见证人的视角来讲述巨人光临某南方小城的经历。在这个人们身材普遍矮小的南方城市里,巨人无疑是作为他们对自身不足的补偿而出现的,即,那些虚幻的、活动于深夜街头的巨人们,实际上是人们想要超越自身世俗生活局限的一种理想式的隐喻。“只有一个巨人才能不犯弱小者的罪,只有成为巨人才能摆脱落在弱小者身上的折磨。帮助你就是要使你从弱小者变成巨人。”“我们巨人难以置信的高度其实首先是精神的高度,其次才是肉体的高度。只要你努力提高精神的高度,不知不觉中你的肉体便进化为巨人的肉体。”巨人的这种表白坦示了作者设置这种人物的隐喻意义,说明了他们是作为人们超脱庸常人生状态、进行自我精神提升的一种象征物。巨人对“我”进行反复规劝,希望“我”也能加入到巨人的行列,但“我”坚决不肯。尽管“我”非常清楚自己极为平庸的生存处境,每天都干着一些弱小者的卑琐行径,诸如“虐待老婆、被老婆虐待、过度手淫、计较金钱、买冰猪肉讨价还价、将亲友所赠礼品转送第三者、打面的寻享受、吃隔宿饭菜、厌倦工作、献媚上级、看电视当成唯一娱乐……”等等,但“我”还是不愿成为巨人,“说起投靠巨人行列,还有不少后顾之忧。如巨人只在深夜活动,白天睡觉,而我正好是那种天一抹黑就老打呵欠的人。如何适应?投靠巨人后得过巨人式的集体生活,抛妻弃家,我却又还舍不得小丽。”这无疑表明了世俗生存方式对人类精神自我提升的巨大制约,隐射着作为群体的、社会的、现实的人,无法真正地逼近自身理想状态的尴尬境域。实际上,海力洪正是通过这种带有梦幻特质的巨人与现实生存中的“我”的一次意外交流,完成了人类自身的精神理想与现实生存的一次对话,并在这种对话过程中揭示出人性上的许多缺憾,隐含着人类自我超越的艰难性。
《丧与殇》首先从叙事视角的择定上就将整个故事带入一种梦幻般的虚拟境界。作为叙述者的“我”是一个不具备任何理性判断能力的弱智者,而且在复述这个故事时已成为飘荡于世间的幽灵。于是,小说以一种回望的方式,让“我”站在未来的某一个时空点上,带着早已不具备现实意义的眼光来穿越时空的隧道,回顾自己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幕家庭悲剧。在这里,“我”既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一个有限的旁知视角,同时又似乎无所不在,不断地展示着家庭成员各自的生存状态甚至心理活动。“我”的所见所闻虽然没有多少价值上的判断,但真实地表达了整个家庭内部人物之间极为冷漠的情感关系。尤其是父亲与“我”最后漫无目标的逃跑,正是这个特殊的叙述者,将一场残酷的阴谋彻底地诗意化了,使那个驾着鲤鱼沿河漫游的青年的形象、“我”跳向远去的列车进行逃生的场景都显得生机勃勃。《药片的精神》中,我们无法确定叙事中有关“药片”的具体指向,它调节着“我”的牙痛和尿路感染,对付着陈医生与王娟做爱时小猫的乖戾,又使卢俊和“我”的儿子成为弱智……这里,它不仅起着连接故事整体的作用,而且成为人物之间精神境况趋近和疏离的纽带。《寻仇记》里动用了更多的梦幻情节。从小华的飞刀给“我”带来的恶梦到父亲死后托梦要“我”为他报仇,从“我”在省城街头看到的一场不朽的棋局到小华“强迫症”的不断发作,使整个的寻仇过程既充满希望又不断地落空,既显得生机勃勃又变得毫无意义。如果彻底地剔除这些完全没有现实可能性的叙事成分,我觉得这篇小说也就失去了任何诗性的气质,有可能会成为对余华的《鲜血梅花》之类作品的简单模仿。《水淹动物园》并不是一篇成功的小说,但是由于在整个情节的营构中,不少带有喜剧性的虚拟细节的展示,也使它的叙事显得相当鲜活,诸如处理死去动物尸体的方式、大水来临后群兽的表现、鳄鱼在洪水中的表现、王宝在洪水中的传奇式遭遇,都在一种近乎夸饰的言语中显得别有一番审美情趣。
值得一提的还有《大风》和《苦埃咒》等短篇。众所周知,相对于中长篇而言,短篇无疑包含着更多更高的艺术智性,也更贴近文学的诗性特质,它从话语方式、文本结构、情节设置等各方面都对作家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海力洪在短篇小说创作中虽然还没能写出颇为纯粹的作品,但他对短篇的叙事要求似乎有着明确而清醒的认知。因此,在他的短篇中,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梦幻话语中精妙效果。《大风》在审度现代社会中人的欲望时,将故事的高潮完全消融在人物的梦幻境界里。杨爱武偷窥的目的,是通过王强的梦境加以阐释的。而王强的远行动机,又通过杨爱武在梦游中的死亡而得以解构。梦境在这里不仅成了推动故事走向不可预知的结局的重要支点,还为展示人物的内在人性提供了一个可靠切入口。《流感场》里,正是人物由于对疾病的恐惧而产生的丰富联想,才使整个小说的话语保持着相当流畅的状态。其中的西瓜汁与血、感冒药与性欲、南方温热而充满病菌的生存环境与北方冰雪覆盖的景象都非常奇妙地关联一起,体现了作家很强的艺术整合能力。《苦埃咒》尽管在故事的整体上带有某种虚幻的意味,但是,海力洪却将人性内在的各种欲望之间的冲突隐含到对有关某种咒语的实践性过程中,使我们看到关于“我”的情感欲望与何仙姑的物质欲望在潜在的交换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喜剧性变化。
对梦幻成分的隐喻式发掘,还小说以想象与虚构的本质,同时又不过份地讲究叙事的变形和荒诞,构成了海力洪对小说审美意蕴的独到追求。这使我们感觉到,作为一个注重个性与风格的小说家,他正在积极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叙事理想,犹如东西对悲剧意蕴的喜剧性表达、鬼子对日常生存中苦难境遇的着意关怀、李冯对古典叙事的现代演绎,都体现出广西青年作家们极为可贵的叙事品质。
当然,海力洪之所以在每一篇小说中都努力地尝试着梦幻话语与现实话语的糅合,不仅仅是他在叙事上的某种审美追求,从根本上说,这意味着他对现实拒绝完全的认同。他也许不会像马尔克斯、余华等作家那样试图证明自己的写作是绝对真实的,因为他的审美目标似乎就是为了改造人们对叙事真实性的长期依恋。他不断地袭用着大量的梦幻细节,在终极意义上就是想通过虚拟的手段,使小说最大限度地恢复它的诗性特征。
无庸置疑,小说必须回到意义上,必须回到对人类存在深度的追问之中。这是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存在的价值和理由。如果我们赞同米兰·昆德拉关于小说的定义:“小说不是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注:《小说的艺术》第4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那么,当我们以此来观照海力洪的小说创作时,他的局限就非常明显了。对人性内在可能性的隐秘生活的揭示,他似乎很难触及到更深一步,而只是更多地停留在对它们之间内部关系的表达上,而且从内蕴上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重复。尤其是对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发展过程所有可能形成的生命状态,在追问中难以让人感到淋漓尽致。在整个的话语运作中,有不少作品很好地体现了他的诗性气质,但是,也有些作品过于明确地呈现出作家的理性支配叙事的倾向,制约了叙事在自由流动中可能会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审美发现。当然,对于颇具艺术智性的海力洪来说,超越仅仅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1998.11.11.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