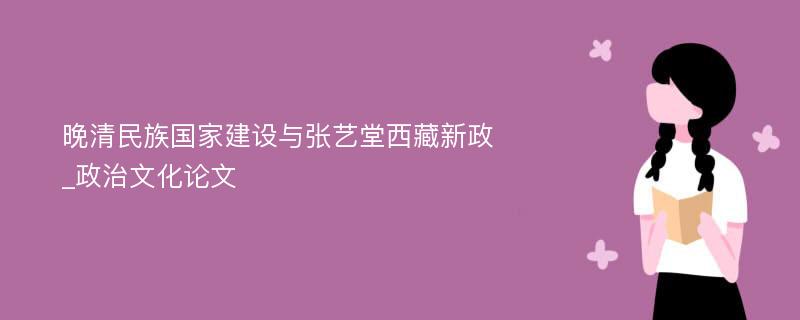
清末民族国家建设与张荫棠西藏新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清末论文,新政论文,民族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06年7月,张荫棠结束在印度“与英国议约全权大臣”之职,以查办大臣身份入藏办事。在藏11个月期间,他参劾贪吏,建章立制,推行新政,史称张荫棠西藏新政。这段历史历来为史家关注。检索以往的研究,可以看到一种大体雷同的叙事方式:一方面从中央政府治藏的角度出发,强调他重树中央权威,强化边疆管理,巩固国防体系等方面的努力与功绩;另一方面从民族平等原则出发,对他在西藏大张旗鼓倡导的文化革新活动,进行了分析性的批评,认为尽管具有近代化的先进因素,但“推行汉化”等主张带有明显的大民族主义思想,最终未能得到当地民众的拥护。①这种叙事方式局限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史的范畴,强调在边疆危机加剧之时,张荫棠体国忠君,励精图治的个人品质,却忽略了张荫棠西藏新政与清末国家整体性变革之间的联系,未能充分注意到张荫棠所主张、推行的思想、举措与此前清朝两百多年的治藏政策之间的明显差异,而恰是这些差异反映出清末在国家治理理念上的根本性变化。
芮玛丽(Mary Wright)、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等曾指出,清末新政是在民族主义(nationalism)以及“现代化”的招牌下进行的“民族国家建设(state-making)”,②期间推行的如建立新式学校、实行财政改革、创建警察和新军、划分行政区域、建立各级“自治”组织等活动,与此前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在封建王朝体制下救亡图存努力的区别,在于它突破了“中西体用”之辨,寻求建立“民族的国家”,这是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全新命题。从这个意义说,民族主义是理解清末新政的一把钥匙。近年来学界就清末民族主义思潮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为我们展示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图景。③然而,这些研究多侧重于对知识界、舆论界的研究,较少关注统治集团在新的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施政实践,更少论及这些新思想、新政策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影响。
本文试图以张荫棠西藏新政为案例,从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特别是民族国家建设和国族建构的视角,对清末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新政进行梳理和解读,以期能更深入地理解这场改革的意义。需要说明的是,作为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核心内容之一的“民权(民主)”问题在张荫棠的奏章中几乎未曾提及。这与他在西藏的时段有关。清末新政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以张之洞、刘坤一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指导思想,第二阶段以讲求“民权”的立宪活动为重点。张荫棠在藏之时,朝廷尽管已经派官员出洋考察政治,但尚未明确表态是否“立宪”,而此前清廷对“民权”之说持批判立场,“民权”自然不会成为张荫棠必须思考并奏报的内容。因此,本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权建设和国族构建两个方面。
一、“收回治权”:建立一体化的中央集权制
早在印度参加中英交涉之时,张荫棠就对英俄觊觎西藏,以及西藏在国际竞争中之危险处境有了初步的了解,为此他于光绪三十一年(1906)十二月十三日向朝廷发电提出了“收回治权”的建议:“遴派知兵大员,统精兵二万,迅速由川入藏,分驻要隘,所有一切内政外交,均由我国派员经理,并次第举行现办新政,收回治权。其达赖班禅等,使为藏中主教,不令干预政治。”④尽管对西藏的实情尚无切身体会,但是张荫棠根据在西方数国的经历,已不难察觉传统体制下地方权力集团的存在与西方民族国家体制之间的区别。⑤清朝被认为是“一个能够容纳多种制度、法律、文化和宗教的多元帝国”,⑥在这种体制下,皇权并不是对境内所有的地区和属民实施直接的、同一的管理,在边疆地区保留着许多享有一定自主权的政治势力,⑦如西藏地方政府以及广泛分布在西南、西北等地的土司、部落等。这种政治格局使清朝中央以较低的成本维持了国家统一和地方稳定,但其缺陷是这些介于朝廷与民众之间的中间环节固化了地域性认同,某种程度上对更大的政治共同体比如国家层面的认同构成阻碍。它们分享政治权利和属民的忠诚,有时候甚至形成与中央皇权的博弈。当中央政府的政令与地方势力的意愿相背相违时,就可能出现某种形式的对抗,直接削弱中央政府的动员能力。这种政治格局还给西方列强质疑中国对上述地区的主权提供了口实。因此,张荫棠建议中核心的一条便是实现中央对西藏的直接管理,而非假手中间环节。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五,张荫棠经哲孟雄、亚东入藏。在进藏5个月、抵达拉萨3个月后,张荫棠向朝廷呈交了《治藏办法》,⑧详细论述了有关西藏政权建设的构想。
按照张荫棠的设想,“收回治权”首在废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在政治上的权威,将其权威限定于宗教事务。这是管理体制上的重大变化。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规定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共同管理西藏事务,但后来特别是嘉庆朝以后,由于驻藏大臣个人品行、能力等方面的欠缺,特别是琦善任上放弃对地方政府经济权的监控后,“驻藏两大臣,徒有办事之名,几同守府”,“久已放失政权”。⑨另一方面,“政权多出藏僧之手”。⑩因此,要“收回治权”,建立新的体制,就必须限制或废除他们对政务的参与权。张荫棠提出,“达赖、班禅拟请赏加封号,优给厚糈,专理黄红教事务”,“尊为藏中教主”,虽然“体制尊崇,与印度土王相埒”,但受汉官监管,受拟新设的行部大臣节制。(11)
张荫棠拟按英国统治印度之法在西藏建立新的体制。(12)他提出应“将驻藏大臣、帮办大臣两缺裁撤,改设行部大臣,似宜特简亲贵或内外文武兼资大臣,畀以重权,便宜行事,以资镇摄”。行部大臣之下“设会办大臣一员,统制全藏”,这相当于印度总督,“下设参赞、副参赞、参议、左右副参议五缺,分理内治、外交、督练、财政、学务、裁判、巡警、农、工、商、矿等局事务”。(13)这样,就可在西藏建立一套新型的虽与内地各行省有所区别,但所有内政外交之权全部由中央控制的管理体制和机构,实现“收回治权”的目的。
然而,“立新”虽易“废旧”却难,对于如何处理西藏地方原已存在多年的官僚系统,考虑到西藏的现实情况和新政方案的可行性,(14)他提出一个双轨并存的妥协性过渡方案。首先是“照旧制复立藏王体制”,“由行部大臣饬三大寺大公所会同选定奏补”。显然颇罗鼐时代“藏王”与驻藏大臣关系融洽的历史对他有所启发。更为重要的是“藏王”作为世俗官员是可选可废的,最终决定权在行部大臣,而不似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那样具有身份先赋的特征,其存废难以由驻藏官员决定。藏王之职仿照印度各邦土王的体制,是西藏官员的首领,其职责“专管商上(西藏地方政权)事”,而其他向来“掌握政权”的四名噶伦、统带番兵的戴琫等,“均宜由我(指朝廷)优给月薪……每日赴(行部大臣)署秉承办公,归行部大臣节制”,成为行部大臣的属下。在地方上,他指出“西藏向以番官管理地方职任,如内地州县官”,“拟请于各营官分驻之地,择繁盛冲要之处,如江卡、察木多……等处,先设巡警局、裁判局作为差使,勿限以官阶,暂用陆军巡警法律学堂毕业生署理”。(15)根据他制订的“九局章程”,巡警局负责“缉捕盗贼,安靖地方,弹压械斗,保护中外往来官商,兼分段修治道路”;裁判局负责“户婚钱债词讼”等事。(16)
西藏原先的噶伦以及地方的宗本(张荫棠称“营官”或“番官”)都是一身兼管行政、司法和税收,张荫棠不触动原有体制,保留原有官员,而另设负责同样事务的“汉官”(清末有关西藏文献中之“汉”,主要指与“藏番”相对应的中国内地人或儒家文化,而非专指汉族,满族、蒙古族等皆在“汉”属之列)。显然,“番官”、“汉官”在职能上相互重叠。这种叠床架屋的双轨体制,既是无奈的权宜之举,也是以退为进的策略,目的是为了监督“番官”,便于将来取而代之。(17)
无论如何,对于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官员来说,实现上述目标至少在宣示主权方面已经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现代国家的主权宣示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西藏的对内主权在张荫棠看来并不存在很大的问题,尽管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有泰关系不睦,但对于皇帝仍然表示效忠、服从。但是,传统体制在国际主权的宣示上却屡遭质疑。英国人屡次表示驻藏大臣在藏不能过问政事,为藏众所轻视,不能尽主国义务,因此在藏无主权。英国军官吉治纳曾言“西藏之事,我政府非不愿与贵国交涉,因贵国在西藏不能尽主国义务,藏人不遵守(光绪)十六、十九年条约办理,使我政府不能不行与藏直接政策”。(18)国际承认是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前提,因此,张荫棠特别注重宣示主权。比如他建议让达赖、班禅赴京陛见,认为这是对外宣示“主国名义”的大好机会。(19)他阻止英国直接与藏官签订协议,阻止由藏官直接支付战争赔款,阻止中英关于西藏的协议条约文本用藏文,也是为了防止英国借此而质疑清朝对西藏的主权。“收回治权”之后,种种对外宣示主权的行动便自然有其法理和事实的根据了。
为了顺利实现“收回治权”和抵御外来侵略两个目的,张荫棠对国家强制力量(包括军队和警察)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他最初建议由“贵胄统带精兵二万总制全藏”,但“经费浩大,国帑支绌,诚属为难”。(20)但进藏后,他发现“藏人……积弱已极,官皆纨绔,愚懦无能,兵器寙败,人心涣散”,只要朝廷“稍有兵力坐镇”,西藏“断不能为边患”。因此,为收回治权实际上无需要太多的兵力,他指出“或谓收回政权,藏官恐滋反抗,致酿第巴桑结、朱尔墨特之乱。臣料藏人贫弱而愚,现在尚无反抗之能力,即有小衅,苟有练兵三千,足资镇抚”。(21)因此这个时候,他练兵的目的主要是抵御外来侵略。他相信英国的军事威胁迫在眉睫,随时有可能再次发兵进藏,“非有实力以盾其后,万不足恃”。(22)综合形势的需要,他提出了练常备军4万,先练6千,逐年增加的计划。根据他的估算,要实现他提出的最低要求,至少需要180万两白银(练兵需120万两,巡警局需60万两)的年度经费,这还不包括枪炮制造等项支出。在他举办新政的年度经费预算(300万两)中,用于强制力量建设的费用超过3/5。而事实上,在张荫棠离开西藏后,朝廷最终拨给驻藏大臣联豫的年度经费只有20万两,是张荫棠全部要求的1/15。他对这种经费状况本有认识,他的策略是,“练汉军以资震慑”、“练番兵以自谋保护”,“番兵”之饷由西藏地方政府自筹,以减轻朝廷负担。同时通过“使番兵均归汉官教习统带”,将全藏兵权掌握在“汉官”手中,以防尾大不掉之弊。(23)而要逐年扩充军队,真正训练一支足堪抵御外侮的军队,靠朝廷支拨经费,显然难度极大。因此,他指出练新军必先筹饷,欲筹饷,必先振兴农工商业,“盖商务旺则其国富,国富然后可以筹饷制械而兵强”。(24)在当地寻求利源似乎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他提出并建立的九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训练军队、筹集经费之用:外交局是对外交涉和掌握外部信息的机构;督练局是负责训练军队、保卫国家主权的机构;巡警局是维持内部秩序,保证税源稳定的机构;学务局是培养军队后备人员、增强国家认同的机构;而其他盐茶局、财政局、工商局、路矿局、农务局都是负责增加利源、筹集军饷的机构。
总之,张荫棠试图“收回治权”的种种举措和构想,就是要废除、解构中间权力结构,建立一个与中央相衔接的专门化的官僚体制,实现中央对西藏各项政治权力的绝对控制。然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仅有组织机构、法规制度等外在的特征尚属不足,其久远的成功还必须仰赖全体国民的认同与支持。这就需要有计划地进行国族建构。
二、“合同而化”:构建文化同质化的国族
所谓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是借用一种建筑学上的比喻,指“引导一国内部走向一体化,并使其居民结为同一民族成员的过程”。(25)换句话说,指国家对具有不同历史、文化的人口进行整合,以确定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维系民族统一的一体化过程。国族建构作为一种官方推进的政策发端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政治统一的建设,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政策的实施,建立国民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另一方面是文化的统一性建设,即通过制度、政策和教育宣传等促进国内文化的同一化和以国家为中心的统一民族认同,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从而实现民族(nation)的“同质化”。(26)张荫棠新政的目标之一就是如何让藏人与内地“汉人”拥有共同的文化,实现文化的同质性,最终成为一个文化—政治共同体——国族。为此,他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并将之付诸实践。
(一)文化的同质化努力
关于文化的同质化问题,当时国内主流的社会舆论认为应当通过多途径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如康有为建议“蒙、回、卫藏,咸令设校,教以经书文字语言风俗,悉合同于中土,免有歧趋”,(27)通过学校教育实现“合同而化,永泯猜嫌”。(28)梁启超借鉴伯伦知理的思想,提出“谋合国内多数之民族使之化成为一民族”,“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29)尽管并未说明“合”和“组成”的具体方法,但显然也是谋求一种共同的文化特征。张荫棠就是立足于“合”、“化”的思想,在新政措施中融入了宗教改革、学校教育、民俗改良等文化革新的内容,其目的就在于实现“合同而化”,最终形成全体国民的文化同质化。
1.宗教改革 通过近两年与英印政府就西藏问题的交涉,使张荫棠多少对宗教在西藏社会中的巨大影响有了一定的认识,他在奏折中称,“臣自抵藏,屡与喇嘛演说佛理,即借宗教以联络藏众,因所明以通所蔽”。(30)在具体措施中,张荫棠虽然未提宗教改革之名,但他试图推广儒家三纲五常学说,确有宗教革新之实,包括两个方面内容:
第一,改变西藏民众对佛陀和宗教领袖的崇拜,转而以清朝皇帝为崇拜、效忠的对象。近代民族主义主张民族(nation)和国家是人民效忠的对象,然而对于“家天下”的封建王朝来说皇帝就是国家,皇帝才是臣民的唯一效忠对象。在《传谕藏众善后问题二十四条》中张荫棠屡次宣示大皇帝的权威,《训俗浅言》亦言“西藏人皆是大清国百姓,当遵奉大皇帝政教,忠心事主,心如铁石,至死不变”。(31)《藏俗改良》中说:“西藏系大皇帝土地,达赖系大皇帝敕封,唐古特系大皇帝百姓,依托大清国庇荫,故能安居乐业,黄教昌盛。”(32)他指出列强屡次怂恿西藏“自主(即独立)”,然而其背后却是夺地灭国的阴谋,“尔等观印度、哲孟雄等处,土地已归他人,受人鱼肉,佛教衰微,渐为耶稣教所灭”。(33)在《游布达拉山记》中,他比喻英国、俄国为“夜叉罗刹之国”,“挟兵力以行其妖教”,乃佛教之敌,要振兴黄教只有依靠中国皇帝的保护。(34)因此,忠于大皇帝,否定“自主”才是正确的选择。
第二,用儒家的纲常伦理取代佛教思想。时人认为,“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35)张荫棠便试图以“中国之宗教”替代黄教。在他颁发的《训俗浅言》中指出“大清皇帝为黄教之主国”,而“教”之要件包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五伦”学说。张荫棠还阐发了儒家的博学、审问、慎思、明办、笃行,以及智、仁、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思想。认为这些思想应该成为藏人所信仰宗教的内容。这是他对清末新政纲领性文献《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所提出的“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36)思想的忠实履行。
为了使藏民能够接受儒家说教,他还做了两个方面的努力:
其一,以佛教思想来解释儒家纲常。比如儒家之所谓“仁”,乃“仁者爱人,施舍衣食,以活穷民。教人读书,使明道理。己所不欲,勿以施诸人”之意,张荫棠指出这与佛法所宣扬的慈悲、普度众生同义。儒家的“勇”包含“忠勇之事,奋勇做去;非礼之事勿动,非义之财勿取,勇于知非;痛自改悔,不蹈前非;临阵独当前敌,收队独居人后,是谓勇于公战”等含义。而佛教宣扬的“佛入地狱,以救众生,亦只是个勇字”。(37)儒家的忠臣义士与佛家破除无明、献身利他的“勇”者一样死后可以登天堂,证佛果。他还以因果报应说解释贪利之害,说即使不败露,贪官死后做骡马猪狗还债。
其二,解构佛教的合理性。他虽然没有直接说佛教教义具有虚假性,但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例批评佛教。他认为做喇嘛,沿街讨钱,望人施舍,是苟图安逸的行为。(38)批评僧人“日诵经典,望神庇佑,望人布施,是为分利之人,非生利之人。人人皆思分利,愈分愈薄,国安得不贫,贫斯弱矣”,出家为僧寄生食利,于社会发展、国家富强毫无益处。他指出“天道不外福善祸淫,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非延僧诵经祈祷所能为力。妇女小儿之畏鬼神者,皆由无见识妄生恐怖。切不可迷信降福,卜卦符咒”,“月蚀、日蚀、电雷、雪雹、风雨、孛彗、山崩、地裂,皆天地运行自然之理……乃经纬度一定之理,切不可听神怪之煽惑”。百姓应当“敬鬼神而远之,不可谄渎祈祷”。(39)他特别批评西藏政教上层“战而无备,不练兵”,“平日漫无战守之预备,无兵无饷,一旦驱未经训练之愚民,持朽腐锈坏之武器,贸贸然与强敌战,视同儿戏,是不啻手刃屠戮其民”。这是严重违反“佛教慈悲戒杀之旨”,属于“残害无辜”,因此“纵免国刑,必遭阴谴”。在优胜劣败的时代,“虔唪经典,不足以御巨炮也,谬信符咒,不足以御快枪也”,(40)因此,“喇嘛诵经功课,宜在早晨六钟,或在夜里九钟,白昼不必诵经。宜兼做农工商业,以生财,不可望人施舍”。更进一步是要绝大多数僧人逐渐与世俗无别,其理由是:“西藏本系佛地,藏民人人为喇嘛……或虑喇嘛多则生齿寡,不知佛教真诠,原不禁人娶妻生子吃肉。其不愿娶妻者,别为苦行喇嘛,其愿娶妻者听。喇嘛仍可充农工商兵诸业。”(41)
2.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是向所有的公众灌输“公民”意识,强迫人们接受整套国家认同符号的最有效方式。(42)清末新政期间官僚阶层对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已有了全新的认识。张之洞名噪全国的《劝学篇》对如何结合中西,发展中国特色的学校教育开出了药方,他和刘坤一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一折就专门讨论学校教育问题。出国考察立宪的官员亦对学校教育的重要性有精彩论述。(43)张荫棠对学校教育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他在《奏复西藏情形并善后事宜折》中谈及治藏策时认为,“为今之计,自以破除汉番畛域、固结人心为第一要义,以收回政权、兴学练兵为入手办法”。(44)所谓“破除汉番畛域、固结人心”就是要强化认同,增强凝聚力,而兴学是其中的重要手段。
张荫棠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秉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杂糅“中国古学”与“中国新学”(即西学),尤其对推广汉语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张荫棠在《善后问题二十四条》中称“藏民愚蠢,多不识藏文。既系中国百姓,又不识汉文,不懂汉语。应汉藏文兼教,使藏民人人能读书识字”。(45)这是一种全新的、极富时代特色的观念。此前各王朝的边疆治理理念是“齐其政不易其俗,修其教不易其宜”,朝廷并不要求边疆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汉文,从来也不认为学习汉语是西藏官民作为皇帝臣民的条件。将一种方言国语化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原则之一。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方言被认为是不易接受新的文化和新的政治生活的、妨碍民族(nation)统一的障碍,消除方言,统一国语被认为是新型国家的特征。(46)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语境中,张荫棠推广汉语,实际就是要解决语言的统一问题。
张荫棠为推行汉语汉文设计了具体的策略,要求在“户口稠密之处遍设初等蒙小学堂,专课汉文汉语。凡男子七岁以上,皆许就学,延用邻省教习,语言易通,选用浅近课本,教以识字谈话之音,造句成章之法,以期渐归同化”。为了加快藏族学生学习汉语的速度,他还主张“学生在学堂中宜专讲汉语,所用服役小娃宜用川人”,(47)在生活交往的过程中提高汉语能力,这样学生一年可全通汉语。
具体来说,张荫棠对汉语学习的强调,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都与民族国家建设息息相关:其一,“语文不相通,办事致形隔膜”。换句话说即是语言统一方可使政令通行、管理便利。即如安德森所言“发展标准的国家语言,助长了文书的可换性,而这又增强了人员的可换性”。(48)其二,推广汉语以增强认同。张荫棠认为汉文汉语是“属地与祖国同化之要枢”。(49)其秘书何藻翔也说:“语言文字相通,然后能团结其祖国思想。”(50)同时代的程淯条曾在奏折中指出:“结合民志宜实行统一语言也……王者之治,文轨大同……是以昔贤有云:通天下之志,必自发言始也。盖语言所以代表思想,语言不一,则情意隔阂而无感触,志趣涣散而难团结……(语言)归于一致,则声气易通,情志不隔,全国团体结合自坚,此各国行之已有成效之事。”(51)可见,通过推广汉语以增强国家认同似乎已成为清末官僚阶层中的普遍看法。其三,学习汉语乃是西藏得以进化(发展)的必要途径,因为“先练习中文,通晓汉语,然后考求西国文字技艺。因西国各种技艺,中国皆有已译成之书也”。(52)考求西学是进化的必然手段,然而藏文除了注疏佛经外,尚无译介西学之书,而汉文中西学著作多已译备。因此,学习汉语即可阅读西学论著,从而获得进化。(53)因此,欲得进化只能是先学汉族,再学西方,只有遵循藏族→汉族→西方这样的学习路径,才能实现藏族文化的进化。
3.民俗改良 张荫棠于民俗改革用力尤重,先后颁发《藏俗改良》、《训俗浅言》,专论民俗改革问题,除了其中的部分条目提倡科学的生活习惯外,多数条目都是在倡导一种与内地文化和生活方式趋同的风俗习惯。比如在《藏俗改良》(34条)中有关风俗改革的内容共19条,许多条目直接涉及生活方式,如:
·一妇只配一夫,兄弟不得同娶一妇。·闺女寡妇,不得私通苟合。·兄妹姊弟叔嫂婶侄,不得同炕卧宿。·父母老病,为子妇者宜侍奉汤药饮食,以终其身。一息未绝,不得弃置别室。·人死宜用棺木,或氆氇扎束,掘地七八尺,埋荒野。勿用天葬,以喂鹰狗。勿用水葬,以喂鱼。因秽气四扬,水染尸毒,于他人卫生有碍,不得已或用火葬较可。·身体每日洗浴,头发宜常梳洗,衫裤勿使污秽。·衣服宜改短窄,以便做事。·儿童七八岁宜教识汉字,学汉语,以便到内地为官或为商。否则人人专做喇嘛,未易发大财。·男子出外谋生,充农工商乌拉,妇人在内管理家务,养育儿女。·夫死,其妇宜留以侍养翁姑,抚育儿女,不宜改嫁。如系赤贫,无人倚靠者,亦应俟一年服满后,方可改嫁。故妇死,其夫亦一年后方再娶,以尽夫妇之义。·见客礼,宜以合掌为常见礼。凡曲躬吐舌竖指头之礼,贻笑各国,皆不可行。中国礼做作揖请安,外国礼做握手免冠,在各人因时择用亦可。·男子不宜戴耳环,妇人不宜用儿茶涂脸,又,饭碗等物不宜藏胸怀里,此皆各国所无,免失观瞻。·两兄弟同娶一妇,则生育子女必寡,因妇人必隔年方能孕育一子女也。生齿日寡则国弱,必为外人所侵凌。各国均无此风俗,令人耻笑。·妇人配定一夫后,必不可与人偷合,此最耻辱之事。且生子女受毒,不能养育。
这些习俗的是非标准一是儒家的伦理纲常,二是西方可接受的礼仪,三是符合现代科学的要求,四是有利于经济发展。凡与这些标准不符的传统习俗,都或明或暗地遭到了否定和嘲讽。张荫棠指出,他的目的是指出藏俗的污点,使藏人“徐遵以孔孟三纲五常之正理,爱国合群尚公尚武之新义”。(54)这些举措的最终目的是让当地藏人虽然有着自己的血统和肤色,但是他们的品位、意见、道德与思维能力却是儒家式的。然而,在张荫棠看来这既是进化的必然,也是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先决条件。
(二)锻造国族气质
张荫棠不仅期望通过上述的方法改造藏人的文化,使之与内地同一化。同时,他还期望具有新文化的藏人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是谋求自强所不可或缺的,其中包括:
1.合群思想 自严复译著《天演论》以来,合群以图进化、求富强,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共识。梁启超即称:“以物竞天择之公理衡之,则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合群之德者,以一身对于一群,常肯拙身而就群;以小群对于大群,常肯拙小群而就大群,夫然后能合内部固有之群,以敌外部来侵之群。”(55)张荫棠早在印度期间就已经知道不仅“汉”藏之间存在隔阂,就是西藏内部也存在前、后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既是此前清朝实施分而治之、以夷制夷政策的结果,也是后来英国蓄意挑拨离间的产物。到西藏之后,他还发现藏传佛教各教派之间也存在或浅或深的矛盾,这种力量的分散状态根本违反“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的公理。因此,他在西藏极力宣扬合群进化思想,曾经亲临大公所(民众大会)“痛陈天演物竞”之理。同时指出“汉藏畛域”、“自分畛域”的危害,各种力量“互相猜忌,互相倾陷,置国事于不顾,适以堕敌之狡计之中”。
他从几个方面强调了合群思想的具体内容:(1)汉藏合群:“西藏百姓与中国血脉一线,如同胞兄弟一样。”(56)将汉藏民族之间的关系描述成为具有血缘关系的兄弟手足。(2)格鲁派与其他教派合群:“西藏黄教、红教虽分两派,实同一家。应如何互相联络,释前嫌而共谋御外侮。”(3)前藏(噶厦政府)和后藏(札什伦布寺拉章)合群:在《致班禅函论拉章商上不宜各分畛域》中,他说:“前后藏唇齿相依,同种同教,不宜各分畛域……此时唐古特人等同心协力,尚恐难以御外侮,不应同室操戈,以中外藩之计。盖前后藏合则力厚,分则力薄,譬如树枝然,一树枝则柔脆易折,合十树枝成一束,虽极勇力者不能折之矣。”(57)(4)西藏与喜马拉雅山国家合群:“西藏与布鲁克巴(本中国属地,英人谓布丹国)、廓尔喀地势犬牙相错,实如唇齿之相依。应如何互相联络,以冀巩固吾圉”。“速派噶布伦、戴琫亲往详查,参仿其兵制以练新军,改良一切政治。与廓尔喀结攻守同盟之约,无事相亲睦,有事相扶持”。(58)(5)提出应将那些因故革职或卸任的官员也团结起来,因为“彼等更事较多,阅历较深”,有丰富的经验,起用他们充任九局官员或请其参加会议,征求意见,可以起到集思广益的效果。(59)总之,他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厚积实力,抵御外侮。
2.尚武思想 清朝末年,严复译著《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警言已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奉,最终必然指向对武力的推崇。张荫棠在西藏便大力鼓吹尚武思想。他指出“方今地球各国玉帛往来,无不恃枪炮为后盾,所谓武装世界也。遇曰有强弱,无是非,诚有慨乎其言之。我苟不能自强,势必受人鱼肉。果人人有发奋为雄之志,有誓死报国之心,以铁血为主义,以军国民自任,一洗琐委宽博之态,具有威武不屈之风,一群皆血性男儿,虽有强者,亦莫予敢侮。但斗力不如斗智,必设武备学堂,以考究战阵学问,培养将材。虽不可轻开边衅,而武备不可一日不讲。日日练兵,人人讲武,是八字要诀。凡国民年二十岁不能骑马执枪当兵打仗者,是为废人。是在上有以教之,以养成其尚武精神”。(60)认为弱肉强食的世界公理,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得以生存,就必须练兵尚武。
他首先以1904年藏英战争的失利来警醒藏人:“拉萨城破,达赖出奔,实为唐古特千年未有之奇辱。尔等宜将战败杀戮惨状绘为图书,悬诸三大寺门口,永远不忘此耻。勿谓今日和约可长恃,当常思念敌人猝来挑衅,长驱直进,尔等有何策以御之。”(61)并以廓尔喀为自强之榜样,“廓尔喀地虽小而兵甚强,近来采用西法,改用洋操,有精练民兵三十万,又有制造厂,能自铸枪炮,选聪强少年往外洋游学”。(62)
他提倡人人尚武。称“毛瑟枪为人生保护性命室家之根本,无枪必受人欺凌。每枝价银卢比三十六元,子药每千粒卢比七元。四川、印度等处均有卖。无论男女均各售一枝,共费卢比四十三元。无事时往各山打猎,猎得白狐、猞猁、虎豹数只,便可够枪子之资本,以后均为溢利。如外敌盗贼等来侵,各携枪齐心协力出战,为佛教出力。各如报私仇,倘杀得一敌人,便死了亦够本,杀两人便算溢利”。“只许外国来通商贸易,断不许其侵占我土地,誓死与之拼命,死后升天成佛”。(63)张荫棠的全民皆兵,甚至要僧人拿器武器杀死敌人、打猎求利的主张,反映了他备战御敌的强烈愿望,然而其中的许多内容无疑是脱离现实的。
三、结语
张荫棠西藏新政是清末新政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以民族国家建构为核心内容,是传统西藏社会现代转型的最初探索,揭开了西藏现代化发展的序幕。细察张荫棠奏稿,不难发现他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举措,与此前清朝两百多年的治藏政策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不再满足于通过噶厦政府实施间接的羁縻控制,而强调“收回治权”由中央进行直接管理;不再推崇宗教(包括宗教领袖)的崇高地位,转而批判宗教的虚妄和对社会的消极影响,主张政教分离;不再奉行文化上的多元主义和宽容态度,而是期望通过民俗改良、学校教育等方式输送儒家文化,以期实现藏族文化与内地文化的同质化,等等。把这些变化仅仅看成是边疆危机加剧背景下在管理力度、方式等层面的变化或疆吏个人的励精图治,并不完全准确。要理解、解释这些变化就必须将其放置于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寻求国家整体性变革的总体框架之中。具体来说,清末新政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在理念上已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即不再固守用传统的宗藩关系实现秩序和谐,而是试图建立一个将边疆与本土融为一体,更具凝聚力、竞争力的现代民族国家。然而,正如“新政”整体的悲剧命运,张荫棠西藏新政的努力在实践层面远不能算是成功的,有人甚至认为他是失败的。(64)因为他的部分构想根本未能得以实施,一些措施随着他的离任而终止。然而,在辛亥革命前后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如何在一个多民族社会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成为革命者、维新派和当政者,都必须面对的时代性命题。无论张荫棠西藏新政成功与否,他对如何将边疆民族地区纳入新的体系之中,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转型,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其间成败得失,以及所凸显的问题的复杂性,是值得我们进行一番梳理的。
张荫棠看到了传统王朝与现代民族国家在政令畅通和资源动员能力上的差异。欧洲国家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全体国民,通过统一的号令调动全国资源,参加国际竞争或对外扩张。按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合全体国民能力以实行“民族帝国主义”。(65)要应对这样的国际环境,就必须提倡民族主义,组织完备之政府,发展农工商以丰军饷。总之,要强化政府的权威,消除那些构成障碍的中间权力环节。因此,张荫棠“收回治权”的主张符合时代的要求。但问题是如何实现新旧转变,随后又建立一个怎样的政体。
张荫棠提出“收回治权”,他的最终目标是废除西藏地方政府原有的架构,以此实现中央的直接控制。即便不是行省化,也要实现中央皇权对西藏地方的绝对控制。实现目标的途径当然可以有激进与和缓两种选择。如果采取改良性的方案,改革的阻力自然可以化减,但需要漫长的协商、博弈过程,列强环伺、内忧外患,岂能容忍漫无际涯的等待。如果采取革命性的方案,势必要触犯当地的利益集团,有可能发生“顽梗不从”,“铤而走险”之事。张荫棠虽倾向于革命性的方案,但是军力薄弱和财力支绌,又不得不做出妥协,权衡之下,他设想了一个双轨并存的过渡性政治体制,以减缓震荡。
关于新型体制,张荫棠的构想是将清朝的新定官制与英印政府的管理体制结合起来,用少量的“汉官”取代藏官,实现对西藏各级地方权力的管理。这就是说,张荫棠所主张的“收回治权”,从终极目标上看,不仅要实现中央集权,而且要在地方治理的各级决策集团中弱化当地人的影响。当然,这并不是张荫棠独有的,而是辛亥革命前后许多政治精英所持的主流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边疆政策实际上引发了更多的矛盾,边疆危机也随之加剧。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的原因是张荫棠等人只看到民族国家体制在增强国力、维护统治方面的长处,却没有看到或者说不愿意承认西方国家内部的“民权”制度,只单方面要求民众“忠心事主,心如铁石,至死不变”,但不愿赋予当地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权利。事实上,民族主义要求个体对国家的效忠,必须是建立在全体国民权利平等的基础之上,没有个体的政治权利平等和相应的利益表达渠道,国家利益的要求就不具有“合意”性质。(66)“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张荫棠单方面强调当地民众对皇帝、国家的效忠义务,却忽略当地民众的政治参与权利,就与近代民族主义的理念背道而驰了。
与当时公共媒体上多数的论者相似,张荫棠也深受单一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持一种“根基论(强调血统、文化、语言等的纽带作用)”的国族思想,相信“一国之内,若有无数异族,则思想不同,语言不同,风俗不同,因而利害相弛,感情相背”。(67)因此,要建立一个能够维护原有版图、囊括原有众多民族的现代国家,就必须对语言、风俗、观念不同的边疆民族实行文化同化,只有这样才能锻造出能够相互“吸集”、“固着”的具有文化同质性的国族,才能形成合力以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张荫棠的国族建构不仅要形成共同的政治文化和对国家的认同,同时还要求全体国民在语言文字、生活方式、道德观念上的同质化。他在西藏努力推行的文化革新活动,试图使西藏民众放弃他们原有的文化,逐步转变成为具有儒家式的品位、意见、道德与思维能力的人。这是一种割裂当地历史文化传统的行为,必然会引起抵触与抗争。张荫棠之后,联豫、赵尔丰等都为实现文化的同质化而进行过各种努力,然而收效甚微,最终随着清朝的覆亡而不了了之。
具有根基性纽带联结的群体在共同行动中可能具有更多的优越性。查尔斯·蒂利曾言:“在一个同质的人口中,普通百姓更可能认同他们的统治者,交流可以更高效率进行,在一个局部行之有效的管理革新也可能在其他地方奏效。而且,感受到同源的人们更可能团结起来反抗外来威胁。”(68)但是,具有同质性文化的群体并不必然地产生共同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本质上是一种认可、参与、政治忠诚和承担义务,是与特定的利益诉求相联系的。因此,多元文化认同并不必然成为国家认同的障碍,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证明,国家认同完全可能超越文化同质化而得以实现。清末新政对单一认同的追求,既非中国的历史传统,也未成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它只是特定时代对欧洲国家的简单模仿。
注释:
①参见多杰才旦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99页),伍昆明主编:《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鹭江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页),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67-970页),赵云田:《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②参见Mary Wright, 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 1900-1913,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pp.3-4:[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2页。
③相关讨论参见李国祁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唐文权:《觉醒与迷雾——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罗福惠:《中国民族主义思潮论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王春霞:《“排满”与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等。
④张荫棠:《致外部电请迅速整顿藏政收回政权》,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4页。张荫棠在不同的奏折中使用“收回治权”和“收回政权”两个词汇,事实上“收回治权”更为准确。
⑤宁骚先生从5个方面总结民族国家的主要特征:(1)具有得到内外承认的主权和统一的领土;(2)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中央集权制,废除任何的中间权力结构;(3)主权人民化,民众具有政治参与权;(4)国民文化的同质化,具有稳定的同一的认同;(5)统一的民族市场,国家内部没有市场壁垒。参见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281页。
⑥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一部:《物与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2页。
⑦何伟亚并不十分准确地将清朝描述为以满清皇室为最高君主的多主制帝国。参见[美]何伟亚著、邓常春译:《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⑧参见张荫棠:《致外部电陈治藏刍议》,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28页。
⑨张荫棠:《奏复西藏情形并善后事宜折》,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98页。
⑩张荫棠:《致外部电请代奏办事艰难情形吁恳收回政权》,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17页。
(11)参见张荫棠:《致外部电请迅速整顿藏政收回政权》,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04页。
(12)英国政府管理印度,女王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内阁设印度事务大臣,负责管理印度事务,由一个15人组成的印度会议协助,总督(后来有副王头衔)由女王任命,受印度事务大臣指导,总督之下有分工明确的参事会。地方仍由土王治理。参见林承节主编:《殖民主义史——南亚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177页:[印度]恩·克·辛哈、阿·克·班纳吉著,张若达、冯金辛等译:《印度通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992-993、1018-1019页。
(13)张荫棠:《复奏西藏情形并善后事宜折》,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98页。应该注意到张荫棠屡次提到应该由“贵胄”、“亲贵”总制全藏的提议,这是清末政治中特有的现象,因为在“排满革命”呼声日渐高涨的时候,作为汉族官员如何对待满族亲贵成为判断政治态度的标志。张之洞在“变法三折”中关于派员游历列国时就曾言,派“庶僚不如亲贵之更有宜……亲贵归国,所任皆重要之职事,所识皆在朝之达官,故其传述启发,尤为得力”(朱寿朋编纂:《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4754页),也是旨在表达对亲贵的尊崇态度。根据英国内阁设有印度事务大臣的模式,张荫棠认为行部大臣不一定亲赴西藏上任,可以“遥领”,这又为免除皇亲国戚们的劳顿辛苦留下退路。
(14)张荫棠认定“整顿西藏非收政权不可,欲收政权非用兵不可”(张荫棠:《致外部丞参函详陈英谋藏阴谋及治藏政策》,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06页),然而,“驻藏汉兵除护粮台官兵外,只有六百二十一名”,兵威不壮,因此“兴革各事既有多方掣肘之虑,尤有变生意外之险”。(张荫棠:《致外部丞参函详陈英谋藏阴谋及治藏政策》,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06页。)故对他而言,所有革新举措不能不考虑这种现实条件。
(15)以上均见张荫棠:《复奏西藏情形并善后事宜折》,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98页。
(16)张荫棠:《咨外部为西藏议设交涉等九局并附办事草章》,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44页。
(17)张荫棠和驻藏大臣联豫在“九局”初设时皆任命藏官为负责人(参见见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通史——松石宝串》,第969-970页),张荫棠解释了其中的原因,“藏中汉官无可派之人,派而不得人,不如不派之为愈”,并指出“将来俟有廉能之员,每局再派汉提调及教习等”。参见张荫棠:《致外部丞参函述筹藏详情及参劾番官原委》,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58页。
(18)张荫棠:《与吉治纳问答节略》,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66页。
(19)让达赖喇嘛、班禅进京陛见“则万国观瞻所系,主国名义愈见巩固”。参见张荫棠:《致军机处外务部请代奏达赖班禅应令其陛见》,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30页。
(20)张荫棠:《致外部丞参函详陈英谋藏阴谋及治藏政策》,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06页。
(21)张荫棠:《复奏西藏情形并善后事宜折》,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97页。
(22)张荫棠:《复奏西藏情形并善后事宜折》,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96页。
(23)张荫棠:《复奏西藏情形并善后事宜折》,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99页。
(24)张荫棠:《传谕藏众善后问题二十四条》,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34页。
(25)[美]米勒等主编、邓正来等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7页。
(26)参见王希恩:《论“民族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7)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1-342页。
(28)康有为:《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611-612页。
(29)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第2册,第76页。
(30)张荫棠:《致军机处外务部电请代奏辩未强令喇嘛改装》,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28页。
(31)张荫棠:《训俗浅言》,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53页。
(32)张荫棠:《藏俗改良》,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57页。
(33)张荫棠:《谕全藏僧俗官民筹办要政亟图自强》,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73页。
(34)参见张荫棠:《游布达拉山记》,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74页。
(35)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202-203页。
(36)朱寿朋编纂:《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709页。
(37)张荫棠:《训俗浅言》,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53页。
(38)参见张荫棠:《藏俗改良》,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56页。
(39)以上均见张荫棠:《藏俗改良》,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58页。
(40)张荫棠:《传谕藏众善后问题二十四条》,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第1334页。
(41)张荫棠:《传谕藏众善后问题二十四条》,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第1337页。
(42)参见[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48页。
(43)参见《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奏在日本考察大概情形暨赴英日期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页。
(44)张荫棠:《复奏西藏情形并善后事宜折》,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97页。
(45)张荫棠:《传谕藏众善后问题二十四条》,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36页。
(46)参见刘大明:《“民族再生”的期望: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民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页。事实上,清朝末年的语言统一努力不仅包括少数民族学习汉语,也包括各汉语方言向“官音”的统一。“各学堂皆学官音。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实由小学堂教字母拼音始……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应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210页。
(47)张荫棠:《上外部条议筹办藏政经费说帖》,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449页。
(48)[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55页。
(49)张荫棠:《奏复西藏情形并善后事宜折》,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98页。
(50)何藻翔:《藏语》,上海广智出版社1910年版,第119页。
(51)《分省补用道程淯条陈开民智兴实业裕财政等项呈》,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52)张荫棠:《谕全藏僧俗官民筹办要政亟图自强》,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73页。
(53)与张荫棠同时代的杨度从另一个角度论证、支持这种观点。杨度把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概括为三个不断进化的阶段,认为蒙、回、藏等民族尚在游牧社会,其“语言、文字中所包含之美富不及汉人万一”,“汉人尚恨不及英、美、德、法之人,满人尚恨不能丝毫尽等于汉人,而蒙回藏人乃更远不及满汉两族”。杨度:《金铁主义说》,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367页。
(54)张荫棠:《复奏西藏情形并善后事宜折》,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95页。
(55)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9页。
(56)(61)张荫棠:《传谕藏众善后问题二十四条》,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35页。
(57)张荫棠:《致班禅函论拉章商上不宜各分畛域》,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72页。
(58)(62)张荫棠:《传谕藏众善后问题二十四条》,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36页。
(59)参见张荫棠:《译行商上暨札噶厦劝令速办九局事宜》,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71页。
(60)张荫棠:《训俗浅言》,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55页。
(63)张荫棠:《藏俗改良》,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下册),第1357页。
(64)参见郭卫平:《张荫棠治藏政策失败原因初探》,《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赵云田:《清末西藏新政述略》,《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
(65)梁启超:《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0-51页。
(66)梁启超曾言:“人权者,出于天赋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服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见《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19页。
(67)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1903年第2期),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490页。
(68)[美]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