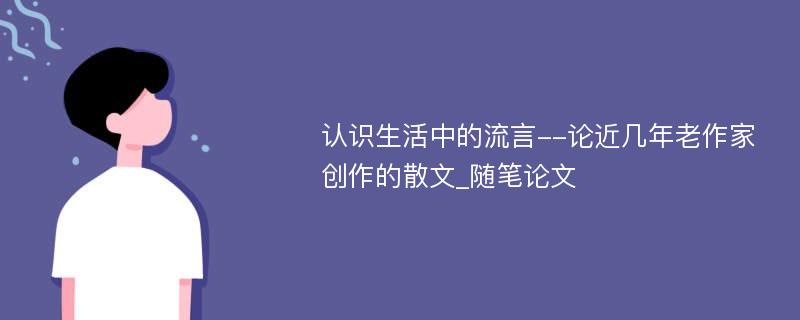
了悟人生 任心闲话——论近年来老作家创作的随笔小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闲话论文,小品论文,随笔论文,作家论文,人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一批饱经沧桑、学贯中西的老学者、老作家创作了不少的随笔小品。这些老先生在借鉴西方现代随笔的任心闲话和批评功能时,也特别注重承传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小品的艺术特长。影响比较大的,如张中行的《负喧琐话》、《顺生论》、《留梦集》、《张中行小品》,金克木的《燕口拾泥》、《蜗角古今谈》、《金克木小品》,汪曾祺的《蒲桥集》、《榆树村杂记》、《塔上随笔》,季羡林的《人生絮语》、《季羡林小品》。萧乾的《我的年轮》、《关于死的反思》,另外象柯灵、周汝昌、吴冠中等也时有佳作见诸报端,颇能引起读者的注意。
这是一支阵容较为整齐、不容忽视的随笔创作队伍,他们有力地推动了当前正在掀起的随笔创作热潮。由于这类随笔小品,与当今中青年作家创作的随笔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值得我们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
这些老先生,生活在一个文化层次较高的文化圈里,有的长期在高校任教或出版部门、研究单位工作。他们饱览诗书,才学过人,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儒家思想的安贫乐道、自强不息的精神,佛道的随心任性、超尘脱俗的思想,都在这些老知识分子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因而,从本质上看,他们的知识结构、个性气质、审美趣味都与传统的士大夫更为接近。
首先,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士人阶层文化思想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以重“道”、守“道”为核心。积极入世是外向性的一面,它着重于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讲究精神修养,则是强调人内在心灵世界的纯洁和立身处世品行的端正。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将道德的自我完善作为积极入世倾向的前提和基础。张中行先生于1993年出版的《顺生论》这本学术小品集,便是体现作家“修身以立道”的见证。张老运用厚实的人生经验和丰赡的人文知识,把人生的方方面面梳为六十个问题,诸如生命、天道、读书、恋情、婚姻、家庭等等,条分缕析,追源溯流,把高深的学理化为平实的知识,令后生动容,深受教育。老作家汪曾祺在《祈难老》中引用了孔夫子说:“及其老也,戒之在得”,颇为感慨,他认为:“要想难老,首先旷达一点,不要太把老当一回事。”萧乾先生《关于死的反思》,畅谈“死亡”观,历数自己亲眼、亲历的感受,指出:“‘人只有一辈子好活’。认识了死,才能活得更清醒,劲头更足,更有目标。”这些知人论世的话都表现出他们能自主自律、安贫乐道、积极向上的儒家精神。
同时,他们还常常以入世的精神来关注日常现实世间的生活,即儒家所谓的“道在伦常日用之中”,汪曾祺先生业余爱好有三样: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他说:“到一个新地方我不爱逛百货商场,却爱逛菜市,菜市更有生活气息一些。”(《自得其乐》)正由于他富有济世之心,热爱人生,依恋尘世,因而他在《我是一个中国人》中这样说:
我认为陶渊明是一个真正的儒家。“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我很熟悉这样充满人的气息的“人境”,我觉得很亲切。
又如张中行先生在谈到人进入老境后,有时闷坐斗室,特别感到寂寞时,很希望有人来破除沉闷,拜访叩门,化枯寂为温暖。他把这叩门声拟喻一个很有诗意的说法,叫做“剥啄声”:
期望的是人,但比人先行的是剥啄声。试想,正在苦于不知道究竟来还是不来的时候,忽然听到门外有剥啄声,轻而又轻,简真像是用手指弹,心情该是如何呢?这境界是诗,是梦,借用杜工部的成句,也许正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吧?(《剥啄声》)这反映了作家对人生的积极追求,达观乐生,随缘玩味,善于把生活的体验升华为审美的愉悦。因而,这是一种对现实世间生活的肯定和满足。
如果说儒家精神让人积极入世,强调精神修养,格外看重尘世的生活,那么佛道思想却能引导人去追求随心任性、清净恬淡,自然适意的生活境界。入世与出世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是相辅相成、和谐统一的。季羡林先生是一位长期从事佛教史研究的专家,最近推出一本《人生絮语》随笔集,书内收入不少谈佛论禅的文章,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相当精辟的剖析。张中行先生在三十年代曾涉猎过佛法,亲近过佛堂,编过佛学期刊,近年又出版了《禅外说禅》一书。金克木先生在《蜗角古今谈》中有一篇《再阅〈楞伽〉》,从中可以看出金老佛学功底非常人所能比肩。
这些丰厚的学识和修养,使老先生热爱生活却不执着于功名利禄,淡泊超脱却没有消极避世,返朴归真却不忘人间的是非美丑。季羡林的《二月兰》,他把一腔情愫倾诉在燕园内生长的二月兰上,恣意渲染,尽情泼墨,看那“宅旁、篱下、林中、山头、土坡、湖边,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间以白雾,小花开得淋漓尽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二月兰这种“十分平凡的野花”竟在季老的“生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季老几十年来生活变迁的见证者,成为季老悲欢情感的依托对象,尤其是当那些朝夕相处、甘苦与共的亲人先后离去,所造成的情感空白,二月兰便成为季老维系过去,寻觅温暖,记述温情的“有情物”。张中行先生近年来的随笔创作,常常涉及到“梦”字,他说:
我的所谓梦不然,是想望(或竟是幻想),是希冀,是爱慕,有时也许朦胧,但并不无力;于是之后是或移近,成为梦的现实,带来惊异甚至欢娱,但更多的是远离,成为现实的梦,带来怅惘和愁苦。这样的梦是未入睡时有的,是情之所钟,在生涯中占重要位置的,我视之为梦,或称为白日梦。(《留梦集·自序》)这表明作家看重笔底情趣,精神愉悦,它与中国传统文人追求修身怡性,玩味个中情趣的生活方式极为近似。张老的随笔小品大致两类,一类是写知见,一类是写情怀。尤其是后一类,多写“白日梦”,总是有所偏爱,“单说写时候的心境,是含着眼泪写永远放不下的深情”。(《留梦集·自序》)他在《归》一文中,谈及读丁宁《还轩词》那份感觉很特别,也很耐人咀嚼:
这词境可以说是苦吗?又不尽然,因为其中还有宁静,有超脱,以及由深入吟味人生而来的执着、深沉和美。又如:
读词集,相看泪眼,如面对其人,就说是有限时间吧,生命就真是得了所归。人生有多种愁苦,心的无所归是渺茫的,惟其渺茫就更难排遣,所以得所归就特别值得珍重。在词境里,寄托片刻的漂泊心境,感受一番温情和美的精神世界,这对一个长期跋涉在人生旅途的人来说,这种“得所归”确实愈显得珍贵而难得。难怪张老年逾八旬,却依然孜孜不倦地“含着眼泪写永远放不下的深情”的文章
随着岁月的增长,阅历的丰富,这些老先生在他们创作随笔小品中常常表现出思乡怀旧的情结。这固然有狐死首丘、叶落归根的恋家意识,更有他们对往事的追怀,对重建精神家园的关注和探索。在他们笔下,故土风俗,家乡小吃、犊车驴背,童年往事,亲情母爱,故旧情谊等等,无不写得温情醇厚,让人神往。汪老的随笔小品,就有不少是谈故园风物旧时情:家乡似乎“并不热闹”却别具一格的元宵灯节(《故乡的元宵》),让人陶醉、撩人情思的故乡野菜(《故乡的野菜》),各种各样风味独特的小吃(《故乡的食物》),四时八节,富有地方色彩的风俗礼制(《城隍、土地、灶王爷》、《岁交春》),乡下郎中治病的神奇技艺(《对口》)等等。读他们这些随笔小品,让人如入花阵,乐不知返。当然,有时这些老先生对“乡情”的执着追寻和陶醉,甚至会表现出一种相当有趣的蛮式审美心理和思维方式:
说起狐死首丘,也是一言难尽。我们家乡离北京不远,可是语音有小别。小别有难于说清楚的,是韵味。极少数有显著分别,如“看不出来”,普通话或京腔,“来”读阳平,我们家乡读阴平。普通话不用这个音,所以撇京腔的人听了会觉得怯;我则仍坚守月是故乡明的原则,不只不觉得怯,反而感到亲切。总之,回到家乡,白天逛集市,杂人入目,杂话入耳,都觉得好;入夜,不只月明,连蟋蟀叫声也显得特别清灵。(张中行《吃家乡饭》)
这是典型的“月是故乡明”的心理情结,出现这种价值天平的偏差,是源于作家对“乡情”的迷恋和自信,是一种强烈的感情归属感的表现。鲁迅先生早在二十年代就曾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思乡的蛊惑”,并且说它会“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1]
诚然,怀旧心理在老一代知识分子身上具有普遍的现象,它突出地传达诸多学者、文化哲人的极大忧思。这是对经济起飞和都市扩展后社会和人心受到物质严重侵蚀的触景生情,是对日渐衰微的昔日田园的怀恋和昔日价值观念以及自然生态和人际关系的肯定。张老感慨地说:“生活由乡而城,由四合院而高层楼,总是离田野越来越远了。入门上高楼,出门上公路,脚不再踏草,耳边也就断了蟋蟀声。这就是走向文明吗?”(《蟋蟀》)象这种眷恋传统文化,抨击现存价值观念,表明了作家笔下的乡土,是一种心理上的乡土,是作家借以表达对于一种文化价值的追怀与呼唤。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萧乾先生急切呼吁人们“但愿北京能少拆几条,多留几条胡同。”的焦虑痛惜的心情(《老北京的小胡同》),也不难理解汪曾祺先生观光香港后,而写下的《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树》、《香港的鸟》里所表达的那份对城市异化的忧心。
总之,张中行、汪曾祺、萧乾、季羡林等老先生历尽沧桑,饱经忧患,进入老境后,了悟人生,明心见性。他们的随笔小品自叙经历、纪行述感、谈论人生、映现世态,字里行间流露着清淡的人生感兴和知性色彩,表现出一种随缘玩味、率性自然的古典风范。不过,他们毕竟身处20世纪中国东西文化碰撞、交汇之际,因而,他们师承传统,但却没有作茧自缚、固步自封,而是积极运用现代理性批判精神,来参与重建现代人的“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对当代社会世道人心的反思和批判,有它的深广和尖锐性,显现当代随笔小品的生气和力度。
二
西方的Essay,现通译为随笔,以前中国现代作家也有把它译作论文、美文、小品文、絮语散文等。周作人早在1921年写的《美文》就这一文体作过介绍:“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2]关于这一文体的特点,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在《出了象牙之塔》曾作过了精辟的阐述,而后经鲁迅之手的翻译,已成为我国现代作家和读者耳熟能详的经典性定评: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致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既有humor(滑稽),也有Pathos(感愤)。[3]
可以看出,Essay这类文体具有亲切、平易、有趣的审美特点,所谓“兴之所至”、“任心闲话”便是它的最好诠释。
而中国的小品文历史久远。小品一名,始于六朝翻译的佛经。《世说新语·文学》有一句,“殷中军读小品”,刘孝标注:“释氏辨空、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到了晚明,公安、竟陵派对前后七子揭起反叛旗帜,主张创作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因而,他们所写的题材就由庙堂移到村野,写法行云流水,无拘无束,甚或杂以嘻笑怒骂。有的文人便从和尚那里借个名堂,称自己的这类作品为小品,如王思任的《文饭小品》,陈继儒的《晚香堂小品》等。因此,到了五四时代,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对这些晚明小品大为激赏,顶礼膜拜。周作人说:“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人的情趣几乎一致。”[4]
正因为西方的Essay和中国古代的小品文有一定的相通之处,所以,随笔这一文体才会备受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推崇和重视。朱自清就曾这样说:“选材与表现,比较可随便些;所谓‘闲话’,在一种意义里,便是它的很好的诠释。”[5]窃以为此话很可以移来解释当代老学者、老作家在随笔园地笔耕不辍的缘由吧。在当今文坛,随笔,正以它是最便当的抒情写意的文学样式,而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与价值。
当下老学者、老作家创作的随笔小品,都是一些乘兴而作,随感而发的文章,读来既亲切实在,又引人入胜。金克木先生在《燕口拾泥》中,涉猎东西,独抒己见,把自己平常的读书心得和盘托出,单看每节小论题,就五花八门,独标一帜。诸如“诗与真”、‘解构’六奇”、“说‘边’”、“内和外”、“二圣”、“妇女群像”、“译路坎坷”、“语言禁忌”、“诗的倒读”、“书的反读”等等。这些抒写自我感兴,探究人生哲理,体察风习世态,都带有浓厚的学术气味,但金老并不在那里正襟危坐地谈玄论道,而是没有系统,没有方法,没有拘束,偶有感触,随时记录,意到笔随,意完笔止。如《说“边”》开头这样说:“现在的人喜欢讲中心,不大讲边,其实边上大有文章可作。没有边,何来中心?中心是从边上量出来的。”此话要言不烦,讲的虽然是生活中常理,但却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又如,张中行先生在《案头清供》里从容闲话,他案头上有三样清供:老玉米、看瓜、葫芦。作家心有余闲,把这三样东西的来历一五一十地娓娓道来,表现他玩味人生境遇,表达悠游自在的意趣。他说:
我是常人,因而也就如其他常人一样,有想望,也有寂寞。怎么处理呢?其中一种可行的是如清代词人项莲生所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其实,这意思还可以说得积极一些,即如我这些案头清供,有时面对它,映入目中,我就会想到乡里,想到秋天,而也常常,我的思路和情丝就会忽然一跳,无理由地感到,我们的周围确是不少温暖,所以人生终归是值得珍重的。
可见,这类随笔小品,只要作家心有所感,便可信笔挥洒,不拘形迹。柯灵先生说:“文苑之有随笔,恰如人生之有闲话”,“闲话可以抒发性灵,交流心得,活跃思路调节神经,是理想的精神度假村。”[6]因此,亲切闲适,富有个人情趣和娓语笔调便就是这类随笔小品的审美特质之一。
而平淡冲和乃是老学者、老作家创作随笔小品的另一种审美特质。中国艺术向来把平淡冲和视为最高的审美境界之一,明代陈继儒认为:“渐老渐熟,乃造平淡”,[7]这是很有道理的。那种激越飞扬的想象能力,炽烈浓郁的浪漫个性,绚烂华丽的抒情乐章不再为老者所倚重。春华消褪,秋思老成,他们的文章摆脱了载道明理、匡时济世的重负,由着自己的性情写一点轻松洒脱的文字。这类文字来之不易,它是对丰富的最大限度的浓缩,是对深刻的最真实的反映。张中行先生的《桥》这样写道
桥来于水之阻而人不愿受阻。不愿,有偏于物的,如两个小村庄,距离不远,人难免有来往,物需要通有无,可是中间有条河,河上就最好有个桥,不愿还有偏于心的,《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在水的那边,可望而不可即,如果有桥,不就好了吗?
张老写“桥”,仿佛信手拈来,是智谈“物”之桥,更是善解“心”之桥,人情练达,笔法清淡,在淡泊中寄至味,使文章顿生情趣,给人艺术美的享受。
当然,平淡冲和不仅需要作家疏旷豁达的心境,更在于长期的知识储备。平淡并非淡而无味,淡而无物,而是要写得耐读有趣,体现这类随笔的文化品位和理趣美。鲁迅先生颇为欣赏外国作家著述的一些学术文艺的作品,认为它们“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8]我国当代这些老先生的随笔小品,举凡天文地理,民情风俗,饮食男女,生老病死,街谈巷议,人生世相,均可入文,真是做到吸养文化,畅论人生,而又不乏隽永幽默的韵味。季羡林论老年,谈养生,随缘自在,妙语解颐。汪曾祺先生像洞悉人生三昧的智者,善于从琐碎平淡的生活中揭示人生。如谈疟疾,说牙疼,祈难老,品风俗,逛菜市等等,均能信手拈来,别有会心,涉笔成趣。《牙疼》一文,他对一位牙科医生颇有好感,原因不在于他的“手艺”如何,而是候诊室放有一本A·纪德的《地粮》。“牙科医生而读纪德,此人不俗!”让人读来,不觉扑哧一笑,回味无穷。
不过,当这些老先生以戏谑笔墨来展示知识分子艰辛窘迫的生活境遇时,他们的笔端常常会流露出一种含泪的微笑,诸如金克木的《叹逝》、萧乾的《外调奇遇》、汪曾祺的《随遇而安》,都是属这一类的文字。汪老说:“我不是1957年打成右派,是1958年‘补课’补上的,因为本系统指标不够。划右派还要有‘指标’,这也有点奇怪。这指标不知是一个什么人所规定的。”平淡的话语道出人生最不幸的一页,让你感到个中含有一种笑不出的苦味。尤其是“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由此,汪老能深深体会出金圣叹临刑前给儿子的信中说:“字谕大儿知悉,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滋味”,这种沉痛的人生苍凉感。同样,张中行在《书》一文,也讲述他在文革中不能读书的苦痛,不得已,只好乞援心里的书,背诵起玄奘译的《心经》,并“赖菩萨保佑,进步人物就竟至没有发现,因而也就未定性,免于批斗”。这也是用戏谑笔墨,抒写“辛酸泪”。它比起那些义愤填膺的声讨或痛哭流涕的诉说,来得更有份量,更能发人深省。
综观所述,这些老先生到了晚景,历尽沧桑,了悟人生,学识丰厚,庄谐杂出,真正达到信手拈来,迂想妙得,随心所欲,自成法度的艺术境界,他们创作这类富有文化韵味的随笔小品,对于拓宽随笔的表现天地,提高随笔的艺术品位,都将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注释:
[1]鲁迅:《朝花夕拾·小引》。
[2]周作人:《美文》,《晨报副刊》1921年6月8日。
[3]厨川白村:《出了象牙塔》,鲁迅译,见《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4]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5]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文学周报》第345期。
[6]柯灵:《随笔与闲话》。
[7]陈继儒:《容台别集》卷之一。
[8]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