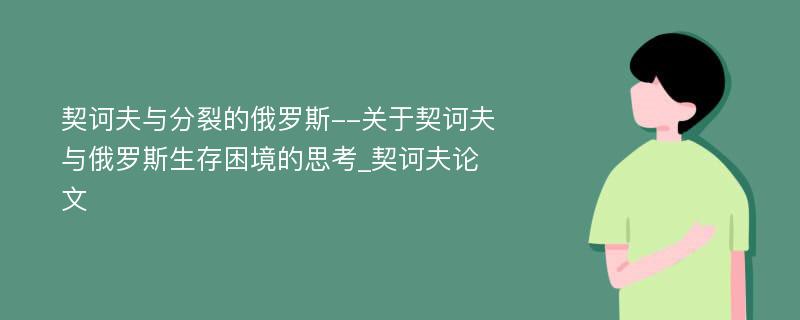
契诃夫与分裂的俄罗斯——关于契诃夫与俄罗斯生存困境的思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契诃夫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契诃夫——存在于俄罗斯的空间却又超越了俄罗斯的时代
众所周知,在俄罗斯文学批评界和文艺界,并且不论是苏联之前还是苏联时期,安东·巴夫罗维奇·契诃夫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天才小说家(这一点早就无人置疑),但是,与其说他是对社会思想有巨大影响的人物,不如说他是洞察人类心理的专家和风俗派作家。当然,这看来还是比较温和的说法。著名的苏联文学活动家К.И.丘科夫斯基,在一篇极具深度,但我认为思想并不完整的个人随笔《关于契诃夫》中写道:“如果我想要援引那些把契诃夫描绘成‘软弱的’、‘消极的’、‘没有个性的’、‘萎靡不振的’文章和小册子,恐怕得有好几百页。整个80和90年代(19世纪——作者)的批评界都是在炮轰他这一点。甚至在1929年(即布尔什维克体制时期——作者)出版的《契诃夫全集》中也作为前言附上了长篇大论,并且还明确地说,契诃夫不论是在生活还是在创作中都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消极、敏感’的人,‘忧郁和天生软弱’的人。”[1]
在丘科夫斯基的著名随笔中最长最好的部分内容恰恰有力证明了,一位伟大的俄罗斯小说家不是“天生消极、敏感”的。对此我们回头再说。
完全可以理解,对于俄罗斯特别是苏联第一个十年时期的政治领袖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思想家们来说,对俄罗斯的个人的日常生活有着细腻且广泛兴趣的契诃夫,当然只是一个“窝囊废”,尽管他被世人所承认,而且还幸运地没来得及活到“世界大战”的开始。但是不能忘记的是,俄罗斯不仅是激进的,当病危的契诃夫完成《萨哈林之旅》(已被列入文选),当作家面临病痛的折磨和精神的忧患之时,19-20世纪之交的自由的俄罗斯出版界,仍然认定,契诃夫是一个“无原则的,无思想的,对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利益和需求抱以冷漠态度的作家”。[2]
安东·巴夫罗维奇,他的个人生活与创作显然没有完全融入到19-20世纪的俄罗斯奔腾着的巨大但却是悲剧式的激情中去,这种激情不仅是带有社会-政治特质抑或是带有哲学-宗教色彩的,而且也包括文学方面的。事后不能不承认,所有这些激情最终都将俄罗斯引向了民族的灾难,而且它迄今仍以隐蔽方式存在着,不幸的是,越来越多迹象表明,在某一时刻,它将重新变得开放……
契诃夫甚至没有活着看到1904-1905年革命的街垒。他没有看到,灾难是如何开场的。与其他作家同行不同的是,他似乎甚至都没有参加过备战……譬如,Л.H.托尔斯泰或者是A.M.高尔基都从各方面并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参加了这个在当时看来是伟大、迷人且美好的事业……
契诃夫因自己的文学创作特点及短暂的生命存在而只能俯视“激战”。多数人甚至认为他是“超脱于激战之外”……偶尔,翻阅契诃夫的创作,我心中会升起一种感觉,契诃夫在俄罗斯文学,在俄罗斯文化空间中的地位是真正超越时空的。他比伟大的托尔斯泰——永远是一位无可争议的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家,要更加超越时空。
同时,契诃夫是一位对于同时代人及后来的读者来说最令人费解的俄罗斯作家之一,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因此,对于其创作的严肃研究,似乎,每一个著名的文学研究者都不可避免地走入了语言学、个人传记以及作家心理学肖像的研究视域。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契诃夫及其在19-20世纪俄罗斯民族灾难中的创作遗产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换言之,契诃夫令人费解的本质及其关于文学和历史现象的遗产的特性是什么?
我认为,对契诃夫在1917年以前是“性格软弱的风俗画作家”这一评价,以及苏联时期官方对其所持的宽容、忍耐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作家的确从未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标榜过自己在俄罗斯革命前的话语中的思想政治倾向。准确地说,他没有按照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的社会论调的规则来标榜它们。而这场由国内社会-文化的分裂所引发的实质上是一个巨大的思想纷争的论调的规则,要求思想精确、评价极端和绝不妥协以致达到幼稚的荒谬程度。契诃夫,与大多数以自己方式创作然而仍然伟大的作家同行不同的是,他没有按照规则出牌,因而成为了令人费解甚至令很多同时代人和后来人感到陌生,包括那些真诚地赞扬过他的文学才能的人。我认为,这正是契诃夫令人费解的历史之谜以及他创作中超越时空的本质所在。
然而,在民族灾难之际的俄罗斯历史中的契诃夫之“谜”是更为深奥的。毋庸置疑:契诃夫看见和理解了正发生在他周围的一切。问题在于,他是怎么看和理解的,他预见和预感到了什么?
分裂的俄罗斯磨盘
关于1917年俄罗斯民族灾难的起因,著名的俄罗斯历史-宗教思想家H.A.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共产主义的起源与思想》一书中首次试图从社会-文化分裂的角度进行了思想上的探索,该书于1937年出版,当然,是在苏联境外并且是英文版的。别尔嘉耶夫利用宗教范畴的事物进行思维,并在以《俄罗斯的宗教思想和俄罗斯国家》为题的前言部分对于俄罗斯的分裂予以了经典描述。同时,其中所表述的基本思想,可以具有完全非宗教性的阐释。作者写道:“俄罗斯人民在自己的精神结构上属于东方人。俄罗斯——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东方,在两百年间遭受着西方的巨大影响并在自己的文化表层同化着所有的西方思想。俄罗斯人民的历史命运是悲惨的,并且在经过了文明类型的中断与变更之后以灾难性的速度发展着。在俄罗斯历史中,不参考斯拉夫主义者们的意见,就找不到有机的团结。俄罗斯人民不得不占据过于辽阔的地域,因为来自东方的危险过于巨大,必须要防御鞑靼人的侵犯,此防御同时也保护了西方,可来自西方的危险同样巨大。在历史中我们看到了五个不同的俄罗斯:基辅的俄罗斯,鞑靼人统治时期的俄罗斯,莫斯科的俄罗斯,彼得时期的俄罗斯,帝国时代的俄罗斯,最后是新的苏联时期的俄罗斯。”[3]我以个人名义补充一点,如今我们看到了下一个俄罗斯的国家产物——一个“苏联之后”的俄罗斯,对它的分析,当然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接下来H.A.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人身上总是有两种因素在碰撞——信奉原始、天然的多神教、来自俄罗斯辽阔大地的自发性与来自拜占庭东正教的向往彼岸世界的禁欲主义的结合。在俄罗斯人面前总是有一个艰难的任务——开拓自己广袤无垠的大地。俄罗斯土地的辽阔与无疆体现在了俄罗斯人灵魂的建构里。俄罗斯人灵魂的画面与俄罗斯大地的画面相契合,那是一幅无边无际、一心向往着永无止境的画面……可以说,俄罗斯人是自己辽阔土地和天然自发性的牺牲品……俄罗斯人由于宗教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不是正统派就是异教徒、分裂分子,他们是启示录的恪守者和虚无主义者。而且,某种正统派的宗教信仰总是居于重要地位,总是决定着俄罗斯人的特征。”[4]
清楚地记得,大约20年前,当我刚成为莫斯科大学二年级学生时,我第一次通读了别尔嘉耶夫的这些话并立即成了他俄罗斯历史观念的热烈崇拜者。需要强调的是,别尔嘉耶夫思想的宗教部分我从未认同过。只是,在苏联存在的最后时期我目睹了所发生的一切,从我对它在文化-历史甚至是日常生活层面的理解而言,我觉得别尔嘉耶夫所描述的分裂的俄罗斯形象是理想化的。
当然,如今我对别尔嘉耶夫思想并不是完全赞同的。我想,东西方之间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冲突在俄罗斯根本不是像B.O.克柳切夫斯基和之后的H.A.别尔嘉耶夫所认为的那样从彼得大帝改革时期开始的,而是起源于莫斯科公国的建立,因为它既是“基辅的欧洲部分”也是“金帐汗国的东方部分”的继承者。
引发争议的是,别尔嘉耶夫认为,彼得大帝改革之后在俄罗斯的“文化表层同化了所有的西方思想”。20世纪的民族悲剧表明,俄罗斯这些所谓的“文化的精华”①吸取西方思想和精髓的过程具有极端矛盾性和不平衡性,以致于使自己的“精华”也同样地落入一种模糊和零碎状态。
我认为,别尔嘉耶夫关于“俄罗斯人宗教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以及“某种正统派的宗教信仰”决定了“俄罗斯人的特征”的说法是饱受争议的。不得不解释的事实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对于俄罗斯宗教生活中所有基本的精神建构的极大破坏并未遭到大多数或者说几乎是所有受过洗礼的居民的群体抗议,而是遇到了消极冷漠的态度。别尔嘉耶夫后来写道,俄罗斯人接受的只是宗教仪式,内在的精神上的精髓只被个别人奉为法宝。如果是这样,那么消极的宗教教条主义,冷漠,恐惧,极端个人主义和心灵的苦修——这一切在“俄罗斯人的灵魂”中都可以找到。并且,审视这一切,在如此错综复杂的特征当中,关于某种或多或少操控全局的决定性因素就不必谈了……
别尔嘉耶夫思想中一系列历史观点的争议性及其并未被所有读者所认同的宗教观不能抹杀一个事实,即他针对在俄罗斯社会和国家中所发生的深层的社会-文化分裂所持的思想观念在方法论上,对于俄罗斯历史命运(而且绝不仅限于19-20世纪)的阐释是精辟的。
著名的当代俄罗斯研究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亚历山大·阿希耶泽尔指出,“应该首先在造成分裂的条件、形式和结果中去探寻俄罗斯历史的特点,有可能的话,还应在克服了这些先决条件之后从分裂的发展和实现中寻找”[5]。他认为,在俄罗斯整个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分裂具体表现为“特殊的、互相冲突的社会-文化团体的确立”[6],他们彼此间围绕着所有社会问题所展开的影响很难具有积极性意义。我个人补充一点,这些团体从其内在结构上看本身就是没有固定形式的,因此不仅在团体之间,而且在其内部的互相影响也难以获得积极意义。
关于形成这种分裂的条件及其在漫长的俄罗斯历史行程中的再现之原因,亚历山大·阿希耶泽尔认为是“由于现实的复杂性而导致民众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造成的”[6]。简言之,俄罗斯的社会和国家体制,除了驾驭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外,要么总是灾难性地滞后,要么基本没有能力解决综合性现代化的诸多问题。当然这里不是要详尽分析这种历史倒退的原因。我只是想指出,俄罗斯辽阔的地域和历来政权的高度集中制完全可视作其中的原因之一。
19-20世纪之交是俄罗斯分裂达到顶峰阶段的时期。我自觉无法分析,倘若不援引几行别尔嘉耶夫格言式但实质上准确的语句。他说,“没有一个国家不同时生活在各个世纪。俄罗斯的阶级团体总是软弱并附属于国家的,他们甚至是由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只有吸收了西方专制制度的君主制和人民才是强有力的,他们令文化阶层饱受压力。俄罗斯贵族阶级中最好的文化团体感到了自己的地位是不正常和不符实际的……帝国在精神和社会方面都是不健康的”[7]。
契诃夫与俄罗斯的分裂
安东·契诃夫,如上所说,没有按照时代的论调规则表达自己的思想立场,因而不为大多数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所理解。但是他完全看见并感觉到了俄罗斯的分裂。正如作家所指出的:“俄罗斯人只关心一点边缘上的东西,对中间部分却不感兴趣,一般来说这部分什么也不是,或者说意义很小”[8]。尽管如此,契诃夫本人还是以自己的生活和创作将这场分裂完全表现了出来。他完全不违背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精神。让我们回忆一下他文选中的一句名言便足以证明这一点:“在人的身上一切都应是美好的……”。在一次与A.M.高尔基的谈话中作家直截了当地说道:“如果每个人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做了他可以做到的一切,那么我们的家园该是多么美好啊!”[9]
在契诃夫的手稿中,大概,只有一处地方与其说是表达了自己的社会和人类学观点,不如说是思想政治立场:“我不是自由主义者,不是保守主义者,不是渐进论者,不是僧人,不是冷淡主义者……我憎恨所有这些人的谎言和暴政,并且宗教管理所的秘书们和我也是对立的,如同诺托维奇与格拉多夫斯基的对立。伪善、愚笨、专横不只是笼罩着商人的住所和牢房;我在科学领域、文学书籍及青年人身上也看到了它们的影子。我认为最神圣的东西是——人类的身体、健康、才智、天分、灵感、爱和完全脱离于权力和谎言的自由”[10]。
在这里我们能说什么呢?或许,首先应该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理智的、精神的、个人的同时又是社会-政治的悲剧。一场纯粹的俄罗斯的悲剧。摆在我们面前的实质上是一个绝境。一方面,契诃夫有意且明显将自己的观点非政治化并且又摒弃了其中的任何一种思想成分,以此将自己从革命前的思想暴动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作家将抽象的“人类的身体、健康、才智、天分、灵感、爱和完全的自由”神圣化的同时,也将自己排除在了社会的大门之外。我想,不只是俄罗斯社会的大门。总能找到这样的人,他们认为,契诃夫作为一个天才诠释了自己的时代。他如果活在“后现代主义”时代……可能会……对我个人而言契诃夫的名言首先便证明了他的个性是富有战斗精神的。而且,这种个性完全不是自私的,因为患肺病的作家乘驿车穿越整个西伯利亚前往苦役岛萨哈林的旅行已经排除了即便是少许的自爱和自私。在这里,或许有必要补充契诃夫的另一句名言:“把奴性从自己身上像水一样一滴滴挤出去”……这种在分裂社会中富有战斗精神的个性——理应承认是一种隐忍精神,是不同寻常且强有力的个人精神堡垒,而且它往往可以造就伟大的功勋。然而,它也同时会成为个人生存的绝境。
显然,安东·巴夫罗维奇没有将俄罗斯的美好未来与党派、阶级、社会权势和思想团体,甚至是个别的自由主义者联系在一起,而是将未来与个体的人联系在了一起:“我相信一些人,我看见了分散在全俄罗斯的那些人身上的拯救力量——他们是知识分子或者农民——他们富有力量,虽然很少”。不足为奇的是,A.П.库济切娃在契诃夫诞辰150周年之际出版了关于作家的长篇传记[11],她在卷首题词中便援引了契诃夫的这句话。
对于“后现代主义”在契诃夫时代的俄罗斯能否实现,作家本人很清楚。随着病情日渐加剧,应该说,作家对任何幻想都已经消失殆尽。这也是一个绝境。
毫无疑问,他是一个被世人所承认的文学家,但却是一个不被理解的作家和人。而与此同时,契诃夫渴望在有生之年被人所理解。很多关于作家的传记和回忆录作者以及熟悉他的人都认为,安东·巴夫罗维奇是一个内向的人,但远不是一个因高傲和虚荣而令人敬而远之的人。应该承认,他的这种个人的“令人费解”瞬间引发了近乎病态的反应。И.A.布宁的一段回忆录颇耐人寻味:在一个隆重的宴会上没有客人愿意为“阴郁歌手安东·巴夫罗维奇·契诃夫的到来”而举杯。一向因彬彬有礼而闻名遐迩的作家这次却忍不住不合时宜地离席而去。
不问政治、思想怪异、“后现代式”的人道主义者、富有战斗精神的个性化的人,一生都在凝聚自己优点的作家,安东·巴夫罗维奇·契诃夫没有任何机会在分裂的俄罗斯成为一个被人所理解的人。这又是一种绝境。
我们不应忘记,这不只是契诃夫在俄罗斯的绝境,这首先是俄罗斯自己的绝境。
契诃夫创作中关于俄罗斯的分裂
关于俄罗斯共产主义的起源,别尔嘉耶夫写了一本著作,他在其中的一章叫《19世纪俄罗斯历史和它的预言》中非常公正地指出:“这个世纪的分裂把俄罗斯创作带入一种空前紧张状态。从果戈理开始俄罗斯文学便成了教育式的,它的任务是寻找真理并教人如何实现真理。俄罗斯文学……为人民的悲苦命运和拯救全人类而生”[12]。接着别尔嘉耶夫列举了著名的俄罗斯作家和文学活动家,他们的创作,在他看来,正是俄罗斯文学“空前紧张状态”的体现。这些人有A.普希金,H.果戈理,Φ.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M.莱蒙托夫,Φ.丘特切夫,A.霍米亚科夫,B.别林斯基,B.伊万诺夫,A.别雷,A.布洛克,К.列昂季耶夫,B.索洛维约夫,H.费多罗夫。实在令人称奇,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在这个名单里竟没有天才作家、19世纪伟大的真理寻觅者之一契诃夫。别尔嘉耶夫忽略了契诃夫,很可能正是因为,如前所说,安东·巴夫罗维奇的立场和创作与时代的论调规则格格不入。
但是生活于另一时代、有少许政治化倾向的К.И.丘科夫斯基却在我们提到过的《关于契诃夫》随笔中指出:“……应该注意到契诃夫心理面貌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我想把其形容为:极度真实。他严厉抨击了即使是被普遍接受的、细微的、看上去并不令人气愤的谎言。关于这一点,他的所有作品就是力证”[13]。丘科夫斯基甚至将契诃夫的一篇短篇小说《命名日》称作是“一部坦然加进作者意图的小说,它的全部内容都指向一个唯一的目的:任何情况任何时候都不要对任何人说谎”[14]。在这方面,应该说,小说的确近乎病态。这里暂且不提主人公奥尔加·米哈伊罗芙娜和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夫妇之间极其复杂的、最终以新生儿之死为悲剧收场的个人关系。我只想引用小说中一段俄罗斯人关于政治,或者按照当时的说法,关于“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对话的精彩描述:“……在用餐时她的丈夫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和她的叔叔尼古拉·尼古拉维奇就一场有陪审的审判,出版业和妇女教育问题展开了争论;丈夫的争论,通常不仅是为了在客人面前炫耀自己的保守思想,更是为了顶撞这个他不喜欢的叔叔;而叔叔和他作对并处处话里挑刺则是为了向用餐的人们显示,尽管自己已五十九岁,仍然不乏年轻人的朝气和自由思想。而奥尔加·米哈伊罗芙娜本人在用餐结束时则忍不住开始笨拙地为妇女培训班而辩护,并不是因为这些培训班需要为之辩护,而是因为她想惹恼在她看来不够公正的丈夫。争论令客人们感到疲倦,但所有人都找到了自己想要说的并展开了高谈阔论,尽管不论是有陪审的审判还是妇女教育问题都不关他们的事……”[15]。由于这个小说的缘故,丘科夫斯基引用了契诃夫与文学杂志《北方公报》主编之间通信中的一段话。主编向刚步入文坛的作者契诃夫指出——“小说中看不到任何思想倾向”。契诃夫则反驳道:“难道在小说中我不是从头到尾都在抗议谎言吗?难道这不是思想倾向吗?”[16]
作家的日记中保存着不少有代表性的句子:“如果一边吃饭,一边高谈人民的自觉意识,谈人民的良心和自由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与此同时饭桌旁围绕着身穿燕尾服的奴仆,还有那些同样是奴仆的马车夫还站在严寒中等候派遣——这就意味着在对神圣的心灵撒谎”[17]。在这里我们看不出非政治化的、思想怪异的人道主义者契诃夫与左倾激进分子有何区别。考虑到那个时代俄罗斯社会的普遍状况,不能说,契诃夫与炸弹手之间的距离还很遥远。但不管怎样,信奉托尔斯泰“勿以暴力抗恶”的契诃夫,怀着对托尔斯泰的万分崇敬之情,从未签名加入战斗。大家肯定记得,在中篇小说《无名氏的故事》(1893)中契诃夫以高超的创作水平和令人信服的心理描写将主人公描绘成一个反对君主专制的激进分子的代表,同时对他表达了鲜明的同情之感。而这部小说中的某些语句恰好与契诃夫日记的内容相契合:“他(老爷)坐在饭桌旁,喝着咖啡,翻着报纸,而我(主人公)和女仆波丽娅恭敬地站在门边并看着他。两个成年人必须极其严肃认真地看着第三个人喝咖啡和吃面包。想必,这是非常可笑和荒唐的……”[18]然而,结局却完全是一个悲剧式的绝境,因为早在小说开始主人公就患上了肺病并内心充满了“对普通人生命的热烈渴求”[19]。
当然,我不想将契诃夫想象成一个前程似锦的炸弹手。问题不在这里。所有俄罗斯经典文学的有思想的读者以及熟悉契诃夫创作的人,永远都将赞同丘科夫斯基对契诃夫的“极度真实”的论断。顺便说一句,当人们想起晚年托尔斯泰的政论作品和生活方式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想到“极度真实”?别尔嘉耶夫写道:“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寻求真理是一个主要的整体倾向。但是在这里并且在此刻我只想谈契诃夫。当我认真了解了他的创作以后,我时刻感觉到,在契诃夫对真理的寻觅、追求与期望中隐含着某种内在的痛苦的冷酷。
在这里出现了至少两个问题。第一,俄罗斯文学寻求真理的执着特别对契诃夫而言从何而来?第二,这种痛苦的冷酷从何而来,是针对谁的,与契诃夫众所周知的人道主义精神又何以契合?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再回到俄罗斯社会-文化的分裂问题上来。生存在这样一个政治专制体制只能维持社会不至于彻底解体的社会中,人们不得不说假话,或者,最多说一半真话。这是因为,第一,你的真话对别人来说永远可能是假话,第二,任何一句真话在政治上都是危险并会受到政权制裁的,因为它对于社会和国家体制的整体存在而言是危机四伏的。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生存使人们感到众多不适,而且完全是非公开化的政治和物质上的不适。当然首先指的是大多数人在生活上的心理感受。这往往体现在某种生存困境的下意识的感觉中。一方面,俄罗斯人基本上习惯了在如此不适的环境中生存。另一方面,当俄罗斯人的思想和行为处于极度困境之时,这种不适总是能使人认识自我。大概,这正是众所周知的“俄罗斯灵魂之谜”的第一个谜底,此外谜底还需包括俄罗斯文化中无可争议的宗教特质,人们对政治专制的忿恨以及政权阶层对内部演化和综合性现代化进程的无能。与“无所不在的谎言”的斗争和对某种“普遍真理”的寻求(不管是在大的政治环境下还是在家庭生活中,都不重要)成为了克服社会不适之感的不可避免的方式。富有战斗个性的契诃夫,一个“把奴性从自己身上像水一样一滴滴挤出去”的作家,他首先感兴趣的不是政治,而是个体的人,因而他不能不彻底地将自己奉献给寻求真理的事业。但是,这项事业不是为了全球化思想的建构,而是致力于对俄罗斯人细腻的关注和理智、精准的风俗画描绘。
关于契诃夫所隐含着的冷酷,探其缘由,应该说是很多的。作家的艰难生活,多年来为坚持“没有谎言”的个性世界而进行自我斗争(这一点许多与作家亲近的人都提到过),最终导致的便是日渐加剧的绝症。当然还有——我确信——刚刚指出的日益加重的个人状况,对俄罗斯处于绝境的担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愈来愈多的忿恨,这些都促使作家在内心中生出一种冷酷。M.O.梅尼希科夫,一位从1892年开始便和契诃夫保持友好关系直到其生命结束的文学批评家,在1896年的日记中列举了契诃夫的典型特点,他首先指出的便是作家“无法忍受俄罗斯自身生活的糟糕形象”[20]。1893年四月,契诃夫在一封给保守派的著名报社《新时代》主编A.C.苏沃林的信中这样形容俄罗斯状况:“……一个亚洲国家,没有出版自由和良心,政府和社会十分之九的人都在像对待敌人一样监视着新闻工作者,人们生活得如此紧张和糟糕并且看不到美好的未来……”[21]契诃夫敏感觉察到了社会分裂带来的不适,也明白了绝大多数人不可能“从自己身上挤出奴性”,自我克制力的缺乏、对自我个性的了解以及对来自社会的不解的深刻认识,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作家的忿恨,继而是冷酷。然而,契诃夫并未将这种冷酷表现为“用暴力而战”的大声呼告,而是无情地表现了主人公的悲苦命运,对俄罗斯生存之绝境的日常生活表现予以满含痛苦的嘲笑抑或是公开讥讽,其笔触细致入微又滑稽可笑。契诃夫完全没有违背犬儒主义,在我看来,令许多当代人和更多的后来读者所折服的正是其中的智慧。
别尔嘉耶夫指出,19世纪俄罗斯文学“本质上不是文艺复兴式的文学”[22],因而契诃夫著名的人道主义(在俄罗斯遭到刚出校门的人的炮轰)也不是文艺复兴式的。换言之,契诃夫根本不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为了歌颂人类灵魂和创作之伟大。他以精湛的技艺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绘表现了俄罗斯的分裂,并且隐含地越来越多地表达了对其所写之物和人的忿恨。他一点也不热衷于表现“革命的牺牲品”!在他内心深处的希望是——至少,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必将从绝境中找到一个有积极意义的和平的出口。小说《决斗》(1891)便是一部在俄罗斯分裂的背景下寻求普遍真理的缩影。作为自己真理的代表并且执著寻求真理的人,主人公“多余人”、“摇摆不定的知识分子”、小公务员菲南索夫·拉耶夫斯基和新一代富有个性的代表冯·科伦,甚至在行走的路上互相开枪射击。但是在小说结尾,他们似乎和解了,并且互相握手告别。这时拉耶夫斯基甚至在想:“谁都不知道真正的真理”。革命前的评论界对于人物的真实性给予高度评价,但又猛烈抨击了结尾的矫揉造作[23]。
因此可以说,契诃夫的人道主义在人物塑造方面绝不是但丁的“绝妙的喜剧”里的人道主义,也不是马克西姆·高尔基带有革命气息、透着血腥味的“人道主义”,它更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天后现代主义的“宽容”:是的,他们是本真的,给他们一条活路吧,或许会有益处的。因为存在着一些“个体的人,他们拥有自己的个性,分散在全俄罗斯,在他们身上具有拯救力量……”只是,契诃夫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人“很少”。
伟大的作家安东·巴夫罗维奇·契诃夫为世人所承认,却不被人所理解,在他的笔下,分裂中的俄罗斯所面临的社会-历史及文化发展的绝境变成了日常生活的绝境,变成了作品人物戏剧化的悲喜剧和没有价值的存在。
俄罗斯的绝境历史性地被过度延长了,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会永远持续下去。
注释:
①俄罗斯的“文化层面”或者说“文化精华”指的是什么——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