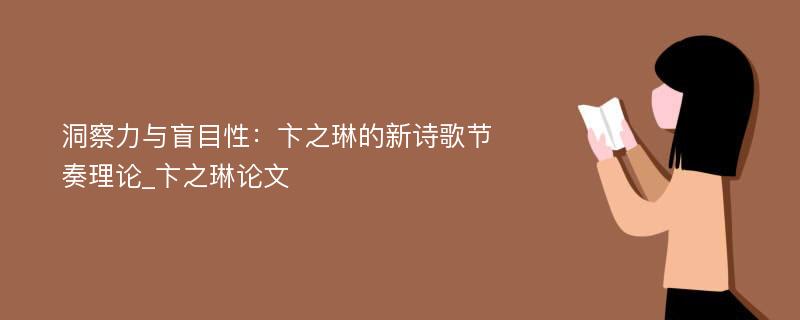
洞见与盲视:卞之琳的新诗格律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律论文,新诗论文,卞之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972(2007)02-0054-04
一、“顿”是新诗格律的中心环节
卞之琳基于对“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原理的认识,考究了我国古典诗词和西方诗歌中“无韵体”(black verse)的规律,借鉴了“新月派”的“新格律”实验失败的教训,探查了现代汉语的基本规律,特别是根据现代口语的内在特点,提出“顿”(或“音组”、“音尺”)在建立新诗格律中占据着关键性位置,是新诗格律的中心环节。这种理论主张的提出,也是建立在卞之琳自己的创作实践基础之上的——除了初期的作品及少数自由体外,卞之琳的诗歌(包括他在新时期的诗歌创作)多是格律体。
卞之琳认为我国的古典诗词的格律基础都可以用“顿”来分析,而不是像一些人所认为的“押韵”。(比如何其芳在《关于现代格律诗》就说,如果只是顿数整齐而不押韵,它和自由诗的区别就不明显。)他说,“脚韵与格律不可分,但与更属诗艺的双声叠韵一样,不是格律的中心环节”[1] 136。对于诗歌格律的研究来说,这种主张是非常有见地的。例如,赵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并没有押韵(且前、后两行的字数并不相同),其格律效果就是通过诗行的有规律的顿数实现的。这首诗中每行的顿数都是三顿:“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同时,他考察了西方的诗歌,认为西方诗歌中的“无韵体”,比如莎士比亚的一些诗剧和米尔顿的长诗《失乐园》就是“无韵而有格律”。他还认识到,在白话新诗的“顿”(或“音组”)内部不必讲究平仄或轻重音,因为白话中插用了虚词,平仄就不起关键作用,而音的轻重又往往随地区而异。
卞之琳分析了“新月派”时期的“豆腐干诗”在实践方面失败的原因。他虽然批评说,以“戴着脚镣跳舞”为格律体辩护“只能是自我嘲弄”,闻一多在20年代开始探讨新诗格律而“不幸向西方借过来的这句糊涂话不知害苦了多少同道上的探索者”,但他并不苟同于一般人对“新月派”机械模仿西洋诗格律的指责,认为“豆腐干诗”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勉强用字数为量度诗行的单位”。而究其根源在于,当时的格律诗试验者和反对者缺乏对现代汉语和现代口语的研究,都没有意识到“现代口语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来,而是自然分成几个字一组说出来的”。[1]179-180但他还是赞同闻一多提出的“音尺”概念(也即卞之琳常用的“顿”),并对其进行了高度评价——“由说话(或念白)的基本规律而来的新诗格律的基本单位‘音尺’或‘音组’或‘顿’之间的配置关系上,闻先生实验和提出过的每行用一定数目的‘二字尺’(即二字‘顿’)、‘三字尺’(即三字‘顿’)如何适当安排的问题,我认为直到现在还是最先进的考虑”[1] 14。
卞之琳在1953年写的《哼唱型节奏(吟调)和说话型节奏(诵调)》中,同意艾青所说的诗的语言基础是日常用语;也赞同何其芳在现代口语的基础上建立格律诗的主张。他还澄清了两点事实:其一,中国字是单音字,但中国语言不是单音语言;其二,现代的日常用语是白话,不同于单音词占大比重的文言。卞之琳分析说明了现代口语的规律和特点:我们说起话来,多是以二、三音节词或分、合成二、三音节组,来一个停顿,也有一音节词一停顿的,但在诗行里往往可以随全行的主导形势而粘附上、下一个二音节词作一顿,也有按四音节一停顿,以语助词或“虚字”(的、了、吗之类轻音节)为条件,否则四音节组自然会分成两顿。他举例说,“大多数的”是一顿,而像“社会主义”这样的四音节组可分为两顿读[1] 121。他还区分了“顿”(或“音组”)与词和词组的区别:
音组是汉语白话诗律的关键因素,而音组一般等于一个词或词组,但也不一定相等,例如“偶然在小河里游”,实际上念起来的自然(也就是客观)分顿是这样——“偶然在|小河里|游”(以音组或顿建行,亦即根据此),而不是这样——“偶然|在小河里|游”(主观上要这样念当然也可以)。[1] 162
由以上卞之琳所做的分析和论断,我们可以看到,在卞之琳的新诗格律论中突出了“顿”的中心位置,而且对“顿”的内涵做了较为清晰的阐释。因为“顿”(或“音组”)内部可以有字数的变化,这就使得由顿数组成的诗行内部有更多的组合、变化。但是,卞之琳认为现代口语中二、三字顿最常见。基于对何其芳主张在现代口语基础上建立格律诗的认同,根据现代口语的规律和特点,他强调诗体与散文体不同,“主要更需要以二、三个音节成组,突出与散文体的区别”[1] 216。他还提出“参差均衡律”,即在不强调平仄、不拘轻重的情况下以二字顿和三字顿适当调配——如果诗歌中行行、段段都用一样的顿法,就难免会单调呆板,因此“需要在不破坏基调的条件下有种种变化”[1] 144。
二、“说话型节奏”和诗歌的语言音乐性
在1953年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中,与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和非现代格律诗的分类不同,卞之琳把诗歌区分成了“说话型节奏”和“哼唱型节奏”两种基调,即“诵调”和“吟调”。[1] 141① 他这种具有理论创新价值的划分,就是以诗行中结尾是“二字顿”和“三字顿”的不同为依据的:“一首诗以两字顿收尾占统治地位或者占优势地位的,调子就倾向于说话式(相当于旧说‘诵调’),说下去;一首诗以三字顿收尾占统治地位或者占优势地位的,调子就倾向于歌唱式(相当于旧说‘吟调’),‘溜下去’或者‘哼下去’。”[1] 41他认为,两者同样可以有“语言内在的音乐性”。“吟调”的长处是“韵脚响亮、节奏明显”,而“诵调”的特点是“比较柔和自然,变化也较多”。[1] 41
笔者看来,卞之琳这种诗歌主张的提出,是对当时关于新诗形式大讨论中提出的一些诗歌理论主张的借鉴或呼应。何其芳在那篇产生广泛影响的文章《关于现代格律诗》中说:“为了更进一步适应现代化口语的规律,还应该把每行收尾一定是以一个字的一顿这种特点加以改变,变为也可以用两个字为一顿。”[2] 10因为,这是“为了适应现代口语中两个字的词最多这一特点”,而这样做“是和我们的口语更一致的”。[2] 10何其芳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用现代口语二字尾写的新诗与用五七言单字尾写的古体诗、民歌在句法上的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并因此提出要建立一种“符合我们的现代口语的规律的”[2] 10新的格律体系。而“新格律”的另一“重镇”林庚在1950年的《九言诗的“五四体”》一文中认为,“在节奏上看来,一个诗行的下半段是更有重要性的”[3] 111。由此看来,我们可以说,卞之琳以诗行结尾的“二字顿”和“三字顿”的不同划分“哼唱型节奏”和“说话型节奏”,是对当时诗歌理论主张的吸纳、总结,同时也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发展。
卞之琳不同意何其芳把诗歌划分为格律诗和非格律诗,而是着重从节奏上区分诗歌的形式,这在中国新诗理论上是一种新见,也是具有其合理性的。因为恰如美国客观主义诗派的中心人物路易斯·祖柯夫斯基(Louis Zukofsky)在《诗歌声明》中所说,“诗歌形式是作为话语和声音的驱动力而形成的,即,是作为发生声音交互作用的节奏这一决定性因素而获得的”[4]。同时,卞之琳主张诗歌的形式从节奏方面划分也是对诗歌音乐性的探寻。他说:“诗的音乐性,并不在于我们旧概念所认为的用‘五七唱’、多用脚韵甚至行行押韵,而重要的是不仅有节奏感而且有旋律感。”[1] 26卞之琳这种理论主张,在笔者看来,是受到了艾略特《诗歌的音乐性》一文中的观点的影响或启发。在这篇文章中,艾略特写道:“在音乐的种种特点中和诗人关系最密切的是节奏感和结构感。我想诗人可能会与音乐过分接近而写出类似音乐的东西:结果可能是造成矫揉造作;但是我知道,一首诗或者诗中的一节往往首先以一种独特的节奏出现,而后才用文字表达出来,这种节奏就会产生意念和形象。”[5] 229
同样是在《诗歌的音乐性》这篇文章中,艾略特提出,“诗的音乐性必须是一种隐含在它那个时代的普通用语中的音乐性”[5] 229。而卞之琳则主张,诗的音乐性就是“在活的语言以内去探求,去找出规律的要求”[1] 28。卞之琳不仅赞同或呼应了艾略特关于诗歌的音乐性的主张,而且常以此作为尺度去衡量诗人的创作。除对闻一多用口语写得干净利落、圆顺洗炼的有规律诗行给予高度赞誉之外,卞之琳还高度评价了徐志摩的诗歌创作:
徐志摩的诗创作,一般说来,最大的艺术特色,是富于音乐性(节奏感以至旋律感),又不同于音乐(歌)而基于活的语言,主要是口语(不一定靠土白)。它们既不是直接为了唱的(那还需要经过音乐家谱曲处理),也不是像旧诗一样为了哼的(所谓“吟”的,那也不等于有音乐修养的“徒唱”),也不是为了像演戏一样在舞台上吼的,而是为了用自然的说话调子来念的(比日常说话稍突出节奏的鲜明性)。[1] 33(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笔者注)
也正是基于诗歌的音乐性应在“活的语言”,即日常语言中寻求的认识,对脍炙人口、“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叶圣陶语)的戴望舒的《雨巷》,卞之琳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雨巷》不过是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用惯了的意象和用滥了的词藻,却更使这首诗的成功显得浅易、浮泛”。[1] 66相反,他认为较有分量和新意的是戴望舒的《断指》:“在亲切的日常说话调子里舒卷自如,敏锐,精确,而又不失它的风姿,有节制的潇洒和有工力的淳朴。日常语言的自然流动,使一种远较有韧性因而远较适应于表达复杂化,精微化的现代感应性的艺术手段,得到充分的发挥。”[1] 66
卞之琳说:“新诗的语言音乐性固然并不系于格律(自由体也可以有语言音乐性),但是新诗,无论格律体或自由体,总首先还得有像这种探索所涉及的语言规律性的感觉。”[1] 35卞之琳关于“说话型节奏”的理论主张,显示了白话新诗在理论层面上对语言规律的探索和语言内在音乐性的寻求的成绩。
三、新诗格律论的意义与局限
卞之琳对“说话型节奏”和“哼唱型节奏”的划分(在卞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更重视前者),以及对诗歌语言的规律的探寻,特别是对在现代口语中寻求音乐性的努力,是对当时渐成主流的诗歌古典化和民歌化的风尚的小心翼翼的突围,或者说,小小的抵抗。而这种努力的旨归在于,确立与古典和民歌的区别,并与之疏离,从而确立新诗的合法性——因为在当时民族文化本位思想拥有道德优势的语境下,特别是在“最高领袖”将“古典+民歌”视为诗歌的发展方向的条件下,以外国诗歌作为乳母的新诗已然处于弱势地位,甚至一种“新诗的发明可能是历史的错误”的潜在论调也在悄然酝酿之中。具有多年现代诗写作经验的卞之琳显然能够意识到新诗所面临的危险,从而参加了关于新诗形式的大讨论,并对新诗格律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卞之琳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忆及当年“诗的形式问题”的讨论,他说:“不承认真正的格律体新诗的存在和初步成果,势必贻人所谓‘全是散文化’的口实,导致对新诗的全盘否定。”[1] 180而且,从某种角度上我们可以说,相对于“歌唱”来说,“说话”具有低语性和指向内心的性质,因此“说话型节奏”的强调也显示了在“战歌”、“颂歌”的时代喧响中,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诗人力图保持有限的个体主体性的努力。(这或许有过度阐释的嫌疑了。)
卞之琳的关于新诗格律的理论主张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尤其是在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实践中。而这种局限,或许是格律本身的局限。格律被一些人视为新诗确立自身的审美独立性和重温古典“辉煌”的路径(甚或是唯一的路径)。而对新诗格律的探讨,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关于现代汉诗与现代汉语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它具有严密、系统的理论承传性。但是,这些新诗格律的探讨者就诗句的“顿”或“音组”所做的精致分析,虽然构成了其理论作为学术探讨的严谨的一面,但易于滑入技术主义的窠穴。让我们看一下卞之琳对“顿”所做的分析:
“正如从风暴里来”只能作“正如从/风暴里/来”,除非主观地念快些,才能作“正如/从风暴里/来”,或念慢些而成“正如/从/风暴里/来”,主观上要念快些,也未尝不可以一口气念成“正如|从风暴里来”。[1] 163
尽管卞之琳对“顿”做了耐心的分析,但人们可能对“顿”的划分还是感到茫然。因为诗歌中的语言具有鲜明的个人性,其节奏受诗人的情绪的渲染,与诗人的呼吸节奏有关,毕竟不可能脱离“主观”。诗歌的外在节奏与内在节奏,即诗歌语言外在的声音节奏与诗歌语言内在的意义节奏及其所伴随的情绪节奏是扭结成一体的。而这就为顿的划分带来了难度。让我们再以卞之琳在《谈诗歌的格律问题》一文中所举的自己的诗来检验一下他的诗歌理论。“我们|合作了|开好渠,|我们|合作了|筑好堤,|我们|加入了|合作社,|我们|参观了|拖拉机!”这节诗每行三顿,且以三字顿收尾,就是卞之琳所谓的吟咏式调子。但是我们读起来会感觉到有些别扭。略一观察,我们就不难发现此中原因:由于现代口语中两字顿居多,但诗人为了吟咏式的调子而凑三字顿,但“开好渠”、“筑好堤”这样的三字顿在意义上欠清晰准确。
对于卞之琳的这套格律论,袁可嘉虽然承认是“持之有理,行之有效”的,但紧接着他就质疑了这套理论在写作实践中的作用:“问题是诗的题材和表现文法是各种各样的,未必都适用这样的严格的格律。我们九叶诗人在接纳它时并未全部照搬,而是在具有一定的格律意识后,走较宽泛的路子,以便表达现代人复杂多变的思想情绪。”[6] 而郑敏虽然认为有必要研究汉语本身的音乐特质,以探讨新汉诗的音调,但对于如何创造自身的声调模式,至今仍然困扰着她:“如今我写诗时多靠自己的听觉直觉,而说不出理论。”[7]
尽管卞之琳的关于诗歌格律的理论主张是“言之成理”的,但从整个现代汉诗的效果史及当今的诗歌写作实践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包括卞之琳在内的对新诗格律的探求都是“失败的理论”。如果用结构主义的理论对这些理论进行观照,或许能给我们以启发,让我们察明它的症结所在。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文本是具有不同层次的系统。罗兰·巴尔特(Roland Batel)曾提出一条原理,即必须超越一个层次才能理解该层次,在层次之内,我们只能看到分解组合的关系,而看不出意义。[8] 8作为文本的诗歌也是具有不同层次的,在格律诗中格律只是其中的一个层次,我们考察诗歌格律的功能和意义也只能“超越这个层次才能理解该层次”。只有格律这种外在的形式与诗歌中情感与意义等层次发生合力时,格律才能被激活,诗歌作为一个系统才能释放出能量。否则,脱离诗歌文本中的其他层次而只谈论格律,只能产生“无用的正确”。路易斯·祖柯夫斯基在《诗歌声明》中谈论诗歌中的音律问题时,有一段话说得极好:“韵律学对于诗人来说是第二位的兴趣……对所有的音律因素反映敏感,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并不把这种计算强加在所说或所做的事情上——因为可以从他们诗歌的冲击力方面去进行判断。”[4]
注释:
①笔者更倾向于“说话型节奏”和“哼唱型节奏”的命名。“诵调”、“吟调”固然简洁,但此系“旧说”,且没有前者准确、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