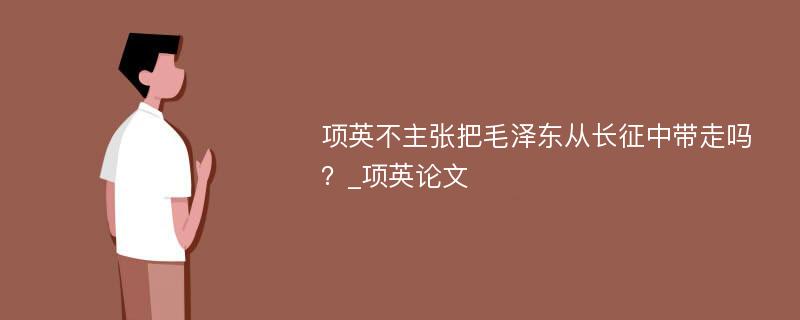
项英不主张长征带走毛泽东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项英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是一件长期以来悬而难决的问题,因为当时的一些事情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因素。
中央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下旬的突围西征,实际上是万不得已之下提前行动的慌张逃跑。同年9月下旬,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等人,于江西德安获取了蒋介石在庐山制定的“铁桶计划”,不顾生命之险送到了瑞金。博古、李德眼见局势万分危急,决计提早跳出敌人的围击圈。这一仓促决策,在中共中央局的会议上都没有提出来,初时连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也不知道。直到10月3日,临时中央才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名义,发出《为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书》,字里行间明显地透示这样的信息:主力红军将实行战略转移,全苏区的民众准备投入坚守苏区的游击战争。
确定红军主力8.6万余人西征而去,另有1.6万军政人员留在中央苏区,包括设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乃至负责人的任命,等等事宜都决议下来了,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确定哪些人留下来。
根据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长的李维汉事后回忆;对于哪些人留下来或随军出发,是按管理范围分级决定的,即各级上报,最后由博古、李德定夺。
随军出征还是留下坚守,关系到每个人的前途命运,实际上也涉及到博古、李德等人感情上的好恶,隐密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妙因素。诚如伍修权的回忆文章所言:“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所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这些人后来大部分牺牲了。”
于是,患病体弱、被博古等人另眼看待的瞿秋白,腿部负伤、一张嘴巴很厉害的陈毅,被视为“毛派分子”的何叔衡、周以栗、陈正人、古柏、毛泽覃、曾山等人,都从中央组织局上报的名单中勾划掉了。李维汉在《回忆长征》一文中写到:“毛泽覃原来在组织局工作过,本来是定了随军出发的,名单报上去,博古不同意,我就没能把他带走。以后毛泽覃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牺牲了。对于他的牺牲,我长期感到内疚。”李维汉又心情沉重地写到:“贺昌,我对他很熟悉,长征前他负了伤,曾到组织局要求随军走。我去问博古,博古不同意。后来,贺昌也牺牲了。……何叔衡的留下,是博古他们决定的,我没有参与其事。”
透过李维汉的回忆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留与走的干部名单中,对于少数的“重要人物”,是由博古、李德直接决定的。
与瞿秋白、何叔衡等人相比,毛泽东是最为显目、最为敏感的人物。他的走与留牵动着博古、李德的神经,令他们颇伤脑筋。有资料讲到:博古等人最初的想法是让毛泽东留在中央苏区。可是一种放心不下的心理,又让他们改变了主意。“母羊在离开原地的时候,担心最顽皮的羊羔,情愿叼着走”,有人作了如是的比喻。
李德,这个被博古视为“战神”而拱手让权百般放纵,以致于凌驾于全党全军之上的洋顾问,也为毛泽东的去留费神,他决计同项英讨论,听取他的看法。李德在这时候找项英,那是项英具备了别人无可相比的特殊条件。
首先,项英是作为博古“左”倾中央所信赖的“股肱”人物,留在中央苏区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的,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具有直接的关联作用。其二,项英对毛泽东的了解具有一定的权威。项在中央苏区三年又十个月,几次与毛泽东交换职务——两人都担任过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两人都行使过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后来毛任了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是副主席。这种交叉平起平坐的政治地位,工作上的频繁接触,自然有着对对方的深刻了解。再次是毛泽东给项英的印象是不会说假话。他俩并非那么地思想投契,感情融洽,双方的内心都存在隔阂,都是互有微词。而且,毛是博古“左”倾中央千方百计要架空,使之成为“加里宁”的人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有职无权)。也就是说,一个坐在了冷板凳上,而另一个却正受到重用。以上这些就是李德找项英进行讨论的基础条件。
对于李德与项英的这次“几乎是一整夜”的长谈,李在其后的《中国纪事》中,这样写道:“……像以前一样,项英这次也对毛的恐怖政策,以及毛在1930年左右对忠于党的干部所进行的迫害,作了明显的暗示。同时,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的暂时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可是,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
按照李德所说,项英对毛泽东一直保持着警惕的心理,主张应对毛严加提防,不可把他带走。而正是博古的“书生意气”和“优柔寡断”,才为毛泽东的随军长征作了最后的拍板。无怪乎李德犹有怒气地写到:“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从这句话可以揣测到李德的心情:他对长征带走毛泽东是深为后悔的,怨怪这是博古的重大失误。
对于李德所写到的这一情况,有人认定说,那是李德胡乱编造出来的,目的是嫁祸于项英。其最大的理由是伍修权讲过:他没有听到李德有过这样的讲话。
是的,对于李德与项英的这次彻夜长谈,在场的人只有翻译伍修权。1984年3月28日,对红军长征抱着极大兴趣进行研究的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对伍作了专门采访。其后,索氏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据李德后来回忆,项英临别讲的几句话是告诫要提防毛泽东。项英说:毛现在缄默不语,但李德不应受骗上当。毛将会在他军队中的支持者的帮助下,一有机会就夺取党和军队的控制权。李德对这种担心也有同感。可是,据他后来回忆,当他几天后把项英的这一警告转告博古时,博古比较有信心,认为一切都会很顺利的。李德同项英谈了很长的时间,以至他到第二天才赶上军委纵队。”
索尔兹伯里在采访伍修权时记下的这段话,与李德《中国纪事》一书中的那段叙述,内容基本上是吻合的。如果伍当时明确地加以否认,索氏是不会这么记载的。而对伍修权曾经予以否认的另外一件事,索氏也写到了:
“李德在回忆中说,出发前的几天晚上,项英与他谈话,谈了长征出发后会遇到什么情况?李德说项英警告了他,说毛泽东已经作了准备,要在长征路上找李德的麻烦。你听到这个话没有?伍修权回答说:“没有,我没有听到项英说过那样的话。”
正是根据这一点,有人作出了前一点也是李德乱编出来的认定。
这里撇开像索氏这样的外国作家一般不会歪曲事实,作假成书的前提,且从事情的本身加以两方面的推论,就可以得出结论。
首先是李德没有必要在几十年之后去嫁祸于项英。从个人感情来说,李德与项英的关系是比较好的。昔日的洋顾问以“太上皇”的架势凌驾于全党全军之上,最后弄得上下怨怒,四处关系紧张,除了一班从苏联归来的留学生外,在苏区的党内和军中,没有多少人与他合得来,项英算是与他关系最好的。不然,在长征前夕,李德不会找项作那样的长谈。而两人自从这次分手后,就不曾在一起共事了,关系维持在原来的水准上。事隔几十年,项英早已作古,李德不会无端嫁祸于项,不必这样做。
另一方面,从来也没有谁说过李德不赞成长征把毛泽东带走的一件事,李氏缘何会作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举动?乡间俗话所说的“屎坑不臭挑起臭”,李德岂不明白?他犯不着这样做。没有的事情,根本不用去说。事情必定有一个接近真实的来由,李德才于几十年后的回忆录中这么提及。
在排除了李德胡乱编造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后,再从项英与毛泽东的关系和一些往事的分析,笔者认为项英在与李德的长谈中,就是这样奉劝式的、警告式的谈论毛泽东。
史实不可否认地表明,在中央苏区时期,项英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远不是那种心灵相通、亲密团结的情状,而是在不少问题上、事情上存有歧见,产生芥蒂,以至于相互之间不是补台,而是一有机会就加以毫不客气的挞伐。
首先从党内地位来说,两人之间的情状非常微妙。尽管毛泽东具有党的创始人之一的优越条件,但项英的入党时间也很早,1922年4月就以武汉工运领袖的身份加入了党。而在其后的六七年,项英以卓越的才干和革命业绩,后来居上走到了毛泽东的前头。他是党的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28年7月曾出席共产国际“六大”,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在克里姆林宫受到斯大林的单独召见,还赠给一支精制的小手枪,在讨论中国革命时对项说过“四川是最好的根据地”的话。1931年1月,项英受中央委派来到中央苏区,是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成为毛泽东的领导。其后,就是王明中央再把“中央三人代表团”派到瑞金,项英仍然代理过中华军委主席。项英在毛泽东面前,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表露出这样一种情绪:自己在党内比毛泽东地位高,马列主义水平也低不到哪儿去。因此,不用说毫无甘愿称臣的心态,反而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政治上的架子放不下。
二是项英在中央苏区时期,与毛泽东既有团结合作的一面,也产生过不小的矛盾,向对方进行过政治打击的一面。而这种情状大多数是项英向毛泽东出手的。1931年1月,项英甫抵中央苏区,在处理“富田事变”时,其思想立场、工作方法,与总前委是方底圆盖,根本合不到一起。项英对毛泽东作出的尖锐批评,于毛泽东非常不利,使得他在政治上处于难堪地位。1932年10月上旬,在博古“左”倾中央蓄意解除毛泽东军权的“宁都会议”上,项英坚定地站在“后方局”一边,以毫不留情的态势,与凯丰等人向毛泽东“猛烈开火”,并对周恩来的“温和主义”、“调和行动”有所抱怨。直到把毛泽东从指挥台上轰下来,才止息“炮火”,得意地与顾作霖等人传递条子。1933年1月至11月,项英取代朱德担任中革军委代理主席,全权指挥红军的作战。他全盘地接受共产国际远东局军事总顾问提出的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错误战略,将红军分成“东方军”和“中央军”两方面的军事行动。毛泽东极力反对这种自损优越、“将长裤扯成短裤”的错误战略,曾几次向项英陈述利害,力谏不要分兵,被项英抛于一边置之不理。结果,使红军“一个拳头置于无用,另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处于被动、失利的不利战局。还有,身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项英,在与主席毛泽东共事期间,为执行《国际来信》和《劳动法》等问题,双方合作得并不愉快,产生了矛盾。
政治上的事物是敏感的。以上林林总总的思想感情上的纠葛,使得项英和毛泽东都在内心有着一种不能融洽、亲和的隔阂,甚至存在着政治上的戒备。因此说,在红军将要离开中央苏区的前夕,李德就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征求项英的看法,项英以推心置腹的姿态,流露出对毛泽东的担忧,或者说一种思想上的戒备,说了那段直抒胸臆的话,那是可能的。笔者认为李德对此事的回忆大体上可信,即在项英的思想深处,他是不主张把毛泽东带走的。但后来博古作了拍板,他也就没有办法了,实际上到这种时分也顾不上此事了。
而对项英来说,他当时对李德那样地谈论毛泽东,是出于对党的忠诚和负责任,才不加掩饰地说了真话。因为在他看来,他是非常了解毛泽东的,有着对毛泽东一般人不可窥测的政治上高远的洞察。事情的本身也表明,项英的观察力和预见力是有别于博古等人的,具有符合事实的辩证唯物观点。如果当时不把毛泽东带走,让他留在中央苏区,就决然不会有其后的“担架上的阴谋”、“马背上的阴谋”,以至于有其后的“遵义会议”了。那个时候毛泽东在党内还没有形成领袖身份和统帅地位,项英那样做也不犯重大的政治错误。至于在遵义会议以后形成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位置,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说,项英不主张长征带走毛泽东,决不可上升到“路线错误”、“政治错误”的高度。
标签:项英论文; 李德论文; 中央革命根据地论文; 毛泽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博古论文; 伍修权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