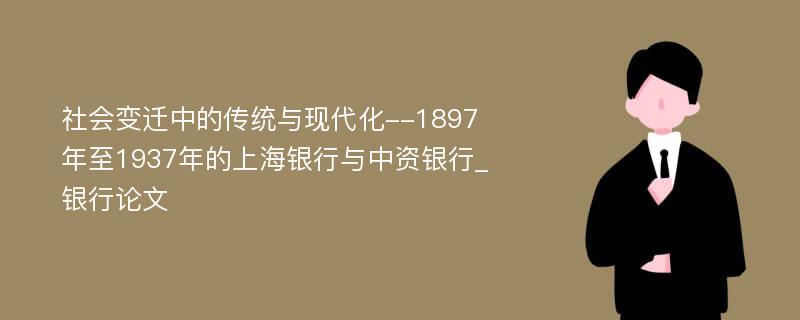
变革社会中的传统与现代——1897-1937年的上海钱庄与华资银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钱庄论文,上海论文,传统论文,银行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19世纪末20世纪初,尽管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整个经济已向近代化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无论在全国还是在近代化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的上海地区,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根植于传统社会的钱庄继续满足着这部分经济的需求,并随着中外贸易繁荣起来。现代银行则因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且刚刚来华,立足未稳,尚未被一般工商业者和市民所熟悉,它与工商业界的联系相当程度上还需要钱庄的帮助。两业人员互相兼职,经营等,正是这种现实的反映。从当时整个金融市场来看,不同层次、形式的资金需求只有两业共存才能得到满足;内容各异的业务方向、往来方式迎合了不同习惯的工商业者的需求。
我国钱庄比银行历史悠久。各地钱庄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进入近代社会后,随着内外贸易的繁荣,不但确立了它在经济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而且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熟悉中国复杂的货币体制、了解各地计量单位和商情的金融人才。钱庄业对金融市场的开拓和造就的大批人才,是中国新式银行出现的前提之一。
我国早期银行业高级管理人才主要来源是:钱业和外国留学生。学金融类的学生大多在辛亥前后才归国或进入银行业(注:上海滩金融界名人如钱新之,1909年结业于日本神户高等商业学校,1917年才进入交通银行;李铭,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后,1912年才进入银行界;陈光甫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州大学,辛亥后进入江苏省银行等等。详见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旧上海的金融界》(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等书。)。在我国银行业最初的十多年间的经营者中,钱业出身者占极重要的地位。中国通商银行首任“华大班”陈笙郊是咸康钱庄经理、第二任谢伦辉亦是钱业中人,曾任户部、大清、中国银行之首席副理的胡逵芗早就在经营钱庄,即使到191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时,陈光甫还聘用余大钱庄经理宋云生,利用其经验和社会关系开拓业务(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49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第82页。)。据不完全统计,在上海地区有数十钱业人士曾为银行的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49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第82页。)。华资银行较少从钱业界引进人才大体是在二十年代以后,随着势力的扩张和各种业务的开展,钱业人才慢慢不能满足需要,才开始从国内大学商科、银行学校、高中毕业生中选用。因此,钱庄为华资银行业的出现在人才上起到了一种奠基石的作用。
另外,钱庄业也为银行业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开办资本。从部分银行的开办资本可以看出,钱庄资本向银行资本的转移从一开始就存在,浙江兴业银行创立时的股东就有钱庄股东郑岱山,他是该行的董事,占有1%的股份,同时也在杭州投资开办了开泰、元泰两钱庄(注:根据浙江兴业银行档案。转引洪葭管《从借华资本的兴起看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完整形态》,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2页。)在四明商业银行的50万两开办资本中,与钱业有关的资本计55,000两,占11%,后来钱业出身的孙衡甫的股份逐渐增加,最多时达5,258股,金额为2,621,900两,一人便占该行资本总额的35%(注:根据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档案,转引来源同[4]第314-315页。)。据《上海钱庄史料》统计,这时期确实可考的同时为银行和钱庄的投资者为9人。产生这种资本流动的原因有三:第一,上海钱庄的股东一般都是些比较殷实的资本家,他们也在钱庄投资中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资本;第二,人才的流动带动了资本流动,钱业人才进入银行业必然会随着他们对银行业营运状况的了解带动一批钱庄资本流入银行业;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早期银行,特别是中小型银行其实与钱庄无太大区别(注:早期银行,主要是中小型银行,名为银行,实为钱庄,浙江实业银行前身浙江银行的规章制度、业务方向、经营方针等都沿袭钱庄;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即使在孙衡甫盘进后,虽采取了一些资本主义银行的经营方式,但钱庄的烙印还是不少,如其发行钞票,竟沿袭钱庄发行庄票,无准备金,漫无节制。),两者的相似性使投资者觉得投资银行等于投资钱庄。
华资银行产生后,在经营中两业是相互支持的。主要表现在钱庄帮助银行发行钞票,银行拆款给钱庄,双方共组银团等方面。早期银行为了推广钞票,曾允许钱庄以六成现金、四成公债、期票领用十成钞票,这种方式对钱庄而言是使周转现金由六成变成了十成,银行则借此扩大了影响。有些银行的钞票如果发生挤兑,也常利用钱庄分布广的优势帮助平息风潮,挤兑银行只要刊行某某几家钱庄代兑的广告,人心即可安定,挤兑风波就会慢慢平息。有时钱庄还给挤兑银行一定的现金通融(注:《上海钱庄史料》第143-147页。)。
钱庄资本向来不丰,即使最盛时上海汇划钱庄的平均资本也不过二十余万两,有四五十万两资本的大钱庄寥若晨星。但钱庄的资金往来常十倍或数十倍于其资本,其中除发行庄票、收受存款外,银行拆款是其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华资银行势力未盛时,钱庄拆款多源于外资银行,但二十年代后,华资银行的拆款远超过了外资银行,最多时有千余万两。由于传统关系,我国钱业与工商业的联系更为密切,当银行资本暂时没有更好的出路时,以钱庄为中介放款给工商业可适当减少资金呆滞产生的损失,当然钱庄也因此扩张了业务,获得了可观的利率差。此外,很多华资银行因需钱庄代理票据清算,也不得不存款于钱庄(注:当然钱庄营运资本流向银行的情况亦是有的,当银根缓和时,钱庄也会出现一定数量的资本暂时闲置,为避免亏耗,一般都将其存入银行,这既可保证资金的稳妥,又能减少一些损失。)。
银钱两业共组银团进行联合放款的史料,最早是在1921年。当时,上海银行业鉴于市场上银元混杂,成色不一,遂提议筹办造币厂以整理银元市场。是年3月,上海银行公会会同钱业公会组织了上海造币厂借款银团,由财政部发行国库券250万银元,由银团担任发售,作为专项借款充上海造币厂购地建厂及购买机器等项之用。同年7月,银行公会以通泰盐垦公司急需资金,经该公司股东会议决定,发行通泰盐垦公司债票银元500万元,由各银行及钱庄共同组织经募通泰盐垦公司盐票银团,负责债票经募事宜(注:《上海钱庄史料》第147-148页。)。其后,很少有两业联合放款的史料,原因很可能是随着银行业羽翼渐丰,已有能力独立承担高额贷款。
此外,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也符合两业的共同利益,近代上海金融市场因种种原因容易发生风潮,而钱庄营业中的不严谨使它对金融风潮的免疫力较弱,为了维持市场稳定,银行不时在关键时刻支持钱庄。这种支持在20年代以后显得尤为重要。
所以,从华资银行的创立及银钱两业早期的关系中,我们看出现代对传统并非一味排斥,现代银行的诞生和立足曾经得到过传统钱庄在人才、资金方面的支持;双方在业务经营中也多互相支持。现代取代传统、传统发展进化到现代还有待时日。
2
“一战”前后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重要时期。经过十年左右的飞速发展,上海地区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进步神速,整个社会经济中近代经济成分日益增强。同时,中国银行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到二十年代不管是银行家数、还是资本总额都远非辛亥前可比;更为重要的是,华资银行业的经营管理方式在辛亥后已有重要发展,大批留学生学成归国,积极传播西方银行学知识,或按西方标准改造原有银行,或另起炉灶重建银行。这批留学生给中国金融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大大丰富了19世纪以来中国人在银行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此后银行走上了崭新的发展道路。随着中国经济的变迁和现代银行业的发展进步,银钱两业间出现了日益尖锐的对立和矛盾。
银行业突然闯入钱庄业的世袭市场,曾引起过钱业的恐惧,有的进而抵制。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陈光甫的锐意经营下,业务发展很快,就引起钱庄的妒忌,上海一家老牌钱庄曾拒收该行开出的本票,这对它的信誉影响很大(注:《旧上海的金融界》第145页。)。在南通、常州、芜糊,上海银行的分行都曾遭到过钱业的排挤。在南通,当地钱业公所于1925年春宣布与它断交,其原因是:“本行分行,自开办以来,与各界来往,感情素极融洽,业务进行异常顺手,在无意之中,或许使人发生相形见绌之感,”因此煽动公所,宣布断交(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83-84页。)这种现象可能在中小城市针对中小银行的较多,对其影响也较大。
从总体上看,银钱两业经营着大致相同的业务,如此则势必引起竞争。首先是存款,近代银行业毕竟是更为适合工商业发展要求的先进的金融机构,它们一般都拥有较雄厚的资本,并以此号召,招揽存款。华资银行至少从四明商业储备银行起就开始大肆经营存款,越到后来,各银行间为争取存款,其中特别是储蓄存款可谓八仙过海、花样百出。当外商银行的可靠性面临挑战后,华资银行的存款更是突飞猛进。据资料显示,从1928年到1937年,各主要银行的存款数额,按不变币值计算,增加了三倍以上。这种增长幅度是惊人的。相反,钱庄囿于传统关系,历来都不怎么注重收受存款,二十年代以后这种局面才开始有所改观。很显然,在争夺存款的竞争中,钱庄始终处于下风,尽管其存款亦有所增加,但其增幅不及银行。其次是放款,双方一开始就进行着较激烈的竞争。在银行的积极推动下,抵押放款逐渐为商家所接受,而钱庄也在营运中慢慢体会到了抵押放款的优点了,也开始经营这种放款,很多钱庄还自营堆栈以存放顾客的押品。同时经营抵押放款,竞争是必然的。实际上很多钱庄都以银行为业务竞争对手,强调与它进行市场争夺,而银行抵押放款业务的扩张确实也给钱庄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引起过钱庄的抵制。前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芜湖设置堆栈,当地钱庄“以为商记堆栈,既非钱庄,又无银行,此次兜揽交易,实属破坏规章,禁止同业与本行堆栈往来”(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83-84页。)。第三,从内汇业务上看,19世纪很大部分掌握在票号手中,票号衰落后,钱庄因与内外贸易密切的关系,在内汇业务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银行兴起后,利用资金雄厚、机构遍布等优势,大力开拓内汇业务,中国银行1930年办理的内汇为575,600,000元,1935年则为1,020,153,000元;交通银行1935年办理的内汇与1934年相比几乎翻了一翻(注:洪葭管等著《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27页。),到1935年左右,钱庄基本被逐出了内汇领域。
尽管我们可以把银钱两业看成是基本相同的金融机关,但是钱庄毕竟来自传统社会,带有不少传统社会的痕迹,在其发展过程中,它总是尽力维护某些传统。相反,银行则完全来自西方,本质上是一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较完备的金融机构。双方在共存中,不时因制度、习惯等差别产生争论,甚至对峙。
钱庄因混乱的货币制度而产生,也得益于这种货币制度,通过对银两、银元、铜钱等货币之间兑换的操纵,既可获得此涨彼落的差价,又可控制金融市场。银行业兴起后,特别是市场上出现银荒或洋荒时,双方多次就银两、银元混合本位产生激烈的争论。钱业是既得利益者,一直坚持固守旧制,钱业界认为,工商业对两种筹码的不同需求,正是金融业用以调节金融市场的最佳手段。实际上两种本位的同时存在,时常给市场带来无谓的混乱,反映在市场上就是银拆和洋厘的反方向波动,但是银拆、洋厘的波动并不完全反映上海的金融缓急,因为除了市场对两种货币的不同需求外,有时这种波动纯属人为造成的。“两元”制度的存在也给社会商品交换造成一定的困难,按照传统,大宗交易以银两为单位,小额交易则以银元,商家不得不同时准备两种不同计量单位的货币。因此,银行界及多数经济界人士都呼吁改用银元。国民党政府着手改元后,钱业公会决议取消存在已久的“两元”进出兑换佣金,以消除人们对钱庄死守“两元”制度的看法。在改元过程中,钱业公会或以集团名义,或由代表人物出面,多次发表谈话,甚至直接上书财政部,陈述改元的必备条件,有意无意地阻挠改革。
大肆经营信用放款是银行界批评钱业的重要证据之一(注:其实银行也经营信用放款。华资银行出现后,抵押放款不易推行,为了扩展业务也只好办理信用放款,只是比重不大。)。其实,早期钱庄经营无抵押的信用放款是有一定依据的,有的与经营某种商品的商人联系密切,有的与某一地区的商人交往广泛,有限的服务对象使钱庄有可能充分了解客户的营运状态、资信情况,这为其经营信用放款提供了可能,尽管后来钱庄业逐渐摆脱了一些传统的羁绊,但对人信用仍是钱庄营业的重要特征之一。在近代社会复杂的经济环境中经营信用放款毕竟是不稳妥的,贷款人一旦倒帐,就会危及钱庄的安全,进而牵动整个金融界,引起风潮,使大家都遭受损失。所以银行界及钱业中很多有识之士都告诫钱庄少做信用放款。
银行对钱业汇划制度的“反抗”也很激烈。银行在资力上早就超过了钱庄,可钱庄依靠其独具特色的汇划制度牢牢地控制着金融市场,使大部分银行只好忍气吞声、俯首听命。银行势力渐丰后,曾企图挣脱钱庄的控制,1921年3月,部分银行决定自4月1日起自定银洋价格,但因银行没有自己的票据清算中心,对市场上银洋需求信息掌握不全,最后是不了了之(注:《上海钱庄史料》第154页。)。1924年袷丰钱庄倒闭时,双方又因划条问题短兵相接,按上海钱业习惯,“如甲庄以乙庄划条付丙庄,丙庄持交乙庄,乙庄将其收入丙庄帐内,同时再以划条还于甲庄,彼此转帐,现在乙庄倒闭,而丙庄并未收现,由是在再向甲庄说话,此在钱庄之中,如发现在当晚8时结帐之前,甲庄在惯例上理应负责,而银行则否,一切以票据为根据。”钱庄要求银行将票据已清算而尚未收现的款项集中移交钱业公会,银行公会则要求搁浅钱庄代理收付的款项一律退还原委托人,并把其对银行之债务列于优先地位,这遭到钱业的拒绝。最后银行不得不妥协(注:《上海钱庄史料》第133-136页。)。三十年代银行自己的票据交换中心成立后,银行才最终摆脱了钱庄汇划制度的控制。
3
尽管上海钱庄在二十年代就有向现代金融业发展进化的趋势,但始终没有跟上上海地区经济近代化的步伐,到三十年代整个经济的变迁越来越不利于这种传统金融机构的生存。
从对外贸易来看,部分外国垄断资本集团开始以经销、包销的方式推销其商品。这些财团资力雄厚,一般均以赊销方式将进口商品交华商经销或包销,如买办周宗良等1920年组织的谦和靛油公司,资本达140万两银子,负责包销谦信洋行的靛青,谦和在全国各地设分号或代销处,以各地染坊为销售对象,且一般都做放账生意,逢三节(端午、中秋、春节)才结帐。美孚石油公司在“一战”后便废除了买办制,采用经销商制度,即在其划定的区域内物色合适的中国商人经销美孚石油,经销商再从乡镇商业中心物色商户成立分销处,从而形成三级销售网。英美烟草公司采用类似的销售方法。垄断财团的这些推销方式并非限制中国中间商人在洋货销售的作用,而是直接渗透到产品在中国销售的大部分过程中,这种渗透的结果是钱庄慢慢失去了在这些商品销售过程中的资金供给功能(注:可参阅上海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及杜著前引书第185-188页。)。
对钱庄在贸易中的地位影响最大者为国民党政府对贸易的统制政策。1933年实业部制定了1933-1936年《实业四年计划》,计划在政府的通盘筹划下,将粮食、棉花、煤炭等重要产业物资统制起来(注:《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二册第427页。)。1934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全国粮食局,在沪成立“七省粮食运销局筹备局”,推行粮食统制。1935年,又以“解决农村金融问题”为由,举办农业仓库,吸收农民的粮食抵押借款(注:陆仰渊等编《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392页。)。对于棉花,棉业统制委员会组织银行团投资了300万元,以推广美棉,农民所产棉花,不准私自加工,必须一律售与政府(注:陆仰渊等编《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393页。)。早在1933年,江苏、浙江两省建设厅就牵头成立了蚕业联合统制委员会,该会在实业部指导下控制了两省蚕茧的收购,“凡丝茧商欲租行收茧者,须先向该会将拟收茧数,租开行名,收茧地点及范围,准备资本等,申报登记……”,委员会还准备从1934年春季起,“两省所产蚕种,概由两省建设厅统制管理,规定价格,分发各县,售给农民”,计划从种子、产量到销场、价格等方面进行全面统制(注: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工商访问局编辑《工商半月刊》第5卷第19号。)。此外,国民党政府还曾对火柴、桐油、猪鬃及部分矿产品进行统制。
国民党政府的统制政策改变了这些商品的运销方式,使钱庄基本丧失在这些商品贸易中的投资地位,投资环境的这种改变足以动摇钱庄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
同时国民党政府的金融政策(主要是指废两改元、法币政策)对钱业亦很不利。其实,废两改元对钱庄每年的赢利影响是不大的,就“两元”兑换利益而言,按惯例钱庄在一进一出间每万元可得3元左右的收入(注:王逢辛《废两改元之后钱庄业前途之展望》,《钱业月报》第12卷第11号。),考虑到钱庄每年的营业额一般都不大,再加上改元前汇划中银元公单越来越多,这种收益在其年利润中的比例当不会很大。废两改元之关键在于此后钱业丧失了对金融市场的控制能力,钱庄起源于混乱的货币制度,尽管汇划钱庄的生存并不依赖货币兑换,可它却利用旧货币制度控制着金融市场,银两本位,更为直观的是以九八规元为标准的记帐单位的废除,使钱庄利用两、元两种货币单位操纵市场盈亏、缓急的能力基本丧失,其在上海金融中之“霸主”地位亦随之失去。
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的金融改革总的看来是倾向银行的,钱庄业虽尽力夸大与银行的差别,以求制定单独的《钱庄法》未果,而被纳入银行业,这对于已不具任何优势的钱庄业来说,等于丧失了全力坚守的最后一块阵地。
4
从上海钱庄与华资银行四十年的共存情形来看,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社会的经济组织的兴衰更替给我们如下启示:
第一,传统与现代共存,代表传统社会经济特征的上海钱庄之所以能够在近代社会长期存在,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中的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现代银行业也发展起来。但是近代中国始终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经济共存的混合经济社会,反映到金融业上就是传统钱庄与现代银行的长期共存。
第二,尽管有传统与现代之分,但同属金融业,且西方银行来华必须适应中国独有的货币制度、工商业状况,这些都要依靠传统钱庄的支持。因此,双方存在着互相支持、利用的一面;银行业发展壮大起来以后,双方的矛盾亦随之尖锐。
第三,在传统与现代的兴替过程中,除社会经济近代化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外,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对经济进行改组,人为地推动其近代化进程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早在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就曾指出:“近数年来商业不振,恐慌屡见,推其原因,皆由于金融机关之不能敏活,而钱庄实属其咎。”从而制定《约束钱庄暂行章程》以加强对钱庄的管理(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55-457页。)。说明很早以前就有人注意到传统钱庄与现代经济的不适应,并着手推动钱庄的近代化。
第四,传统钱庄在整个近代社会能长期存在、一度在与银行的竞争中能保持不败的原因之一是与中小工商业的紧密联系。在银行业尚未为国人所熟悉、其触觉尚未深入到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以前,带有许多传统社会烙印的上海钱庄曾为上海地区经济发展作出过一定的历史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