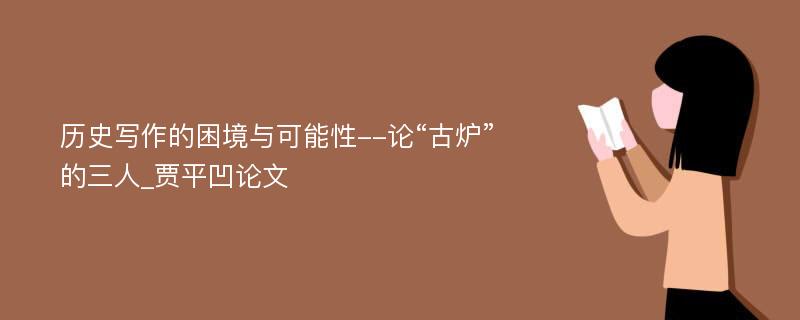
历史书写的困境和可能——《古炉》三人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的古典写作
杨庆祥:新世纪以来历史写作面临着两难之境,一是如程光炜所言,作家们尤其是一批比较重要的作家都意识到,必须写历史才能出大作品,而另外一方面,怎么去写历史,怎么去处理当代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记忆又是非常困难之事。包括莫言、王安忆、贾平凹、阎连科等作家这几年的创作实际上都在这种两难之境中挣扎。最近贾平凹的长篇《古炉》出版可能也是对此的一种回应。我想能不能就以这个作品为引子,讨论出当下长篇小说的历史书写问题。
我个人阅读《古炉》时感觉很碎片化,这种“碎”还不是现代主义的,而是像《金瓶梅》、《红楼梦》,是旧小说、笔记体小说中的写法。我把它命名为一种“现代的古典写作”。我认为从《废都》开始,贾平凹就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尝试,尤其是《秦腔》。这种写法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知道,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实际上是一个很“西方化”的概念,是像托尔斯泰式的,有主导性的情节、全能的叙事者,人物性格随着故事来成长,甚至可以说现代以来的小说都是“成长小说”或者“类成长小说”。但这种观念在贾平凹这里被完全改写了。贾平凹小说中也有“故事”,但这种“故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每一个人物身上发生的一连串小故事,故事和故事之间没有很多关系,就像说今天上街买东西,买完这个故事就结束了,没有一个连贯性的后续发展。在这种写法中,故事和人物是互为呈现的,这些小故事很容易把很多个人物带出来。你会发现,中国的古典长篇小说,像《红楼梦》、《金瓶梅》、《三国演义》等等,几百个人物很难用一条主线写下去,但西方小说,像《约翰·克里斯多夫》、《包法利夫人》,都是一个人为主,其他人物作陪衬,相比而言,我觉得中国传统小说的魅力就在于这种写法,哪怕是一个很次要的人物,也有他鲜活的魅力,有血有肉,有他的生命特征。这种绵密的小故事,我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很大的网,每个小网上都要打一个结,最后才能织成一张大网。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叙事方式。像格非就说,他到了三十岁以后才发现《红楼梦》的“好”,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你不能说《红楼梦》就一定比托尔斯泰好,但它是另外一种叙事方式,是不同于西方现代性小说叙事模式。我觉得贾平凹在尝试这样一种可能性,但也因此给我们的阅读带来了很多挑战。
杨晓帆:我很赞同师兄的判断,《古炉》中的确没有现代小说意义上的“故事”,一方面可以从你所说的贾平凹对古典小说技巧的继承来解释,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也与贾平凹对“写实”的追求有关。贾平凹在各种场合中都曾强调,他所追求的小说境界是真实和朴素,用细节去写日常生活。那么,怎样达到这种写实性呢?像你讲的《红楼梦》,里面有很重要的一块笔墨用来写器物,比如一小碟茶点,从瓷器的精致写到食物的造型,就是为了用细节去一点点堆砌出逼真的氛围。我觉得古典小说的美,就在于它能够在这种非常实、非常密集的写作中穿插出“虚”的艺术境界,这一点是贾平凹有意追求的。另外,陕西作家一直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贾平凹自己也承认,他很难、并且也不愿意再因袭这种旧的现实主义写法,因为这种写法要求作家有很强的历史和社会分析能力,能够在小说中安排一个史诗性的结构,而贾平凹更想展示生活中日常的、平淡的一面,所以他必须钻到细节中去。这种盯住鸡零狗碎的不遗余力,在写实效果上是很成功的,但它也会带来了新的问题。就像你所说的,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大多是成长小说,每个人物在出场时可能只有一个名字,一个身份,他的形象必然是在情节推进中慢慢丰富起来,但在贾平凹的小说中,人物的性格、甚至语调在一开篇就被固定下来。我读《古炉》时,会联想到现在非常流行的农村题材电视单元剧,每一集大概就是讲婆媳关系,或者左邻右舍的恩怨纠纷,这种电视剧的人物设定是非常明确的,作为视觉媒体,它的完成度非常高,演员一出场就已经从形象上限制了观众对角色的理解。《古炉》也是这样的,比如狗尿苔,他在开篇时是这种低贱、屈辱的形象,翻过几章他还是这样,再比如霸槽,人如其名,他的性格即使在干革命之后也没有什么变化,“文革”这么大的历史风波似乎没有在这些人身上留下痕迹。
杨庆祥:对,《古炉》里的人物在一开场就是被设定好的。这恰恰是我刚才讲的,它是一个反现代的叙事。现代小说中人物是成长的,性格是随时间推移的,如果用福斯特的观点,就是圆形人物,而像贾宝玉、西门庆都是扁形人物,一出场性格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一直是一种品质。我觉得这一点就区别了贾平凹的农村题材小说和以前像柳青等陕西作家的同类写作。比如赵树理,我觉得赵树理的写作还是在一个革命叙事或者现代历史的框架内,是成长小说,不管是小二黑,还是《三里湾》的人物,他们都是有变化的,有一个目的论的东西。而你会发现贾平凹没有目的论,他的写作是一种循环,《古炉》甚至在结构上也采用了春夏秋冬的四季轮回。
陈华积:刚才师兄关于小说是一张“网”的比喻很精彩,晓帆“单元剧”的比喻也很有意思。一部小说充斥着诸多的“细节”正如网上的一个个小结编织起来,而“小结”之间所呈现的封闭而开放的关系,这一点我觉得非常贴近贾平凹近年来的创作实验。考察贾平凹多年来创作观念的流变,实际上对我们深入了解贾平凹的创作也是很有帮助的。贾平凹在80年代初期已经非常注重写法问题,但那时他还受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成规的限制,80、81年左右他开始尝试突破传统的写法,结果受到“笔耕”文学组的批判,中途被迫转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路线来写作,《商州》系列作品很明显就是这种创作理念的“成功”实践。直到《浮躁》的出现,贾平凹才又开始有了新的突破,并逐渐形成比较成熟的文学观念,像《太白山笔记》里那种“狂放不羁”的写法与他以前的作品相比就显得很独特,而在《废都》的创作中,贾平凹这种自觉的更是自觉的文体创新形式和不断翻新的创作理念,甚至走向了极端化的地步。这种极端化叙事,恰似贾平凹一直在反叛你所说的西方现代小说。细细考察起来,贾平凹的创作理念一直以来都有他“变”与“不变”的实践,追求整体的、浑圆大气的创作气象却是贾平凹多年来不断地丰富、发展的核心创作理念,贾平凹在《废都》后记中就曾把他的创作观形象地比喻为如何去呈现出成一座大山,他不是要写山上的一草一木,而是要把大山那种混沌的整体呈现出来,一草一木自然包含于其中。他后来一直在实践这一点,反对理念式的写作,追求整体性,而不是精雕细刻。《古炉》中所体现出的叙事特征也确实有师兄所说的网状叙事,晓帆说的高密度“写实”等特征,我的理解也和你们的也差不多,我觉得贾平凹在这部新作中把他的叙事艺术更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同时把极端化的叙事与“汤汤水水”式的“混沌”叙事结合起来,形成一个非常奇特的文本。当然,这种散漫而混沌的故事对我们习惯于阅读那种逻辑性很强的故事而言,造成了很大的挑战。《古炉》“枝蔓”与“混沌”的叙事特征,在特定时段的封闭叙事中想要把众多人物性格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呈现出来,大概也是不容易做到的,不过,从最新创作的《古炉》来看,贾平凹还是没有突破一贯以来人物塑造的“概念化”问题。
杨庆祥:“混沌”不仅仅是结构上的,也表现在细节上,而且贾平凹的历史观念也是混沌的。中国的古典小说,《金瓶梅》、《红楼梦》,在阅读这些小说时我们会发现有很多闲笔,对于故事是没有用的,甚至有点卖弄才华的感觉,事无巨细地罗列出来,我觉得这恰恰是一种东方人的思维。它没有西方那种非常理性的、对生活非常强的分析能力,也没有西方那种发展的观念和对逻辑的强调,中国小说是混沌的,它认为历史本身就是杂乱的,各种东西,美、丑、善、恶交织在一起。我觉得贾平凹在这一点上是有自觉的历史意识的。
杨晓帆:关于贾平凹回到古典这种历史意识,我想到一点解释。贾平凹在80年代初没有形成自觉的文学观念,他后来说过,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文学思潮对他有很大的冲击,让他感到必须在形式感上作文章。先锋文学的形式感是从模仿西方那来的,事实上没有自己的内容,那么如何寻找另一条推进形式探索的道路呢?我觉得《废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已经很难去说它是一个什么题材的小说。贾平凹之前的创作是可以用题材来分析的,农村题材、改革题材、文化寻根题材,但从《废都》开始,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文体”意义上的小说。中国古典小说为什么有闲笔,就是因为古典小说观念不是后来我们所讲的那种主题性、虚构性的现代小说概念,它是个文体概念,会穿插诗歌、笔记,传统的“文”本身就是杂文、文章,小说的区别只不过在于它是“小道”、是比较世俗的“文”罢了。《废都》里就有这种传统的“文”的意识。而到了《秦腔》、《古炉》,我觉得,贾平凹的探索从“文体”进一步收缩到了“语体”。在《古炉》中,长篇小说的结构不是靠人物或故事去完成的,而是靠语体的混杂性来表现层次感,比如方言的运用、人物命名时涉及的风俗土语,外来革命小将黄生生操着一套革命话语,支书的话介于官方政治语汇和农民之间,风景描写则延续了贾平凹散文中的文人腔调等。以语体、文体的变换来结构长篇,这一点正好呼应了中国的诗学传统,我想,它也是贾平凹在艺术形式上要有所突破的必然趋向。
杨庆祥:你说的“语体”这一点是个发现,我想是不是可以用一个短语来概括贾平凹的写作,他是不断地“回到历史深处”去挖东西,他既是面向当下的,但同时他的语感、文体又是回到历史的,这种在现代性传统中的古典写作,恰恰才是贾平凹最强烈的现代感。现代感不是说用一种最流行的手法写一个现实题材,你会发现像狂飙突进运动、文艺复兴,都是用古典的形式来处理当下的题材,是以复古的方式去革新。其实早有评论家说贾平凹的作品是一种古典式的写作,我觉得恰恰是这种在现代的古典写作,才更具有现代感,这里面有一个悖论性的东西。
陈华积:对,贾平凹的写作有双重性,他跟现代以来的白话小说和古典小说都有区别。像《废都》虽然借鉴了很多《金瓶梅》的东西,包括写法、结构、人物的命运,但我觉得他恰恰是用这种古典的方式覆盖了他真正的创新,用这样一个很古旧的、一眼就能让人觉察的东西把主题隐蔽起来,在表层之下深藏着另一个创作动机,贾平凹的“狡黠”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双重性”的创作动机上。现在批评一谈到贾平凹作品中浓厚的古典气息,就很容易把古典和现代对立起来,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一种误解,“废都批判”时期所指认的“古典”,与你所说的“古典中的现AI写作作”,其意义指向是很不一样的。
地方性与世界性
杨庆祥:我觉得贾平凹在《废都》以后的写作,慢慢地开始固守在一个地方。《浮躁》里面,金狗是要走出去的,是一个进城的叙事,但是你会发现《古炉》里的人物都没有走出去,走出去的人要不就死了,要不就像霸槽走出去一圈后又回来,而且贾平凹没有写他走出去的生活。这种固定在某一个地域的写作,对贾平凹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历史意识到底是什么?
杨晓帆:我想,你所说的这种固守,一方面原因跟贾平凹进入中年写作的心态有关。他在《古炉》后记里面说写“文革”,动机是因为年纪大了,有种想要回家乡,想要把那个村庄已经消逝的风尘往事记录下来的冲动,是用个人记忆写国家记忆。这里好像有一种“回心”之力,不再喜欢青年时的扩张型写作。另一方面,这种固守又让我想到所谓地方性写作和世界性的关系问题。当代文学界现在有很多关于汉语写作、母语写作的讨论,像当年的先锋小说家格非在创作《人面桃花》时就特别强调要回到古典,但我觉得这种提倡,实际上有一个明确目的是要与世界文学对话,怎样用中国人自己的语言讲一个中国故事,初衷可嘉,但也容易陷入另一个陷阱,就像张艺谋的电影,是在讲述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风景,虽然强调地方性、民族性,但恰恰是默认了以西方为世界性标准后、由他者判定的中国的特殊性与边缘位置,这事实上阻断了、也放弃了中国文学可能提供一种带有普遍性价值的思考的主动性。相比而言,贾平凹所谓的回到某种地方性,恰恰没有这样一个对外证明自己的强烈焦虑,所以他的地方性、特殊性反而有更自觉的生命力,它可能自己生长成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东西。
杨庆祥:对,恰恰是因为贾平凹没有这种对话欲望,反而呈现出一种真正的世界性,而不像其他人始终摆脱不了一种他者的投射。他就是写他的村庄、写西京,并没有一种乞求获得世界认同的诉求。这里可以得出一个小结论,越是往后的写作,越是回到一个地方的写作,可能就越具有开放性和世界性。
陈华积:师兄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贾平凹的“退守”,反而使他获得了更强的“世界性”,这个说法姑且不论它是否能成立,不可否认的是,贾平凹笔下的“商州”故事,确实已在中国文坛上稳占一角。晓帆对贾平凹创作心态、创作心境的归纳很好,贾平凹固守“商州”一隅的写作方式,在八十年代已是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了,“商州”作为贾平凹重要的创作资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大致经历了认识上的三个层面吧: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贾平凹在年近六十以一种俯视人生的态度重新来观照“商州”这块血脉相连的地域时,他的这种“回归”已经不仅仅是地域意义上人情世态的观察,这里面更有某种“觉醒”的东西。我们看格非、张艺谋等人以变形的“他者化”的眼光来观察中国时,那种镜像式的机械和僵硬是很容易察觉到的,这一类型的创作更多的属于“自发”行为,而贾平凹在《古炉》中表现出的这种带有强烈生命俯照的意识,也与他前期的作品有很大的区别,更类似于某种认识上的“自觉”行为。“自发”与“自觉”不同,前者会有意识地回应外国人的眼光来讲述中国故事,而“自觉”则完全不考虑外界的评价或世界性的认同,他只是要把自己最核心的记忆的东西呈现出来。正如刚才师兄所说,贾平凹很自觉的把自己的创作与古典文学传统联系起来,才使的空间上的小村庄具备了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的世界性。
杨庆祥:的确如此。这几年关于汉语写作的国际性等话题非常热,但中国作家到底以什么样的形式参与世界文学,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我觉得格非的探索是一种形式,贾平凹又提供了另一种形式。跟八十年代一边倒的学西方比起来,这种趋向是很好的。
陈华积:贾平凹的这种“参与”形式,与年轻一代作家的参与形式确实有着较大的差别。我们会发现很多年轻一代的作家在观念、形式的模仿中亦步亦趋地与世界“接轨”,而贾平凹这一代与传统文化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作家,却是一直保持自身创作的某种“自足性”。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焦虑,他们因为急于走出国门,急于获得世界性认同,而摈弃自身的独特性,这也是前些年一些青年作家常遭诟病的地方,而从50后这批作家成熟的创作观来看,他们这种更带有“本土性”写作的“参与”世界的方式,无疑为我们的华语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本”。
杨庆祥:刚才提到《秦腔》,我突然想起莫言的《檀香刑》。莫言也一直在找一种很传统的语感,比如“猫腔”跟秦腔,都是一种腔调,一种民俗。写作永远不是一个普遍化的东西,我觉得没办法把美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做价值上的比较,标准应该是看小说是否在具体语境中真实地、或者用最好的形式呈现出它了的面貌。
回到历史深处
杨晓帆:正如师兄所说,《古炉》无论从结构还是故事上都是空间性的,甚至人物、乡村伦理也主要表现为一种常态性的存在,但《古炉》处理的历史时段是基层“文革”,它毕竟涉及如何理解中国的现当代史、特别是中国革命。相比“十七年”小说写农村的社会变革,像《三里湾》、《创业史》,无论是《古炉》还是《檀香刑》,似乎都缺少之前作品中那种对历史朝向“现代”之“变”的分析与把握。
杨庆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承认一点,无论是贾平凹还是莫言,他们在处理历史问题时都还有欠缺之处。涉及历史的写作必须有广度和深度,你会发现贾平凹把村庄、武斗都写得很好,但是这个村庄毕竟是一个大历史背景中的村庄,武斗毕竟涉及全国范围内的“文革”甚至是有世界性意义的东西,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理解与作家的气场和见识密切相关。如果今天我们讨论中国作家与西方作家的差距在哪里,我想可能就差在对事物的分析能力上。但后来我也反思自己的这个判断,如果我们用这一点来要求作家,是不是站在了另一个知识系统上。比如说我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立场上来要求他们进行分析,但贾平凹的历史观念可能是从中国土生土长的那种传统的混沌的时间观中发展来的,历史就是含糊的,我只能看到我的历史,两种意见谁对谁错,应该怎么处理,这是个矛盾。一方面我们要求作家有全景化的意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全景化是一个很虚幻的意识,没有谁能做到全知全能。
杨晓帆:对于这一点,我的想法也很矛盾。以前那种单一宏大叙事固然有遮蔽历史复杂性的一面,但现在所谓的新历史写作会不会走向历史虚无主义?不能否认,现在的确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总体性的历史终结了,怎样回溯历史,只能依赖个人视角和微观经验。《古炉》的结尾,霸槽等人被枪毙,狗尿苔等人成为行刑的看客,村庄又回到了常态,这让我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在《阿Q正传》的结尾,鲁迅写了一小段阿Q看见被狼追的幻觉,阿Q突然在临死前喊出了一声“救命”。我觉得鲁迅在写出了流氓无产者革命的荒诞,讽刺了“革命”、“革革命”的历史轮回之后,还是保留了一种积极的东西,他同情阿Q,他最后还是要让阿Q发出一声有生命自觉意识的呐喊。相比而言,《古炉》的结尾是死寂的,贾平凹似乎感到了鲁迅窥视到的黑暗和虚无,却缺少鲁迅式的反抗。
杨庆祥:鲁迅说“救救孩子”,接着还说他要“肩住黑暗的闸门”,鲁迅那种启蒙的东西,在贾平凹这里没有了。贾平凹不是个启蒙者,在贾平凹一代作家身上的确流露出某种历史虚无主义,或者说是对历史的绝望。这种绝望不仅是对历史的绝望,也是对自身能力的绝望。他们能否把握中国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废都》中的庄之蝶是一个对自己彻底绝望的人,他最后想寻找新生却倒在了火车站,因中风而成为了“废人”。再看《古炉》,最后活下来的是谁,是狗尿苔,是一个猥琐、卑鄙、无能、长不大的侏儒,另外是霸槽的儿子活下来了,而他是“恶”的象征,就像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作家似乎无法挣脱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中因袭的、鲁迅所说的那种黑暗。比如《古炉》结尾的“人血馒头”,虽然贾平凹说是真事,但我觉得它的确与鲁迅的《药》形成了一个对照。刚读时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重复的文本,鲁迅写过了,不新鲜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夸大一点,这也是一个隐喻,历史在不断地重复。
陈华积:贾平凹的“历史虚无感”与他对笔下人物“绝望”的处理,或许与贾平凹这代作家的“文革”创伤不无关系。贾平凹、王安忆、阎连科、莫言等这代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大多经历过政治的压迫和家庭的变故,如贾平凹的父亲原是一个中学教师,“文革”一来就成了“右派”,被关了起来;“文革”中“武斗”的荒诞与惨烈也极容易使这一代作家对历史产生“不信任感”,他们对“文革”的记忆无疑有着更为复杂的情感,而“文革”在贾平凹这代作家中本身也是一个“隐喻”。但是,“历史的虚无感”也未必是这代作家所共有的特征,王安忆的《文革“轶事”》就很难体察出这种“虚无”来,作者竭力摒弃描述“文革”冲突而把主要的笔触都集中于“亭子间”温情的儿女故事,却也是另外一种“文革”叙事。不可否认的是,贾平凹这一代作家的近期创作都在以不同方式回到“文革”,像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她琐碎的笔法其实和贾平凹《古炉》中写鸡零狗碎的村庄生活的叙述非常像,只不过写的是城市里的“文革”经历。所以这批作家也一直存在着“自身经验”与如何面对历史发言的问题。
杨庆祥:我现在读《古炉》、《启蒙时代》这样的作品,其实有点“隔”,我想一个人经历过历史和没有经历过历史有很大的差别。像我们80年代出生的人,我们身上没有历史,像“文革”、“大跃进”都没有亲历,和贾平凹这批作家相比,我们的历史是很“轻”的。所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通过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我们更年轻的作家应该该怎么办?我们有必要为自己制造、或者寻找一个历史感。这很难,我们靠什么去建构历史感?这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没有具体事件。所以你看现在有更年轻的作家写工厂、写底层,马上就火了,因为他至少有生活经验,有实感。
陈华积:80后的作家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历史,但是却有自身的历史。对于这一点是不能苛求的。所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学也正是在这样相互交错的发展中而呈现出其丰富的创作面貌来。
杨晓帆:80后作家缺少历史感,这一点我觉得在其他代际作家身上也存在吧。像余华八十年代最早发表的《星星》等作品,他当时就很老实地表示,因为自己没有插过队、没有当过工人,没有上一代人的坎坷,所以只能写这种“一点点”的小情调。像他后来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不是他故意创新,而是他只有这样写才顺手。因此,当这些作家人过中年,站到了上一代作家的历史位置上,开始觉得自己有责任去书写历史,他们缺乏历史实感的软肋自然暴露出来。作为80后的读者,我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其实特别希望能从中认识历史,这种认识既包括事实层面,也包括价值层面,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作品的确能在事实层面给我们展示许多历史的细节,打开那些常识判断遮蔽的东西,但在价值层面却无法给我们提供一种有力的呈现,甚至是混乱的、缺失的。
杨庆祥:我个人认为,从读者角度讲的确存在你说的事实和价值两个层面,但从作家角度来说,也要考虑道德主义的悬置。小说应该有道德,但不应该有道德主义。一个真正好的小说要怎样通过历史事实呈现作家的价值判断,我觉得还是要通过文体、语感、故事、描写等手段来完成。所以我们可以对这一代中国作家求全责备,但要注意从哪个方面去谈,我们不能说作家没有历史判断,而是要问,作家是不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手段把价值判断放到了小说的叙事里面。作家肯定有价值判断,但他们没有很好地把它融到作品中去,又不愿意扮演一个道德说教者,必然会面临创作的瓶颈。
杨晓帆:对,其实《古炉》中的人物还是寄托了贾平凹对道德伦理的思考。像善人讲天命,讲人应该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其实讲的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在“文革”中被破坏了,让人性恶的东西滋生蔓延,而当下也缺乏这种秩序。贾平凹说现在政府倡导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是“谁”来建设却成了问题,农村留不住人了。他其实是带着对当下现实的价值判断在写历史。
杨庆祥:你提到“天命”,我觉得这一点在贾平凹的创作中非常重要。“天”,本来在中国人的概念里就是非常含糊的东西,它不像上帝那么明确,但又无处不在,是一个很混沌的神。中国人在“五四”之后一直在寻找一个东西来安置自己,比如你讲的秩序,我们发现现在的问题是,每个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也是产生历史虚无感的原因。比如在《红楼梦》里有强烈的秩序感,《金瓶梅》开篇就谈善恶报应、因果报应,而且这种观念是被古代人普遍接受的,但现在我们找不到一个普遍认同的东西。
陈华积:“天命”这些东西在贾平凹的创作里可能更多情况下是一种噱头,作为线索把故事串起来,制造一种阅读的空间感。比如《古炉》中的狗尿苔有一种特殊技能,一有大事发生,就能闻到特殊的气味,其实构成了一种推动情节的设置。这种设置在《高老庄》中也出现过,里面讲到一个叫“龙湫”的很神秘的地方,传说没有人到过那里,唯一到过的人后来变疯了,而且他总是在疯癫地叙述听到神秘的声音后,村子里就会有怪事发生,这类“噱头”非常吸引人。这种神秘叙事,在《浮躁》的“看山狗”、《高老庄》的“龙湫”以后,似乎成为了贾平凹一种必不可少的一直叙事方式。
杨庆祥:狗尿苔闻气味这一点,如果从叙事线索来讲,它是必需的,它起到了把一个长篇串起来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从《废都》以来贾平凹一直在尝试这类写法,确实又显得重复和拙劣。而且你会发现,狗尿苔为什么能闻到气味,后来发生了什么,小说里都没有写。
陈华积:《古炉》是非常强地体现出了贾平凹在《废都》时提出的创作观念,就是要处理他常说的“实”与“虚”的关系,他要把一个东西做的很实,再来传达某种神韵。这一点是他从传统书画里体悟出来的。比如他的早期作品《腊月正月》,当时贾平凹已经写出了改革题材方面的作品《小月前传》、《鸡窝洼人家》,都是非常正面的写改革,写农村新的经济形势对古老农耕传统观念的冲击,但在《腊月正月》中,他跳出了这种写法,他从反面人物来写经济改革,以理解同情的态度来写韩玄子这样一个人物的时代悲剧性,从这个小说中就可以看到,贾平凹在运用正反对照手法时对传统书画艺术的借鉴。所以在《古炉》里我们会读到很多枝蔓,一个人物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可能跟下一个故事毫无关联,就像一棵大树,上面有很多枝枝丫丫,任它发展,用很繁茂细密的树冠把主干覆盖起来。《古炉》从这一点上说,可能是迄今为止对“枝蔓感”实现的最好的一部艺术作品。
杨庆祥:但是现在贾平凹在《古炉》里给我的感觉是没有让我们看到这样一棵大树,看到的都是枝枝蔓蔓。他的叙述、人物设置、或者历史观念没有完成他的创作意图,他成功地把我们拉近看枝蔓,却没能把我们再推开到看整体的位置。
陈华积:对。这也是这部作品在创作理念与创作实践上带给我们的一种落差。贾平凹想要给读者呈现一棵筋络分明的大树或是一座浑然一体的大山,但结果却是让读者看到密密麻麻的枝叶,而主干意识却极为薄弱,这也是贾平凹所一直努力的先“实”后“虚”,以“实”写“虚”的一种书画创作观嫁接到文学创作的实践,从目前的效果来看,显然是差强人意的,至少贾平凹的这种历史“分寸感”就没有把握好。从贾平凹的创作观这一层面来看,贾平凹过于追求他的创作理念,而恰恰忽视了“形而上”的深入把握,这也跟你前面所提到的贾平凹对历史题材的处理乏力是一样的道理。贾平凹更多地给我们呈现出“形而下”的丰富性,而没有“形而上”的抽象性,如何平衡“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关系,也是《古炉》带给我的一点思考。
杨晓帆:我突然想到一个词,贾平凹的“恋物癖”。《古炉》里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比如狗尿苔的气味,蚕婆的剪纸,霸槽挖出的太岁,很容易让我在阅读时陷入对这些小细节的把玩中,虽然它们的确起到设置悬念、推动情节等作用,但当它们大面积出现时,的确会分散对小说主干的把握。比较《红楼梦》,通灵宝玉也是“物”,同样兼具虚实的本事,但它自始至终是跟小说主题拧在一起的。
杨庆祥:这有一定道理。像贾平凹在《废都》里写女人的脚、鞋,写得非常细。比如《废都》中的奶牛,作为一个象征物很有意思,但跟通灵宝玉比较起来又显得太单薄。《古炉》中那个太岁,背后本来应该有更多的故事,但它的起源终结都没有交代。
陈华积:“物象”与“事象”的运用,具体还是要看作品中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王安忆曾说过,作品本身蕴藏着自身表达的形式,作家所要做的就是把这种形式呈现出来。如果我们认同王安忆这种表述方式的话,《废都》中庄之蝶对女人小脚迷恋的这种病态,恰好是作品所要表现的形式,这其实也不应该成为“诟病”《废都》的重大缺陷之一。“恋物癖”作为一个问题出现于贾平凹的作品中,我觉得更多的是贾平凹对“物象”的泛滥使用,而又没有更好的创新。如贾平凹在《远山野情》中写过太岁的故事,在《古炉》中又被横向移植了过来。《古炉》其实汇聚了许多他以前作品中的内容和想法,包括一些细节,这也是一个多产作家所不能避免的自我重复。
杨庆祥: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当主人公气场足够强大时,还是能把小说撑起来的,像金狗、庄之蝶、刘高兴都是生命力很旺盛的人,但《古炉》中的狗尿苔很弱,与其说他是小说的主人公,不如说他是一个观察者。这一点相比贾平凹以前的创作,的确是创新。总而言之,当下的历史写作面临着种种的困境和可能,当然这是一个大问题,仅仅凭借一个文本、一个作家可能还不足以展开,我想随着新的文本的出现,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想必可以更深入、全面一些。
标签:贾平凹论文; 古炉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论文; 红楼梦论文; 金瓶梅论文; 废都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小说论文; 浮躁论文; 秦腔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