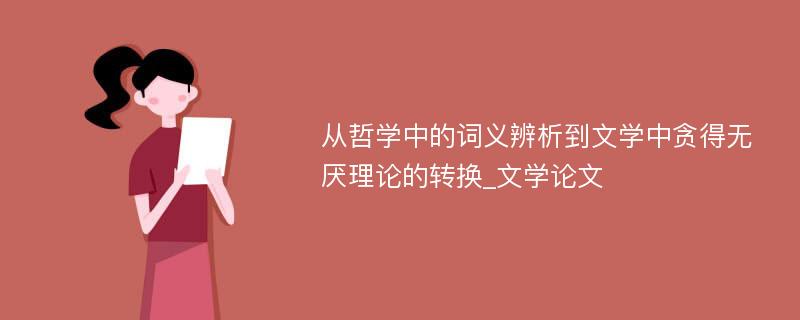
从哲学上的言意之辨到文学上的言不尽意论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言不尽意论文,哲学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言不尽意论是我国古代文论一个重要命题,它与我国古代哲学中的言意之辨有紧密的联系,但也有很大的不同。本文试从哲学、文学的角度来探讨古代哲学和文学中言和意的关系,并落脚于文学创作。本文认为言不尽意论是在对语言表达功能充分肯定的基础上深化了对言意问题的认识,我国古代对言意关系的认识由三部分构成;一是言以达意论;二是言不尽意论;三是言外之意论。由言以达意、言不尽意到言外之意,既承认了言和意的一致性,又指出了它们的矛盾与冲突,同时也找到了解决冲突的途径和方法,这样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言意论。
一
言不尽意论是言意问题的深化认识,人们对言意问题的重视主要是由言不尽意引发的。文学创作中言不尽意论的提出是立足于文学创作自身去探讨创作规律的。但是,在我国古代文论中言不尽意论的提出除了文学的因素外,主要受到了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因为言不尽意的提出首先是在哲学领域中而不是在文学范围内,《周易》、老庄、玄学都不同程度地论述了言意关系。哲学的分析加深了对言意的认识和理解,为文学理论中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供了理论参考和认识方法。为了帮助理解古代文论中的言不尽意论,也为了区分哲学问题和文学问题的不同,在此先简析一下我国古代哲学中的言不尽意论。
《周易》从认识论出发认为语言的表达功能是有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系辞上》)言不尽意的原因在于《易经》大意的深奥和《易经》形式的特殊。《易》通天理,《易》之“意”深奥玄妙,《易》是由“象”构成的。“言”只是对“象”的一种描述、解释,由“言”到“象”再到“意”相互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从此意义上讲言是不能尽意的,而卦象和爻辞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仅从言方面看,它是不能尽意的。《周易》中的言不尽意涉及到语言表达功能问题,但它并不否定语言的作用,它论述的中心是象而不是言。言不尽意是为了突出“立象以尽意”。
老庄所代表的道家主要从本体论出发谈言意问题,在道论的前提下论言意。道具有玄远、精微、博大、渊深、恍惚等特点,它以无为本,道的特征决定了它不可能与任何具体事物相对称,“言”作为人类的表意符号系统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广泛的应用性,但和道相比它仍然是一种具体的存在,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尽道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大道不称,大辨不言”(《庄子·齐物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庄子·知北游》)对于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二十五章)所以庄子才认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所不能论,意所不能察者,不期精粗也”。(《庄子·秋水》)“世之所贵道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庄子·天道》)显然老庄的言不尽意主要指道之难尽,是为了突出道的特征而不是否定语言的功能,他们认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指出了语言功能的有限性。老庄还在道统有无的基础上指出言意关系中意为本、言为用,言意为二,它们间是一种工具和目的关系,《齐物论》中庄子指出“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里指出了语言不等于语言表达,为了达意需借助于言,但不能把言当作意,理会意时不能局限于言。这显然是告诉人们怎样正确地处理言意关系,既要利用语言但又不局限于语言,所以老庄一方面主张言者物之粗,言不尽意,要“忘言”,另一方面却积极地利用语言。老庄的言不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论是相互联系的,有言不尽意才有得意忘言,它们的提出是为了突出道的地位和作用,它们对语言的态度是积极的,对言意关系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这不仅影响了《庄子》一书语言特色的形成,也影响了后来的文学创作及理论。
魏晋玄学的言意论同它的其他哲学命题一样是在对前人主要是《周易》、老庄的理解、发挥中形成的,是对《周易》、老庄所论的综合和发展,与《周易》相通的是提出言不尽意时从认识论出发注意“立象以尽意”;与老庄相通的是从本体论出发提出言不尽意,并突出意不可尽和得意忘言。玄学的言不尽意论主要在《荀粲传》、《周易例略·明象》、《言尽意论》以及《世说新语》的有关章节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弼的《明象》。在《老子指略》中王弼以“无”释“道”,认为言不尽“无”,因为最高规定性的“无”很难以某一具体存在来完整地解释它,“名之不能当,称之不能既”。“言之者失其常,名之者离其真”。《明象》中王弼指出:①“言生于象,象生于意”,从发生认识出发说明言是为达意而存在的,意是借言以生存的;②“言者所以明象”,“象者所以存意”,“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从本体论出发指出言意之间前者为体后者为本,二者是统一的但是不同的,所以得意可以忘言。王弼所论显然是对《周易》、老庄的综合。欧阳建的《言尽言论》表面上看与言不尽意论是相对的,若把它和《明象》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它的论点是停留在《明象》的第一层意思上。这样我们可以说玄学的言意之辨是言和意间本体关系的论辨而不是言尽意与言不尽意间的论辨,玄学言意之辨的主要论点是言不尽意论。这从当时人的玄言清谈等方面也可以看出,如《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庚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也,非赋所能尽;若无意也,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有意”说明言能达意,“无意”说明言不尽意。“有意无意间”说明当时人们对言意的认识正是言能达意但言不尽意。
老庄、玄学的言不尽意论立足点在于“意”,他们看到了语言的作用也指出了语言表达的局限性。这对于在文学创作和理论中去认识言意关系有很大的启发性。
二
在古代文论中言不尽意论的提出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与走向成熟的创作理论开始对文学创作进行深入思考是一致的,言不尽意论是同期创作理论中一个主要论题。陆机《文赋》的中心论题是讨论言、意、物的关系,《文心雕龙》、《诗品》中也都有关于言不尽意的论述。文学创作中的言不尽意论与哲学命题中的言不尽意是相通的。哲学上的言不尽意主要指“道”“无”等无法用对等的语言形式把它们完整清楚地表达出来;文学上的言不尽意指出了创作中的情、志、意、理、趣、思等内心世界及心理活动无法用语言具体生动完整地表达出来。但是哲学和文学对言不尽意的认识是不等同的。哲学所论重“意”,文学创作中的言不尽意不仅重“意”也重“言”,以及言和意相互间的关系,言不尽意不仅在意之难尽,还在于言的不尽意性。同时文学创作理论中因为对言不尽意的充分认识,使它能够超越于言不尽意而积极地去追求言外之意。这样既可以把言不尽意看做文学创作中一种局限,更应该把言不尽意视为文学创作的一种特征。在哲学的阐释中是不允许有什么言外之意的,它要求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哲学思辨把问题说清楚,虽然《庄子》中的寓言及禅宗里的故事往往寓理于故事之中,给读者充分地思考玩味的余地,但这只能说是它们借用了文学表达方法,而不能说明哲学论述中有意去追求言外之意。
陆机在《文赋》中论述了对创作中言不尽意的认识。陆机首先从创作的感受、体验等方面谈到作者在创作中因言不尽意而产生的困惑。“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蠢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陆机从三方面指出言不尽意的可能:①从对前人作品的分析中理会到“放言遣辞”的变化多样;②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感知“意不称物,文不逮意”。③从创作的具体过程认为“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指出创作有成法而无定法,在每一部作品的具体创作中言和意的组合都是一次全新的构建。这样不仅创作中存在言不尽意,而且对创作规律变化的认识也不能以言尽之。陆机的言不尽意论主要指“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亦即观物之妙不能了然于心,了然于心却不能了然于手。陆机对言不尽意的认识是与对创作过程的分析结合在一起的。首先,他认为创作是一种创新活动,是“无”中生有,“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愈深”。这说明文学创作是作家对生活独特感受、独特发现的独特表现。一部作品的诞生相对于别人、相对于作者已有之作都是一种从无生有;同时,文学创作是感之于心、明之于心、发之于心的,寸心中可容滂沛之博大,那么就要求尺素中函绵邈之深远;再者,创作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现象:在语言表述中总觉得在语言所能表述之外有更多的语言所不能表达的东西,在对玄妙事理、复杂情感的体悟中越想会感到它越丰富深刻。这样的文学创作当然会出现言不尽意了。陆机此处的对言不尽意的分析显然受到老庄、玄学有无论的影响。其次,陆机着重分析了创作活动中复杂微妙的心理空间、心理活动过程,语言表达的多种要求和限制。文学创作一方面“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抱景者咸叩,怀响者毕弹”。而另一方面语言表达却有应、和、悲、雅、艳等标准,有顺当、简赅、创新、佳句等要求,在言和意之间又存在不一致性,要离方遁圆去穷形尽相有很大的困难。再次,陆机从“达变识次”的角度分析创作中“感应之会”的难以把握。“变次”指创作中的一般规律,“感会”指创作中的灵感,这些都是可感、可知、可遇而不可强求的,有“言泉流于唇齿”的时候,也有“操末以续颠,谬玄黄之秩序”,“豁若涸流”的时候。陆机在此指出言不尽意在创作总体中是存在的,但也并不是处处都存在。这相对前面对言不尽意的“质”的分析,可以说是“量”的分析。针对创作中言不尽意的困惑,陆机最后感叹到文学创作“虽此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谈到言不尽意。《序志》中说:“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虽复轻采毛发,深及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远,辞所不载,迹不胜数矣”。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对文学创作的讨论是相当全面深刻的。刘勰从个人写作感受认识到仍有“似近而远”“不可胜数”的“曲意密源”为“辞所不载”。刘勰在《神思》中指出:“方其搦翰、气倍辞前,及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受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议在咫尺而思隔山河”。刘勰和陆机一样是从对创作过程的分析中论述言不尽意。他认为作者创作时在没有进入语言文字表达前的构思时往往会进入情绪高涨、气盛神飞、灵感突至、思维敏捷的境界,有一种气倍辞前的强烈创作冲动,即“神思方运,万途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这是指创作蕴积达到充分饱和状态。可是这种强烈的创作冲动在作者苦心经营形成文字以后,却是半折心始,所见所想表达出来的只是部分而不是全部,这对于创作者来说不能不是一大遗憾!而造成这种遗憾的原因主要是言不尽意。刘勰从言意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来谈言不尽意,首先,“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意在借语言表达之前是一种流体的动态的散状的隐形的存在,“翻空而易奇”;言却是实在的受约定俗成制约的可知可见的依靠一定形声的语汇和特定的语法规则而存在的,“征实而难巧”。以实而难巧去尽空而易奇当然是比较困难的。其次,在创作过程中文学胚胎的形成和降生经过“意受于思,言受于意”的承递转化过程,在思——意——言的转化过程中,思主要指创作的想象活动,它是自由的、多变的、丰富的,可以“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可以“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心超形外、心形不一。意指文学意象,它是神与物游的结晶,是情与景、事与理的统一。思——意——言的转换并不是一一对等的替换,而是相当复杂的,“密则无际、疏则千里”,即有时妙语连珠思、意、言很好地完成了转化,有时想象的野马奔驰到很远很远却仍然找不到一片碧草蓝天的绿洲,或有强烈的创作激情却感到无从下手,或若思冥想与见之于言的却相差遥远。“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言意间这种不对等的、不确定的转换关系使言不尽意成为可能。这说明言不尽意是文学创作的本性所决定的,它反映了文学创作的特征。文学创作是为了以言达意,而在创作的始终都隐藏着言不尽意的可能,这便成为文学创作中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在文学创作中“象”的地位和作用尤其突出,文学创作的思维被称为形象思维,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被称为文学形象。文学创作中的立象过程大概由观象、取象、立象、成象等部分构成。观物取象是创作的基本方法,《诗经》比兴手法的大量使用就是为了立象以尽意,对此,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宋代朱熹《答何叔景》、明代张蔚然《西园诗尘》、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等都有论述。《诗经》比兴手法的运用是一种不自觉的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后来意境、境界的提出则是对立象以尽意的有意追求。因此在古代文学创作和理论中非常重视景、物、境,刘勰的《物色》可以算作物象论的代表。同期梁简文帝《答张缵示集书》、钟嵘《诗品序》都有相关论述,以后的论家就更多了。
从陆机、刘勰等对创作过程的分析看,言不尽意已是当时创作理论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他们已自觉地从创作中的困惑入手去探寻言以达意背后的深层问题。他们立足文学创作自身而不是从哲学抽象来谈言不尽意;他们已认识到言不尽意是文学创作中实实在在的问题。他们从对创作过程分析中形成的关于言不尽意的基本认识便构成古代文论中言不尽意论的基本点。
三
言外之意论是言意论的一部分,也可以看作言不尽意论的延伸和发展。它的提出为言不尽意找到了合理的解决途径,即利用寓言外之意于言内之意,扩展有限的语言表达能力,使之在所达之意的基础上更富有深层含义。刘勰等人对此已有约略的认识,但真正明确提出“意外之意”的则是在隋唐及其以后。
刘勰在《隐秀》中指出:“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秀指言和意和谐一致,文通字顺,人情物理尽现于寥寥数语之中;隐指以含蓄委婉、意在言外之辞把文情心术曲折地表达出来,隐以“复意为工”,强调“文外之重旨”。“重旨”、“复意”就是言内之意和言外之意的统一,所以隐的特点是“义主文外”,有“隐”的作品才可以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刘勰《文心雕龙》中有意地以味论文,用味中味和味之不厌之味来指代作品的言内之意和言外之意。《文心雕龙》中至少有二十处提到味,其中如《体性》“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附会》:“若流绪失宗,辞味必乱”,“道味相附,悬绪自接”。《物色》:“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宗经》:“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限秀》:“深文隐蔚,余味曲包”。《明诗》:“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等等。刘勰借感官上的只可品评而无法尽说的滋味来论文章的只可意会而不可尽达的情意,说明了言外之意的存在。
钟嵘从比兴来论言外之意,他认为“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这里不但从新的角度来认识“兴”,同时把意之有余、味之无极视为一种创作境界。
隋唐以来的作家理论家已经在言不尽意论的基础上集中、明确地把言外之意作为创作中的言意问题加以论述。
第一,创作审美标准的言外之意。言不尽意存在于具体的创作中,与之相应作家在创作中有意追求言外之意。司空图以“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与李生论诗书》)“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与极浦书》),从韵、味、景、象等方面来论言外之意,并认为那种“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不知所以神而自神”、“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的言外之意才是作品的最高境界,由此司空图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视为创作的最高品格。宋代把“言有尽而意无穷”作为创作目标。梅尧臣说:“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其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含不尽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欧阳修《六一诗话》)姜夔从含蓄的角度提出“若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文矣’”。(《白石道人诗话》)严羽从兴趣出发认为盛唐诗的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迫,如空中之音,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唐宋时代已明确了言外之意在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明代以来,如徐渭《南词叙录》、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袁中道《淡成集序》、《吴表海先生诗序》、李维桢《来使君诗序》、李渔《闲情偶记》、梁廷楠《曲话》、刘熙载《艺概》、王夫之《古诗评选》,以及冒春荣、吴雷发、王士祯、吴乔、郑板桥、况周颐、章学诚等人都不同程度地论述了诗、文、词、曲中的言外之意。
第二,以有无言外之意作为评判作品的标准。文学评判标准是与创作标准相应对的,所以隋唐以来许多评论者在评判作品时都以有无言外之意为标准。皎然《诗式》中以“两重意”论曹植的“高台多悲风”。以四重意论《古诗》中的“行行重行行”。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评韦应物、柳宗元的创作“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 ”张戒《岁寒堂诗话》认为“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等句“其词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贵也”。魏庆之《诗人玉屑》中认为《长恨歌》等“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吴可《藏海诗话》评《贫女》诗“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在隋唐以来的许多论诗评文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例证。
第三,文学欣赏中的言外之意。创作的追求决定了欣赏的追求,评判、欣赏又反作用于创作。因此人们在欣赏作品时自然地把言不尽意的因素考虑进去,在理会言内之意时更寻求对言外之意的理解,欣赏活动中重视心领神会,而不注重咬文嚼字。《六一诗话》中欧阳修认为“作者得之于心,鉴者会之于意,殆难指陈以为言也。”这说明作者的心得难以言尽,只好存于言内显于言外,读者欣赏时也只能把语言视为工具,力求在语言之外去体味作者的本意,因此欧阳修指出作者与读者之间”不相语而意相知”(《书梅圣俞稿后》)。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中说“文学之佳胜,正贵读者之自得,如饮食甘旨,衣服轻暖,衣且食者之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欣赏作品“得意文中,会心言外”。一般说来欣赏作品时对字面意义的理解往往分歧较少,对言外之意的理解往往会溶进更多的个人因素,而这些溶进去的个人因素也许正是读者的独得。因此言外之意需要读者的心领神会,同时也为读者的心领神会提供了可能,而真正的文学创作就应该为读者留下余地。言外之意的存在正反映了文学创作的特征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