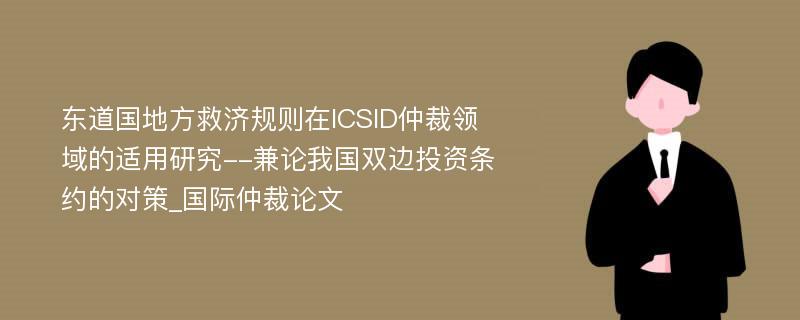
东道国当地救济规则在ICSID仲裁领域的运用研究——兼论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应对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道国论文,条约论文,中国论文,规则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205(2015)03-0179-(011) 一、国际法上的东道国当地救济 东道国当地救济(Local Remedies)通常包括司法救济与行政救济,意指东道国的司法机构或行政机构依据东道国的程序法与实体法来解决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端。[1]22-42作为一项古老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受到东道国侵害的外国人在未用尽东道国法律对其仍然适用的所有救济手段之前,不能要求外交保护,或进行包括启动外国法院诉讼或国际仲裁在内的国际求偿。[2]817 在国际法上,除非另有约定,“用尽”一词通常包含两方面要求: 一方面,应当使用当地所有可适用的行政与司法救济程序。换言之,申请方须依照东道国法律规章将争端诉诸有管辖权的机关,即行政、司法机关所组成的完整救济体系。当行政机关的救济不具有终局性时,则需诉诸司法机关,或者在没有行政救济规定的情况下直接诉诸司法机关。 另一方面,应当充分使用国内法律体系中所有可适用的诉讼程序措施。首先,国内法上一切必要的程序性救济方法和手段,包括传唤证人出庭作证、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等,都应当被充分而正确地使用。其次,申请人应当就执行对其有利的当地终审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执行;否则,亦不能认定用尽当地救济。 (一)当地救济被视为已经用尽 东道国当地救济在何种情形下被视为“用尽”,美国法学会(American Law Institute)《对外关系法》(第二次重述)第208条认为,在以下任一情形中外国人可豁免于用尽当地救济:(1)当地救济显然无法达到程序正义要求;(2)考虑到在实质相同的案件中已有该国最高有权机关作出的一个或数个不利决定,求助当地救济将是徒劳的;(3)同一侵害行为主要构成对外国人国籍国的直接损害,该国主张自己的独立的主要的请求①。也有学者认为,下列情形无需用尽当地救济或可视为已用尽当地救济:(1)倘若没有可资利用的救济方法,则未用尽当地救济不构成国际求偿的障碍;(2)倘若可资利用之救济方法不适合于求偿的内容,或实际上已表明或清楚地确定当地救济无法产生实效,则勿需用尽当地救济,譬如东道国最高法院是在行政机关控制下,而遭控诉之行为乃行政机关行为;或者控诉所针对的决定是依据明确的国内法规定作出的,因而较高级别的法院不可能推翻决定或判决给付损害赔偿;抑或在通常情形下损害是政府以政府的地位所做行为的结果,此时未用尽当地救济,并不妨碍国际求偿的提出。[1]258-59 笔者认为,应当辩证地看待上述西方国家学者的观点。以一国法制之不健全或司法体制之不完备为由作为适用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例外,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为保护本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蔑视他国主权,为逃避适用发展中国家的法律找借口而已,其真实目的是根本不愿意利用当地救济。[3]352-53例如,对于美国法学会《对外关系法》(第二次重述)所认为的视为用尽当地救济的三个例外,第一个例外不外乎是早已遭到发展中国家反对的国际标准的翻版,毕竟各国之法院系统与诉讼程序并不相同,以本国特有之制度作为衡量他国诉讼程序完善与否的标准显然是不合理的,国内救济应当首先依据国内法的法定程序。对于第二个例外,每一个案件案情迥异,不可能会完全一致,且一国之政策、法律或规章并非一成不变,以过往求助当地救济无效的陈例来否定现今无需遵从当地救济规则,显然有失偏颇。对于第三个例外,同一侵害行为构成对外国人母国的直接损害,通常是由于该国在受侵害的公司中拥有直接的重大利益②;1952年The Anglo-Iranian Oil Co.(United Kingdom v.Iran)case案中,英国政府就代表英伊石油公司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并宣告伊朗政府有义务将伊朗与英伊公司之间的争议交付仲裁庭解决,或请求国际法院判决伊朗实行国有化法律违反了国际法和违反伊朗根据1933年协议所承担的义务。但是,以资本输出国作为原告、以东道国政府作为被告的做法已经遭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事实上,纵然国家在公司中拥有主要利益,但这毕竟是以公司的名义进行的投资活动,不能因此改变公司的法人实体身份,因而国家的利益只能通过公司得到保护,也就不存在独立的请求权。 那么,究竟何种情形可视为当地救济以及被用尽?笔者认为,其一,有权主管机关作出的最终决定,此时已不存在上诉机会。其二,出现拒绝司法(Denial of Justice)的情形。在实践中,拒绝司法的概念在过去往往被用作外国政府代表其国民对所声称的损害进行求偿的修饰性借口(Rhetorical Excuse)。[4]17因此,对“拒绝司法”的界定是极为必要的。从广义上而言,拒绝司法包括了国家责任的整个领域,并适用于国家对外国人不当行为的所有类型;而在狭义上,拒绝司法则仅指国家对获得法院救济的拒绝或者法院未能对案件作出判决。[5]9在当代,拒绝司法不仅涉及传统的程序不公,通常也包括实体缺陷。例如,依据Freeman的观点,稳定的国际实践以及绝大多数法律权威承认不仅公然的程序不当和缺陷,且裁决本身存在的严重实体缺陷,均可成为外交抗议的正当理由。[6]404这也就是说,拒绝司法包括程序和实体两方面因素。至于何为实体方面的“不公决定”(Unjust Decision),则通常是指:(a)决定显然并歧视性地违反了所涉国家的法律;(b)决定不合理地悖离了世界法律体系中公认的正义原则;(c)决定涉及了国家对条约的违反。[6]11 (二)当地救济规则已被放弃 作为国家属地管辖权的体现,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在被确定已为东道国所放弃时,则可以不适用该规则。2006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文草案》肯定了国家放弃用尽当地救济的要求,构成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例外情形③。关于当地救济规则已被放弃,最大的问题在于放弃的形式和对放弃与否的判断。通常说来,明示放弃当地救济要求是有效的,许多仲裁协议中都载有放弃条款。此种放弃可以通过国家之间的协定事先或事后明确规定,亦可通过东道国政府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协议明确规定。除了明示放弃,法律上的放弃还有推定放弃,能否对当地救济规则进行推定放弃,即当地救济规则的默示放弃问题,在国际投资实践中存在争议,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将在下文展开。 二、ICSID机制下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适用 (一)默示不等于放弃:传统国际法与《华盛顿公约》 1.国际法院ELSI案与国际法委员会《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 国际法院在1989年的Case Concerning Elettronica Sicula S.p.A.(ELSI)(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Italy)案④中,对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适用作出了解释。在该案中,国际法院认为,条约对一项重要的习惯国际法原则未作规定,并不意味着该原则不能得到适用,因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法则不能被默示地放弃⑤。国际法院的这一裁决,秉承了国际法的传统理念,即争议解决条款中未规定当地救济规则通常并不构成对该规则的默示放弃(Implied Waiver)。[1]250-51与此相契合的是,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也正致力于将用尽当地救济规则这一习惯国际法公约化。国际法委员会于1996年通过了《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Draft Article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的一读,其中第22条规定了只有当外国人用尽了他可利用的所有有效的当地救济后仍未获得应有的公平合理的待遇时,才能认为东道国违反了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才会产生相应的国际责任⑥。这也就是说,有效的当地救济措施未用尽前,并不存在东道国违反国际义务的情形,外国投资者母国无权行使外交保护。尽管2001年11月国际法委员会第53届会议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删除了一读中第22条的规定,但仍保留了第44条关于国家责任在“如果争议适用用尽当地救济规则而可利用的有效当地未用尽”的情况下不会产生⑦。由此,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已然成为一项被各国普遍认可的重要国际法原则,作为各国公认的原则其适用并不取决于预先约定。因而,投资条约中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阙如,并不构成对这一规则的默示放弃。换言之,要构成对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放弃,需要有关国家的明确表示,抑或在条约中作出明确的放弃。 2.《华盛顿公约》第26条与ICSID实践 《华盛顿公约》第26条规定:“除非另有规定,双方同意根据本公约交付仲裁,应视为同意排除任何其他救济方法而交付上述仲裁。缔约国可以要求以用尽该国行政或司法救济作为其同意根据本公约交付仲裁的条件。”据此,《公约》颠覆了传统国际法中默示不构成放弃的观念,规定了成员国未明确要求将争议诉诸ICSID前需要用尽当地救济,则视为成员国放弃了有关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要求。虽然在《公约》起草过程中,来自拉丁美洲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坚持维持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传统国际法要求,但终究未能挡住来自法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当地救济的优先适用未能作为诉诸ICSID的强制性前提条件,而只是在国家明确表示适用时方可适用。[7]58,96,7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执行董事会在《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的报告》中也肯定了这一“仲裁作为排他性救济”(Arbitration as Exclusive Remedy)的立场:假设一个国家与一个投资者同意将争议交付仲裁,同时并未保留寻求其他救济或要求先用尽其他救济的权利,则双方同意将仲裁作为排他性的救济方式。这一解释规则体现在《公约》第26条第1句中。为了澄清这一条款的目的并非在于更改关于用尽当地救济的国际法规则,第2句明确认可国家要求优先用尽当地救济的权利。[8]528-29 虽然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执行董事会的报告澄清了《公约》第26条的目的并不在于更改默示不构成对用尽当地救济的放弃,但实践中东道国却极易于忽略明示要求适用用尽当地救济规则这一步骤,从而导致失却当地救济这一保护方式。在Amco Asia Corp.v.Republic of Indonesia案的撤销程序(in the Annulment Proceedings)⑧中,对于针对军方和警察人员行为国内救济的用尽问题,印度尼西亚首先主张,有关军队的警察人员在1980年3月31日至4月1日的行为并不构成印度尼西亚须负责任的国际不法行为。在印尼看来,仅当印尼法律对此类行为没有提供充分的救济时,它才承担国际责任。但是印尼法律不论对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提供了此类救济。倘若Amco公司自行决定不去利用那些救济,则此种放弃不应损及印尼。印尼进一步辩称,仲裁庭裁定Amco可不遵循用尽国内救济这一一般国际法规则事先在印尼法律中寻求赔偿,而将有关军方和警察人员行为导致其损害的赔偿主张直接提交ICSID仲裁庭,仲裁庭明显超越了权限。尽管仲裁庭在裁决中对不要求Amco用尽国内救济并未附具任何理由,但专门委员会认为,裁决的这一部分不能基于此种考虑而被撤销。这是因为,承认ICSID管辖权,而不依《公约》第26条保留事先用尽国内救济的权利以作为同意提交ICSID仲裁的条件,由此视为印尼放弃了此项权利⑨。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表明,接受ICSID管辖而未明确要求将争议诉诸ICSID前须用尽当地救济,则视为成员国放弃了《公约》第26条项下有关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要求。 (二)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附期限问题 从双边投资条约的实践来看,诸多国家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都在规定用尽当地救济规则时附加一定的期限,这一期限从3个月到24个月不等;在所附期限之内,倘若外国投资者寻求当地救济无果或不满意此种救济结果,则可寻求ICSID仲裁等其他国际救济途径。显然,此种附期限的规定是对东道国用尽当地救济权利的一个限制,对东道国的司法与行政机构在处理争端的效率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外国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此种附期限的规定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这一对东道国权利的限制,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投资者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寻求东道国当地救济的希望落空后,还能够及时寻求国际层面的救济。但这一规定引发的问题是,附期限的用尽当地救济规则所规定的时间,是指争端发生后所经过的时间,抑或经东道国当地救济程序所消耗的时间?换言之,外国投资者是否可以不经过东道国当地救济程序,而仅仅是待所附期限届满后直接寻求国际救济? 在Emilio Agustín Maffezini v.The Kingdom of Spain案⑩中,ICSID仲裁庭认为,《双边投资条约》第10条第2款规定争端“应当提交”(shall be submitted,será sometida)至东道国有管辖权的法庭,第3款a项继而规定倘若法庭在18个月内未能对争端的实质问题做出裁定,抑或裁定虽作出但双方争端仍继续存在,则经任一方当事人申请,争端“可以提交”(maybe submitted,podrá ser sometida)国际仲裁。这一措辞表明,《双边投资条约》的缔结双方——阿根廷和西班牙,都想要给予各自法庭机会以使在规定的18个月期间内、争端诉诸仲裁之前来解决争端。申请方声称此非第10条第2款的原本意思,而是在18个月期限后,不论国内法庭程序的结果如何,任一方当事人仍可自由将案件提请国际仲裁。对此,仲裁庭认为申请方忽视了两个重要考量:其一,无论国内法庭程序的结果如何,当事人在18个月期间届满后都可自由寻求国际仲裁,这是正确的,但仅在他们不满意国内法庭裁决时他们才可能会这样做。更进一步地,倘若他们被说服国际仲裁庭亦会作出与国内法庭同样的裁决,他们肯定不会这么做。在这个意义上,缔约方法庭被给予机会去证明双边投资条约所保证的国际义务。考虑到条约的措辞,这是缔约国被推断为希冀为它们的法庭所保留的角色,尽管只能在受到限制的期间内。其二,申请方关于第10条第2款的解释剥夺了该条款的任何意义,其结果与普遍接受的条约解释原则不相符,特别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的条约解释原则(11)。据此,如果申请方只有上述理由,则仲裁庭将会拒绝本案管辖权。但是,鉴于申请方还提出其有权依据双边投资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直接将争端提请仲裁的事实,仲裁庭最终依据最惠国条款一致同意管辖本案(12)。这一案例表明,ICSID仲裁庭肯定了附期限的当地救济规则,当条约规定了附期限的用尽当地救济规则时,当事人需要在该期限内寻求当地救济,而非仅是待该期限届满就直接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 (三)用尽当地救济规则与终局性要求 1.The Loewen案I CSID机制下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适用,有时候还会涉及属于实体性的终局性要求的放弃问题。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在性质上究竟是属于程序性抑或实体性仍存在争议。在学理上,J.E.S.Fawcett教授认为当行为违反当地法而非国际法时,用尽当地救济规则起到实体规则的作用,而当行为违反当地法以及国际协议或习惯国际法时,用尽当地救济规则起到程序规则的作用。但是,在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远未停止,由此引发了ICSID仲裁庭在管辖权决定上关于界定用尽当地救济规则与终局性要求之间关系的问题。ICSID仲裁庭在The Loewen Group,Inc.and Raymond L.Loewen v.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一案(13)中,就认为当地救济不等同于终局性要求(Finality Requirement),东道国放弃了程序性的当地救济要求,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属于实体性的终局性要求。 2.对The Loewen案的评论 仲裁庭的裁决可归结为,如果外国投资者所遭受的损害来自东道国国内法院审判本身时,适用终局性要求,即使投资条约放弃了用尽当地救济规则,仍然要满足终局裁决的要求;而如果投资者遭受了除东道国国内法院审判之外的其他损害,诉诸东道国法院寻求救济时遭遇拒绝司法,则投资条约放弃了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就同时放弃了终局性要求。 尽管NAFTA已明确规定其决定对其他案件不具有先例效力(14),The Loewen案的影响将是深远的。The Loewen案的裁决作出后,NAFTA专家小组在短时间内召集,寻找其他仲裁庭如何裁断相似问题的作法,并致力于对自身仲裁庭先前不当作法的解释。[9]857对于The Loewen案的裁决,持异议者不在少数。有学者从以下四个方面对The Loewen案的裁决作出了批评:其一,终局性与拒绝司法在理论上并没有不同之处;其二,当地救济包括了本案仲裁庭所谓的终局性要求;其三,只有当非国家的个人行为损害外国投资者时,拒绝司法才是实体性的;在其他情形下,拒绝司法都是程序性(15);其四,NAFTA第1121条放弃了当地救济规则与终局性要求。[10]1131按照该学者的观点,在国际法上,没有任何证据或先例证明在拒绝司法问题与国家的其他国际法责任之间,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适用存在不同。仲裁庭对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理解完全忽视了NAFTA第1121条的效力,至少在涉及东道国拒绝司法的国际赔偿请求中,申请方依据第1121条作出放弃国内救济的表示后,却依然要受到国内裁决终局性要求的限制,否则仲裁庭将会以此为由驳回申请方的请求,那么NAFTA第1121条的存在还有何实际意义可言?事实上,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包括了对裁决的终局性要求,在东道国拒绝司法的国际投资争端案件中,没有必要对用尽当地救济规则与裁决的终局性要求作出区分,否则将会造成逻辑的混乱。 有学者直言,首先,NAFTA并未设定用尽当地救济的义务,至少未将用尽当地救济作为寻求第11章之仲裁的程序性障碍。NAFTA第1121(1)(b)条和第1121(2)(b)条只是要求外国投资者在启动NAFTA仲裁之前,放弃启动或继续国内诉讼程序的权利。其次,现如今,评论家已经澄清了NAFTA草案并未要求用尽当地救济规则。这正是Loewen所坚持的论争,即第1121条只是规定了放弃当地救济的义务,而非用尽当地救济的义务。但是,仲裁庭未认可Loewen的辩称,反而是接受了美国关于终局性要求不同于当地救济规则的观点。这无疑将使仲裁庭成为国内法院的上诉机构。[11]428-30 尽管学者们对The Loewen案进行批评的理由不同,但都表明了同样的立场,即仲裁庭对用尽当地救济规则与终局性要求的适用存在偏颇。笔者认为,除却上述论断,仲裁庭的裁决引出了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终局性要求的适用范围。仲裁庭最终认定NAFTA第1121条并未放弃这个实质性要求:申请方声称因司法行为而导致对国际法的违反时这个司法行为应当是东道国的终局司法行为。实际上,这意味着在声称国家违反国际法前,申请方必须用尽一国司法系统内的所有救济。虽然如此,仲裁庭仍保留了以下可能性,即申请方声称的违法行为并非产生于司法行为,则第1121条仍可以有其他的解释。在探讨第1121条具有何种其他解释之前,需要考虑仲裁庭在The Loewen案中划定的界限。首先,仲裁庭的观点是,因司法行为导致的对国际法的违反要求用尽当地救济,还是仅仅因司法行为导致的拒绝司法要求用尽当地救济?美国政府可能认为The Loewen案的决定应当限制在依据NAFTA第1105条因司法行为导致的拒绝司法要求用尽当地救济。但Carie Jones认为,The Loewen案的仲裁庭更倾向于NAFTA第11章项下的申请方寻求因司法行为导致的损害赔偿时,该司法行为必须是终局的司法行为,不论该司法行为是拒绝司法、歧视,抑或征收等。事实上,The Loewen案的裁决文本不仅仅是将其规则限制在拒绝司法的诉求,而是适用于基于司法行为的任何诉求。例如,裁决载明:“对于因司法行为导致对国际法违反的申请,第1121条并未放弃其寻求当地救济的义务。”[12]10这也就是说,终局性要求不仅适用于拒绝司法,还适用于违悖公平公正待遇、最惠国待遇、征收或国有化等行为。 第二个问题是,双边投资条约中的“岔路口条款”将名不副实。岔路口条款主要是规定在争端产生后,外国投资者应当在东道国国内救济与国际救济之间选择其一,且一俟选择作出,即为终局。按照岔路口条款,外国投资者选择了当地救济,则不论国内法院或行政机构作出何种决定,都不能再寻求国际救济。但是,The Loewen案仲裁庭的意见表明,外国投资者选择国内救济程序后,认为东道国法院裁决或行政机构的决定存在不公正之处,便可以遭受东道国法院不公待遇为由,以东道国作为被申请方将争端诉诸国际仲裁庭。如此,外国投资者既利用了国内救济,亦寻求了国际救济,从而使得双边投资条约所规定的岔路口条款形同虚设。 三、中国BITs中的当地救济规则及其完善建议 (一)中国BITs中的用尽当地救济规定 早期中国对外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基本坚持了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大多数双边投资条约都规定了发生争端时,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在争议发生之日起一定时间内协商不成则可向东道国的行政机关申诉或向法院提起诉讼,若是有关征收或国有化补偿款项的争端,在以上程序均无法解决时可提起国际仲裁(16)。1990年之后,中国对适用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立场出现了转变,一些双边投资条约并未规定用尽当地救济规则,而是可以将争端径行提交国际仲裁解决,这些争端通常仅限于因国有化和征收补偿款额产生的争端。例如1992年中国-哈萨克斯坦BIT直接规定了“缔约一方与缔约另一方投资者之间任何有关征收补偿数额的争议可提交仲裁庭”(17),而不再强制要求先行将争端交由国内法院或行政法庭。1996年中国-沙特阿拉伯BIT亦作了相似规定(18)。1997年以后,中国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对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基本立场是:当地救济分为司法救济和行政(复议)救济,司法救济与国际仲裁择一终局,而行政救济则作为国际仲裁的前置程序。这就是说,允许外国投资者将其与东道国政府的投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但通常要求用尽东道国国内的行政复议程序。这又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当局要求用尽行政复议程序(19)。另一种情形是中国单方面要求在一定期限内须首先进行国内行政复议程序(20)。这一规定只是要求在中国进行投资的德国投资者遵循,而中国在德国进行投资的投资者无需经行政复议程序即可将争端交付ICSID解决。这一类型的规定,多出现在中国与发达国家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中,例如2001年中国-荷兰BIT以及2004年中国-拉脱维亚BIT(21)等。 (二)用尽当地救济规则:中国的取舍问题 《华盛顿公约》第26条及ICSID仲裁实践,将传统国际法中的“放弃需明示”转变为“要求需明示”,即接受ICSID管辖而未明示要求在将争议提交ICSID前须用尽当地救济,则视为成员国放弃了公约第26条项下有关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要求。这一举措已形成了对用尽当地救济规则适用上的不利,发达国家的学者更进一步质疑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对发展中国家的有效保护作用。Christoph H Schreuer教授就认为东道国坚持用尽当地救济优先于ICSID仲裁是否可起到任何裨益,是存在疑问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提交ICSID仲裁前寻求当地救济对投资者而言是时间与资金的浪费。[13]395在实践中,国际仲裁庭也并不期望投资者在诉诸当地救济时耗费的大量不合理的时间。[14]267例如在将用尽当地救济作为违悖公正与公平待遇的一个条件问题上,ICSID专门委员会在Helnan v.Egypt案中撤销了仲裁庭的裁决,因为该仲裁庭认可如下作法:埃及有管辖权的行政法庭就管理合同的终止作出决定,随后投资者对该决定进行的挑战是为了证明条约诉求实质有效的要求。专门委员会指出,仲裁庭的此种作法带来的后果将是严重的;专门委员会认为,诉诸当地救济的要求,将会产生申请方无权将未获得公正与公平待遇的事由直接以条约争议诉诸国际仲裁的结果,且在投资者面临代表国家执行的决定时的应对方式上注入了一种难以接受的不确定性程度(An Unacceptable Level of Uncertainty),并取代了ICSID公约允许诉诸仲裁的明确规则(22)。在另一相关案件——Chevron v.Ecuador案,申请方提出,在东道国国内法院遭受的异乎寻常的延迟,使得美国违反了厄瓜多尔-美国BIT第2条待遇条款(23)。这表明,对于申请人而言,国内救济往往是繁冗而耗时的。 笔者认为,上述学者的观点以及ICSID和UNCITRAL特别仲裁庭的实践,往往倾向于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权利与利益,这与在当前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的申请方往往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不无关系。对于这些观点及作法是否代表了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在适用上的趋势,笔者首先不认同这些观点及作法本身,亦不赞同其代表着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在适用上的未来。针对Christoph H Schreuer教授的观点,倘若投资者认为东道国国内救济的结果是合理的,且认为国际仲裁庭极有可能作出相似的决定,那么投资者可能就不会继续将争端诉诸国际仲裁,这完全符合投资者追求成本与时间效益的惯常作法。特别地,东道国的行政复议等程序基本是免费的,投资者无需在此投入更多资金。对于国际仲裁庭当前的实践,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说,坚持用尽当地救济规则更能维护国家主权,这一立场也特别符合中国当前及未来较长时间内的境况。 第一个境况是,中国日趋成为一个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以及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一个以资本输入为主的国家现实。这也就意味着,较之中国对外投资企业与东道国政府间可能产生之争端,外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间可能发生之争端在数量及标的额上远甚于前者,因而当前的主要关注点应更多地放在在华外国投资上。由此,将外资企业在华产生的争端首先交由中国国内行政或司法机关解决自是顺理成章,也是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 第二个境况是当前中国外资审批制度与操作均存缺陷。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逐步意识到优惠政策对吸引外资的激励作用具有局限性,并从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1993年开始,采取一种渐进式的方法,有步骤、有计划地取消存在的某些不合理的限制与优惠措施,在综合考虑对民族工业与国内市场的适度保护的基础上,逐渐地实现外资企业全面的、实质的国民待遇。但是,由于现行外资审批制度存在诸多缺陷,例如在立法上,审批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互不协调;且在操作上多元审批、分级管理的统一性与协调性不足,往往使得在实践中地方外资主管机关为追求政绩而在审批项目时承诺外商或外商投资企业特殊的待遇,而一俟承诺无法履行,争端的产生在所难免。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中国加大了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力度,外资审批进一步放权至地方政府(24),由此潜在的外资与东道国政府间的争端将逐步增多。同时,因外资审批而导致的争端还包括外资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隐名投资、股东侵权、因继承、承包、设定质押等导致的争端。[15]在这一大环境下,倘若放弃当地救济要求,则外国投资者可将争端直接提请国际仲裁,中国便将面临着数量巨大的被诉案件。而事实上,这一类案件通过中国国内行政或司法程序,完全可以获得有效的解决;特别是引起争端的行为本身违反了中国相关法律规章时,国内行政或司法机构有能力定纷止争,且在熟悉中国法律规章方面不会逊色于国际仲裁庭。因此,坚持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对中国而言总体上是裨益颇深的。 (三)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在中国的具体适用问题 1.当地救济的例外问题 2002年10月28日,中国代表薛捍勤女士在第57届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第54届会议的报告”议题(外交保护和委员会的工作)的发言在关于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及其例外情况问题上指出:特别报告员分别在条款草案(25)的第10条和第14条对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及其例外情况作出了规范。中国代表团认为,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作为提起外交保护的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已被广泛接受,特别报告员关于该条的建议草案也未在委员会引起较大的争议,但对于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例外情况,国际法委员会则应谨慎行事,以使用尽当地救济与其例外情况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如果不当地扩大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例外情况的适用范围,将对外国人所在国的国内管辖权构成侵害,某些情况下还会导致两国因管辖权发生冲突,进而可能影响国家间关系(26)。基于此,中国代表团认为,关于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例外情况应符合明确的条件,例外情况的适用应相对确定,例如当地救济显然无效或不当拖延,被告国(不法行为国)放弃了用尽当地救济的要求等(27)。这一发言,代表了中国在用尽当地救济规则适用例外上的立场,表明了中国反对不当地扩大了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例外情形的适用范围,主张应当明确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例外情形。至于何种情形可认为是已用尽了当地救济,笔者在前文中已作阐释,兹不赘述。 2.当地救济的前置程序——磋商 在中外双边投资条约的缔结中,通常要求投资争端在诉诸东道国司法或国际救济前,应当先由当事双方进行磋商、友好协商、和解等(以下统一合称为“磋商”)(28)。中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在投资者与缔约一方争端解决问题上,基本都规定了如上述中国-西班牙BIT中规定的磋商条款,且对磋商了一定的期限,通常为6个月。ICSID仲裁实践已经对附期限的磋商进行了界定。在Murphy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Company International v.Republic of Ecuador案(29)中,ICSID仲裁庭批判了先前的案例——Ronald S.Lauder v.Czech Republic案(30)和SGS SociétéGénérale de Surveillance S.A.v.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案(31),认为厄瓜多尔-美国BIT第6条关于当事人应当先在6个月内通过磋商和谈判来解决争端的规定,并非申请方或其他仲裁庭所声称的只是一个当事方可以选择或不选择适用的程序规则或目录和程序规则(Directory and Procedural Rule);相反,它构成了对申请方的一个必要的强制性要求,申请方在依据ICSID规则提交仲裁请求前必须遵守。鉴于申请方并未满足这一要求,仲裁庭裁断其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16]8在Burlington Resources Inc.v.Ecuador案(32)中,仲裁庭作出了与Murphy案相似的裁断。仲裁庭认为,等候期间(Waiting-Period)要求的目的只有在违反条约的声明作出时才有效,6个月的磋商期间从声明作出时开始计算。本案中,仲裁庭认为申请方在将争端提交仲裁前并未作出关于东道国违反条约的声明,因而裁断该争端不能提交仲裁。[16]8 从ICISD仲裁实践可知,附期限的磋商是强制性的,未符合这一规定而直接将争端诉诸仲裁将导致被驳回的结果。鉴于中国对外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均载有附期限的磋商条款,无论是寻求当地救济,抑或通过岔路口条款直接选择将争端提交国际仲裁,外国投资者应当首先通过磋商寻求争端的友好解决,倘若投资争端自书面请求通知之日起6个月内未能友好解决的,投资者方可寻求当地救济或国际救济。 3.行政复议救济问题 当前中国对外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允许外国投资者将其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端交付国际仲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用尽东道国的国内行政复议程序。规定用尽行政复议程序而非司法程序,原因在于有关部门提出,中国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后经过一定期限未上诉的判决及经两审终审后的判决在中国已经成为终局判决,即有关争议在中国的法律框架内就已得到最终解决;倘若在终审判决后仍可将争议提交ICSID调解或仲裁,就意味着中国法院判决需要接受国际调解或仲裁庭的审查,将使中国司法审判的独立性、严肃性以及终局性受到挑战。[17]326在政治上,这也不利于维护国家主权的尊严。而司法救济与行政复议救济虽然都属于当地救济的范畴,但二者的性质与效力却有所区别。在中国,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救济,行政复议机关与被申请复议人同属于行政机关系统(33),行政复议决定在性质上仍为行政决定,与被申请复议的性质行为并没有性质上的区别。在效力上,行政复议决定通常不具有终局法律效力,相对人对行政复议不服的,仍可提起行政诉讼(34)。而由于法院行使的是国家审判权,可对包括行政复议在内的各种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判,对行政争议具有最终决定权,其地位和效力显然高于行政复议。 笔者认为,有关在国内进行司法救济后仍可以将争端提交ICSID调解或仲裁则会损害中国司法的独立性与严肃性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中国政府于1990年2月9日签署《华盛顿公约》,且公约于1993年2月6日对中国生效,这意味着中国自愿承担该公约所要求的义务并对自身的管辖权(甚至是审判权)进行一定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这些限制并不会构成对中国主权的损害。其次,倘若中国的司法机关能够给予案件公正的审判,或者通过ICSID仲裁庭做出与中国法院相同或相似的裁决,则不仅表明了中国承担《华盛顿公约》要求的义务,同时彰显了中国对外国投资的保护。国内司法救济与国际仲裁只能择一,外国投资者出于不熟悉中国立法与司法状况的缘由,可能就会放弃国内救济,而这兴许并非其本意之体现。 尽管不认同未将司法救济作为ICSID仲裁前置程序的观点,但笔者认为将行政复议程序作为国际仲裁的必经程序仍然是可取的。由于投资条约争端发生在中国政府或各级地方政府与外国投资者之间,倘若在中国政府尚未在中国法律框架内做出最终决定前就提交ICSID仲裁庭,随后ICSID仲裁庭作出的裁决在中国寻求承认与执行又需要中国政府的接受,这显然不利于中国政府。因此,将用尽行政复议程序作为把争端提交ICSID仲裁的前置条件,一方面可使中国政府有机会在争端提交ICSID仲裁前矫正政府行政部门或下级政府行政部门的不当行政行为,另一方面则可尽量将争端在中国国内解决,减少不必要的国际仲裁程序。 关于行政复议救济在中国的适用问题,笔者认为还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其一,二级复议问题。我国《行政复议法》规定,对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依照本法的规定作出最终裁决(35)。这一规定虽然并不构成类似于德国、西班牙等国规定的二级复议前置制度,但却属于二级复议的选择。在二级复议情形中,倘若只经过一级行政复议而未经过二级行政复议的申请,在一级复议决定生效后,能否视为已用尽了当地救济?对此,中国法律付之阙如。 其二,因抽象行政行为而引起的国际投资争端问题。当前,中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尚未健全,现有的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根据处于混乱状态,即不同审查根据之间的关系缺乏逻辑上的统一性,导致学理解释上的尴尬和司法实践中的混乱,以及各个审查根据所包含的标准不清晰给司法实践带来很大困难,影响了对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权利的保护。[18]司法审查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了一些抽象行政行为在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上无法审查。《行政复议法》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但仍有两部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复议之外:其一是国务院制定的包括行政法规在内的所有抽象行政行为;其二是所有规章(36)。尽管已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了行政复议范围,但《行政复议法》的制度安排仍然存在缺陷(37)。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法院依职权能够审查的抽象行政行为,与行政复议相比,扩大到了案件所涉及到的单个的规章,但对行政法规同样不具有司法审查权(38)。由此,倘若国际投资争端是由于行政法规等抽象行为引起的,则外国投资者无法在中国国内救济,用尽当地救济规则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4.当地救济的附期限问题 Christoph H Schreuer教授质疑东道国坚持用尽当地救济的另一理由在于,有些双边投资条约在规定当地救济时附以严格的时间限制,表明对待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犹豫特征。[13]395如前所述,中国对外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中有些确实是要求外国投资者将争端提交国际仲裁庭前应当在一定期限内提交行政复议程序,即在规定当地救济时附以时间限制。那么,这一规定是否表明了东道国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因而坚持用尽当地救济对东道国并无助益呢? 笔者以为,双边投资条约在规定当地救济时附以严格的时间限制,并不表明对待用尽当地救济规则时的犹豫。相反,规定用尽当地救济规则是赋予外国投资者从国内司法机关获得救济的权利,毕竟相关争端是由东道国政府之行为引起的,国内法律规章或救济程序兴许就能解决这些争端;同时,为了避免东道国当地救济耗时过长,使得投资者的相关损失加剧,对当地救济的适用施以严格的时间限制,不仅敦促东道国国内司法机关尽快解决争端,促进东道国司法及行政机构的效率,亦解除了投资者的后顾之忧,投资者仍可继续将争端提请ICSID仲裁解决。 就中国对外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而言,将争端诉诸ICSID前应当先进行国内行政复议程序,且存在用尽行政复议程序和在一定期限内先行利用行政复议程序两种情形。然而,这两种情形所带来的具体结果是不同的,仅规定用尽行政复议程序的情形所引致的结果更加不确定。一方面,从申请复议到作出复议决定需要长达数月的时间。用尽国内行政复议程序,一般应当理解为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以出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这一行为为标志。依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60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30日(39)。从《行政复议法》所规定的时间来看,自申请行政复议到行政复议决定的作出,在无需转送其他行政机构作出行政复议时,其期间约为2个月;倘若还需要对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加以审查,则可能需要延长期限;若是还要送达其他机构作出决定,则总的期间可以达到3个月。此外,甚至有可能行政机关收到复议申请书后却没有作出答复。由此可知,用尽行政复议程序的期限长且结果不确定,这对投资争端的解决是极为不利的。另一方面,双边投资条约通常只规定外国投资者具有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而未规定其可提起行政诉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外国投资者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但当复议机关对外国投资者的复议不作出或不及时作出决定时,外国投资者仍可能会无所适从。因此,为了使投资争端不至于久拖不决,无论是经由复议再到诉讼的案件,抑或只经过行政诉讼审理的案件,都应当明文规定一个具体的时间限制。因此,双边投资条约在规定当地救济时附以一个时间限制,不仅给予了东道国充分行使管辖权的机会,同时消除了外国投资者的后顾之忧,不对投资者向ICSID寻求救济设置不必要之障碍。 5.当地救济的终局性问题 中国BITs中同样载有类似于NAFTA第1105条关于“公正和公平待遇”、“充分的、持续的保护和安全”、“不得采取任何随意的或歧视性的措施”等规定,譬如2003年中国-德国BIT就规定了缔约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的投资应享受持续的保护和安全;缔约一方不得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投资的管理、维持、使用、享有和处分采取任何随意的或歧视性的措施(40);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的境内的投资应始终享受公平与公正的待遇(41)。这些条款的存在,为中国今后出现类似于前述The Loewen案提供了可能性,即外国投资者与中国企业发生普通合同争议并经中国法院裁断后,外国投资者可能会认为中国法院判决不公,进而认为中国未遵守双边投资条约中的“公正和公平待遇”、“充分的、持续的保护和安全”、“不得采取任何随意的或歧视性的措施”等规定,遂以中国政府为被申请方,向ICSID提请仲裁。 尽管学界对The Loewen案的决定持异议,认为The Loewen案无疑是在错误的方向上迈出的一步,留下独立的终局性要求和更多的不确定性。[10]1137但既然存在重蹈The Loewen案覆辙的可能性,自然应当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在双边投资条约中明确把针对东道国国内法院判决本身的是非问题排除于国际仲裁的范围之外,不失为最佳方案。次佳方案是参照The Loewen案仲裁庭的意见,在双边投资条约中规定把当地救济规则与终局性要求分离开来,双边投资条约只能够放弃属于程序性的当地救济规则,而不能放弃属于实体性的终局性要求。[19]225换言之,双边投资条约放弃了当地救济规则,倘若投资者认为是法院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损害了其利益,则可直接依据双边投资条约提请仲裁;而投资者认为损害其利益的是法院的裁决,则投资者在启动国际仲裁程序前仍需要先寻求可获得上诉程序,以满足终局性要求。 四、结论 作为一项古老的习惯国际法规则,东道国当地救济规则在以ICSID机制为主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领域中的适用上突破了传统国际法的适用惯例。在默示适用问题上,ICSID公约颠覆了传统国际法中默示不构成放弃的观念,规定了成员国未明确要求将争议诉诸ICSID前需要用尽当地救济,则视为成员国放弃了有关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要求。在用尽当地救济规则与终局性要求上,ICSID仲裁庭在Loewen案中的裁决可归结为,倘若外国投资者所遭受的损害来自东道国国内法院审判本身时,适用终局性要求,即使投资条约放弃了用尽当地救济规则,仍然要满足终局裁决的要求;而如果投资者遭受了除东道国国内法院审判之外的其他损害,诉诸东道国法院寻求救济时遭遇拒绝司法,则投资条约放弃了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就同时放弃了终局性要求。 1997年后中国双边投资条约对待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基本立场是:当地救济分为司法救济和行政(复议)救济,司法救济与国际仲裁择一终局,而行政救济则作为国际仲裁的前置程序。总体而言,坚持用尽当地救济规则对中国是有利的,但在具体适用问题上,应当注意下述问题:(1)在当地救济的例外问题上,反对不当扩大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例外情形的适用范围,应当明确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例外情形;(2)在当地救济前置程序问题上,规定无论是寻求当地救济抑或通过岔路口条款直接选择将争端提交国际仲裁,外国投资者应当首先通过磋商寻求争端的友好解决;(3)在行政复议救济问题上,将行政复议程序作为国际仲裁的必经程序仍然是可取的;(4)在附期限问题上,双边投资条约在规定当地救济时附以严格的时间限制,并不表明对待用尽当地救济规则时的犹豫立场;(5)在终局性问题上,明确把针对东道国国内法院判决本身的是非问题排除于国际仲裁的范围之外。 注释: ①Restatement(Second)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208(1965). ②例如,由国家管理、投资或经营的国家控股公司(State-Controlling Company),在公司的全部资本中,国家资本股本占较高比例,并且公司由国家实际或相对控制。 ③Art.15(e)of Draft Articles on Diplomatic Protection. ④I.C.J.Report 1989,15-121. ⑤Id.,42. ⑥When the conduct of a State has created a situation no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result required of it by an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 concerning the treatment to be accorded to aliens,whether natural or juridical persons,but the obligation allows that this or an equivalent result may nevertheless be achieved by subsequent conduct of the State,there is a breach of the obligation only if the aliens concerned have exhausted the effective local remedies available to them without obtaining the treatment called for by the obligation or,where that is not possible,an equivalent treatment.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违约是指一国违反其对另一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即东道国违反它对投资者母国所应承担的义务,而非东道国违反其对外国投资者所应承担的国际义务。 ⑦The responsibility of a State may not be invoked if:(b)The claim is one to which the rule of 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 applies and any available and effective local remedy has not been exhausted. ⑧Amco Asia Corp.v.Republic of Indonesia,ICSID Case No.ARB/81/1,Ad hoc Committee Decision on the Application for Annulment of May 16,1986,25 I.L.M.1439(1986). ⑨Id.,1453-54. ⑩Emilio Agustín Maffezini v.The Kingdom of Spain,ICSID Case No.ARB/97/7,Decision of the Tribunal on Objections to Jurisdiction of January 25,2000,40 I.L.M.1129(2001). (11)Emilio Agustín Maffezini v.The Kingdom of Spain,ICSID Case No.ARB/97/7,Decision of the Tribunal on Objections to Jurisdiction of January 25,2000,40 I.L.M.1135(2001)1129. (12)Id.,1435-39. (13)ICSID Case No.ARB(AF)/98/3,Award of June 26,2003. (14)Art.1136(1)of NAFTA. (15)此种观点认为,倘若损害时源于个人行为,则不会立即产生国家责任,要求引发国家责任就必须用尽当地救济。在此种情形下,当地救济规则才是实体性的。当损害是源于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时,就会立即产生国家责任,此时当地救济规则仅仅是程序上的要求,须在外国投资者寻求国际层面的解决时适用。 (16)例如,1984年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的协定》第8条。 (1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第9条。 (18)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第8条。 (19)参见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国政府关于鼓励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第10条第2款。同年缔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科特迪瓦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中也有相似规定。 (2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的议定书》第6条。 (2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荷兰王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议定书》“关于第十条”规定了:“荷兰王国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其要求有关的投资者依照第十条第三款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之前用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当地行政复议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完成该程序的最长期限为三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拉脱维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的议定书》“关于第九条”做了大抵相同的规定。 (22)Helnan v.Egypt,Decision on Annulment,14 June 2010,paras.52-53. (23)Chevron v.Ecuador(I),UNCITRAL,PCA Case No.34877,Partial Award on the Merits,30 March 2010,para.326. (24)国务院2010年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第4点规定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外,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国务院有关部门可将本部门负责的审批事项下放地方政府审批,服务业领域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金融、电信服务除外)由地方政府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审批。由此,总投资3亿美元以下的鼓励类、允许类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地方政府。参见孙书博:《外资审批进一步放权地方》,《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4月15日A04版。 (25)指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为外交保护拟订的法律规则。特别报告员提交了三份报告,共计16项条款草案;此外,报告员还提交了第三个报告的增编以及两份专题工作文件。ILC第54届会议对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的剩余内容、第三次报告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进行了审议,并审议了起草委员会关于第1条至第7条的报告。 (26)参见第57届联合国大会文件:《中国代表薛捍勤女士在第五十七届联大第六委员会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第54届会议的报告”议题(外交保护和委员会的工作)的发言》。 (27)参见第57届联合国大会文件:《中国代表薛捍勤女士在第五十七届联大第六委员会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第54届会议的报告”议题(外交保护和委员会的工作)的发言》。 (28)参见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第9条第1、2款。 (29)ICSID Case No.ARB/08/4,Award on Jurisdiction,December 15,2010. (30)UNCITRAL Final Award,September 3,2001. (31)ICSID Case No.ARB/01/13,Decision on Objections to Jurisdiction of August 6,2003,42 I.L.M.1290(2003). (32)ICSID Case No ARB/08/5,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of June 02,2010. (33)2007年国务院颁布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11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依照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的,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申请人。 (34)1999年《行政复议法》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法律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的除外。该法第14条、第30条分别规定了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的两种情形。 (35)《行政复议法》第14条。 (36)《行政复议法》第7条。 (37)一是申请人可以在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复议申请的同时,一并就作为该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审查请求。二是《行政复议法》只规定了申请人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请求权,而没有规定行政复议第三人的审查请求权。参见胡锦光:《我国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演进与问题》,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38)1990年《行政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据此,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以行政法规为依据。而2000年《立法法》第90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依据本条规定,法院如果认为行政法规违宪或违法,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或建议。因此,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对行政法规没有审查权。 (39)《行政复议法》第31条。 (4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第3条第2、3款。 (4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第3条第1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