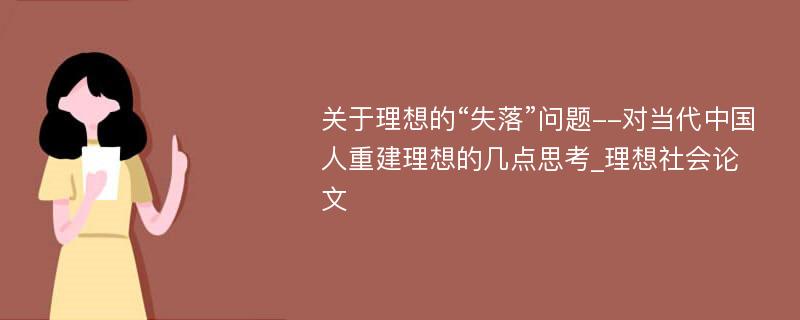
理想之“失落”的追问——关于当代国人重建理想的一些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想论文,国人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社会转型期,无论是党政部门还是民间组织的调查都显示:从普通民众到一般党员乃至党员干部的理想都发生了变化,“失落”现象相当普遍,许多人没有了精神追求,而津津乐道于物质生活与感性享受。对此,社会上有人大声疾呼,痛感世风日下,希望回归传统;更多的人则处之泰然,以为本该如此。如何认识这些现象?如何重建理想,在社会常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这无疑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思考与解答的问题,笔者的思考如下。
一、理想失落、精神危机与乌托邦告别
何为理想,《辞海》的解释:理想是“同奋斗目标相联系的有实现可能性的想象”,很明显,理想有两个特性:“实现的可能性”与“想象性”。由于仅仅存在着实现的可能性,就隐含着理想实现的曲折性与不确定性。而理想分不同的层次,越是高端的理想,其想象的成分越多,所以其“实现的可能性”中曲折性与不确定性就越大。本文所要探寻的是一种最高层次理想——这一理想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被称作“大同世界”何以失落的原因。由于该理想具有“想象性”的特点,并无任何已经实现的先例,其乌托邦空想的成分显而易见,所以人类关于社会理想的思想也被称为“乌托邦思想”,如此美好的社会理想,何以有这么多的人要与之“告别”?这里要说明的是,社会理想作为一种高端的理想,具有精神寄托的内涵,其与“信念”“信仰”都属于精神现象,都有精神支持、精神追求的含义——尽管信念偏于世俗生活、信仰偏于宗教生活——但在我们日常的生活语境中对这三个概念并不加特意区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探讨的“理想失落”问题,也是一种“精神危机”或“信仰危机”问题;而“乌托邦的告别”则是人们在经历了“失落”与“危机”之后,面对不顾客观条件而追求完美的理想社会目标以至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痛定思痛中所作出的冷静而无奈的选择。
二、理想失落:从“潘晓讨论”到“5+2=0”
从三十多年前《中国青年》编辑部推出“潘晓讨论”开始,到上世纪90年代末,社会学、教育学界提出——中国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可能正处于“5+2=0”的绩效状态,中小学生的实际思政德育工作出现了“小学生讲共产主义,中学生讲社会主义,大学生讲‘七不’文明规范”的奇怪现象。其实在相当程度上,这种现象正是我们整个社会理想困境的反映。时至今日,尽管在汶川大地震等突发的自然灾害面前和个人生命存亡的关键时刻,民族与人类的道德亮点曾经一度闪烁,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灾难过后中国伦理道德的危机以及理想失落的困局,仍然横亘在我们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上。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理想的失落是一个普遍现象:“部分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缺乏、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淡薄,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更是令人担忧。部分党员干部虽然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共同思想基础,但却认为它只是政治宣传,不起实际作用,没有现实应用的价值和意义;有的表面上把马克思主义摆在重要位置,嘴里喊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却不付诸行动;有的虽然付诸行动,却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在对大学生的调查中,学生的理想主要集中在生活和职业理想上,只有10%左右的关注社会和道德理想。”由此可见,三十多年过去了,国人理想失落的问题不仅是事实,而且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其阻碍着经济政治的科学发展,制约着社会文化的和谐进步,同时也侵蚀着国人的躯体与灵魂。追根究源,笔者以为“5+2”的问题,应是我们探寻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路径的症结所在。
这里解说一下“5”与“2”。“5”在广义上是指主流文化的教育与传播,狭义上是指现在既定的理想体系与既定的实现路径,因为有许多人认为那是一套“完备性的学说体系”和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2”是指盛行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生存方式、习惯与行为取向,以及在此基础上积淀下来的观念与处事规则,这实际上是一种独立于主流文化,但在一定社会背景(如乱世、转型社会)中行之有效的另类文化生态现象。
纵观人类历史,代表人类发展愿景的主流文化,尽管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与不同民族中有不同表述,但是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内蕴着“大同社会”和“乌托邦”的追求,这种美好的愿望是无可非议的,作为理想更应肯定。问题在于这些理想依附着某种学说,遵循着既定的规律和设计路径,传播实践,但又一次次的幻灭;而那些远离理想的潜规则、惯行办法却反复影响乃至左右着人们的生活与行事。久而久之,人们会痛苦地看到,由于“5”很难面对日常的实际问题,往往处于“空转”状态,或是拿来做做“表面文章”。所以“5”难敌“2”,自然就等于“0”了;更可怕的是,我们所说的“2”,对于人们的理想生活、理想社会而言,实际上是“-2”,而且现在的“-2”正在侵蚀、消解“5”,并大有取代之势,其负面效应正呈叠加之态,以至“-2”变得更负。所以,告别关于乌托拜的某类学说和某种路径设计,并不意味着放弃理想本身;而回归日常生活,也并非一味沉沦于陋习陈规。在这两难中寻求新生活、新路径,走出误区,跨越陷阱,正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这里,探寻“5”失落的深层次原因,无疑是我们总结教训、走出两难再建理想的出发点之一。
三、“失落”追因:从质疑模式、直面问题到反思理念
将理想失落归因于领导干部与思政工作者的精神危机与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实在是一种就事论事的判断。实际上这一原因之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其精神危机来自何方,其理想失落源自何处?
正如著名思想史家林毓生教授所言:造成灾难的原因非常复杂——笔者也以为将乌托邦主义引向反面的责任不宜完全归咎于个人,许多灾难往往在诸多因素的互动中发生,因为个人不是神,其理性总是有限的;一个民族乃至人类的理性也受到历史的限制,甚至还时不时地受到短视的、趋利避害之本性的支配。总之,对于如此复杂的历史问题不能以简单的、线性的因果论去把握,而应以关联性、系统性思维方式加以探讨。
林教授指出“作为(动员群众的)政治工具的乌托邦主义颠覆了乌托邦主义。这是乌托邦主义的异化,换言之,它的崇高目的,虽然事实上根本不可能达到,而被当做政治工具使用以后所产生的后果则是:它本身的理想也产生了异化,因为它背叛了它自己!”
尽管这只是一个学者的思考,但必须承认这是对我们“绕不过去的问题”的深入而认真的探讨,并有相当的代表性,其对中国乌托邦主义走向反面之深层次原因的分析十分中肯。
当然,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也不应止步于原因的探究而更应注重于教训的吸取。早在十多年前,历史哲学家就极其沉痛地告诫我们:“人们不去反思历史之中是否真的存在着一经发现就将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问题的规律或神律,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将之归咎于认识的偏差和实践的失误,结果推翻或放弃了原来的权威,又在新的‘世界历史人物’身上去寻找这种规律的化身。”由此可见,如果我们的理论研究与宣传意识不到这种思维定势的制约、止步于就事论事的水平,那么在重建理想的研究与宣传又如何引领社会潮流!
然而,这种以过程代目标,追求绝对真理,迷信伟人圣贤的理念与思维方式,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妨从两个方面略作解析。
第一,把理想与为实现理想之某种路径选择服务的学说体系等同起来,并将学说体系人为地“绝对正确”或“唯一正确”化,由此学说体系的问题也就与理想本身捆绑在一起了。
如果说,我们能以“试错”的理论与人的“有限理性”的认识去分析把握问题的话,去认识路径选择中的错误以及学说体系之不完备的话,会感到错误与不完备是正常的,更不会对理想本身产生怀疑。然而,问题恰恰是:长期以来,我们认同“完备性学说体系”与“唯一正确理论”的理念,以为必定有实现目标的一整套理论将揭示一条我们一般人无法找到的历史规律,有了这个规律,理想的实现就如同囊中取物。一旦规律不灵,学说体系显示出不完备,真理远离了我们,理想也随之动摇起来了。
其实,这种现象的产生要从两个方向上去把握,一方面,当年的路径选择者自己也受到追求“完备性学说体系”思维定势的操控,希望能一劳永逸地找到一条带领民众实现目标的道路,从而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直奔目标,完成大业。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生活于封建专制制度之下而养成了依附性人格的国人,尽管被宣告“从此站起来了”,但文化基因一时很难改变,自然也希望能依赖某种学说体系,躺在现成的某种真理之上,以实现人间天堂的愿景。正是在这种美好的但却是虚幻的互动中,一旦完备性学说不再完备、真理也难依赖之时,本来就乏力于独立思考与创新的那部分人,就会感到天昏地暗,失去了靠山、失去了方向目标。
小平同志在新时期改革之初提出了一句名言,我们今天仍记忆犹新,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对于上述问题的中国式破解,意义极其重大。不追求也不相信有什么完备性学说体系,才会有忧患意识,才会不断进取,少犯错误;敢于摸着石头过河,才会有创新意识,才能离理想的目标近一点。
第二,把理想与某种实现路径的设计者联系在一起,将路径设计者的局限性视作理想本身的问题。
任何学说体系都由人创立,因此与对“完备性学说体系”依赖心态相伴相生的是对创立学说体系的“天人”——也可称之为圣贤、伟人、领袖——的无保留的信赖与依托,这种情况对于长期习惯于权威依赖的国人而言,尤为严重,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对好皇帝、大清官、大侠客(在文艺作品中)乃至好领导、好长辈(在现实生活中)的渴望与依赖,在今天仍被视为一种很正常的思维、很正确的观念。其实这也是长期以来人治盛行、法治难推的社会心态与国民精神基础,甚至可以说已经是一种文化基因。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情况甚至在运用最新技术的网络上也得到了体现——有学者研究后指出,盛行于中国网络的微博社会其体现的社会结构关系仍是一种众多粉丝面对博主的“众星捧月”式的关系,是粉丝希望获得有一定社会名望和影响力的博主的庇护。
然而,任何圣人、伟人的智慧与理性都是有限的,并不可能成为“天人”,人类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天人”。任何圣人伟人的明察秋毫只是人们的美好愿望。伟人难免犯错,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与权力,产生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即使是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领导,在主观随意性或者贪腐欲念的操控下,也会产生相当的经济与政治后果。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路径的设计者和实际操作者将自己当做理想信念的代言者、表率者。由此,设计者的错误、执行者的堕落引起的连锁反应就是人们将其与平日宣传的东西一并抛弃,这里从崇拜信奉到虚无背弃往往只是一步之遥。
笔者以为,破除思维定势,走出理念误区,本来就是理论研究与相关宣传的职责,更是我们与时俱进的基础。由此,我们才能掌握主动,真正获得话语权。
四、重建理想:超越理想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的现实主义,走向理想的现实主义与现实的理想主义
理想的重建应该建立在“对于社会的‘实际’的经验性考察,对于‘应有的’理想社会的理论性构筑,对于实现这种理想社会的‘可能性’追求”这三者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这就决定了这种重建必须超越理想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的现实主义,而走向理想的现实主义和现实的理想主义的互补结合。
这里,理想的理想主义就是以上论述中分析的纯观念的完美的乌托邦主义,而现实的现实主义就是犬儒主义、实用主义。历史已经一再证明,这是人类发展的歧途。
为此,我们要解说的是理想的现实主义和现实的理想主义以及两者相互联系与相互补充的特点。
一般认为:“从和平、正义、人权、环境保护、公共之善、多种文化的相互承认、和解等哲学概念出发,在现实生活中冷静地寻找实现这些理念的途径,”这就是“理想的现实主义”。不过,理想的现实主义与理想的理想主义,即乌托邦主义亦不相同,它站在社会科学的角度冷静思考,分析这种梦想、希望在现实社会中能否实现。如果情况允许,也可以采取次善之策或是选择招致灾祸较轻之途。
另外,“现实的理想主义”是从对现实社会的考察出发,在考察过程中探寻建立较为理想社会的可能性。与从理念出发的途径不同,现实的理想主义的出发点是实际的社会分析,并以现状分析为基础,探索打破现状建立更好的社会的可能性。这也与乌托邦主义等理想的理想主义迥然不同,与犬儒主义等现实的现实主义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上述理想的现实主义和现实的理想主义,在重建理想、推进和谐社会愿景时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两种思路应突破途径的差异,将“现实的社会认知”和“理想的实现”统一起来,反对犬儒主义、乌托邦主义。
(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