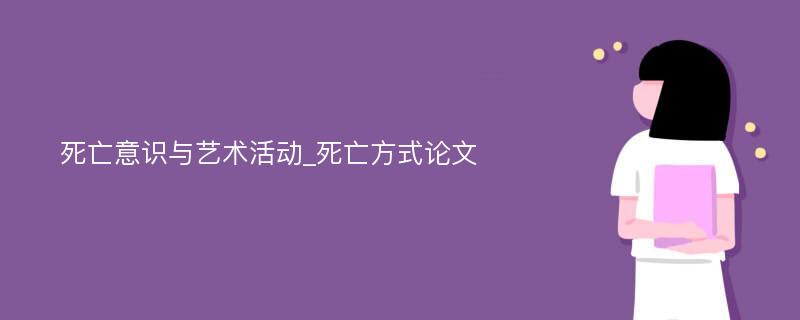
死亡意识与艺术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2)06-0076-04
一
求生避死是所有生物共同的本能,但动物没有死亡意识,也就意识不到自己与其他存在物的区别,没有生命的意义,只是本能地存在。惟有人清醒地意识到死亡的意义。死亡意识是人类产生的最后标志。死亡意识标志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人类认识到自己与其他存在物的区别,意识到生命的有限,结束了人类的盲目自信。在这个意义上,死亡是人类有限与无能的终极象征,人类从此由无限的存在转而为有限的存在;从视死如归转而为视死如敌;生命从无足轻重转而为弥足珍贵。人类从此躲避、抗拒、仇视与死相关的事物,亲近、欢迎、创设一切有益于生的东西。人对生存意义的理解是从对死亡的感受中建立起来的,没有死亡意识,人类就无法意识到人生的整体存在。
死亡的恐惧来自于生命的欲望。生命的载体是身体,对生命的珍惜首先表现为对身体的重视,延长肉身的生存成为超越死亡的最初努力。求取长生是人类最持久的活动,自我意识越强,就越重视身体,越希望延长身体的存活时间。肉身的主要内容有二:食和性。食是维持人类现实生存的基本手段;性是人类延续生命的基本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食和性都源于死亡,没有死就没有食和性,食和性是生命进化中出现的对抗死亡的机制。因此,两者成为生命力的象征和逃避死亡恐惧的方式。只要能吃和有性力,就可借助其有效地将死亡恐惧排除于意识之外。然而,作为肉身基本生存方式和生存手段的食和性无不受到时间的制约,身体只是时间牢笼里的囚徒,无法逾越时间这一障碍。身体不可能永存,人人必死。
放眼中外,从平民百姓到英雄豪杰,从文人墨客到哲人智士,面对人生短暂难免一死这一事实时,无不感叹嘘唏,形之于色,发之于声。死亡于是成了艺术永恒的母题,“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卧龙跃马终黄土”、“死去原知万事空”……这些诗句,引发多少心灵的共鸣。就连孔夫子这样不语怪力乱神的至圣先师,想到死亡也不免感叹:“逝者如斯夫”。曹操这样一世枭雄,也忍不住慨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西方学者发现的死而复生的神话叙述程式,其实就是死亡恐惧的体现。毋庸置疑,死亡恐惧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基本焦虑。美国现代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称死亡是潜伏在人类幸福欢乐的虚饰之后的“深藏的蛀虫”。
当逃避死亡的人们转过来面对人生虚无的恐慌时,自然会采取最简便也最通常的方法来替代性地满足对永恒的渴求:生育。生育的实质即将子女当作自身生命的延伸,希望通过肉身的延续达到对永恒的追求。孔子所奠定的传统没有把人的价值维系于灵界和来世,而把人生的意义定位于现世,在于民族、国家和人类生命的无限承传,在人的再生产过程中,在传宗接代的活动中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转化为族类生命的无限延续,从而超越死亡,个体生命也因此而不朽。老庄突破了孔子的视域,不再限于宗族人类而达于天地自然,在自然运化中得到永生。(因此,中国古代文化的特征之一即贵生)承接这个传统,儒道化的佛教——禅宗——弃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而主张在尘世中超脱生死。宗教思想将生与死统一起来。图腾文化把生命视为生与死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其后的宗教通过对灵的推崇和对肉的否定,把生与死、灵与肉的二元转化为一元,从而使“死”成为人类终极关怀的切入点。(注:可以看出,在这种哲学努力中,已经包含了对人的现实世界的否定。)原本不具有绝对意义的死亡因而对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有的宗教、信仰都为人类建构了一个“终极存在”,既缓解了死亡恐惧,又把人生境界从一己提升为族类、人类的超越性存在,赋予人生以超越性,使人生具有意义,人类生命从生物性的生存转化为社会性的生存,人类不再是个体性的、自私的,而可为族类、人类献出个体生命。理想性成为人类生命的本质规定。死亡使人认识到生命只是一个有限的过程,人类所做的一切均是对死亡的反抗,是超越死亡的努力,死亡超越是人生的主要目的之一。对死亡日益深化的理解使人深切地认识到,过程固然重要,但过程的意义源于结果,没有结果的过程是不可能具有任何意义的。德·波伏瓦笔下的雷蒙·福斯卡由于对死亡的恐惧而苦苦寻觅不死的秘诀,然而,当他再也不受死亡的威胁之后,他却发现,须有死亡,人生才有意义,不死的人生毫无价值。德·波伏瓦说道:人,不死是荒谬的。没有死,就没有爱和激情,没有冒险和悲剧,没有欢乐和痛苦,没有生命的魅力。[1]总之,没有死,就没有生的意义,生的意义最终由死来赋予。一切人生观、价值观皆源于死亡意识,行为的意义和价值均须置于死亡的天平上加以衡量。死亡赋予生命以意义,人生因了对死亡的理解和态度而呈现出高下。死亡意识中对永恒与绝对的追问,直指生命与世界的真义与本原。任何一种深刻的人生观都能正视生命悲剧;对生存意义的终极追问,使得生命的真实性得以呈现。
二
在上述哲学里,时间只是一种测量的时间、一个现成的现在之流,是事物发展的条件。自由——神(上帝)的假设和灵魂不朽——即超越时间。的确,神(上帝)的假设和灵魂不朽可以解决人的时间性存在与自由存在之间的矛盾,但这种假设的前提是人终有一死,即人是时间性的存在。也就是说,所有的宗教、信仰为人类建构的“终极存在”这种非时间性的存在必须以时间性存在作为前提。这也就意味着,存在自身必以时间为前提。时间是存在的时间,存在是时间的存在,任何时间只能是具体的时间,任何存在只能是具体的存在。因此,人的生命存在必是一种整体性的存在,不能割裂为时间存在和自由存在两个方面。这样,在人的生命整体中,自由不再与时间相分离,相反地,必以时间为根基。
讨论至此,我们不能不提及一个人——马丁·海德格尔。毫不夸张地说,现代哲学对死亡和生命存在研究的突破,是以海德格尔为标志的。近年我国对“死亡与艺术”这一论题的讨论,也多以其理论为起点,为其理论引出。承接狄尔泰的研究,海德格尔突破了康德的局限,把人定义为时间性的存在,从而将时间与存在联系起来。他认为,存在是与人共属的存在,人也是与存在共属的人。“在”就是“我在”,就是作为此在之我的生存活动。作为时间性的存在,人作为此在而存在,领会着世界而存在。作为有限的此在,人类没有理由为自身之外的目的生存;但死亡于他并非外在事件,而是作为此在最本真的可能性存在而展开的。既然人类不能用既定的某种东西来界定,就只可能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既然此在终有一死,此在就是向死亡的存在,受到死亡的规定。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在生命中,此在才能先行到死亡之中,把死亡作为自身的可能性来承担。此在的存在之所以是一种整体存在,并不在于它活着,而是因为它是包含着死亡的生命存在。真正的生命存在活着,同时也死着,没有死亡的生命本质上不是生命。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把人类生命的整体存在分为本真方式和非本真方式两种。非本真的方式不是先行到死亡之中,把死亡作为死亡本身展开来,而是逃避死亡,沉沦在世。死亡被理解为自身之外的可能事件,非本真的向死亡存在就是预期着死亡而存在。本真的方式则是先行到死亡中,把死亡作为可能性无遮蔽地展开来,成为自由的自身。向死亡的存在就是整体的存在,向死亡存在在生存活动中就展现为时间性。时间成为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前提,意味着本源时间意识的觉醒。在本源意义上,时间性就是向死亡展开。时间性的统一展现——过去、现在、将来的统一展现——整体存在才成为可能。所以,整体存在必须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统一。海德格尔认为,过去(已在)并非不存在,此在只能是已在的存在,已在就是曾在,而且一直在,此在作为自身存在总是已在。如果此在虽曾在但目前已经不再在,就说明它已不再作为此在存在。只有自身曾在而且一直存在才是此在的存在具有同一性。如果自身存在总是已在的存在,那么先行就是一种重演。已在在重演中继续存在。任由过去,就因为过去还存在。不过,此在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不因为已在,更由于此在的存在是将来的存在。将来是已在的前提,换言之,此在有将来,它才能有已在。倘若此在没有将来,它就取消了自身。因为存在即时间性的存在,此在只能取消各种日常可能性,但绝对不可能越过死亡这种最本己的可能性。因之,此在只要存在就必有将来,就是将来的存在。将来并非“什么”,并非现在尚不存在以后才出现的“什么”。如此理解的“将来”是概念的、抽象的将来而非生存性的、实际的将来。作为时间性的一种方式,将来现在就存在,作为可能性而在。
从此出发,海德格尔批判了非本真性存在,他认为非本真的存在者因担心死亡、逃避死亡而不再持守死亡,遗忘死亡这种最本己的可能性而遗忘了自身。不同于本真的存在总是和将来与当前同时展现,于此在相遇的存在者总是作为他自身呈现出他自己,非本真的存在总是让存在者作为某种——如可做的……,紧迫的……,不可或缺的……,可满足的……什么而出现,以对存在者有所求,有所期待为前提,这就关闭了自身,关闭了此在的本真存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异化。近代以来,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的眼光不再只盯着来世而转向现世,现实人生得到高度的重视。与此相伴的,是孤独感的增加,荒原感的凸现。人类从有限的存在转为有限性的存在,死亡不再是群体性的问题而成为个体性的问题。扩张生命、超越死亡的有效方式似乎就是竭力抓取眼前可资证明自我存在,显示自我尚有生命力的东西。其结果就是把肉身等同于生命。这是一种以终止价值关怀的生存方式对生命的追问和回答,其特征是占有外物。然而,当死亡来临之时,占有者终于发现,占有与死亡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死亡使占有与其结果成为悖论。当我们将整个生命耗费于维持肉身的存在时,生命不可能不被“物”分割得支离破碎,物的尺度已内化为生命价值的尺度。回避死亡的最终结局是取消生命的真实性,这种生存假象在死亡降临时暴露无遗。非本真的存在即让存在者作为某种什么出现,以前做过某事,现在应该如何做,下一步该如何做,……时间被领会为不断到来而且可以取之不尽的东西。死亡之是一件倒霉的事,谁死了,即谁被抛在时间之外。生者在悲痛和同情之时,也在庆幸自己的活着。以掩盖死亡来安慰自己,使自己安于日常状态,安于某种什么。这实际上关闭了可能性的展开,因为人是同时包含了已在、现在和将来的整体性生命,时间即其存在的展开。沉溺于日常状态,就意味着错过了自己种种可能性存在的展开,从而浪费了时间,虚掷了光阴,也就遗忘了自身。人类不是某种现成的东西,而是可能性的存在,有着种种可能性。珍惜时间,珍惜生命,就是珍惜自身种种可能性的展开。人类生命不是实然的、现存的,而是应然的、可能的,向未来敞开着无限的可能性。[2]
三
现在我们就可以明了,超越死亡并不指超越时间的规定,进入一个非时间的领域,而是充分展开我们的可能性,使我们成为他人的已在,融于后人的视界,在后人的生存中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从而获得永生。一旦我们脱出他人的视界,我们的生命就此终结。具体地说,就是在时空上离开他人之后,他人的生活和生命里出现了一个无法填补的空白,这就是人生的价值所在,也就是对死亡的超越。由此,我们便可知晓为什么自己、尤其是老人担心被人认为“没用”;为什么有个性比没个性好;为什么那么多人希望成为名人;为什么有时人们愿意在得不到任何好处甚至贴本的情形下做一些事……这些,正是人们追求永恒的努力,是人们面对死亡的威胁采取的积极行动,目的是反抗死亡,泯除死亡恐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便可更好地理解创造的特质。与物是某种什么不同,创造永远不是创造某种什么,它只是可能性的展开。因而,创造是人类活动的核心。创造活动起于对死亡的超越和征服、对永恒的追求与渴望。获得永恒就是在人类的精神文化中打上个人的烙印,成为他人的视界——文学艺术史、文化史、政治史、思想史……一句话,历史的一部分。
对艺术创造的研究表明,在创作冲动中,永恒意识占有突出的位置。创作是个人赖以永恒的手段。古今中外,无数艺术家以常人难以想象的热情,执著于创作。“借问别来何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为了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杜甫已到了“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地步。卡夫卡曾经说过:写作是为魔鬼服务。这话精当。周益平在《平园续稿》中说:“昔人谓诗能穷人,或谓非止穷人,有时而杀人。……唐李贺……之不寿,殆以此也。”中国文人自古就有通过立言以不朽的思想。《左传·襄二十四年)所说的“三不朽”,揭示了早在先秦人们就已普遍认识到,创作上的成就,如同道德和事功的成就,是个体得以不朽的保证。以立德、立功、立言获得生命的延续和生命意义,是中国文人基于理性自觉而确立的人生理想。这种永恒意识一旦确立,便把人对死亡的恐惧,转化为对永恒的追求。尼采说: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的形而上学活动。谢林说:艺术本身就是绝对的流溢。只有艺术和审美的创造,才是惟一战胜生命焦虑的力量和对生命的最终慰藉。即使没有自觉到这一点,对死亡的敏感也会使很多艺术家不知不觉地走上以写作寻求解脱的道路。
梅洛·庞蒂说道:
生命与作品相通,事实在于,有这样的作品便要求这样的生命。从一开始,塞尚的生命便只在支撑于尚属未来的作品上时,才找到平衡。生命就是作品的设计,而作品在生命当中有一些先兆信号预告出来。我们把这些先兆信号错当原因,然后它们却从作品、从生命开始一场历险。在此,不再有原因也不再有结果,因与果已经结合在不朽塞尚的同时性当中了。[3]
艺术具有两重性,既是把内在欲望对象化的媒介,又是把个体与现实隔离开来的屏障。欲望和焦虑在特殊的语境中消解,凝聚为隐喻性的幻想,通过观赏活动,个体与幻想的距离被弥合,实现对现实的想象性征服。在艺术作品中,主体在外在对象无限可能性的激发下,通过创造性的努力,把个体幻象与外在现实结合起来。艺术对象既是主体欲望的目标,又是外在的客观实在。通过这个中介,主体欲望获得了具体的投射对象,物质性的材料转变为现实社会关系的表征形象,从而建立内在欲望与外在现实的深层关系,主体通过艺术形象这个中介达到与现实的结合。这种结合既是主体自由的实现,形象也因此具有了人性的光辉,欲望的表达因此突破了自恋性而趋向开放。通过扩张主体的内在世界和情感深度,个体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得到调整。个体丰富而完整的欲望获得了现实化,主体片面发展的现实个性升华为全面发展的审美个性,现实世界也成为审美个性的对象化,艺术因此成为真正的自由的生命活动。[4](P149-150)艺术从生存的本真境况出发,将隐藏的生命本质昭示出来,将人的超验的价值内涵昭示出来,它让我们在寻求永久依托的过程中,竭力接近生命的永恒。一个人,如果真正关心自己的灵魂,他就会发现艺术成了他与世界的一种独特联系,透过艺术,他发现了世界对他昭示的一切。艺术只有真正成为人感受生命的方式,心灵才会得到真正的慰藉。对于热爱生命又为终极关切苦恼的人来说,艺术的确是对生命的最好慰藉。艺术在每一个生命的深处实现并体现了它充满人性温暖的对心灵的终极关怀,世界因此而充满生机。
在现实中,主体与对象、生存与死亡、理想(将来)与现实(现在)是分离的。现实意味着人的有限,人却通过艺术想象自己的无限;死亡意味着自我的解体,艺术却是人类伟大的表征,理想给了人类超越现实和战胜死亡的勇气。艺术最可贵之处不在于写了什么,而在于展现出各种生命自身和生命的种种可能性,使欣赏者领悟生命的丰富性,人们从中得到启发,从而创造新的生命可能。艺术超越现实解释,创造了超越的意义世界,它揭示了主体的想象力和直觉力,突破文化障蔽,直接领悟存在本身,获得生命的真正自觉。在这个意义上,理想性即否定性,艺术是对现实的批判,它克服了现实认识和现实价值的局限,使人获得自由的意识,通过对现实人生缺陷的解释和现实世界的批判,使人产生对现实人生的批判意识,引导人们追求更加美好的人生。可以说,艺术的真正诞生地是死亡,没有死亡,就没有艺术,没有死亡,人类便无所畏惧,无所悔恨,无所理想,也不用创造一个虚幻的艺术世界弥补现实人生的遗憾,满足对永恒的追求与向往。正是由于死亡的不可避免,人们才创造了艺术,唤醒人类激发人们改造现实、超越现实,超越死亡的激情,使人迈向更加美好的生活。这,便是艺术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生命活动方式的主要原因。
收稿日期:2002-0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