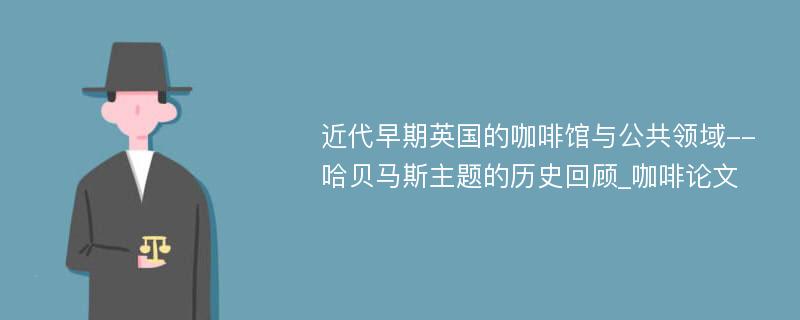
咖啡馆与近代早期英国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话题的历史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斯论文,英国论文,咖啡馆论文,近代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问世以来,有关“公共领域”的学术研究就从未停止,其中不乏批评和争议。除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率先讨论外,史学界的研究尽管相对滞后,但显得尤其必要。因为理论概念的界定廓清,离不开具体的历史考察作为基础。① 哈贝马斯提出的西欧近代公共领域,涉及其凭借的空间和媒体,包括此时兴起的各类社团及其活动场所沙龙、咖啡馆、剧场、音乐会、展览会、图书馆、俱乐部,以及初兴的报纸刊物。于是,这些空间和媒体成为近年来西方政治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学者异常感兴趣的课题。英国咖啡馆由于史料比较丰富,并且被哈贝马斯视为近代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公共领域,因而成为史家特别注重的研究对象。英国咖啡馆的兴起以及伴随咖啡饮用进行的社团活动,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西欧近代公共领域形成的历史面貌和基本特征。本文先就英国近代早期咖啡馆的兴起过程作一简要回顾,随后对此期咖啡馆的平等性问题和咖啡馆与以俱乐部为代表的社团关系问题,结合哈贝马斯的相关理论进行一点初步的辨析。
一、英国咖啡馆兴起的历史概况
咖啡原产于西亚北非地区。英国首家咖啡馆出现于1650年的牛津,由犹太商人雅格布(Jacob)开设。据研究英国咖啡馆史的早期学者艾多·埃利斯(Aytoun Ellis)所述,这也是整个基督教世界最早的咖啡馆。② 1652年,英国利凡特公司商人丹尼尔·爱德华兹(Daniel Edwards)的随从、希腊人巴斯卡·罗塞(Pasqua Rosee)开设了伦敦第一家咖啡馆,并且张贴和散发广告,宣传咖啡不仅提神醒脑,而且具有暖胃、治疗痛风、助孕等多种保健医疗功效。1663年伦敦咖啡馆的数量达到82家,1700年更增至2000多家,每家一天都有三、四百人光顾。安妮女王统治时期(1702—1714年),伦敦咖啡馆的数量最多时达到3000多家。17世纪下半叶由于火灾、瘟疫的发生,咖啡馆的经营一度遭受重大损失,但是到19世纪末,伦敦的咖啡馆仍有1400多家。③ 由于以其低廉的消费价格为光顾者提供了休闲解乏、了解新闻、沟通信息、切磋学问、议论世风、褒贬时政的公共空间,咖啡馆在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各地市镇得到迅速发展。1675年托马斯·乔丹在赞颂伦敦市长的一首韵律诗中写道:“如此伟大的一所大学/我觉得从未有过/在这里你可以成为学者/只要你花上一个便士”。④ 从此,“便士大学”(penny university)成为英国坊间对于咖啡馆的习称。
英国咖啡馆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阻力来源于民间和政府两个方面。民间的阻力出自原有的酒店业主的经济考虑并以妇女名义发表的舆论非议,政府的阻力则出自政治统治上的担心和忧虑。咖啡馆的兴起拉走了大批原来沉湎于酒馆的顾客,酒店业主对此十分恼火。为此,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激烈攻击咖啡馆的舆论小册子,而这些小册子又往往冠以女性的名义。一本题名为《啤酒店女老板们对咖啡馆的痛诉》颇具代表性,它指责咖啡馆不仅“破坏了善结人缘的传统美德”,并且直接影响到夫妻生活和后代的繁衍。因为饮用咖啡使男性功能严重下降,“喝咖啡对男人造成的伤害,是造成其生命的本源枯竭,有损于妻子与后代”。⑤ 另一份小册子也说,喝咖啡的坏处在于“使男人越来越虚弱无力,精力枯竭,无法繁殖后代,就像非洲的沙漠一样干涸”。⑥ 实际上,这种指责完全缺乏科学根据。就当时英国妇女的整体文化水平而言,这些作品也很难说是出自女性笔下,不如说是假冒女性身份的男性之作。攻击产生的真正根源是经济利益和饮料消费市场的竞争。
更重要的是,对于咖啡馆的舆论指责还包括政治上的攻击。有的海报声称,历史上最大的叛乱者在他们干坏事之前都喝过咖啡。还有人说,喝酒是表示对国王的忠诚,是否喝酒是辨别一个人是否忠于国王的标志,因为当时人们喝酒的惯常用语是“为了健康,特别是为了国王的健康”。为此,一本小册子的作者声言,啤酒店的常客“是国王陛下最安分守己的臣民,也是最顺从君主政府的人”。⑦ 与酒馆相比照,这些信奉国教的王党分子认为咖啡馆是暴乱的温床,是各种政治阴谋的滋生之地。⑧
喜爱咖啡的民众则针锋相对地予以反驳。1674年,一本名为《男人对妇道人家反对咖啡请愿书的回应》的小册子坚持认为:“咖啡不仅无害,而且具有治疗功能,它是上天仁慈地赐予我们的饮料。当叛乱即将爆发的时刻,当整个民族陷于极端狂热之时,喝上一杯咖啡,就立即会使我们镇定和乐观起来。”作者为此强调指出,“咖啡馆是公民的学院”。⑨ 次年出版的另一本小册子《为咖啡馆辩护》,在诉说咖啡馆对于人们陶冶身心、增进健康、扩大交往、获取知识等方面的各项益处后,最终将咖啡馆概括为“健康的圣殿、节制的苗圃、节俭的乐园、文明礼貌的学堂和培养聪明才智的免费学校”。⑩ 17世纪末,英国皇家学会成员约翰·霍顿认为,咖啡馆不但不会使人向恶,反而会促进文明的进步。他指出,“咖啡馆给各色人等提供社交场合,富人和穷人、有学问的和没有学问的人,都在这里会面;它促进了艺术、商业和其他各种知识的发展”,因此,“咖啡馆与大学一起,共同促进了有益知识的增进”。(11)
1660年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曾先后于1675年12月29日和1676年1月8日两次发布取缔咖啡馆的国王文告。第一份文告宣布,自1676年1月10日起禁止零售任何咖啡、巧克力和茶,责令各地所有治安法官联手行动,吊销此类营业执照并禁止发放新的执照。同时,文告宣布,对于起诉造谣中伤者给予50镑奖金的高额奖励。该文告一发表便遭到咖啡馆业主的强烈反对。1676年1月6日,一批业主向查理二世国王面呈请愿书,认为该文告是最不公正的文告,足以毁灭从事此业人们的生计。次日,经枢密院紧张计议,敦请国王再予决断,终于使得查理二世在1676年1月8日下令发布第二份所谓“补充文告”,给予咖啡馆业主以6个月的出清存货和了结营生的延长期。实际上,取缔咖啡馆文告的最终结果是不了了之,文告施行不足两周便难以为继,咖啡馆业主和钟爱咖啡的顾客为维护咖啡馆经营及其公共领域社交活动的斗争获得成功。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大卫休谟后来对此事有过比较客观的评论,他说,“国王注意到民众的不满情绪正在加剧,于是决定向咖啡人的请愿让步,撤回了该项文告”。(12) 进入18世纪后,尽管英国政府当局出于稳定统治的需要,仍密切注视咖啡馆的社交言论和活动,不时加强对咖啡馆的监视和控制,但是咖啡馆的经营和消费已经获得了合法地位。
二、咖啡馆公共领域的平等性问题
哈贝马斯视平等性为近代公共领域的首要属性。他认为,咖啡馆等社交场所“首先要求具备一种社会交往方式;这种社会交往方式的前提不是社会地位平等,或者说,它根本就不考虑社会地位问题。……所谓平等,在当时人们的自我理解中即是指‘单纯作为人’的平等,唯有在此基础上,论证权威才能要求和最终做到压倒社会等级制度的权威。”(13) 就英国咖啡馆的历史考察,这种观点并非全然如实,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历史的动态分析和对于咖啡馆社交类型的分析。
的确,咖啡馆开设之初,并未对顾客的身份进行限制,社会各阶层人物均可入室啜饮咖啡和彼此交往。史料中不乏这方面的生动记载。1673年题为《咖啡馆的特征》的小册子写道:“每个人似乎都是平等派,都把自己看成是一介平民,完全不论地位和等级。所以你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愚蠢的纨绔子弟,一个可敬的法官,一个自命不凡的家伙,一个举止得体的市民,一个知名的律师,以及四处转悠的扒手、非国教徒、虚伪的江湖骗子。所有这些人都聚在一起,组成了一个鱼龙混杂的大杂烩。”(14) 这种印象对后人的影响至深。例如,1927年起曾长期担任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的大史家乔治·马考莱·屈维廉,在其名著《英国社会史》中仍强调说,“‘英国普遍的言论自由’……是咖啡馆生活的精粹所在。”(15) 但是,这种情况并非一成不变。尽管兴起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咖啡馆具有较大社会空间的平等性和自由度,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场所也逐渐形成了人以群分的状况,原先的平等性和自由度都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阶级、利益群体、党派、性别的差异逐步增大,社会分化在咖啡馆公共领域的体现日趋显著,排他性、特权性增强。
首先,伦敦等地形成了具有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利益关系的咖啡馆聚会场所。例如,辉格党人愿意光顾斯米纳咖啡馆或圣詹姆斯咖啡馆,托利党人则经常聚会于怀特咖啡馆和可可树咖啡馆。经纪人喜欢聚集于乔纳森咖啡馆谈论股票行情,随后乔纳森咖啡馆又逐步演变为今天的伦敦证券交易所。法律界人士集中于骑士团圣殿附近的咖啡馆,而文人以威尔咖啡馆和巴顿咖啡馆为探讨文学的场所。士兵聚集在老人咖啡馆和青年咖啡馆发泄他们心中的怨气和不满。寻常百姓不可能形成自己专门的咖啡馆活动场所,最多在各咖啡馆四处转悠,打听一点社会新闻和市场行情,他们逐渐成为咖啡馆社交场所的边缘化群体。(16)
其次,咖啡馆内部的空间结构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一个咖啡馆内,尽管中心地带是长形的大桌子形成的活动场所,有着较强的开放性。但是,大厅周边和楼上小型及专用的咖啡间包厢逐步增多。这些咖啡间的私密性和排他性也逐步增强。一般百姓基本上被排除在这类空间之外。18世纪中叶以后,许多咖啡馆或咖啡间的消费门槛提高,活动的专用性加强,有的甚至变成专门团体或政治党派固定的活动场所,已不再具有往日咖啡馆开放的特征。政治分野的因素越来越影响到咖啡馆的社交空间。在18世纪晚期,持共和主义观点、赞同法国大革命的顾客,不留心进入拥护君主制氛围较强的咖啡馆发表言论,往往会遭到围攻、起诉甚至入狱的下场。
18世纪90年代英国曾经出现过有名的弗罗斯特审判案。约翰·弗罗斯特是伦敦印花税务局的事务律师、“宪法知识会”(Society for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的创建人之一,同时也是名声更大的“伦敦通信会”(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的骨干成员。他赞同共和主义,曾随著名的共和主义者托马斯·潘恩前往法国,并代表宪法知识会向法国国民公会致词,祝贺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成立。1792年11月6日,弗罗斯特出席某农业社团聚会后顺楼而下,在楼下珀西咖啡馆的走廊上与熟人、药剂师马修·耶特曼相遇寒暄,不经意惹出一桩官司。耶特曼询问法国的形势,弗罗斯特却就此十分外露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主张平等,不要国王。”在场饮用咖啡的家具商约翰·泰特等人冲出靠墙的厢座向他厉声质问,并在日后以煽动诽谤罪将他告上法庭。这场官司最终判处弗罗斯特6个月监禁和1小时枷刑示众。尽管由于狱中染疫而重病在身,弗罗斯特最后的枷刑得以免除,但是这桩案件表明,18世纪英国的咖啡馆决不是哈贝马斯式的可以反对专制政治和充分保障言论自由的公共领域。
再次,即便在18世纪早期比较开放的咖啡馆公共领域,主导室内社交活动的言谈和舆论,包括可以自由阅读的报刊的导向,从表面上看来不乏互动讨论的平等色彩,但是其基调仍然是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道德规范。这些刊物张扬的是中产阶级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念,突出的是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文明水准,所要规训的是下层民众应当自律的道德规范和应当遵守的并非平等的社会秩序。在一时声誉颇高、由斯蒂尔和艾迪生先后创办的《闲聊者》(the Tatler)、《旁观者》(the Spectator)等咖啡馆刊物中,不难看出当时辉格党人所要达到的目的。
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与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1672—1729)生于同年,从小就是亲密无间的伙伴,青年时代同入牛津大学读书,后来在政治生涯中又同属辉格党,是继培根之后出现的18世纪初英国著名的随笔作家。1709年4月斯蒂尔首先创办《闲聊者》。这个刊物每周发行三期,内容分为新闻、诗歌、学术、社交娱乐、随感录等五项。至1710年12月最后一期为止,《闲聊者》共发行271期。斯蒂尔在第一期开篇中明确表示,该刊“主要是为那些从事政治的人们使用的”。(17) 他以“艾萨克·毕克斯塔夫”为刊物主编的笔名,声称刊物“旨在揭穿生活中的骗术,撕下狡诈、虚荣和矫情的伪装,在我们的衣着、言谈和举止中提倡提倡一种质朴无华的风尚”。(18) 斯蒂尔批评‘狡诈、虚荣和矫情’等不良习气,矛头直接指向当时宫廷贵族的行为举止,希望由此倡导中产阶级简朴、节制、勤奋、礼貌的道德风尚和行为标准。
1711年3月1日,艾迪生与斯蒂尔合办《旁观者》,到1712年12月6日停刊,每日一期,共出了五百多期,主要由他们两人撰文。1714年6月,艾迪生又单独复刊,改为每周三期,为时半年。《旁观者》的影响比《闲聊者》更大。在该刊的主要阅读传播场所布顿咖啡馆里,艾迪生特地设立了一个张开大口的狮子头信箱,邀请读者踊跃来信发表意见,并以“来函照登”或“答读者问”的形式发表和进行交流。《旁观者》号称是由一位“旁观者先生”以及他的俱乐部主办的,这位旁观者学识渊博、阅历丰富,通晓各行各业,但从不插手实际事务和党派之争,只在自己的俱乐部里发表意见。而俱乐部成员包括6名成员,除牧师、见习律师、军人、风流雅士各一人外,刊物主要突出了另两名成员——伦敦商人安德鲁·弗利波特和乡绅罗杰尔·德·考福来爵士,并刻意将他们作为比照对象。编者笔下的弗利波特显然是道德行为的正面典型,他理智、节俭、敬业、善于理财,把海洋称为英国的公共领地,认为勤奋获利长远,懒惰足以亡国。反之,考福来则不拘小节,生活浪漫,甚至不修边幅。(19) 艾迪生借旁观者先生之口,强调刊物“要让道德带上智慧的光芒,让智慧受到道德的约束”,依靠“持久不懈的教化”,铲除罪恶和愚昧,“把哲学从私室、书库、学校和学府带到俱乐部、聚会场所、茶桌和咖啡馆之中”。(20) 正如哈贝马斯所言:“艾迪生把自己看成是风俗和道德的检察官。”(21) 这些刊物连篇累牍、反复进行的说教,无非是要用中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来规范社会。对于下层民众,刊物则要求他们学会保持“谦逊”和“克制”,做行为得体的平民。(22)
最后,咖啡馆基本上是男性的活动空间,妇女很少进入其中。性别的不平等在咖啡馆内体现得尤其明显。咖啡馆内并非完全没有女性。上层社会妇女偶尔也会伴随夫君出席少量礼仪性质的聚会,但不会经常参与咖啡馆的言谈和讨论。咖啡馆也不乏女店主和女仆,但她们只是商业性质的经营者和劳动者,谈不上是这类公共领域的参与者。
其实,早在17世纪咖啡馆初兴之际的1674年,一份名为“咖啡馆的规则”(The Rules and Orders of Coffee House)的海报,就提醒顾客切勿“大声喧哗争执”和莫谈“国事”,从中可以揣摩当时经营者希望咖啡馆能够维持平静气氛、避免政治麻烦的谨慎心态。(23) 所以,不能将英国历史上咖啡馆公共领域的平等性过于理想化和绝对化,设想为没有任何前提限制的完全自由的言论空间。
三、咖啡馆与社团的关系
已有关于英国咖啡馆的诸多著述,多将咖啡馆的衰落与俱乐部等社团的兴起联系起来,似乎后者是前者衰落的一项主要原因,并且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咖啡馆与俱乐部是英国近代公共领域前后相继的两个发展阶段,两者的关系是俱乐部取代咖啡馆。(24) 晚近有学者指出,在错误判断英国咖啡馆自1730年后为私人俱乐部取代的问题上,哈贝马斯可以算得上是最早的发端者。(25) 不仅如此,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一些学者还认为,咖啡馆形成的公共领域首先是“文学公共领域”,其次是“政治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产生出来的”,政治公共领域的“前身”是文学公共领域,两者在时间上也形成前后关系。(26) 实际上,只要对17、18世纪的相关历史进行比较具体的考察,就可以看出以上观点值得修正。
咖啡馆与俱乐部兴起的时间大体相仿,均在17世纪中叶前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两者相互并存,在空间上相互重叠。距离牛津首家咖啡馆开张5年后的1655年,一群牛津大学的学生和新近被确定为受资助的研究生,鼓动药剂师阿瑟·蒂利亚德(Arthur Tillyard)在自己的住所里向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公开出售咖啡,同时他们在这间咖啡馆建立了俱乐部。成员中人才济济,有后来接替威尔斯博士担任牛津大学自然哲学教授的托马斯·米林顿(Thomas Millington),成为皇家学会最早会员的彼得·佩特(Peter Pett)和马修·雷恩(Matthew Wren),获得医学博士的拉尔夫·巴瑟斯特(Ralph Bathurst)和约翰·兰普夏(John Lampshire)。才华最为出众的成员是克利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人称“英国的莱奥纳多达·芬奇”,擅长音乐、数学、哲学、建筑学,多才多艺。与其交往的约翰·伊夫林称赞他是“顶尖的年轻学者”。(27)
蒂利亚特俱乐部活动至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随后大多数成员流向伦敦。其间,克里斯托弗·雷恩曾经又加入牛津的另一个科学俱乐部。不久,这位青年学者受聘为地处伦敦的格雷沙姆学院天文学教授,而格雷沙姆学院恰恰是英国皇家学会的诞生地。1662年7月15日该学会获得皇家特许状,克利斯托弗·雷恩及马修·雷恩均被钦定为皇家学会理事会成员。因此,从最早的起点追溯,牛津的咖啡馆俱乐部成为孕育皇家学会的孢子。往后的情况大体如此,晚近研究英国咖啡馆史的学者布赖恩·科恩也强调,“奥古斯都时代”(即1702—1714年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笔注)俱乐部的历史,与17世纪晚期咖啡馆社交界的兴起紧密交织在一起。(28)
传统观点认为,英国咖啡馆的“黄金时代”出现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而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则是它的“衰落阶段”。(29) 其中一项突出标志,便是俱乐部等社团组织的涌现。因为咖啡馆是“开放”和“平等”的,而俱乐部是“私密”和“排他”的,两者的性质互不相同。于是,俱乐部的兴起也就意味着咖啡馆的衰落。实际上,晚至1840年,据议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报告,英国每年仍有一百家左右的新咖啡馆开张。(30) 可见,在社团组织进一步发展的19世纪上半叶,咖啡馆仍未见衰落,社团依然将咖啡馆作为自己主要的公共领域和活动场所。
早期咖啡馆公众议论的话题,也不仅仅局限于文学范畴,有的俱乐部聚会的咖啡馆甚至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政治气息。1659年共和主义者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1611—1677)创立的政治辩论团体性质的“罗塔俱乐部”(Rota Club),就以“土耳其人头像”(Turk's Head)咖啡馆为活动场所。Rota的含义是指俱乐部成员以轮流坐庄方式主持团体活动。哈林顿所著《大洋国》一书的篇目,大多来自俱乐部的讨论话题。因此,并不存在那种前后分开的“文学公共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
与咖啡馆大体同时产生的俱乐部以及更早出现的一些社团,一开始就具有多样化的类型和多种结社宗旨,甚至超出“文学”和“政治”的范围。据彼得·克拉克初步估计,16世纪晚期至18世纪英国各种协会、学会、俱乐部等社团组织的种类多达130余种,包括科学、医学、学术、文学、美术、音乐、读书、工艺、商业、农业、园艺、体育、慈善、互助、政治辩论、法律诉讼、习俗改革等诸种类型。1586年成立的博古学会被视为英国第一个具有近代色彩的社团,从事考古和历史研究。1660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更是声名远扬,在推动科学探索和技术应用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后的发展越发引人注目,各种辩论会促进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形形色色的互助会缓解了下层劳动者的经济困境,各种以改革为宗旨的协会不同程度地推动着英国议会的政治改革。由于英国近代社团兴起过程所呈现的繁荣局面,1732年英国的《绅士杂志》声称:“在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城镇或村庄不拥有自己的俱乐部。”(31) 由此看来,哈贝马斯有关公共领域的阶段划分和性质界定,至少就英国相关的历史而言值得进一步加以思考和修正。回到本文开篇时所说的想法,对于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各国近代公共领域进行细致深入的历史考察,必将大大拓展人们的知识视野,避免哈贝马斯已经反思的、在理论概括方面可能出现的“巨大风险”,有效推进公共领域这一既具历史价值、又富有现实意义的课题研究。
注释:
① 哈贝马斯自己回顾说:“倘若我们不能像历史学家那样追本溯源,而仅仅依靠二手材料,那么,这个问题当中将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历史学家批评我经验欠缺,是十分中肯的。”[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1990年新版序言”,第3页。
② Aytoun Ellis,The Penny Universities:A History of the Coffee-house,London:Secker & Warburg,1956,p.18.
③ John and Linda Pelzer,“The Coffee Houses of Augustan London”,History Today,vol.32,n.10(October 1982),p.47.
④ Thomas Jordan,The Triumphs of London,London,1675,p.23.(http://eebo.chadwyck.com)
⑤ The Ale-Wives Complaint Against the Coffee-Houses,London,1675,p.5.(http://eebo.chadwyck.com)
⑥ A Character of Coffee and Coffee-Houses,London,1661,pp.3-4.(http://eebo.chadwyck.com)
⑦ Poor Robins character of an Honest Drunken Curr,London,1675.p.7.(http://eebo.chadwyck.com)
⑧ Steve Pincus,“Coffee Politicians Does Create”:Coffeehouses and Restoration Political Culture,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67(December 1995),p.827.
⑨ The Mens Answer to the Womens Petition Against Coffee,London,1674.pp.2,5.(http://eebo.chadwyck.com)
⑩ Coffee-Houses Vindicated in Answer to the Late Published Character of a Coffee-House,London,1675,p.5.(http://eebo.chadwyck.com)
(11) John Houghton,Husbandry and Trade Improved,London,1728,vol.3,p.132.(http://galenet.galegroup.com/servlet/ECCO)
(12) David Hume,The History of England,Indianapolis,Ind.:Liberty Classics,1983,vol.6,p.296.
(13)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41页。
(14) The Character of a Coffee-House,London,1673.p.3.(http//:eebo.chadwyck.com)
(15) G.M.Trevelyan,English Social History:A Survey of Six Centuries Chaucer to Queen Victoria,London:Longmans,Green and CO.LTD.,1942,p.324.
(16) [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6页。
(17) Steele,The Tatler,Tuesday,April 12,1709.ed.George A.Aitken,New York:Hadley & Mathews,1899,p.11.
(18) Steele,The Tatler,“To Mr.Maynwaring”,ed.George A.Aitken,New York:Hadley & Mathews,1899,p.8.
(19) Steele,The Spectator,Friday,March 2,1711,ed.G.Gregory Smith,London:J.M.Dent & Sons LTD.,1915,pp.7—9.
(20) Addison,The Spectator,Monday,March 12,1711,ed.G.Gregory Smith,London:J.M.Dent & Sons LTD.,1915,pp.38—39.
(21)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47页。
(22) Steele,The Spectator,Friday,October 26,1711,ed.G.Gregory Smith,London:J.M.Dent & Sons LTD.,1915,p.142.
(23) Quoted in Edward Forbes Robinson,The Early English Coffee House,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 CO.,Ltd,1893,p.110.
(24) 见:Aytoun Ellis,The Penny Universities:A History of the Coffee-house,London:Secker & Warburg,1956,pp.223—239;[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第27页。
(25) Brian Cowan,“Publicity and Privacy in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History Compass,vol.5,no.4(2007),p.1202,n.9.
(26)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34、35页。
(27) William Bray ed.,The Diary of John Evelyn,New York & London:M.Walter Dunne,Publisher,1901.vol.I,p.289.
(28) Brian William Cowan,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Commercial Culture and Metropolitan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1600—1720,Dissertation of Princeton University,January 2000,p.119,n.5.
(29) 哈贝马斯认为英国咖啡馆的黄金时代是在1680—1730年,见Jürgen Habermas,The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trans.by Thomas Burger,The MIT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91,p.32.《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引中文版第37页将1730年误印为1780年。
(30) Brian Cowan,“Publicity and Privacy in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History Compass,vol.5,no.4(2007),p.1197.
(31) Peter Clark,British Clubs and Societies 1580—1800:The Origins of an Associational World,Oxford:Clarendon Press,2000,p.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