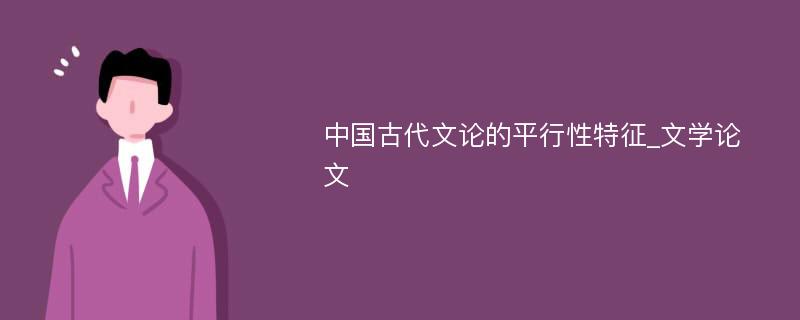
中国古代文论的平行性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中国古代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014(2016)03-0086-10 中国古代文论具有一种平行性特征。这一特征使得古代文论展现出最深刻的民族特色,并从根本上与西方文论区别开来。甚至不妨说,平行性是中国古代文论其他一切特征的原因与来源。因此,本文的任务就在于,揭示古代文论的平行性特征,分析其具体表现,并论述与其相对应的西方文论的切入性特征,以便从比较中更好地把握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并凸显古代文论在全球化语境中的独特意义与价值。 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浩繁著述中,其基本特点,当然不可能不为人们所注意。如钱钟书先生提出“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就是“把文章通盘地人化或生命化”[1]316-326;李又安(A.A.Rickett)教授将中国古代文论从直观经验出发、点到为止的论说方式和特点描述为“闭路式”(closed circuit)的批评世界[2];王先霈先生则阐述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圆形批评与圆形思维”特征[3];叶嘉莹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文论是“偏重主观直觉一派的印象式的批评”,“不长于西方之科学推理的思辨方式”[4];叶维廉先生指出“中国传统上的批评是属于‘点、悟’式的批评”[5]9;欧阳桢(Eugene Chen Ouyang)先生提出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为“文学评点”(literary jottings),而非是针对理论主题的综合分析,使用的是直觉性描述,而非分析性术语[6];黄维樑先生将历代诗话词话的特点概括为“印象式批评”,这种文评方式能有效地、自由地出入于原作的诗情画意之中,但缺陷在于宽泛笼统、粗略含混、不能证伪、难以厘定[7];刘若愚(James Y.Liu)先生、林理彰(Richard Lynn)先生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论述样式往往是不成体系的、零散的,需要发展一种分析系统[8];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指出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系统解释术语的尝试极为罕见,缺乏对定义的追求[9];李建中教授标举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10],等等。但是这类研究,一则不够客观,常常以西方文论的标准来强行衡量古代文论,故其感性、模糊、缺乏体系等特征一直为人们所诟病,又或者一味地彰显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一则偏于笼统概括与描述,尚可进一步推进、深入与具体化。有鉴于此,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特征,仍是一项现实的任务。 一、何为平行性? 所谓平行性特征,指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较少采用逻辑、概念、分析、综合、因果、推理、论证等方式直接切入性地表达观点,而常采用一种平行的方式,即如用比喻、象征、类比、寓言、拟人等方式来间接言说,并使言说内容与评论对象平行的特征。换言之,当中国古代文论家需要阐述“何谓X”时,并不是从与X相交的Y切入分析,而是通过与X平行的X’来暗示,其所依据的正是由平行性所蕴含的相似、同质、同构与共振。 那么,具体而言,中国古代文论是如何平行的? (一)形象的比喻——本体和喻体的平行 中国古代文论家喜用形象化的比喻来品评作家与作品以及表达文学理论观点。在这里,本体和喻体之间是平行的关系。如钟嵘《诗品》有: 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邱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11] 曹旭先生将此称为钟嵘的“形象喻示法”,它“重在‘形象’的‘喻示’,即用‘形象’喻示‘形象’,用自己创造的新的‘批评形象’沟通原来的‘诗歌形象’。换句话说,这是把‘批评’理解成‘创作’,把对评论对象的理论阐述,用创作的方式表达出来,最典型集中地完成感性—理性—感性的批评过程”[12]166。换言之,批评家创造的新的“批评形象”与他的评论对象即原来的“诗歌形象”是平行的,“批评”和“创作”是平行的。正如叶维廉先生所说,这种批评“在结构上用‘言简而意繁’及‘点到而止’去激起读者意识中诗的活动,使诗的意境重现,是一种近乎诗的结构”[5]9。也就是说,钟嵘用与诗平行的结构,去唤起读者对诗境的再造,进而去迹近原先的诗境,这是一个几重平行的过程。钟嵘这里并没有运用概念、逻辑、推理等去直接分析两位诗人及其诗作的具体美学特征,而“四句之中,只用二个比喻加两个形容词,十六个字便品评了两位诗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当你读完这十六个字以后,相信你对这两位诗人的诗风特征,自会有一种妙不可言的领悟,感受到甚至比定性分析更清晰的内容”[12]166。从作为评论对象的“诗歌形象”到批评家创造的“批评形象”,完成了一次跃升,即从感性形象到理性思考再到感性表述的批评过程,这种跃升只有在二者平行时才可能发生。平行则一方面可以拉开批评距离,一方面可使两种形象同质沟通,令人感受到比切入性的逻辑分析更清晰、更全面、更深刻的内容。 再如刘勰在论述“文—质”关系时说道: 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文心雕龙·情采》)[13]537 要说明文依附于质、文以质为本体的道理,刘勰并没有直接分析,而是用两个比喻来强调质的决定性意义;要阐述内在的质有待外在的文来显现的观点,刘勰亦没有用逻辑推理,而是再以两个比喻来凸显文的重要性。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刘勰总以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平行性,让人从形象中把握抽象,从具象中捕捉玄妙。即使自20世纪以来,《文心雕龙》一直被奉为中国古代文论史上最具理性特征、最富体系性的文论巨著,但刘勰依然是平行性传统中的继承者与发扬者。 又如陆机《文赋》有: 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14] 探讨创作心理问题和作家思维活动,实在是“良难以辞逮”。在平行的骈文中,陆机却用两个精彩的比喻将写作时源自语言的痛苦与快乐描绘得贴切之至,痛快淋漓,令人拍案叫绝。若以陆机的理论反观《文赋》,他实在做到了“意之称物”“文之逮意”,而他之所以能将此理了然于心、于口、于手,其一就在于他运用了平行的形象比喻,让人立即“逮”到他要表达的道理。 (二)意象或意境的平行——默示与自我指涉 当康德进行美的分析时,他从质(无功利的功利性)、量(不涉概念而有普遍性)、关系(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情状(来自共同感的必然性)等四个方面将审美判断的特征逻辑严密、体系周全地条分缕析[15]。但是当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家面对类似问题时,却并非如是处理。 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便是平行性文论的代表作。试举两品: 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犹之惠风,荏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曰载归。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16]5-6 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16]12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各以韵语十二句体貌之”[17]。也就是说,二十四首论诗诗,各用十二句比喻的韵语,塑造不同的意象,提示二十四种诗境风格。清代孙联奎《诗品臆说自序》称《二十四诗品》“意主摹神取象”[18]。“摹神取象”亦即对诗境的描绘。许印芳《二十四诗品跋》:“比物取象,目击道存。”[19] 实际上,这二十四首论诗诗自身的风格及其所塑造的意象和意境,分别与其所欲提示的二十四种诗境风格是一一平行的。即如“典雅”一品,司空图并不分析也不论述什么是典雅,而是描写了一位隐居佳士的形象,又用“春”、“雨”、“晴”等所表征的悠然时光和“茅屋”“绿阴”等所提示的幽静空间勾勒出一片淡泊岁华,用“竹”、“菊”、“书”、“琴”、“玉”等所象征的雅士品格和“白”、“绿”等所渲染的高洁色彩烘托出一片怡远意境,让人从云鸟戏逐、飞瀑叠山中,从品酒赏雨、抚琴吟诗中,更清晰、深刻地领悟到“佳士”的精神状态与内心世界,领悟到所谓典雅。换言之,“典雅”一品塑造的典雅意象及意境,与它本身所要表述的对象即典雅的诗境风格是同质平行的。 这一平行性特征使得它似乎什么都没有说——没有分析、没有解释、没有界定。但是读者却可以从一个个意象中领悟到这二十四种风格的真谛。易言之,二十四诗品乃是自我指涉的。 再如明代邓云霄《冷邸小言》有: 问:“诗何谓真‘丽’?” 曰:“‘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 问:“何谓真‘壮’?” 曰:“‘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如此类推,可得其解。”[20] 当邓云霄要解释“丽”和“壮”的意境时,并没有直接分析,而是各用两联诗句来烘托,让人从诗境中去体认相应的审美体验与风格特征。在这里,范畴与诗句是平行的,是可以互释的,范畴概括并标示了诗句的意境风格,诗句又诠释了范畴的诗意内核。汪涌豪先生指出:“古人一定觉得,这样形象生动的表述很适合范畴内涵的传达,而且,因其形象生动,这种内涵还最大程度地保存了它原有的气足神完。”[21]“气足神完”正赖平行而得以存在。 批评如是,批评之批评亦如是。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 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22]7 近人陶明濬《诗说杂记》卷七则释曰: 何谓高?凌青云而直上,浮灏气之清英是也。何谓古?金薤琳琅,黼黻溢目者是也。何谓深?盤谷狮林,隐翳幽奥者是也。何谓远?沧溟万顷,飞鸟决眦者是也。何谓长?重江东注,千流万转者是也。何谓雄浑?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者是也。何谓飘逸?秋天闲静,孤云一鹤者是也。何谓悲壮?笳拍铙歌,酣畅猛起者是也。何谓凄婉?丝哀竹滥,如怨如慕者是也。[22]7 关于诗之九品,严羽只给出了寥寥数语,但当陶明濬来阐释时,并不单刀直入地分析,而是用意象、意境间接地描绘、比拟、象征,让人从“荒荒油云,寥寥长风”中体会“何谓雄浑”,从“盤谷狮林,隐翳幽奥”中体会“何谓远”,而这二者实际上是平行的。“笳拍铙歌,酣畅猛起”的意境与“悲壮”的意境是平行的,“沧溟万顷,飞鸟决眦”的意境与“远”的意境是平行的。换言之,当古代文论家需要阐述“何谓X”时,并不是从与X相交的Y切入分析,而是通过与X平行的X’来暗示,其所依据的正是由平行性所蕴含的相似、同质、同构与共振。因此,由X’及于X,本质上乃是一种自我指涉。 (三)平行蒙太奇①——由彼及此的类比 类比是原始时代的典型思维方式,一如维科所指出的那样:“人在无知中就把他自己当作权衡世间一切事物的标准”[23]201,亦即以己度物和后来的取物喻人。 在文论领域,严格意义上的类比不仅仅是比喻、取象或拟人,而在于当需要论证A如何时,并不从A自身的逻辑着手,而是先指明B即如是,然后便得出A亦如是。因此,这里有一个隐含的逻辑——A和B之间是类比的、平行的关系。只有当A与B平行时,由一个现象或规律于B成立,才能推出这一现象或规律于A也同样成立。这实际上是一种类比论证。譬如董仲舒在论证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时,并不像孟子或荀子那样,从性善或性恶的逻辑起点开始进行推理,而是认为自然宇宙中天尊地卑,那么人类社会中便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董仲舒是在用自然宇宙来论证人伦秩序,同时也为自然宇宙赋予了人伦意味,天与人是平行的、相互感应的。 刘勰也常常以自然来论证文学,直接以自然作为文学的依据。当他需要论证文学如何时,不是从文学本身来进行分析,而是认为自然如何,那么文学就如何,将自然的规则平行地移入文学中。他通过“道法自然”这一逻辑,通过骈文这一形式,完美而精致地把自然世界和文学世界并列起来,形成“自然—文学”的平行蒙太奇。 例如,当刘勰探讨文学本质问题,亦即“人之文”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人之文”与“道”的关系时,是通过自然来平行类比论证的。《文心雕龙·原道》开篇便讲:“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13]1日月山川是天地之文,天地通过日月山川来显现道,这是自然之道。接着,在由天与地共同构成的平行结构中,作为天地之心的人于其间“仰观吐曜,俯察含章”,刘勰指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也就是说,人用“文”、用“言”来显示道,语言、文学即是人类言说、表现道的独特符号,而这一过程是自然而然的,一如天地用日月山川来显现道,所以仍是自然之道,此即文学的本质。随后,刘勰又突然将镜头拉远,形成一个大全景,他说:“傍及万品,动植皆文。”刘勰利用骈偶构成自然与人为的平行对比,一会儿认为“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有逾”、“无待”强调自然之美;一会儿认为“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调如”、“和若”又以人为之美作为标准。在几个特写之后,刘勰依然强调“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无论是动物的纹理色彩,还是云霞草木,无论是风林,还是泉石,它们都通过自身的文采来表现“道”,那么,“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人之文更属自然而然、理所当然。所以接下来,刘勰便梳理了一部从伏羲到孔子的、简明而璀璨的中华文明史,得出结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而刘勰之所以弘扬人文,正以“自然之道”、“道法自然”作为逻辑论证的终极依据。在刘勰看来,人文与自然之文乃是平行的,由自然如是能直接推理出人文如是。 再如,当刘勰要论证“丽辞”的合理性时,仍然以自然作为依据,诉诸自然与文学的平行性,认为:“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13]588既然自然界中事物必双,那么文辞便自然成对。刘勰并不从文学作品本身着手去分析丽辞的依据,而是认为骈俪的现象与规律在自然界中成立,那么在文学上便同样也成立。 换言之,在刘勰这里,自然与文学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比喻关系,而是一种必然性推理,由自然可以直接推出文学,自然可以直接作为文学的依据,二者之间是平行的。唯有当自然与文学平行时,由自然如何推出文学如何才是有效的、合理的。 (四)迂回与进入——庄子的寓言 庄子自道其言说方式为:“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24]947寓言其实是庄子为了避开语言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而采取的一种独特的话语策略,即“藉外论之”。例如,当庄子要表达“言不尽意”之义时,除了使用一些充满相对性和反讽性的语句来达到语意的深处之外,点睛之笔便是寓言: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矣!”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24]490-491 借儒家圣贤君子系统中的“桓公”(庄子虽未言“齐”,但他利用人们惯常的前理解,欲盖弥彰地影射出了“齐”。“齐”虽不在场,而“桓”乃良谥,仍是儒家式的贤君)和虚构的神乎其技的“轮扁”,庄子设计了一个与社会历史相平行的寓言世界,用迂回的方式使话语与现实拉开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接着,庄子进行了“倒置”——由满口道家话语的轮扁来教育儒家系统内的桓公,通过这个“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故事间接地暗示出“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的道理,由此实现言说策略的有效性,由平行的寓言表征出隐藏的意义。 弗朗索瓦·于连认为:“言语的一切间接迂回使我们达到了实在的根本。”[25]在我们看来,平行即是一种间接的迂回,它通过寓言、隐喻、形象、类比等与言说对象以及要表达的内容拉开距离,使人能够由此及彼地推想、体认、领悟;但同时它又能够比用因果逻辑、条分缕析、理论建构等来直接切入取得更加意想不到的效果。 (五)散漫的话话——影子的诗性平行 当中国古代文论与其对象平行时,就必然沾染上其对象亦即文学本身的特点,如诗性、散漫,形成一种同质关系。如果借用柏拉图的比喻,中国古代文论即是与文学平行的影子,它在平行中“摹仿”文学本身的诗性。 这种平行的方式由来已久。孔子自称“述而不作”[26]153,于是人们只能从《论语》所记载的他与弟子之间的交谈对话、行为举止来理解和把握孔子。孔子实际上摹仿了天: 子曰:“予欲无言。” 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6]464 换言之,孔子是从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运行中体悟到“性”与“天道”的。这恰恰和人们从《论语》记载的零散言行来理解孔子是一样的。或者说,孔子自我呈现的方式摹仿了天的自我呈现方式,二者是平行的。宇文所安认为:“《论语》这样的著作恰当和真实地把‘善’展现为一个真正善良的人的随时随地地样子。从表面看,它必然是破碎的、不连贯的,其整体性只能到那个作出具体言行的人的内心中去寻找。”[27]一如天的完整性要通过时序更替、万物生长的那种鲜活的零散体现出来一样。 孔子摹仿了天,后代的诗话又摹仿了《论语》。诗话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主要话语模式。从外在形态上看,每一部诗话都由数“则”篇制短小的诗话条目汇集而成,它的外观呈现为一则一则的条目式。若进一步观察便不难发现,每一则条目的内容充分独立,能够自成一体;且“则”与“则”之间在布局上并无严格的逻辑关联。也就是说,诗话本身是无序的松散整体,而不是像西方文论那样的严密逻辑序列。 诗话的对象或曰场地是诗歌。这个场地不是一个有某种逻辑贯穿始终的、系统性的独立整体,而是由为数众多、篇制短小的诗歌汇集而成的松散整体。诗歌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各可自成一体。因此,所有的诗歌在总体上也呈现为无序性的散点分布。诗话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它的场地的这种特质。如果一切诗话汇集在一起,那么将与诗歌总体在整体上完全同构。可见,这是创作层面和批评层面的同构相应,是一种诗性的平行。在这样的平行中,诗话使用的不是线性逻辑的严密推理、论证,而是印象式的批评,和它的对象即诗歌本身一样带有诗意,因为二者是同质平行的。 从散漫的诗话中,诗话作者所看到的并不是凌乱、破碎与断裂,而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完整的统一。因为他所感受到的世界对他的呈现方式以及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正是如此。那是一种散点透视式的世界感受,它与“道生万物”所描绘的世界生成模式和“月映万川”的呈现方式是一致的。易言之,诗话的完整性正存在于其散漫的话语之中。诗话通过平行地摹仿散漫来达到完整性。与此不同,西方那种定点画法、焦点透视式的世界感受则是要围绕着一个唯一的认知主体视角去切入、去观察、去组织世界。 二、平行何如? 那么,平行性给中国古代文论带来了哪些结果?表现为哪些特征?或者说,中国古代文论的特征如何能通过平行性得到解释呢? (一)平行的游戏 现代语言学大师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并没有必然性的关系[28]。转换到文论领域,实际上,中国古代文论无论范畴还是比喻都表现出能指的诗意滑动与平行游戏。 黄维樑先生曾用调侃的语气描述过一片“印象式批评的文字迷宫”: 由于神、气、韵、致、风、格等都是抽象名词,听起来难免使人有神秘不可捉摸的感觉。这些抽象名词,在诗话词话作者笔下,可以自由排列组合,比七巧板还要灵活。倘若再加上一二其他字眼,效果简直如万花筒一样。下面所举,都是据实从诗话词话摘下来的,并非出于笔者的独撰。请看这个抽象的花花世界:风韵、风神、风味、风调、风致、风度、风力、风骨、韵味、韵致、韵度、格韵、意趣、意兴、意味、意气、气势、气韵、气调、气格、气骨、骨气、神气、神韵、神味、神情、神理、神骨、情韵、情味、情致、兴味、兴趣、骨力、格致、格制……[7]78 这些极难彻底辨清含义的抽象名词,令人们争论不休、无法诠释。黄维樑先生又说: 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上面这些名词,至少有一半可以用简简单单,现代最为通行的“意境”或“风格”二词概括和替代。……我们还会醒悟到:这些乱人眼目的名词,不过是印象式批评家利用来表达雄浑、飘逸等印象而已。……换言之,气象、风韵这类字,率多只是陪衬物而已,雄浑和飘逸这类形容词,才是批评家真正要传达给读者的。[7]79 换言之,气象、风韵这类抽象名词,所要概括和描述的都不过是作品的审美特征,是“风格”的代名词。如果将气象、风韵等一系列抽象名词视为“能指”(signifier),将“风格”视为其“所指”(signified),那么,这二者之间是平行的。正因为平行,所以气象、风韵等“能指”,可以无限地同质替换,可以任意滑动,可以互释共通,并最终形成能指的游戏。这很像是德里达所谓的“延异”(differance)。当然,在这里,“延异”所表达的是中国古代文论范畴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平行以及由此而来的能指之间的同质替换。这一点与西方文论范畴那种切入性的、线性因果式的特征迥异。 不仅范畴,古代文论中的比喻亦然,本体和喻体之间同样也是平行的游戏。文论家常常“近取诸身,远取诸物”[29]153。刘勰云:“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13]650颜之推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膂,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30]实际上,他们是通过“近取诸身”的比喻塑造了一个与文体平行的人体。叶燮在体系性与逻辑性方面常与刘勰并称,然而他却是最喜爱使用比喻来说理的文论家。当叶燮论述古今诗之工拙上下时,以房屋为喻: 汉魏诗,如初架屋,栋梁柱础,门户已具,而窗棂楹槛等项,犹未能一一全备,但树栋宇之形制而已。六朝诗始有窗棂楹槛屏蔽开阖。唐诗则于屋中设帐帏床榻器用诸物,而加丹垩雕刻之工。宋诗则制度益精,室中陈设,种种玩好,无所不蓄。大抵屋宇初建,虽未备物,而规模弘敞,大则宫殿,小亦厅堂也。递次而降,虽无制不全,无物不具,然规模或如曲房奥室,极足赏心;而冠冕阔大,逊于广厦矣。夫岂前后人之必相远哉!运会世变使然,非人力之所能为也,天也。[31]62 刘勰则喜用“器物之喻”,如规矩、绳墨、辐毂、檃栝、矫揉、杼轴、铸型、模范、陶钧等等,以器物制作的参照准则来比喻文章写作的法度与典范[32]。李渔用缝纫为喻阐明戏曲创作规律:“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后顾数折。”[33]9-10又有以“锦绣”喻文者[34],又有以“镜花水月”喻诗境者[35],等等。这些“远取诸物”的比喻亦表征出诗文之道与神明之德、万物之情的平行。 (二)诗性思维的平行本质 这样一来,中国古代文论的许多特征便可以得到解释。正因为平行,所以中国古代文论具有整体性和生命性,它是整体的、平行的取喻、比拟,而非切入的分析、剖擘、肢解,所以极大程度地保持了对象和内容作为生命有机体的生气灌注。正因为平行,所以中国古代文论具有模糊性、间接性和形象性,它用迂回的方式去平行地类比、譬喻,而不使用严格的界定、清晰的概念和明确的定义、严密的体系,所以它到处充满了朦胧的印象、模糊的描述和感性散漫的只言片语。 因之,中国古代文论常常被认为是富有诗性特征的。维科认为:“诗性的智慧……一开始就要用的玄学就不是现在学者们所用的那种理性的、抽象的玄学,而是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像这些原始人所用的。这些原始人没有推理的能力,却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23]181-182所以,维科指出,最初的比譬、隐喻、转喻、借代、替换、类比、寓言等等都是诗性智慧的必然结果。 在我们看来,诗性思维其实从根本上是一种平行性思维。它必须运用精神性内容与形象之间的某种相似性、平行性来使认识和创造得以成立。例如“最初的诗人们就用这种隐喻,让一些物体成为具有生命实质的真事真物,并用以己度物的方式,使它们也有感觉和情欲,这样就用它们来造成一些寓言故事。”[23]200在这里,“以己度物”成立的前提便是平行性。只有当最初的诗人把万物看作是与自己平行的、同质的生命体时,才会认为万物都和自己一样有感觉、有情欲。按照维科的说法,原始人类是欠缺推理能力的。他们并不能用概念、理性、逻辑等去分析万事万物的性质,而只能通过平行性去感觉和想象万物,所以“人在无知中就把他自己当作权衡世间一切事物的标准……人把自己变成整个世界了”[23]201。换言之,通过平行性,原始人类与世间一切事物在感觉上和想象上都可以同质替换,于是便把自身的生命性感受推广到了整个世界。 这种平行性思维也与汉字的特征有着莫大的关联。和字母文字的以音表义相比,汉字更加偏重于以形表义。早在1921年,心理学家刘廷芳先生便通过实验发现,汉字字形对字义的作用大于字音对字义的作用[36]。40年代末,著名语言学家艾伟先生在《汉字问题》中提出,汉字的基本辨义原则是“形—义关系”[37]。换言之,汉字有着通过字形来表义的特征。另一方面,汉字的字形又极富象形性,它具象地指称着物体形貌,通过“观物取象”从而“立象以尽意”的方式来表义。也就是说,汉字不是抽象形式化的,不是独立于物象之外的,相反,它并不脱离物象,且以字形状物为表义的支点。概言之,汉字乃是“及物”的,因而它也是形象的、蕴含着直观经验的。这样一来便出现了汉字世界与物象世界的平行,当我们使用或看到某个汉字时,它悠长丰富的意义总是在指称着某个物象,永远在对应着某个形象。冯黎明先生指出:“这种对自然物象的外观的展示使人在文本中时刻感受到生活世界的物性存在,而不致走向超验的纯观念境界。……汉语以字为本位的状物使汉语文学的自然物象呈现为一种平列对应的构成方式。”[38]在这里,诗与画是平行的,字与象是平行的,文字的表意世界与字形所产生的具象的、有着视觉联想意义的物象世界是平行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字的“及物性”恰恰极大限度地保持了诗性思维的特征,它或许就是中国古代文论能够在漫长的历史时间中一直富有平行性的原因。 (三)天人合一 中国古代文论的终极价值是从平行走向合一。 中国古代文论所推崇的往往都是文学作品中情景交融、物我一体、心物赠答、意与境偕、主客合一、天人合一的艺术特征。这种特征恰恰需要平行性来完成。只有二者是平行同构的时候,才有可能亦此亦彼并最终重合;而切入分析者永远是异质的,界限分明的,不可能走向合一。 从根本上说,中国古代文论与文学是平行的,所以文论沾染了文学性与诗意。即使从批评文体来看,从陆机的骈赋到刘勰的骈文,从庄子的语言到司空图的论诗诗,从司马迁的书信到韩愈的序跋,中国古代文论的载体常常是诗性的,与文学平行的,更是同质的。它用文学的笔调来反思文学、评论文学、鉴赏文学,它通过平行的方式来让人见出一种直觉的跃升与一种若即若离、亦此亦彼的距离。 同时,中国古代文论又以无生命者作有生命者看,以非人作人看,换言之,把文学视为生命、视为人,将文学生命化、人格化。因此,中国古代文论实际上塑造了一个与人平行的文,一个与万物平行的人。所以,人有气,文亦有“文气”;人有情,故“以类万物之情”;对人物进行品藻的用语,慢慢便会延伸到对书画乐文的品评上;树叶有根干枝叶实核皮壳、虎兕有皮毛色泽,文便相应地有了形式和内容的比喻性区分……人们总是试图塑造一个与人平行的文,在这样的文学作品中,文如其人,作者的性格和作品的体貌表里相符,同质平行。所以当敖陶孙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39]时,我们可以确信人之性格和文之风格在这里是有可能平行以至浑然一体的。 因此,中国古代文论塑造出的是一个万物平行的世界。天地、日月、山川、动植万品,直至人和文学,一切都是平行的,所以它们之间才有可能同构共情,所以人才有可能“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9]153。这是一个天人合一的世界,是平行的最终与最高指向。 三、为何平行? 那么,中西文论为什么会有平行与切入的差异呢?究其根本,在于中西文论家对待文学作品的态度和立场有所不同,也就是精神价值取向特征不同。西方文论家把文学作品视为客观对象,所以要剖析毫厘、擘肌分理,如同用手术刀切入进行解剖。而中国古代文论家则将文学作品看成是与自己同质平行的活生生的生命整体、气足神完的主体,所以去体认、品味、涵咏。钱钟书先生认为,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一个特有的特点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1]318。这便是人与文的平行并立,即把“我”的情感体验平行移动、注入、投射到“文”中去分享“文”的生命。李春青先生指出,西人提倡的是一种“主体缺席”式的研究,其中贯穿着一种“理性逻各斯”或“语言逻各斯”,主体精神被这种“逻各斯”所消解;而中国古人则将作品还原为活的精神状态、情感、意趣来体会、品味、咀嚼[40]。这正是对待文学和文论的态度与立场不同所带来的差异。换言之,平行是两个平行的主体,而切入则一主一客。一如“庄周梦蝶”是平行的,“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24]112,而弗洛伊德则要切入梦去作“梦的解析”。 由精神价值取向的不同,便必然带来思维特征的不同。西方文论往往从抽象的概念或观念以及清晰明确的定义或界定出发去切入,而中国古代文论则从体认、体验、体悟出发去平行地类比。譬如,即使像“道”这样看似比较抽象的范畴,老子亦绝不会去作纯粹逻辑的设定,而是去体认其所包含的感性内涵,感到“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41]156,然后再将这种朦朦胧胧的心理体验用描述性的而非定义式的话语表现出来:“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41]169。古代文论家亦不对具体的作家作品下定义或作分析,而只是用诸如“雄浑”、“沉郁”、“飘逸”、“淡远”等词去描述某种感觉、印象或审美体验,让人们从这种描述和阐发中去体认其所指的那种“意境”、“神韵”、“气象”或“妙趣”。这些形容词和名词都无法精确地界定,只能去体认。古人就是以这种平行的类比、移情、体认的方式去面对外在世界的,所以他们总是能够在外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总是在追求一种情景交融、心物一体、主客浑同、意与境谐、天人合一的境界。 平行性的思维特征也必然显现为平行性的话语特征。即间接的、迂回的、模糊的、朦胧的、诗性的、形象的表述方式。与其说这是古代文论基于语言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而使用的话语策略,毋宁说是一份不忍破坏生命整体的诗意。《庄子》曰:“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24]83此“封”为封域界限,“常”为定[24]83-84;亦可理解分析、剖解,定性、绝对。在这个意义上,切入性的话语将致“道”亡,而平行性的话语则可保持“道”的“未封”状态和“言”的无限性。切入性的话语是用逻辑和理性解剖文学文本,而平行性的话语则将气韵生动的有机整体保存完好,使得活生生的意蕴通过平行的类比、比喻、象征等而暗示出来,故而有着无限的阐释空间。切入是异质话语的相交,平行则是同质话语通过距离和亦此亦彼的平移、置换等营造出的最终合一。 四、似非而是的平行与似是而非的平行:中西文论间暗昧地带的辨析 或许有人会说,其实中国古代文论亦不乏说明性的批评,不无分析、归纳等方式。由表面观之的确如此,但深而究之则中国古代文论即便是论说性的文字却仍与西方分析性的批评有着本质的不同。 譬如叶燮《原诗》论杜甫“碧瓦初寒外”、“月傍九霄多”、“晨钟云外湿”、“高城秋自落”[31]30-32;吴淇《六朝选诗定论》论陶潜《饮酒》其五;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论杜甫《春望》;等等。因上述批评篇幅较长,兹且录一段,以见其神貌: 如玄元皇帝庙作“碧瓦初寒外”句,逐字论之:言乎外,与内为界也。初寒何物,可以内外界乎?将碧瓦之外,无初寒乎?寒者,天地之气也。是气也,尽宇宙之内,无处不充塞,而碧瓦独居其外,寒气独盘踞于碧瓦之内乎?寒而曰初,将严寒或不如是乎?初寒无象无形,碧瓦有物有质;合虚实而分内外,吾不知其写碧瓦乎?写初寒乎?写近乎?写远乎?使必以理而实诸事以解之,虽稷下谈天之辩,恐至此亦穷矣。然设身而处当时之境会,觉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划然示我以默会想象之表,竟若有内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实相发之。有中间,有边际,虚实相成,有无互立,取之当前而自得,其理昭然,其事的然也。[31]30-31 叶燮将一句杜诗的多重复义娓娓道来,将寥寥五字带给读者的审美体验细腻辨出,甚至颇有欧美新批评的细读功力。然而从根本上说,它仍然不出平行性的范围。首先,叶燮认为“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划然示我以默会想象之表”,意味着他并不相信诗有某种“逻辑的结构”可以切入地剖析。其次,叶燮说“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表明他想尽力保留这句诗所给予读者的直觉的、浑然的、形象的、具体的审美经验,因之平行地去迹近、逗引这句诗的艺术性真谛,而并不从抽象的理路和有限的言筌去切入分析。再次,叶燮使用的是疑问句,这透露出了他的批评姿态、态度与精神价值取向,即对诗作的尊重及与读者的对话,所以他想最大限度地存留诗句审美呈现的完整性与生命性,这无疑源自于平行的态度。对此叶维廉先生指出:“疑问句的分析方法,与凶巴巴而来的权威性的肯定句的分析是不同的:疑问句有待读者的点头,叶燮把心感活动非常技巧地还给读者;在后者的情况下,一切要听批评家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叶燮给了我们非常有效的说明性的批评而无碍于美感经验呈示之完整,这正是由于他了解到诗的‘机心’,‘使必以理而实诸事以解之,虽稷下谈天之辩,恐至此亦穷矣’。而缺乏了这种基本的顾虑的批评家,必将诗分割到无可辨认而后已。”[5]8换言之,叶燮不是通过擘肌分理的解剖臻于诗之三昧境地,相反,叶燮的细读与分析其实源自于并最终指向平行。 西方文论偶尔也会出现疑似平行性的特征。例如柏拉图的摹仿说看似也承认理念世界、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平行关系,尤其“影子的影子”之喻更增添了平行的效果。然而这三者的平行其实从根本上显示了理念对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穿透与切入:理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都依存于理念。在这里,“摹仿”的目的和功能并不是趋近、类同或合一,而是划分、区隔与远离,并使理念、现实、艺术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明晰,使真理和艺术隔得越来越远。因此,这是一种伪平行,也就是说,它以看似平行的方式更好地完成了切入,平行只是其逻辑分析的一种方式和手段,透露的仍然是浓郁的理性主义精神。 再如以人喻文,即将文章比作人体。朗吉努斯《论崇高》云:“在使文章达到崇高的诸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莫如各部分彼此配合的结构。正如在人体,没有一个部分可以离开其他部分而独自有其价值的。但是所有部分彼此配合则构成了一个尽善尽美的有机体。”[42]柯勒律治说:“诗的精神同一切其他生命能力一样……必须得到具体体现从而展示自己;但既为生命体,就必定有组织——何为组织?这岂不就是部分与整体相连,因而各个部分都集目的和手段于一身了吗!”[43]这些比喻看似和中国古代文论最喜用的以人比文极为相近,但实际上仍然貌同心异。第一,它往往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和论证技巧出现,是非常严谨的“始、叙、证、辩、结”修辞法则和论证逻辑中的一环。第二,它从根本上将人与文看成是异质的,而非同质合一的,这表明了与中国古代文论迥异的批评态度和价值取向。西方文论的以人喻文更像是人体在X光下的透视与显影,是各要素各部分如同精密仪器般的有序结构;中国古代文论的以人喻文则是将动物、植物、人体、文章等平行世界氤氲得浑然一体,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万品”全都晕染在一起。一如李渔所言:“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倘先无成局,而由顶及踵,逐段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33]4中西文论视域下的“以人喻文”便似有化生全形与逐段滋生之别。第三,这两种比喻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评价态度,其一是人与“万品”的平行并立,其一是人对“万品”的俯视与剖析,在前者,人的生命与身体结构着文论的思维,在后者,工具理性的分析控制着人的生命、解剖着人的身体。因而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在西方,那些把文章比作人体的文学批评大多“不过是偶然的比喻,信手拈来,随意放下,并未沁透西洋文人的意识,成为普遍的假设和专门的术语”[1]320,文和人永远是分立的、异质的二元。 所以,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切入性特征是似非而是的平行,熏陶着它的依然是平行的精神;西方文论中的平行则是似是而非的平行,是为了切入,是剖析的工具。 概言之,平行性特征是中国古代文论所固有的根本特征,它内在隐藏着的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精神价值取向,亦即将文学视为与人并立的有生命的整体,而不是分析解剖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平行性,正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精神之所在。 ①平行蒙太奇,电影术语,指在镜头语言的剪辑上将几条情节线索并行表现,分别叙述,或几个事件相互穿插表现,最后统一在一个完整的情节结构中。这里喻指类比论证由A直接论证B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