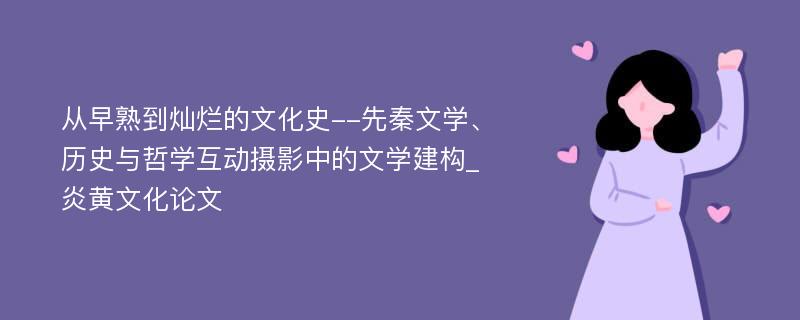
由早熟到辉煌的文化史路——先秦文史哲互摄中的文学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史哲论文,文化史论文,先秦论文,辉煌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象古希腊文化是欧洲文化的源头和高峰一样,先秦文化则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高峰。而在源头和高峰时代形成的先秦文学,不仅是先秦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它和总体文化构型之间存在着互涵互动的关系:文学受文化建构过程中整个作用所驱动,同时又以自身的变革参与了文化建构;而文化构型,也不是静止不变的,它是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中,因此,文化或文学的生命和运动,实则又是在一条具有既定物质条件而又充满了人的创造精神的历史道路上形成和展开的。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是在其独特的历史道路上构型了自己的文化,我国文化的开创、奠基期——先秦时代,则是在“亚细亚型”的历史道路上,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历程,由“早熟”而走向辉煌,建构了一个蓄积丰厚、“大器晚成”,因而以气魄宏伟、博大精深为特色和底蕴的民族文化体系。同这一文化体系一道生成并同步发展的先秦文学,即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以文史哲互摄的架构,承载着一个伟大的文化价值体系,揭开了中国文学史上恢宏壮丽的篇章。
一 早熟的历史及殷周之际发轫的文化转型
我们对开创、奠基期的先秦文化作一整体性的审视,且与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加以比较,可以确认,先秦文化是在不同于古希腊的亚细亚型的历史道路上生成、发展,经历了由“早熟”到辉煌的历程,显示出大器晚成、有容乃大的民族特色。
与希腊相比,起于大河流域农业文明的中国古代,适应着较为有利的自然条件,早在公元前21世纪,便走出野蛮状态,在华夏大地升起文明的曙光,显示了自己早熟的历史和文化;而古希腊则在公元前8世纪叩开文明时代的大门,在另一种自然和社会条件下开启了西方的历史。古代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经历了不同的道路,有“早熟”和“正常”的两种类型,而“早熟”与“正常”相比,又表现为东方奴隶制与古典奴隶制的区别:前者形成于农业文明的土壤上,后者建立在城邦经济的基础上,二者在经济结构、政治体制、阶级关系、劳动分工、文化构型以及旧传统的瓦解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希腊凭借爱琴海区域海陆交错,适合于建立城邦并有利于商业发展和扩张海外市场的条件,在古典奴隶制的基础上,其文化以迅疾而猛进的气势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不但以神话为“土壤”和“武库”,产生了对后世具有不可企及的魅力的史诗、悲剧、喜剧以及绘画和造型艺术,而且产生了足以代表人类理性精神和科学成就的各种哲学流派,由此而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光辉起点。对比观照,形成于农耕经济基础上,历时一千余年的中国夏、商奴隶制社会,带有“早熟”的特点,走的是“维新”的特殊途径,建立的是宗教族隶制度。与这些相联系的是,夏商奴隶制时代的文化更多地保留了原生社会的模糊性与混融性:文明的曙光虽已从华夏大地升起,但“人神杂糅”的迷雾仍未驱散,图腾巫术崇拜中朦胧的理性因素,仅仅上升为一种天帝宗教观念,祖先崇拜、祖帝一元的观念成为普遍的信仰,理性和哲思尚在“天人宗教”的形式中孕育、生长;诗歌乐舞还作为宗教仪式的构成部分没有完全取得独立的性格,民族史诗一类叙事文学也仅露苗头,不超过《玄鸟》、《生民》等雅颂祭歌;文史则杂糅着“怪诞不经”的神话,处于甲骨卜辞的简单记事的水平。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中国较早地跨入了文明时代,然而,与此相应,夏商所建立的则是不发达的奴隶制,其意识形态也与巫术宗教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周灭商,行封建、立宗法,建立了早期封建制——领主封建制。殷周之际实现的奴隶制向领主封建制的变革,在中国政治制度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周代商,实行了封国制度、宗法制度、采邑制度、世卿制度,伴此而来,文化上则经历了一次由巫术文化向“人文”文化过渡的重大转化[①],其标志便是“以德配天”、“以德辅天”和“敬德保民”等天人合一观念的确立,由此,宗教观念逐渐为理性精神所取代,神本位开始了向人伦本位的转化。对我国文化产生了定位性深刻影响的《易经》与《诗经》,就是在殷周之际巫术文化向人文文化转型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易经》的意义在于:它代表了华夏民族早熟的文化智慧,以宗教玄秘为道德理性,表达了人们的血缘情感和对生命本体的感悟,人与世界的联系和潜在的完满性。它在中国由巫术文化向人文文化转型的起始阶段,确立了中国哲学的走向:把宗教哲学化,化为伦理的文化,它不仅奠树了中华民族理性精神的第一块基石,而且蕴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基因。《诗经》的意义同样在于反映了殷周之际巫术宗教文化向人文文化的转型。不同的是,它以一部周民族(少数作品除外)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在五彩缤纷的人生图像上,形象地表现了人伦文化的精神,无论是“国风”还是“雅”、“颂”都渗透着敬德保民、事天近人之类的观念,各种题材(农事、征戍、爱情等)的诗篇所蕴含的乡土情蕴、伦理情味以及关注现实人生的态度,都体现了中华民族根源于自己的历史特点和精神性格而形成的文化精神。范型了中国古典诗歌发展与走向的“风骚”传统,即由《诗经》而发轫。文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易经》和《诗经》,不仅从民族智慧和民族情感这两大方面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确立了中国文化的走向,而且由它们发轫的文化转型,孕育着一个文化高峰时代的诞生,开辟着一条通向辉煌的文化史路。
二 春秋战国的社会转型与轴心期文化的到来
继殷周之际的社会变迁后,被史家们称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春秋战国之世,实则是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过渡的社会转型期,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全面剧变的时代。
领主封建制为地主封建制所取代的这个社会转型过程,从春秋初叶开始,至战国后期完成,演进凡四百年,其进程可缕列的大略情况是:井田瓦解,私田代兴;王权衰落,诸侯崛起;礼崩乐坏,上下交征;天下纷争,竞逐统一;学下私人,士群活跃;工商勃兴,文化汇通;哲学突破,艺术繁荣;学术分裂,复归整合……上述事实已为大量先秦文献和出土文物所证实,从而可知春秋战国时代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的社会转型,不仅是比殷周易鼎、领主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更为深巨的社会变革,而且是中国古代社会由“早熟”走向“成熟”的一次决定性的飞跃,这个飞跃,使中国与希腊同步进入了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亦即西方学者卡尔·雅斯贝斯所说的“人类文化的突破期”。从世界历史的宏观视野来审视,可以发现人类文明的进程有其整体性的规律。时当春秋战国时期,即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约在800年至200年之间,人类精神的基础同时独立地奠定于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今天,人类仍然依托于这些基础。”[②]约当春秋战国时代,希腊、印度、中国这三大文化圈几乎同时独立形成,进入了“文化突破期”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以哲学突破为先导,扩展到整个文化领域,打破了古代文化数千年长期的宁静,使精神领域喧闹沸腾,兆示出人类意识的觉醒,其特点是,一方面产生了激烈的精神冲突和思想分裂,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地讨论、争辩和相互交流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树立起最高的追求目标。古代东西方民族,是经由不同的历史途径,进入这人类文化“真正起点”的轴心期的。“正常”类型的古希腊,是在古典奴隶制的社会条件下,建立了西方文化“真正的起点”;“早熟”类型的中国,则是在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转型的社会条件下,通过特殊的历史道路和鲜明的民族形式,体现了人类轴心期文化的特点和普遍性的内容,实现了“人类文化的突破”,迎来了东方文化的“真正的起点”。“早熟”的中国在历经了夏商周三代的准备之后,华夏民族在其开辟创造的前进道路上所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和智慧,终于在变革时代现实条件的催化下,以郁积磅礴之势喷涌而出,形成了以理性精神和人本思想为内涵的波澜壮阔的人文主义思潮,衍射于文史哲诸领域,产生了众多的文化巨人和无数奠基性的伟大作品,进入了堪与古希腊文化媲美的时代,在人类文化轴心期迈出了普遍性的步伐。尽管由于民族历史条件的不同和文化构型的差异,没有产生希腊那样众多的自然哲学与思辨哲学的大师,但却出现了一系列探讨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流派和诗化哲学;虽然没有产生希腊那样典型的史诗,但却出现了具有史诗功能,且在规模上超出希腊史诗的史传文学;虽然没有产生希腊那样成熟的叙事诗和戏剧,但却出现了气势宏大的抒情诗楚骚。以此为标志,文史哲在互涵互动的辩证发展运动中,将先秦文化推上辉煌的峰顶,而先秦文学则以其广阔而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文史哲融为一体的综合形态,展示出一种俯视百代的恢宏气象,成为源头和高峰。
三 建立起真正起点的诸子及哲学的诗化
春秋战国时代,哲学的突破不仅推动了整个文化的发展,而且认知思辨的活动,其本身也与审美活动相互联系、往返转化。百家论辩,各驰其说,无论是形而上的本体论的描述,还是形而下的有关社会人生问题的探讨,在名实、言意关系上,抽象思维非但不排斥形象思维,而且需要它来补充知性分析的某些缺陷。于是,在感性与理性相互联系、往返转化的思维“二重化”的运动中,“以美启真”的致思方式和“以形见理”的表达方法,不仅被进行激烈争辩的诸子所发现,且在其理论建构中得到广泛运用,诸子中大量的形象化的成语,生动的比譬以及作为譬喻高级形态的寓言的出现,实则都是认知与审美、感性与理性“二重化”的相互作用的体现。这种“二重化”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哲学艺术化的倾向。先秦诸子散文程度不同地表现出认知与审美,感性与理性,抽象与形象这种“二重化”的倾向和特点,先秦诸子之所以个个都是语言的大师、艺术的巨匠,它们之所以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上有着双重性的地位,原因即在于此。根据诸子散文“二重化”的特征,我们应称其为“哲理艺术散文”,《老子》、《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即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在人类文化轴心期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体现了哲学突破的诸子散文,一方面作为游于无穷,包罗万象,各成体系,开宗立派的思想家的学术理论和哲学思考,以极高的理论思维和相反相成的思想,在冲突中实现着整合或融合,建构了中华民族有容乃大,从而博大精深的思想库和她的价值体系,于其中儒家表现为“仁爱”,道家表现为“豁达”,墨家表现为“笃行”,法家表现为“纲纪”,其深邃的智慧和可贵的精神品质,成为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不竭的思想源泉和价值支柱;另一方面,具有“二重化”倾向,由哲学家而兼任艺术家或文学家的诸子,他们在把民族审美心理和审美经验凝炼为有理论深度的美学命题的同时,还将其与哲学体系紧密联系的美学思想付诸于个性化的创作实践,从而形成了诸子散文不同的美学风范和各具异彩的艺术风格,如孔子表现为宽仁博雅与雍容温厚(《论语》),《老子》表现为淡然超漠与深邃睿智;《孟子》表现为正大刚直与浩然之气;《庄子》表现为遗世独立与恣肆诡谲;《荀子》表现为绵密严谨与富赡恢宏;《韩非子》表现为孤愤沉郁与冷峻峭拔……风格各异的诸子,以不同的精神气质和美学风范,确立了后世士大夫文人人格、思维、审美的楷模。他们不仅站在一个需要巨人并且能够产生巨人的时代,而且他们自身就是那种“建立真正起点”和“树立最高追求目标”的思想文化巨人,他们既是民族文化的开创者,又是奠基者。
由于先秦诸子多属以人为本的哲学,作为体现这种哲学主潮的儒、道两家,其差异只是在于:前者属于宗法社会本位论的人学,后者则属于宇宙自然本位论的人学,因此在他们情理俱现和真善美交融一体的“诗意的沉思”中,便显现了一种诗意的光辉,出现了所谓诗化哲学或哲学的诗化。在这个“奠定了人类精神基础”、“树立最高追求目标”的时代,以不同的求道方式表现了人文主义精神的孔子(《论语》)与《老子》,已显示出儒道两家所建构的人生哲学,不仅都高扬了人的价值,而且无论是老子“法自然”的人生理想还是孔子求仁致道的人生主张,都含有一种超越现实的诗意的人生追求。在战国中期的社会形势下,《孟子》与《庄子》更从入世与出世的不同方面,把人格价值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说孟子“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精神及其“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显示了一种刚正的人格理想,并表现了他那由善而美的人生境界所具有的“诗意的光辉”的话,那么,庄子扬弃俗世的价值,超越于物质世界的形相拘限的“逍遥游”精神,则体现了对现实的一种充满诗意的超越,它所展露的恰是一个富有美学魅力的精神本体,显示的是由真而美的诗意化的人生。《孟子》与《庄子》之所以在诸子哲理散文中显得最有光彩,即是因为他们最成功地完成了理性与人性的结合,从而以诗意哲学的面目提出人的价值的重大课题,使人性、人格升华出“诗意的光辉”,将人文文化推向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其后出现的《荀子》和《韩非子》,尽管在学术上更臻成熟,但在战国后期兼并战争推动集权政治发展的历史运势下,人文文化已开始向政治文化转化,法家政治文化模式渐成,理性精神暂时向集权政治归附,他们代表了这一历史趋向,故其哲理艺术散文虽有较高的成就,表达的技巧更为丰富,却已失去了孟庄哲学那种人性的光辉、诗意的超越。战国后期法家政治文化模式的出现,只是“理”“势”交胜中人文主义思潮的一次退落,而不是它的终结,文化上“真正起点”的建立毕竟是以儒道高扬的人文主义为标志的。重视人道、人生、人性、人格价值的儒道人文主义,在“天人关系”这个文化最基本的问题上,以理性的形态,完成了中国传统哲学和伦理学的逻辑建构,并在趋同中表现出异趣,对立中实现了互补,从而以“合而不同”的形态,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潮哲学。
四 人意史观的确立与史著的文学化
文史哲是一个互涵互动的整体,哲学的突破必然伴随着文史的发展。而史学的功能及其在中国文化中所占有的位置,在文化奠基的时代就表现出来了。中国由于文明的早熟,且因其深深植根于农业型的自然经济和血缘宗法社会的土壤中,对氏族和祖先的史迹特别重视,故民族的历史意识萌生较早,其朦胧的历史意识,甚至可溯源于氏族社会的图腾时代:“史”字之意,《说文》释称:“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其意是手持“中”为“史”。清代学者江永认为“中”指簿书,吴大澂断言“中”乃“册”之简字,章炳麟释“中”为“本册”,凡此都表明:手持简册簿书以记事为“史”。但原起始,“中”是个象形字,表示同一血缘部落的中旗,手持“中”,就是手持氏族部落的中旗,把图腾绘在其上,本册、簿书等意,都是后来“中”的引申意。据传黄帝时代就有了“史”,传为造字的仓颉就属于“史”,故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有“史肇轩黄”之说。然而那时的“史”,只是在中旗上描绘图腾的公职,还不是官职。到了夏代,随着国家的建立,需设置一系列官职,其中即有史官——太史令,至此,“史”意由一般描绘中旗者变为官职名称。商、周进一步发展了史官制度,殷商史官,甲骨文中称作“史”、“尹”等,西周初,周天子置史官,后来各诸侯国也设置了史官,周朝史官的名称有太史、内史、御史等。夏商周三代常设史官,其所职掌之事,包括记录时事、起草公文、规谏献策等。由史官撰写的史籍,便形成了所谓史官文化。仅从得以存留下来的先秦史籍看,中国史官文化的发达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春秋末期,在官学下移、士人文化兴起的潮流中,孔子以其所修成的编年体的《春秋》,创百世相沿之体例,而又首开私人修史之风,使史书从官书中解放出来,其影响和意义,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所说:“《春秋》之所以独贵者,自仲尼以上,《尚书》则缺略无年次,‘百国春秋’之志,复散乱不循凡例。又亦藏之政府,不下庶人,国亡则人与事偕绝。……令仲尼不次《春秋》,今虽欲观定哀之事,求五伯之迹,尚荒忽如草昧。”编年记事体的《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成系统的史著,它的问世,表征了继史官之后第一次出现了史家。史家的诞生,私人著述史籍的开始,在文化下移中,推动了历史知识的传播并促进了历史意识的自觉,带来了史学上的一次伟大变革。如果说,开创了编年史书体例的《春秋》首创难工,还带有很大的原始性的话,那么,继它之后不久出现的《左氏春秋》,则是一部史实详备、富有文彩、文史完美结合的编年体史著。《左氏春秋》从史学方面体现了“轴心时代”文化的特色,全书不仅在记言记事中表现了那个时代的人本思想、无神论思想的特征,而且以其所确立的人意史观评价人物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开创了史传文学的新纪元。在这方面,作者以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记录了大变革中的春秋时代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第一次以一种自觉的英雄史观观照历史政治舞台上的英雄人物的活动,举凡各国君位的嬗变,执政者的谋权夺势,贵族内部的倾轧争斗,侯国之间的欺诈侵掠,疆场荒原上的兵戎相对,无不具现其史笔之下。另一部史著《国语》,也是同样有代表性的史传文学。它虽非《左传》那种自成体系的著作,但在通过“记言”亦即通过人物对话而成功地表现历史人物生动形象与鲜明性格方面,比详于记事而略于记言的《左氏春秋》也有胜强之处。可以互补的《左氏春秋》和《国语》,它们对历史事实的陈述没有采取史笔笔法,而是通过众多历史人物在各种事件中的各种表现,展示了那个动荡时代历史的全部过程。《左传》与《国语》都是那个时代的史诗性的历史文学著作。
《战国策》记载了“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刘向《战国策书录》)之事。作者为了宣扬策士们的权谋智术和表现其危言耸听的说辞,已把某些历史改造成谲怪恢奇的故事,以至古今史家多将其排除“信史”之列。但“敷张而扬厉”的《战国策》在反映战国时代的历史特征,特别是反映在贵族领主与封建地主及其各个集团间纵横捭阖与上下交征的尖锐斗争中,逞其才智,推波助澜的时代骄子们的精神风貌和他们的鲜明性格特征等方面,不仅达到了本质上的真实性,具有历史“实录”的价值,而且其“极行人辞令之美”的夸张性的说辞的大量运用,也使人物带上了浓厚的传奇色彩,使事件的发展和情节的展开也带有一种奇崛性。“传奇”和“奇崛”表征着战国时代史传文学的开拓和发展,也衍射出一种扬厉奋张的士子自我意识。
以《左传》、《国语》与《战国策》为代表的先秦史学,开拓并奠基了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这些史著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在叙述对民族生存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时,重视历史人物生气勃勃的创造作用,而且着重于展示人物的活动和揭示其精神世界,并通过他们的光辉形象和不屈的性格,反映了华夏民族根源于自己的历史文化特点而形成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由于史传文学以人系事,重视表现人物活动,并运用文学手段和追求一种文学的效果,这便具有了史诗的功能。《左传》、《国语》、《战国策》,实属具有史诗功能的作品。中国古代有悠久的史官文化传统,发达的史学在文化构型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对哲学、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章学诚《章氏遗书》),而且史著文学化的特点直接作用于文学形态的转换,使得中国“史诗”未能在文学的苑地中以诗的形式成熟,却在史学的沃土中以发达的史传文学的特殊形态表现出来。每个民族都根源于自己的历史特点而建立起不同的文化构型,在由野蛮进入文明的初期,早熟的中国文化未能诞育出象古希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那样宏大的史诗,但在春秋战国这个文化突破的时代,却产生了具有史诗功能,并在规模、结构、形象和故事情节等方面足可与古希腊史诗媲美的史传文学。“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中国古代“史诗”的真正成熟,没有在文学的形态中实现,而是在史学的形态中完成,这正是中国文化区别于希腊文化的具体体现: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代表的史传文学,是“无韵的史诗”、“历史形式的戏剧”,它以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民族形式,表现了中华民族开拓创造的性格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面貌,并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两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后世历史文学的发展,使文史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上的亲缘关系。
五 与哲学、史学鼎足而立的楚辞文学及其大师
在哲学、史学竞逞辉煌的时代,文学也揭开了自己历史上最瑰丽的一页,其标志便是楚辞的“奇文郁起”和屈原、宋玉两位文学大师的出现。楚辞与诸子哲理艺术散文和史传文学都是在文化超越时代相同的精神氛围和思想潮流中产生的。楚辞虽以“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黄思伯《校定楚辞》)的地方色彩而得名,但她实际上有着比《诗经》更为纵深的历史继承和更为广阔的文化铸熔:一方面,依托于楚文化的沃土,楚辞保留了一个色彩斑澜的神话世界,从而在纵深的历史继承中,弘扬了神话的艺术精神,把人类最古老、最深沉的原始意识调动起来了,使她比《诗经》显出更瑰丽的色彩和更为雄浑的气象。另一方面,她吸纳了华夏文化的精华,并在感性形式上,代表了百家争鸣的时代精神和一种新的价值观与审美判断,从而在新的层次上超越了《诗经》。楚辞的这两个方面,充分地体现在屈原的全部作品中,在其代表性的诗篇《九歌》、《九章》、《离骚》和《天问》中,甚至可从多种艺术类型的比较上,看到楚辞在文化上的兼容性、开放性和时代性。如果说其中属于超实型艺术而渊源于祭歌的《九歌》,与属于现实型艺术多写诗人“纡轸之怀”的《九章》,其“超实”与“现实”的差别,体现了南方神话巫术的文化系统与中原礼教文化系统在诗人艺术世界中的撞击或取舍的话,那么,“现实”与“超实”相结合的《离骚》(长诗前半部分叙写实境,后半部分叙写虚境),则反映出上述两个文化系统在屈原创作中的兼容。至于“人间天上,无非疑端”的奇诗《天问》,则属于哲理型的问题诗,它是通过怀疑方式来探询真理的诗作,更为明显地体现了“百家争鸣”的时代精神和表征了人类意识觉醒的轴心期文化的特征。楚辞正是立于时代精神的高度,凭借纵深的历史继承和广阔的文化熔铸,才能以恢宏的气势和突发的异彩与诸子哲理艺术散文、史传文学鼎足而立,形成了文史哲交相辉映的文化盛大局面。
在文化史上,楚辞之所以能够同诸子哲理艺术散文和史传文学形成鼎足而立、并驾齐驱的地位,与楚辞作家群的产生,特别是出现了屈原、宋玉这样的巨匠和大师是分不开的。楚辞不仅是通过屈、宋的创作而最终定型,成为一种新的诗体,而且也由屈宋的作品展示了一种新的诗潮,体现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判断:屈原作品把春秋战国时代由百家争鸣在哲学与政治领域建立起来的理性精神和士人阶层新的价值观,显象于巫术感性形式中,结晶为“惊彩绝艳”的楚骚,在诗美的高度上,确立了一种迎战现实、拥抱理想的道义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种情感形态的个人价值原则,从而也是中国文人抒情诗的灵魂,它支掌了秦汉以后几乎所有时代的文学实践。“屈平辞赋悬日月”,代表了后世诗人的共同评价,屈原之所以“名垂罔极,永不刊灭”(王逸《楚辞章句》),“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不仅是因为他以其璀灿惊世的诗篇为奔腾流涌的中国诗歌长河,开拓出一个生生不息的艺术源头,同时也是由于楚骚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所铸造的诗魂。
如果说,屈原代表了先秦文学的高峰的话,宋玉则标志着先秦文学的终结和转型:他以骚体的《九辩》为先秦诗歌作了光辉的终结;又以“述客主以首引,极音貌以穷文”(《文心雕龙·诠赋》)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作品,开赋体文学之先河,有力地推动了文学的转型。
《九辩》以天人一体的视界,在自然运化与生命活动的大背景中,展示出富有人文意蕴的秋的意象,它是以“悲秋”为题材而抒写士人愁心的一篇动人肺腑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整个作品突出了自然与人感受的对立,表现了由“秋”向“愁”的形象转化和心理对应,把人类“悲秋”的情结摹写得淋漓尽致,渲染得无以复加。《九辩》激起了不同时代的文人在感情上的共鸣。其他赋作,或写动人的神女与丽人,或状千姿百态的自然景物,每有调侃,令人解颐,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文学俗化的倾向。屈宋相比,他们代表了两种类型的文学:前者属于悲剧型、升华型的作家,后者属于喜剧性化解型的作家。
宋玉是在“百家争鸣”的尾声中出现的诗人,他的作品缺少屈原作品中那种雄浑的气势,崇高的英雄精神和超凡的悲壮气概,但他的作品却以一种平凡而真实的人间情怀、动人的感伤情绪、浓重的文学气息和世俗的情趣,兆示了一个呼风啸浪的思想开拓时代的结束,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始。宋玉不属于“诗哲”类型的文化巨人,而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大师。
结束语:迟缓的知识分化与文史哲互动中叠起的三个高峰
先秦文史哲具有的综合形态,与中国古代知识与学术分化过程相对迟缓有着内在的关联。文化上的混融性、综合性,曾是世界各民族远古时期的共性,古希腊早期“哲学”便是全部知识的总称。但知识的分化过程又是历史的必然,在这一点上,建立在城邦经济基础上的古希腊的分化过程早一些,而植根于农业经济土壤的中国古代,则相对迟缓了一些。不过,知识分化过程迟缓一点并不是一个缺点,而是文化上“大器晚成”的体现,正是由于“分化过程迟缓”,才使文史哲之间的渗透由表及里,相互滋润,得以避免单科独进的偏执与蔽限,更有利于本身深入全面地发展。以哲学为例,分化较快而迅疾发展的西方哲学,其高度抽象和思辨的经典作品虽说义理深微,但若无耐心,实难读懂,到康德、黑格尔更发展到了顶点,其思辨性与艰涩性几成正比。而中国的哲学如老庄等著作,则常在玄言妙语中贯穿着史观与诗情,理论趣味横生、血肉俱全地展示着真善美的合一。在这一方面,以思辨性著称的西方哲学似又相形见绌。
先秦时代文史哲的互涵互动形成了中国文化发展中文哲不分、文史结合的文化学术传统。文哲结合可以“庄骚”互映为代表:庄子是哲学家,但同时又是文学家,庄子哲学充满了诗意的光辉,体现了哲学与艺术在最高灵境上的融通,最恰当的称呼应该是“哲诗”。而文学家的屈原,同时又是一位哲人,他那“惊彩绝艳”的诗篇中,蕴涵了深邃的哲学意识,如果说,庄子是“哲诗”的话,屈原则恰好是“诗哲”。文史结合的典型便是以《左传》、《战国策》为代表的史传文学,它们体现了史著文学化的特点。从历史的角度看,是文学的历史;从文学的角度看,是历史的文学。文史哲互渗的特点,在综合形态的先秦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示。
两汉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逐渐从先秦时代的综合形态中分化出来,文学的样式和表现技巧获得了新的发展,与此同时,先秦时代奠定的文化传统亦在此期间有明显的延续。总揽此时期文章、辞赋、诗歌的内容与意境,大抵不外渊源于周秦经典,采撷诸子思想的芬华,出入于儒道义理,兼取道教神仙的幻想和意境,形成辞章的灵魂或旨趣。迨及隋唐之间,随着佛学的勃兴,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以儒道释三家为主潮的文运,在文史哲互涵互动的发展中,文学进入了鼎盛期。
文史哲在其互涵互动的发展中,曾相继矗立起三座高峰:哲学在战国时代率先步入高峰,其标志是诸子百家的出现,并由哲学的突破,带动了史学和文学的发展;继此之后,史学又在汉代矗立起巍峨的丰碑,其表征便是巨史《史记》和《汉书》的出现。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更被誉为“史家之绝唱”;继汉代史学高峰之后,文学又在唐代攀上了高峰,其标志是唐诗的繁荣——体裁赅备,流派众多,大家辈出,各领风骚,群星丽天,诗苑绚烂。在这三座高峰中,哲学高峰的出现代表了一个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价值体系的建立,而史学高峰滞后于哲学高峰,是因为对历史的认识、总结,离不开哲学思想的指导。文学高峰之所以在哲学、史学高峰之后出现,是因为她需要有更充裕的文化准备,至隋唐时代,儒道释三家为主流的中国文运已经形成,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已经进入全面成熟阶段,在哲学、史学高峰之后,必然会有文学高峰的叠起。
在哲学、史学高峰之后出现的文学高峰,经历了文史哲之间的更为深入的渗透和融合。最能代表中国文学特色和成就的唐诗,即是在诗与哲的相互滋润中培植起来的奇葩,可以说,唐诗中那些韵味隽永、意境高深的作品,都内涵了深邃的哲思。处于文学高峰的唐代乃是一个将认知和审美化合了的时代,它的哲学就融入于最能体现时代精神和文化成就的诗歌之中,是真正诗化了的哲学,审美化了的认知。试诵“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焕)、“莫羡檐前柳,春风独早归。阳和次第发,桃李更芳菲”(权德舆)这类在唐诗中颇有代表性的小诗,不正可以感受到其最深的层次上体现了一种哲思吗?事实上唐诗中的名篇佳句几乎都因为渗入了一种人生哲学或历史哲学而熠熠生辉,如果说“江上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张若虚)、“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昨夜圆非今夜圆,却疑圆处减婵娟”(李建枢)这类抒情诗显示了作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的话,那么,“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章碣),“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这类咏史诗,则表现出诗人对社会历史的哲学沉思和卓荦不群的史识。没有文史哲之间长期的由表及里的渗透,是不可能产生这种充满了哲学沉思和深刻历史感的诗篇的。
中国文化发展到了全面成熟期的唐代,儒道释三大哲学思潮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文化的每一个部分,在有形无形之间,随时随处滋润灌溉着诗苑,不仅对题材的选取、流派的分野、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或显或隐的影响(如山水田园诗派即与道释玄禅有明显的关系,而风格上王、孟的闲雅,韦、柳的孤寂,也都与道释相关),而且儒道释三大文化思潮还培植出了三位“对应性”的伟大诗人,这就是被称为“诗圣”的杜甫,“诗仙”的李白和“诗佛”的王维。
杜甫,就其思想和创作的基本倾向来看,无疑体现了儒道释三种思潮交汇中儒家的支配性的影响。“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种真诚、挚着和深重的忧患意识,以及其沉郁悲壮的诗风,正是衍射着儒家精神的影响。被称为“诗仙”的李白,他那“愿乘冷风去,直出浮云间”的逍遥游精神和飘逸出群的作品,便镌刻着道家和道教的明显印痕。而“诗佛”王维则在禅风吹拂下,引禅入诗,创作了“澄澹精致”的山水诗,他的一首后世争相传诵与高度评价的山水诗《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声,纷纷开且落”,人们咸认为此乃“入禅”之作,然而这里没有搬弄一个禅门语偈,却禅趣天成,意境幽深。“涧户寂无声”不是普普通通告知你“户内无人居”,而是说,主体消融于客体之中了,情化解于景之中了,人归于物之中了。这种主在客中、情在景中、人在物中的情况,使客观景物生动起来,使主观人情彻底解脱,但又不流于幻灭而有了安顿。诗人睿智沉思并未妨碍诗情的荡漾,却平添了感情的内在的深邃智慧的神韵。王维的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等等,都呈现出一种物我冥一的空灵之境,闪耀着似有若无的禅意玄思。
从战国时代以百家争鸣为代表的哲学高峰的崛起,到唐代以诗苑的百花齐放为表征的文学高峰的出现,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前后媲美、相互辉映的文化伟观。
哲、史、文这三个相继叠起的文化高峰,不是单科独进的结果,而是融为一体的文史哲相互渗透的内在发展规律的体现。它们出现于不同时代,体现了相互之间的渗透和重心的转移。当文化发展的重心由哲史渐次偏移到文学方面时,文史哲之间不仅经历了由表及里的渗透,而且传统文化亦完成了她在中国前期封建社会的发展。
注释:
① 这种人文文化在内涵上不同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但在以理性代替宗教神学的知识意向和重视人生、人性的价值意向方面,二者也有可比之处。确切地说,这种人文文化乃是人伦文化。
② 〔德〕卡尔·雅斯贝斯《智慧之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3月北京版69—70页。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史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诗经论文; 国语论文; 战国策论文; 春秋论文; 散文论文; 国学论文; 九辩论文; 辉煌集团论文; 左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