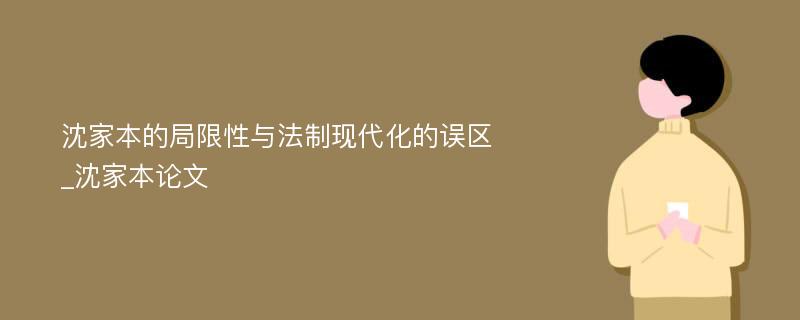
沈家本的局限与法律现代化的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区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末大规模的修订法律活动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开端,主持其局的沈家本也被人们誉为“中国法律现代化之父”。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分析,这一评价并不过分。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时代变迁以后回眸清末法律变革,我们仍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清末的修律活动如果作为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发端,从一开始便存在致命的缺陷;而作为“中国法律现代化之父”的沈家本,曾因缘际会地肩负起了终结中华法系的历史使命,但面对开拓中国法律现代化之路这一高深的课题,捉襟见肘的知识背景决定了他不可能胜任领导者的角色,勉为其难的结果是使这一巨大工程缺乏良好基础,从而最终将中国法律现代化引入了歧途。回顾中国法律近百年的发展历程,这个沉重的结论或许也是我们澄清历史疑惑的出发点。
一
“法学匡时为世重,高名垂后以书传”。作为中国法律发展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沈家本以其执着的追求和不懈的努力,为中国传统法律的跨世纪变革立下了不世之功。“天降斯人以竟斯役”,沈家本以一个没落王朝膺命重臣的身份,一跃而为卓尔不群的中国“法律现代化之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个人所具备的博古通今、兼容中西的思想品质。出身于官宦世家的沈家本自幼熟读经史,受传统文化影响至深,步入仕途后又长期侧身刑曹,久经历练。尤为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古代法律曾进行过全面的检讨和精细的考证,古代法律之演进、历代法制之得失均了然于胸,其中更不乏对中国传统法律独具慧眼的认识和精深的见解。另一方面,面对当时扑面而来的欧风美雨,沈家本表现出了兼收并蓄的大家风范,与盈于朝野之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者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因为具有容纳的态度,使他对西方政法制度有了初步的了解乃至领悟。他曾说:“近今泰西政事,纯以法治,三权分立,互相维持。其学说之嬗衍,推明法理,专而能精。”(注:沈家本:《寄簃文存·法学名著序》。)他还说:“泰西欧美各邦,近日治化日进,……义声所播,各国从风,……采用尊重人格主义,其法实可采取。”(注:沈家本:《寄簃文存·禁革买卖人口变通旧例议》)尽管只是停留在道听途说和片言只语的感性认识阶段,但放眼当时之中国,具备这种眼光和姿态者实属凤毛麟角。
然而,仅凭借于此,尚不足以具备领导一场法律现代化运动的资格。但历史的进展不能以我们后人的意志为转移,它之选择沈家本,既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无奈。也许选择本身没有错,错的只是选择的时机。也许当时没有比沈家本更合适的人选,但正是由于沈家本思想的局限,决定了他领导的这场法律变革运动的最终命运。
沈家本对中国传统法律抱有视若家珍的个人感情,对此他不仅不隐讳,反而常常刻意传扬。在《法学名著序》中,他曾充满自信道:“夫吾国久学,自成法系,精微之处,仁至义尽,新学要旨,已在包涵之内,乌可弁髦等视、不服研求?”虽然他也赞同学习了解西方法律,但前提却是必须立足于“中律之本源”,如果不能考求中国传统法律得失之所在,“而遽以西法杂糅之,正如枘凿之不相入,安望其会通哉?是中律讲读之功,仍不可废也。”(注:《寄簃文存·大清律例讲义序》)他真诚地相信,如能“就前人成说而推阐之,就旧日案情而比附之,大可与新学说互相发明”。(注:《寄簃文存·刑案汇览三编序》)正是这种“互相发明”的心态,终使沈家本无法跳出传统思想的窠臼,达到自身认识的升华。
沈家本认为:作为儒家文化的基本范畴,“仁”乃中西法律的共同精义之所在,也是中西法律会通和结合的立足点。他一方面总结了中国古代的所谓“仁政”,另一方面又认为当时的“新学”要旨已为“仁至义尽”的中国旧学所包涵。在他的思维和语言中,“仁”是一个与西方法律的精神或原则相类似的概念。他甚至断言,西方法律所体现的自由、平等、法治、人权等精神,可以归纳为一个“仁”字。在这个前提下,他得出了一个荒唐的结论:“各国法律之精义,固不能出中律之范围”。(注:《寄簃文存·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不仅如此,沈家本还像清末所有托古改制论者一样,费尽心机地对历史陈迹作现代意义的诠释。甚至西方的“法治主义”他也认为可以征稽于中国典籍之中。“管子曰:立法以典民则祥,离法而治则不祥。又曰: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废也。其言与今日西人之学说流派颇相近是。法治主义,古人早有持此说者,特宗旨不同耳。”(注:《寄簃文存·新译法规大全序》)他甚至认为西方的分权制在中国也是古已有之:西周之时,政官与刑官之职守便各不相侵,“故能各尽所长,政平讼理,风俗休美。”而“近日欧洲制度,政刑分立颇与周官相合”,故政刑分离,“尤西法与古法相同之大者。”(注:沈家本:《历代刑法考》)此外,他还认为西法中“刑之宣告,即周之读书用法、汉之读鞠乃论、唐之宣告犯状也。”西周“乞鞠限以期日,今东西各国皆用此法”;而西法中“狱之调查”也即“周之岁终计狱,弊讼登中于天府,宋之类次大辟,奏上朝廷也。”(注:沈家本:《历代刑法考》)沈家本之如此不惮其烦地论证中西法律的“会通”,并非像许多托古改制论者那样只是出于一种宣传策略的需要。他是发自内心地笃信中西法律不仅能够融合汇通,而且在内在精神上已经是相通的。他知识和思想的局限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理解法律发展变化的历史以及西方近代法治的真正含义,却偏偏乐于做出充满中国传统色彩的解释,其结果不仅作茧自缚地限制了自身思想观念的提升,同时也迷惑了当时乃至后世的无数人士。
上述粗略分析表明,沈家本基本上仍属于传统派的法律家,只是由于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下,他个人的优秀品性,帮助他捐除了狭隘的门户之见,选择了一条中国传统的变法求新之路。他对中国传统法律的迷恋以及对西方法律的误读,必然对他所领导的法律现代化运动带来致命的影响。
二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有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逐步深化的过程。清末修律前后,社会共识基本达到了第二个阶段,即不再自欺欺人地认为西方的强盛仅在于它的坚船利炮,而在于其“良法美意”的政治法律制度。虽然绝少有人能像严复那样意识到西方制度后面所包含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精神准则具有决定意义,但面对一个腐败愚昧的王朝,即便是表层制度的变革,就足以引发一场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在清末各种思想的大碰撞中,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后期洋务派思想最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庚子之乱后,它不仅成为朝廷的主流,更广为社会各界所接纳,这与张之洞的中间道路符合中国人信奉的中庸之道直接相关。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方面超出了单纯“变器”的层面,另一方面又划地为牢地坚守着传统思想的阵地。耐人寻味的是,张之洞竟将法律制度视为一种器具,“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注:张之洞:《劝学篇·变法》。)法律被当作一种纯粹的工具,自然可以任人拿捏摆弄。条文尽可变来变去,精神和原则却是不能染指的禁区。这是一个没落王朝聊以自保的最后一道思想防线,也是清廷最终被迫同意进行大规模修律的一种心理慰藉,它作为一种具有支配力的心态,对整个修律活动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更可怕的是,主持修律的沈家本在思想深处对此并无真正的隔阂,甚至具有心领神会的一面。清末修律的最终命运由此决定。
于是,清末在修订、编纂一系列新式法律,基本完成形式意义的变革的同时,又最大可能地保持了传统法律的精神旨意。而形式上的变化,又掩盖了本质上的保留,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整个修律活动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也导致人们忽略了这一致命缺陷对中国整个法律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其实,只要我们对清末修律的成果略加理性的分析,是不难发现要害之所在的。这里,不妨对评价颇高的《大清新刑律》作一简单的剖析。
《大清新刑律》公布于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部专门的刑法典,它由总则、分则和暂行章程三部分组成。从形式上看,它摆脱了中国传统法典混合编纂即所谓“诸法合体”的模式,以规定犯罪和刑罚为内容,所采用的是西方近代刑法典的体例结构。在内容上,也不乏新意,如引进了许多西方近代刑法制度,取消了在适用刑罚上的等级制度,对故意、过失、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等作了明确的规定,确立了假释和缓刑制度,增加了有关国交、选举、交通及妨害卫生等新式罪名。然而,这些形式上的改变,仍然是立足于传统的“仁政”思想,或者说是“仁政”思想的新型法律解读,而并非西方法治主义理念的体现。所以,现代刑法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原则,如尊重人权人格、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都无法从这部刑法典中反映出来。恰恰相反,它利用一种新形式,再一次维护了中国传统刑法的根本精神。这首先是表现在对皇权和皇室给予了与过去一样严密的保护,所谓“侵犯皇室罪”、“内乱罪”无非是以往“谋反”、“大逆”、“大不敬”之类罪名的现代说法而已。同时,传统的礼教原则仍对定罪量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暂行章程”五条便是典型例证。这些足以表明沈家本在修律中基本实践了他尊奉的“修订大旨”,即“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注:《大清光绪新法令·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进呈刑律分则草案折》。)只不过是前者流于形式和表面内容,而后者却确保了新旧律之间内在精神品质的连贯和同一。
三
同为东亚大国,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面临西方文明的挑战。中国近代变革中遇到的一切问题,日本也都不同程度地遇到过。比较一番中日两国变法改制的不同经历和结果,或许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明治维新之初,日本天皇即于1868年4月发布《维新政体书》, 从而为最初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法律制度的改革确立了基本原则。作为改革的纲领,它开宗明义宣布了天皇的五条誓文: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2.“上下一心,大展经纶”;3.“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4.“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5.“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随之而来的,是一场以“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为三大口号,以政治、法律、经济、军事等为内容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全面展开。可以说,日本的改革一开始便把目标定在国家的现代化上,上下一心谋求的是与西方列强的共同发展。很快,“一个西方型的民主国家取代了昔日的封建国家。日本经历了一次蔚为壮观的突飞猛进,一跃而成为当代世界贸易中第一流国家之一。”(注:勒内·达维德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中译本,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564页。 )而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中国,依然久久放不下老大帝国的架子,哪怕是微小的变革都不曾主动做出,不到万不得已、走投无路,绝不肯对任何改革的动议报以回应。“改革的目的毋宁说是为了保卫清政府不受汉人与外国人两者的攻击。换言之,改革是为了保住清王朝。”所以,它“只需要保持改革的门面,而对实际内容则毫不关心。”(注:费正清著:《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74页。 )统治者出发点和心态的不同,对整个过程的最后结果具有根本影响。
在法律改革问题上,中日两国当权者的态度也完全不同。日本奉行的是全面革新的策略,它以“脱亚入欧”为口号,采取了全盘吸收西方法律制度的姿态。这种“求知识于世界”的结果,是使西方的法律观念得以广泛传扬,现代法治主义的真谛颇能深入人心,从而为现代法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反观中国,一贯采取的是挤牙膏似的渐进改良措施,它企图在不根本触及专制政治的前提下,借用西方法律的外壳来包裹传统法律的僵尸。对传统的自信,以及对法治主义的无知,使朝野上下习惯于满足法律上的皮毛变革,以满足强作颜色后面的自尊心。“良以三纲五常,阐自唐虞,圣帝明王,兢兢保守,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所以,“凡我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庶以维天理民彝于不敝。”(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858页。)对自身传统的态度,正是中日两国最重要的思想分野, 这种分野所带来的不同政治法律的发展模式,决定着中日两国现代化的进程和归宿。
明治维新的日本,在中央有三条实美、岩仓具视等开明贵族,也有大久保利通、林户孝允、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积极推动改革的大批藩士,他们占有明治政府全部官员的三分之二,并事实成为政府的核心力量,这是推行根本性变革的组织保障。而清末政坛,颟顸愚昧者盈朝、固步自封者遍野,即便能分出新旧两派,也不过是顽固派和洋务派的区分而已,真正洞明时世、力主变法图强者,除沈家本、伍廷芳寥寥数人外,可谓绝无仅有。而沈家本又为其身份地位所累、认知能力所制,真正能施展手段的空间和可能性都是有限的。《大清新刑律》中被迫加入“暂行章程”五条,直观地说明了这一点。
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曾掀起了一场波及全国上下的“自由民权运动”,民众在运动中提出的推进民主改革、实行民主宪政的要求很快获得了全国各阶层的热烈响应。这场运动其实也是现代政治法律观的普及运动,它为日本民族法治精神的传扬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舆论基础。从此,“不仅旧的习俗被当作落后于时代的东西而遭到排斥,还大量地吸收了西方的近代思想和学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取代了过去的儒教和神道而流行起来,天赋人权的思想也受到提倡。”(注:依田熹家著:《简明日本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3页。)而这个过程尤为中国近代所欠缺。 除了严复的微弱声音外,无论洋务派,还是改良派、维新派,都不曾向国人认真介绍或宣扬过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而对当时的一般百姓而言,这些观念可谓闻所未闻。在全社会现代法律知识基本处于空白的背景下,闭门造车,企图从立法着手来完成中国法律现代化这一旷世工程,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四
任何制度的变革,都不能不以思想的变革为先导。如果一种新制度来源于异质文化,如果这种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根本差异,则思想的变革将会变得异常的艰难。但无论如何艰难,这个过程是必须完成的,即首先必须培育接纳新制度的思想土壤、社会土壤,然后再循序渐进地对制度本身进行引进和移植。道理讲起来人人都懂,但一当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功利主义的心态、实用主义的方法,往往取代了人们的理性思维,以至于置思想条件的空白或不成熟于不顾,动辄立法建制。这种现象,最多地出现在清末“法律现代化”之后的中国法律领域,其滥觞之处,即在于沈家本领导的清末修律本身。
一方面,以沈家本自身的素质与能力,不足以领导一场前无古人的法律现代化运动;另一方面,清末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本质特征,更不能容忍一种直接威胁其生存的法律制度在中国立足。而比这两点更重要的是,一个思想不曾启蒙的社会、一个观念依旧陈腐的民族,根本不可能建造起一座法律现代化的大厦。但历史的阴错阳差,恰恰赋予了沈家本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而在许多人看来,沈家本完成了这个使命。在他的主持下,具有西方法律形式特征的各类法律法规竞相出台,传统法律制度在名义上被废弃,中华法系的丧钟被敲响。这一切实实在在地表明中国法律完成了由古代到近代的转变,这一转变既倾注了沈家本的毕生心血,也为其不朽的功绩树立了历史的丰碑。与此同时,沈家本却又不自觉地将中国法律的现代化进程引向了一个误区:清末修律的表面成功,掩盖了其自身致命的缺陷,并给人造成了一个错觉,即法律的现代化其实如此容易,似乎一夜之间便能完成;而法律现代化的过程又是如此简单,无非照搬照抄西方法律的条文而已。从此以后,陷入这个误区的近现代立法者以及法律家们,只知埋头致力于并满足于对西方法律形式化的移植和模仿,反而对最有价值、最终决定法律现代化是否成功的法治精神和原则无动于衷,他们无视的是这样一个真理:在一个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不曾深入人心的社会,永远不可能真正完成法律的现代化;而不曾将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贯注始终的法律,绝非真正现代化的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