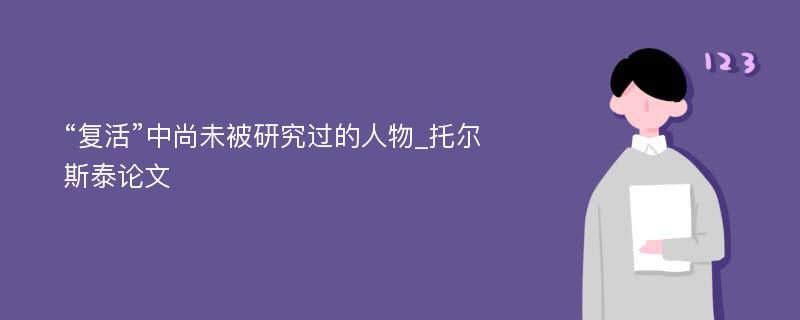
《复活》中一个尚未研究的人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训明 译
读过小说《复活》的人,想必都记得那些描写被流放的革命者的章节。他们当中,有一个十分惹人喜爱的年轻女子玛丽亚·巴甫洛夫娜·谢金尼娜。正是她在监狱里首先对女囚犯玛丝咯娃表示关切,并促进了卡秋莎精神上的复活。
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描写的那样,她是一个“体态丰满,面色红润,相貌美丽的姑娘。长着一双大眼睛,穿着灰色的连衣裙,披着短披肩……这个姑娘处处都长得很美丽;那双又大又白的手,那波浪似的短发,那端正的鼻子和嘴唇……不过,她脸上最动人的地方,却是那双羔羊般的褐色眼睛,善良而又真诚。
这个形象是否有原型呢?
文艺界一直没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我们知道,托尔斯泰具有天才的典型化技巧,他的许多人物形象后面都有作为模特儿和未来角色“种子”的真实人物。小说“复活”中的革命者形象也是如此。这些形象展示了托尔斯泰进行思想探索和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的一个完整领域。托尔斯泰与民意党人——列宁把他们称为“七十年代革命者中的杰出人物”的鲜为人知的交往,他为改善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处境而进行的斗争,这些人的形象在托尔斯泰作品中的生动表现——这一切,乃是这位伟大作家传记中极其光辉而又未被充分认识的重要一页。
玛丽亚·巴甫洛夫娜谢金尼娜的原型是年轻的革命者、民意党积极活动家娜塔丽垭·亚历山德洛夫娜·阿尔蒙菲立德。她于1850年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贵族家庭里。她的父亲亚历山大·奥西波维奇·阿尔蒙菲立德是菲斯科大学的教授,果戈里和阿克萨科夫兄弟的密友。
列夫·托尔斯泰也同阿尔蒙菲立德一家相识,到过她家在阿尔巴特街附近的住处。在小说《战争与和平》中,他曾多次提及她家的祖先、俄国爱国者、参加过1812年战争的古斯塔夫-莫尼兹·阿尔蒙菲立德将军。
娜塔丽娅·亚历山德诺夫娜·阿尔蒙菲立德曾在海德堡大学受过教育。在那里,她在数学上表现出很大的才能,音乐和绘画也学得不错,还掌握了几门外语;她那时就出落得很漂亮。年纪还很轻的时候,她就参加了革命青年团体,从而将自己的一生同为人民事业而进行的斗争永远结合在一起。
娜塔丽娅·阿尔蒙菲立德早在少女时代便与托尔斯泰结识。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是从她的密友和同志,民意党人恩·阿·莫罗卓娃的回忆录《我的生活故事》中得知的。她后来的服苦役时的书信中对托尔斯泰表示的那些热诚而友好的问候,更证明了她在精神上与托尔斯泰的亲近。托尔斯泰也热情地分担了娜塔丽娅·阿尔蒙菲立德的命运。
附带提一句,托尔斯泰并不同情民意党人采取的暴力斗争手段,他从自己的宗教伦理观念出发,对他们进行了批驳。同时,他又不能不赞赏年轻一代革命者的高尚道德、勇敢和无畏的精神,这些革命者为全俄罗斯的利益同沙皇制度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毫无惧色地走向监狱,流放地和绞刑架。
关于托尔斯泰热切关注这一斗争的许多见证都已保存下来。比如,后来以农民拉巴托夫之名写进《复活》的著名民意党人叶·叶·拉扎列夫在其回忆录中谈到,1883年夏天,许多同情革命的青年在托尔斯泰的沙马尔庄园里找到了“避难所”。
托尔斯泰置身于这些青年朋友当中,感到精神十分舒畅。“在我们这些青年伙伴中”,拉扎列夫回忆道:“连他自己也变得年轻了。他受到我们爱开玩笑的性情的感染,谦逊地接受了青年们对他不切实的理想主义和政治上的幼稚所进行的猛烈攻击……当一个十七岁的高校女生怒气冲冲地责难他,说列夫·托尔斯泰像一个天真的孩子那样不懂得真正的生活而还妄加评论时,情景极其感人。”
托尔斯泰之所以对民意党人感兴趣,是因为他把他们看作一种新型的战士,看作他极其钦佩而又衷心喜爱的十二月革命党人队伍的接班人。他后来在阅读民意党人尼·柯·莫罗佐夫的回忆录时说:“观察革命者的心灵”是十分有趣的事情。
1884春天,托尔斯泰从安娜·瓦西里耶夫娜·阿尔蒙菲立德那里得知,她儿女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服苦役并在那里患了肺结核,他就向她提供帮助,设法把病人转移到危害较少的地方去。在这件事情上,他指望得到彼得堡上流社会的亲戚、堂婶亚历山德娜·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夫人的帮助,因为她当时是玛丽亚·费多诺夫娜皇后的高级宫廷女官。
1884年4月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午饭后到阿尔蒙菲之德家去……读到有关阿尔蒙菲立德的第四号案卷”。第二天他又在日记里写道:“读了娜塔丽娅·阿尔蒙菲立德的信。一个高尚的人。”在阿尔蒙菲立德母亲那里,托尔斯泰遇到过一些革命者,对他们很感兴趣。民意党人、地方自治会统计员符·伊·奥尔洛夫也常到这里来,他的统计材料后来曾被卡尔·马克思和符·伊·列宁用过。在阿尔蒙菲立德家的住宅里,托尔斯泰还会见过薇娜·扎苏里奇的姐妹亚历山德娜·伊万诺夫娜·乌斯宾斯卡娅及其朋友们。“这是些朝气蓬勃的人,口才很不错”。他在日记里这样提到他们。
在同这些人交谈当中,特别是在读了从流放地寄来的信件之后,他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年轻的革命者们是一些道德高尚,心地善良而又富于人道的人,他们之所以采取暴力物段,只是由于“他们真诚而善意的言论”遭到禁止。他在这些“可怕的”(正如人们所形容的那样)革命者身上看到了他们善良而又光辉的内心世界,从而一反自己的成见,极力为他们辩护。
1884年4月17日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清早起床,给托尔斯泰夫人(按指作家的婶娘——译者)写信。对我来说,既不能向最高当局提出呈文,也不能去哀求皇族。只好请求神圣的皇后,请她停止对妇女的折磨!”
这则日记标志着托尔斯泰连续多年为减轻娜塔丽娅·阿尔蒙菲立德苦难生活而到处设法的开端。娜塔丽娅的母亲写的许多呈文,托尔斯泰都觉得“十分糟糕”,就为她另行草拟,甚至还写信给住在彼得堡的阿·阿·托尔斯泰夫人说:
“我在此地碰到阿尔蒙菲立德老太太,到她家去过,详细询问了她女儿的病况,见她十分痛苦。她对我说,她曾请求搬到卡拉奇去住,以便就近照料女儿,但却遭到拒绝(她的呈文是送给皇上的),因此,她请求皇后对此开恩,我赞同她的这个想法……”
5月5日,阿·阿·托尔斯泰夫人写给列夫·托尔斯泰的回信送到了清田村,使他大失所望,因为他本来期望皇后会发善心。阿尔蒙菲立德母亲的请求未能获准,而托尔斯泰亲自为她拟的那些呈文,则被送到各个不相干的部门,终如石沉大海。
阿·阿·托尔斯泰夫人转达皇后态度的回信,使列夫·托尔斯泰十分痛心。他在5月16日写给她的信中流露出对自己的强烈不满,太过于相信“最高当局”的德性了。
他写道:“倘若阿尔蒙菲立德夫人不能获准同女儿住在一起,将会痛苦不堪,因为她曾满怀希望。我怎么想就怎么说:如果母亲想同不幸的女儿住在一起——而她之所以不幸又是由于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叫她服苦役——这样的事还需四处哀求、奔走张罗,那我们所处的究竟是一种什么世道啊?”
求告“最高当局”而感觉到的痛苦经验,特别是同革命者交往的经验,更坚定了托尔斯泰帮助那些被沙皇专制政权迫害的人们的决心。在他这一时期的日记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值得特别注意的记述:
“重读一遍文稿,然后将它誊写一遍。但愿它的刊印能对不幸者有利……他们在向我伸手求援。”
托尔斯泰还由此酝酿出一篇著名论文:《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当时,其中几章已由《俄罗斯思想》杂志发排,但检查官绝对禁止将它付印。
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接到彼得堡拒绝其呈文的批复之后,给托尔斯泰寄来了一封充满新的痛苦的信。她已经断了将女儿迁移到别的监狱去的念头,只求准许她自己搬到监狱附近去住,以便照料患病的女儿。于是,托尔斯泰又以极大的顽强精神重新去设法。
5月28日,他写信给阿·阿·托尔斯泰夫人:
“昨天收到阿尔蒙菲立德夫人的来信,现奉上一阅。它比我更能在您心中唤起那种如同在我心中唤起的感情。上帝保佑!人们实在太卑鄙了,居然会造下这样的罪孽!”
同时,他又给阿尔蒙菲立德的母亲写了一封长信,可惜未能保存下来。不过,从在流放中曾与娜塔丽娅·阿尔蒙菲立德关押在同一号房里的民意党著名活动家安娜·巴甫洛夫娜·普利贝列娃后来所写的回忆录中,可以得知这封由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寄给女儿的信的内容。托尔斯泰关切地询问娜塔丽娅的身体状况,鼓励她,而且,在向她致以热烈问候时,还要她说明需要什么东西。信中,他还叫娜塔丽娅将鞋码子寄来,好亲手给她做一双暖和的皮靴子,因为这对于在西伯利亚过冬是十分必要的。(当时,托尔斯泰对制靴手艺极感兴趣)
正如阿·巴·普利贝列娃记述的那样,娜塔丽娅·阿尔蒙菲立德拒绝将鞋码子寄给托尔斯泰,说她不愿让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把时间浪费在为她做皮靴上。关于这件事,普利贝列娃还补充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当与娜塔利娅同关在一个号房的女友们得知她拒绝将鞋码子寄给托尔斯泰之后,就开玩笑说,她之所以不接受这个建议,是因为自己的脚长得太大而不大好意思。普利贝列娃写道:“对于这个玩笑,娜塔莎自己比大家更笑得厉害,说真是这么回事。可是,大家都深知她为人谦逊,她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愿让托尔斯泰为她做鞋耗费时间。”
6月25日,阿尔蒙菲立德的母亲通知托尔斯泰说,她得到彼得堡的一个最新通知;她的申诉全被断然驳回,她的请求遭到完全拒绝。
尽管托尔斯泰帮助娜塔丽娅的一切努力都遭到失败,但他并未因此而丧失信心。彼得堡的拒绝使他更加接近年轻的女革命者和其他政治苦役犯的家庭。这使许多民意党人受到鼓舞,而那些还未失去自由的民意党人则设法与他会见。在托尔斯泰这个时期的日记中,提到了其中几次见面的情况。比如,1884年5月3日,他在日记里写道:“一个沃罗格达市的姑娘到这里来,显然是个革命者。我与她谈得颇为愉快,只是谈得不多。”
在隐蔽得极为秘密的革命者当中,有一个斯·阿·伊万诺夫(化名)与民意党领导中枢十分接近。他在寻求同托尔斯泰见面的途径时,曾请一个政治苦役犯的母亲阿·符·德莫霍符斯卡娅安排他同这位作家会见。尽管这要冒极大的风险,托尔斯泰还是答应了。会见在阿尔巴特街的一处出租房间里秘密进行,持续了几个小时。托尔斯泰对民意党的理论纲领和实践活动、对这个组织代表人物的世界观和精神状态极感兴趣。虽然他和伊万诺夫就革命“暴力”的可能性问题多次发生争论,但最终还是谈得颇为投机。托尔斯泰对这次会见极其满意。他再次坚信,革命者的目标和努力是高尚的,他们勇于自我牺牲,抛头颅,洒热血是为了给社会造福。
在这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当中,托尔斯泰去看望娜塔丽娅的母亲,同她一起承受从苦役地传来的那些令人愁苦的消息。娜塔丽娅·亚历山德诺夫娜在一封信中生气地写道:母亲向“身居高位的人们”提出请求的行动使她感到可耻。对此,托尔斯泰在日记里赞许地写道:“的确如此”。
娜塔丽娅在向敬爱的作家表示热烈的问候之后,请将他的作品寄给她。托尔斯泰乐意地将自己作品的全集交给阿尔蒙菲立德的母亲,后者为此在1884年6月25日写信给他:
“衷心敬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近日收到你的全集,实在感激下已。《战争与和平》已邮往卡拉,剩下的待我到莫斯科之后再亲自付邮。”接着,她谈到了自己的女儿:“可怜的闺女大概还在等着我去,而我却没有勇气将我和您的请求遭到拒绝的情况拍电报告诉她。”
在此之前,阿尔蒙菲立德的母亲意外地收到从卡拉寄来的、由监狱长签署的一封令人纳闷的信:“娜塔丽娅·阿尔蒙菲立德告诉您,她很健康,感觉身体良好。”她天真地把手里这不寻常的纸条解释为监狱长发的某种“善心”,准许她儿女向亲属写信报告自己的情况,在经过为时数月的检查拖延之后,阿尔蒙菲立德的母亲才能让托尔斯泰分享自己的欢乐。
“我将这一点小小的慰藉告知您,是因为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对待那些受苦受难者和我那亲爱的、受尽折磨的女儿是多么热情……
紧握您善良的手。
阿尔蒙菲立德”
正如与娜塔丽娅·阿尔蒙菲立德在一起服役的女友们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讲的那样,即使在监狱里,她也非常勇敢和善良:就跟在自由的时候毫不吝啬、毫不迟疑地献身于革命斗争一样,她在监狱里也忘我地为同志们,特别是为那些身体衰弱和患病的同志们服务。她擦地板、倒马桶,洗衣、劈柴、生火、照料病人。除此而外,她还绞尽脑汁地在监狱的院子里种上几畦葱,这对于几乎全患了坏血病的苦役犯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一起服苦役的同志们都知道托尔斯泰参与营救娜塔丽娅·阿尔蒙菲立德的活动。放风的时候,她母亲的来信从这双手传到那双手,监狱里关押的人全都读过了。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或许是因为娜塔丽娅要她母亲寄来的,除了托尔斯泰的作品之外,还有他的照片。于是,作家没有被查禁的作品和照片就传进关押苦役犯的监狱里来了。托尔斯泰也毫不厌倦地为阿尔蒙菲立德的事情操心,希望能取得一个良好的结局。后来,终于突然出现了黎明的曙光……
1884年夏末,当阿尔蒙菲立德的母亲对自己的请求不存在获准的任何希望时,她突然收到彼得保发来的通知。在最初那一刻,她恐惧万分,认为这定是告知她女儿的死讯。可是,当她看到是要“安排”她的事务时,才又充满希望。
托尔斯泰当时住在清田村,于是阿·符·阿尔蒙菲立德就往那里给他寄了一封信:
“亲爱的、衷心敬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听说您不在莫斯科,我感到很惋惜,因为我希望在出发去彼得堡之前能见到您。科罗诺维奇叫我到那里去,说是为了‘最终安排’我的事务,我必须去一趟。如果我需要你的帮助时,请允许我来找您。
阿尔蒙菲立德”
通知到彼得堡去这件事,的确与改变娜塔丽娅·亚历山德诺夫娜的命运有关。沙皇政府拒绝了将她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的请求之后,担心囚犯们会大批地传染上结核病,就决定把她和关在卡拉的其他肺结核病人搬到所谓“自由队”去,也就是说,实行永久流放。这意味着,她可以从挤得满满的牢房里搬出来,住到单独的房子里去,准许她母亲到那里去照料她。这对于母女两人,无疑是喜从天降!……
“衷心崇敬的、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我多想为这件喜事亲自向您表示感谢,它已呈现在我的现前,只要我能活到那一天……紧握您善良的手!
阿尔蒙菲立德”
为办手续又拖了4个月,直到1885年5月,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才得以成行。在她出发之前,列夫·托尔斯泰送给她一笔路费,并将自己的照片请她转交给女儿,他还在照片背后写了几句热情洋溢的赠语。
直到半年之后,即1885年10月14日,托尔斯泰才收到一封被检查官扣压了3个月的信:
“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经过近两个月的长途跋涉之后,我终于在7月8日到达下卡拉我女儿可爱的住处。在这里,我站起身来就要碰到天花板,还有种种舒适之处。我们两人都感到欢乐而又幸福。
娜达莎太出老了,身体结实,精神饱满。她向您表示衷心的问候,非常感谢您给她的照片。
别听信那些小道消息:说什么这里的规矩有碍于吐露真情。
紧握您的手。
阿尔蒙菲立德”
两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西伯利亚没有信来。母女二人大概都不愿给受监视的托尔斯泰写信,以免使不利于他的材料落到暗探手里。这几年来对于她们母女俩来说是十分艰难的。娜塔丽娅嫁给了著名的政治苦役流放者阿·伊·科莫夫。他是193号案件的要犯,曾被判处十五年徒刑,1886年也因患有结核病而获准改为终身流放。一年以后,这对夫妻生了一个小女儿。婴儿患了重病。这使娜塔丽娅·阿尔蒙菲立德的身体状况更加恶化。除了严重的肺结核之外,她又患了喉结核。于是,安娜·瓦西里耶夫娜当时决定采取最后的步骤:回莫斯科去请求托尔斯泰帮助,再次争取把女儿转移到气候比较暖和的地方去。然而,唉!这一次仍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当局断然拒绝减轻对这个即将死去的女流放者及家庭的折磨。
为了救活自己的女儿,娜塔丽娅·亚历山德诺夫娜按照同志们的建议,同意把她送到莫斯科去。原来照看过娜塔丽娅的老保姆拉丽莎·瓦西里耶夫娜得来照料小女儿。至于老母亲,已经十分衰弱,不能再坐火车来看她了。忠心的保姆还没有赶到卡拉,娜塔丽娅·亚历山德诺夫娜的病情就急剧恶化,喉咙出血。不到两天,他便离开了人世。她那心力交瘁的老母亲,也几乎同时在莫斯科猝然而逝。老保姆总算到了卡拉,把小女孩从她父亲手上接过来,然后带着她踏上返回莫斯科的路途。但是,小女孩的体质太弱了,她们才坐火车走了几百俄里,她就死去了。可怜的保姆别无办法,只好回到卡拉,把婴儿同她母亲埋葬在一起。孩子的父亲本来就病重,也未能承受住这接二连三的打击。……这就是那个多灾多难的英雄家庭的结局。
在小说《复活》中,娜塔丽娅·亚历山德诺夫娜·阿尔蒙菲立德的特征是如何体现在玛丽亚·巴甫洛夫娜·谢金尼娜的形象中的呢?
首先,使她们毫无疑问地相似的,是她们的经历几乎完全一样。玛丽亚·巴甫洛夫娜也同娜塔丽娅·阿尔蒙菲立德一样,出身于世袭的“将军”门第。她们俩从少年时代起就不愿过优裕的生活,很快就离开家庭“到人民中间去”。她们被捕和受审的经历也差不多完全一样。娜塔丽娅·阿尔蒙菲立德1879年春天在基辅的一套秘密住宅里,人事武装反抗,被秘密警察发现而被捕。当时,在黑暗中有一名警察被流弹打死,双方都有人受伤。
在法庭上,娜塔丽娅·阿尔蒙菲立德为了拯救受到死亡威胁的同志们,承担了全部责任。虽然开枪的并不是她,而且,正如托尔斯泰笔下的谢金尼娜一样,她的手“从来没有拿过枪”。
在刻画年轻的玛丽亚·巴甫洛夫娜·谢金尼娜时,托尔斯泰当然并未去追求她与娜塔丽娅·阿尔蒙菲立德外貌和姿态上的维妙维肖。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刻画那使她们相似的主要之处;外形的美和心灵的美。同娜塔丽娅·阿尔蒙菲立德一样,玛丽亚,巴甫洛夫娜对同志、对卡秋莎·玛丝洛娃无限善良。被流放的革命者们,特别是玛丽亚·巴甫洛夫娜的这种关切和帮助,使玛丝洛娃麻木的心灵逐渐温暖并变得活跃起来,理解到战士们为人民事业而进行斗争这种全新生活的意义。起初,她只是不自觉地置身于这一事业当中,后来则全心全意地为这一事业奋斗。
当然,玛丽亚·巴甫洛夫娜·谢金尼娜尽管有现实典型作为依据,但毕竟是一个综合形象。在这个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许多杰出的俄罗斯妇女。比如索菲亚·别罗夫斯卡娅和薇娜·扎苏里奇等,托尔斯泰在评论她们时,总是诚心诚意地称赞不已,甚至打算将她们的事迹写下来。而其他一些女革命家,如纳杰日达·康斯但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薇娜·米哈依诺夫娜·维里厅金娜,玛丽亚·米哈依诺夫娜·霍列文斯卡娅等人,托尔斯泰则先后与他们有过书信往来。她们都具有善良、人道、自我牺牲等品质。而托尔斯泰则把这些品质毫不吝啬地赋予他笔下的人物。
玛丽亚·巴甫洛夫娜·谢金尼娜的形象至今尚未引起文学研究家的注意,而它对于托尔斯泰走过的复杂道路是极为重要的。虽然托尔斯泰主义者们极力试图把他描绘成一个远离尘世的隐士,但是,即使在这个远非中心人物的角色身上,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与当代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艺术家。作为一个不倦地进行精神探索的人,作为一个具有宽广襟怀的人,他欣嘉地注视着预示新时代到来的曙光,寄同情于为人民幸福而斗争的新一代战士。
列宁称托尔斯泰的作品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在小说《复活》的这个范例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导致十月革命的十九世纪末斯的俄国现实生活,在这面镜子中反映得多么有力、多么深刻而又多么透彻。
(译自《文学问题》1981年第10期)
注释:
①阿·施弗曼,莫斯科托尔斯泰博物馆高级研究员,语文学博士,此文征得作者同意,在本刊发表。——编者
阿·符·阿尔蒙菲立德致列·尼·托尔斯泰的书信保存在国立托尔斯泰博物馆手稿部里。本文所引用的许多信件都系首次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