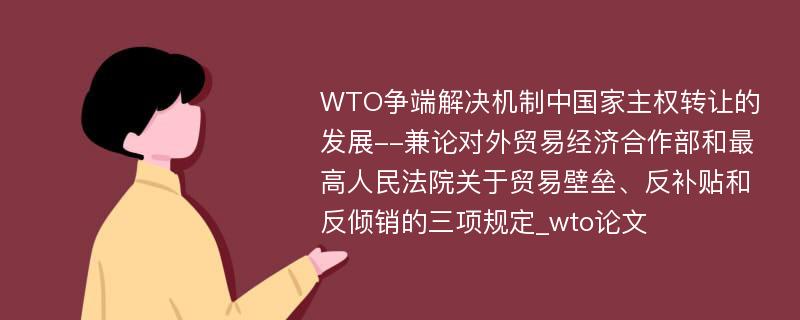
国家主权让渡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发展——兼评外经贸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贸易壁垒、反补贴、反倾销的三个规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经贸部论文,争端论文,贸易壁垒论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论文,国家主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512(2003)02-0092-05
在全球化大趋势下,各主权国家为了共享经济成果,进行国际合作,不能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须尊重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国际社会的制约。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在各国经济生活中的不断提高,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作用逐渐减弱,不得不在一些适当的领域限制或让渡国家主权。
一、国家主权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让渡
目前,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它们对稳定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包括WTO在内的国际组织的特征之一,即其构成了对国家管辖权的直接制约,各成员方加入WTO,即意味着主动限制自己的主权或将自己的部分主权交给WTO行使。WTO采取“一揽子”签署方式,只要成员方签署“一揽子”协议,就表明同意接受其争端解决机构(DSB)的管辖,履行其应尽的义务。WTO各成员之间及WTO与其成员方之间因解释和适用WTO框架下各涵盖协议所产生的争议,都须且只能通过DSB解决。
在WTO建立之前,因GATT采取“肯定一致”的原则,即当事双方之间的争端是否交予专家组审理及专家组审理的报告是否能被通过要经过全体缔约方协商一致决定,故有可能出现任何进入专家组审理的程序被起诉方所阻挠,专家组报告被败诉方所否决。这种类似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体现了GATT缔约方的“主权”。而现今WTO争端解决机制所采用的“一致否定”原则为解决各类与WTO法有关的争端,提供了一条畅通的准司法途径。(注:张乃根:《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几个主要国际法问题》,《法学评论》2001年第5期。)因为依照该原则,对成立专家组程序,只需一方请求,DSB就应成立专家组,除非协商一致决定不成立专家组,对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报告,除非DSB一致决定不予通过,否则该报告即被通过。这实际上等于授予DSB对争端的强制管辖权,被诉方除了接受DSB的管辖外别无选择,因此被有的学者称之为对传统国际法中“不得强迫国家违反其本身意志来进行诉讼规则的重要突破,”(注:赵维田著:《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页。)是对国家主权的限制。由于DSB不是也不可能是凌驾于主权之上的超国家争端解决机构,故只有当国家愿意放弃司法豁免权,DSB才可行使对其管辖权。
成员方这种对其自身主权的必要让渡可以说是WTO争端解决机制发挥效用的关键,若一味过分强调“国家主权至上”,主张成员方的自觉遵守,有可能使其效用大打折扣。
正如WTO首任总干事鲁杰罗所说,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已被公认为是“WTO最独特的贡献”。在统计表明,经过进一步主权让渡的WTO争端解决机制较先前的GATT争端解决机制得到更频繁、更有效的利用。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WTO的建立带来了国际经济法领域的一场“革命”;并且该体系仍处于变动中,其基本的主权概念、领土管辖、主权平等都必须修改。故笔者认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继续深入,为使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更有效、更公平地发挥作用,国家主权在DSB中进一步让渡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二、国家主权在私人诉权方面的让渡
如前所述,WTO争端解决机构DSB的强制管辖权,体现了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时,国家司法豁免权的让渡。而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司法豁免权对国际经济贸易主体地位愈来愈突出的私人进行一定的让渡也将成为可能。不仅如此,在DSB的执行机制中,国家强制执行豁免权的让渡也将保证其裁决得到更公平的执行及私人诉权得到有效执行。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私人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地位愈来愈突出,并且随着“多边贸易体制必然不仅由国家组成,而且,甚至主要是由单个经济经营者组成”这个在美国301条款案中专家组的结论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允许私人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首先,在DSB中私人诉权的行使,有助于保护私人的合法权益。
按传统方式,私人要对外国提出控告,须请其本国政府通过国际外交程序提出,即行使外交保护权。但是,在国际法中,国内政府官员有权最终决定是将该公民的请求提交侵害国注意,还是提交国际诉讼程序。该理论意味着有时候一个国家出于政策上的考虑,有必要在保护本国国民利益的问题上自我节制。小国为了同大国保持友好关系,也不会支持由本国少数公民提起可能触犯大国利益的诉讼。(注:John H.Jackson:《世界贸易体制——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与政策》,张乃根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
由于WTO的成员是国家和单独关税区,只有它们才可在DSB提起诉讼,私人包括个人和企业不可能在DSB行使诉权,故WTO争端解决机制未对其作专门规定。但在现今的国际贸易中,私人是主要的角色,恰恰是他们的利益会被某国的违法政策损害。因此为鼓励私人从事国际贸易交往,维护他们在交往中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允许其参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在DSB中解决与其他主权国家间的贸易争端。否则,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有可能出现一旦某国违法的贸易政策损害了他们的私人的利益,而私人所属国政府又不愿冒政治风险将争端诉诸DSB时,违法的贸易政策将延续。(注:Glen T Schleyer:Power to the peope:Allowing private parties to raise claims before the WTO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Fordham law Review,Aprail 1997。)
其次,在DSB中私人诉权的行使有助于争端解决的非政治化,进而有助于实现WTO在其宪章中所陈述的对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一个安全的,可预见的机制。
虽然在现今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下,受大国强权干涉的局面正在扭转,争端的解决更多地依赖于多边贸易协议公平、合理的实施,但因其规定仅允许国家对违反WTO的贸易法律、法规及政策提起诉讼,故是否在DSB提起争端解决仍有可能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由于私人不易受政治压力的影响,如允许其在DSB行使诉权,可使许多成员方之间的一些贸易纠纷非政治化,与一国提出的反对另一国的诉讼不同,(注:Glen T Schleyer:Power to the peope:Allowing private parties to raise claims before the WTO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Fordham law Review,Aprail 1997。)会被视为外交策略,不至导致国际关系的恶化。
有鉴于此,将国家司法豁免权的让渡扩大到私人诉权方面,允许WTO多边协议的最终受益者——私人参与其争端解决机制,处理与其他主权国家间的争端,会使WTO争端解决机制更有效力。
WTO在私人诉权方面也作了微小的尝试。在其《装运前检验协定》(PSI)中,要求那些要求商品在国内装运前接受检验的政府责成检验机构为出口商提供一个申诉程序。在申诉提出两个工作日后,出口商或检验机构可以将争议提交于1995年WTO与国际检验机构联盟和国际商会合作设立的独立机构。当争议提交上来,该独立机构将设立一个仲裁小组,其决定对出口商和检验机构有约束力。这个审查程序给予出口商根据WTO规则提起诉讼的权利,要求进口方政府(即装运前检验机构)改变其违反《装运前检验协定》的行为。换言之,个人被授权通过WTO的独立机构执行国际贸易法。(注:Steve Charnovitz:《WTO与个人权利》,张若思译,《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
虽然WTO争端解决机制未对成员方支持私人诉权作出规定,但某些国家包括我国都已制定了关于私人恳请本国政府采取行动以回应他国被宣称的不合法的贸易政策的国内法,两个最有影响的例子,即美国301条款和欧盟的《贸易壁垒规则》。依照美国301条款,任何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都可向美国贸易代表提出申诉,要求其采取针对某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的行动。贸易代表作出最终决定是否立案,一旦立案,如在150天内达不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将提交WTO争端解决机制进行裁决。欧盟的《贸易壁垒规则》允许受贸易壁垒损害的自然人、法人或企业协会都可向欧委会提出申诉,欧委会有权决定是否接受申诉。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在2002年9月23日发布的《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中也就私人诉权进行了规定。该规则第五条规定:与被诉贸易壁垒涉及的产品生产或服务供应有直接关系的国内企业、国内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企业、国内产业的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组织,可以依照本规则的规定向外经贸部提出贸易壁垒调查的申请。该规则在第九条规定,外经贸部应当自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申请及有关的证据材料之日起60天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作出立案与否的决定。规则第二十九条规定,如果被指控的措施或做法被认定构成本规则第三条所称的贸易壁垒,外经贸部应视情况采取如下措施:(一)进行双边磋商;(二)启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三)采取其它适当的措施。美国、欧盟和我国的规定虽有差别,但都给私人诉权的实现提供了一条实现的途径,说明这些国家都对私人诉权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但是无论美国的301条款或欧盟的《贸易壁垒规则》和我国的《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都不能保证美国贸易代表、欧委会或我国外经贸部出于某种政治或外交的考虑一定采取行动或接受申诉。故虽然在美国、欧盟和我国私人可依本国国内法对其他主权国家行使诉权,但WTO的成员方普遍未有类似规定,若各个成员方相继对此作出规定,难免所适用的标准程序不统一,而且可能会与WTO争端解决机制产生冲突,甚至威胁到WTO的存续。为使私人诉权得到有效实现,有必要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中进行统一规定。
此外,某些现存的国际条约也赋予了私人解决与其他主权国家间争端的诉权,如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条约(ICSID)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第11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欧洲共同体法是对私人诉权给予充分肯定的国际条约,共同体法不仅为个人规定了义务,而且赋予了他们权利。依据这一原则,在一定情况下,由于成员国没有履行《欧洲共同体条约》义务而给本国个人造成损失的,个人可以向欧洲法院对成员国提起诉讼。这在第41/74号案(凡·黛案)、第C-6/90和C-9/90号合案中均得到体现。
故此,笔者相信,正如WTO专家杰克逊先生所说的那样,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参加国将会考虑采用一些修正的方式,在“过滤”某些滥诉情况之后,允许个人和企业直接运用争端解决程序。
三、国家主权对DSB裁决执行机制方面的让渡
现存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不仅确定了DSB对建议和裁决进行监督的职责,建立了DSB对执行的定期审议和被执行方的通知制度,而且设计了赔偿和中止减让的救济措施,以促使有关争端方对建议和裁决的执行,体现了国家主权对执行机制的一定的让渡。但笔者认为,在DSB裁决执行机制方面仍存在不尽人意之处,国家主权有必要进行进一步让渡,即在执行机制中放弃国家强制执行的豁免权。
在现存的机制下,当DSB裁决一成员的国内某一措施不符合WTO某协定或虽然符合但对其他成员造成了损害后,该成员不可能再推翻裁决时,它可以有下列选择:(1)应优先考虑在合理期间内撤销或调整该项措施,如果对方就该执行措施有异议,双方应诉诸争端解决程序。(2)不采取执行措施,而是向对方作出补偿,双方在合理期间期满再加20天内就补偿达成协议。(3)既不采取执行措施,也不提供补偿,等待胜诉方经DSB授权的报复(分为报复,跨部门报复,跨协定报复即所谓的交叉报复)。(4)在达不成补偿协议后,胜诉方向DSB申请授权报复,败诉方对报复水平提出异议,申请进行仲裁,在仲裁确定的水平上接受对方经DSB授权的报复。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WTO争端解决机制并没有有效的机制保证建议和裁决的执行,即没有要求败诉方无条件接受DSB的建议和裁决。而后三种选择无疑会给争端的有效的公平的解决带来种种障碍。
当败诉方作出第二种选择,向胜诉方作出补偿。按照DSU第22条,败诉方就可以在合理的期间内仍维持其违反WTO协定或对胜诉方造成损害的措施,某些情况下,这对胜诉方遭受损害的企业显失公平,而得利的是受到补偿行业的企业。并且,前已述及,美国、欧盟、中国等国家都在其国内法中对私人诉权进行了某些肯定,除前述的美国301条款、欧盟的《贸易壁垒规则》、中国的《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还于2002年11月21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允许与反补贴和反倾销行政行为具有法律关系的个人或者组织就有关补贴或倾销幅度、损害或损害程度、是否征收反补贴税或反倾销税及其他涉及反补贴或反倾销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但在现存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下,会使美、欧、中诸国的上述国内法在实施过程中遭遇尴尬。试想,当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内企业耗费大量财力、精力在本国提起立案申请或司法诉讼,并且在本国政府接受申请或在本国法院胜诉,且本国政府将其提交给WTO争端解决机制,并得到了获胜裁决时,败诉国却选择和本国政府达成和解协议(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本国政府不可以和败诉国达成补偿协议),对本国其它行业进行补偿,从而使提出申请或诉讼的企业没有因自己的努力而获益,显然这样的结局对受损企业而言无异雪上加霜,更加无法接受。
无论败诉方作出上述(3)或(4)的选择,胜诉方都无法强迫败诉方采取措施撤销或调整其违背WTO规定或对已造成损害的措施,只好诉诸报复措施。而报复措施,尤其是交叉报复措施并不能使争端得到公正解决。
首先,报复、交叉报复措施对败诉方企业有失公平。因为其针对的是WTO成员,而受到惩罚的却是该国境内无辜的企业、公司。
其次,交叉报复措施有可能给败诉方非因违反WTO法的规定或政策而受益的产业造成损害。这是由于WTO允许在进行报复时,如果胜诉方在受损产业的中止减让义务不足以弥补所造成的损害时,允许在其他产业进行报复,而被报复的产业并未从其本国政府违反WTO法的政策中获益,故对其连带惩罚显失公平。并且胜诉方国家的经济也未必会从报复中获益,很可能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
再次,在全球化的今天,特别是跨国公司国籍色彩日益淡化的情况下,交叉报复措施这种国对国的报复,有时会出现一种荒谬的结果。例如,某跨国公司在甲国从事纺织品行业,而在乙国从事电子行业。当乙国违反WTO法的政策损害了甲国的纺织品行业(即该跨国公司在甲国的纺织品企业也受到了损害),甲国经DSB授权在纺织业协议范围内实施对乙国报复不奏效时,将报复措施扩大到了电子行业时,使乙果的电子行业受到损害,这也恰恰使该跨国企业在乙国所投资的电子企业也受到了损害。这就使该跨国企业在这场争端中承受了双重损害的荒谬结果。
另外,还要考虑的现实问题是,美国、欧盟各国经济实力雄厚,DSB若准许其对其他国家实施报复措施,其他国家很有可能因此而服从裁定。而如果一个小国获准对美国、欧盟各国实施贸易报复,会产生效果吗?最终受到利益损害的往往是这些小国的经济。
如笔者在该文的前部分所述,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引入私人诉权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但在现存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中无法使私人诉权得到有效体现。这是因为当败诉方不执行DSB的建议和裁决时,私人没有办法和权利对败诉方实施报复,更不可能采取所谓的交叉报复措施,这样会使DSB在私人诉讼中的建议和裁决变成一纸空文,也就无法使私人诉权得到有效的体现。
显然,赔偿、报复以及“交叉报复”措施在败诉方不执行DSB的裁决时,并不能使争端得到公正解决,也不能保证前述的私人诉权的有效行使。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赔偿、中止减让或其它义务均没有全部实施建议以使某一措施符合适用协议更为可取。故笔者认为国家主权对DSU执行机制应进一步的让渡,即在签署一揽子协议时承诺无条件接受DSB的建议与裁决,否则视为自动放弃WTO成员资格,也就是说成员方在缔约时完全放弃在DSB中的被执行的豁免权。
标签:wto论文; 国家主权论文; 法律论文; wto争端解决机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