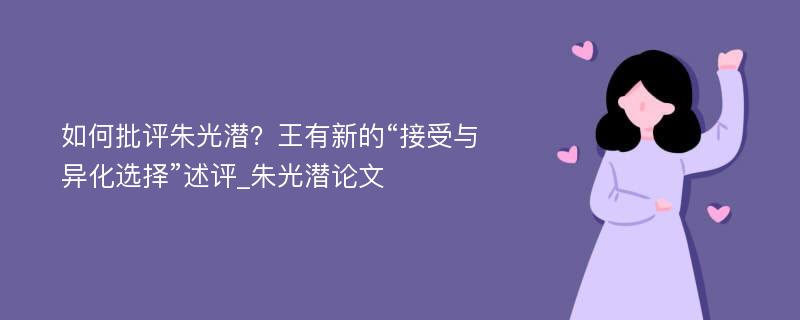
怎样批评朱光潜?——评王攸欣的《选择#183;接受与疏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朱光潜论文,评王攸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为写一篇评述朱光潜美学的论文,读了一批论述朱光潜的著作,其中包括青年学者王攸欣撰写的《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以下简称“《选择》”)。邓晓芒教授为该书作序,给予极高的评价。他的评价是:“我深感本书(《选择》——引者)是国内目前从西学东渐的立场考察近百年来学术思想变化的最深入、最具启发性的一部专著。”(注: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第7页。)邓晓芒教授高度评价使我关注此书。但是,认真研读《选择》之后,我对它的评价与邓晓芒教授有很大差别。我的评价是:《选择》是一部有许多学术错误,并且学风、文风不端正的书。
《选择》虽然只以王国维、朱光潜为研究对象,但涉及问题很多,包含的错误也很多。限于篇幅,本文集中讨论该书作者用作全书基本论据的两个判断:(1)朱光潜误解和扭曲克罗齐美学;(2)朱光潜误解和扭曲尼采美学。我通过下面的讨论要揭示的是:《选择》作者不仅没有把握朱光潜的美学思想,而且也没有把握克罗齐、尼采的美学思想。(本文只就《选择》的有关论断讨论朱光潜对克罗齐、尼采美学的理解和接受,关于朱光潜与两者之间的差异、矛盾和分歧,我将另撰专文阐述。)
一、朱光潜不理解克罗齐美学吗?
《选择》的一个基本论断是:朱光潜长期不理解(误解)克罗齐美学,而且为了达到借用克罗齐美学暗传自己的传统观念的目的,误译甚至改变克罗齐的概念;克罗齐美学的核心概念是“直觉”,朱光潜曲解和误改克罗齐美学,最典型地表现在他对克罗齐直觉概念的理解和改变上。《选择》说:
从直觉是形象霎时占满意识、形象的具体新鲜、直觉是心灵的活动、直觉与名理的分别这几点看,他(朱光潜——引者)都和克罗齐一致,但有两点与克罗齐不同:一是先认定有外物形象,二是把直觉的形象当成物“呈现”于心的形象,这样形象的形成就是被动的。克罗齐直觉则强调创造,而且被动感受的观点恰恰是克罗齐批评的对象,他认为把直觉当成单纯的感受,违反常识,直觉是心灵活动创造性地把一些模糊不清的感触、情绪综合为具体的形象。在《诗论》及30年代其他单篇论文中,朱光潜仍然保持了《文艺心理学》的直觉观念,而且把它当克罗齐的观念:“在你凝神注视梅花时,你可以把全副精神专注在它本身形象,好像注视一幅梅花画似的,无暇思索它的意义或是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这时你仍有所觉,就是梅花本身形象在心中所现的‘意象’。这种‘觉’就是克罗齐所说的‘直觉’”(注:《选择》引朱光潜这几句话有数处文字误、漏,特别是漏掉了朱光潜原文中插入的英文单词“form”和“image”,而且误注出处为“《朱光潜全集》第1卷,页51”。疑《选择》此处的引文不是来自朱光潜原著,而是从他人另文中转引。朱光潜原话正确出处是: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朱光潜为何会误解克罗齐呢?当然首先得归咎于他自己下的功夫不够,后来翻译了《美学》原理部分后就纠正了误解;另一原因是克罗齐的直觉与中国传统文论差别太大,传统文论极少把直觉当成创造性综合过程,几乎都在反映论的意义上使用直觉一词。朱氏习惯于在传统反映论的哲学背景中理解直觉,出现了重大误读,这种误读在《克罗齐哲学述评》中才得到了改正。(注: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第175-176页。)
这是《选择》中很重要、很有代表性的一段话(类似文字在该书中多次重复出现),是其作者批评朱光潜误解、改变克罗齐美学的立论基础。在这段话中,有许多问题(错误)应当澄清(纠正),但现在我只紧扣朱光潜是否理解克罗齐的直觉概念做三点分析:
第一,《选择》断定朱光潜与克罗齐在直觉观念上的一个区别是:朱光潜“认定外物有形象”,而克罗齐否定。的确,克罗齐认为形象是由直觉赋予感受、印象的,是直觉对它们的表现,是直觉的创造。在这个意义上,克罗齐否定外物有形象。但是,克罗齐仍然承认感受、印象作为直觉对象(材料)的自然性(natural),认为它们是心灵被动接受的东西(注:B.Croce,The Asethetic as the Science of Expression and of the Linguistic in General,tr.By C.Lya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6,.)。朱光潜是否“认定外物有形象”呢?不是。在《诗论》中,朱光潜说:“所见对象本为生糙零乱的材料,经‘见’才具有它的特殊形象,所以‘见’都含有创造性。”(注: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在《文艺心理学》中,他更明确指出:“美感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这里所谓‘形象’并非天生自在一成不变的……它是观赏者的性格和情趣的返照。观赏者的性格和情趣随人随时随地不同,直觉所得的形象也因而千变万化”(注: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215页。)。
读者应当注意,在上面《选择》引述的《诗论》的话中,朱光潜分别使用了“形象”与“意象”两个概念,并且说“这时你仍有所觉,就是梅花本身形象(form)在你心中所现的‘意象’(image)。这种‘觉’就是克罗齐所说的‘直觉’。”(注: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在这段话中,形象与意象两个词,正如它们分别附带的英文单词form和image,是有不同的意义的:在这里,“形象”只指对象提供的粗糙的感觉材料(相当于克罗齐的“感受”、“印象”),而“意象”才是克罗齐所谓的直觉形象(注:在《文艺心理学》中,朱光潜有“一种很混沌的形象(form)”和“一个无沾无碍的独立自足的意象(image)”两个说法,并且明确指出“意象”才是直觉的形象。(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206页,第208页)这两种说法可证明我的区别。)。因此可以说,朱光潜很清楚:梅花本身的“形象”,只是粗糙的感觉材料(构成“梅花”审美形象的条件),不是克罗齐所说的直觉形象,而对它的“见”——直觉——所得的“意象”,才是直觉形象。在这个问题上,朱光潜与克罗齐是基本一致的。《选择》作者在朱光潜与克罗齐之间所做的区分,不仅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之举,而且表现了他自己严重的知识缺陷。
第二,《选择》认定朱光潜与克罗齐有另一个重要区别,并且由此表现了朱光潜对克罗齐直觉概念的根本误解:朱光潜认为直觉的形象是物被动呈现于心的,而克罗齐认为直觉的形象是直觉创造的产物。克罗齐主张直觉是精神的创造性活动,这是确切无疑的。但是,《选择》根据什么判定朱光潜认为直觉只是被动地接受(呈现)形象呢?《选择》的根据是,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第一章论述直觉时说:“形象是直觉的对象,属于物;直觉是心知物的活动,属于我。在美感经验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觉,物所以呈现于心者只是形象。”(注: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页。)如果朱光潜关于审美直觉只说过这两句话,《选择》之说也许成立。但是,在这一章的结尾,朱光潜非常明确地总结说:“我们在上文说‘直觉属于我,形象属于物’,原是一种粗浅的说法。严格地说,直觉除形象之外别无所见,形象除直觉之外也别无其他心理活动可见出。有形象必有直觉,有直觉也必有形象。直觉是突然间心里见到一个形象或意象,其实就是创造,形象便是创造成的艺术。因此,我们说美感经验是形象的直觉,就无异于说它是艺术的创造。”(注: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5页。)因此,《选择》的论断是对朱光潜思想极武断的断章取义。
进一步讲,稍微了解朱光潜美学思想的读者都知道,主张审美经验(艺术直觉)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是朱光潜一以贯之的思想,是他对美的本质规定。朱光潜说:“世间并没有天生自在、俯拾即是的美,凡是美都要经过心灵的创造。”(注: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强调审美经验(艺术直觉)的创造性,也正是朱光潜的美学在20世纪50年代被持反映论美学观的蔡仪、李泽厚诸学者批判为“唯心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选择》说朱光潜“习惯于在传统反映论的哲学背景中理解直觉”,实在是一个张冠李戴的“重大误读”!
第三,《选择》还认定朱光潜对克罗齐的直觉概念有另一个重要误解:克罗齐认为情感不过是被动的“材质”,决不是支配力;朱光潜却主张“在心灵的创造作用中,背面的支配力是情感。”(注: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第175-176页。)《选择》做出这个判断,原因在于其作者对克罗齐美学从《作为表现和普通语言学的科学的美学》(1901)(注:克罗齐:《作为表现和普通语言学的科学的美学》,以下简称《美学》。)到《美学纲要》(1912)的一个重要变化的无知:在《美学》中,在克罗齐精神哲学总体原则下,直觉是精神活动的初级形式,是精神对机械、被动和自然的感受材料(感触、印象和情感)的主动表现。这就是说,精神作为表现(直觉)者是主动的,而情感作为被表现(直觉)者是被动的(注:B.Croce,The Asethetic as the Science of Expression and of the Linguistic in General,tr.By C.Lya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6,p.8-9,.)。然而,在《美学纲要》中,与克罗齐明确提出了“艺术即抒情的直觉”定义一致,情感由被动的直觉对象变成了直觉的原动力。克罗齐说:“是情感给了直觉以连贯性和完整性:直觉之所以真是连贯的和完整的,就因为它表达了情感,而且直觉只能来自情感,基于情感。”(注:克罗齐:《美学原理 美学纲要》,朱光潜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页。)朱光潜是在介绍克罗齐《美学纲要》中的艺术观时,讲“在心灵的创造作用中,背面的支配力是情感”的(注: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这是符合克罗齐的原意的。《选择》作者在自己既没有分清克罗齐思想的前后变化,也没有把握朱光潜在不同情况下对克罗齐直觉说的引用,就判定朱光潜对克罗齐有“重大误读”,暴露了他自己真正对这两位美学家的著作“用功不够”和草率的研究态度。
二、朱光潜不理解尼采吗?
《选择》的另一个基本论断是:朱光潜误解和歪曲了尼采的悲剧哲学。《选择》此论主要是针对朱光潜在《诗论》中对尼采的酒神一日神冲突说的引用。《选择》说:
诗境的二元性与尼采艺术中酒神与日神的二元性在关系上有近似处,尼采认为希腊悲剧由象征幻象的阿波罗照耀象征情欲本能和痛苦的狄奥尼索斯也确有些像意象体现情趣,日神精神是形象、静观而客观的,也和朱光潜的意象有共同特征。不过就其大者而言,他们的相似之处也就到此为止了。即以尼采美学最为关键的酒神精神而论,朱的理解与原意大相径庭,以构成诗境的情趣与之比拟,更是错上加错。朱氏认为尼采的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分别代表艺术中的主观和客观精神,构成对立冲突的两个方面,而尼采根本否认艺术中存在主观因素,他从不在朱光潜理解的“主观”意义上使用该词,他的酒神代表着人类而不是个人的艺术本能,象征人类的痛苦和迷醉,情欲的放纵与生命的体验,他把主观性当作个人浅薄的意欲而与人类本能的普遍性相对,艺术的形成过程是酒神精神对主观性的克服过程,当酒神苏醒的时候,就是主观逐渐消失的时候,“艺术家在酒神过程中业已放弃他的主观性”。朱光潜的情趣倾向于指诗人个人的情趣,这种情趣的主观性是在获得意象的过程中予以客观化的,事实上他的诗境更倾向于主观,他说:“没有诗能完全是主观的,因为情感的直率流露仅为啼笑嗟叹,如表现为诗,必外射为观照的对象。也没有诗完全是客观的,因为艺术对于自然必有取舍剪裁,就必受作者的情趣影响,像我们在上文已经说过的。”甚至说:“严格的说,一切艺术都是主观的,抒情的。”(注: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第206页。)
这是《选择》集中谈朱光潜对尼采悲剧思想的误解和改变的一段话的前半段(后半段则是对前半段大同小异的莫名其妙的重复)。在该段长达两页的文字中,《选择》用了“错上加错”、“显得可笑”、“不啻当头一棒”等贬义词妄加于朱光潜的头上。在该段前一页,《选择》甚至斩钉截铁地说:“叔本华和尼采在直觉表现上与克罗齐观点截然相反,朱氏同时引证他们为同一论点——诗境论撑腰实在令人吃惊。”(注: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第205页。)面对《选择》这个判断,我的问题是:究竟是朱光潜还是《选择》的作者“实在令人吃惊”?
现在让我们来解读《选择》这段文字。我仅讨论四个与本文密切相关的问题:
第一,尼采的酒神精神的基本含义是什么?《选择》说“他(尼采——引者)的酒神代表着人类而不是个人的艺术本能,象征人类的痛苦和迷醉,情欲的放纵与生命的体验”,这是大致不错的。但是,不止于此。尼采认为酒神精神的意义永远是在与日神精神的矛盾冲突中被肯定、确认和显现的。这是酒神精神的另一个同样基本的含义(而且正是这个含义使尼采的“酒神精神”与叔本华的“意志”概念区别开来!)。在《悲剧的诞生》的第一节第一段中,尼采就明确指出,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作为两种来自于自然的艺术本能,“既是并行不悖,却又总是矛盾冲突,互相给予对方新的生机,并又持续不断地投入新的对立冲突,仅能在‘艺术’的名义下显现一种调和。”(注:F.Nietzsche,The Birth of Tragedy,tr.by C.P.Fadiman,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INC.,1995,p.1.)尼采的酒神精神有两个基本含义,《选择》只讲酒神精神概念代表人类痛苦的生命体验这一层含义,不讲酒神与日神的永恒冲突与联系,如果不是出于对尼采的片面理解的话,只能说是对尼采的蓄意阉割了。
朱光潜是否正确理解了尼采的酒神精神?在《悲剧心理学》的第八章中,朱光潜对尼采的悲剧哲学(尤其是酒神精神)有准确完整的阐释,但《选择》只字未提。在《诗论》第三章中,朱光潜说:“苦痛是狄俄倪索斯的基本精神,歌舞是狄俄倪索斯精神所表现的艺术……静穆是阿波罗的基本精神,造形的图画与雕刻是阿波罗精神所表现的艺术。这两种精神本是绝对相反冲突的,而希腊人的智慧却成了打破这冲突的奇迹。他们转移阿波罗的明镜来照临狄俄倪索斯的痛苦挣扎,于是意志外射于意象,痛苦赋形为庄严优美,结果乃有希腊悲剧的产生。”(注: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朱光潜这段话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尼采的酒神精神的两个基本含义,其准确性与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一对照就知。不知《选择》作者判断朱光潜的理解与尼采的原意“大相径庭”的根据何在?
第二,尼采是否“根本否认艺术中存在主观因素”?不是。尼采反对美学中的“主观主义”,目的在于反对叔本华所主张的主观艺术与客观艺术的对立(注:F.Nietzsche,The Birth of Tragedy,tr.by C.P.Fadiman,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INC.,1995,p.13.)。尼采说:“所谓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在美学中尤其不能成立;因为充满欲望、追求着个人目的的主体只能被认为是艺术的敌人,而不是艺术的源泉。但是,在下述意义上这个主体是艺术家,即他已经摆脱了他的个人意志,并真正地成为一个中介,通过它,那个惟一真实的主体(酒神精神——引者)欢度他在形象中的解放……只有当天才在艺术创作中与这位世界的原始艺术家(酒神精神——引者)融为一体,他才能抓住艺术的永恒本质;因为在这个状态下,他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变成了神话传说中的一张能够随意转动眼睛观看自身的魔像;他现在同时是主体和客体,同时是诗人、演员和观众。”(注:F.Nietzsche,The Birth of Tragedy,tr.by C.P.Fadiman,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INC.,1995,pp.16-17.)尼采的观点非常清楚,他反对的是充满个人欲望、追求个人目的的主体(“清醒的、经验现实的自我”),而不是“根本否认艺术中存在主观因素”。
“根本否认艺术中存在主观因素”,就是根本否认艺术是人的(创造)活动。也许,这种艺术观只有在柏拉图式的“艺术(诗歌)是神灵附体的活动”的古代美学思想体系中才能成立。自康德确立艺术是人的自由创造活动观念以来,在西方现代美学体系中,是不会有人“根本否认艺术中存在主观因素”的。《选择》作者认定尼采“根本否认艺术中存在主观因素”,不仅是对尼采的严重误解,而且是违背美学常识的。
第三,尼采“从不在朱光潜理解的‘主观’意义上使用该词”吗?不是。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和朱光潜在《诗论》中,都在两个相关的意义上使用“主观”一词:第一,经验意义上的“主观”;第二,审美意义上的“主观”。经验意义上的“主观”是艺术家(诗人)个人的非艺术的自然情感(和意志),与之相对,客观则是艺术家(诗人)创造的艺术形象(艺术品)。审美意义上的“主观”,是超经验的艺术的主体性,它来自于艺术家的自我情感(意志)的审美化转换(超越)——艺术家的目我获得了审美的普遍性和超越性。尼采和朱光潜都主张,从经验的“主观”到审美的“主观”的转换,是在艺术中实现主观与客观统一(情感客观化为形象)的前提,是一切艺术的基础。尼采说:“因此,我们的美学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个在一切时代总是诉说着‘我’,用尽一切声调歌唱自我的情感和欲望的‘抒情诗人’怎样变成一个艺术家?”(注:F.Nietzsche,The Birth of Tragedy,tr.by C.P.Fadiman,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INC.,1995,p.13.)他认为悲剧艺术是诗人自我两度客观化的结果:第一,摆脱个人的意志,成为与原始意志统一的酒神艺术家;第二,酒神状态的客观化,即酒神的冲动净化为日神的美丽梦象(注:F.Nietzsche,The Birth of Tragedy,tr.by C.P.Fadiman,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INC.,1995,p.14.)。朱光潜在《诗论》第三章第四节专门讨论“诗的主观与客观”,正是以尼采的“主观客观化”原理为出发点的。朱光潜说:“尼采虽然专指悲剧,其实他的话可适用于诗和一般艺术。他很明显地指示出主观的情趣与客观的意象之隔阂与冲突,同时也很具体地说明这种冲突的调和。诗是情趣的流露,或者说,狄俄倪索斯精神的焕发。但是情趣每不能流露于诗,因为诗的情趣并不是生糙自然的情趣,它必定经过一悉冷静的观照和熔化洗炼的功夫,它须受过阿波罗的洗礼”(注: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显然,《选择》的作者只能理解“主观”的经验意义上的含义,而不能理解“主观”的审美意义上的含义。这是他断定朱光潜与克罗齐在“主观”上根本分歧的根源。另外,该作者还想当然地认为朱光潜在其诗学的情感(“情趣”)概念与尼采的“酒神精神”之间划了等号。朱光潜没有划这个等号,他只是认为,情感与酒神精神都是情绪性的和非形象性的因素(力量),两者的表现都需要一个客观化(形象化)的过程。这正如尼采所说:“悲剧神话只能被理解为酒神智慧通过日神的艺术而获得形象化表现。”(注:F.Nietzsche,The Birth of Tragedy,tr.by C.P.Fadiman,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INC.,1995,p.82.)如果《选择》的作者认真阅读了《悲剧的诞生》第五节、第六节和《诗论》第三章,而且读懂了,就会明白所谓“尼采从不在朱光潜理解的‘主观’意义上使用该词”的说法是妄下断语。
第四,朱光潜的“诗境更倾向于主观”吗?不是。相反,朱光潜与尼采一样,坚持反对诗歌中的主观主义,主张诗歌的理想境界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朱光潜说得很明白:“没有诗能完全是主观的,因为情感的直率流露仅为啼笑嗟叹,如表现为诗,必外射为观照的对象(object)。也没有诗完全是客观的,因为艺术对于自然必有取舍剪裁,就必受作者的情趣影响,像我们在上文已经说过的。”(注: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在《诗论》第三章中,朱光潜论述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诗歌的境界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即情趣与意象的契合(注: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9-73页。)。情趣与意象的契合,即情景交融,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朱光潜的创造性在于,他引用尼采的“酒神精神幻化为日神形象”说入诗学,提出情趣与意象的契合是主观化为客观、情趣化为意象的一个斗争过程。而且,也正因为从尼采的悲剧观念出发,朱光潜认为,艺术境界的极境(情趣与意象的契合),不仅实现了情感的完美表达,而且实现了自我的解放——“从形象中得解救”(注: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4页。)。《选择》作者只凭截取了朱光潜一句“严格的说,一切艺术都是主观的,抒情的”,就断定朱光潜“诗境更倾向于主观”,如果不是存心曲解,就只能是盲人摸象了。
综合上述,朱光潜对尼采的悲剧哲学是有准确把握的,两人之间在许多基本美学观念上具有深刻的一致性。《选择》作者断定朱光潜只是用尼采为自己撑腰,显然是不顾基本事实,指鹿为马。如此治学,已不只是一个“实在令人吃惊”的判断可论定的了。
三、《选择》的出发点是什么?
综合前面的讨论,我认为,如果把《选择》妄加于朱光潜的种种贬斥送还给它的作者王攸欣,是绝不为过的。现在,我要探讨的是,为什么王攸欣完全不顾朱光潜著作的基本思想、内在联系,而苦心纠缠于一些他所谓的“误解”、“扭曲”呢?
根本的原因,就是王攸欣用自己编制的解释框子去套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在《选择》一书中,他谈王国维、朱光潜,目的不在于这两位学者的美学(因此并未用心钻研他们的思想),只是要借这两个重要人物为范例,向学术界展示他的一个关于百年中国学术文化的“西学东渐”的“新”阐释模式。这个模式是:
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化的先行结构和期待视界已经显示出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和扭曲力量……还不止此,中国文化的先行结构极大地限制了审察西方文化的视界,不说接受,仅仅是理解,也多停留于肤浅的层面,西方民族的内在精神尤其是使人与社会健康发展的精神核心未能得到足够关注和透彻理解。”(注: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第283页。)
显然,朱光潜被王攸欣选择为“肤浅理解和扭曲改变西方文化”的范例。但是,就《选择》看,王攸欣对朱光潜美学甚至谈不上“肤浅理解”。比如,他在近半部书中谈朱光潜对克罗齐的“误解”、“扭曲”,却对于朱光潜与克罗齐的真正分歧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那么,他为什么选择自己无力把握的朱光潜为批评对象呢?首先,当然因为朱光潜是一个值得“批评”的对象。其次,还有一个原因,这是王攸欣可能不会承认的:意大利学者沙巴蒂尼(M.Sabatini)和美国学者麦克杜克(B.S.Mc Dougall)对朱光潜的批评诱导他选择了朱光潜为自己的批评对象。沙巴蒂尼批评朱光潜把克罗齐的直觉概念引入文艺心理学,是把克罗齐作为精神活动因素的“直觉”误解为一个关于审美经验的心理学范畴(注:沙巴蒂尼(M.Sabatini):《外国学者论朱光潜与克罗齐主义》,申奥译,载《读书》1981(3),第141页。)。麦克杜哥则批评朱光潜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传统瓦解、社会动乱中“向古老的传统倾斜”(注:麦克杜哥(B.S.Mc Dougall):《从倾斜的塔上瞭望:朱光潜论19世纪20至30年代的美学和社会背景》,申奥译,载《新文学史料》1981(3),第237页。)。认真读《选择》,就会看到,这两位外国学者的观点实际上是王攸欣对朱光潜主要看法的思想来源和精神支持。
正是追随沙氏的观点,王攸欣认定朱光潜长期基本误解克罗齐,到撰写《克罗齐哲学述评》之后才修正自己的错误;也正是追随麦氏,王攸欣认定朱光潜迷恋中国传统观念、利用西方的学术方式暗传自己的传统观念。但是,非常可惜的是,王攸欣意识不到:沙氏和麦氏对朱光潜美学的理解,都是极其有限和有偏见的。从《选择》例示的参考文献目录和正文引注可知,沙氏和麦氏是王攸欣自己通过中文恰好能阅读到的论述朱光潜的两位外国学者。王攸欣自己不理解朱光潜,明里暗里“拉”他们来为自己撑腰,可说是受了祟洋媚外的毒害。困宋在自己预定的套子中,借了两位外国学者的眼睛来看朱光潜,王攸欣除了看到一个他自己需要的“朱光潜”以外,还能看到什么呢?
在《选择》中,还有很多由于作者的学风、文风不端正而产生的问题。例一,在《选择》书末的参考文献中,例入了沙巴蒂尼和麦克杜哥批评朱光潜的文章;在该书正文中,王攸欣有两处提到沙氏,而对麦氏则未置一词。但是,《选择》中有一段长达一页半的、也有仅有的评述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的文字(注: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第166-167页。),与麦氏文章中相关论述的文字和观点都很近似(而且同样空洞!)(注:麦克杜哥(B.S.Mc Dougall):《从倾斜的塔上瞭望:朱光潜论19世纪20至30年代的美学和社会背景》,申奥译,载《新文学史料》1981(3),第244页。)。这使读者不能不意识到《选择》这部分内容与麦氏文章之间存在血缘关系。于攸欣在《选择》正文中只字不提麦氏,如果不是学风问题,也是文风问题。例二,从《选择》例示的参考文献目录和正文引注看,王攸欣根本没有读过克罗齐《美学》的英文版,但他在《选择》中处处摆出对克罗齐此书很有研究的样子,反复指摘朱光潜的中译本将某个英语词“误译”、“改变”了。事实却是,这些指摘的内容都来自朱光潜在《克罗齐哲学述评》中对相关英语词汇的说明。这是“用朱光潜批朱光潜”的伎俩。王攸欣对此事实也是只字不提,实在难辞蓄意掩盖之咎。
四、怎样批评朱光潜?
我以“怎样批评朱光潜?”为本文的题目,就包含了一个前提:朱光潜是可以批评的。事实上,在现代中国美学史上,朱光潜,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代表人物,产生的影响最大,经受的批评最多(批判最重)。建国前,20世纪30年代有鲁迅、40年代有巴金、郭沫若、蔡仪等文化名人批评(批判)朱光潜;建国后,朱光潜更经历了1956-1962的美学大批判,批判队伍包括中国当时有发言权的文艺理论界的诸多权威人物和李泽厚等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文革”结束后,朱光潜美学研究和批评也曾是20世纪后期中国美学的一个热点课题。今天,正因为朱光潜是中国现代美学的代表人物,对他的美学思想的研究和批评,就是我们总结20世纪中国美学遗产、推进新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工作。
但是,20世纪中国美学史的经验、教训证明,批评朱光潜是一个艰深的课题。它不仅要求批评者具有踏实严谨的学风和文风,而且要求批评者必须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深广的理论视野。以王攸欣在《选择》中的学风、文风进行朱光潜美学研究和批评,结果只能是对朱光潜美学的简化和丑化,不仅不能进一步发掘朱光潜美学的真正价值,而且也不能揭示朱光潜美学的真正局限。我写此文的目的,不仅在于批评王攸欣的错误,而且在于呼吁扎实、健康的美学研究和批评。
标签:朱光潜论文; 尼采哲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朱光潜全集论文; 酒神精神论文; 文艺心理学论文; 悲剧的诞生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美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