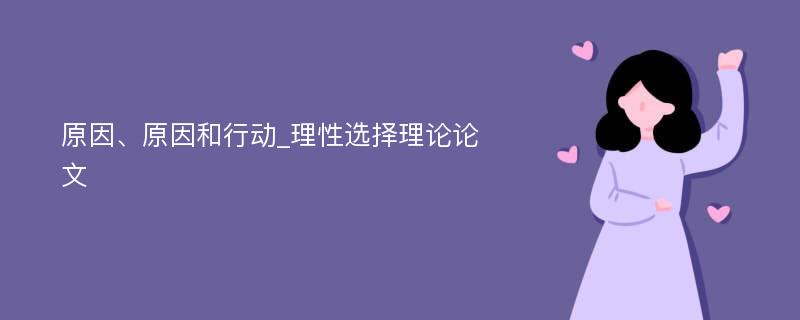
理由、原因与行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由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行动既有其理由(reason),又关乎原因(cause)。从具体的机制看,行动的理由与行动的原因所涉及的,是行动的根据与行动的动因。理由为行动提供了根据,也使对行动的理解成为可能。在现实的形态上,理由表现为一种系统,并关联着内在与外在、现实与可能等不同的方面。以个体意愿与理性认知的互动为背景,理由同时关联着自觉和自愿等不同的行动形态。通过化为内在动机,理由进一步进入因果之域。行动不仅涉及理解与解释,而且关乎规范与引导,后者意味着不能将行动的原因仅仅限定在逻辑层面的理由,而应对其作更广意义上的考察。在这里,形式与实质、逻辑关系与现实背景之间呈现了内在的统一,而理由、原因与行动的相关性则由此得到了具体的展现。
理由包含多重内涵。从理由与行动的关系看,理由可以视为行动的根据:所谓有理由做或有理由去行动,也就是有根据做或有根据去行动。在这一论域中,理由首先与行动的可理解性相联系:没有理由的举动,往往无法理解。在此,目的构成了理由的具体内容:有目的的活动表现为有理由的行动,其过程具有可理解性;无目的的活动则呈现为无理由的行动,其过程往往难以理解。
在行动的视域中,理由的另一内涵涉及权利。就理由与行动者的关系而言,有理由做某事意味着行动者有权利做某事。这里的权利同时包含正当性。行动在某些场合具有“理直气壮”的特点,这里的“理直”,便既以理由的正当性为根据,又基于理由之合乎行动者的权利。以日常的活动而言,在法律与道德所容许的范围之内,个体选择做此事而非其他事,其中的理由不仅与各种理性的考虑及个体的兴趣相联系,而且涉及其所拥有的权利。在很多情况下,“你有什么理由这样做”的追问,也等于问“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
权利在逻辑上与责任具有相关性,理由与权利的联系使之同时关涉责任。对一个教师而言,根据课程的安排到校上课,是其日常的行动,而这种行动的理由,便以责任为实质的内容:作为教师,你有责任在承担课程的情况下按相关要求到校上课。在以上关系中,责任的内涵可表述为“这是你的分内之事”或“你应该这样做”;以否定的方式表示,则是“你没有理由不这样去做”。在这里,有理由去做意味着有责任去做。
如前所述,与可理解性相联系的行动的理由,赋予行动以理性的品格,后者同时表现为广义的合理性。相形之下,以权利为内容的行动的理由,则更多地关乎正当性。在基于责任的行动的理由中,这种正当性得到了更切近的体现:责任所指向的是当然,而正当则表现为合乎当然。如果说可理解意义上的合理性首先涉及逻辑之域,那么权利和责任层面的正当性则更多地与价值之域相联系。相应于此,以理由为根据,行动既体现了理性的自觉,又被赋予价值意义上的正当性。
从具体的形态看,行动的理由呈现多样性。以行动的目标为指向,理由往往关涉“为什么”的问题。在主体选择的层面上,“为什么”首先与目的相联系。以日常生活中的散步而言,“为什么每天散步?”回答如果是“为了健身”,则“健身”便构成了“散步”这一行动的理由。这里的“健身”表现为目的,以“健身”为散步的理由,则意味着将理由的内容理解为目的。与漫无目的的举动不同,有目的蕴涵着理性的自觉。就此而言,目的关乎可理解意义上的合乎理性。同时,目的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别,涉及价值层面的合理性。目的所具有的以上特点,同时也赋予目的层面的理由以二重性。
目的更多地与主体的观念相关,行动的理由则不限于主体的观念之域。在很多背景下,行动的选择往往关乎外在的规则与事实。以学校教育中的考试而言,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已到的情况下,监考教师便会收卷。收卷是一种特定的行动,其理由则涉及两个方面:考试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这是规则;规定的时间已到,这是事实。在此,监考教师进行收卷这一行动的理由便既依据规则,又基于事实。作为理由的一个方面,事实构成了重要的因素:监考中的收卷,不能仅仅以主观上“相信”时间已到为依据:仅仅依据主观上的相信,往往会发生错误(如实际上时间尚未到,却以为时间已到),从而无法成为合理的行动理由。
在规则与事实的结合中,规则相对于个体而言具有外在的性质。从行动者自身方面看,行动的理由往往又与自我的身份认同相联系。现实情境中的行为选择,往往基于这种身份认同。以传统社会中的父慈子孝而言,“慈”和“孝”以关切和敬重为实质的内容,后者乃是通过个体的行动体现出来,而这种行动又以“父”或“子”的身份认同为前提。当然,“慈”和“孝”的行动以什么样的具体形态表现出来,则又取决于特定的情境,这种情境所涉及的是多样的事实。例如,在严寒的季节中,关切的行动一般便体现为如何使相关对象处于温暖之境而非为其降温。此时,何以送暖或保温,便不仅关乎一定的社会角色以及相关的义务(父、子等身份规定了相应的责任),而且也与特定的事实(天寒)相联系。综合起来,在以上背景中,行动选择的理由既以身份认同为前提,又本于一定的事实。广而言之,日常生活中的行动,常常同时涉及身份认同与相关事实背景。在球类比赛中,不同的观众每每会因为不同的球队进球而欢呼喝彩,这种欢呼或喝彩行动,便以身份认同与具体事实为理由:为什么看到某一球队进球就欢呼喝彩?这一行动一方面与身份认同相关:欢呼者认同自身为该队的球迷;另一方面又关乎事实:该队此时进球了。
理由作为行动的根据,涉及广义的“应该”(ought to),事实则表现为“是”(is)。事实与理由的关联,从一个方面表明,“是”与“应该”之间并非完全悬隔。不过,就行动的过程而言,单纯的事实并不构成理由,事实唯有与行动过程的其他方面相联系,才能进入理由之域。在行动基于外在的规则与事实的情况下,事实之构成理由的要素,以它与规则的关联为前提。在前述事例中,“考试时间已到”这一事实之成为收卷这一行动的理由,便是建立在它与考试规则的联系之上。同样,某一球队进球这一事实之构成特定观众欢呼喝彩的理由,也关联着事实之外的因素:只有在欢呼喝彩者认同自身为该队球迷的情况下,以上事实才构成其欢呼喝彩的理由。规则与认同蕴含外在与内在之别,二者与事实的结合,既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事实融入理由的不同形式,也具体地展示了行动理由的多样内容。
关于行动的理论通常以欲望与信念的统一作为行动的理由,按照这一理解,如果行动者形成某种欲望,并相信某一相关事物可以满足这种欲望,则他便具有实施某种行动的理由。然而,信念固然可以构成行动的理由的一个方面,但它本身又有是否合乎事实的问题。唯有在信念合乎事实的条件下,与之相联系的行动才能获得理性的形式。广而言之,行动之有理由在某种情况下并不意味着行动之合乎理性;有理由与理性化之间的这种张力,往往形成于信念与事实之间的距离。
就现实的形态而言,行动并不具有单一的形式,而是展开为一种相互关联的系统。在不同行动的相互联系中,一种行动往往可以成为另一种行动的理由。栽下树,这是一种行动,这一行动本身又构成了浇水等后续行动的直接理由。同样,到商店挑选所需要的商品,这也是一种行动,这一行动同时又成为走出商店之前付款的理由。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两种行动之间的关联具有不同的性质。栽树与后续的浇水等行动之间的联系,基于自然的属性和法则(树木在种植之后需要水分);在商店选择商品后付款,则以社会领域的体制性事实为背景(根据市场经济与商业交易的规则,选定的商品只有在付款之后才能作为已购之物带出商店)。与之相联系,在以上情形中,前一种行动之成为后一种行动的理由,也分别地涉及自然的法则与社会的准则。当然,作为理由,二者又包含相通之点,这种相通性主要表现在,前一种行动之成为后一种行动的理由,以行动者的内在承诺为前提:在栽树的事例中,只有当行动主体在种下树木的同时承诺让所种之树得以存活,栽树的行动才成为后续浇水等行动的理由在选购商品的情形中,唯有行动主体承诺按商品经济中的社会准则行事,选择商品这一行动才会成为付款的理由。以上承诺常常并不是以显性或自觉的方式作出,而是更多地取隐含的形式。在这里,一种行动之成为另一种行动的理由,既基于自然的法则与社会的准则,又与行动者的内在承诺相联系。
抽象地看,以上视域中行动之间的理由关联,似乎可能引向层层的回溯:某一行动在为后续行动提供理由的同时,本身又以另一行动为理由,如此可以不断上溯。然而,就现实的形态而言,社会领域中不同的事物之间固然存在历史的联系,这种联系也体现于前后相继的行动之间,从而,某一行动确乎可以追溯其先行的根源;但行动同时又总是发生于特定的背景之下,后者以综合的形态构成了行动的具体根源:历史的因素本身也通过渗入于其中而发生作用。与之相联系,当我们考察某一特定行动的理由时,往往无需不断地向前追溯,而可以主要基于行动发生时的综合性背景。就形而上的视域而言,前后相继的行动之间的关系既具有内在性,又具有外在性:关系的内在性要求我们关注行动间的历史联系,关系的外在性则使我们可以从现实的背景出发考察行动。同时,从行动与行动者的关系看,行动往往又以行动者为直接的根源,各种历史的关联常常凝聚于行动者之中,由行动者引发的行动,也相应地源于行动者的现实存在。以上事实表明,行动之间的理由关联,并不意味着引向无穷的后退。
作为行动的现实根据,理由并非仅仅以单一的形态呈现,而是展开为一个结构,其中既包含事实以及对事实的认知,也涵摄人的意向、目的。以出门带伞而言,带伞的理由(为什么带伞)便涉及多重方面。从事实的层面看,“带伞”这一行动可能是基于天正在下雨;从行为者的视域看,之所以带伞则一方面基于某种认识(确信天在下雨或天将下雨),另一方面又出于某种意向或意欲(不希望被雨淋湿)。仅仅出现某种事实(如天下雨),并不构成行动(如带伞)的理由;单纯的认识(如确信天在下雨或天将下雨)或意向(如不希望被雨淋湿),也难以成为实施某种行动的理由。唯有一方面在事实层面上出现了“天下雨”这一情形,另一方面行动者又具有“天在下雨或天将下雨”的确信,并同时形成“不想被淋湿”的意向,带伞这一行动的理由才会具体地构成。在这里,理由包括事实(“天下雨”)、认识(人确信天下雨)、意欲或意向(“我不想被淋湿”)等多重因素,这些因素相互联系,呈现为统一的结构。
理由既具有结构性,又涉及时间性。行动的理性品格,在于其理由不只是考虑当下的情形,而是同时兼顾未来:一个理性的行动者,不能仅仅以满足目前或当下的欲望为行动的理由,而完全无视这种行动在未来可能带来的危害。这里既涉及行动的意欲与行动的结果之间的关系,也关乎时间之维(当下观念与未来事实之间的关系),二者从不同方面展现了行动的理由的具体内涵。
与时间性相联系,行动的理由同时具有生成的品格。在宽泛的意义上,行动的理由既与一定的情景相关,又涉及行动者对具体情境的认识以及行动者的内在意欲和意向。行动的具体情境与主体的意欲和意向都处于动态之中,与之相关的行动的理由也具有可变性、生成性:某种情境与主体的认识、意向相互交融而为行动提供理由,这一类现象往往发生于具体的生活与实践过程。事实上,从更广的层面看,个体的言与行在其展开的过程中,本身也可以为行动的理由提供前提。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言,当个体向他人作出某种承诺之后,这一承诺往往便构成了进一步行动的理由:在作出承诺之后,就“有理由”(应当)去履行承诺(做所承诺之事)。作出承诺不同于前文提及的隐性承诺,而是一种自觉、显性的语言行动;这里既体现了语言行动与实践行动的相关性,也从一个方面具体表明行动的理由常常生成于行动者自身的活动。
作为影响行动的具体因素,理由同时涉及内在与外在、现实与可能等不同的方面,并与个体的意欲、理性的认知相关联,后者进一步赋予行动以自觉、自愿等形态。在个体意欲、理性认知与内在动机的互动中,理由在行动中的意义得到了更内在的体现。
从现实的过程看,理由对行动的影响每每通过某些中介而实现,其中动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里需要对理由与动机的关系作一分疏。以理由与动机的关系为视域,理由本身可以进一步从内在与外在两个方面加以考察。宽泛而言,理由的内在之维主要与个体的意欲、要求相联系,其外在之维则涉及外部的事实(如社会的体制)、一般的原则和规范,等等。当个体形成了某种意欲之后,这种意欲常常便从内在的方面为行动提供了理由。尽管如后文将要讨论的,具有某种行动的理由并不意味着应当实际地去实施这种行动,但从逻辑上看,意欲无疑为行动的理由提供了内在的依据。同样,外部事实也每每从一个方面为行动提供理由,如前文所提及的,在日常生活中,“下雨”这一事实常常构成了带伞的外部理由。进而言之,社会领域的一般原则、规范也可以成为个体行动的理由,如交通规则,便构成了人们在行路、驾驶时选择某种方式的理由,这里的理由同时表现为行动的根据。相对于个体的意愿,外部事实与一般的原则、规范存在于个体之外;作为行动的理由或根据,它们也呈现外在的性质。
相对于理由,动机可以视为行动更直接的动因。动机包含多重内容。首先是目的,目的赋予动机以价值的内容:动机的正当与否主要涉及动机所内含的目的。动机同时又与反思相联系,反思的作用主要体现于对意欲的自我评判和取舍。以反思为内在环节,意欲在融入动机之时总是经过了某种“过滤”;正是反思渗入并融合于动机,使动机区别于单纯的欲望而取得了自觉的形态。动机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意向,动机中的意欲本身即包含意向性:在动机之中,意欲与意向相互交融,从而使动机本身既具有指向性,又推动着主体走向行动。可以看到,以目的、反思与意欲-意向的相互关联为现实内容,动机构成了引发行动的内在动力,并为行动的展开提供了具体的引导。
就理由、动机与行动的关系而言,理由更多地从形式的向度为行动提供根据,动机则在实质的层面表现为行动的动力因。在现实的过程中,理由对行动的实际影响往往通过转化为动机而实现。如前所述,从内在的方面看,理由可以基于意欲,这一层面的理由之转化为行动的动机,与意欲向动机的转换具有相通性。意欲可以引发理由,但意欲却无法直接表现为动机。意欲之转换为理由,以自我的反思、评判为前提,其中既涉及价值的判断,也关乎理性的权衡。名利固然具有可欲性,可以成为选择某种行为的理由,但对具有道德理想的人而言,仅仅基于这类意欲的理由难以进入动机之域,孔子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便体现了这一点。同样,到火星去旅游,对人也具有吸引力,并可以成为人的意欲,然而,在现代的科技条件下,人即使形成这种意欲,它也难以成为行为的现实动机,因为它对一般人而言缺乏可行性。以上两种情形虽然侧重的维度各异,但都涉及基于意欲的理由与实际动机之间的关系,其中既可以看到价值的评判,也不难注意到理性的考量,二者在不同的意义上构成了理由转换为动机的前提。
基于意欲的理由具有内在的形式,理由的外在形态则往往关联社会领域的一般原则、规范。如前所述,社会领域的一般原则、规范可以成为个体行动的理由,但这种理由能否转化为行动的实际动机,则取决于多重方面。作为普遍的规定,一般的原则无疑为行动提供了理由或依据,但当这种原则仅仅以外在形式存在时,常常并不能实际地激发行动。唯有当普遍的原则、规范不仅为个体所自觉地认识和理解,而且为其所肯定、接受、认同,这种原则才可能现实地影响个体的行动。相对于理解和认识,对一般原则的肯定、接受与认同渗入了一种态度、立场,其中包含情感层面的接纳和意志层面的抉择。这里的意志抉择内在地关联着从“我思”到“我欲”的转换:“我思”主要是观念性活动,“我欲”则既是观念性的活动,又具有超出观念之域而走向行动的意向。正是通过情感的接纳、意志的抉择以及与之相关的从“我思”到“我欲”的转换,一般原则的外在性得到消解,行动者与一般原则之间的界限也开始被跨越。从一般原则与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看,这一过程意味着外在原则向主体的内化;从理由与动机的关系看,这里又蕴涵着导源于一般原则的理由向特定行为的动机的转换,二者表现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可以看到,行动的理由唯有在转化为行动的动机之后才能实际地引发行动,而这种转化又建立于一定的条件之上。理由可以源于意欲,现代的一些行动理论将欲望(desire)加上信念(belief)作为行动的理由,也注意到了理由与意欲的联系。尽管就理由展开为一个系统而言,意欲并不构成理由的全部内容,但意欲确乎可以进入理由之域。然而,源于意欲的理由之成为行动的实际动机,又离不开理性的反思以及价值的评价。这里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意欲与信念的结合,而且更在于对作为理由内容的意欲本身加以反省;这种理性的省察和价值的评价,构成了理由转换为动机的前提。
与之相类似,基于一般原则的理由,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转化为动机,这种条件包括理性的确认、情感的认同以及意愿层面的选择和接受。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曾提出内在理由与外在理由之分。他所说的内在理由主要与行动者(agent)的意欲、主观动机相联系,外在理由则主要与理性的思虑相关。威廉姆斯质疑外在理由,其主要的依据便是仅仅通过理性的慎思,并不能形成动机。(威廉姆斯,第144-161页)他注意到单纯的理性信念无法直接化为行动的动机,但由此将涉及理性的所谓外在理由与动机分离开来,则似乎忽视了:理性的信念与情感的认同及意愿的选择、接受并非彼此相斥。事实上,理性所把握的一般原则,可以通过情感的认同与意愿的选择、接受,内化为个体的动机。就道德实践而言,当伦理的规范对个体仅仅呈现为外在的理性律令时,它诚然并不能成为人的行为动机,但如果个体在情感上认同这种规范,并且在内在意愿上对其加以选择、接受,则这种规范便能够融入于个体的行为动机:此时,按相关的伦理规范而行动,同时表现为出于个体内在动机的选择。
从更实质的方面看,行动理由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内在与外在的问题。如前所述,通常所说的内在理由或理由的内在之维主要与个体的意欲以及意愿相联系,而源于内在意欲或意愿的行动,则具有自愿的性质。就理由与行动的关系而言,当理由基于个体意欲时,它同时也从内在的方面为行动出于自愿提供了前提。尽管这种基于意欲的理由在转换为实际动机时总是经过理性的反思,但其中的意欲在得到肯定和接纳之后,同时又赋予行动以自愿的性质。在这里,理由向动机的转化,与行动获得自愿性质具有一致性。在引申的意义上,外在理由或理由的外在之维可以视为源自一般规范或一般原则的行动理由:一般的原则、规范在被认识、理解之后,同时也为行动提供了根据。在道德领域中,义务通过一般的规范而得到确认;与上述意义上义务的外在性相应,一般的规范也呈现外在性质。从形式的层面看,相对于行动的个体,一般的规范确乎具有某种外在的特点,以此为行动的根据,也赋予行动的理由以外在的形态。就实质的方面而言,对一般原则和规范的认知和理解,进一步表现为一种理性的自觉,由此出发,行动本身也获得了自觉的品格。基于外在规范的行动的理由之转化为实际的动机固然不仅以理性的把握为前提,而且有赖于情感的认同和意愿层面的接受,但以理性的规范为内容,这种理由确乎又从一个方面规定了行动的自觉性质。规范涉及当然,如前所述,后者在伦理实践的领域往往又以义务为内容。与之相联系,对义务的把握和承担,也可以成为行动的理由:如果个体承担了某种义务,他就有理由去履行这种义务。义务的承担作为行动的理由,从另一重意义上赋予行动以自觉的内涵。
就现实的过程而言,在仅仅基于内在意欲之时,行动诚然可以带有自愿的特点,但每每容易导致非理性的趋向。在单纯出于意欲的各种盲目行为冲动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当行动完全以有关普遍规范、原则的理解和认识为依据时,其过程诚然合乎理性,却常常缺乏自愿的品格。如果说理由与内在意欲的联系为行动的自愿趋向提供了前提,那么基于普遍的原则、规范则使理由获得了自觉的内涵,并由此从一个方面为行动的自觉向度提供了担保。理由的内在性与外在性之外更实质的问题,是行动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自觉与自愿的关系。在理由向动机的转化中,以上问题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了体现。基于普遍原则的理由之转化为行动的实际动机,离不开情感的认同、意愿的接受:这种认同与接受所涉及的,是通过内在意愿、情感的接引,避免单纯地注重自觉以及对理性原则的片面依循,赋予行动以自愿的品格。要而言之,理由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的关联所体现的,是行动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自觉与自愿的统一。
以行动者与理由的关系为视域,理由的内在性与外在性也可以从现实的形态与可能的形态加以考察。当理由为行动者所理解、接受、认同,并成为行动的实际根据时,理由本身便取得了现实的形态。无论是源于意欲,抑或基于普遍原则、规范,理由唯有实际地制约行动,才呈现为现实的形态。现实形态的理由具有内在的形式:对普遍原则、规范的接受与认同,同时意味着将这种原则、规范化为行动的内在理由。理由的可能形态既涉及形式之维,也关联着实质的方面:从形式之维看,其特点首先体现于理由与行动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日常的行动而言,某种食物有益人体健康,而健康对人来说又具有正面的价值,这里体现的是实质层面的事实。既然人一般都希望健康,而这种食物又有益于健康,因此人应该食用或摄入这种食物。这一推论所体现的则是一种逻辑关系。在这里,相关食物所具有的功能,便呈现为行动(选择或食用)的理由。然而,以上关系中的理由,主要基于形式层面的推论:它在逻辑上可以成为行动的理由或具有成为行动理由的可能,但并不一定实际地成为行动的理由。在上述例子中,如果相关食物的口味不如人意或让人难以接受,便不一定为人所选择,从而它所具有的促进健康这一类功能也无法成为行动的实际理由。与之相近,如果个体产生了一定的意愿,而某种行动又能够实现个体所具有的那种意愿,那么从逻辑上说,个体就具有选择那种行动的理由。不过,基于逻辑关系的以上理由,也只具有可能的形态,它与行动的实际理由之间同样会存在某种距离:如果以上意愿和行动与个体确信的价值原则相冲突,则即使这种意愿出现于个体意识中,也难以成为个体选择的现实理由。
在以上情形中,行动的理由同时涉及内在之维与外在之维:以实质层面的事实为前提的理由,具有外在性;基于内在意愿的理由,则呈现内在性。然而,从理由对行动的作用看,更值得关注的是其中所蕴涵的可能形态与现实形态之间的关系。理由的可能形态既涉及实际的根据,也关乎形式层面的逻辑推论,它在显现行动方向的同时,也为行动的多样展开提供了空间:作为可能的根据,上述理由从一个方面预示了行动的某种方向;但它是否被实际地接受为行动根据,则具有未定性,后者又使行动蕴涵了不同的趋向。从理由的可能形态到现实形态的转换,具体地关乎理性审察、情感认同、意愿接受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也可以视为实现以上转换的内在条件。
行动的考察不仅涉及理由,而且也关乎原因。在行动之域,理由与原因呈现较为复杂的关系。一方面,理由既为行动的解释提供了依据,也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行动的原因;另一方面,原因在引发行动的同时,也对行动的理解和说明具有独特意义。在更深的层面,理由与原因之辨,又关乎行动的解释与行动的规范之间的关系。
就理由与行动的关系而言,理由既是行动的根据,又表现为推论的前提,这种推论过程首先与论证相联系。对于行动,通常可以提出其发生是否有理由的问题:一种行动是否有理由,是其能否被理解的基本前提。无理由的行为,往往具有非理性的性质,行动的理由则至少在逻辑的层面赋予行动以合乎理性的品格。在后一意义上,给出行动的理由,同时意味着为行动的合理性提供论证:当我们说某一个体有理由这样做时,我们同时也确认了其相关行动在可思议或可理解的意义上是合理的。
从另一侧面看,对行动合理性的论证又具有解释行动的意义。戴维森已注意到这一点,他认为:“证明一个行动正当和解释一个行动常常是形影相随的。”(戴维森,第393页)“行动的发生是否有理由”这一问题,如果以另一种方式来表示,也就是“为什么某种行动会发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以解释行动发生的缘由为实质的内容,而对行动的缘由的解释,则离不开对行动的理由的分析。关于行动的理由的内涵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不同行动的具体理由也可以各不相同,但行动的缘由(行动为何发生)与行动的理由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这一事实则难以否认。如果行动的理由被揭示和阐发,则一方面其逻辑层面的合理性便得到了确认,另一方面行动所以发生的过程也得到了某种解释。
在逻辑的层面上,对行动的解释以行动业已发生为前提:只有当行动发生之后,才会形成对该行动的解释。理由在为解释已发生的行动提供依据的同时,也具有引发行动的意义,后者体现于行动发生之前。在行动之域,关于“为什么”的问题既指向行动的逻辑缘由,也关乎行动的实际原因。行动的逻辑缘由涉及的是行动与理由之间的关系,行动的实际原因则包括引发行动的各种现实因素,理由构成了这些因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前所述,理由的具体构成包括广义的观念形态(意愿、信念、被认识或接受的规则,等等)与非观念形态(外部事实以及事实之间的关系),二者从不同方面影响、制约着行动的发生。理由的以上作用使之同时具有原因的意义。事实上,就现实的形态而言,理由与原因之间确实存在相关性。
关于理由与原因的以上关联,戴维森曾作了较为具体的考察。在他看来,以理由来解释行动,可以视为合理化的解释,而合理化的解释则“是一类因果解释”。他所理解的理由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其一,对于某种行动的支持性态度,包括愿望、需要、冲动、目的、价值,等等;其二,信念,即相信行动属于那一类别。以上二者所构成的理由又称为基本理由,对戴维森而言,“行动的基本理由即是它的原因”。(参见戴维森,第386-388页)这里所说的态度与信念,都与心理的活动相联系:以态度与信念所构成的理由为行动的原因,其前提是肯定心理的事件可以成为行动的原因。就理由与行动的关系而言,以上看法注意到了观念形态的理由对行动的作用;从理由的内涵看,它则有见于理由所包含的原因之维。在现实的形态上,行动的理由既具有逻辑的意义,又呈现为心理的形态:前者主要与解释和推论的过程相联系(理由为这种解释与推论提供了逻辑依据),后者则体现于行动的具体展开过程(观念形态的理由构成了引发行动的内在原因)。
不过,在总体上,戴维森所注重的更多的是理由的解释意义。他之肯定理由与原因的联系,首先着眼于解释,其基本观点“合理化解释是一类因果解释”,也表明了这一点。解释所侧重的是理解,以行动的解释为关注之点,相应地也主要涉及如何理解行动的问题。戴维森的行动理论在更广的意义上反映了分析哲学考察行动的一般进路:事实上,在分析哲学的系统中,有关行动的理论主要便以解释与理解为指向。然而,就其现实形态而言,人的行动不仅有如何解释与理解的问题,而且面临如何规范的问题。对行动的解释主要侧重于从逻辑关系上把握行动,在此论域中,行动的理由也主要为行动的理解提供逻辑的依据。对行动的规范则关乎行动的现实引导,理由在此意义上则进一步涉及做什么与如何做的问题。
以行动的规范为视域,理由与原因的关系也展示了其更为深层的方面。在以理由为行动的原因这一解释模式中,理由被理解为行动所以发生的根源。根据这一模式,只要把握了行动的理由,则行动似乎也就在逻辑上得到了解释,从而能够被理解。这一理解—解释模式主要限于理由与行动的关系,尽管其中也涉及原因,但这里的原因与理由具有某种重合性:行动的发生源自一定的理由,理由则以关于行动的支持性态度(包括愿望、要求、目的等)与信念为内容。换言之,愿望、要求、目的等(对行动的支持性态度)与信念作为理由的具体内容,可以引发行动。然而,如果越出以上关系,进而对行动的理由加以考察,则可以发现理由本身也涉及所以发生的原因,后者具体地表现为不同的愿望、目的、要求以及信念形成的背景、条件。
从行动与理由的直接关联看,不同的愿望、要求、目的与信念的交融,往往导致了不同的行动。此处的行动首先涉及正当性,其中内在地关联着以意愿、目的、信念为内容的行动理由:理由的正当与否制约着行动的正当与否。如何担保行动理由的正当性这一问题,从另一方面看也就是如何对意愿、目的、价值观念、理性信念本身加以引导。这里既在历史层面涉及意识发生、形成的历史背景,也在观念层面关乎意识本身的自我反思、批判,二者均已不限于理由的层面。要而言之,从行动的规范这一层面看,理由固然可以在化为动机后作为内在原因而引发行动,但它本身又有所以形成与发生的根源,并面临如何获得自身合理性(正当性)的问题。如何通过引导行动的理由以规范行动本身,构成了行动理论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行动理由的引导则越出理由之域而涉及理由形成的更广背景和内外条件,后者进一步关乎如何为个体意愿、目的、价值观念以及信念的健全发展提供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多样的条件。以市场经济背景下常见的广告而言,商品广告的不断重复,往往容易使人形成某种消费的意欲,这种意欲又会进一步为相关的行动(如选购广告所介绍的商品)提供理由。从更广的历史视域看,一定时代的社会背景、价值和舆论导向,也每每多方面地影响人的观念,后者又从不同的层面制约着行动理由的形成。进而言之,行动的理由往往呈现为一个系统,在行动的现实展开过程中,理由与多方面的原因又互渗互融,构成了一个更广意义上制约行动的系统。
对行动过程中理由与原因的以上理解,涉及更一般层面的因果关系和因果观念。从本体论上看,因果关系存在于事物或事件之间,表现为一种具有必然性的关联。然而,从行动的角度考察因果性,同时又应当关注行动者与原因的关系。以理解与解释为指向,原因或因果性首先表现为一种被观察的对象:对已发生之事的解释,总是基于某种旁观的立场,其中所涉及的有关行动原因的推论,也往往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分析哲学关于行动的理由—原因解释模式,似乎基本上没有超出对于因果关系的观察或旁观立场。就行动的现实过程而言,在行动与原因的关系中,行动者不仅仅是观察者或旁观者,而且同时也是实际的参与者,后者为行动者影响和作用于行动提供了可能:他可以通过自身的知与行,生成某种观念和事件,这种观念和事件又作为原因,进一步影响与制约后续的行动。行动者与原因的以上二重维度,在更广的意义上构成了考察理由本身形成之因的前提:由制约行动的理由(这种制约包括为个体意愿、目的、价值观念以及信念的健全发展提供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多样的条件)而规范行动,其根据便在于行动者不仅是行动原因的观察者,而且作为行动的实际参与者而作用于原因本身。可以看到,对行动过程中的因果关系的具体把握,离不开观察与参与的二重维度。
通过参与而影响行动,同时也使行动者本身进入了因果之域。就行动与原因的关系而言,行动的原因在广义上包括事件原因(event-causation)与主体原因(agent-causation):前者体现于外部事件对行动的影响,后者表现为行动者的意愿、目的、信念等对行动的引发,二者对行动的发生都具有制约作用。作为具体的过程,行动既非仅仅出于外在的事件,也非单纯地源自行动者的内在意念。单向地关注主体原因,往往无法避免任意性;仅仅关注事件原因,则无法把握行动的自主性。在现实的行动过程中,既需要以客观的事件(条件)抑制主体的任意性,也应当以主体原因限定事件的外在性。事件原因与主体原因的互动,既体现了行动过程中因果性与自主性的统一,也使行动过程中的原因超越了逻辑的形式而落实在一个更为具体的层面。
行动过程中的主体原因,进一步涉及理由、动机与原因的关系。行动者对行动的推动,首先通过理由与行动的关系而得到体现。这里,需要区分实际的或真实的理由与非实际的或不真实的理由。在某些情况下,个体可以宣称他做某事是出于某种理由,然而,其真实或实际的行动理由可能与之并不相同。一般而言,理由只有在具有真实性的前提下,才能转化为行动的动机,并实际地影响行动。当理由缺乏真实性时,这种理由便无法化为行动的动机,从而也难以作为内在的原因实际地影响人的行动。在此,以理由的真实性为前提,理由、动机与原因呈现相互的关联:真实的理由通过化为动机而获得内在原因的品格。儒家曾区分“为人”之行与“为己”之行:“为人”即为了获得他人的赞誉而做合乎道德规范之事,为己则是为自我在道德上的实现而践行道德原则。以“为人”作为指向,行为的理由与行为的动机之间存在着张力:行动者的真实动机是获得外在赞誉,而他显示于外的理由则是对道德原则的注重。将“为己”作为目标,则行动的理由与行动的动机便呈现相互重合的形态:追求道德上的完善作为真实的理由,已化为其实际动机。显而易见,在前一情况下,遵循道德原则这一理由仅仅具有形式的意义,其作用主要是在逻辑的层面为行动提供某种解释;唯有在后一情况下,理由才通过化为动机而成为行动的内在原因。由此也可以看到,单纯地以解释为关注之点,往往无法把握行动的理由与行动的原因之间的真实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