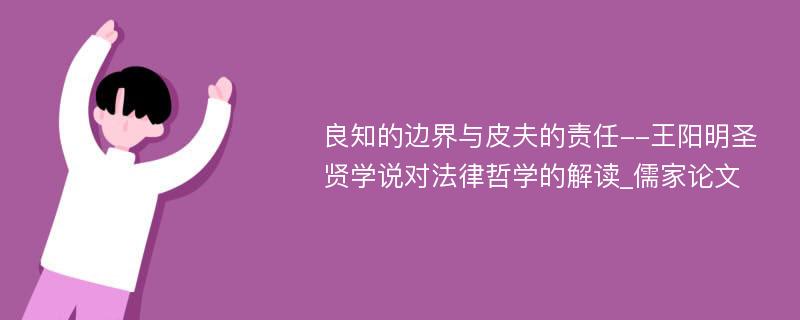
良知的界限与匹夫的责任——王阳明圣贤有分说的法哲学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匹夫论文,圣贤论文,良知论文,界限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6-0018-06
儒家之道,务求自得,而后又必致家国天下,其中仿佛自然地包涵着一种“政治哲学。”① 从历史上看,这种将“学”与“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哲学”,有其历史运会,正如王夫之所言,“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因而儒者之学,必至“为帝王师”,方才能有所成,否则便是政统绝而道统孤,天下陷于衰悲。② 如果说,“得君行道”是儒家在君主专制统治条件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儒家的“政治哲学”进行现代转化,才可能使儒者“君临天下”③ 的心态大有功于中国当代社会?本文拟通过对王阳明的“圣贤有分”说进行法哲学阐释,以期在中西“政治哲学”之异同的讨论中对上述问题有所回答。④
一、必为圣人与愚夫愚妇
阳明曰:“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⑤“本原”,亦被阳明称为“根”、“头脑”等,他在这里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良知学“是有根本的学问”,“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而为为学之“体”;⑥ 二是因为有根,则干、枝、叶、花、实等“自然”随之,天下之治是为学之“用”。⑦ 阳明认为,体用之间不容有隔,大中至正,“彻上彻下,只是一贯”。⑧如此说来,良知学的起点和终点都只能是为大人、做圣贤。就起点,阳明强调“立志”以明良知之“体”:“吾非徒望尔辈但取青紫荣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夸市井小儿。尔辈须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务在光前裕后,斯可矣”;⑨“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⑩“诸公在此,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11)“学本于立志,志立而学问之功已过半矣”。(12) 就终点,阳明强调“万物一体”,认为“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这个“用”,对于良知之“体”有着决定性的意义。(13)
这意味着良知学也即圣人之学,前者特显“体”而后者尤见“用”。(一)良知纯明本有,“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二)圣人具体呈现,必定会将其万物一体之念实际地“推”出去,实然地安全教养全天下之人。这样看来,“圣人”处更显“必有事焉”,而能对治“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14) 的病痛,避免了一个汪洋恣肆的虚境,让良知学不只是一种心体或性体的境界。
然而,良知学的命脉,却不在于圣人的全体大用。阳明在圣人的全体大用中发现了“有我之私”、“物欲之蔽”,而强调人之“圣贤有分”。这就触及到了人的有限性问题:首先,人的肉体性存在必然依赖于外部世界,缺乏与外部世界的物质性交流,人连最起码的吃穿住行都不可能实现。其次,生命强度常常是有限的,人“实有以亲之”的能力,其心智(才胆识力,知性能力甚至德性能力)水平,亦为存在之事,有其等级和分限。最后,人的吉凶祸福、死生寿夭、人“实有以亲之”所能达到的程度等,有一定的遭际,都不是人人所可强求而致者。对于此类“气拘物蔽”,阳明强调,“人品力量,自有阶级,不可躐等而能也”。(15)
问题随之而生:如果说人之才力等等皆异而不能齐一,其“实有以亲之”之用固将有别,则良知之体随之亦将别?如此,良知纯明本有如何理解?难道良知本身就已经意味着差别吗?这是阳明所不能承认的。对于阳明来说,良知本无差别,但其展示却有差别,“须随人分限所及”。(16) 这等于承认,人人可以为尧舜,而人人不即是尧舜。阳明同孟子一样认定“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最终还是把学问的重心放在了知、体、觉、念处。就此良知、心体、性体的普遍性和绝对性,阳明可以在承认圣贤有分的同时,认定“圣人亦是学知,众人亦是生知”,从而把圣人与匹夫等同起来,甚至反对区分二者。于是便有著名的功夫与效验、分两与成色之论:“圣贤只是为己之学,重功夫不重效验。”“若才下得些功,便说效验,何足为恃!”在阳明看来,“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今不自煅炼金之成色,只是问他人金之轻重,奈何!”(17)
这样,我们跟随阳明转了个圈子,又回到了起点:圣人达其万物一体之“用”因其不可强求而不再被突出,立其良知之“体”也就成为了决定性中心。成色、天理之纯而非分两、效验成了关节点。故而在阳明的话头中,自求、自得、自悟、自慊、自见、自觉、自好、自修、自痛、自吃等比比皆是。即此而言,尽管圣贤有分说强调圣人悲天悯人的救世热忱,承认圣贤与匹夫的现实的等级差序,但本质上却不能被界定为“圣贤道德”。毋宁说,圣贤有分说的突出特点,即在于其承认并尊重人的有限性,而把说教的主要目的,从“为帝王师”、“得君行道”等,转向社会大众特别是下层社会大众天理心体的普遍“自觉”。这种普遍的自觉是那无待者,是操之在我求则得之者,是异中之同者。阳明强调,“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18) 于是乎,圣贤有分说也就具有了浓重的“匹夫道德”的色彩,起到自我激励自我解放的作用,而可以反抗一切外在的是非、专制甚至等级、差异等。对此,王心斋有着深刻的体悟:“吾人之学,饰情抗节,矫诸外;先生之学,精深极微,得之心者也。”(19)
二、絜矩之道与隶属原则
现在的问题是,奉陆王一系心学为正统的现代新儒家,他们在履行自己由内圣(心体性体)开出新外王(科学与民主之用)的当代使命中,是如何利用王阳明圣贤有分说这一资源的?
不同于阳明的委婉曲折,现代新儒家以“斯道”的继往开来者自许,将重心又转向新外王,即民主政治、事功、科学等,而明确要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其中牟宗三的建构最为突出。在他看来,中国以前之所以只有“治权的民主”,而没有“政权的民主”,就是因为“君”首出庶物,把一切东西都隶属于自己,人们对它没有任何办法;要改变这种现状,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开出对列之局。所谓“对列之局”,也即《大学》所向往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絜矩之道”。“絜者合也,矩即指方形,絜矩之道即是要求合成一个方形,这样才能平天下。……若必欲比他人高,去征服而使他人隶属于我,即不能成‘絜矩’,天下亦不能平。”(20) 他强调说,“我不能只为自己打算,也得为别人设想,这就是絜矩之道。”“现在讲政治,一定要依从对列原则(Principie of Coordination)不能服从隶属原则(Principle of Sub-ordination)。讲隶属,那就是非现代化。”(21)
至此,现代新儒家所强调的“内圣”还是“匹夫道德”,甚至可以与康德意义上的“启蒙”相系,虽圣贤有分,但人人皆有其责而不能被代替,因而又人人平等。然而,一方面由于看到了西方文化近代以来平面化量化的种种弊病而欲避免之,(22) 另一方面由于遭遇当时儒学凋敝、自身“几乎不能自保”的惨状而欲拯救之,牟宗三旋即把达万物一体之用的任务交给了那些“见道”之人。在牟宗三看来,“今天这个时代,先不谈农、工、商,即使是读书人亦很少有尊重圣人之道的,亦很少有了解圣人之道的。”因而,“理性的原则”只能是圣贤首出,“以学术支配政治,以政治支配经济”。(23) 他说:
内圣外王之学,即所谓经世之学,必须领导时代,方能有其现实之用;而其领导时代,必须领导时代之人亦即沐浴于此学之中。学术为一笼罩之原则,这一客观之骨干,际会风云者,其智能及而仁能守,则一人唱之,百人和之,所谓内外上下契合无间,以此为共信之指导观念,皆向之而趋也。此学术之具客观性,而时代亦为构造时代也。……学术与政事脱节,此学术之悲,亦政事之悲也。(24)
如此,圣凡两途,达良知万物一体之全体大用也就成了一二“智能及而仁能守”的见道者的事业,而圣贤有分,百姓唯能希求为流风所披。这里的问题是:(一)儒者首出庶物,絜矩之道不成;其(二)判断谁曾见道,并无客观标准,而唯由其人本身的证悟为据。这样一来,那些见道者在将自己的万物一体之念推出去的时候,就更加有恃无恐了。(25) 人们若指责他疯狂、独裁、败坏知识和道德、(26) 咒术、阿Q(27) 等,他正可以用王阳明下面的一段话回应之:
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见其若是,遂相与非笑而诋斥之,以为是病狂丧心之人耳。呜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体,而瑕计人之非笑乎!(28)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阳明那里作为否定性(否定自我局限)的东西,被转化成儒家见道者的肯定性行为。由此肯定,儒者提倡民主与科学,但同时又把民主科学等限定为凡俗之事,自己则高高在上,与物无对,故而自我坎陷可,杀人以自救亦可。熊十力尝言:
如菩萨行荒远之域,绝无可得食,仅同伴一人,杀之以食则生,否则死,此将如何?佛言菩萨为续慧命故、续法命故,宁杀人食之。出此险已,力度众生。(29)
我们不能将熊十力的这段话理解为现代新儒家的一时失语或特定情境下的特定表达。其一,在熊十力看来,这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圣人为王而在,万民才能咸和,因而一人之身可以换来慧命法命得续,亦可谓死得其所。其二,我们说,民主与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在根底上现代新儒家特别是牟宗三则根本看不起这种生活方式,而认为这种存在仅仅是虚荡的匹夫之勇、气魄承当,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存在。(30) 其三、这种经过儒释道、中西层层判教而来的“狂”,与阳明万物一体说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更反映出现代新儒家在特定时代中面对“吾道不行”的现实时的焦虑,因而比阳明更过之。其四、不同于阳明之放弃“为帝王师”而将对象转向社会大众,现代新儒家最终在隶属原则下将目光紧紧锁定在某些承当法命慧命的见道者身上,让见道者在“与道合一”的体验中达于了云门禅师三句教之“随波逐浪”的境界,从此可以得君行道、挥洒自如了。
三、道德与法律
随波逐浪的“圣贤道德”让那些以菩萨自任的见道者天马行空,可以完全超越世俗生活而不用理会什么现代民主法制体系等。然而,对于“圣贤有分”的现代诠释而言,这应该并不是定论。实际上,将阳明的圣贤有分说理解为“匹夫道德”,并不会限制儒家的常道性格,反更有可能创造一种心向圣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即是平面化量化的民主与科学,也可以有纵贯的道德和理想,二者并不相违。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中西方的对撞,已经让阳明的圣贤有分成为了整个地球上所有人的事业。我们由以上熊十力“宁杀人以食之”的故事来展开讨论。
熊先生的故事可以作为一个隐喻,来标明人生存中的困境。这种困境不唯中国人遇到,西方人亦有之,如“卡尼德斯之板”的困境。问题是这样的:一块不属于任何人的木板,只能承载两个遇到海难者中之一人,第一个幸运的占有者被另一人暴力地挤掉,问后者有责任吗?
先来看康德的回答。康德认为,“这不是一个纯属温和劝告的问题,即既不属于作为善德学说的伦理学的问题,也不属于作为权利学说的法理学问题,这是允许使用暴力去对一个没有对我使用任何暴力的人的问题。”(31) 在他看来,这属于紧急避难权,“在紧急状态下没有法律”。(32) 我们看到,在“你死我活”这一点上,康德与熊十力是一致的。但亦仅此而已,二人之间实际上是所同难胜所异:(一)康德将之归属于紧急避难权,这种权利(Recht,法、权利、正义等)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并非菩萨有而凡夫无;(二)在康德看来,免于死亡所凭资的,并不是法命慧命,而仅仅是暴力;(三)除了要避免自己的死亡外,这里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更谈不上崇高的目的;(四)康德还认为,这种因自我保存而来的暴力侵犯行为,是错误的事情,虽然能够免于惩罚,但却应该受到谴责,人们不能由于紧急避难就把它合法化;(五)康德要求划界,在承认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的同时,追求一种确定性。
所谓的划界,就是在承认人的存在是一个整体的前提下,要求以不同的侧面来理解和处理这一整体。这是康德的整体思路,具体到这里,便是划定法律和道德的界限。在康德看来,“权利科学的目的在于决定每一个人,取得像数学那样准确的他自己的一份;然而,在善德的伦理学中,却不能企望做到这样。”(33) 也即是说,法律是确定的,它要求“守本分”,(34) 那种不确定的东西如紧急避难权应该单独被处理,以免对权利的正确学说的确定原则带来混乱的影响;而道德却有着本质的不确定性,我们仅仅确定地知道,完成一种道德行为要比法律的要求做得更多,否则就是道德上的缺点或者过错,至于多多少,则取决于行为者必须克服的障碍的大小,不能事先确定。
同样,黑格尔也在玩“跷跷板”(35) 的游戏。他主张法的客观性,但同时看到了这种确定性的有限性和偶然性,“要求人们不要全面成为法的牺牲品”。(36) 在黑格尔看来,法的客观性要求道德的主观性的加入,唯有二者的结合,人的存在才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尊重。有意味的是,黑格尔正是从紧急避难权开始来谈这种结合的:“自然意志的各种利益的特殊性,综合为单一的整体时,就是人格的定在,即生命。当生命遇到极度危险而与他人的合法所有权发生冲突时,它得主张紧急避难权……一人遭到生命危险而不许其自谋所以保护之道,那就等于把他置于法之外”。(37)
由于有了这种结合和过渡,黑格尔的“客观精神”也就表现为三个阶段,即,法的阶段“冷酷无情的人格”必须被道德阶段“作为独立自主的人来互相对待”所取代,直至最终进入国家阶段即“个体独立性和普遍实体性在其中完成巨大统一的那种伦理和精神”。(38) 如果说,国家阶段可以对应于阳明的万物一体的话,那么黑格尔同样能够承认道德上的圣贤有分。唯一不同的是,这种圣贤有分以冷酷无情平等齐一的法律为基础。黑格尔也看到,“给自己保留肆意妄为的那种感情,把法的东西归结为主观信念的那种良心,的确有理由把这种规律看作它的最大敌人”,(39) 但他还是坚持认为,唯因此,才能正确理解和处理“存在和应然之间的争执”,否则便“对偶然意见主张思想应凌驾于法之上大开方便之门”。(40) 在黑格尔眼里,考察这种亘古不变的法与自己良心的法的争执,是思维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否则“良心如果仅仅是形式的主观性,那简直就是处于转向作恶的待发点上的东西,道德和恶两者都在独立存在以及独自知道和决定的自我确信中有其共同根源”。(41)
实际上黑格尔的忧虑熊先生的弟子徐复观也曾感受到了。他一方面强调说,“把问题摆在时间的平面上看,良心似乎无凭而更无力。但把问题拉长在历史之流中去看,则良心是可凭而又是有力的”,但另一方面又看到由于中国人没有“取得像数学那样准确的他自己的一份”,“结果圣人的大公,实所以成就野心家的野心,则圣人依然是白费”。徐复观感叹道,“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政道之穷”,“这是东方人的良心呈现所受的最大的限制”,“这是我们最大的污点”。(42)
由此可知,西方人的存在中并非没有纵贯的道德和理想。康德和黑格尔的万物一体说,与现代新儒家特别是牟宗三一系的万物一体说所差别的,只是对于“分”的理解。
四、政教合一与政教分离
阳明之“分”是圣贤有分观念下的一个自我体验性的概念。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当阳明侧重“体”时,他强调知、体、觉、念等这些良知之“有我”;当他侧重“用”时,他突出的却是无染无着的良知之“无我”;而有(大我)无(小我)之间的明暗转化,却并不足以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它已经为心体性体的本体论(心体之同然)所承诺了。因而,阳明自我体验性的“分”远远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它既没有知识化的要求,实际上也不可能被客观确定地规定。这就有可能带来一种灾难性的后果,把阳明的全部心血付诸东流:现实的等级之“分”可以极为便利地利用人的有限性之“分”来为自己的合理性做出辩护,外在的是非、等级甚或专制等可以十分容易地打扮成圣贤之“分”的模样,把良知之“分”变为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于是,那个从阳明的委婉曲折开始便一直隐隐困扰着我们的问题,现在必须直接面对了:阳明为何如此致思?
从历史上看,明清两代是中国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双峰时代,最先、最直接受到专制和集权摧残的,便是士人,因而阳明从不直接涉及政治理论、以社会大众而非朝堂精英为其说教对象、以避开政治的曲折方式来抗拒政治等一系列做法,只能是一种特定历史时期下的无奈。(43) 这其中的逻辑,韦伯分析得比较透彻。他指出,中国古代士人的思与行有一个绝对不可能被跨越过的既定前提,即那个政教合一的家长制的(patrimonial)国家。在这种国家形式中,无论是“财”(土地、俸禄等)还是“仁”(管理、立法等),都具有家长制的性质,都为君侯所掌握、服务于君侯(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家长制的坚硬和一统,与君侯的神圣不可动摇而又绝对自由专横,结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自足系统,不断地在强化着自身。这又造成了以下三种情况的出现以及它们之间的恶性循环:其一,任何客观化知识化的明确规定,都会因有影响到君侯自由的可能性(民知有刑辟,则不忌于上)而被清除出体系之外,“不仅形式的法学未能发展,而且它从未试图建立一套系统的、实在的、彻底理性性的法律。总的看来,司法保持着神权政治的福利司法所特有的那种性质。就这样,不仅哲学和神学的‘逻辑学’,而且法学的‘逻辑学’,都无法发展起来”;(44) 其二,人们只能在为家长制的君侯的服务(功绩和皇恩)中讨生活,上下级之间的等级关系决定着一切,财产关系只不过是等级制度的一种表现(“按照法律,属下的所有财产是属于上司的”(45),私有制在中国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46) 其三,面对生计问题,士人“精神的自由活动也就停止了”,(47) 代之而来的是竞相游走争宠于君侯之门,“不诚实”的作风被培养起来。(48)
如果说,“哲学是对意识形态的意识”,“哲学旨在达到批判意识形态的自觉意识,而这一批判的出发点则是历史唯物主义”,(49) 那么这里的论述显然与马克思是相通的。但我们不能据此便认为,阳明完全缺乏这种自觉意识,因为对阳明而言,“不诚实”是“从躯壳起念”(50) 的结果,而躯壳恰恰又首先意味着生计。阳明不可能超出他的时代,不可能要求消除等级制度家长制国家,但却不能无视问题的存在,因而最终只好求助于心体、性体一体平铺、审美元分别式的自得、自慊等,以期在社会上培养出一些根苗。这种工作有其无奈软弱之处,(51) 但亦有其坚韧的一面,或许亦可以被看成是启蒙之一种、生生不息之一种。然而,人们可以容忍阳明对等级制度家长制国家的束手无策,却并不能够接受现代新儒家特别是牟宗三一系对阳明之“分”的现代阐释。这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在有意无意地拒斥着历史唯物主义甚或韦伯的视域,另一方面又在着意强化着见道者君临天下的一尊和任性,其道路与其所经受的现代性洗礼以及开出民主和科学的自任,是极端背离的。因而,今天那种既不尊重客观的法律之“分”,又要强调道德的等级秩序是实现人类生活中的民主与科学的直接通途(所谓良知坎陷)的思想,无论如何是令人难以置信和不能接受的。
是故我们说,正是现代新儒家的“圣贤道德”、政教合一的家长制国家,而非王阳明的“匹夫道德”,才理应受到最严厉的谴责。王阳明圣贤有分说的现代价值,并不在于它能产生出某些高出一切、领导一切的见道者,然后再由这种见道者“随波逐浪”的道德显现,把我们引领着走向民主、科学之路;它的价值,只在于守先待后、私奉以为潜修之准绳,以期后起者普遍的自觉行动。今天的儒家哲学如果还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还能够融入生活,恐怕只能缘于此。这同时意味着今天的人们要继承儒家哲学、宏扬传统文化,还需要做很多事情,如必须划定界限,至少划定道德与法律、经济的界限,把道德的交给道德,法律的交给法律,经济的交给经济,在对道德的限制中完成道德自身。
注释:
① 这种见解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识。例如陈寅恪强调说:“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参阅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51页;余英时也指出:“从历史观点看,儒学的具体成就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出版社,2004年,第132页。
②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96年,第429、156页。
③ 按照余英时的看法,现代新儒家均要求当下中国社会实现科学与民主,但却常常籍良知的傲慢而君临天下,将自己置于整个社会体系之外/上,因而有口宣民主而实行独裁之弊。参阅氏著:《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书店,2005年,第544页。
④ 笔者已有专文《“他人食饱,公无馁乎?”——在“万物一体”与“圣贤有分”之间》(载《人文杂志》2009年第6期)讨论万物一体说的性质,认为其与当前流行的政治哲学有很大距离,实质上是一种事关修道的审美直感论。本文沿之进一步深化讨论,与之构成一个问题的上下篇。
⑤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4页。
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9-101、50、18、987、974、123、983、969、118、86、96、95、110、123、3l、1177、107页。
(19)(28)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78、80页。
(20)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新版序。
(21) 牟宗三:《时代与感受》,台湾鹅湖出版社,1984年,第112-6页。
(22)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第4页;《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4、92页。
(23) 牟宗三:《中国文化的省察》,台湾联合报社,1996年,第21页。
(24) 牟宗三:《历史哲学》,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344页。
(25) 韦伯曾指出,虽然巫术性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等观念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对付皇帝的唯一办法,但人们也应该看到,它自身同样存在着变异而为皇帝、或者把替皇帝服务作为自己唯一职责的那种可能性。参阅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0页。
(26) 陈迎年:《感应与心物——牟宗三哲学批判》,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543页。
(27) 林安悟:《解开“道的错置”——兼及于“良知的自我坎陷”说的一些思考》,《孔子研究》1999年第1期。
(29) 熊十力:《十力语要初续》,上海书店,2007年,第35页。
(30) 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360页;《道德的理想主义》,第4页。释道式的存在亦可被归属于此。
(31)(32)(33)(34) 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6、47、44、32页。
(35)(36)(37)(38)(39)(40)(41)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65、130、129、130、43、143、序言第7页。
(42) 参阅徐复观:《中国的世界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13、105页。
(43) 参阅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三联出版社,2004年,第140-145页。
(44)(45)(47) 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4、122、95页。
(46) 谢遐龄亦曾指出:“‘分’是土地公有制(或公有原则占主导地位)情况下才有意义的概念。分是群(公有原则的社会——或社团)中的位置,表现为对一块份地的使用。”谢遐龄:《释“分”》,《复旦学报》1990年第3期。
(48) 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4-186页。李泽厚也强调,“由于他们没能获得近代社会因职业分化和经济自由所带来的人格性,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只能拥挤在‘学而优则仕’这条中国式政教合一的社会出路上,必需依附于皇权-官僚系统的政权结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83页。
(49)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3页。
(50)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9页。
(51) 参阅张蓬:《中国传统哲学的政治依附性与“中国哲学”的特质》,《学术研究》2009年第6期。
标签:儒家论文; 牟宗三论文; 王阳明全集论文; 王阳明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儒教与道教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法律论文; 康德论文; 心学论文; 国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