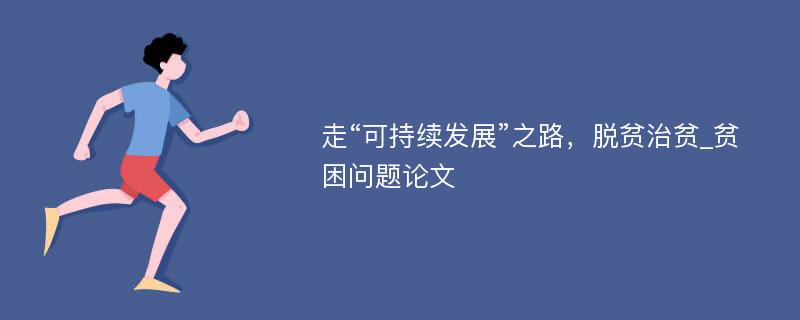
走“可持续发展”的脱贫治贫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反贫困年”,这表明了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和消除贫困的心愿。早在197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首次世界环境大会上,就有学者大声疾呼“贫困是最糟的一种污染形式”。〔(1)〕一些有识之士当时就提出了“持续发展”、“合乎环境要求的发展”等观点。遗憾的是,斯德哥尔摩大会后,这些“呼吁”和“观点”并没有或者很少唤起公众的觉醒,更难得落实在人们的实际行动中。结果是一方面,世界绝对贫困人口总数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全球环境质量则在每况日下。由此酿成了困扰当今世界的所谓“三P”问题,即Population(人口)、Poverty(贫困)、Pollution(污染)。
进入90年代,接连召开的几个国际性大会极大地推进了世人对上述问题的积极关注和广泛认同。首先是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第二次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此次大会针对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人口、贫困和污染三大问题,更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新观念,其要意可理解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发展”。再就是1994年在埃及开罗召开的第三届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大会主题就是“人口、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的发展”。大会认为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持续的经济增长是根除贫困的关键所在。〔(2)〕由此看来,“可持续发展”作为当代社会面向未来所应持有的一种负责态度和明智选择正日渐深入人心,并开始体现在各国政府的治国方略中,这对我国解决长期存在的贫困问题亦很有宏观指导意义。
众所周知,我国民族后进地区的贫困已长期困扰着社会各界。多年来,尽管国家在人、财、物诸方面给予了大量的投入,但收效却终未能尽如人意。时至今日,全国大部分贫困落后地区依然主要分布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区。以统计资料为证,〔(3)〕截止1993年,全国未解决温饱问题的总人口为8000余万,少数民族地区占近4000万。更为令人忧虑的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加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许多边疆民族地区与全国的贫富差距正在呈拉大之势,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思考。
自1994年起,国家为在本世纪内消除贫困问题,解决现今我国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即在全国推出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该计划与过去的扶贫战略相比较,有这样几个显著变化:一是扶贫力度加大,即积极采取行动,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从经费投入和人员配备上都给予大力支持;二是扶贫目标突出,从过去的先易后难转变为现在的深入千家万户,着力抓重中之重、难中之难;三是扶贫方式转变,即从过去单纯给钱给粮的“救济式”扶贫逐步向带项目技术的“开发式”扶贫过渡。扶贫攻坚计划实施时间虽不长,却颇见成效。以云南省为例:其与国家同期配套推出的云南“七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当年就初战告捷,据资料显示:仅在1994年当年内,云南全省就有近90万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全省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去年增加30元,达348元;粮食总产量比去年增加7%,达600469万公斤。这种扶贫成效的确令人欢欣鼓舞,无疑应该肯定。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痛心地看到,一些农业发展水平都还十分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为了脱贫,争相发展乡镇企业、村办企业甚至户办企业,于是乎,有矿的挖矿,来个“遍地开花”;栽烟种茶的户户建烤房,弄得到处冒烟。显然,这些做法都缺乏“持续性”,到头来难免要落入“没有致富的脱贫”或“没有发展的发展”这样一种有违初衷、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如果说:“发展不得降低环境质量,亦不得以降低长远的生产力为代价”,那么,脱贫治贫工作又何尝不该如此呢?
鉴上所述,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至少有三个问题值得商讨:一是脱贫要不要稳定?即脱贫速度与脱贫质量的问题。常言道:“打江山易、保江山难”,脱贫工作亦同此理。何况扶贫攻坚本身就是一场硬战。二是扶贫能不能深入?即扶贫步骤上的巩固与发展问题,我们切不可满足于“解决温饱”这种浅层次的扶贫。其实,仅为温饱而扶贫的做法本身就无助于致富。三是治贫讲不讲策略?即在脱贫进程中的治标与治本的问题。从长远来说,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看物(缺衣少粮)、不看人(精神风貌)的治贫举措是不可取的。据此,我认为在扶贫治穷问题上也需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并希望各地在拟定、实施及评价扶贫攻坚计划的时候,不要单纯地考虑怎样尽快脱贫,而应同时琢磨怎样更有效的脱贫。因为解决温饱在具体实施上并不难做到,难的是解决温饱的方式和认识。为此,在脱贫治贫进程中,我们不仅要看贫困地区各种经济指标的增减变化情况,而且同时要看贫困者自身的心理或观念变化情况,要看扶贫是否能够既解决贫困者的温饱问题,又能够激发贫困者的生存斗志,促其发展。
反思以往扶贫治穷的艰辛历程,不难发现,从客观原因上讲,民族后进地区起点低,基础差,束缚多(民族地区各种禁忌和陈规陋习盛行),致使治贫难度较大,扶贫收效慢。但从主观原因分析,则不能不承认,这其中也有对扶贫治穷工作方略或思路的理解与认识问题,那种仅为脱贫而脱贫,只管扶贫、不懂扶持,以及只把脱贫者视作“照顾对象”,无视他们所应具有的“发展主体”身份的认识仍然十分普遍。有鉴于此,笔者认为,辨明以下一些认识,对我们正在深入开展的扶贫攻坚工作是会有所启示或帮助的。
一、关于“脱贫”与“致富”。时下人们常把“脱贫致富”视作一个特定概念笼统而论。事实上,脱贫与致富并非一回事,不可混淆。从理论上讲,脱贫是致富的前奏,脱贫能为致富创造条件,但脱贫不等于、也未必能够致富。这是因为两者的目的不同,脱贫的直接目的在于解决温饱,而致富的目的则在于谋求富足。只有实现富足才可能远离温饱、告别贫困、步入小康。所以,我认为致富是实现稳定脱贫的保障,那种仅为温饱而脱贫的举措,到头来仍然摆脱不了返贫的阴影。从笔者近年来所做的实地考察来看,发现以往民族后进地区的扶贫工作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局限于温饱。此虽必要,但由于只着眼于温饱,而未能放眼于致富,这就降低了扶贫工作的质量,亦难以获得脱贫效果的持续性。
二、关于“扶贫”与“扶持”。乍眼看来,这两个词仅一字之差,含义上似乎也无大的区别,但细做划分确有其现实意义。我理解,扶贫意在拯救贫困,而扶持则在于辅助发展,虽说两者都非贫困者的自身所能独立为之,而必须依靠外力的作用才能实现,但前者只能有限地利用外力,被扶贫者也只是在被动地接受。我们在一些民族地区调查中就发现,扶贫工作在这些民族地区大多体现为钱粮救济,即便现在开始注重项目输入,也很难得辅之以思想或观念输入。后者则不然,它可以把外力内化,在扶贫中通过逐渐地启发、诱导和激励被扶贫者的主动性和参与感,进而化外力为内力,变被动为主动。“开发性扶贫”就是一种实在的扶持方略,只是这种“开发”不要仅限于对物(资源)的开发,还应同是注意对人(思想)的造就。应提倡变“救济观”为“发展观”,把扶贫着眼点放在“扶持”意向上,寻求为谋求发展(而非仅仅为了生存)而脱贫的扶贫方略。
三、关于“对象”与“主体”。对象总是相对于他人而言的,处在被动的客体位置。而主体则体现自我,处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主动地位。两者所处的位置不同,表现形式及其产生效果都迥然不同。在脱贫致富进程中,对象与主体是两个完全相反的角色,作为脱贫“对象”,就只是接受扶贫和照顾的对象,属被动脱贫者;而作为脱贫“主体”,则旨在强调参与脱贫或主动脱贫,它出自脱贫者自我的内在要求和积极配合。因此,变“扶贫对象”为“扶持主体”,实际上就是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这种观念的更新定将会带来角色的转变。在这方面,无论是“脱贫者”还是“扶贫者”都应一起努力。
从脱贫者自身来讲,要培育这样的认识,即“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穷不思变、甚至以穷为乐”。〔(4)〕只有树立“穷则思变”的生存态度,在接受外在的各种扶持与照顾时,才不至于把自己当作照顾对象,视政府的救济为应该的或必然的。而只有把自己看成发展主体,才有助于革除“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和“穷不思变”、“安贫乐道”之类的生存态度。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一次民族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归根到底,脱贫致富还是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一点希望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要时刻牢记”。〔(5)〕
从扶贫实施者来讲,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在拟定和实施扶贫攻坚计划时,切莫把扶贫项目的终极目标定在温饱线上,只抓脱贫,不管致富。盲目上马一些急功近利、甚至寅吃卯粮的扶贫项目,恐怕只会造成扶贫工作疲软乏力和收效递减的结局。最好是将脱贫与致富、温饱与小康、生存与发展衔接起来,并始终坚持“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脱贫先脱盲”的脱贫治贫原则。
总之,人类文明所应谋求的只能是资源与环境的永续利用和人口社会的持续发展。据此,在“96国际反贫困年”到来之际,在我们为迎接新世纪而展开的这场扶贫攻坚战中,要想获得预期的成效,并使脱贫治穷工作富于“持续性”,则脱贫进程中的角色转换与观念更新乃势所必然。
注释:
〔1〕M.K.托尔巴著、朱跃强译《论持续发展——约束和机会》,中国环境出版社,1990年出版。
〔2〕载联合国出版物《P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on Population and Devellpment》。
〔3〕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
〔4〕罗淳、吕昭河《跨世纪民族贫困地区滞贫治贫研究》一文,载《民族研究》1995年第三期。
〔5〕载《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一书,民族出版社1994年7月版。
